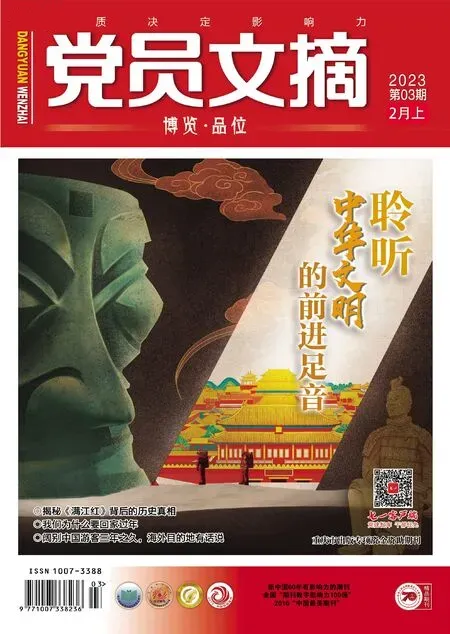我和父亲走过的路
2023-03-06葛亚夫
□ 葛亚夫
“条条道路通罗马。”刚听到这句话时,我并不知道罗马在哪里,甚至,还以为它是一匹马。就像父亲,在那几亩地里埋身耕耘,仰首遥望,偶尔吼两嗓子。
收了庄稼,为卖一个好价钱,父亲会把粮食拉到小城去卖。我对小城的认识,很肤浅,只想饕餮一顿,就打道回家。父亲也是,卖完粮食,就迫不及待地回去。上城父子兵,打记事起,我就是他忠实的马前卒。
那时,通往小城的路凸凹不平,空手走都行行重行行,更别说负重而行。车也是稀有的,出行全凭两条腿。天还未亮,父亲就拉着板车出发了。若是赶上节假日,他会在车把旁留一截绳子,让我在前面拉着。父亲有一肚子“墨水”,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不停地讲,几十里的膝行肘步,让人也不觉得远,反倒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
有一年,行至半路,逢上大雪,一车子蔬菜没有卖掉,我们又悉数拉回去。天地白茫茫一片,明明是白白胖胖、平平实实的路,一脚下去,不是深就是浅。深处有积水,弄湿了鞋;浅处太光滑,容易崴脚。背后还有一车子蔬菜,不时把我往后拽……父亲讲述的精彩故事再也捂不住我的眼,我对这种生活有了质疑和抱怨。
父亲却没有,一路闪挪腾移,像出神入化的杂技演员。手被寒风吹裂了,他就抓把泥土,糊在裂口;肚子饿了,就剥根大葱,就着一把雪,吃得津津有味;累了,就卷根烟,紧紧裤腰带,又生龙活虎起来。四十多里路,于他不过是一身臭汗;于我,却如天堑。也是那时起,我和父亲分道扬镳了。
我一心读书,从村里读到城里。父亲一心种地,供我到城里。时光里,我们并行不悖。我知道了罗马,知道父亲是马,但不是罗马。眼前,小城是我的罗马。
父亲乐颠颠地说,他也要农村包围城市。但,他的宏图大略里没有自己,只有我。他疲于城乡间奔波,只为我出人头地,成为城里人。那么难走的路,他走得如履平地,有滋有味。父亲既希望我守在身边,共享天伦;又希望我远走高飞,功成名就,这种纠结一直缠绕着他。
我进城读书时,父亲给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骑了两次后,我嫌累,改坐公交车。真像父亲说的,我读书读毁了!坦荡如砥的柏油路,二八大杠的新凤凰牌自行车,我都懒得骑。
我把自行车还给了父亲,他终于向现代化迈了一大步。只不过,这一步他迈了二十年,也被我落下两个二十年。有了自行车,父亲进城的速度和频率都快了。隔三差五,就借卖菜顺道去学校,给我送些生活品。那时,我对物质的消耗,步行已撵不上,就是骑车,他也超载而行。只是,我的梦想过于明亮,忽略了这些,以及父亲。直到高考时,我才蓦然发现他老了,有了皱纹,有了白发,有了疲倦。
高考正赶上午收。走出考场,我看见父亲——倚着自行车,呼呼大睡。口水沿着唇角,时光一般,无声流逝。十多亩地的农活,加上四十多里的路程,他还是觉得累了。
我到南方读大学,父亲本打算去送我,起初还算过行程,但最终放弃了。他和他的自行车,早已被时光透支,再也跟不上我了。“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于父亲,通向我的路,并不通向他。有一次,我和高中班主任通电话,他告诉我,有时还会看见我父亲,上学放学时在校门口转悠。我问父亲,他矢口否认。但他和那辆老凤凰牌自行车,任谁瞅一眼也不会认错!
我心里很明白,父亲想我了,但他嘴硬,不肯说。
毕业后,我留在了南方。父亲不再拼命挣钱了,身体却迅速垮下来。2016年,他遭遇一场车祸,老凤凰牌自行车报废了,腿也骨折了。我辞掉工作,回家照顾他。出院后,我给他买一辆电动车代步,他开心极了。
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但是,再好的路,也只是路,不能代人行走,不能替子女行孝。我没有离开太远,留在了小城。这是我距父亲最近的地方,也是他轻易就能抵达的地方。他骑着电瓶车,经常进城卖粮食或蔬菜,顺道去看看我。
辗转于工作、生活和各种琐事,我鲜少回家,就是偶尔回去一趟,也来去匆匆。这些年来,父亲终于习惯了我不在的生活,当我在他身边时,他竟不习惯了。父亲不想让我在路上,像他的马前卒。
父亲频频辗转于城乡,卖些蔬菜,听听戏,有时给我送蔬菜。我和妻子早出晚归,家里平日没人,他就一个人转悠,打扫卫生,把上次带来、如今坏掉的蔬菜带回家喂羊。我回到家,一开门就知道父亲来过,在哪转悠过——他怕弄脏地板,进屋就光着脚丫,但他那从未穿过袜子的双脚太黑了,走一步,盖一个印戳……
去年春节,我没回家。父亲骑着电动车,带母亲来城里了。吃过午饭,他们就要回家。我打开窗户,雪花扑进来。父亲依然满不在乎:这点雪算啥!不够挠痒的,当年那雪多大,我拉架子车都能走回去……
我没容他逞强,开车送他们。雪下得很大,车开得很慢,父亲睡得很香。口水从他的梦里溜出来,沿皱纹翻山越岭。母亲摇醒他:梦见啥了,恁香。他砸吧一下嘴:梦见和娃拉架子车上城卖菜呢!一颗没卖,又吭吭哧哧拉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