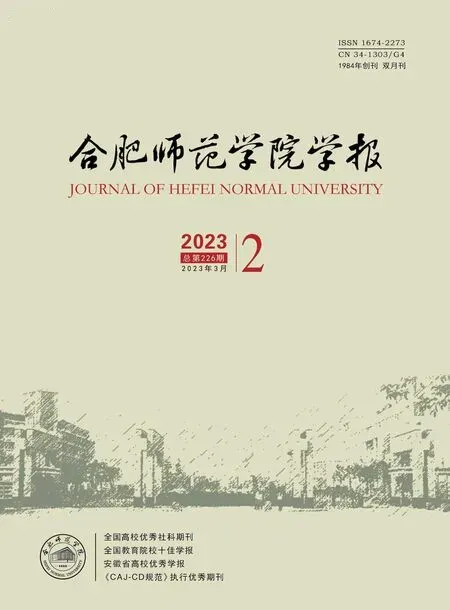论庄子语言观的悖论及其超越
2023-03-05赵诗华
赵诗华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庄子语言观不同于西方语言哲学的逻辑推演和意义分析,它源于主体“得道”及其由此而生发的对个体精神生命的超越追求。同时,庄子的语言思想也不同于以儒墨名家为代表的“循名责实”的语言观。他对语言所承载的名相持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认为语言(常言)所代表的名相及其附着的权力意识不仅是阻碍个体“体道、达道”的障碍,而且还是遮蔽个体本真生存的帷幕。因此,庄子为了破除语言的“魔障”,致力于以精神生命解放和诗意言说为旨归的“道言”——“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建构,以此追求诗意生存和本真生命理想的建构。
一、本真之道不可言:庄子语言悖论的哲学源头
道家之“道”作为不可认识的形而上存在,这是道家的一贯主张。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本文老子引文均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仅注篇名。(《老子·一章》)。就庄子而言,其明确表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本文庄子引文均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仅注篇名。(《庄子·知北游》)。可见,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形而上之道是语言所无法企及和把握的。在庄子看来,“道”本身的超越性本质决定了其对语言的基本态度,一是认为道是不可言的,二是将语言作为主体意识和观念的媒介,基于言说主体有限性,它往往陷入自我偏执,无法获得对道的体悟和认识。
(一)形上之道不可言
从道的本根性和形态来说,道不仅是万物的本源,而且是超越时空的,是人的感官所无法把握和穷尽的,这是道家的基本立场。
具体从道的本根性来看,庄子认为道不仅是自发和独立的,而且还是永恒的、是天地自然万物的根本。这在《大宗师》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庄子看来,道是“自本自根”、长久永恒的,同时又是“生天生地”的——“覆载万物者”(《天地》)、“万物之所由”(《渔夫》),因此,道是宇宙和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一种“大全”和“整一”。从形态上来看,道是“无为无形”(《大宗师》)、“未始有封”(《齐物论》),是“形形之不形乎”(《知北游》),可见,在庄子看来,道是超越时空的,不具有任何形态,且无声无形无象,是任何感官所无法把握的,这决定了道是超越语言的,是语言所无法把握的。《知北游》中借助“无始”之口,庄子明确表达了这层观念:“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在庄子看来,道是不可以听到的,也是不可以看见的,更是不可以表达的,一旦落入感官,所闻、所见、所言之道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了。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它是“大全”的“一”,是语言无法企及的:“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齐物论》)庄子这里所言之“一”即是道,是不可分的,言为“一”,二者不能等同,言说之“一”可无限增扩,产生无数个“一”,“巧历不能得”。这里认为言说的过程就是对道不断分化的过程,在庄子看来,这是无法穷尽道的,只是对道的破坏。
庄子在《齐物论》中就道的整全和语言的独断性进行了批判和揭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从中可以看出,庄子所言之道是整全不可分的,而言是变化无常、没有定准的,若强之以为言、以之辩,可将其分为“左右、伦义、分辩、竞争”等“八德”,而圣人却不以为然。在庄子看来,圣人对“六合之内”存而不论,而对“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就在于不以己意裁夺,以此维护大道的整全。与此相对,众人则以言辩之,越辩则不明。
庄子在这里不仅揭示了“言”之不可达道的缘由,而且揭示了“言辩”蕴涵理性的独断性和盲目性,这是有损整全之道的。因而,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说和命名的,即其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诚如斯言:“在庄子那里,道与言分属于形上形下两个世界,自然不可说,或者说‘言’根本不能触摸到‘道’本体。”[1]
(二)主观之言不达道
道之所以不可言说,不仅在于道的整全性和形上特性,在庄子看来,语言主体的差异性和时限性也是决定其不可达道的另一重要因素。
庄子对个体的差异性与时空有限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庄子在《秋水》中借北海若之口,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主体的历史性和时空差异性:“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蛙不可语大海,受制于空间的有限,夏虫不可语于冬天之冰,拘于时序的限定,以此类推,士人偏于教而不可言道。受制“时、空、教”,言说主体无法摆脱个体“成见”,由“成见”之心而言,其所言只能偏于一隅,无法达到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更不可能通达“道”。《齐物论》中对此有着深刻的揭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孰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这里,庄子揭示了“成见”之言的独断性,他认为以成心作为标准而取法,则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标准,是非标准的预设必然导致语言表达的不同。在其看来,言者之言都是有待的,有待之言无法把握无待之道的,而且现实往往是言者“所待者未定”。心中已有是非之论,这就是“言之华”,以此出发,则大道隐而不彰。在庄子看来,道之所以有真伪,主要还是由于成见之心和浮华之言的遮蔽。
同时,庄子还揭示了个体的差异性及其导致的沟通不可通约性。如其所云:“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庄子认为基于这种个体的差异性而生发的“言之辩”具有不可通约性,这样就会人人言殊,也不可能达到对“道”的理解和把握。在他看来,世间之所以产生无定准的争辩,关键在于“彼此”“我若”之间的差异性,及时引入第三方,都无法达成语言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庄子在此似乎夸大了表达主体差异的绝对性,究其实,其指向的是对语言表达主观性和固着性的警惕。
综上而言,庄子对语言的不信任和怀疑与其对“道”的定位紧密相关,在其看来:一方面,“道”是至高无上的,是无法通过人的感官所能理解的,更不可能通过语言去把握,即“道本就无法通过人的心知与言论来感知,只有通过体验才能参透其中的真谛”[2];另一方面,从人的主观性来说,基于个体所处时空的有限性和立场的殊异性,人是无法穷尽大全的“道”,这是庄子对语言怀疑的症结所在。
二、语言的“牢笼”:庄子对语言怀疑的现实指向
庄子对语言的怀疑除了源于道的形而上之不可言说性以及言说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外,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庄子认为语言本身及其所构筑的“名相”对人的精神生命具有强烈的束缚和宰制作用,这恰是其批判语言的直接动因。
就“名”与“言”而言,由语言所构筑起来的“名”实际上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究其实,语言问题不仅涉及沟通和表达,而且根本上它所构筑的“名相”里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规训功能,换言之,“语言的体制和政治的体制是互为表里的。道家对语言的质疑,对语言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考虑,完全是出自这种人性危机的警觉”[3]。因此,庄子对语言的批判和警觉蕴涵着对人性虚伪和名相强制宰割的洞察。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儒、墨和名家为代表的语言思想批判中。
(一)庄子对儒家由语言构筑之“名”的批判
庄子在老子“知者不言”(《老子·五十六章》)和“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的基础上继承了老子“无言之教”的深旨,提出了“无名”和“不言”,直指儒家的正名。
在庄子看来,“名”当以“实”为主,如其所言“名者实之宾也”(《逍遥游》),但现实生活中,名不副实,欺世盗名之徒盛行,如其所言“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人间世》)。
然就儒家所言之“名”本身而言,无可厚非,孔子本身也极力反对花言巧语的虚伪之态,如其所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但需要主体发自内在的德性修养,以此成就仁义礼智之名,因此,他强调“言必行,行必果”。而庄子无疑洞察了“言”的虚伪性和“名”所潜存的宰制性,他以极端的口吻批判儒家之“言”及其构筑的“名”。庄子常以寓言的方式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为批判的靶子,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借盗跖之口对孔子进行辛辣的批判:“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之事,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盗跖》)借盗跖之口,庄子就孔子所宣扬的儒家之道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孔子所言、所教、所行全乃诈巧虚伪之事,徒有虚名,名不符实,不足为论,最为关键的是“非可以全真”——不能保全人自身的本真之性。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儒家由语言所构筑的仁义礼智信等及其所倡导的仁人君子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保持其“角色伦理”的统一性:“一个人如果想在自我层面做到真正的精进,仅仅扮演或履行一种‘角色’是不够的,他的心也必须参与到其对外部制约的遵守之中,或者说,参与到与其美德的践行中。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与他的外部行为不一致,那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就是空洞的,因为缺乏了个人的承诺。”[4]儒家由于缺乏内在情感与外在行为有效统一的机制,其由言语所建构起来的仁义礼智信等往往挂空,从而沦为虚伪的形式,甚至沦为人求名逐利的工具,造成“实者,名之宾也”的相反结果。在庄子看来,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形是现实社会的常态,这在《田子方》中他与鲁侯关于“鲁国多儒士”的对话里有着形象和辛辣的揭露,当鲁侯下达无儒家之道而穿儒服者一经查实将治罪的公告时,鲁国仅一人敢以儒服见之,而平时以“儒士”著称的假儒生顿然消失殆尽。
(二)庄子对以名家和墨家之言的批判
道家针对“名家”和“墨家(墨辩)”之“名辩”的批判关键之处在于指出“名墨”陷于名辩的形式主义窠臼。
庄子中对名家论述主要集中在公孙龙与惠施两者上,两者都注重名之辩,都离不开语言、离不开思辨。前者强调绝对性,后者强调相对性,一个侧重于名,一个侧重于实。在庄子看来,无论是“白马非马”还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都陷入了由语言所构筑的牢笼里,无外乎“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任为名”“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如荀子所言“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
针对名家所谓“形名”“正名”而言,庄子反对惠施违反常理的“辩说”,在著名的“濠梁之辨”中有着深刻的表现,故此,批评其“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而对于桓团、公孙龙等名家,庄子批评他们是“辩者之徒……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认为名家脱离现实陷入了语言辞令无限的循环辩解而不自得。
就墨家而言,庄子不仅揭示了墨家“以自苦为极”对肉体的摧残,还指斥了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天下》),就“辩者”无休止的言说,从齐物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辩无胜”的主张,“辩也者,有不辩也。……辩也者,有不见也。……大辩不称,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齐物论》),指斥“墨辩”沉湎于“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骈拇》),而非天下之“至正”。
总而言之,庄子对儒、墨和名家由“言”所建构的“名”持有极大的怀疑和批判,认为其中不仅潜存着名不符实的矛盾,而且由此建构的名相往往有违人的生存本真,造成人的宰制和戕害,“德荡乎名……名也者,相轧也”(《人间世》)。在庄子看来,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和名相传达的媒介,容易沦为形式化、宰制人心的工具,成为人性异化乃至精神自由的桎梏。
三、诗性之言:庄子对语言悖论的超越
对语言的质疑和批判,就庄子而言,主要在于他洞察到语言的有限性无法把握道,同时意识到语言所构筑的名相中附着话语权力和强烈意识形态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异化和戕害。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庄子弃绝了语言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庄子认为语言存在着“名言”和“道言”之分,而道言是对名言的克服,为主体解放提供了超越之路。
(一)“名言”与“道言”二分
而庄子对语言的怀疑及其局限性深化了老子从治世的角度对语言宰制性的警惕,同时也呈现了道言的悖论关系,如其在《齐物论》中所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也,且得无言乎?”此处的“一”即“道”,以“一”或“大”来称“道”是道家的常用形式,庄子连续运用了两个反问,实际上也是反映他“道言悖论”的矛盾心态。
事实上,庄子在洞察“道不可言”的基础上,从人的生存本真的角度区分了“言”的两种形态——“名言”(俗言)、“道言”(至言),前者是拘于名相的“俗言”,后者是达道的“道言”,即“当道不可言的时候指的是名言,而其论道之言则是道言”[5]。这在《天地》篇中有着明确的揭示:“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这里的“至言”就是他心目中的“道言”,“俗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名言”,因此,庄子并未完全否定语言在人的生存中的作用,这也是其时常将“道、言”并提的缘由:“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则阳》)。
“道不可言”之“言”是“名言”之言,是“小言”“俗言”,带有强烈的主观目的性和意识形态性。“大辩不言”之“言”即“道言”,超越了日常“名言”和“俗言”,也就是“无言之言”和“不言之言”的“道言”。而在庄子看来,“道言”就是“足”言,成玄英疏云:“足,圆遍也。不足,偏滞也。苟能忘言会理,故曰言未尝言,尽合玄道也。如执言不能契理,既乖虚通之道,故尽是滞碍之物也。”[6]这就是说,“言”能够做到忘言契理,不偏滞,就能通达“道”,否则,“不足”之言,终日“言”也只能拘于形物,无法通达“道”,即所谓“言无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
何为“道言”“足言”呢?从庄子自身的言说来看,就是《寓言》中所提到的“寓言、重言和卮言”。
(二)作为诗性之言的“寓言、重言和卮言”
庄子不是从语言作为媒介的工具论视角来理解语言的传达功能,更多的是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把握语言的。在庄子看来,若要实现个体精神生命的本真存在,就必须化解名相之言的拘束和规训,建构一种可以通达道境的语言——“道言”(本真之言),以此实现精神和生存的双重解放,而这种理想载体就是其精心建构的“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
“寓言”即“寓而言之”。庄子的寓言不是现在所言的文体概念,而是一种包含象征、隐喻等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如其所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探寻一种“道言”的言说方式。所谓的“外”是指与“己”相对的一切外在事物,不仅仅借他人之言,还借草木虫鱼鸟兽骷髅等自然万象入其所“言”,同时还包括其虚构的“知、无为谓、狂屈”等人物形象来达其言说。这种“藉外论之”的方式贵在突破“成心”和“成见”,以一种谬悠之说达到“即言即道”的诗性效果,从而实现对日常语言的超越:“正是借助‘寓言’这种无成心、非对象化的隐喻语言,庄子彻底超越了‘道不可言’的语言困境,实现了‘即言即道’的语言自由。”[7]156
“重言”乃“倚重止息之言”。历代对此有着不同的争论,主要有“借重之言”(林希逸、朱得之、王叔岷、张默生、陈鼓应等)、“庄重之言”(元代罗勉道和今人曹础基)、“重复之言”(王夫之、高亨、崔宜明)和“增益之言”(孙以楷)[7]156-161。“借重之言”主要是假托黄帝、老聃、孔子等先哲、时贤以及重要人物之名的言说;“庄重之言”是指严肃端庄的言说,这与庄子的言说精神“不可与庄语”相逆;“重复之言”是指重复所说之言,显然不符庄子精神;“增益之言”是指“道中人”所述之言,孙以楷将“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中“已”义训为“己”(自己)相关,即与“外”相对的“道言”,这显然与庄子所倡导的“道不可言”相悖。结合庄子对世俗“名相”的批判精神及其后学“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定位,“重言”乃“已言”。“已”,林希逸训为“止”,“已言”就是“止其争辩”之言,亦如钟泰先生认为“‘已言’止息争议之谓。亦惟其能止息争议,所以得谓重言也”[8]。简言之,“重言”即“倚重止息”之言,其旨趣在于化用先哲、时贤等来破除世俗之言,从而达到“依重止辩”的功效。
“卮言”乃“道象回环之言”。“卮”,作为古代的一种器物,最早由郭象提起。后来,成玄英进一步将“卮”视作为一种“酒器”,“卮言”引申为“无心之言”。今人张默生将其视为“漏斗”,将“卮言”解释为“无心、无成见”之言,与成玄英相似。叶舒宪先生从文化人类学的象征视角,结合原型“陶钧”的“回环运动结构”,将“卮言”视作“道言”,且认为“(卮言这种回环结构和思维)契合诗意与哲思,把艺术思维与抽象说理之间的隔膜消化融化,使《庄子》独超众类地获得形式即内容的有机特性”[9]。
“三言”实际上是通过不拘于俗的方式跳脱“常言”的窠臼,主要表现为“无我”“无事”“无心”这个“三无”的具体特征:“寓言”主要借助外物以论之,以此摆脱“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或“与己则应,不与己同则反”的成见;“重言”主要借助古人的虚构言说方式以申述自己的真意,因此,“重言”可以视为“寓言”的一种。“卮言”即“无心之言”,即顺从道性自然所发之言,随物婉转而不强求己意。
(三)“得道忘言”的诗意生存
“三言”的初始目的不仅是针对“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的现实,最为直接的目的在于超越“以形定名”的是非之辩和主观独断,直指道境:“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知北游》)“大得”即“得道”,得道即进入无是无非、无贵无贱以及忘我和“无言”的审美真境。这种得道而生发的审美真境就是庄子所追求的诗意生存境界。
庄子对这种超越的诗意生存理想真境的指示,主要是借助“寓言”“重言”“卮言”的言说方式加以传达的。无论是“无待”的精神逍遥之人,还是入道之后的“无言之美”之人,抑或至德之世的素朴之民,在庄子的笔下都体现为一种无言的唯美形象,表现出一种与世俗相对的淳朴和自由。在庄子看来,这些无言的仙风道骨般的唯美形象都是得道之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就是自得其乐而无言的诗意境界。比较典型的有《齐物论》中,庄子以寓言的形式所描写南郭子綦所言“吾丧我”之后所达到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知北游》中“三问而三不答”的“无为”所处的默言状态,《田子方》中借助重言所描述的“老聃沐浴”之后“蛰然似非人”的枯槁状态,等等。庄子将这种“得道忘言”之人的诗意生存境界推向极致的莫过于《大宗师》中“真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德充符》中“畸人”之内德充盈美好德性的描述。
总而言之,庄子对世俗之言难以冥切道境的怀疑和批判,以致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的吊诡方式指示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其最终旨归在于追求“庖丁解牛”与道泯合的诗意生存境界,指示的是一种处身乱世的生存策略,诚如赖锡三先生所言:“道家一则批判其分别有待的识心,再则批判其‘名以定形’的语言异化之戏论,且由此批判而开启一条治疗和回复之道。”(3)赖锡三,《庄子灵光的当代诠释》,2008年出版。故此,庄子超越语言的“逍遥”精神理想及其“忘言”的生存境界为历代知识分子营构了一种理想的精神图景。
四、结语
庄子运用超越日常语言的寓言、重言、卮言的诗意言说方式指示了一种审美生存境界,从形式上来看,它呈现了一种语言的悖论,但其深层含义在于揭示语言工具功能的弊端,特别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所附着的权力意识对本真人性的遮蔽和宰制。而庄子这种强烈的语言权力符号批判意识和追求诗性言说的语言策略为当下身处图像时代遭受图像符号失真的生存境遇提供了一条反思和自我疗救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