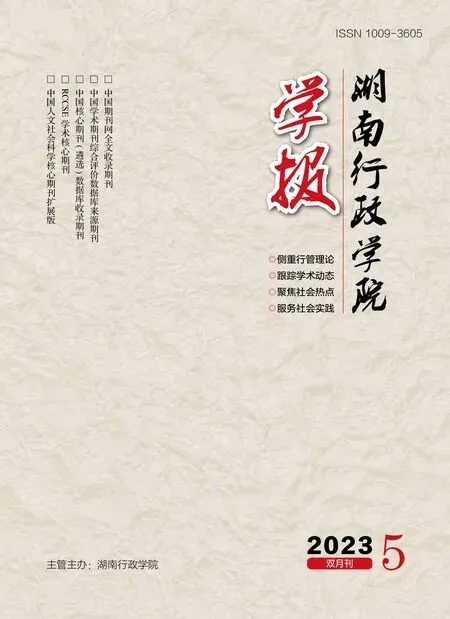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与政法意识探原
2023-03-05谢时研
谢时研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学界普遍认为,政法心理与政法意识属于政法文化的范畴,是隐性政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苏区政法文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界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进行阐释。学界大多认为,苏区政法文化是渊源于苏俄的一种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苏区政法文化强调政治对法律的统领,以及法律的工具主义性质,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实际上,伴随着秋收起义在湖南地区的爆发,毛泽东率先提出要抛弃国民党这面“黑旗”,打出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民主革命这面“红旗”,由此促成了中国政法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苏区的政法实践,彻底打破了农村地区几千年来的乡绅治理格局,摧毁了农村的礼法文化,而代之以政法文化。因此,湖南苏区政法文化作为一种实践理性非常浓厚的法律文化,它同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相比较,公开表明自身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然而,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与意识作为一种隐性政法文化,它是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与意识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农村地区的长期努力下,将农民的利益与革命的目标进行契合,在广泛的政法宣传教育和革命动员的基础上,逐步将工农群众吸收到革命队伍,并开展苏维埃革命政权和政法文化建设的结果。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政法意识层面出发,对湖南苏区传统社会与民众的政法心理之间、湖南苏区文化教育与民众政法意识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对于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和政法意识的影响。
二、湖南苏区传统社会与民众的政法心理
(一)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革命力量进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湖南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在湖南地区,国民党设立惩共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剿匪委员会等机构,疯狂对共产党员血腥屠杀。湖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各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据李行淮、廖瑞年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醴陵的活动概述》一文所述:1927 年6 月,国民党反动派彭承美到醴陵清乡。不到一个月,全县被杀害1000 多人,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到8 月止,全县仅剩下党员500 多人。[1]29
国民党还建立了“十家联防”的组织,在乡村实行“连坐法”控制群众自由行动。在敌人的恐怖政策之下,一些党员失去了斗争的勇气。据说,浏阳南乡有七八百党员,但特委派同志去接头,负责同志你推我拉不愿接头,并认为环境不好,暂应停止活动。[2]《蒋长卿关于湘东各县情形,平、修、铜、武各县情形,红军情形和个人工作经过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信》提到:“浏阳西乡的党的组织异常脆弱,大部分同志都是入过会党的,对党的观念不深切。农民也反动,在‘马日事变’之后,有打砸党部、打党员的事实。”[3]117
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悬赏通缉贺龙。桑植反动团防陈策勋打着“铲共剿贺”的旗号,纠合大批地主武装到贺龙的家乡洪家关等地残酷“清乡”,大肆捕杀群众和贺氏亲属。仅1927 年9 月份一个月,洪家关就有数十人被无辜杀害,霎时间桑植大地上为一片白色恐怖。[4]3据当时红军屈进成回忆:1928 年春,贺龙带着党的指示,从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说,“我最讨厌那些势利鬼,我刚到家时,一些势利鬼都来阿谀奉承,以为我当了什么大官,听我说到什么官也没有当,只参加共产党时,就悄悄地走了”。[4]66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民众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他们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大多不敢和共产党进行接触,担心受到牵连。但是,当时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也并非不可改变。湖南民众,一方面,他们是理性的,因为他们担心工农革命失败;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感性的、情绪化,因为大革命之后他们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容易受到革命情绪的激化,从而有可能参加到工农革命过程中来。尤其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民众敢于起来革命并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比如,《邓乾元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指出,此次暴动给予农民以下几个观念:“有革命委员会作他们的领导者”“有共产党作他们的朋友”“共产党是有力量的,他们有鬼神不测之机,他们一定会成功的”“农民现在完全变换他们从前软弱、萎缩的心理,现在他们不但不怕豪绅,并且实行重新打倒豪绅,乡村中最近发现豪绅请农民吃酒席调和之事很多”。[1]29醴陵暴动之后,农民受此次暴动影响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者甚多,暴动后半月内新加入党组织的同志就达六百以上。
然而,民众的态度也是与革命武装的力量紧密相关的。1929 年6 月13 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平、浏方面情形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平、浏经过长久的斗争,阶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农民群众之同情于我们,犹如豪绅之无不赞助地主统治阶级。不过农民对红军的依赖心非常之深,遇着敌人武装时,农民总是把敌人队伍瞒多报少,怂恿红军去打。”该报告还指出,面对白色恐怖,农民协会因压力太大而平时不敢表现他的力量,但一旦红军到达,便立马起来参加斗争。[3]132-134
同时也发现,随着湖南苏区的逐步扩大和巩固,湖南民众也恢复了革命信心,敢于同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斗争。正如中共攸县党史办组织撰写的《1930 年谭震林在攸县》一文指出,“谭震林率部进入攸县县城后,号召大家克服‘失败主义’情绪,重新振作精神,恢复党的组织,继续进行斗争”“他还针对一些人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敢同共产党接近的心理,召开群众大会,安定民心。会后,军部张贴了安民布告。乡亲们听说谭震林回来了,大家都纷纷回家。”[5]
1929 年7 月2 日,潘心源在《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自秋收暴动后,土豪劣绅看到共产党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没有卷土重来及“死灰复燃”之希望。因此他们当时采取最野蛮的复仇行动,到处捕杀工农,同时种种苛捐杂税更加多了。以前工农所得的利益不但没有了,而且佃东之对佃户,店主之对工人及店员,更加剥削得厉害。因此使工农对于土劣地主之压迫和剥削的凶恶更加认识清楚,他们倒因此而觉得“马日”以前的政权有恢复的必要。于是他们夺取敌人武装及建立自己武装的感想,便随时在他们心中旋转。[3]149-150
(二)土地革命与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
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党领导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为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由于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部队等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犯了单纯的“军事主义”错误,所以对于农民的动员不够。《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指出,安源军在到达醴陵之后,只是出了几张布告,宣布没收土地和恢复农民协会等事项,当时并没有将农民群众发动起来。[6]29《政治纪律决议案》指出,在实施暴动的区域内,根本就没有提出有关土地革命及革命政权的政纲,导致农民认为是共产党在捣乱,尤其是“在工农军所经过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6]41可见,当暴动还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就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
毫无疑问,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动员广大农民在农村地区同地主、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1927年12 月21 日,《中共中央给朱德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一)》指出,“便是这种无广大群众参加的武装力量,杀了很多豪绅官吏工贼,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资本家财主的财产,烧了借主的借契”,这也不过就是一种英雄侠义行为。如果不能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一旦统治阶级的军队打过来,到了不能抵抗的时候,群众中是无法藏身的,更不用说发动群众与反动势力作战。[6]45-471931 年7 月25 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兵运工作与农民土地问题决议》也指出,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与富农及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作坚决的斗争,完全平分土地,击破敌人的“围剿”。[7]92-93
中共通过土地革命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农村社会民众的广泛动员,农民通过参加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对于如何处理被打倒的地主、土豪劣绅,也是土地革命过程农民非常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共湘赣省委报告》指出,“过去红军地方武装为了捉土豪筹款,甚至捉了罪大恶极、群众要求要杀的反动首领也只是罚款释放,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意”“我们最近坚决转变筹款方法,捉了土豪反动派必须由政治部或当地苏维埃裁判部根据犯人罪恶及当地群众意见来判罪,群众痛恨的反动派,必须发动当地群众公开处决,提高群众的阶级仇恨和勇气”。[8]276-277
(三)中共在农村的深入与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
中国农村地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心理具有超稳定的结构,中共所主张的苏维埃文化如何融入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对农民的传统法律观念的改造,是非常艰难的一项工作。据杨建新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到萍乡桐木的一个山村里去,老百姓开始不理睬。我们看到他们把猪牛都关在屋里,尽是猪牛粪,又脏又臭,就帮助他们把猪牛粪挑出去,又帮助他们修建猪牛栏。他们看到我们不怕臭不怕累地为他们做事之后非常感动,很快就跟我们亲热起来了,以后打土豪也积极参加了。”[9]152
诚然,为了将农村地区民众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党必须在农村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政法主张。1927 年12 月6 日,《湘南暴动计划》提出:暴动开始后要“到一处深入一处,务必使民众完全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土地政纲。凡我军占领城市乡村即恢复农民协会及各革命团体。乡村由农协专政,城市组织革命委员会专政,务必全部实现我们的政纲”。[10]10
但是,改变农民群众的政法心理,将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由于党的领导不力,农村民众往往害怕同敌人进行斗争。《蒋长卿关于湘东各县情形,平、修、铜、武各县情形,红军情形和个人工作经过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信》对于浏阳的情况指出:“除了第一区之外,虽然有红军作了游击战争,杀了些豪绅反动派,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对于农民,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农协、工会或建立苏维埃政府,没有训练农民抵御敌人,没有鼓舞农民斗争的勇气,以致敌人时来骚扰(烧屋、杀人),农民因之而逃走。”[3]1191931 年3 月7 日,《中共湘鄂西特委关于红二军团与苏区失掉联系后的经过报告》指出:“党的领导力薄弱的地方,如潜江、沔阳的一部分群众,经不起敌人摧残的烧杀,大多数受其牢笼反水。我们认为在敌人的围攻中,其所以受着这样大的困难与挫折,当然在工作上有许多缺点,党的领导力微弱,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广大群众生死存亡的拥护,群众缺乏自卫的能力,使苏区不能铁一样的坚固。”[7]761933 年2 月9日,《中共湘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政治经济情形、党的组织、游击战争及其他工作等》指出:“群众的组织,虽组织过二千多人的群众,但是不能很好的领导和不能用各种方法更广泛的去组织广大群众,不去有系统的健全各级群众组织,提拔积极勇敢的分子来做干部,加紧他们的教育”“以致一塌台就全塌台,负责人完全变成群众的尾巴,与土豪妥协”。[10]61-62
尽管党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但是要改变民众的政法心理,实际效果并不很理想。1933 年2 月1 日,《湘赣省苏维埃党团报告》指出:“各县建立革命秩序与裁判部的工作,相当的建立了在群众中的信仰。过去因肃反工作错误吓走的群众,大多数不断地回来了,发动了群众到裁判部告状,民刑诉状都有解决。永新妇女被老公家娘残害的有十余人,苏维埃裁判部没有迅速处理这些案件,民刑诉讼解决得非常迟缓,法庭威权不能集中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没有提高起来。”[8]3191932 年8 月6 日,《中共湘南特委给两广省委的报告》指出:“党的影响是日益地扩大和加深了,许多群众来找我们去组织,除一部分反动的以外,其余的对我们最少都是中立的,有些想加入我们的组织,但又怕反革命的摧残。”[10]30
三、湖南苏区文化教育与民众的政法意识
(一)湖南苏区教育与民众的政法意识
毛泽东在井冈山苏区时期很早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1928 年5 月,毛泽东要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必须尽快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于具备条件的区、乡,要开办学校。湖南省委也意识到苏区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有关文件中作了规定,如湘委通过的《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明确提出要“设立夜班学校成人学校。”[6]406大体言之,尽管湖南苏区很早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塑造民众政法意识的教育主要还是在湖南边界苏区。
首先,湘鄂赣苏区就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并将教育作为苏区民众政法意识培养的重要方式。从当时来看,湘鄂赣苏区的学制有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和研究院三种。学校课本一般由县苏维埃文化部门编辑,交省苏维埃文化部审查出版,这些课本大多灌输了打地主和土豪劣绅方面的政法思想。湘鄂赣苏区的各类教育主要目的是宣传党的政策,破除封建迷信,扫除文盲,在学习过程中为工农群众灌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方面思想。据杨建新回忆:“记得那时把对待俘虏的政策作为政治课的重要内容。着重讲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及其根据,讲执行这一政策对瓦解敌军所起的作用,讲如何贯彻执行好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如何用阶级教育去启发俘虏的觉悟,改造俘虏,从而端正了大家对俘虏的态度”。[9]149-153由于湘鄂赣苏区办学条件极为困难,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三个月(四五六)工作计划》指出:“各级苏维埃尽量开办俱乐部,列宁初高小,劳妇职业学校,工农夜校……提高群众文化程度。”[11]131《少共湘鄂赣省邱策新在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教育工作是不够的,红色小学校识字运动、列宁俱乐部等工作没有在广泛的青年群众中去进行,红色小学校不健全,至于反迷信、反宗教、反旧社会教育、反国民党党化教育等斗争还是忽视了。”[12]
其次,湘赣苏区也非常重视教育工作管理,注重通过教育方式开启广大民众的政法意识。《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指出:“文化教育工作是没有做得好,列宁学校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教员没有经过审定,多半是豪绅地主富农的子弟,以致列宁学校发现许多AB 团改组派的组织。”[13]正因为如此,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草案》明确规定要“用阶级的文化教育做斗争的工具”,尽可能地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和开展阶级斗争,要通过“开展思想斗争,揭穿国民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教育来武装群众的头脑”。[8]605
最后,湘鄂西苏区也开展了广泛的教育工作。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教育决议案》明确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已成了苏维埃主要任务之一。根据上述规定,各县普遍设立了列宁小学,有些县还办了高级小学。当时湘鄂西苏区各类学校使用的教材,均由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负责组织编写。至1931 年3 月,华容、沔阳、江陵、石首等四县的列宁小学就有292 所,在校学生多达12000 人。[14]180-181湘鄂西苏区通过建立列宁书店、逸群书店、图书馆等,以及举办贫民夜校、识字组、通俗讲习所、读报组等方式,广泛向民众进行革命教育,鼓励他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二)湖南苏区文化宣传与民众的政法意识
毛泽东于1927 年12 月提出的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其中就包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井冈山苏区发动群众时,工农革命军就非常注意做好宣传工作,努力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帮助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为做好宣传工作,要求军队中的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都要派五个人做宣传工作。[15]《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关于苏维埃、共产主义、土地革命、红军、暴动队等方面,都要制定专门的宣传纲要,及时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尽可能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在湘鄂赣省苏维埃成立之时,《湘鄂赣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指出,苏区的文化工作要抓紧宣传国民党军阀的种种罪恶,增强广大群众的政治识别能力,强化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从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与国民党新军阀作坚决的斗争。[11]12-25
从宣传效果而言,标语是土地革命政法文化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湖南苏区的标语对于民众政法意识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井冈山苏区,工农红军每到一处,在墙壁上写满标语口号,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16]比如,酃县水口有一幅标语写着:“不分姓氏,只分贫富”。该标语是当年肃清地方主义、宗族主义和土客籍矛盾的真实记录。湘赣边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肃清了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的影响。1929 年7 月2 日,潘心源在《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经常宣传的口号是“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反苛捐杂税,反谷米涨价,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给农民”。[3]163在湘鄂川黔苏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湘鄂川黔的标语口号》提出:“我们不让周矮子、朱疤子、陈渠珍等国民党军阀再来剥削压迫,奸淫抢掠、屠杀工农群众,就应当用一切力量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捕杀敌人的侦探”“谁帮白军做探子,捉起来交群众,公审枪决!”[17]但是,湖南苏区早期的标语宣传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指出:“红军在成立初期宣传工作仍沿用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每每红军经过某村,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丝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土匪打。”[18]
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苏区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农武装割据初期,红军创办了一些油印、石印甚至铅印的报纸,如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等。[19]据统计,1933 年下半年时,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先后出版过《战斗报》《列宁青年》等10 多种报刊,湘赣革命根据地现存的革命报刊也有《湘赣列宁青年》等11 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有中央分局办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和《布尔什维克周刊》等20 余种报刊。[20]其中,1930 年7 月,在红军攻打长沙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由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责主编的《红军日报》,史称“红军第一报”。该刊注重于政法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在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红军日报》政法文化宣传的大部分文章都体现了对于工农群众的鼓动,以及对反革命分子实施镇压和肃清。针对反革命分子抢商店、烧民房、割电线、打黑枪的现象, 袁国平亲自为《红军日报》撰写社论,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巩固苏维埃政权,以专政手段镇压反革命。譬如,袁国平在《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一文提出:“我们必须学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对敌人不存丝毫的妥协和宽恕,加以彻底的肃清,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对苏维埃的危害。”[21]显然,我们可以发现,《红军日报》政法文化宣传对于鼓动工农群众支持红军攻打长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城区的守军,进而成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湖南苏区文艺与民众的政法意识
土地革命时期,湖南苏区文艺工作主要是为革命工作服务,并设立了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文艺工作的开展。1927 年9 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同时,还在士兵委员会内设立娱乐科。关于娱乐科的设置,《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也提到了红五军政治部宣传科之下设娱乐股、新剧股等机构,士兵委员会之下也曾设立娱乐科等。[6]561娱乐科(股)、新剧股等部门通过娱乐、新剧节目,寓教于乐,工农红军战士及工农群众在观看节目过程中受到启发,对苏区民众政法意识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笔者研究发现,在井冈山苏区,就曾经涌现出许多由根据地军民创作的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中,一部分是借旧的民歌、山歌、情歌的曲调,编上新的革命内容,劳苦大众唱着《诉苦情》《倒苦水》《雇农苦》《十杯酒》等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也有部分歌谣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军士兵进行策反,号召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杀土豪、斩劣绅,如《土地革命歌》《劳苦工农翻身》《暴动歌》等。正如湘委在《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指出:“以工农革命的事实和豪绅阶级的罪恶编成戏曲歌谣来表演,使群众对革命以响应而有兴趣地去求得认识。”[6]406
在湖南边界其他苏区,同样也广泛地开展了以革命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湘赣边界劳苦大众受革命歌谣的启发,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走出家门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意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劳苦群众才有出路。湘鄂西苏区各中心市镇设立的俱乐部,经常通过开晚会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介绍红军的先进事迹。湘鄂西省文委编的关于活捉张辉瓒的话剧,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苏区劳动人民中广泛流传的革命歌谣,歌颂共产党、红军、苏维埃,宣传妇女解放,讴歌革命胜利和表达劳动人民翻身的欢乐。[14]181湘鄂川黔苏区部队中唱歌、跳舞、演戏等文艺表演非常活跃,与政法相关的歌曲有《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纪律歌》等。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政法相关的民谣、民歌,如《拿起梭镖跟贺龙》《苏维埃干部好作风》等。据郭亮县政府副主席刘家乾口述:郭亮县成立了八个宣传队,经常在龙家寨、李家寨、碑立坪等地教唱红军歌曲和搭台演出各种小型文艺节目。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武装政权的时候,曾涤同志为我们教唱了《暴动歌》《要求解放必革命》这样两首歌,在那个时代,每当我们唱到这些革命歌曲的时候,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力量,打土豪、分田地,讲干就干,没有一点私心杂念。[22]上述这些文艺作品,主要描述了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反映苏维埃干部严于律己的作风。实践表明,湖南苏区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政法理念,无疑对当时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语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礼法文化”,已经固化为农民的生活方式,形成超稳定的心理定式。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并摧毁了农民协会,这导致了民众对共产党政权表示怀疑。当毛泽东等人将苏维埃文化移植到湖南地区,湖南民众最初内心自然充满怀疑、排斥,甚至是抵触。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影响的政治精英人物,他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思考传统农村社会。随着共产党在湖南农村地区深入开展政法文化宣传教育,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公开反对地主阶级,并带领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使得民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的,开始接纳这种外来文化。湖南苏区通过司法过程的大众化参与,将广大农民的目标和党的目标进行契合,成功找到了一条进入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网络,苏维埃政权及政法模式得到了工农群众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