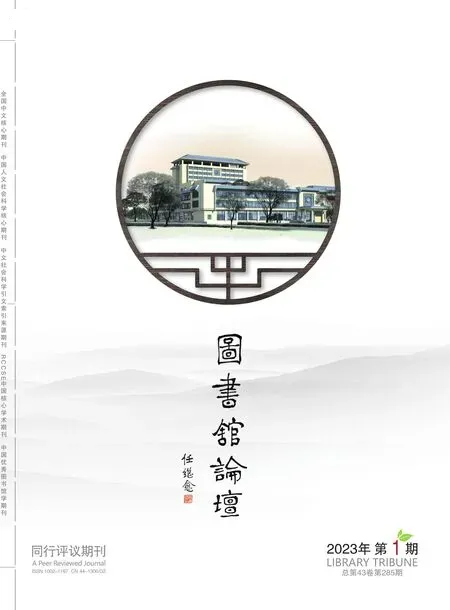广东藏书史料的整理、内容与价值*
2023-03-05蔡思明
蔡思明
0 导言
地方文献史料的专题汇编有助于保存历史文献,提炼地方人文精神。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粤港澳人文湾区[1]背景下,广东需要对历史人文进行深层次挖掘。《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开展岭南文化资源普查,加强对岭南文明源流、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等专题研究,提炼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3],强调对古籍文献开展系统、深度、集成性地整理出版。地方文献史料的专题汇编正是宣扬历史文化、系统开发古籍文献的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在区域藏书史研究视野下,选取“广东藏书史料”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广东藏书史料是关于广东历代书籍刊刻、聚散、流通等文化现象的直接记录,蕴含着古代学人开卷求知、为学上进、钩深索隐的书香精神和学术精神,是宣扬广东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亦是塑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宝贵素材。目前在诸多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中已涉及部分广东藏书史料,但未有该主题的专题汇编成果问世。2019年以来,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鹏副教授主持的“广东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对广东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进行搜集与汇编整理。本文即以课题组搜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结合中国藏书史研究的一般规律以及广东藏书史的历史特征,选择典型性范例进行分析。尽管本研究主旨是从广东这一有限的区域揭示本地藏书史料,但着力尝试从更为通用性的层面对史料的来源、内容及其价值展开探讨,以为其他区域乃至全国的藏书史料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 概念界定、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1.1 概念界定
首先对“藏书史料”概念进行界定。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材料,来源包括文字的(各种文献书籍及铭刻)、实物的(出土文物和考古遗迹)以及民间口传的[4]。本文所指“藏书史料”专指关于藏书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不包括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藏书史料分布在各种类型的文献中,其搜集无法穷尽,因而其范畴并无定论。
其次,本文史料搜集的重要途径是以“藏书家”为中心,因而必须明晰“藏书家”概念。古今学者就“藏书家”蕴含的人文内涵和理念进行过阐释。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5类[5];叶德辉(1864-1927)将其发展为著述家、校勘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6]。徐雁等认为藏书家是私家藏书的开创者或私家藏书的传人、皇家藏书的管理者于藏书事业作出贡献的人[7]7。范凤书认为藏书家需具备3个条件:一是“多书”,即有相当数量的超过一般人的收藏;二是收藏图书具备相当的质量;三是对藏书应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应用[8]。以上学者均围绕藏书目的和藏书兴趣而展开讨论,最大分歧在于“掠贩家”是否能被称为藏书家。从我国藏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出发,范凤书关于藏书家的定义与本文的研究范围较为契合,因而采纳范氏观点。
1.2 研究范围
关于时间范围,本文中文献史料的时间范围为1949年前,即文献产生于1949年前。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近代图书馆出现前以私人藏书为主体的藏书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图书馆史本应属于藏书史研究范畴,但考虑图书馆史关注的重点是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公共藏书事业,且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广州书刊文献中的图书馆史料进行过详细分析[9],因而笔者将文献时间节点划定在1949年,对私家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过渡时期的若干重要文献予以吸收,如杜定友《广东省立图书馆与广东文献》[10]44-47、徐信符《广东省立圕沿革》[10]35-43。
关于地域范围,本文中“广东”所代表的区域应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广东”在古代有过“越”“粤”“南越”“南粤”等称谓,而其所载的范围,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因本文搜集到的史料涉及明代、清代和民国3个时期,明代“广东”辖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10府及罗定直隶州,下辖8州、77县[11];清代“广东”基本沿明制,全省领9府、3直隶厅、7直隶州、1厅、4州、79县,另设同知管理澳门事务[12];民国时期“广东”所辖范围与清代大致相同,民国末辖85县、2市[13]。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调研法,调研思路包括:一是先通过各类型《藏书纪事诗》、地方史志等整理出1949年前广东藏书家以及藏书处所名录,继而以藏书家和藏书处所为关键词,以藏书家的著述为重点,析出其中的藏书史料;二是以历史上广东行政区划内各地域为中心,再结合关键词(如“藏书”“藏书楼”“藏书家”“图书”“书籍”“文献”“刻书”),对广东地方史志以及相关书刊文献进行广泛搜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下文涉及一些统计数据,但文章的重点在于讨论藏书史料的搜集及史料汇编的价值,且史料搜集工作无法穷尽,因而并不作量化统计。本研究所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已由“广东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初步汇编成册。受篇幅所限,文章未能将史料目次列出,仅选取典型性范例予以分析。
2 广东藏书史料的主要类型
基于以上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笔者整理出广东历史藏书家(截至1949年)203位以及广东藏书史料633种①。这些史料广泛分布于地方史志、历代诗文集、日记、尺牍、家谱、年谱、近代报刊等文献中。根据藏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以及实际搜索路径,藏书史料大致包括以藏书目录、藏书题跋、藏书记、藏书史论著等为核心的基础史料,藏书家相关的日记、尺牍、年谱、家谱等一手史料,以及其他载有藏书史实的诗文序跋、碑记铭文、传状记述等相关史料。以上仅从藏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大致划分,实际上各类别也存在部分交叉的情况。
2.1 基础史料
在我国历史藏书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记述藏书活动、总结藏书思想、反映藏书概况的文献,主要包括藏书目录、藏书题跋、藏书记、藏书史论著等。这类文献是藏书史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史料。
藏书目录是为反映特定藏书概况而编制的书目。藏书题跋“专指写于被收藏的典籍图书卷册前后(有时在书卷中间的隙处)的题识文字”[7]23。有的藏书目录带有题跋,同时也是藏书题跋,如民国东莞藏书家莫伯骥(1878-1958)所撰《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14],是其在藏书目录《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基础之上删补增订而成的。《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有着诸多关于藏书家交游往来、书籍流向、文献刊刻与流通的信息,于书籍之源流、版本之考证、内容之考释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颇值得学界关注。
藏书记是以“记”的形式,专门记载藏书家藏书经历或藏书楼藏书概况的文章,多由藏书家自撰或亲友撰写。如明代丘濬(1421-1495,琼州人)《藏书石室记》[15]4356-4357、清代吴荣光(1773-1843,南海人)《赐书楼藏书记》[16]、陈澧(1810-1882,番禺人)《传鉴堂记》[17]、民国伦明(1875-1944,东莞人)《续书楼藏书记》[18]等,均是藏书家自述其藏书经历的宝贵文字,从中可以体会到其所秉持的藏书理念与精神。
藏书史论著是指围绕某些藏书问题所展开的论述性或汇编性著述。如明代丘濬撰《图籍之储》[15]1449-1468,援引历代典籍中有关图籍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建立国家图籍收藏制度的建议;张萱(1558-1641,博罗人)撰《西园闻见录》,其中卷八“藏书”,收录张居正、高拱、张四维、吕调阳、张应元、李廷机等6人关于国家藏书建设的言论。清末民初时期,深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影响,广东藏书家莫伯骥撰《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19](文稿今未见存)、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20]、徐信符(1879-1948,番禺人)撰《广东藏书纪事诗》[21],延续叶氏纪事诗体风格。
此类史料主要分布于广东历代地方史志、历代诗文总集、个人诗文别集、近代报刊等文献中。因主题与“藏书”紧密相关,故搜集起来相对容易,可以此为基础史料进行拓展式搜索。
2.2 一手史料
一手史料是指直接反映历史记录的原始文献,如日记、尺牍、家谱、自订年谱等,是当事人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关于藏书家的一手史料,反映了其生平经历,有其藏书、访书、论书、读书、交游等活动的记载。
以南海孔氏家族为例,目前所见一手史料有孔广陶(1832-1890,南海人)的《鸿爪前游日记》和《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鸿爪前游日记》现存清光绪十八年(1892)三十有三万卷堂刻本,记录孔广陶于清同治九年(1870)五月至次年五月,从广州出发至京师,游览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经历。据所载,孔广陶在京师约半年,除外出游览以外,其余时间或拜访友人品观书画碑帖,或出门购书,或居家阅读。诸如:“(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三十日,晴。买书,都中古书之聚甲宇内,元明刻本影钞旧本所在多有,宋椠偶或一遇,至纸色熏染伪印,鉴藏坊贾时时为之,是在人之精鉴而已。”[22]45尽管孔氏并未对购书细节作详细记录,但从其离京时所述“分装三十捆,约九万余卷”[22]55的记载来看,每次购书数量当有数百上千卷,方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9万余卷书籍。
《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撰修于清同治四年(1865),载有南海孔氏家族各成员的生平履历及其历代所建各收藏处所,如南园、濠上观鱼轩、岳雪楼、滚雪楼、十二研斋、云山得意楼、三秋图室;编有家族成员的撰著书目,如《复之书目》中载孔传颜(1772-1809)编《濠上观鱼轩书目二卷》,黄培芳(1778-1859)撰跋文云“复之先生,乡有南园吟咏地也,居有观鱼轩藏书处也……计所藏四万卷有奇”[23],由此方知其家族自孔传颜起便有藏书。
《鸿爪前游日记》反映出孔广陶好游历、嗜佳善本、喜金石书画等艺文情趣;《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则清晰呈现南海孔氏家族四世藏书的更迭情况。然而,日记、尺牍、家谱、年谱类史料在利用上存在较大难度,一是因为一手史料多属于私人资料,未经公开之前,个人难以获取;二是对于已公开的史料,还面临着点校整理问题,如日记、尺牍往往因字迹难以识辨而利用困难。
2.3 其他相关史料
其他相关史料是指在以上两类史料之外载有藏书史实的文献,其主题往往与藏书史不直接相关,包括诗文序跋、碑记铭文、传状记述等多种类型。比如,广东揭阳藏书家姚梓芳(1871-1951)在《姚氏学苑碑铭》一文中记载了修建秋园藏书楼的始末:“甲子冬,先慈见背,自东浙南归,既归五年,颓然不复有用世意,园居无事,乃辟兹苑以毕吾宿愿。苑址旧游击废署,视园积殆倍之,广袤可三百余方井,旷远朗爽。地处城中央,无鸡犬之惊、卑湿之患,以庋书图,较故园为宜。苑中建楼七楹,眉曰‘秋园藏书楼’,楼上祀先君栗主,右屋移书储之,其下以居儿息。”[24]再如,广州番禺藏书家潘飞声(1858-1934)所撰《晨风阁丛书序》谈及《粤雅堂丛书》书版流入海外的史实:“余尝遍览沪渎书肆。书贾为余言,去岁日本人来华,收去各种古籍,值七万余元。美洲人亦载去十四五万元。伍氏《粤雅堂丛书》选刻最精,又为法人购全板片,移置巴黎博物院。”[25]诸如此类的文献,尽管主题与藏书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其所谈及内容关涉重要藏书史实,仍是不可忽略的藏书史料。实际上,因为主题广泛、类型繁多,这部分史料数量相对较多,搜集起来难度亦较大。研究者往往不能利用常规的文献检索方式来轻易获取,而需详览正文进行提取。
3 广东藏书史料的主要内容
藏书史料涵盖的内容涉及历史人文研究的诸多课题。从藏书史研究视角而言,广东藏书史料主要涉及广东私家藏书、广东文献、书院藏书、官府藏书、寺观藏书、近代图书馆等内容。
3.1 广东藏书家的生平以及藏书活动
在所搜集到的史料中,涉及广东藏书家生平与藏书活动的史料十分丰富。据统计,有私人藏书目录63种、藏书题跋26种、藏书记33种,这些类型的史料记录了藏书家的藏书类别、藏书数量、藏书楼的创建,是研究其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的首要文献。其次,分布在各类地方史志中的传记资料以及私修撰文,是了解藏书家生平的重要史料。
以清中期广州南海藏书家曾钊(?-1854)为例,其生平经历可见于《清代粤人传》[26]和《国朝岭南文钞》[27]577。曾钊藏书目录有两种:《曾诂训堂藏书总目》一卷,现存有广雅书局校钞本,收录书籍1,295种;《古输廖山馆藏书目录》,清道光刊本,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曾氏藏书楼名“面城楼”,有两篇藏书记文:一为曾氏好友马福安在楼建成之前所撰《面城楼记》[28],述及曾钊嗜书、读书、聚书等日常活动。面城楼落成后,曾钊又自撰《面城楼记》[27]584,自述其楼创建之始末以及命名之由来。曾氏于广东乡邦文献多有关注,辑有多种广东古代方志文献,并为《杨议郎著书》《交州记》《始兴记》《异物志》等文献撰写多篇跋文。以上述若干种文献为基础史料,再进一步延展至曾钊同时代友人、学者的相关文集,可对曾氏藏书、著书、校书、刻书等活动进行深入研究。
3.2 广东文献的聚散与流通
广东文献的发展史与广东藏书史息息相关。实际上,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是历代广东藏书家的显著特征。在搜集到的史料中,有大量诗文序跋、题记类文章涉及历史文献的成书经历。例如,从明代丘濬《曲江集序》[15]4021-4022《武溪集序》[15]4022-4023两文,可知丘氏亲手抄录馆阁所藏《曲江集》《武溪集》,并在丁忧返乡期间付梓刻印,两书得以传世。从藏书史的角度,藏书的聚散实质也正反映出地方书籍资源流通聚散的轨迹。广东地处偏僻,藏书事业明代方才兴起,但发展程度远不及北方,直至清代中后期南北藏书家才得以频繁往来与互动,其中重要表现为广东藏书家在本土以外广泛搜罗书籍。例如,从莫友芝《持静斋藏书记要序》[29]、林达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30]、叶昌炽《丁氏持静斋书目序》[31]等序文可知,丁日昌(1823-1882,丰顺人)藏书主要来源于为官期间所搜购的江南藏书家流散之书。而在丁氏藏书散出后,南北藏书家又争相求购。丁氏藏书之聚散呈现出南北书籍互通景象。
3.3 广东书院藏书的创建与管理
与广东书院藏书有关的史料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书院藏书楼的题记类文章,如张锡麟撰《冠冕楼藏书记》[32]和顾椿撰《丰湖书院书籍碑记》[33]分别对广雅书院以及丰湖书院藏书楼的创建有着较详细的记载;二是关于书院藏书的规章条制,如与广雅书院有关的《广雅书院学规》[34]1309-1311《广雅书院续增学规十条》[34]1311-1312,与学海堂有关的《学海堂志》[35],与端溪书院有关的《端溪书院原定收借书籍规条》[34]1364,与丰湖书藏有关的《丰湖书藏四约》[36],从中可以了解到书院藏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以广州番禺藏书家梁鼎芬(1859-1919)制定的《丰湖书藏四约》为例,包含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和捐书约四部分,是近代较为完整和规范的图书管理规章制度,体现了公藏思想在广东的传布。
3.4 广东官府藏书与寺观藏书
相较之下,关于广东官府藏书与寺观藏书的史料较为匮乏。广东官府藏书方面,现存史料多与广雅书局有关,目录类有《广雅书局书目》(广雅书局编,清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本,现藏湖南图书馆)、《广雅书局史学丛书目录》(吴翊寅编,清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广雅书局拟刻史学丛书目定本》(王秉恩编,稿本,现藏中国台湾)、《官书局书目汇编》(朱士嘉编,1933年印本)等,反映出广雅书局刻书、藏书概况;创建与管理规章类有《重订广雅书局推广办法暂行简章》(1909年《政治官报》第680号)、《广东提学司详报督院重兴广雅书局推广办法文》(1909年《北洋官报》第2209期)等,多刊载于近代官报或民国报刊中;另有《广雅书局及学海堂等版片述略》(徐信符撰,1934年稿本,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论及广雅书局版片的保存与流散情况。
广东寺观藏书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广州海幢寺设经坊刊刻佛经典籍。冼玉清(1895-1965)在《广东释道著述考》中考述海幢寺刊刻的部分书籍[37]。海幢寺经坊广受近代西方来华人士的关注,在他们关于广州的著作中有过一些零星记载。比如,英国传教士米怜(1785-1822)在1820年的著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记载:“在广州对岸的海幢寺经坊,有大量的印刷工作,他们按天雇用需要的工人。”[38]美国人亨特(约1812-1891)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记载:“如果用英语来讲,这座庙的名字是‘海的帐幔’(Sea Screen)。它拥有一个内容充实的图书馆和一个印刷作坊。在那里,教义被刻在木版上,木版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39]据学者研究,海幢寺藏书大量流失海外[40],故笔者目前所获取到的相关史料十分有限且零散,有待日后深度挖掘。
3.5 广东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私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大发展。实际上,广东在明代已出现公开借阅的藏书楼,从罗亨信(约1377-1457)《同邑礼部侍郎陈琴轩公行状》[41]、丘濬《藏书石室记》[15]等史料可知明代东莞藏书家陈琏(1370-1454)的“万卷堂”藏书楼以及丘濬的“石室”藏书楼,都面向当地学子公开阅览,屈大均(1630-1696)赞其“藏书以惠学者,皆盛德事也”[42]。
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加速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兴起。1911年,梁鼎芬有感于江南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公藏机构的创办,念及广东尚未设立此类机构,遂将私人藏书楼“葵霜阁”改为“梁祠图书馆”,将所有藏书面向公众开放借阅。梁祠图书馆建立后,公开发布《梁祠图书馆启》[43]87,订立《梁祠图书馆章程》[43]88-97,并附观书约、钞书约、借书约、读书约、捐书约,对图书馆的运行和管理进行详细规定。可见,梁祠图书馆已初具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此外,广东诸多藏书家在广东近代图书馆的初创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曾为广东公藏机构服务过的藏书家徐信符自广东省馆建馆始,一直作为图书馆的骨干成员。他以藏书家的专业能力,整理馆藏文献,搜购珍稀古籍,其事迹见于其子徐汤殷(?-1978)在《广东藏书纪事诗》后所撰《叙传》[21]261-270。徐信符另撰《广东文献馆征求文献小启》[44]244-245《广东族谱目录序》[10]82-83《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序》[44]251《广东省立圕藏广东乡贤著述书目序》[10]84-85《广东省立圕沿革》[10]35-43等,既是其服务于广东图书馆事业的见证,亦是反映广东省馆在初创阶段发展概况的重要史料。
4 广东藏书史料搜集与整理的价值
本研究所搜集到的史料以笔者可获取范围内的书刊文献为主,必然存在不少遗漏,但从现有关于广东藏书史研究的各类型成果来看,应涵盖了绝大部分核心文献,能大致反映广东藏书史料的基本概况。随着全国上下各类大型古籍文献整理项目的推进,以“藏书史”为主题的史料汇编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而,有必要重申广东藏书史料搜集与整理的价值。
4.1 深化学术研究,助力藏书史及相关课题研究
“盖材料者为研究学问之基础,故研究史学,即当以搜集材料为第一义”[45]。从上文对广东藏书史料主要内容的分析可知,现有史料涉及藏书史研究的几大核心主题,反映了以书籍生产与流通为中心的诸多文化现象,涉及地方学术、教育、经贸、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实际上,越来越多学者从藏书史、书籍史的角度来思考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例如,美国学者麦哲维一方面从本地历史、诗词与选集入手,论证广东学人如何通过著述来重塑地方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关注到这个过程中本土书籍收藏与刊刻的繁荣[46],藏书的繁荣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从而有了历史研究、诗词、选集等方面的重要成果。再如,凌一鸣以瑞安孙氏玉海楼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士绅家族如何通过藏书活动来提升家族的地方权威[47]。因而,无论从中国藏书史的研究视野,抑或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广东藏书史料都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可以为中国藏书史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一手史料。
4.2 弘扬藏书文化,推动藏书史料的汇编与整理
关于我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整理工作,李希泌与张椒华早在1982年便编撰《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48],按照内容和年代进行编排,汇集200余种文献史料。徐雁等在1988年呼吁全面开展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提出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清理史料堆,编辑集文献大成的《中国历史藏书资料汇编》或《索引》[7]16。如今虽有《中国藏书通史》[49]《中国图书馆史》[50]两种通史性的著作问世,但仍未见关于藏书史料的集成之作。学界在藏书史料的汇编整理上,主要体现在历代藏书目录与藏书题跋的整理与出版上。实际上,在以藏书目录和藏书题跋为主的基础史料受到高度关注之余,广泛分布在历代地方志和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亟须进行科学的编次整理。如笔者在部分广东方志中发现若干未被各类《藏书纪事诗》收录且鲜见于其他文献的广东藏书家,如宋代周克明(生卒年不详,南海人),《粤大记》载其“颇修词藻,喜藏书”[51];明代徐韶奏(生卒年不详,程乡人),光绪《嘉应州志》载其“归田手不释卷,著诗文甚富,里有‘架有千书,囊无一钱’之谣”[52];清代黎文燧(生卒年不详,番禺人),乾隆《番禺县志》载其“藏书数百卷”[53]。诸如此类的记载尽管多为只言片语,但仍然是广东历史藏书活动的重要文献印证,它足以引导研究者从区域史、书籍史的角度去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弘扬具有广府特色的藏书文化,推动我国藏书史料的汇编与整理。
4.3 保存地方文献,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地方文献影印出版面临“存世状况不清,影响底本征集”与“破损情况严重,制约底本扫描”两大难点[54],因而急需对现有古籍文献进行抢救式保存与开发。广东藏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助于促进图书馆对珍稀文献、乡邦文献的整理利用,从而深度挖掘古籍文献的历史价值。从上文关于藏书史料的主要文献来源可以发现,大量史料散落在个人诗文集以及与藏书家密切相关的日记、尺牍、家谱、年谱等文献中。然而,这些文献多深藏于各类型图书馆,在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上文提及的《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机构;孔广陶《鸿爪前游日记》,始经由《广州大典》影印出版才得以被大众所利用。广东藏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正是希冀保存珍稀历史文献,深入挖掘文化精髓,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注释
①种数的统计方法为:单篇文章或同题名的系列文章被视为1种,如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分为5篇刊载于《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统计时视为1种;已刊印成册的著作被视为1种,其中所收录的单篇文章不再单独进行统计,如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被视为1种,其中单篇的跋文不再单独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