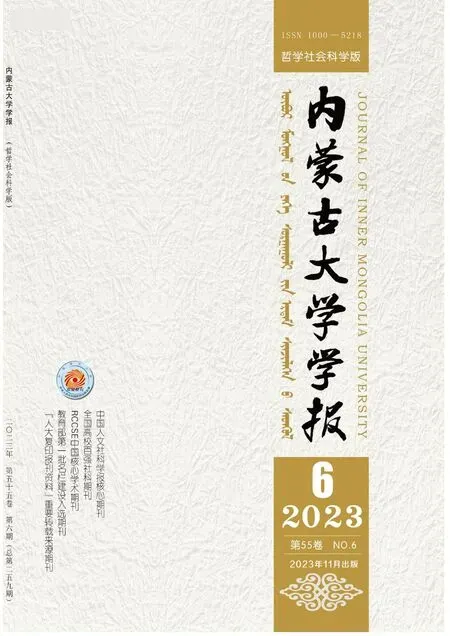契丹文化与北疆文化研究浅谈
2023-03-02孙久龙迟安然
孙久龙,迟安然
(1.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建筑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契丹文化并非单一族群文化,而是受到奚、渤海及中原汉文化多重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 契丹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其他族群文化而形成的。 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契丹文化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为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契丹族是发源于松漠地区的鲜卑宇文别种,其原本活动区域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和戈壁之间,因而契丹文化发源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 如契丹人日常居室为可自由拆卸的帐篷,日常出行多骑马或骑骆驼,大多数契丹人在各自的畜牧地内过着游牧生活,日常以放牧牛、羊和马为主。 他们平时放牧,战时作为部族一分子而出征。 辽朝建立后,辽统治者基于这种生活习惯建立了群牧制和部族军制,使辽朝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可以说,契丹族这种日常游牧生活是辽朝在10—11世纪称雄东亚的基础。 在契丹人日常生活中,男性与女性分别从事放牧和采集食物等工作,契丹族内男女地位也相对平等。 这种现象直到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人群中仍然存在,也影响了契丹本族的收继婚制度。 收继婚的盛行最终使得契丹人内部形成以父系皇族耶律氏和母系后族萧氏为主的两大姓氏族系,其他契丹姓氏逐渐没落。 此外,这种游牧文化也是契丹人建立辽朝时实行四时捺钵和斡鲁朵制度的基础之一。
契丹文化也包括一些渔猎文化和农耕文化。渔猎活动是契丹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契丹贵族对狩猎异常痴迷。 辽朝在四时捺钵之际,春夏秋冬都会开展大规模渔猎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头鱼宴”和“头鹅宴”。 时至今日,源自契丹渔猎文化的查干湖冬捕仍是东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盛景。 至于农耕文化,契丹族世代居住的松漠地区本就是农牧交错地带,耶律阿保机也曾在整合契丹诸部过程中率领族人从事一些简单的农耕生产。 与突厥、回鹘甚至更早的匈奴相比,契丹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其民族文化从形成之初就不是基于单一经济生产方式,这也造就了契丹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和吸收性。
中原文化对契丹文化影响深远。 辽朝建立前,随着大量汉族人的迁入,中原文化已传入契丹社会。 伴随着燕云地区被纳入辽朝版图,汉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 如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均借助汉字偏旁加以改造创立而成。 辽朝建立后,两种文字并行,政务往来的大小公文、贵族和官员的墓志大多由两种文字书写,且因不同情况而有所偏重。 很多入朝为官的契丹人和上层亲贵都是双语使用者。 此外,《贞观政要》《论语》《大学》等汉文书籍也都被译成契丹文字并广泛传播。 如道宗本人的汉文学素养就非常高,他在面对北宋使臣时,谈到本族文化曾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1](22)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学中的一些观念,如儒家三纲观念,逐渐成为契丹人日常处世中所遵奉的准则,一些儒家思想甚至改变了契丹“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2](221)的观念和收继婚风俗。 如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3](1260)。 作为宗室贵族的耶律宗政在父亲死后,拒不与后母成婚,[4](157)不再遵循收继婚的婚俗。
汉文化在契丹的盛行造成辽朝南北二元政治的出现。 为方便王朝治理,辽朝建立了南北面官制,并延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政治传统,强化了枢密院的地位,使其成为王朝中枢政务流转的中心。在地方上,无论是州县,还是部族之地,都广设源自唐末五代的节度使,以及类似的职官机构,如转运司、统军司等。 契丹南面官的官衔基本遵从了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官员系衔规制,包括散官、检校官和职事等,并走出了一条与北宋官职系衔完全不同的道路。[5]科举制度在辽朝也日渐盛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人早期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即使有些契丹人对汉文典籍比较熟悉,也只能通过军功和荫补等方式进入官僚系统。 但到辽天祚帝时期,已有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其中佼佼者也同样取得了进士身份,并获得官职。 如建立西辽的耶律大石,不仅参加了科举考试,还取得了殿试第一的成绩,直接被授职翰林应奉,进入辽朝核心职官系统。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契丹人开始烧制瓷器,辽三彩多承袭了唐三彩的烧制工艺。 契丹人还根据游牧生活的需要,将汉文化瓷器的形制加以改良,其中以鸡冠壶最为典型。 这种借鉴中原地区瓷壶并改良而成的瓷器成为契丹瓷器的代表性器物。
上述事例都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之深。 契丹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建立的辽朝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活,既顺应了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又因地制宜,结合契丹本族文化和历史现实,开辟出了一条与北宋平分秋色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存在着自辽朝开始的“第二个南北朝”[6]理论的依据之一。
不仅如此,奚、渤海和党项文化也影响了契丹文化。 沈括曾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 车工所聚曰打造馆。”[7](95)契丹人本不善于造车,其造车技术主要源自奚人。 渤海的崇佛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契丹人,契丹上层贵族多崇信佛教。 渤海人聚居的辽东是当时重要的铁矿产地,渤海国被灭后,其冶铁技术为契丹人所掌握。 渤海人能歌善舞,渤海乐也成为辽朝宫廷音乐的一部分。 另据《契丹国志》记载:“渤海厨子进艾糕。”[8](252)渤海厨子所做的艾糕,深受契丹贵族喜爱。 相比奚、渤海文化,党项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较小。 这是由于生活在辽西的党项人作为两属族群,经常在西夏与辽朝之间摇摆不定,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也一直在辽和北宋之间左右逢源。 在这种情况下,党项与契丹的文化交流主要依赖双方的榷场贸易,其中对契丹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通过与西夏的贸易往来,辽朝获得了佛教经典,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契丹社会崇佛氛围的兴盛。
契丹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影响的产物。 契丹族因所处地理位置与多族群交错生活的环境,在发展游牧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族群文化,并以此改造自身文化。 这是契丹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契丹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 以契丹始祖传说中的青牛白马为例,“刑白马为盟,无论华夏、北族,皆属古已有之,但将牛、马并用,以青、白相别,且对应天、地祭祀,则无疑为契丹人首创,后世与之相类的盟誓、祭典皆可溯源于此,惟具体表述稍有不同,或作乌牛白马,或作黑牛白马,其实一也”[9]。这种影响甚至通过草原游牧族群,扩大到了与之接触的北方渔猎、农耕族群。 如满族多次使用白马乌牛的盟誓仪式,就是直接借鉴与其联姻的蒙古诸部。 因此,契丹文化是一种基于游牧文化,并与周围农耕、渔猎族群的文化交融后产生的文化共同体。 契丹文化的一些特征在辽朝灭亡后仍然影响着后来的蒙古族和满族文化,且在中原汉地也影响深远,并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