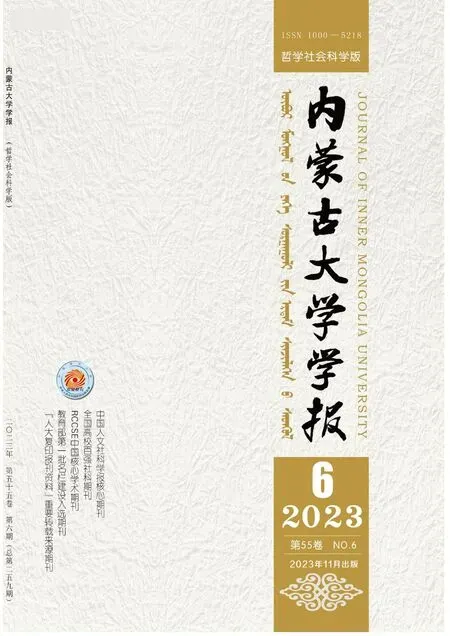浅议“北疆文化”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再读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2023-03-02仲伟民
仲伟民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4)
拉铁摩尔将大于“中国”的“亚洲”置于范围小于它的“中国”范围之内来思考,很有深意,这对我们今天从全球史或世界史角度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极有启发。 尽管目前全球史方法很热,但真正能从全球史视野来理解中国历史,其实非常难,尤其是在传统中国史料及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我们很难接受以他者眼光来观察中国历史。
“北疆文化”是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论述的一个重点,也是其立论的基础。 他敏锐观察到,最能够代表中国边疆历史的地方就是蒙古草原。 这个观点看上去颇难让人接受,但深入中国历史实际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睿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统一多民族历史的理解。 北部边疆非常辽阔,按照地理次序,从东北部多样的地理环境,到新疆的绿洲和沙漠,再远及西藏的寒冷草原,“在这之间诞生了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种变形的社会。 这种改变的形式是受到蒙古情势的影响,也受中国势力的影响,这种势力虽然各地不同,大体上却是一样的”[1](39)。 之所以说蒙古草原在边疆历史中最为典型,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不仅民族交融的频次特别高,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 所以,拉铁摩尔认为,蒙古草原有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甚至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的关键。 突出表现为,在中国强盛时,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它是北方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 就蒙古地区而言,鄂尔多斯草原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是多个朝代疆域最不确定的部分,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秦朝以后的政权边界几度南移北挪。
我们可以长城为例来观察北疆文化的复杂性及边疆与边界的关系。
中原政权的传统边界是长城,且成为汉民族的重要历史记忆。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记忆,可能离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因为不仅历代长城变化大,而且历史上真正以长城为边界的朝代并不多。 比如汉唐时期,秦长城变为内墙;五代两宋时期,中原政权控制疆域大幅度向南收缩,秦汉长城成为化外之地;元朝建立后,历代长城都彻底变为内墙;明代疆域比元代大为收缩,并重新修建长城,但明朝统治者实际上并不甘心以长城为边界。 所以拉铁摩尔认为,长城也只是一个近似的绝对边界,它是环境分界线上多种社会影响的产物。 确切地说,长城实际上只是传统中国人心理上的边界。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原王朝建设长城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但长城客观上也有防止中原人民外出的目的。 对此,拉铁摩尔有深刻的论述,他敏锐观察到北方边境的特殊性,指出多个朝代都曾修建或维护长城,依靠长城及其边防,中国不但要抵御外来侵略,也试图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 因为汉族如果过于深入草原地区,就会与游牧民族融合,甚至会与中国分离。所以他说:“即使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推到长城以外,并设置戍军以支持的时候,其目的也不是对外发展,而是一种防御性占领,以填充可能被利用来攻击中国边界的缺口。 要使这种政策发生效用,就必须限制长城以外的汉族事业。”[1](164)他甚至说,“长城的意义,主要是使他们获得控制南部‘汉族土地’ 的力量,而不在于对草原的控制”[1](307)。 比如,秦始皇扫荡了草原边缘地区,但他并没有侵入草原,他的目标也不是要建立一个包含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联合帝国。 中国南方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历代王朝无论怎样向外发展,汉族不仅不会与中国分离,反而会开疆拓土,并逐渐使当地居民与其融合。 所以,就长城起源来讲,即拉铁摩尔所说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汉族的离心力。
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实,即长城不仅没能阻挡蒙古高原上少数民族的冲击,而且也从来没有阻断南北人民的直接交往。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内地农业地区与草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不仅没有形成政治上的隔绝,而且客观上存在一个面积广大的农牧交错带。 虽然不止一个王朝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长城,但长城没有成为铜墙铁壁,边疆也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 沿长城或边界形成的农牧交错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以上论述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 绝对固定不变的边疆,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将长城视为边疆,是一种偏见。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拉铁摩尔提示我们:“从这种不能完全稳定的平衡中,亚洲内陆边疆之中终于生长出一个处于中间的边境世界来! 一个渗透着中国及草原的影响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 因此,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1](322)我们从全球史或世界史角度来看,长城对于汉族来说可能是边缘地带,而对整个亚洲内陆来说却是一个中心。
第二, 需要明确边疆(Frontier) 与边界(Boundary)的概念,不应该混淆。 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重视边界、强调边界,容易忽视边疆。 而客观上,因为边界的变化极大,包括长城的位置,历代多有变化;甚至在同一朝代,也可能难有固定的边界,“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 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1](163)。
第三,中原农业民族与蒙古草原民族在人种学上几无差别,原本可能就是同种同源。 拉铁摩尔认为,草原民族很可能就是从中原被赶出去的比较落后的一支。 他说:“很可能,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族,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1](281)这个见解非常重要,对我们理解草原民族的起源非常有帮助,如果能够证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有意义。
北部边疆在帝制中国后期的大一统中,显得非常特殊且重要。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大致上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这大致不错。但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此,就南北而言,中国历史的北向发展不容忽视。 我们不能仅看到游牧民族南下,还要看到汉民族北上。 正是在秦汉长城与明长城之间的广阔空间,农业民族逐渐站稳脚跟,才有了元代以后中国的基本地域格局,北京也才真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中心。 可以说,没有北部边疆的稳固,就不可能有元以后600年中国的大一统。
北部边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一,北部边疆是中国人逐渐打破“天下观”的关键区域,这一点在宋辽西夏金混战时期特别显著,传统“天下观”从此开始被打破;其二,华北地区在先秦至秦汉时期曾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区,但东汉以后长期处于混乱和停滞状态。 元代以后,北部边疆的稳定使华北地区再次一跃而起,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乃至经济中心。 同时,元代也是华北核心区成为中国重要区域的关键时期,明代朱棣迁都北京标志着帝制后期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 其三,北部边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价值,因为“对于西北部、北部以及后来东北部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中,虽然都是含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为非中华民族”[1](42)。 就此而言,北部边疆在中华民族凝聚与融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