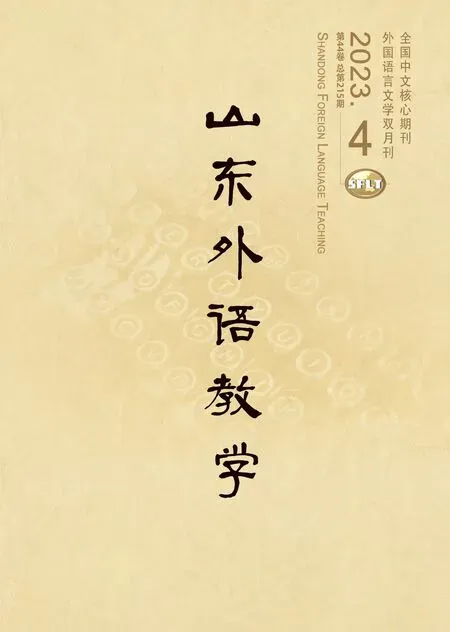四手联弹的“四个四重奏”
——《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述评
2023-03-01曾巍
曾巍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1.引言
王卓教授毕十年之功精研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丽塔·达夫的专著《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出版,对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界热门的当代女性创作研究、族裔文学研究,以及随着诗人访问中国掀起的“达夫热”聚起的读者群体来说,都是大有裨益。书名对达夫馈以“黑色维纳斯”之谓,然而全书并未特别对这一雅称加以详释,可见该书并不是以“后自白诗人”“跨种族诗人”“世界主义诗人”等标签,将这位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美国第一位黑人桂冠诗人纳入流派分析框架之中,也不是有意将诗人“神话化”。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评论家文德勒(Helen Vendler)借“Dove”一词的双关语义所美誉的“黑色的鸽子”(1995:156)—— “鸽子”暗喻诗歌想象力的飞翔,“维纳斯”更多意谓达夫的创作深受欧洲文化传统的滋养。在符号意涵层面,维纳斯是美的化身,达夫的创作始终将艺术之美作为追求目标。王卓向读者含蓄表明,她对达夫的研究,将超出作家作品研究中常见的“知人论世”路数,上升到文化和美学的维度。
2.一分为四的主题分析
作家作品研究常见的程式是结合作家(诗人)的生平,依照创作时间先后对作品(诗集)进行细读,进而发掘主题、提炼风格、阐论价值。这种思路有探幽索隐之趣,但可能失之对作品整体的总览,而且前后分析往往缺少足够呼应。王卓的达夫研究选择从横剖面切入,将作品划分为成长书写、空间书写、历史书写、文化对话四个主题群,继而条分缕析,显示出对诗人创作全貌了然于心。达夫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诗歌研究和文化研究专家,因而对其作品“最好方式莫过于将其置于女作家本人的诗学理念的框架之中,并在两者的交互参照中相互投射、相互诠释”(王卓,2022:35)①。这样,四个主题群又分别与非裔女性诗学、空间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构成和弦式叠置关系,显示出总体的完整、丰满和协调。
在简短的介绍性“序曲”之后,四个主题分析俨然是生命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第一乐章 “女性成长之路”聚焦于黑人女性的身体、精神与艺术成长。王卓从形式、内容、风格、内涵等差别颇大的诗作中梳理出四种主要类型——其叙事对象分别是历史真实人物、具有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主体、神话人物以及父亲。而四种类型又聚焦于黑人女性,从种族、性别、阶级、美学四个维度多层次揭示,呈现出“一个文化混血儿,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女性—文化混血儿—公共知识分子’的全面成长”(39)。
第二乐章向广阔的世界空间弥散。研究者从《街角的黄房子》《博物馆》《农庄苍茫夜》等诗集的名称和许多冠以地名的诗题中准确捕捉到达夫诗歌中“占有的空间的诗性意识”(Dove,1995:15),并发现其作品中的空间位移,即在“家宅空间”与“旅行空间”两个显性坐标点之间不停游徙。因此,达夫的空间书写可隐喻性地抽绎出“双向通道”:一端是生命、种族、文化的源点,一端是多样化的外部世界。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双重作用下,“家园和世界是双向互动的两个物质坐标轴,而内心世界则是不断钻掘到精神深处的隐形的动态的点”(172)。所有空间要素都交叉会聚于此,在具体生动的诗作中变幻出万千空间景观。第三乐章的基调是浑厚的悲怆与深沉的激越。王卓发现,达夫的历史书写并没有面面俱到的雄心,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种族身份,从黑人的家族史、奴隶史、解放史、世界史四个亚主题群“反映了达夫对黑人的族群身份、黑人的文化身份、黑人的政治身份和黑人的历史身份的书写”(401)。诗人重新塑造被宏大历史忽视、遗忘的日常生活,或语焉不详甚至扭曲的重大事件,以微观历史与公共的宏大历史展开对话,为历史增加了个体的温度和情感的强度。
在文化书写的终章部分,王卓将视线转向了达夫的小说、诗剧以及编选的诗歌选本。她指出,这些创作和编辑活动恰恰是诗人诗学理念的另一重要体现。小说《穿越象牙门》是对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互文书写;诗剧《农庄苍茫夜》是对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的现代改写;《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也因编选标准掀起了与著名评论家海伦·文德勒的论战。这三者都“深切地体现了她与世界文学经典的协商、对话以及对其的挪用和改写意识”(404)。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达夫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定位赋予了她用世界公民的声音诠释这个世界的权力,并在杂糅诗学建构、历史书写策略和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中体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452)。
3.四合为一的诗学建构
在这部专著中,四个主题分析形成了四章,“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来讲”,“回答的分别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何时成为‘我’?‘我’如何成为‘我’?这四个颇具哲学意义的问题”(35-36)。除第四章外,前三章又分别讨论四个亚主题。这样,乐章之中又可以辨出重奏部分。在具体剖析中,王卓从不拘泥于单一视角。如关于诗集《母爱》,该书指出诗人是在四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情节上偏离了她的黑人文学女性先辈,发现了更丰富的文化谱系和精神营养。又如对诗集《博物馆》的空间解构,将时空交错的文化遗产分陈到四个展区,从而在崭新的文本空间中重述了历史,在消解中心的同时让被边缘化和刻板化人物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达夫的每部诗集几乎都有一个精巧的形式设计,王卓的研究则不仅发现了她的匠心,而且在更大的整体上发现了一种架构,指向了诗学理念的有机统一。
这种有机统一和整体性的延展,就是“多元主题与身份建构的统一、多元主题与文化杂糅的统一以及多元主题与对话叙事的统一”(461)。首先,身份建构贯穿于成长、空间、历史、文化的书写之中,分别建构了完整的身体自我、具有空间感的动态自我、发展的历史自我与多元文化参照下的世界主义的自我。这些实际是一个自我的多重面相,具有内在和谐,并展现为扬弃了黑人文学先辈美学原则的诗学理念。其次,文化杂糅既是一种写作策略,也是文化身份和观念的建构。正是随着主体自我的成长与旅行空间的扩大,达夫接触到更多元的异质文化,她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诗歌资源,将西方文学谱系与非裔文学谱系融会起来。与此同时,她在对“分离主义”和“融入主义”的审视中,发展出包容差异、积极互动、倡导合作的世界主义,这一理念也内化在她的诗学之中。最后,在对话叙事中,达夫作品的主题和谐与文化杂糅性得以彰显。在微观层面,对话表现为不同叙事声音的交流,以及以轮言叙事完成对同一故事的多视角讲述和补充。在宏观层面,对话发生在为性别之间、微观史与宏大历史之间、历史事实与虚构事件之间、当代文本与经典文本和文学传统之间。
跟随研究者走近达夫作品中的不同主题,读者领略到“四个四重奏”不同乐段中诗人的多重身份,在某一旋律成为强音时,诗人仿佛呈现出不同“分身”,但这些“分身”并不意味着自我的割裂,它们将最终汇聚为一体,以其独特性确证诗人的主体自我,确证她在美国非裔文学传统、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独树一帜的位置。一些研究者深感达夫属于一直“避免被归类的作家”(Righelato,2006:1),认为她“引领了一直延续的世界主义传统线索的非裔美国诗歌史的一个新阶段”(Pereira, 2003:11),这与其说从她的诗歌中发现了新主题和新风格,毋宁说敏锐察觉到与众不同的诗学理念正在形成——它在诗歌四重主题的交汇处凝聚,编织出绚烂的生命乐章和符号乐章。
4.双向奔赴的共鸣合奏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这部达夫研究专著在结构缺少了一块拼图,即第四章由三个分节组成,与前三章都有四个分节不一致。如此一来,“四个四重奏”的提法似乎难以成立。这是作者的疏漏还是有意的留白?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达夫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达夫研究在几近完备的结构上留出余地,既是对诗人将来创作的期待,也是向其他的达夫研究者发出邀请,召唤具有启发性的学术对话。此外,还可以进入文化书写寻找原因。前已述及,该书的第四部分是围绕几场文化对话展开。第一场发生在黑人女性作家内部,是由相仿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引出的关于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思考。第二场对话跨越了民族文化的边界和久远的时间,达夫大胆与西方经典文学的代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进行“商榷”,表明“黑人群体的精神维度远远超越了悲剧英雄本身的个人力量,并将成为黑人种族获得解放的最终希望”(432)。第三场对话由达夫编选的诗集引起。对话或者说对垒双方是达夫代表的美国非裔诗人和文德勒领衔的白人评论家。看似争辩的是优秀诗歌的美学标准,实则显露出不同种族、文化间的分歧,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症结。而我们关心的是,如果还有第四场对话,将在达夫与怎样的交谈者之间展开?显然,最合适的对象可能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并能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中与诗人感同身受、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或批评家。这样的对话可以想见将碰撞出闪亮的智慧火花。
事实上,从这部达夫研究著作的第一个字落笔的那一刻,这场对话就已开启。王卓教授长期浸淫于当代美国诗歌研究和族裔文学研究,理论功底深厚。这使得她对达夫的阐论既能深入作品的内在肌理,又能延展到宽广的社会历史空间。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她能更敏锐地捕捉达夫诗中对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的书写。作为中国学者,她对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一时所带来的文化偏见,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群体切身感受到的边缘地位亦有清醒的认识。如何重新定位、建构当代知识女性的文化身份,成为身处大洋两岸的诗人与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达夫以四大主题的文学书写对此进行了艺术性的呈现;王卓显然是一位艺术素养与学术素养俱佳的读者,她从达夫作品中找到了精神共鸣,并对其展开了深入阐发。可以说,这是一次高质量、高品位的关于诗与思的对话,是心有灵犀的女性对话。它一直贯穿于此前的多个乐章之中,而在这里成为了最清亮的音符。
5.结语
《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无疑是一部作家作品研究的力作,甚至可以说是从宏观视角全局把握作品总体、将诗歌与诗学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范型。聂珍钊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肯定了其研究特点,称之“多而不杂、繁而不乱”,“在文本细读中将理论运用于无形,在归纳总结中形成独到观点”(4)。王卓的达夫研究给我们带来启示:诗歌批评与诗歌鉴赏,不能仅停留于细节处的把玩,不能孤立地对诗歌评头论足,还应在总览全貌的基础上详察,这样才能看出脉络,看出结构。这也正是具有形而上性质的诗学理念从具体诗歌文本中超拔而出的绝佳契机。
注释:
① 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