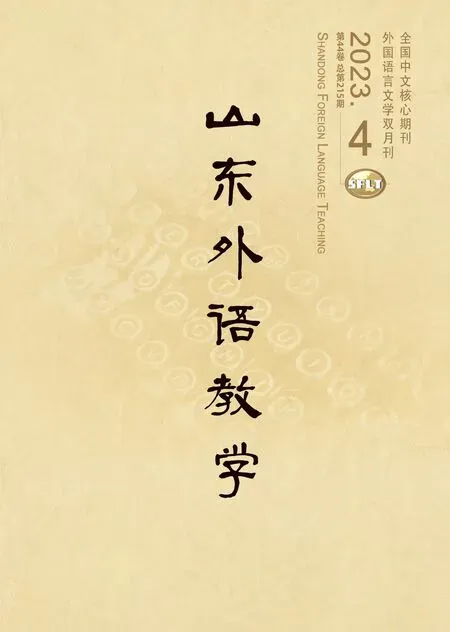辜鸿铭《论语》英译的文章翻译学解读
2023-03-01王宇弘
王宇弘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1.引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典籍外译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向相关翻译实践和理论建设发起诸多挑战。就实践而言,外译典籍的出版与日俱增,其海外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且当代鲜有蜚声海外的典籍译家。就理论而言,一方面,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热火朝天,但同典籍翻译实践尚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译论明珠蒙尘、不受重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历史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经典范例进行系统梳理,并基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深入分析,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典籍翻译研究体系提供助力。
辜鸿铭以创造性的方式译就的《论语》(1898/1996)便是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成功案例。辜译《论语》大量征引西方哲言及文学经典,以之类比儒学概念,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阐释了儒家思想体系,突破了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一经问世即广受赞誉。从文章翻译学的视角进行考察,可知辜译本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译者坚实的文章学基础、深邃的文章学思想和精妙的文章学表达。研究辜鸿铭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文化形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屠国元、许雷, 2012)。
2.辜译《论语》的文章学基础
由潘文国提出的文章翻译学(最初名为“文章学翻译学”)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该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章之学,是对严复翻译思想的直接传承和系统发展(潘文国, 2017:443)。从文章学,到严复翻译思想,再到文章翻译学,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观点,即文章(包括译作)并不是单纯的文字作品,而是具有社会政治目的、服务于社会政治需求的文化产品(潘文国,2017:400-401)。辜鸿铭选择并能够完成《论语》的英译,首先取决于他作为多语者、学者和文化使者的身份与经历、道德与才识。
辜鸿铭生于南洋,青少年时在欧洲游学多年,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而后毅然回归祖国,成为张之洞幕僚,以自身所学为国效力。“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刘中树等, 2015:2)的独特人生经历,令其自称“东西南北人”。他的母语是汉语,同时精通英、法、德、俄、拉丁语等欧洲语言,英文著述能力不输同时代的西方文学大家。他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思想启蒙,熟稔西方历史文化,却始终服膺于中华传统,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深邃思想主张的人文学者。辜氏博采中西融会贯通,这为他的儒经英译实践提供了深厚的知识与能力基础。
传统文章学向来将作文章视为经世治国的重要手段,文章自古以来便蕴含着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这种观念激发的社会责任感在辜鸿铭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在中国最积贫积弱、被西方文化强势裹挟的年代,他希望通过解读儒家思想、彰显春秋大义挽中国社会于倾颓,希望通过译介和著述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和经世价值,扭转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偏见。辜鸿铭(1996:303)曾谈到自己沟通中西文化的最终目标:“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这样深刻的社会政治觉悟、超前的文化互通观或许正是他选择英译《论语》的目的和初衷。
3.辜译《论语》所体现的文章学思想
辜鸿铭的经历、学识等为英译《论语》奠定了坚实的文章学基础,而其翻译理念则体现了深邃的文章学思想。林语堂(1998:61)将辜译儒经实践总结为“一种创作性的翻译”,这与文章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类文章的观点相合。提出“信、达、雅”译事三难的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与辜鸿铭是同时代人,严氏和辜氏分别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代表人物。文章翻译学是对严复翻译思想的继承和深化。从文章翻译学的视角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严、辜二人虽分别擅长外译中与中译外,但翻译理念颇为相似:辜译《论语》清晰地体现了“信”于读者、“达”诸意旨、“雅”乎文辞的文章学思想。
3.1 “信”于读者
“信”于读者是辜鸿铭文章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根据严复的原意,“信”并非忠实于原文,而是对读者的“诚信”,对应他在《天演论》译例言所引“修辞立诚”之“诚”(严复, 1984:136)。有学者曾指出,中文作品外译的传播效果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者心目中没有真正考虑到译作的受众(王宇弘、潘文国, 2018:96)。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首先要问自己是为谁翻译,因为只有对目标读者具有清晰的认知并在翻译过程中多为其着想,译文才有可能被广泛接受,进而达成预期的文化交流效果。辜鸿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正如他在《论语》译文首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尝试让这本完全用中文写就的小书,在表达上能让普通英文读者容易理解,我们确信,这本书给中国人提供了智力与道德的装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尝试了让孔子及其学生们如同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那样去说话,而表达的则是与中国先贤们相同的思想。”(辜鸿铭、王京涛, 2017:5)
辜鸿铭将译文的目标读者设定为普通英文读者,并且努力用易于读者理解的英文去表达孔子等中国先贤的思想,体现了明确的读者意识。为此,他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尝试,例如有意删减特殊名词(如略去《论语》中的人名)、用欧洲作品或文化名词为译文作注解等。林语堂(Lin, 1938:34)评价这种译法“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很适合西方人阅读。
3.2 “达”诸意旨
严复翻译思想中的“达”是指“达旨”,即意义的正确传达。严复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西学东渐”。为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思想学说,译者将重点放在传达作品精神主旨和思想内涵上,因此往往突破语言的表层结构,在翻译中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正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严复, 1984:136)中所解释的那样:“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原文。”虽然辜鸿铭主要从事中译外的实践,但其翻译思想与严复不谋而合,其译作也体现出“达旨”的特点。
《论语·八佾》中有子夏问《诗》一情节。子夏问老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字面上是指先有洁白的底子才能进行彩绘,深层的寓意是事物的本质是首要的而文饰是次要的。理雅各将“绘事后素”译为“The business of laying on the colors follow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lain ground”(Legge, 2016: 78),不可谓不忠实于字面;辜鸿铭将其译为“In painting, ornamentation and colour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e groundwork”(辜鸿铭, 1996:362),虽在字面上有所改动,但点出了主次关系,更易于英语读者领会这句话的真正所指。
忠实的翻译观曾经被奉为圭臬,但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多元思考。黄兴涛(1995:90-92)认为辜译儒经过于释义化,译者时常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改写。对改写的不同看法则体现出翻译观的差异。翻译究竟要传达什么?文章翻译学给出的答案是“达旨”,因为翻译同作文章一样,需要向读者传达某种思想主旨和精神实质。如果认同严复“达旨”的主张,那么辜氏的释义行为不仅无可厚非,更是实现翻译目的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3.3 “雅”乎文辞
严复进一步提出翻译应在“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984:136)。潘文国认为,严复提倡的“雅”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文雅”,也不是梁启超所谓“渊雅”,而是指“雅正”,即主张采用一种通用的、正式的、标准的、成熟的语言来从事翻译,因为只有用这种语言才便于“达旨”(2017:405-407)。严复用标准文言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一系列西方思想名著,雅正的译笔所传达的新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若将“雅”理解为“雅正”,则不难看出辜鸿铭翻译儒经所用的英语与严复所用的汉语文言在规范性方面惊人地相似。辜氏的英文行文被公认为具有维多利亚时期典雅、风趣、流畅而美妙的风格,几乎所有读过他论著的英美人都有同感(黄兴涛, 1995:6)。林语堂对辜译《论语》的语言推崇之至,认为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宋炳辉, 1997:149)。辜氏所译的儒经深受西方读者欢迎,想必与其流畅雅正的英文行文不无关系。
4.辜译《论语》的文章学表达
辜译《论语》做到了“信”于读者、“达”诸意旨、“雅”乎文辞,同严复的翻译主张相一致,体现着中国传统文章学思想。而能够在翻译实践中真正做到“信、达、雅”,还要依靠译者精妙的文章学表达。文章翻译学认为,典籍翻译在语言表达方面应做到“义合”“体合”“气合”;其中“义合”要求译文和原文在字、词、句、篇各层面的意义必须相合,“体合”是指文体形式相合,“气合”是指译文与原文“神气相合”(潘文国, 2014:99)。从文章翻译学的视角进行解读,辜译《论语》体现了春秋之“义”、合宜之“体”和贯通之“气”三合。
4.1 春秋之“义”
“义合”中的“义”是指文本的语义。翻译《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对经义的解读是重中之重,辜译《论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义合”。
其一,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初衷是彰显“春秋大义”,使西方人“重新定义对中国人的看法”(辜鸿铭、王京涛, 2017:7)。辜氏对“春秋大义”的理解极具洞见,认为儒学在本质上并非宗教,而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因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教导人们做一个善良的人,儒教,则更进一步,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的公民”;儒教认为“个人的生活……与他人及国家密切相关”(辜鸿铭, 1996:43)。辜译《论语》中一些儒学概念的翻译可印证上述观点。例如,辜氏将“孝”译为“the duty of a good son”,“弟”(通“悌”)译为“the duty of a good citizen”,将“为政”译为“discharge your duties in the government”,反复使用“duty”一词突出这些概念的社会伦理属性,强调人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所肩负的责任。
其二,辜鸿铭认为儒家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不以暴抗暴,而应诉诸义礼”(辜鸿铭, 1996:17);黄兴涛(1995:81)也认为,辜氏之所以选择翻译儒经“与他对儒家文化道德特质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辜鸿铭将孔子的思想体系概括为“君子之道(the law of the gentleman)”,而“在欧洲语言中,与孔子的君子之道意义最相近的是道德法 (the moral law)”(辜鸿铭, 1996:55-56)。基于以上认识,辜氏在翻译《论语》中一系列核心概念时也着重体现其道德属性,例如在不同语境中将“仁”译为“a moral life”或“moral character”,将“德”译为“the moral feeling”“the moral sentiment”或“the moral worth”,将“善”译为 “moral grandeur”等,“moral”一词作为主线贯穿其间。
《论语》中的概念术语众多且内涵丰富,在西方文化中难以找到对应词汇,如译者处理不当,往往会令西方读者不知所从。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核心概念时着意凸显其伦理与道德属性,辜译本对相关概念的系统诠释无疑有助于英语读者迅速理解和认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这种系统翻译方法同文章翻译学的主张一致。潘文国(2014:96)将“义”分为字辞义、组织义和系统义,提出“义合”是“义”的灵活对应和匹配而不是逐字死译。只有从篇章精神主旨的高度来统筹具体表述的翻译,才能做到真正的“义合”。
4.2 合宜之“体”
“体合”中的“体”指文体风格,辜鸿铭对《论语》英译文体风格也尤为重视。辜氏的英文著述能力超群,其自身对译文的文学性也有很高的要求。他在英译《论语》序言中提到了理雅各译本文学性的欠缺,认为从理雅各“开始翻译这些书所表现出的文学训练的欠缺,到最后表现出的在批判性洞察力与文学观念上的彻底匮乏,说明他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而已”(辜鸿铭、王京涛, 2017:3)。辜氏的评价有些尖刻,但的确道出了理译本在文学性上存在的弱点。试看下例:
例1:
原文: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第三)①
理译:
1. Tsze-hea asked, saying,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passage — ‘The pretty dimples of her artful smile! The well defined black and white of her eye! The plain ground for the colors?’”
2. The Master said, “The business of laying on the colors follow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lain ground.”
3. “Ceremonies then are a subsequent thing.” The Master said, “It is Shang who can bring out my meaning. Now I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the odes with him.” (Legge, 2016:78-79)
辜译:
A disciple asked Confucius for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verse:
Her coquettish smiles
How dimpling they are;
Her beautiful eyes,
How beaming they are;
O fairest is she
Who is simple and plain.
“In painting,” answered Confucius, “ornamentation and colour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e groundwork.”
“Then art itself,” said the disciple, “is a matter of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My friend,” replied Confucius, “You have given me an idea. Now I can talk of poetry with you.” (辜鸿铭, 1996:362)
《论语》通篇均为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或问答,以口语体为主,但例1首句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故也涉及诗体。下面以此为例分别来看理译和辜译对两种“体”的把握。
从口语体的角度看,原文是子夏和孔子的两轮问答。子夏第一次发问时,理译还原了疑问语气,辜译化问句为描述,或许是为了凸显被引诗句。子夏第二次发问时,理氏将原文中孔子的第二答译为“It is Shang who can bring out my meaning. Now I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the odes with him”,可见其误以为“Tsze-hea”和“Shang”不是同一个人。其实,子夏为字,其人卜氏名商,在这场面对面的交流中,孔子肯定了弟子的见解并表示愿意同对方更深入地探讨《诗经》。辜译本将子夏的第二问“礼后乎”的内容和发问者译出,句首的“Then”很自然地承接了孔子的第一答,“Is (art itself) a matter of ‘secondary’ consideration”的疑问紧随其后;同时,下文孔子的答语用第二人称“you”来称呼子夏,并增译了呼语“My friend”,使译文语气更加亲切自然,很好地烘托了对话的情境。
从诗体的角度看,理氏所译的《诗经》引言节拍杂乱、韵律全无,缺乏诗句应有的形式和美感。前两句的译文虽然句式相似,但相对应的成分长短悬殊,第三句译文则与上文明显缺乏连贯。而辜氏以类似民谣体(ballad)的形式,将三句诗译为4-3-4-3-4-3节拍的六行,句式匀称音韵和谐,使《诗经》简约而淳美的语言风格跃然纸上。此外,“美目盼兮”中的“盼”原意为“黑白分明”,理氏按字面将其译为 “The well defined black and white of her eye”,不仅缺乏美感,而且在英语读者看来可能有些古怪;辜氏则将“盼”模糊处理为“beaming”, 显得更加优美自然。总体来看,辜氏的译诗做到了“以英诗传统规范为主导,兼顾汉诗诗学元素与特征”(张保红, 2019:107)。
综观例1的翻译,理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的字面,而对文体的把握不够精准;辜译文在文学性方面明显高出一筹,可谓译诗优美如诗,译话明白如话,体现了合宜之“体”。
4.3 贯通之“气”
文章翻译学理论认为“义合”与“体合”是对翻译的基本要求,翻译的至高境界是在二者的基础上做到“气合”。“气”是中国传统文章学概念,广义的“气”可细分为“神”、狭义的“气”以及“脉”(潘文国, 2014:99-100),下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论述。
4.3.1 对“神”的把握
“神”是传统文章学中重要的概念,所谓“传神”,简单地讲就是模仿他人语气。《论语》涉及人物较多,除先圣孔子之外,孔子的众多弟子也都个性鲜明,言行独具特色。与理译相比,辜译《论语》在再现不同人物的语气方面更加传神,例如:
例2:
原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论语·先进》第十一)
划线处理译:
Tsze-Loo hastily and lightly replied...
The Mater smiled at him. (Legge, 2016:384)
划线处辜译:
“I could,” answered the intrepid Chung Yu at once, without hesitation...
On hearing this, Confucius only smiled...(辜鸿铭, 1996:427-428)
例2《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论语》中一段著名的师生交谈。面对老师的提问,四位弟子中子路最先做出了回答。原文用字“率”包含“不加思考”和“直爽坦白”等义项,“率尔而对”一般解为“不假思索地回答”。理雅各译为“Tsze Loo hastily and lightly replied”,字面较为规范,不足之处在于“hastily”给人以仓促、慌忙之感,未必符合当时的情境。辜译文将该句处理为“answered (...) at once, without hesitation”,更能够体现子路侃侃而谈的情景;又在子路的名字前增译了“intrepid”一词,向读者交代其果敢直率的性格,交代了“率尔而对”这一行为的成因。“夫子哂之”是孔子对子路言谈的反应,理译为“The Mater smiled at him”,辜译在原意“Confucius (...) smiled”外增译了“On hearing this”和“only”,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子路的观点不置一评但内心并不认同的反应,可谓神态毕现。简言之,相比理译文的规范,辜译文显然更加细致而传神。
4.3.2 对“气”的把握
在传统文章学中,“气”的本质是音义互动,即“字句和音节的调配,包括长短句的安排、散偶句的运用,以及声调、停顿的操控等”(潘文国, 2014:100)。翻译同写作一样,需要“气”的正确运用,来看下例:
例3:
原文: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第三)
理译:
...“Things that are done, it is needless to speak about; things that have had their course, it is needless to remonstrate about; things that are past, it is needless to blame.” (Legge, 2016:94)
辜译:
...“It is useless to speak of a thing that is done; to change a course that is begun; or to blame what is past and gone.”(辜鸿铭, 1996:365)
对于例3中连续三个结构相似的四字格,理译完全遵循了原文的语序,相同的句式“Things that...it is needless to...”粗看形式工整,但前两句的末尾“speak about”和“remonstrate about”均包含两个重读音节,而最后一句末尾的“blame”只有一个音节,不太符合英语中的尾重原则(end weight)。而辜译先用“It is useless”总起,后接三个不定式,句末分别为“that is done”“that is begun”和“what is past and gone”,末尾押韵而且节拍不断加长,气势不断积累并在最后一句达到顶峰,读起来一气呵成。可见辜氏对英语中“气”的把握是相当高超的。
4.3.3 对“脉”的把握
“脉”字最早见于《文心雕龙·章句》“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附萼相衔,首尾一体”(周振甫, 1986:308),说的是文章有统一的思想脉络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脉”即贯穿全文的线索和思路。《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经典,内容繁杂且篇目连续性不强,翻译时若能从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高度对文本进行宏观把握,译文便能更好地实现气脉贯通。辜鸿铭涵泳儒学多年,归国后又得大儒张之洞指授,对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因此比起理译《论语》,辜译本对文脉的把握和思想的系统解读理应更胜一筹。
从另一个角度看,辜鸿铭翻译的儒经也因追求译文整体思想的一致性、用释义的方式翻译术语而招致批评,王国维(1984:197)曾撰文批评辜译《中庸》有“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之病”。黄兴涛认为王国维的批评确有其据,但未免有失偏颇。他指出辜鸿铭在翻译某些名词时进行释义,并不纯粹是为求统一,其中还包含着辜氏对这些名词意义的深层理解;王国维并未将辜氏的翻译置于儒经西译的历史过程中,而是从自身对儒经精湛的理解出发,将辜氏译文与儒经原文进行对照,这样就难免只看到辜译的缺点而看不到长处(黄兴涛, 1995:98-99)。从历史的角度看,辜译儒经为了更好地传达经义脉络而进行释义,在当时对于儒学西传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贯通之“气”是辜译《论语》以及其它辜译儒经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义合”“体合”“气合”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内在要求,三者相互依存、协同作用,译文才不至成为原文僵化的复制品,而是成为承载原文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风貌,同时像原文一样具有独特生命力的文章。
5.结语
文章学对中国传统译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翻译学上承传统译论,其核心主张是“翻译就是做文章”(潘文国, 2017:442),这一创新的思想将“文章”的概念从一种语言和文化延伸到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拓展了我们对翻译本质和原则的理解,也敦促我们思考如何重新理解翻译、理解读者和译者。概而言之,翻译是用目的语及其文化重新书写原文,译作是一种特殊的文章;译作所面对的并非源语人群,而是目的语人群,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译者游走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不但起到媒介的作用,而且是一位特殊的作者,其译法和笔法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成败。
辜译《论语》体现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章学思想,带给我们诸多启示。首先,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知己知彼, 采取比较视角,才能作好翻译这类特殊的文章;其次,对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感同身受,并努力扫清障碍、架设桥梁,才能最大限度争取目标读者;最后,以整体观念来重塑文章“义、体、气”,才能用异国的文字还原中国文化典籍的灵魂。辜译《论语》体现了春秋之“义”、合宜之“体”和贯通之“气”,历经百余年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论语》译本之一。文章翻译学研究方兴未艾,正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之中。以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支撑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体系,必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强大助力。
注释:
① 全文示例中的《论语》原文均选自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译注简体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