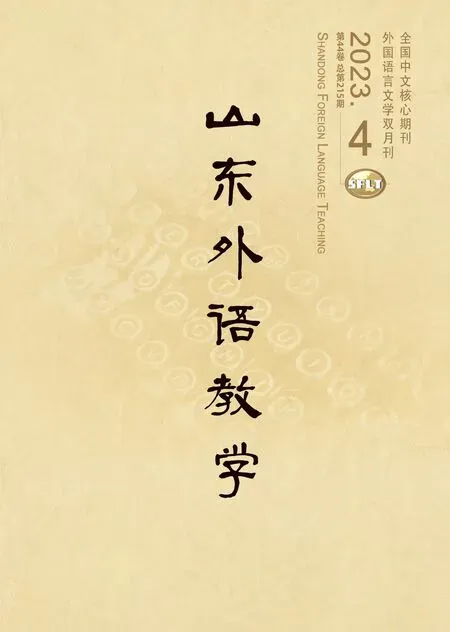文章翻译学的源与流
2023-03-01冯智强
冯智强
(天津外国语大学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天津 300204)
1.引言
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经历了“西化”洗礼,如今已经很难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翻译研究亦未脱此劫,西方译论叠进,本土译论倍受冲击。西方翻译理论虽为解读纷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诸多新颖视角,但其见解与观点多围绕印欧语间的转换展开,对于类型迥异的英汉语间的翻译,则仍显解释力不足。返观本土译论,面对西方译论的“虹吸效应”,许多宝贵的本土翻译思想和材料都被简单地归入了西方的译学体系,进而简化为“直译”“意译”之分,或是“归化”“异化”之别,甚至成为西方译论的附庸,令人扼腕。
事实上,我国既有源远流长的对外交流,又有成果丰富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有如“文质”之争和“信、达、雅”等关于翻译的思辨论述。当下若能总结前论,去芜存菁,完全可以产生起源于本土、应用于实践、凝华于理论的中国本土译论。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就坚信“我国两千年翻译实践中能提炼出大量的翻译思想”,并呼吁“如何将这些思想理论化,是我们这些后人需要系统化的内容”(张汨,2020:4-5)。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以中国之力推动国际译学的发展,已成为翻译学界的共同呼声。21世纪初,基于对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学、特别是翻译学等领域多年的实践与思索,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理论长期的涵泳,著名语言学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先生首倡文章翻译学。创建源自中国传统译论的本土翻译理论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翻译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学术创新的宗旨。倡导者(潘文国,2013)深信,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建设既可以有助于解决翻译领域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也可以回答中国翻译学发展前途的问题。
2.文章翻译学创立的背景:文化自信觉醒后的学术自觉
2.1 打破“以西律中”格局,促进译学良性发展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多以西方为圭臬,理论先行,削足适履。许多讨论主要还是围绕“信、达、雅”“直译”“意译”以及“归化”“异化”进行,有的研究甚至对于这些范畴的真正意义尚未搞清楚。学术的正常发展至少应该是中西方理论相互影响、取长补短,而非“一边倒”。只有打破这种失衡格局,才能真正促进译学良性发展。
2.2 建立平等对话机制,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抑或翻译学的中国学派,不但可以尝试解决中西互译的现实问题,还可以为国际译学多样性做出贡献。理论是由术语构成的学术体系。因此术语的创生尤为重要。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众多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术语诸如“信、达、雅”“文”与“质”被误解、歪曲和异化。一味追随西方译论概念,便难以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更不能奢望理论系统的形成。中国有着极具特色的语言和文化,更有着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和丰富的译学资源。之所以没有产生西方学术意义上的长篇大论和所谓系统化、理论化的翻译学,主要是由于东西方的认知维度和表述方式不同。有着多年对外翻译与传播经验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今天,我们需要澄清误解,需要讲清楚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传播中国文化、进行国际舆论斗争”(王晓辉、曾佳宁,2022:2)。努力发掘本土资源,积极吸纳西方学术方法,发扬中国特色优势,建立起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不但必要,而且可行。
2.3 突破中西交流壁垒,走出汉英互译困境
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差异巨大,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民俗传统等颇为不同。从语言类型学而言,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和屈折语的英语分属汉藏和印欧两大不同语系,类型上的差异使得这两种语言间的跨语系转换成为复杂的世界性难题。以印欧语系内部诸语言转换为基础的西方译学,在指导和诠释英汉汉英翻译时往往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因此,建构有汉语与汉文化参与,以汉英、英汉之间转换为基础的译学理论迫在眉睫。无论普通语言学还是普通翻译学,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其加盟和融入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但是汉英翻译实践的需要,更是突破中西交流壁垒的需要。
3.文章翻译学创立的基础:古今中外碰撞出的智慧思辨
3.1 文章学传统的延续
文章在中国自古便被视为“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曹丕,2013:176),文章学发达且历史久远:从发轫先秦并成型两汉的训诂章句之学、六朝的辞章声律之学,到隋唐的注疏之学和宋元的圈点之学,再到最终完成于明清的评注之学。“文心”“文则”“文镜”“规范”“通义”等文章学概念被秉承数千年,文体、文道、文风、文气等也是文章学不断探讨的命题。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更是文章学的集大成之作。中国传统译论与文章学相伴相生,从汉代佛经翻译到严复的西学翻译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思想,概莫能外。发轫于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实践活动,通常是胡僧口授、华僧笔受的中外合作方式,精力主要集中于译文润色加工,注重译文的质量,并由此出现“文质之辩”,做翻译此时已是在做文章了。文章翻译学正是发轫于这些传统译论,这也应该成为文章翻译学秉承的特色。正如潘文国先生强调,特色是“特点+优势”,不是自外于一般理论,而只是更强调发掘相关的特点和优势(王宇弘、潘文国,2018)。
3.2 中西互译与交流的需要
《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西方以语法为中心,重口语、建理论、轻实践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语言学乃至翻译学等领域。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比之印欧语内部诸语种间更为复杂,这也必然反映在翻译理论上来。如果说描写翻译学尚可以对翻译现象进行分类、分析和研究的话,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特别是典籍外译则越发无能为力了。中西译论有着不同的理论形态,中国自古以来有重文章、重书写、重修辞的传统,与此相应的中国译论走的是一条人文主义的路线,这与西方译论所走的技术主义路线大不相同(潘文国,2014)。中国的典籍几乎都是经典美文,关于美文的翻译显然不只是达意那么简单,因此这种“美文需美译”,即文采问题,只有文章翻译学才能够有望得到解决。由此,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西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构建具中国特色的本土译论的同时,也弥补了国际译学在汉外译论层面的不足。
3.3 翻译学发展的趋势
随着中西互译翻译实践的不断推进和翻译空间的不断拓展,不断拓展的翻译活动需要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的重新审视以及中西翻译理论比较之中,文章翻译学逐渐孕育生成,其优势也已得以彰显。基于文章学概念的翻译理论及实践,有助于外译中和中译外的双向提升。将译者即作者、翻译即是做文章的理念带入翻译的全过程,既是理论上的突破,也是实践上的解放。
4.文章翻译学建立的途径:“道器并重”理念下的译写合一
4.1 重释“信、达、雅”
根据潘文国先生的研究,“信、达、雅”并不是翻译的标准,而是做文章的标准,是文章学的要求。“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这里严复是将“文章正轨”借用作为“译事楷模”(潘文国,2014:94)。文章学翻译学正本清源,消解长期以来学界对“信、达、雅”的误解,倡导“翻译就是做文章”,要用做文章的方法来对待翻译,指出其第一要义是“信”,强调文章的地位和对文章的态度,即对翻译事业高度的责任感。第二要义则是“达”,是思想或内容得到充分的表达,即达意,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而第三要义“雅”,则是强调文章要有文采,有表达力,文字当求尔雅,否则不能传远,这是对翻译的极高要求。严复的“信、达、雅”是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人品、翻译过程、双语素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对翻译要素的整体观照,是集责任意识、读者意识、审美意识于一体的翻译哲学。另外,争论了几千年的“文质”问题其实是直指文体问题,即文章风格的雅驯与质直问题,而西方译学中的“直译”“意译”讨论的却是翻译方法。“文质”与中国文章学传统一贯注重的“文采”息息相关,将其类比于“直译”“意译”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只有为“信、达、雅”“文质之辨”正名,还原其本义,打破“以西律中”的惯性思维,立足本土资源,打通古今学术,会通中西译学,重新建构中国翻译话语,才能逐步建立翻译学的中国学派。
4.2 再现“义、体、气”
如果说“信、达、雅”属于“道”的范畴,那么“译文三合:义、体、气”则属于“器”的层面。根据潘文国的研究,译文和原文要在三个方面做到“相合”,即“义合、体合、气合”;从译者角度做到“三传”:“传义、传体、传气”;而从读者角度(即批评标准)则有“三品”:“品义、品体、品气”。原文与译文关系中“义合”是最低要求,“气合”则是高要求(潘文国,2014:95)。进而言之,“义合”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图和主旨上的契合,是文义方面切合题旨与立意;“体合”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是文序、文声、文体、语辞层面切合题旨与立意;而“气合”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脉上的契合,是文情、文势、文品方面切合题旨与立意。既然翻译是创作、是做文章,那翻译就是一个创生过程,这就意味着翻译的标准要具有有机、整体和动态的生命观。文章翻译学以全息视角综合考量译者的创作动机、译者素养及其对“义、体、气”的整体把握,使翻译批评变得更加立体、丰富和全面。“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在跨语际层面的传承和发展,是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的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要求。可以说,“三合”既是具体的翻译标准和原则,又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法。
4.3 践行“三位一体”
当今学术的发展,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人云亦云,唯西学马首是瞻,更不能极端地厚今薄古或是厚古薄今。为此,潘文国先生提出了古今中外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发展之路,即“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赵国月等,2017:11),认为首先要从改变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态度,改变一味不遗余力引进,不加鉴别和检验照抄照搬的局面,改变以往“格义”式的研究方法,避免西方概念先入为主,而要以传统译论为本体,努力挖掘其本身内涵。然后再与西方译论相比较,互相阐发与融通。只有基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翻译实践,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派。
5.文章翻译学的主张:从人文合一到译文三合
5.1 重人品(信):为人先于为译
中国传统译论建基于文章学,强调为人和为文的一致性,即为人先于为文,人文实为一体。面对技术理性的泛滥和工具理性的扩张,翻译的人文价值受到空前的挑战和侵害。中国几千年的文章学传统强调做人和做文的一致性,正所谓“道德文章”要求先有道德,后做文章。由此而论,“信、达、雅”要求译者必须做到“德、学、才”兼备(潘文国,2014:95)。文章学翻译学正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其翻译标准就是在实践和评价上贯注人文精神。
5.2 重辞达(达):“译文三合:义、体、气”
“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的高标准,而针对具体的翻译实践即语言转换和文化传译,文章翻译学提出了“译文三合:义、体、气”(潘文国,2014)。之所以如此重视“合”,强调译文与原文的相合与对应(correspondence)和匹配(match),而不是“逐字死译”(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正是为翻译过程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法和执行标准。
“义合”要求译文与原文在字、辞、句、篇各方面的意义必须相合,强调的是两种文本在客观意义而非主观意义上的“合”。这里的“义”可以具体化为“字辞义”“组织义”和“系统义”,主张原文的每一个字的轻重、雅俗、古新、褒贬等在译文中都要力争做到灵活照应(潘文国,2014:96)。“体合”重点强调的则是形式。只有内容的翻译,没有形式的转写,其实不是完整的翻译。“体”首先指“文体”,但又不囿于“文体”。翻译中的合“体”,要求形式相应,也就是诗要译成诗,词要译成词,辞赋、骈文的特色在译文中都要有所体现。对于中国古代文章的翻译而言,只要掌握其四大要素,即“韵、对、言、声”,“体合”也不难做到。
“气合”则是文章的最高要求,可以统合“义合”与“体合”,产生灵动的翻译效果。“气”是文章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历代文章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和自我修养的手段。中西互译特别是中译外同样也应该传递原文之“气”,在目的语中以适当的形式予以表现,作为翻译的崇高追求。“气”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中国文章学的灵魂,主要是指音节的调配与句子长短的安排,也就是注重“音义互动”的汉语的基本规律。文章翻译学认为可以从“神”“气”“脉”“味”四个维度进行把握。而西方人写文章必然同样讲究节奏、韵律和写作技巧,也有其“行文之气”,这是实现“气合”的基础,这一点中西相通,可以实现对接。
5.3 重文采(雅):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从文章翻译学的角度,翻译就是做文章,一切文章都要讲究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时刻提醒我们,文采是文章的要素。中国的文章,上至诗词歌赋、下到公函奏折,无一不注重行文的文采,从内容到形式,从韵律到节奏,从平仄到声调,从风格到修辞,都有美的要求和标准,否则难以称文。从整体出发,反对人为过度割裂,这不但是对内容本身的要求,对文体风格亦是如此。
6.文章翻译学的贡献:还原翻译的本来面目
6.1 突破了翻译与创作的边界
文章翻译学重新思考和界定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及其相关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就是做文章”,这是文章翻译学的基本精神。既然创作通常是通过创造性书写以生成一个新的意义空间,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创造性活动,那么翻译必然具有创作的普遍特点,因此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这种书写行为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由此译者主体性便会得到最大的发挥,同时读者期待也会得到最大满足。这是中西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创见,必将带来翻译理论与实践上革命性的变革。
一种新理论要能够看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解释他人不能解释的问题(冯智强、潘文国,2022:98)。从文章翻译学出发,有望继续提高翻译的地位。一直以来,翻译始终被视作为他人做嫁衣的雕虫小技,翻译得好,是原作者之功;反之,则是译者之过。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高度,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翻译的创造性和复杂性,从而纠正以往对待翻译的不公平的看法,进而提高翻译的质量,加深翻译的研究。同时,修正对翻译的成见,增强了译者主体性,也极大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6.2 打破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藩篱
传统的中国文学只有散文与韵文之分,而文学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分乃是外来的分类标准,这的确给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同时也导致了诸多问题,尤其是使得文学翻译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蜡,甚至佶屈聱牙。文章翻译学倡导翻译就是做文章,具有超“文学”性和超“语法”性(潘文国,2012),并不做文学和非文学的严格分,主张一切文章皆需具有文采,这会给当下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枯燥无味的行文风格和令人乏味的表达方式带来革命性的生机。同时,文章翻译学也告诉我们,中国传统译论中原本就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所谓非文学翻译的论断与思想。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译论本来就是面向所有一般翻译现象和问题的,并非只是针对文学翻译。例如严复的翻译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政法、经济学等社会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这同时也昭示出,严复的主要翻译思想并不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
6.3 搭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以往从西方引进的翻译理论在描写和解释中西翻译活动时,经常会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隔膜,而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又会出现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和针对性不强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长期以来对“信、达、雅”的误解,又造成了大量中国本土翻译资源的误用与遮蔽。文章翻译学的出现,可以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作为“道”的“信、达、雅”是更高层面的翻译哲学;作为“器”的“义、体、气”是指导翻译的操作性指导原则,二者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又相互观照。这样,既有形而上的纲领性理论指导,又有指导具体翻译实践的操作原则和标准,由此文章翻译学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了会通的桥梁。由此,文章翻译学既突破了古今中外的界限,又打通古今学术,会通中西译学,使传统走向了现代。同时也突破了译入译出的界限,使得典籍外译和美文中译也有了彼此对话的可能。
7.文章翻译学的展望:从理论、实践到道器合一
7.1 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文章学视角下,出于对文本生命的尊重和体悟,对译者与原文的关系有了新的喻义,如若即若离关系、对话交流关系、交互作用关系、各美其美关系等,译文作为有机整体而自然地保持。这些全新概念和领域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挑战,从而填补了翻译理论,特别是中西互译领域的空白。同时,必须考虑文章翻译学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其是否受语种的限制,以及该理论解决的是具体哪个翻译层次、哪些方面等重要问题。
文章翻译学发展与译介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核心概念怎么翻译,源自中国的概念如何与西方的(所谓现代的)学术对接,如何使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人接受,以及如何使已经丧失传统、文化自卑的国人认同和接受等问题,也是接下来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7.2 应用领域尚需拓展
文章翻译学倡导在充分传达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写出具有文采的文章,上至文学作品、名著典籍,下至应用文体、日常表达,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从而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进而,文章翻译学会通了中译外和外译中两个不同的翻译方向。严格说来,中译外和外译中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信、达、雅”的重释与“义、体、气”的提出却使我们看到了彼此会通的可能。潘文国多年来“典籍外译”和“美文中译”的实践以及张德让(2019)对严复《原富》翻译的文章学研究,冯智强和庞秀成(2019)对林语堂“创译一体”著译作品的文章学解读,林元彪(2019)对语言科技时代翻译人文任务的文章翻译学诠释,李志强等(2021,2022)将文章翻译学用于《尔雅》外译的研究,都进一步证明了文章翻译学的解释力与可行性。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文章翻译学的原则推广到更广阔的翻译实践与研究领域。
7.3 理论与实践需要进一步紧密结合
近年来,翻译研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译论潮水般涌入却难以真正落地,中国译论博大精深却难以把握。英汉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给英汉互译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为习惯以印欧语系内部诸语种翻译立论的翻译理论家提出了难题。西方的学术一般有严格理论与实践之分,而中国的道器合一、情理互通可以使译论与实践融通相辅、相得益彰。文章学翻译学的问世,给译界带来了新的生机。用写文章的态度对待翻译可以还翻译学以人学。这个承继传统、源自实践的指导思想会使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标准、认知过程、翻译单位、译者地位、译者素养等一系列翻译理念发生改观,而文章学的概念如文资、文意、文序、文境、文色、文声、文势、文术、文品、文体、文病等在这一过程中都会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以“义、体、气”为基本维度的生命有机论也会为翻译学突破语言学这一基础框架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为翻译学提出新的课题,带来切实可行的操作标准,从而使相关翻译理论更具解释力,更有可操作性,进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密。
8.结语
文章翻译学为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其思想、原则和方法既可以具体化到字、词、句、篇,又可以指导立意运思、谋篇布局、辞采风骨等诸多领域。文章翻译学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翻译,重新审视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策略以及认知过程等,这对于翻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义、体、气三合”的提出更是对翻译实践有着具体的指导作用,使得翻译实践有了有效可行的抓手。更为重要的是,文章翻译学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中国话语的翻译学,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价值,特别是重振了翻译学者的士气,重拾了人文学者治学的信心,有望为中国的学术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