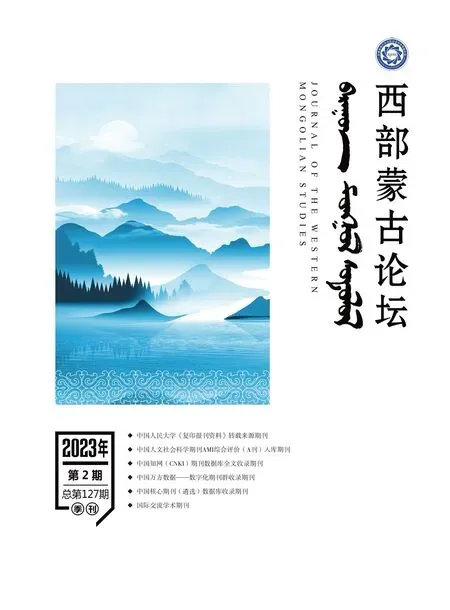红枣何以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的“德吉”*
——基于饮食人类学视角的解读
2023-02-28乌日格木乐查苏娜
乌日格木乐 查苏娜
(1.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8;2.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内容提要] “民以食为天”,食物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前提,不仅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文章通过田野调查资料,结合饮食人类学理论,展现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红枣被作为“德吉”这一现象,并分析隐含于红枣当中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社会文化,从而阐释关于红枣如何作为“德吉”的文化结构和符号象征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物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前提,不仅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透过食物这面“镜子”可以映射出当地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变迁过程。
一、饮食人类学研究综述
饮食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Food)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利用人类学理论与视角对某个族群或某一地区的饮食文化、饮食行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饮食人类学的视角也是一种文化视角,即饮食习惯或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表达,透过饮食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生态、礼仪和习俗等方面,从而进一步研究其文化特征。
在西方,饮食人类学研究历史逾百年,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①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第48页。。最早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追溯至1888 年由人类学者马勒里(Garrick Mallory)在《美国人类学家》发表的《礼仪与进餐》一文。①巴责达、张先清:《回顾与反思:近二十年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评述》,《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7期,第72页。之后,博厄斯等早期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对“异域他者”的饮食文化、食谱作了详尽的记录。而现代饮食人类学则以20 世纪50 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者对食物的社会意义研究为开端。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自然物种被选择作为食物,不是因为它们是“好吃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好想的”,因此被定义为是文化唯心主义的解读。②〔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4页。20世纪60年代后,人类学者道格拉斯通过《洁净与危险》一书,认为人类学家研究饮食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解码它们所包含的神秘信息。20 世纪80 年代之后,西方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延伸至更大的社会领域,比如政治经济价值的创造、象征价值的建立以及社会对记忆的塑造。③Sidney W.Mintzand Christine M.DuBois,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Eating,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31, 2002,p.99.饮食人类学相关理论日趋成熟。
在我国,饮食人类学尚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将西方饮食人类学理论进行梳理并引入中国饮食的是中国香港人类学家吴燕和教授等。随后,中国台湾学者创办的《中国饮食文化刊物》成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国内早期的饮食人类学主要以介绍西方饮食人类学理论、翻译相关研究著作与文献为主。2000 年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具体饮食行为进行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如,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撰写的文章《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④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92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志扬《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人类学调查》⑤刘志扬:《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第108页。、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⑥郭于华:《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萧家成研究员的专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⑦萧家成:《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33页。,以及其他学者针对土家族饮食、客家饮食、川菜、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等研究对象的专著与论文。2013 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彭兆荣教授出版的饮食人类学著作《饮食人类学》⑧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标志着中国饮食人类学逐渐成熟。
本文以饮食人类学为视角,对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红枣进行了研究,尤其关注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取食系统”。取食,即在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中哪些植物、动物被选择成为食物。当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生态关系之后,便会衍生出人类与食物之间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伦理。⑨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第48页。因此,探索鄂尔多斯蒙古族就地取材红枣所创造出的独特饮食文化,可以呈现文化如何对红枣赋予意义,进而发展成为当地蒙古族的地域身份。
二、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红枣研究的缘起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毗邻陕晋宁三省。其中,距离陕西省榆林市仅有150 公里。鄂尔多斯市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鄂尔多斯市生活着4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89.34%,蒙古族人口占9.67%,蒙古族人口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90.76%。鄂尔多斯蒙古族作为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习俗。了解和分析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特色文化,对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往研究中,关于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服饰、民歌、婚礼、祭祀仪式等内容的学术成果颇丰,被人熟知。
笔者之所以关注红枣与鄂尔多斯饮食文化,缘于笔者近两年春节前往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拜年期间,无意间发现红枣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新年仪式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家家户户待客餐桌上的奶食摆盘里必有几颗红枣;每个走访亲友携带的伴手礼(盒)上放有几颗红枣;在邀请客人品尝“德吉”①“德吉”为蒙古族的一种传统礼仪,主要表现为:在重要节日或场合用餐时,会向宴请的客人或家中的长者献上食物中最尊贵的部分,即“德吉”,在献完“德吉”后即可开始用餐。的时候也是吃一颗红枣。于是,笔者开始对其他旗县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展开访谈,发现红枣的确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生活中,尤其是新年仪式、献祭礼仪中十分重要的食物,甚至具有相当于蒙古语语义中“德吉”的高尚含义。
然而,笔者在尝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除了红枣种植相关的农业经济发展类研究文献以及鄂尔多斯蒙古族研究文献中将红枣作为“既定”的民族风俗描述之外,暂无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探讨或研究。此外,笔者进行访谈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无论长幼都十分认同红枣是其饮食文化中重要的元素,但对“如何成为”的过程无从了解。这激发了笔者浓厚的研究兴趣。
因此,本文通过展现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红枣被作为“德吉”这一现象,尝试对当地蒙古族民众对这一饮食文化现象的解释进行阐释,从而分析隐含于红枣中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及其关于“德吉”文化结构和符号的象征意义。
三、“德吉”与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的红枣
(一)德吉的涵义
“德吉”在蒙古语中有着深远的内涵。根据蒙古文字典的释义,“德吉”具有如下含义:1.新年献祭的食物或是为尊贵的人②这个人可以是家中的长者、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或是客人中辈分或岁数最大的人。分享的食物,如酒的德吉、奶食的德吉、茶的德吉。2.作为一种礼仪,有若干种动作过程,如尝德吉、献德吉、要德吉等。3.形容事物里最好的部分,同汉语中的“上等”或“圣洁”。③朝日格图、乌云塔娜主编:《现代蒙古语解释词典》(双色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5页。
可见,用来献祭的食物只是德吉的本意,而在蒙古族礼仪文化语境中,“德吉”具有分享福分、供奉圣洁之物的涵义,是一种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因此,红枣在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更多的是扮演着这样的意义和角色,而并非作为“德吉”本身。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二)鄂尔多斯蒙古族节日习俗与饮食文化中的红枣
鄂尔多斯蒙古族沿用夏历,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小年、除夕夜和新年。红枣在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通过以下重要节日习俗得以体现。
(1)小年祭火仪式中的红枣
我国蒙古族与汉族及其他大部分民族一样,在春节前夕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小年对蒙古族尤其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来说,又被称作“祭火日”(gal tahilgnn-uedu) ,具体以祭祀火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只是各地祭火时间有的是腊月二十三,而有的是腊月二十四。祭火日这一天是送火神(也叫灶神)归天欢聚和上报人间事务的日子,腊月二十三到大年初一接回火神的日子称为“无神七日”(ejegui dologon honog),他们认为火神是保佑香火、守护一家人平安的神灵,所以过年前的七日需格外小心,忌出远门、宰牲畜和借债等。
相对其他地区而言,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祭火仪式十分隆重。在祭火日当天要制作祭火饭(gal-un budag-a),它是祭火时用的献祭品。具体做法是:牛羊胸叉骨加上酪带子(鄂尔多斯地区的一种奶酪)、红枣、葡萄干等煮好后,捞出胸叉骨,肉汤里加小米和大米煮熟。进行祭火仪式时,选出一整块胸叉骨,削掉肉露出骨架,用细毛线连接胸骨柄,然后用五色纸、五色丝线、五色绸布、五色纸、艾蒿、香烛、哈达等装饰后,上面放几颗红枣并在炉灶里焚烧供奉给灶神。老年人把祭火饭里的红枣称作“红色的土牛”(ulagan biruu),寓意为牛羊乃至所有畜群的福泽。
(2)除夕夜仪式中的红枣
除夕夜里,鄂尔多斯蒙古族也会包饺子,寓意为团团圆圆。包的饺子里除了硬币以外还会有红枣、盐、炒米、茶叶、酪带子。如吃到硬币寓意新的一年财源滚滚,若吃到红枣寓意畜群膘肥体壮,吃到盐和茶寓意丰衣足食,吃到炒米寓意五谷丰收,吃到酪带子寓意奶食充足,或白色寓意着一切平安吉祥。
除夕夜天黑之前,鄂尔多斯蒙古族会往家用水井里放两颗红枣并盖上井盖,正月初一太阳升起来后再打水(有些旗是正月初一早晨投放红枣),这种献祭仪式寓意为感谢大地提供源源不断的井水,用蒙古语叫作gajar usu tahihu。
(3)新年仪式中的红枣
鄂尔多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应该是每家房屋或蒙古包外竖立着的一根或两根旗杆,旗杆顶端迎风飘扬着印有骏马图的布幡,这是象征成吉思汗军徽神祇的玛尼宏杆,是鄂尔多斯蒙古部的古老习俗之一。①巴音道尔吉:《鄂尔多斯玛尼宏杆的祭祀习俗》,《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212页。“玛尼宏”译自蒙古文中的“hei mori”,意为天马、神马。玛尼宏杆被当地人称之为“桑更苏日”,在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庭的重大节日,尤其是新年仪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鄂尔多斯蒙古人一般寅时起床(通常为凌晨四点钟),换新装、洗漱完毕后,天亮前(卯时)在玛尼宏杆东南方干净的地方燃起篝火,篝火用的木柴为除夕那天男主人背过来的干蒿或干枯的沙柳。这种篝火被当地蒙古族称作珠喇火(zula-yin gal),有些文献资料也称作点天火。火旺起来后,顺时针方向围着篝火转三圈,再加木柴。然后在玛尼宏杆北边跪拜天地,东、南、西、北等四个方向顺时针方向各叩拜三次。然后取若干种食物放置在小勺中制作“德吉”进行献祭,这些食物有除夕夜煮好后开餐前盛出来若干个放在高处的饺子,还有红枣、月饼、馓子等,再加上一点未放盐调制的奶茶,将其往东南方向高过头顶祭洒。这个仪式,有些地方是在篝火里焚烧用以献祭的德吉,如酒、牛奶、肉、红枣、糖果等。玛尼宏杆仪式完毕后,回到屋内向着家中的炉灶三叩首,意思是接回腊月二十三祭火后上天的灶火神。
接下来举行家人之间互相拜年的仪式。晚辈请长辈上座,然后双手递奶食“德吉”(当地人称hqagan idege amsahu),接“德吉”的人需要坐着双手接。通常这种“德吉”为小杯子里盛的酥油,有时酥油里还会放一颗红枣,现在大部分地区用木碗盛酪带子。献“德吉”的仪式按照辈分和年龄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人品尝完毕后将“德吉”放回桌子,然后进行哈达和鼻烟壶交换仪式。这种家人之间拜年的仪式同样适用于前来拜年的客人,是客人与主人之间首先要做的仪式。
从鄂尔多斯蒙古族待客的讲究来看,该地家家户户餐桌上用馓子、奶食、糖果等叠放的摆盘上一定会有红枣。其中,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的蒙古族民众通常制作红枣馅儿的酥饼或用炒米拌酥油、红枣和葡萄干做出象棋状的团米招待客人。
此外,过年期间走访亲友的伴手礼会放两颗红枣来充当德吉。礼盒出现前,杭锦旗地区最古老的拜年方式是携带六个圆饼,上面放一颗作为德吉的奶食和几颗红枣,这种“德吉”被称之为dog。在拜年后将其带走,继续给下一家拜年。同时,拜年时会给儿童分发装有红枣、糖果、苹果、月饼等的包裹,叫作给孩子的伴手礼。
(4)婚礼仪式上的红枣
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婚礼仪式非常隆重,有着许多重要的环节和流程。其中,宾客给举办婚礼的主家献伴手礼的时候(蒙古语称之为saw talwah),宾客会向主家要一个盘子,在盘子底部放一块砖茶,上面叠放六个圆饼,顶上放置“德吉”,德吉旁边放两颗红枣。对现代鄂尔多斯蒙古族来说,伴手礼已经演变成其他的礼盒或者物品,但是六个圆饼、德吉和红枣是不可缺少的。
(三)红枣作为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德吉”
正如蒙古文字典中所解释的,本文阐释的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中的“德吉”有两层涵义。首先,“德吉”是食物本身,如用来献祭的食物,给长辈或客人首先品尝的食物。在有些地方用来作为“德吉”的食物是固定的,可能是奶食,而大多时候任何食物都可以作为“德吉”,通俗来说就是分享食物的第一口或是最珍贵的那部分。而本文侧重的是“德吉”的第二种涵义,即被赋予圣洁的意义之过程,如红枣如何被作为食物中的“德吉”。
(1)在“德吉”的旁边
在上述的节日礼仪中,红枣大多时候出现在“德吉”的旁边——这里的“德吉”是真正作为“德吉”这个物的本身,是名词意义的“物”。例如,鄂尔多斯蒙古族在祭火仪式中用各种食物制作的“德吉”(饺子、红枣与无盐奶茶),或是大年初一拜年时用的“德吉”(小杯子里装的酥油,有时酥油里还会放一颗红枣),结婚仪式及其他场合中的“德吉”(六个圆饼上放奶食及其旁边的红枣)。可见,这些通常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吉”,往往有红枣。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我虽然不是德吉,但我必是德吉旁边的红枣”,用来形容在某个过程中虽然不是主角但一定伴随在主角旁边,抑或是形容人们之间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感或义气。通过这样的民间俗语可以看到,红枣在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承担着“在德吉的旁边”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
(2)作为“德吉”
在鄂尔多斯蒙古族重要的节日礼仪中,可以看到红枣出现在腊月小年和正月大年初一祭祀的仪式中,出现在伴手礼盒上,会为祈福投放到家用的井水里,也会成为当地民众待客食物中所迭用的重要食材。可见,相较于是否真的被作为“德吉”,更重要的是红枣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表征着鄂尔多斯蒙古族对传统仪式的重视,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尊重长者、重视客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风俗。
四、红枣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德吉”的几种解读
饮食人类学探究的是食物之所以成为文化象征的过程,正如红枣如何成为鄂尔多斯饮食文化中的“德吉”,是一种意义被赋予的过程。因此,要解读这个过程,首先应分析鄂尔多斯蒙古族与红枣二者背后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以更有效地解释该地区蒙古族饮食行为与饮食现象。
(一)自然生态环境
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鄂尔多斯通常被誉为“三面黄河一面城”。具体而言,鄂尔多斯东、西、北等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与黄土高原相连,其地貌环境以北部黄河冲积平原、东部丘陵沟壑区、中部库布齐沙漠与毛乌素沙漠、西部半荒漠草原为主要特征。正是这种盐碱地、沙地的土壤性质,造就了鄂尔多斯地区红枣种植业的发展空间优势。从经济效益、生态保护等角度来说,枣树是落叶乔木经济林树种,不仅生态适应性强,具备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性能,而且营养价值丰富,具有食用、药用等经济价值,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营造林的先锋树种。①卢立娜、高崇华、贺晓辉等:《鄂尔多斯地区红枣引种及开发利用现状》,《防护林科技》2016年第4期,第99页。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政府大力发展枣树种植业,尤其以蒙枣科技等企业打头阵,在乌审旗毛乌素沙地发展生态枣业,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据鄂尔多斯市政府数据统计可知,目前已在全市9个旗区推广种植3万多亩,枣树成活率均在90%以上,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水平。②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沙漠上建枣园的敢为者》,网址:www.moa.gov.cn/ztzl/scw/cyrhnc/201803/t20180301 6137713.htm.
(二)红枣种植历史
我国是红枣的原产地,占世界分布总量的90%,种植历史已有3000 多年,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药食文化和风俗习惯之中。③刘孟军:《中国红枣产业的现状与发展建议》,《果农之友》2008年第3期,第3页。《本草纲目》记载,红枣具有“润心肺、止咳、补五脏、治虚损、除肠胃瘅气”之效④蔡健:《大枣的营养保健作用及贮藏加工技术》,《中国食物与营养》2004年第9期,第16页。,我国人民历来把红枣视为馈赠亲友的滋补佳品。2011 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力德苏木首次引进红枣这一经济林作物,小面积尝试种植,获得了较好的效益,此后陆续成立了乌审旗顺达红枣种植专业合作社、毛乌素枣业研究所、乌审旗内蒙古蒙枣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蒙古族关于红枣作为“德吉”的记忆非常久远,早已成为当地蒙古族民众的一种传统。
(三)社会文化与红枣的溯源
笔者在访谈田野调查对象过程中发现,鄂尔多斯蒙古族民众虽十分认同红枣在上述仪式中的角色,却对红枣出现在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的历史及其原因都无从得知。因缺乏相关文献资料,暂且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自然生态环境是根本原因。如上所述,鄂尔多斯地区多为沙地,不适宜种植瓜果蔬菜,因此,在过去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民众饮食结构相对单一。众所周知,鄂尔多斯距离榆林市只有150 公里,而榆林是我国著名的红枣产区。根据记载,榆林有3000 多年的枣树栽培历史,并且现存有1300 多年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枣树。⑤郭瑞霞:《榆林市红枣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科技信息》2011年第26期,第343页。榆林12 个县均有枣树栽植,总面积达170 万亩,约占陕西省的75%,全国的10%。其中吴堡县、佳县、清涧县等地的红枣种植历史尤为闻名。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的《吴堡县志》有“枣甚盛”“枣为多,居民以此为业”的记载①引自吴堡县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8 月26 日文章《吴堡县获“中国药枣之乡”称号》,网址http://www.wubu.gov.cn/xwbd/tbyw/58230.htm.。据清代《清涧县志》记载,历史上自店房坪直抵黄河,百里都是枣林。该县老舍古乡王宿里村有一株古枣树,据测定树龄有1000多年,是著名的“红枣之乡”。红枣作为草原上少见的食物,因“物以稀为贵”而成为蒙古族招待贵宾或是献祭的“德吉”。这便是本文所强调的红枣作为“德吉”并非“物”本身,而是象征着珍贵的意义之所在。
其次,在特有的社会文化中被赋予意义。鄂尔多斯蒙古族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献“德吉”礼仪就是一种尊敬长辈、厚待宾客的体现。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红枣恰巧因其珍贵而被赋予了“德吉”的身份。因此,作为“最好的食物”出现在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仪式上,或是招待客人的餐桌上——以祭火饭、红枣馅酥饼、炒米拌红枣等形式。更进一步变成了一种吉祥的祝愿,如伴手礼上的红枣。田野调查受访者对红枣的寓意有以下几种解读:红枣在鄂尔多斯部分地区蒙古语方言中被称之为“红色的牛”,寓意着五畜丰盈;饱满的形状和鲜艳的色泽寓意着圆满与红红火火。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中流传着一个关于红枣的谜语——“肚子里长着骨头的羚羊”(Yangir imaa yasan gujeetei),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人自幼耳熟能详的。羚羊生活在高岩上,是珍贵的动物,未被人驯化过,是神秘的自然神灵(nawtagsawtag)般存在。在《山海经》中《西山经》提到的麢,就是羚羊,而羚羊也常出现在北方民族的神话传说里。因此,把羚羊的毛肚比作红枣的核,这谜语背后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把红枣看作自然神灵一样崇敬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鄂尔多斯蒙古族社会文化与红枣的深远联系。
五、结 语
食物体系是一种对物质生存的选择体系,也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的合作体系。因此,选择食物不仅是一种认知过程,也是一种再生产模式。鄂尔多斯蒙古族的饮食文化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也承载着他们深厚的社会文化。本文在解读红枣如何及其为何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中“德吉”的过程中,以饮食人类学为视角,阐释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社会文化与红枣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红枣产于榆林,传播至鄂尔多斯地区,发展成为具有特殊的族群或地方文化象征的意蕴,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鄂尔多斯文化赋予红枣文化象征意义的过程。这是“物”与文化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