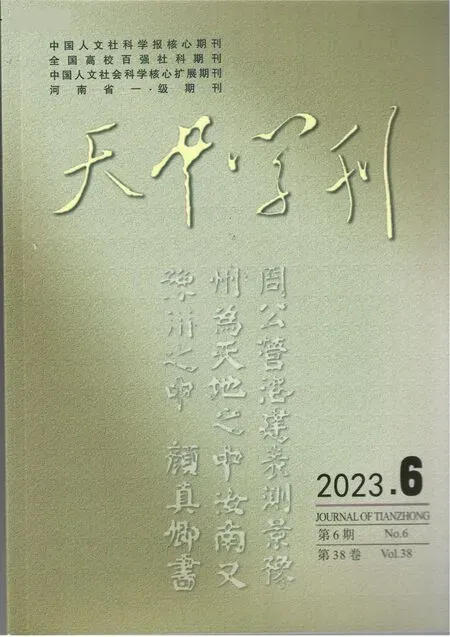论赋体因素在戏曲作品中的旁衍——以汤显祖戏文创作为中心
2023-02-27宋永祥
宋永祥
论赋体因素在戏曲作品中的旁衍——以汤显祖戏文创作为中心
宋永祥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1)
赋体因素大量存在于戏曲作品之中,是一种尚未得到学术界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的创作现象。在汤显祖的戏文创作中同样具备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有:于戏文中嵌入赋作,以赋法用赋典,以赋体写人、事、景、物等。汤显祖在书写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从赋体中汲取了大量营养,这一创作实践对加深戏文主旨、生动刻画心理活动、差异化展现人物形象等都能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是其戏曲创作不可或缺之一环;但同时也可能会对戏曲作品的登台演出造成一些损害,汤显祖认识到了这一负面作用并通过对赋体妥当地取舍成功地进行了纠补。
赋;戏曲;汤显祖;《紫箫记》;临川四梦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同文体的交叉研究已然成为一方热土且业已出现一大批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诗歌的绝对优势地位,此种研究范式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古典诗词与其他文体的交叉研究,而诗歌以外的不同体裁的比照研究,虽有涉及但仍稍显薄弱。如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辞赋,目前学术界对其与其他文体的交叉关系研究多数仍局限在诗歌、骈文等领域;而与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这一体裁的关系研究就较为欠缺,存在着对创作和批评进行深入挖掘的空间。
作为成熟较早的文学体裁,辞赋作品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表现手法来看,都堪称沾溉后世,其泽甚远。即使抛却具体的作品本身不谈,赋家的本事、逸闻都可能成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将之运于笔下,成于文中。具备篇幅灵活性高、写人叙事抒情兼顾等特点的戏曲作品自然也从辞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赋体因素旁衍至戏曲作品中这一现象已为少数学者所注意并指出:朱恒夫《戏曲与赋》一文罗列了若干宋金杂剧、元杂剧、南戏、传奇等作品中具备赋体特点的段落,如目连戏《救母记》中的《种田赋》《茶叶赋》《无常鬼自述赋》等、南戏《双烈记》中的《长江赋》《金山赋》等[1]24–31;邹星旺《古代戏曲中的用赋研究》在朱恒夫上文的基础上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2]。根据前贤的研究成果及笔者对部分戏曲作品的检视来看,赋体因素在戏曲作品中的存在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区别只在于早期如宋金杂剧中赋的篇幅较为短小、元杂剧中赋的语言偏于俚俗。赋体较为广泛和成规模地旁衍到戏曲作品中大略是在南戏、传奇作品中,而这亦与古典戏曲作品的生成发展周期基本同步。本文在论述赋体在戏曲作品中的旁衍、作用及其评价时选择以汤显祖的戏文为中心,一因汤氏是公认的我国古典戏曲作品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二因他本人的辞赋创作成就在当时就为人所推重,某些作品“在明赋中都应属于上等”[3]546,如帅机《玉茗堂集序》所云“其所为《罗浮山》、《青雪楼》赋,编星濯锦,当令《天台》汗颜”[4]350,在辞赋造作上亦有独到之处。因此,以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紫箫记》为中心的讨论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①。
一、直接造作
赋体因素旁衍于戏曲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以整篇赋颂的形式在戏文中直接存在,同下文将要论述的用赋体刻画人物、写景抒怀等不同的是,作者直接在行文中以赋名篇,这样的例子在汤显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两个,且二者行文结构和所起作用几乎一致。先看《南柯记》中田子华献赋:
〔田〕处士臣田子华,文墨小臣,躬逢盛典,谨撰《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奏上。
〔王〕奏来。
〔田跪念介〕幽哉!大槐安之为国也。前衿龙岭,后枕龟山。龟山者,玄武之精也。西望则有西王母之龟峰焉。东顾则有东诸侯之龟蒙焉。尔其为山也,其上穹窿,其中空同。形如巴丘之蜕骨,势似鳌山之顶蓬。草木生其背,禽兽穴其胸。文有《河》《洛》之数,武有介胄之容。驸马都尉臣淳于棼右丞相臣段功等,仰首叹曰:丕休哉龟山!郁郁葱葱。吾王不游,虎兕出于匣外;今日不乐,龟玉毁于椟中。君王感焉,武功其同。是月也,凉风至,草木陨。鹰击鸟,豺祭兽。君王乃冠通天之冠,被玄衮之袍。佩干将,登华芝。雨师洒道,风伯清尘。因是以左丞侯,右淳侯,率其蚁附之属,若大若小。纷纷蛰蛰,乘玄驹而缀步趋者,殆以万计。金鼓震天,旌旗耀日,雷炮霜刀,风矰雨毕,周圆而阵于七十二钻之上。时至令起,人喧物哗。挂飞猿,跐长蛇。碎熊掌,糜象牙。咀豹文,嘬犀花。髓天鸡,脑神鸦。至于雉兔数万,他他藉藉,君王未之顾也。最后得一甲兽,盖鲮鲤云。带穿山之甲,露浮水之嘴,舐啖至毒,不可胜纪。穴于山腹。火而献之。君王欣然,仰天而嬉曰:龟山有灵,此其当之矣。寡人鄙小,其敢朵颐?盖兹山以土石为玄壳,以草树为绿毛,今此之猎尽矣。乃遂收旗割鲜,鸣钟举酒,凯歌而旋。既醉既饱。微臣授简作颂,献于座右。颂曰:隆隆龟山,龙冈所蔽。玄玄我王,卜猎斯至。非虎非罴,曰雨曰霁。服猛示武,遗膻去智。愿以龟山,卜年卜世。蝼蚁微臣。愿王千岁千千岁。
〔王大笑介〕妙哉赋也!昔汉武皇见司马相如《子虚赋》,叹恨不得与他同时。今寡人与子同时。幸哉![5]2867–2868
田子华是《南柯记》主人公淳于棼之“文友”[5]2825,槐安国王知其与淳于氏交好,故而擢为赞礼,田子华在随淳于棼赴任南柯太守前亦曾陪驾游猎,《侍猎》一出即敷演此事。根据槐安国王的宾白,此处用的是司马相如献赋于汉武帝之典故——自相如为武帝作《天子游猎赋》后,帝王田猎之际有文臣献赋成了一个赓续不断的文学传统。《文选》有“田猎”赋3卷,《历代赋汇》亦专列“蒐狩”一类。此处田子华所献《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虽然从篇幅上较之《子虚赋》《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等远为不及,但从内容和结构看都符合田猎赋的特征,此为汤显祖直接将赋作移植于戏曲作品之一例。又,在《邯郸记》中可以看到一段与上文结构几乎完全相同的戏文:
〔上〕前岸屹然而立,头向河南,尾向河北者,何物也?
〔生〕铁牛,以镇水灾。
〔上〕宣裴光庭,卿长于文翰,可作《铁牛颂》,以彰卢生之功。
〔裴〕万岁。臣谨奏。
〔上〕可奏来。
〔裴〕天元乾,地顺坤。元一元而大武,顺百顺而为牛。牛其春物之始乎。铁乃秋金之利乎。其为制也,寓精奇特,壮趾贞坚。首有如山之正,角有不崩之容。至乃融巨冶,炊洪蒙。执大象,驱神功。遂尔东临周畿,西尽虢略。当函关之路,望若随仙;近桃林之塞,时同归兽。昔李冰镇蜀,立石兕于江流;张骞凿空,饮牵郎于汉渚。盖金为水火既济,牛则山川舍诸。所谓载华岳而不重,镇河海而不泄,其在兹与。臣光庭作颂。颂曰:杳冥精兮混元气,炉鞴椎牛载厚地。巨灵西撑角岧崹,冯夷东流吼滂沛。坚立不动神之至,层堤顾护人所庇。帝赐新河名永济,玉帛朝宗千万岁。
〔上笑介〕奇哉颂也。卢生刻之碑铭,汝功劳在万万年,不小也。
〔生〕万岁。[5]3023
从写作程式看此处戏文与《南柯记》田子华献赋相同,讲的是卢生为方便唐玄宗顺流而下游览盛景而花数年之功开凿永济河,又立铁牛镇之,使得龙颜大悦。上令裴光庭作颂以彰其功。裴氏所作《铁牛颂》虽名为“颂”体,实际亦可称作“赋”,如刘勰所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6]156–158二者并无绝对区别,如“马融的《广成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谓‘纯为今赋之体’,是赋与颂有时亦相混”[3]6。故而,此处亦可视为汤显祖于戏文中直接嵌入辞赋造作又一例。另外,同田子华献游猎赋相同的是,裴光庭于玄宗东巡时作颂也有其历史渊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有马融《东巡颂》、班固《东巡颂》《南巡颂》,崔骃《四巡颂(西、南、东、北)》等作,戏文中玄宗宾白“奇哉颂也”一句亦是用《后汉书·马融列传》所载“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7]1971之典。
发挥赋在戏文中的作用,符合我国古代上层文学的创作传统。《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是天子游猎赋题材的同题书写,《铁牛颂》是帝王巡幸颂文的异代回响。汤显祖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嵌入这两篇辞赋,既能够通过文学创作更好地塑造田子华“文友”和裴光庭“长于文翰”的人物形象,又能用于史有征的“赋学纪事”手段使得虚构的戏剧故事显得更加自然真实。同时,若将视野跳脱出单一场次的情节而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审视,笔者认为这两篇赋作还具有加强戏文讽刺荒诞意味、提升主旨的作用。
从题材内容看,《南柯记》和《邯郸记》属于“官场现形戏”或曰“政治问题戏”。两部作品的结构相同,主体部分都是借主人公的梦境叙述其宦海沉浮,反映政治黑暗,写尽上至帝王下至群臣之百态。淳于棼和卢生在梦中都高官得坐,而终归一败于官场倾轧,一死于穷奢极欲。而这样跌宕起伏的经历,只是南柯、黄粱之梦。汤显祖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射时政,寄托怀抱。
《南柯记》中的大槐安国是一个由蚂蚁族建成的所谓“王国”,蚁国国王在田猎之际,臣子奉上了一篇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故事相媲美的游猎赋。《邯郸记》中的卢生穷数年之功逼迫百姓凿石开河,挑选千名女郎为龙船摇橹,而这些举措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一己私欲。裴光庭在其所作颂文中,竟将卢生的行为与李冰治水、张骞出塞相提并论,如此描写,颇具讽刺意味。《南柯记》和《邯郸记》所营造出的这种梦境与现实冲突的剧烈效果得益于汤显祖对梦境铺张扬厉的描绘,而《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和《铁牛颂》在相当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赋典画心
除了直接在戏文中进行辞赋造作,用赋典,即借用经典赋作的本事或语言来刻画人物心理、或推动故事发展,也是赋体旁衍于戏曲作品的表现之一。前文论述汤显祖在《南柯记》中设计田子华为槐安国王献大猎赋的情节,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也是用相如典故的创作手法。在《临川四梦》的唱词和宾白中,用到赋家或赋作典故的例子很多。在《紫箫记》中,这种用赋典的情况更具代表性,用典繁密且对人物塑造、故事发展都起到渲染之功,可以概括为“以赋法用赋典”。
《紫箫记》第十一出《下定》讲的是李益托媒于鲍四娘,在家等候回音,通过侍女樱桃的“巧探”后下聘于霍小玉的情节。其中前半部分在描写李益等候四娘回话时,戏文中大量用赋的典故来刻画人物心理。先看其在本出戏的登场方式:
〔清江引〕〔李十郎上〕梅花晓帐红云碎,细叶笼金翡。旅思欲萋迷,梦远春迢递。扶头酒,会心人,萦肠事。
〔愁倚阑〕云花落,雨香飘,索春饶。皱蹙柳丝吹不断,翠条条。银蟾暗咽春朝,知他在第几朱桥?说与晓莺休唤,怕魂消。昨日到鲍四娘闲亭,许为媒求霍郡主小玉。归来春宵枕上,睡得不沉,醒得不快,是真是假,且把《昭明文选》来醒眼。〔翻书介〕呀!好彩头,就翻着第十九卷一个“情”字。过了便是《高唐赋》,第二篇《神女赋》,第三篇《好色赋》,第四篇《洛神赋》。呀!由来才子,都是这般有情。[5]2303
李益在首次登场自述中就说自己“年已十九……尚未婚宦……以此长叹”[5]2264,可看出其求偶心切;第九出《托媒》中他与鲍四娘有一段对话:“〔十郎笑介〕好容易得名姝!我要有三件的:一要贵种,二要殊色,三要知音。〔四娘〕呀!蚤是你说起知音的,俺前在花卿处,闻你有‘风帘动竹’之诗,说与一女郎听,那女郎好生吟爱,可是知音?〔十郎惊介〕有此知音女子,定有好容颜。〔四娘〕绝精。〔十郎〕可是大家儿?〔四娘〕不小。〔十郎〕问是谁家姝?〔四娘〕他是霍王之女。〔十郎〕可求否?〔四娘〕到有几分。”[5]2295从中可以看出霍小玉完全符合李益的“求偶标准”。当他在等候鲍四娘的回音时心情急切,甚至连睡眠都受到影响,只能通过读《文选》以排遣无聊,且看的全是“情”赋。戏文通过如此情节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李益急切的心理,十分有趣,也直接引出了下文用赋典刻画其情绪波动的戏份。现将李益读《文选》四篇“情赋”后有感而发,所唱之词抄录如下:
〔皂罗袍〕《高唐赋》呵,忆昔高唐枕席,正择日垂旒,把诸神醮礼。只见高唐去处,凄切杳冥,相似鬼神来了一般。抽弦障袂好增悲,松声直下深无底。怀王正望间,忽见朝云之女,侍他昼寝。可惜止是朝暮之间,若久长相处,真个延年益寿。霓旌翠盖,登高此时;朝云暮雨,相逢美姬,教人九窍都通利。
看《神女赋》呵。
〔前腔〕见一妇人奇异,似屋梁初日,照耀堂墀。人间那得更须臾,神心蚤逐流波去。襄王呵,这样神女,只梦一梦也够了,醒后又想他怎的?玉鸾低盼,芬芳已离;精神记取,私怀语谁?教人向曙空垂涕。
再看《好色赋》呵。
〔前腔〕何处东家之子?□嫣然一笑,下蔡魂迷。谁教宋玉有微辞?兼他体貌天闲丽。宋玉呵,你有这样人做邻,自然文赋生色,说甚邯郸、郑卫?三年未许,东墙自窥;芳花有意,春风几时?教人顿有章台思。
再读《洛神赋》呵。
〔前腔〕正自凌波拾翠,向神霄解玉,纵体通辞。流风矫雪映绡裾,轻云蔽月笼华髻。子建呵,这样有情仙子,不得蚤就,后来懊恨,可如何矣!当年未偶,明珠献迟;人神异路,君王怎归?教人洒遍长川泪。[5]2303–2304
第一段唱词说《高唐赋》。《高唐赋》,宋玉所作,主要描写巫山地区的山水风物,但开头叙述了一段楚怀王在梦中与巫山高唐神女相遇的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巫山云雨”也成了一个带有暧昧意味的词汇。戏文此处不仅用了《高唐赋》的本事典故,且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情节需要。《高唐赋》最末为“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8]881–882,该赋体终了,归于讽谏的常规写法。而在此处用原赋中的文辞,改写成“可惜止是朝暮之间,若久长相处,真个延年益寿”“朝云暮雨,相逢美姬,教人九窍都通利”等句,非常符合李益这一人物的心理。
第二段唱词说《神女赋》。此赋紧承《高唐》而来,写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求而不得,襄王为之心伤之事。赋中极力刻画了神女之美丽。李益所唱的这段戏文几乎也全部脱自于《神女赋》“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愿假须臾,神女称遽……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8]887–889,当李益读到《神女赋》“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襄王为之“徊肠伤气,颠倒失据”等情节,而鲍四娘又迟迟没有回音,李益的情绪已受到赋作的影响而不免略带悲观了。
后两段唱词同上两段一样,所造之语基本也出自对应的《登徒子好色赋》和《洛神赋》。《登徒子好色赋》内涵一个美丽的东邻之女苦苦追求宋玉的故事,而《洛神赋》中女性形象美丽绝伦,但终因人神殊途而不能结合。四段唱词之后还有一段总结的宾白:
看这四篇赋呵,洛川形貌千秋恨,江汉风流万古情。小生虽无好色之心,颇有凌波之想,不免抛书枕几,也学高唐昼寝。想将巫峡云来。小玉姐呵,不知你为是瑶台客?为是宋家邻?为是章华艳?为是洛川神?鲍四娘为何音信沉沉。没些定夺。
这四段唱词是李益读罢四赋之后的心声。四篇赋作皆有男女相求之事,与李益此时所处情状类似。汤显祖在这段戏文中用此四赋典故,就塑造人物而言,符合李益饱学之士的形象设定;就情节需要而言,使得李、霍的结合过程完整——托媒、下定、纳聘、就婚。而其更主要的作用,则是借这四部辞赋的典故描摹李益的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动——一个遇到符合自己求偶标准的佳人且有可能追求成功的未婚青年,在等候媒人回音时的心态。四段唱词用了四部辞赋作品的典故,人物情绪由期待进而不安、复又憧憬再转叹息的变化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四段唱词的最末一句分别为:“教人九窍都通利”“教人向曙空垂涕”“教人顿有章台思”“教人洒遍长川泪”。这种密集用典的创作手段,本身就是一种“赋”法,汤显祖用四段唱词渲染仍未尽兴,还要在宾白中让李益连发四个“为是”之问来进一步加强。就此般“以赋法用赋典”的方式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效果来看,本出戏文可以算得上是辞赋成功渗入戏曲作品的又一经典案例。
三、赋写百相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6]136。戏曲作品中有人、有事、有景、有物,用赋体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效”且往往能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手段。现主要就以“赋”写人、旁及景物进行论述,审视赋体在其中起到的功用。
戏曲作品的核心在于故事情节,而人物又是故事的核心。古典戏曲作品中对于人物的出场无论是“自述”还是“他述”,往往都有一定篇幅的交待。“以赋摹人”这一现象,在研究辞赋与戏曲关系的相关论述中基本上都有提及。如大家都会注意到类似于《紫钗记》中郑六娘介绍小玉时所说的“老身霍王宫里郑六娘是也。小家推碧玉之容,大国荐涂金之席。阳城妒尽,那曾南户窥郎;冰井才多,每听西园召客。晚年供佛,改号净持,生下女儿,名呼小玉。年方二八,貌不寻常。昔时于老身处涉猎诗书,新近请鲍四娘商量丝竹。南都石黛,分翠叶之双蛾。北地燕脂,写芙蓉之两颊。惊鸾冶袖,谁偷得韩掾之香?绣蝶长裙,未结下汉姝之佩。”[5]2421这样句式齐整的戏文段落在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介绍人物时比比皆是。而相关研究几乎都仅仅局限于指出这一现象之存在,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用赋体描摹人物是戏曲作品的一种“套路”,但运用这一“套路”的不同方法,却可以起到区分形象差异性的作用。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介绍人物时行文骈散与否及篇幅不同,展示人物形象的差异性。才子佳人戏为古代戏曲小说作品的一大类型,男性主人公多为饱读诗书的青年才俊,作者在安排其上场时自述多用赋体,在汤显祖戏文中于此端有代表性的是《紫箫记》中李益的出场:
小生姓李,名益,字君虞。陇西人氏。先君讳揆,前朝相国;先母辛氏,狄道夫人。贵袭貂裘,祥标鹊印。朱轮十乘,紫诏千篇。王子敬家藏赐书,率多异本;梁太祖府充名画,并是奇踪。小生少爱穷玄,早持坚白。熊熊旦上,层城抱日月之光;闪闪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对江夏黄童之日晷,发清河管辂之天文。兄弟十人,生居其末,俗号十郎。正是:贾家三虎,伟节最著;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朱公叔之恣学,中食忘餐;谯允南之研精,欣然独笑。文犀健笔,白凤雕章。悬针倒薤之书,云气芝英之简。坛场草树,院宇风烟。闲则飘举五方,游戏三昧。经称小品,还下二百签;赋为名都。略点八十处。看郭象之注《逍遥》,何如向子?断平叔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颇吟《招隐》之章,辄动《怀仙》之操。笑时流义轻于粟,鄙儒辈知不如葵。悲蒯生一说而亡三,诧墨子九拒而余六。园池幸足,台阁无心。争奈朋友弹冠,郡县劝驾。赵元叔河南计吏,张昌宗丹阳孝廉。忝春官桃李之尘,杂上苑桂林之玉。正及殿试,忽奏吐蕃入破陇西数郡,抄至咸阳,烽火照于甘泉,车驾亲屯细柳。暂辍龙轩之对,俱奔燕幕之生。比向陇西,奄成塞北。杨祖德家惟弱柳,殷仲文庭止枯槐。三川为饮马之泉,陆浑缠兵妖之气。旁藩列镇,据穴横兵。井树无遗,干戈满地。金鱼玉碗,感朝暮之情多。宝轴龙文,叹文武之道尽。顾松楸而耿涕,去桑梓以遥奔。依止神京,春燕并巢林木。摧残旅馆,秋鸿半落芦洲。且喜生意渐回,春光再转。今日是元和十四年正月朔旦,兼逢是日立春。天下朝觐官员,应制士子,俱入云龙门太极殿朝贺。万叠云中窥日,九光霞里朝元。车喧百子之铃,庭现九金之鼎。戏鱼成殿,预章宫里朝仪。舞马登床,花萼楼前故事。帝御青龙之座,光生万户千门;人斟白虎之尊,响动千秋万岁。朝毕之后,光禄赐宴。皇恩洽,群臣醉。降氤氲,调元气。谁道七哀无象?由来万乐有声。只是一件,小生年已十九,逢此佳节,尚未婚宦。椒花可颂,不逢刘氏之媛;柏叶空传,未取戴凭之席。以此长叹,及此春新。所喜五陵豪杰,多所知名;四姓小侯,争来识面……[5]2263–2264
除却为数不多的几句串词,这段文字全用赋体结撰,文富典赡,尽铺排之能事,俨然就是一篇《李生自述赋》,且赋文内容兼摹人、叙事、状景等功用。人物以这样的方式登场,不管是观众还是读者,立时对主人公身世显赫、才学兼善、广结胜友等特点留下印象。此外,这一大段铺排也能够为后面戏文李益“状元及第”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
当戏文人物极富才学时,汤显祖会不惜笔墨地铺排其自述以突出形象特点。而当非“才子”身份的人物出场或叙事时,则多不用文辞典雅的赋体。如《紫箫记》中《换马》《纵姬》两出,说的是李益于花卿处饮酒赏曲,听闻国舅郭锋骑射,花卿以侍妾鲍四娘换其名马,国舅后又将四娘送至霍府教唱一事。同上文李益在宾白中自述家世、经历、交游等全用赋体不同,郭小侯自述全为散体,皆作口语,如《纵姬》:
自家姓郭,名锋,世号小侯。祖是汾阳王郭子仪;姊是当今贵妃娘娘,带管皇后玉玺,生下太和公主一人。小子身是国舅,自小封侯。昨日走马射鸟,过花骠骁门首,他看上我所骑之马,请入歌楼,便以爱姬鲍四娘换去。那鲍四娘离别花卿,好生愁绝。到我府中,涕咽忘餐。呀,大丈夫何忍伤人之意乎!小使,我吩咐你,送鲍四娘闲庭别院,随他自便。只到良辰佳节。入我府中相随歌舞便了。[5]2278
可以看到,不管是出场时郭锋的自我介绍,还是他叙述换马、纵姬之事,都以散体文交待,这与作品中刻画李益形象时表现出很大差异。戏文中人物在宾白中的语言骈散不同,契合其身份特点,这在汤显祖的作品中表现得甚为明显:《紫箫记》中的花卿、石雄等偏“武”的形象与李益、霍王等偏“文”的形象,其宾白语言差异分明,这种差异也符合观众或是读者的审美期待。
第二种方法是当人物在自述时,通过赋体文辞的典雅或俚俗的不同,展现人物形象的差异性。上文李益自述就属典雅一路,一通文繁词缛的宾白下来,一位满腹诗书的翩翩公子形象就跃然于纸上(或台上)。而有些同样以赋体出现的宾白,虽然句式整饬有加,其遣词造句却平直易懂、不加雕饰,贴合人物形象。如《南柯记》的主人公淳于棼出场时自述:
小生东平人氏,复姓淳于,名棼。始祖淳于髠,善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颇留滑稽之名;次祖淳于意,善医,一男不生,一女不死,官拜仓公之号。传至先君,曾为边将,投荒久远,未知存亡。至于小生,精通武艺。不拘一节,累散千金。养江湖豪浪之徒,为吴楚游侠之士。曾补淮南军裨将,要取河北路功名。偶然使酒,失主帅之心;因而弃官,成落魄之像。家去广陵城十里,庭有古槐树一株。枝干广长,清阴数亩,小子每与群豪纵饮其下。偶此日间,群豪雨散。则有六合县两人:武举周弁,吾酒徒也;处士田子华,吾文友也。今乃唐贞元七年暮秋之日,吩咐家僮山鹧儿,置酒槐庭,以款二友。[5]2825
淳于棼在戏文中是一个嗜酒任性、精通武艺、不拘小节的人物,并不以才学见长。因此其登场自述时,虽同样用了形式齐整的赋体宾白,但只称得上“骈语”而算不得“丽辞”。这样的行文方式,一则能够保留赋体摹人的优点,二则不至于因文辞过于华丽,而使观众或读者产生人物语言与形象相舛的违和感,堪称高明。又如《南柯记》中的一个丑角“溜二”,其自述为:“自家扬州城中有名的一个溜二便是。一生浪荡,半世风流。但是晦气的人家,便请我撮科打哄;不管有趣的子弟,都与他钻懒帮闲。手策无多,口才绝妙。有那等吊眼子,敲他几下,叫做打草惊蛇;无过是脱稍鬼,松他一筹,则是将虾吊鲤。着甚么南庄田,北庄地,有溜二便是衣食父母;难起动东邻邀,西邻请,则沙三是个酒肉弟兄。知音的说是个妙人、好人、老成人;少趣的叫我败子、俫子、光棍子。且自由他笑骂,只图自己风光……”[5]2838观其自述,一个伶牙俐齿的泼皮形象活灵活现。同塑造淳于棼的手法相似,这里用俚俗的语言、赋体的形式来刻画人物,同样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由此,通过对汤显祖几部作品中若干人物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到,赋体因素旁衍于戏曲作品中是广泛存在的,也是作者自觉采用的一种创作手段,对于展现人物特点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概而言之,是否用赋体,如何用赋体,对于描摹角色,使观众或读者接受其人物设定都颇具影响。此外,除了用赋体表现“千人千面”,戏曲作品在摹物写景时也多用赋体,只是这类戏文在汤显祖的作品中出现得不像写人那样集中,篇幅也往往不及,一般是以几句骈俪的语段存在于宾白之中,前文所引《大槐安国大猎赋》中其实就有写龟山之景及其风物的段落。《牡丹亭·冥判》中的“花”名排比,《紫箫记》中的“曲”名罗列,《邯郸记》中卢宅的描摹等,都采用了赋体的形式,于此不复赘述。
四、批评取舍
“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9]1,说的是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其内涵广大。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言“传奇”指的是成熟于元末明初的戏剧作品,在此之前宋金院本、元杂剧等篇幅较之南戏传奇要短小得多。明清的戏曲作品动辄数十上百出,剧作家拥有广阔的空间任其逞才使气,且由杂剧散曲而至南戏传奇,从文辞风格看经历的是一个逐渐“雅化”的过程。因此明代剧坛的“沈汤之争”,从某种角度看包含“本色”与“文采”之争。整体而言,汤显祖的作品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都是偏“雅”的,这从上文分析其大量使用赋法丽辞可以明显看出。明人祁彪佳评价《紫箫记》“工藻鲜美,不让《三都》、《两京》”[4]774,将戏文与赋作并提,揄扬其美。但是对汤显祖远离“本色”,又常因顾及文采而坏曲律的做法,批评之声亦多。例如即使推其为“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的王骥德也说:“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4]650其实《紫箫记》作为《紫钗记》的原型,汤显祖自己也不满意:“《记》初名《紫箫》,实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5]1558这一自我认识与他人之批评相一致。
戏曲最初创作出来是为了满足演出的需要——“填词之设,专为登场”[10]66。如果仅仅把戏曲作品当做“案头之书”来读,正如前文所论,赋法、赋典等渗入戏曲,能使作品成为一篇华丽的“美文”。但若过于冗长,对于戏曲演出确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汤显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从《紫箫记》到《紫钗记》的一些改动就可以看出:如前文所引《紫箫记》李益出场就是一篇近千字的赋体自述,而在《紫钗记》中削减至一半不到,且所用语词更加平实;又如《紫箫记》中《下定》一出“以赋法用赋典”的情节在《紫钗记》中就完全消失了。又,从汤显祖的作品完成时间来看,《紫箫记》最早,其后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仅仅从适合演出的需要来说,作品也表现得越来越成熟。王骥德《曲律》评价说:“《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类,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为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剩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4]650这里的“汰其剩字累语”和“遣辞复俊”应当就是针对作品中过多的骈语、用典、僻字等现象而言,而这些都是赋体的特征。因此,从《紫箫记》到《紫钗记》的改造,“四梦”愈发适应舞台演出这一历时层面的变化来看,汤显祖认识到赋体丽辞可能对舞台造成的伤害并做出了成功的补救。
对汤显祖戏曲作品的这种批评和他本人对戏文中赋体因素的取舍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地评价赋体因素旁衍至戏曲中?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于到底是以“纯文本”还是以“纯底本”的眼光看待戏曲文本。如果是以“纯文本”的眼光,笔者认为即使将之完全作“案头之书”来读亦无可厚非;而从“纯底本”的视角来看,正如吕天成《曲品》所言:“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4]648也不应完全排斥赋体因素的存在,毕竟赋体在文学创作上有其特殊作用,而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可以也应该恰当地运用。正如“矩矱”和“才情”合之才能“双美”一样,当辞赋研究和戏曲研究发生交叉时,也应当同时兼顾两种体裁的艺术特点和衡量标准,方能在文体交叉研究领域得出客观的结论,做出合理的评价。
① 目前学术界讨论汤显祖戏文作品与辞赋关系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郭慧茹《“临川四梦”与赋体关系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此文在分析用赋缘由、赋体与戏文结构等方面颇有其可取之处,但不足之处是将《紫箫记》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1] 朱恒夫.戏曲与赋[J].同济大学学报,2001(4):24–31.
[2] 邹星旺.古代戏曲中的用赋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3]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 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 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I206
A
1006–5261(2023)06–0048–09
2023-06-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9)
宋永祥(1991― ),男,安徽安庆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