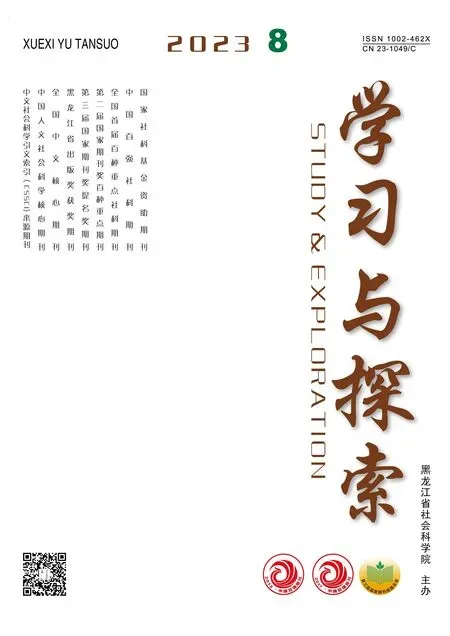劳动与工具行动①
——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问题
2023-02-26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钊译谢永康校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夏 钊译,谢永康校
(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系,纽约 10027;2.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3.海南大学 人文学院,三亚 570228)
在最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一种旨在政治行动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成为问题:“革命理论的危机”这样的论点标志着,作为马克思理论规划核心部分的资本分析几乎不再被拓展去规定批判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的目标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当前现状进行有实践取向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但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种程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以方法论上的一种交互可译性(wechselseitige Übersetzbarkeit)的主导观念——绝非一种具有系统性的资本分析与实践导向的革命理论在主题上趋同的观念——为基础的,而当前恰恰就是这种理论互补关系受到质疑——资本分析危机理论的诸范畴似乎不再能触及转移了的危机领域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冲突。这种不对称此刻就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探讨的理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
然而在这期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被推至针对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现实性这种理论怀疑的中心,(1)Vgl. Andreas Wildt, “Produktionskräfte und soziale Umwälzung. Ein Versuch zur Transforma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U. Jaeggi/A. Honneth (Hrsg.),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7, S. 206 ff. 在德国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接受中,“劳动”范畴(如果它还是主题的话)在整体上充当着一种针对无秩序的主体性的核心概念的反概念角色。Vgl. Gerd Bergfleth, “Kritik der Emanzipation”,in Konkursbuch. Zeitschrift für Vernunftkritik, Nr. 1, 1978, S. 13 ff.而劳动概念在其最初理解中就承诺表现一种连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范畴环节: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劳动概念不仅应该突出社会实践维度,在此维度之上,人类世界才从自然的生命关联中产生出来并在社会文化意义上进行再生产;而且劳动概念同时应该规定行为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认识的诸潜力得以释放,这些认识潜力总能让统治地位得以转变并使社会自由的进化扩展成为可能。马克思不仅想在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用途上,而且也想在解放的教化的规范性—实践性用途上来理解劳动,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在关于“活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的应用原则、同时也属于唯物主义革命理论这个本性陈述中展开。
这一范畴特权化(Privilegierung)的后果就是,在能回溯至马克思的传统中,劳动概念必须承担更多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的功能。在社会理论上,马克思想借助作为协同改造外部自然的社会劳动来表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形式;依这种方式,社会化过程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的关键就在于社会劳动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组织。在认识论上,马克思已在其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将社会劳动理解为行为关系,出于这种行为关系人类才能在认知上向自身展示现实;依这种方式,对科学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关键就在于对自然进行协作改造所取得的认识成果。最后在规范性—实践性意义上,马克思愿意相信社会劳动具有一种教化过程的功能,在此教化过程中劳动主体意识到其自身能超越社会结构所允许的可能性的诸能力与诸需求;依这种方式,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生产中所释放的有关解放的诸视角。
劳动概念凭借这三重功能规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据垄断地位,但这一地位在目前社会批判理论的继续发展中受到了触动。在并未挣脱马克思概念形成之行为理论根基的客观主义根本方法的诸传统思路中,劳动概念在社会理论和认识论上的首要地位都受到了怀疑。在社会理论方面,社会劳动范畴要么在批判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转向中被交往行动范畴所补充,(2)Vgl.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Kap. I, Frankfurt/M. 1968; Albrecht Wellmer, “Kommunikation und Emanzipation”,in Überlegungen zur ‘sprachanalytischen Wend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U. Jaeggi/A. Honneth (Hrsg.),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a.a.O., S. 465 ff. 可参考本篇文章第三部分。要么在之后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中被扬弃为一种再生产所必需的实践形式的类型学。(3)Louis Althusser/Etienne Balibar, Das Kapital les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认识的社会构造条件要么出于一种社会发生学认识论的目的被转移到社会分配领域,(4)Vgl.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M. 1970.要么出于一种唯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被扩展到经符号中介的互动维度。(5)Vgl. Karl-Otto Apel,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Bd. II, Frankfurt/M. 1973.当然,鉴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实践导向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第三个功能规定——以社会劳动的解放内涵为目的,才会引起体系性的兴趣。在这一视角下,汉斯-于尔根·克拉尔(Hans - Jürgen Krahl)在其关于“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报告中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为疑难提出来,他提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否成功地将劳动的辩证法,也即社会劳动的辩证法,不仅规定为利用资本的不幸,也规定为解放的那种否认资本的生产力?而且在马克思那里是否证明了这些生产力本身就展现出同样多的解放手段?”(6)Hans-Jürgen Krahl, “Produktion und Klassenkampf”,in ders.,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M. 1971, S. 387 f.笔者通过反对在马克思之后开始的对劳动概念的淡化,试图将一种批判的劳动概念变得正当,以间接地促成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在简要地、导入性地陈述马克思的论证之后,笔者会追溯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社会史,直至范畴视野变得立体;而在此视野下哈贝马斯引入了工具行动的概念,在对这一概念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笔者期望重新获得一种批判的劳动概念的轮廓。
一
马克思已经在近代劳动概念的框架内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理论基础。在他对社会劳动的理解中,马克思暗中将不同的意义元素集合在一起,凭借这些意义元素,现代社会哲学理论在劳动概念上历经历史的变迁过程从而得到澄清,并且这一变迁过程逐渐让人们意识到是以社会的方式被组织的生产,而不再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和代表性行动成为一切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近代哲学在(劳动)范畴的重新解释中对这一经验内涵作出回应,即它把劳动从古代—基督教传统的否定性含义中抽取出来,并明确肯定地将其提升为社会行为的成果,而这种范畴的重新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规划中得到完成的。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经济学化进行了批判性回溯,而在这种经济学化中,古典国民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扩大和加速的时代经验归因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里政治的、代表性的或者深思熟虑的统治实践作为非生产性的活动形式被解除了其在人的行为方式评价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并且首先被农业劳动、其次还有手工业与工业劳动这类创造价值的活动形式所代替;而劳动行为的经济学地位的提升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获得决定性的表达。当然,马克思还将解放理论的意义内涵引入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并且也正是这种意义内涵让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自我意识的构成环节。后者通过将在外化模式中改造对象的活动设想为意识内容的对象化,从而把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倒译回先验哲学的意识理论框架;与哲学传统相反,黑格尔把劳动行为本身解释为认知能力的阐明过程,在这点上也就解释为教化过程,(7)Vgl. Manfred Riedel,“Hegel und Marx. Die Neubestimm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Theorie und Praxis”,in ders., System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m historischen Standort von Hegels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73, S. 9 ff.; Karl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zsche, Hamburg 1978 (7. Auflage), S. 286 ff.因为他认为对劳动主体来说劳动产品具有一种可追溯的意义。当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劳动状态批判为一种社会异化关系,且这种异化关系逐步放弃了劳动活动的阐明和对象化特征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劳动概念的这一意义维度。当然也只是在从他所处的时代的另一哲学理论——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中获得的思考框架内,马克思才掌握了劳动概念的批判性内容:因为不再是以同一性哲学方式所说明的精神形成史,而是以人类学方式所阐明的人类生命过程充当了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在此背景下他把劳动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为人特有的对象化能力,而在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诸劳动主体都被骗走了这种能力。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辨认出黑格尔精神概念的特征是人的迄今未被把握的自然特性,从而其人类学的类概念是马克思引入其劳动概念的第三个传统组成部分。现在这一(劳动)概念的复杂性才得以呈现,而在这种复杂性中现实主体改造自然的活动同时被理解为生产要素与教化过程。
马克思将近代劳动概念的核心意义元素融入对社会劳动的设想之中,而此设想规定着他的社会理论的范畴构造。历史哲学的启发性力量从这样的想法出发,即人类是在同一个社会劳动过程中社会性地再生产其生命,同时也看到其需要和能力,而正是这种启发性力量使得劳动概念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范式。在(马克思)哲学的思考框架中,早期著作中人类学指向的异化理论与在经济学著作中发展起来的资本理论都同样地被确定,而这种思考框架通过劳动将世界历史规定为一种社会的自我产生、自我保存与解放的过程:不仅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首先肯定性地论证了由人特有的劳动能力所赋予的人的主体性潜能),而且在其经济学批判著作中(他似乎否定性地分析了通过资本的独立化而对活劳动能力的压制),马克思借助在人类学意义上极端化的劳动的外化模式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解释成一种社会经济学的组成,这种组成在结构上妨碍劳动主体在其自身产品中的自我认同或者使其成为不可能。(8)这一论点以Ernst Michael Lange的教职论文为根据。Ernst Michael Lange, Arbeit - Entäußerung - Entfremdung, Ms. 1978.不过关于将社会劳动的模式与其他行为方式区分开的范畴界限,还有关于使劳动概念与个别的或共同的行为主体相关的解释范围,马克思自己并没有在其作品的任何地方明确解释;毋宁说,劳动这一行为哲学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推动其理论规划不同创作阶段的思考范畴,一直伴随着马克思的作品。
现在在这一未被清晰使用的范畴中,马克思让改造自然的活动类型与这样的行为类型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即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称号将其明确强调为政治—解放的实践;而且在同一提纲中解放理论的革命行动概念与这里认识论上意求的劳动概念在不明确的“实践”总概念中以特有的方式恰好相合。(9)K. Marx, Thesen über Feuerbach, Werke Bd. 3, S. 5 f.在这一等同之后,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解放内涵似乎不再仅仅具有历史哲学意义,即人类在扩大的协作性的自然改造过程中,在产品上证实其自身的能力,而且也具有一种劳动行为的革命力量的直接意义;他从劳动中奠基于对实践能力进行逐步阐明的、间接的主体性教化,回推到一种也在政治上构造意识的劳动动机。因为在其理论的劳动哲学基本范式中,马克思以改造对象性现实的模式将一切行为方式同质化,他明显进入了重要的思考限定,即只在劳动概念的范畴背景下才能解释实践的解放行为结构。这种范畴一元论——近年来一些关于马克思的阐释已经注意到这点(10)Jürgen Habermas,“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in 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S. 9 ff.; Albrecht Wellmer,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M. 1969, Kap. II.——给马克思提供了可能性,将一种革命功能加之于具有解放意义的社会劳动上。马克思想以两种论证模式在行为理论意义上确保社会劳动的这种革命作用,而不是在一种受资本主义典型生产力增长迫使的制度危机中、在决定性地参与规定其晚期著作的经济理论纲领中去确保这种革命作用。它们一方面与“巴黎手稿”的人类学异化理论相关,另一方面与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工业生产过程的一些零散规定相关。
在第一个论证模式中,马克思试图把劳动过程直接理解为一种教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主体能通过劳动产品中的个人经验认识到自己在个体的或集体的意义上就是建构历史的行为主体;这一想法不言而喻是一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理论的主奴辩证法的历史经验应用。马克思受其历史哲学的基本思考引导,即人类历史必须被思考为一种在“劳动的类生命”中人所特有的全部“本质力量”持续对象化的过程。不过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学建制异化了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历史展开过程,因为它没有使劳动主体自身自由地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而仅仅让非劳动阶级的物质财产确立起来;而国民经济学则将这种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术语来表达的社会历史事实去历史化,并掩饰了它,因为国民经济学在范畴上将个体劳动与“职业活动”(Erwerbstätigkeit)等同起来。为反对这种概念结合,马克思以不明确的方式提出了解放剩余劳动——他同黑格尔一道坚持这一点:因为从社会异化状态中获得社会解放应该只在同一行为活动中才能达成,而在这一行为活动中人类的诸潜能同时既被压抑又被保留,所以对社会劳动来说——命题“人的自我异化、本质外化、去对象化和去现实化作为自我获得”(11)K.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1844), Werke, 1. Ergänzungsband, S. 58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才能得到解释。最终这一思考致使马克思认为,工人解放、异化劳动条件下活动者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在同一历史行为中的人类解放,因为对劳动的社会异化状态的实践扬弃也保证了人的全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在历史上得以延续。
马克思没有在其“巴黎手稿”的任何地方进一步为这一论证的关键论点奠基,即工人解放应该仅仅出于异化劳动的内在关系就能得到说明。为了把一种进行启蒙—革命的作用赋予与资本主义一起建立的劳动社会形式,马克思有依据可以不去消除似乎必须被弥合的鸿沟,即人类学所认为的劳动行为的对象化特征与社会劳动的历史异化状态之间的鸿沟。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使与主人对立的奴仆在改造自然中走向自我确证和自我组织,从而获得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因而尽管这一主奴辩证法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背景动机,但是并没有提供一把经验解释的钥匙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马克思来说,与黑格尔意识理论思维形象的直接对接之所以已然不可能,是因为根据其理论意图他必须使自己理解一种敦促变革异化的劳动状况的社会意识,一种恰恰不同于黑格尔那种通过主人旨在主体间承认的社会意识。托马斯·迈耶尔(Thomas Meyer)早已搜集了那些妨碍马克思顺应其自身意图去重新解释主奴辩证法的原因:“在涉及‘革命的背反论’(Antithetik)时马克思为贯彻无产阶级的原则,其目的并不在于中介(调和)主人意识,而在于用新的奴仆意识代替主人意识,所以通过工具化的奴仆作为中介而对象化主人意识,并不是用直观其劳动的对象性产品的方式就可以变成奴仆自身的自我意识。因为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关于在已由其满足的条件水平上获得主人的承认,而是有关实现一种原则上新的看法,一种在当前的劳动原则中被否认的看法。此外在黑格尔那里奴仆可能获得适当的自我意识,这假定了这种自我意识先于劳动开端而预先实存,尽管是在主人的方面。”[1]174
随着马克思理论的继续发展,他从“巴黎手稿”的规范—人类学的有关观点中揭示出劳动概念的两个不相关的方面,并将这两个方面赋予劳动的经验社会史,此时他也没有解答这个借助黑格尔主奴辩证法论证模板为自己提出的理论问题。对劳动行为一种本源的直观化特征的理解,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劳动研究提供了规范性背景,这种理解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被扬弃为劳动的一种手工业的、深入对象的以及自我封闭的富含经验内容的形态;而之后对劳动行为的一种完整的、由劳动主体自主规划和实行的理解,丰富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的)规范性蓝本。由此,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进行批判的《大纲》中,一种由劳动主体自身的知识所引导的、要求人的全部行为能力的生产规划,替代了一种在“劳动的类生活”中对人所特有的需要进行对象化的人类学规划的位置:“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12)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Rohentwurf), Frankfurt/M./Wien, o. J., S. 505, S. 397, S. 584(作为大机器生产的对比景象); vgl. K. Marx, Das Kapital I, Werke Bd. 23, S. 362 ff., S. 4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同样,居于“巴黎手稿”核心的异化劳动概念,本应用来刻画一种塑造主体性的劳动行为在被产品所支配的劳动活动中的颠倒特征,而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中使其与机械化的、分解了的工业劳动的资本主义现实相适应。在“抽象劳动”标题下,资本分析试图将资本主义典型对劳动活动内容的抽象过程规定为一种价值实体的现实生成,而马克思则描述了所有手工业劳动行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逐步瓦解:“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全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13)K. Marx, a.a.O., S. 204 f.; vgl. ebd., S. 584 f., S.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此后,这一类摆脱劳动主体经验知识的、被分解成盲目的零散操作活动的劳动行为,对马克思来说构成了他以手工业模式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劳动形式的对立面。然而,这样一种分析结果就使他现在陷入两种社会历史之劳动形式的二元对立之中,仍缺乏概念手段去把握可能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教化过程。如果马克思在这个激进的位置上遵循其早期的意图,那么他似乎就会把劳动过程直接理解成一种释放实践—道德动机的教化过程,从而他似乎就必定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规定成一种交往关系,在这种交往关系中,手工业劳动过程中诸劳动主体间的对象化特征的要求就不会丢失:在其中,劳动主体总是已经反事实地(kontrafaktisch)抢先触及一种自身封闭、自我控制以及描摹知识的活动实施维度。然而,这样的思路并没有在马克思这里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为了在其经济学著作的框架内依然能将革命化的力量继续加之于劳动过程,他选择了一种工具主义的论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仅仅承担一种无产阶级的组织媒介和纪律媒介的角色。
这第二种思考模式不再论证手工业—有机的劳动与机械化的工业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而是线性地遵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阶段。马克思所进行的视角转换在方法论上使其被迫重新规划其在资本分析中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根据内在批判的蓝本让社会行为关系自身只在诸资本规定形式下被主题化。马克思在其论证模式中考虑到,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劳动过程似乎会使工人阶级社会化为一种有纪律、有组织以及有技能的集体主体。三个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的假设融汇在这种看法之中:第一,资本的集中总是会在某个生产地点聚集更多的工人,以至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在直观上变得显而易见;第二,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技能发展培养了工人的合作能力,同时发展了他们的自我约束;第三,工业相关教育机构内的生产力在技术上的继续发展,最终使其超越了工具性的行为权限,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知识储备。这种假设的结果是,马克思能够从压迫的经验、理智的加工工作以及严守纪律的反抗准备之间的一种持续反馈过程出发,在此过程中雇佣工人的社会阶级会奋起反抗资本主义。在这种革命理论意义上,马克思才提到“工厂学校”:“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14)K. Marx, Das Kapital I, a.a.O., S. 790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
在类似此处的地方,马克思依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框架内坚持一种以革命理论方式被要求的劳动概念。但是,替代那种论证模式(即努力直接从劳动的教化潜力出发来阐明社会解放之可能性的论证模式)的,是一种要求稍低的模式,即工人阶级通过工业化的工厂劳动得到技术培训和纪律化的模式。在其有关社会劳动的晚期著作的经济理论中,当马克思想从劳动中的行为经验来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观念时,他显然不再相信他必须假设的实践—道德的学习潜力,毋宁说他只是还想假定一种技术上的教化过程的学习潜力,这种教化过程策略性地支撑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第一种论证模式使他陷入疑难,即必须恰好为社会异化状况预设一种道德—实践的、在规范性上澄清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关系的劳动教化潜力。而按照他自己的分析,这个社会异化状况却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掏空劳动行为的直观化特征,从而掏空其教化潜力。而马克思的第二种论证模式则完全处在这一要求之下,即要设定社会劳动在革命理论意义上享有特权:马克思在这一论证高度上只能解释,无产阶级如何理智地呈现其早已发展出的规范—批判性的解放意识,以及如何学会策略性地将这种解放意识转化为革命—实践的行为能力。然而,这种解放意识的教化过程本身应该以何种方式在社会劳动的行为结构中被锚定下来,在这一论证模式中最终仍然是无法澄清的,亦如在其早期著作中那样。
劳动概念在革命理论意义上的要求显然将马克思带入一种基本概念困境之中,他已经不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他对劳动行为在解放理论上的重新评价给思维所施加的强制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在理论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试图将应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学习过程归结为社会劳动的内在关系,而没有为这种归结提出一种行为理论上令人信服的论证模式。这一范畴上的两难困境的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激发了大量的理论尝试,它们都试图借助扩展了的诸论据把社会劳动的解放意义解释清楚,以能够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一系列的阐释尝试中,对革命理论的客观主义理解表明了对马克思意向的弱化:贫困化理论的普通心理学规划(15)Vgl. Wolf Wagner, Verelendungstheorie-die hilflose Kapitalismuskritik, Frankfurt/M. 1976.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版本(16)Andreas Wildt, Produktivkräfte und soziale Umwälzung, a.a.O., S. 211 f.都是某些阐释的例子,这些阐释精确地切除了对社会解放与社会劳动之间关联的追问,而对此问题马克思则试图用手工业—有机的劳动形式与被以资本主义方式分解的工业劳动之间的张力来回答;在这种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之革命化后果影响的追问是有其位置的。以这种方式,就完全无法看到马克思疑难的诸多维度,因为使政治解放过程得以可能的条件不再在行动主体的社会经验层面上被设定,而是被高高地投射到独立自主的体系进程层面上。当然,在这种传统路线之外,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也有一种哲学—反向的传统,这种传统试图自身在一种实践哲学的论证高度上回答马克思理论中所蕴含的关于劳动与解放关联的问题。
二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经验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手工业的—充满感性的劳动形式与工业自动化活动方式事实上同时并存,因此,其理论的这一核心概念的复杂性,乃是对其时代的那些社会劳动形式之间的事实平等的某种范畴表达。这种局面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被第二次大工业化的推动所打破。对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来说,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利用技术进步,以及在经济上开发新能源,逐渐将可感受对象的、可直观检查的手工业活动形式从直接生产的中心排挤出去,并将其推到二级生产(维护保养,劳动准备)的经济边缘地带——在这种手工业活动形式中,马克思同黑格尔一道都明确看出了劳动行为中一种对象化的可能性[2]Teil II。随着工业大型企业的繁荣以及向可控工序的大规模生产的过渡,单个劳动行为被分解并且与机器的机械强制节奏相适应。这种在经济上对人的劳动效率的优化,构成了支撑1896—1913年这段繁荣时期经济快速且相对平稳增长的基础。在那之后,对科学—技术合理化的革新就在为资本主义所利用的压迫之下被持续地转化为对工业劳动形式的生产技术合理化。
劳动行为技术的彻底合理化关键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分析发端于泰勒(F. W. Taylor)的工业研究,他的研究都归结为科学的生产管理概念——它预先计划了在企业管理中所有与生产相关的知识的集中,而企业管理借助于精确的活动观察与时间观测又将单个的生产步骤与劳动操作分解成一些基本元素,并在排除损耗时间的情况下重新规定活动顺序,在这条路上弄清楚经济上最有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已经区分出了三种劳动组织的指导方针,而开始泰勒制化的劳动过程的结构转变就遵循这些指导方针:(1)工业生产过程会系统地摆脱劳动主体的技术知识。布雷弗曼将其称作“劳动过程与工人的熟练技巧之间的分离……必须使劳动过程独立于工人的任何手艺、传统以及认识”[2]93。(2)此外,在工业企业的组织中,技术计划活动会与手工劳动实施过程严格区分开,以至于(3)最后企业管理机构化的知识垄断使得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成为可能。“在科技革命的时代,管理层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从整体上去把握过程并毫无例外地控制其任何元素。”[2]134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经济合理化,即布雷弗曼以这样的主导观点所描述的那种合理化,通过科学上受过训练的企业管理层逐步剥夺了工人阶级共同协作的口口相传的经验知识,这种合理化此时导致了一种对劳动过程高度分化的分解。工人的技能水平并不伴随生产的诸机械化阶段而整体性地得到提高,而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极分化:在不熟练的新劳动形式方面,简单的手工劳动和工业生产中重复性的部门劳动都增加了很大的比重,而理智—复杂的与激发积极性的劳动形式则只占据劳动岗位中很小的比重。(17)对于德国1950年之后技能要求的发展,Friedrich Gerstenberger给出了总结,即一种对高技能命题的批判。vgl. Friedrich Gerstenberger, Produktion und Qualifikation, in Leviathan, 3. Jg./ 1975, Heft 2, S. 251 ff.伴随着这种社会劳动形式的变化,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人阶级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天已经丧失了其经验上的说服力;在革命理论意义上设想一种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劳动中理智的和战略性的社会化,在大量的去技能化(Dequalifizierung)过程的现实面前是失败的。同样,伴随机械化劳动形式的全球化,深层的概念张力,即早期马克思试图将社会劳动解释成一种实践—道德上的学习过程,也失去了所有原初的生动清晰性。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结构变迁,使得马克思由于其对劳动概念的革命理论阐释而陷入的范畴困境彻底变得显而易见。
现在,社会劳动形式划时代变革的同一过程自然反过来从一开始就决定性地限制了马克思之后社会理论发展中的劳动概念所采取的立场。随着工业劳动的泰勒制化,在资本主义的利用命令下早已开始的生产技术合理化达到这一门槛,即大多数社会劳动行为丧失了手工业的—自成一体的活动特征。自世纪之交以来,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诸理论在工业劳动以泰勒制的形态迅速机械化所可能造成的经验压力下,在如下这种程度上逐渐瓦解了劳动概念,即劳动概念那种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主张的、在已然清楚的技术—经济功能面向之间的解放理论的意义元素,已经从这些理论视野中消失,并被转移到文化批判的陌生化框架中去。
社会学历史提供了一个关于劳动概念逐步清除其规范性传统内涵过程的突出例子。这里,这一概念简化的背面就是,在与工业劳动过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劳动行为独立成为这样的劳动效率,其社会组织方式主要从提高生产率的方面来考察。这一概念变迁伴随着社会哲学研究,这些研究有针对性地对18世纪末以来哲学的劳动概念所具有的范畴上的特殊地位进行质疑。
在20世纪初,劳动社会学首先以经验性的统计数据形式出现在德国,这些统计数据使工厂劳动对工业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意义成为问题。阿道夫·莱文施泰因(Adolf Levenstein)及其团体对社会政治的早期研究,将社会科学上的、借助态度征询和案例研究对变化的劳动条件所进行的分析嵌入到一种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之中,这一框架追问机械化工业劳动的文明化后果;因为它们在其核心范畴的框架内仍然带有一种劳动概念,在19世纪的社会哲学传统延续过程中,这个劳动概念相信改变自然的生产活动具有塑造人格的力量,所以这些研究也能分析性地整理出工业劳动过程一种不可阻挡的合理化的消极后果。克里斯蒂安·冯·费伯(Christian von Ferber)已经在“劳动愉悦”(Arbeitsfreude)范畴上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方式研究了这种规范性内涵,第一代工业社会学家们的经验性研究范畴工具中就涉及了它。德国社会学初期的劳动概念,尽管未能达到反思水平,却依然完整地传达着解放理论的希望。而带有早期工业化痕迹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则将这些希望寄予社会劳动的启蒙与教化作用上:“劳动是文化过程的支撑部分,借助它每个劳动者至少根据理念要共享统一的文化。劳动通过有助于劳动者情感和精神体验的抒发,构成了一条优先培养人格的道路。简言之,劳动除了其经济功能之外还居于文化和伦理上的关键地位;它是历史力量的结果和展开。”[3]16当这种劳动的文化概念的社会结构前提已经在历史上丧失其意义时,冯·费伯把这一劳动的文化概念——20世纪初工业社会学的统计数据都共同地将其作为前提——追溯到一种手工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的传统中,而这种社会形态之后也依然会在具有社会解释力的学院社会学中继续起作用。这一早期劳动社会学在文化理论上的认识兴趣不仅从这样一种规范性视角获得其社会理论上的解释力,而且得到了其有限的应用可能性;这一视角将手工业的—渗透感性的劳动过程的特定生产状况理想化,以至于在这一积极的背景面前,机械化工业劳动的文明化后果就能够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可是,这样一种从文化理论提问与经验的劳动社会学之间的相互促进中产生出来的工业社会学的批判和解释之成就,必须——在克里斯蒂安·冯·费伯所建议的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在这种时刻停止,即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旨在感性地洞穿一切社会行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图景来说,没有任何社会的支撑性群体成长起来;伴随手工业阶层被边缘化,劳动的文化概念也失去了其工业社会学意义。直到现在,以一种手工业劳动理想形态引导工业社会学的解释动机,随即变为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批判的倒退乌托邦,其中手工业劳动理想充当着一种彻底技术化世界的纯粹对照图景。但是从现在起,一种与一切规范性视角无关的工业—企业社会学便替代了文化理论的劳动社会学。
社会学在这一理论发展中失去了社会哲学的问题关联,这种问题关联会在顺利归类之前就保证社会学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之中,只要社会学已经以一种超越实际劳动社会形式的劳动概念为前提。然而,现代工业社会学被系统地纳入生产技术合理化的螺旋,其中每个科学上觉察到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效率缺口都会被一个新的、经济上更有效率的劳动组织所补充。以这种方式进入社会学的劳动概念,总是把工业劳动过程的研究限定在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合理化螺旋来确定的维度;这个劳动概念不允许通过曾经已建立的劳动组织去探究,并且禁止质疑工业劳动自身的机械化程度。工业社会学转变成一种合理化科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业繁荣期,以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带领下的霍索恩研究(Hawthorne-Studien)为历史开端,霍索恩研究意外地触及了工业大企业中劳动效率的交往和企业氛围的条件。自那以来,为了能够系统地掌握各种新的经济上的生产性缺陷和政治对经济效益的危害,工业社会学一步一步地推进到工业劳动的行为层面;工业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多次围绕进一步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方面“在主题上得到扩充”[4]92,(18)Gert Schmidt在如下过程中使用这一术语,即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合理化螺旋的工业社会学遇到了劳动行为一直新颖的、“能够合理化的”层面。但是从泰勒制中得到的、在企业组织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导方针实质上并没有被抛弃。劳动概念在这一(仅仅被少数从社会理论上做了反思的工业社会学例外地挣脱的)发展过程中,在主题上仍然是通过在生产技术合理化过程中所确立的研究优先性而被外部规定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直到进入德国工业社会学的早期,人们在劳动概念上总是去连带着思考一种渗透着感性的、自我调节的,以及不能与对象分离的活动方式的可能性,这种活动方式在手工业劳动直观生动的完整性上找到了其经验表达,然而现代社会学已经几乎放弃了这个规范性方面。
在社会哲学基础上,劳动概念逐步中立化,这种中立化是在泰勒制直接的压力下发生的,其伴随着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在19世纪借助哲学上极其不同的手段追问并消解了劳动概念在解放理论上的特殊地位。这条社会哲学觉醒之路的理论里程碑,有马克斯·舍勒现象学哲学的一些部分,以及汉娜·阿伦特那本哲学代表作即《积极生活》(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其于1960年在德国出版[5]。
社会劳动从18世纪开始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哲学中就具有了一种特殊地位,马克斯·舍勒一生都在批判性地钻研这个规范的特殊地位,劳动的活动类型不仅构成了他质料价值伦理学的否定一极,而且也构成了他社会学文化理论的否定一极:在对劳动伦理称颂的批判中,舍勒以现象学方式奠基的伦理学间接地关涉到如下社会历史过程,即他的文化社会学在技术—目的理性知识形式侵入公共生活道德目的系统这个观点下所批判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一否定定位构成了他1899年发表的文章《劳动与伦理》的主导观点,这篇文章出于一种马克思之后让哲学与国民经济学重新接近的兴趣,明确以批判政治上的近代劳动意识形态为目的;它有助于对基督教所传达的劳动概念进行系统革新。为了表明劳动活动代表一种必然的外在约束和控制的行为类型,舍勒希望使用一种方法上无限制的概念分析手段:只有自然对象制约着劳动活动的时间结构及事实结构,公共实践的客观目的设置才赋予了“进行劳动”一种行为意义。劳动行为类型原则上并不具有一种自主开放的、可自我规定的活动特性,而只是满足一种工作的负担与劳顿的单纯特性,以至于一种塑造主体性的意义在规范上是不允许被加于其上的:“对‘劳动’的估量是要考虑不愉悦因素的,并且这同样在语言使用上也得到辩护,即‘劳动’意味着再三‘受苦’(leiden)、‘操劳’(sich abmühen),正如古老的、在人类的书籍中所传达的各民族的思想,即‘劳动’是一种来自原罪的恶报。”[6]174
舍勒显然已经在范畴上将劳动行为引入代表着机械化工业劳动层次的社会形式。他的概念分析的推断,即“了解事实上的‘为何’比起促进(劳动)反而更加损害活动恰当的劳动特征”[6]178,干脆明确地泄露了其论证的这一现实背景:因为随着在泰勒制中生产技术开始合理化,劳动知识才开始系统地跟劳动活动相脱离,并且感性的、自身完整的劳动行为才开始全盘分裂为部门劳动作业。当舍勒仅仅给劳动以一种有缺陷的、缺乏反思的行为方式地位时,他必定已经以劳动的本质特征来重新解释这些部门劳动了。在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在这里,舍勒的道德哲学思考接近了汉娜·阿伦特的行为哲学论证。阿伦特的研究旨在以时代批判的方式复活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出于因畏惧一种机械式自我调节的劳动社会图景而作出的当代诊断视角,其研究着手进行概念史的尝试,即透过人的行为方式网络回忆起为语言所中介的互动的实践形式,在这种互动中,只有人的世界一直作为公共—政治的生活关联存在下来。但是从一开始,阿伦特也如此来安排其哲学行为理论的概念系统,这种概念系统只以在机械化工业生产中才获得其最终形态的社会形式来理解劳动。
阿伦特在《积极生活》中系统地区分了三种基本行为范畴,她将行动(Handeln)的主体间活动方式跟劳动(Arbeiten)和生产(Herstellen)这两种本质上非社会性的活动类型区别开来。劳动和生产共有一种行为结构,这种行为根据技术规则在操作层面改造自然现实,不过劳动和生产彼此之间也以对象成果而相互区别。劳动是直接进入类的有机再生产过程的活动方式,在这种活动方式中人可以得到直接对生存有用的产品,不过人在对来自自然界的材料进行生产的行为中就建立了一种持久的且仿佛人造的环境:“我们双手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身体的劳动,手工艺者出于生产的目的对预先给定的材料进行加工,而不是劳动的动物在身体上与其劳动材料的‘结合’,以及对劳动结果的同化,它们制造出了事物几乎无限的多样性,而这些事物的总和组成了由人所建造的世界。”[5]124与此相反,行动与一切物质联系无关,是语言和行动相交叉的实践方式,在其中人类主体彼此相遇,并在借助彼此来揭示的共同性保护下相互表明各自的主体性。阿伦特真正的兴趣就涉及这种行为类型。她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这一概念将以自身为目的的无后果的行动(实践)与依照一种行为外在目的的制造行为(制作Poiesis)相区分,从而表明只有处于语言中介行动结构中的交往实践才展现了一种人特有的生命再生产阶段——虽然劳动和生产这些与物质材料相结合的活动形式也保证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而且近代从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开始,就在人的行为类型评价体系中给它们分配了最高地位,但是只有主体彼此之间的交往行动开启了一种符合人的和在历史上开放的类生存的可能性。唯独这一行为方式为人的生活利益确保了公开的透明性,为诸社会团体赋予了文化同一性,并且给了政治—实践革新以社会空间:“一种没有所有语言和行动的生活……就简直不再是生活似的,而是一种被拖入人生长度的死亡;它似乎不再显现于人的世界中,而是仅仅让自身作为一种消逝的东西总体上被觉察出来。”[5]165
这一行为理论上的差异为当代分析提供了范畴框架,其中阿伦特以世界的异化这一主导观点来诊断现代。行动领域向来是极其不稳定和脆弱的,因为它自身要不断地为实践的积极性敞开,并且没有任何对象性的中介。而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这一领域一点点地被掺入了非社会性的诸活动形式,首先是生产,接着是劳动;它们逐渐吸收了那所有塑造主体间性的和创立传统的生活形式,而这些生活形式据说可以单独确保一种合乎人性的人类世界的再生产。《积极生活》的全部批判都是针对这种技术行为方式的凯旋队伍的;与它相比,任何让马克思的劳动行为社会理论超越经济再生产功能方面的其他意义的维度就完全不重要。汉娜·阿伦特在范畴上将劳动梳剪为可再生产劳动力的纯粹机械消耗,她看到了人的活动总体当前正萎缩为这种看似自动化的劳动作业的行为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她将内在于劳动的那种生动的、在事物联系中可检验的自我经验分离到生产行为领域中,相信其只具有建立“自我确定性”(Selbstgewißheit)和“自我感”(Selbstgefühl)的力量,而马克思则是将这种自我经验纳入他的劳动概念意义范围[5]127。由此,在手工业劳动中,最初曾是未分化的诸行为元素,而在汉娜·阿伦特的基础概念中则最终分裂成两种活动类型,即具有反向的—身体上的劳动作业与充斥着经验、手动的工作活动,区分了劳动与生产;劳动的情况已经固定,它才是工业劳动泰勒制化的历史产物。阿伦特在劳动和生产之间画出的行为理论分离线,描摹了实际的劳动社会形式;而对于批判地反问这些实际形式背后的东西,阿伦特自己的基本概念是不允许她再去做的。所以在《积极生活》中,只是机械技术性的行为模式对政治实践领域的侵入受到批判,而并不是劳动自身的逐渐机械化受到批判。
汉娜·阿伦特和马克斯·舍勒的分析属于社会哲学研究,而这些研究从工业劳动诸形式的历史水平落差中只得到了肯定性结果,因为他们在范畴上将劳动行为从任何解放理论的意义视野中抽离出来。他们共同使用的被剪裁的劳动概念的基本经验就是在生产技术上合理化的劳动行为。工业劳动在科学上被合理化系统地始于大约19世纪末,劳动行为实际上分解成一种简单的、标准化的诸单一行为,以至于在其中几乎不能再认出一种塑造主体性行为的诸结构。
但是,这一改变了的劳动社会关系现在也构成了理论史的起始状况,其中马克思无法解答的社会解放与社会劳动关系问题,树立在了哲学上持反对立场的马克思主义面前。马克思试图将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劳动过程解释成一种社会革命的教化过程,这种尝试使得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部分要面对下列任务,即让解放理论的行为理论基础适应当前变得明显的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现实。就笔者所见,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概念策略,其中一种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理论式的社会哲学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一方面是将马克思加之于具体劳动行为的全部解放潜能交给一种先验主体或共同主体的劳动实践;另一方面则是将劳动行为单一化为一种仅仅实践上控制自然的行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进行了这种单一化。这两种解决方法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验坐标系内消除马克思劳动概念在解放理论上无法解决的张力(泰勒制化的工业劳动背景让这一张力最终显现出来),毋宁说它们以某种方式在历史哲学上将其蒸发掉。
第一种进路简单地将塑造主体性的力量——联系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劳动活动具有这种力量——与劳动的经验社会形式相分离,并将劳动投射进一种超个体的行为过程的反思进程之中;而解放的反思成果会被具体的劳动行为转给一种社会阶级的共同学习过程或者类在整体上构建世界的生活实践。第一种情况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二种情况是马尔库塞的早期文章和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文,它们都必须为这种对解放理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之历史哲学式的拯救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就是一种几乎不再被工业劳动关系的现实性反向中介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这两种以不同方式激发出来的类型,只能坚持社会解放与社会劳动的关联,因为它们将马克思从一种手工业的、富有感性的—完满的劳动行为上看出的诸特性赋予了一种表现为劳动的集体行为。在卢卡奇那里,这种情况就是,采纳黑格尔逻辑中所陈述的精神自我运动,将其映射到一起思考的无产阶级的所有单个社会劳动步骤的反思过程之上[7]257ff.:恰恰在萎缩成其商品特征的劳动活动中,在异化劳动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才能揭露物化形式,这一物化形式用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的普遍化来掩盖一切社会生活关系,而无产阶级也才能认同自身为这种生活关系中创造使用价值的主体。为了得到一种无产阶级自我认识的理论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要连接上这种集体的、锚定在劳动过程中的反思进程。与此相对,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自己的早期文章(19)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Herbert Marcuse,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in Schriften, Band 1, S. 556 ff.; “Zum Begriff des Wesens”, in Schriften, Band 3, S. 45 ff.对这一社会哲学的劳动概念的分解,出现在马尔库塞系统考虑泰勒制化的劳动关系的著作中。Vgl. Herbert Marcuse, “Einige gesellschaftliche Folgen moderner Technologie”, in Schriften, Band 3, S. 286 ff.中参引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将一种人的历史性的基本结构意义赋予劳动范畴。他通过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解释,意图谋求一种革命理论,其中无产阶级能够扮演历史行为主体的角色,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将所有那些与人的此在——作为进行劳动的活动——整体上相适宜的特性现实化。最后,让-保罗·萨特的文章《唯物主义与革命》[8]52ff.将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动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解释传统,在这篇文章中,这些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共享的概念策略获得了最清晰的轮廓。正如早期马尔库塞那样,萨特也将本体论上的劳动解释成人的此在的基本活动方式;但是联系到黑格尔,他给劳动赋予了一种行为特性,借此劳动主体在自然对象的赋形中经验到了其自己的自由。在萨特看来,劳动与解放以这种方式同时发生,因为无产阶级是诸劳动主体的社会阶级,它也就是先天有能力进行革命的集体主体。“事实上,受压迫者的解放性元素就是劳动。在这种意义上,从一开始是革命的东西,就是劳动。它一定是被命令才首先采取劳动者受奴役的形态……但是同时劳动也在这种极限情况下推动了具体的解放,因为它早已同样意味着对统治者的那种偶然和无常的规则的否定……由于劳动者依据一定的普遍规则对该对象产生影响,他便把自身当作是将一个物质对象的形式改造成无限的东西的可能性。换言之,这就是物质的决定论,它为劳动者奉上了其自由的第一幅图景。”[8]90-91萨特的论证落入了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以不同方式所走向的同一结局:因为这三者全部想坚持社会解放与社会劳动的内在关联,而不必另行选择一种确保进步的生产力增长的客观主义设想,他们将其不再相信的工业劳动实在所能具有的解放潜能,给予了一种在其自身中可以一起思考所有单一的、经验上被分解的劳动进程的集体主体;那么这一主体在范畴上似乎就接受了之前为单个劳动主体所占据的角色。因此,在这个理解中,一种通过劳动的解放构想就迫切要求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独白式概念,并且这一主体已不再跟工业工厂中的实际劳动经验相结合。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展开的历史哲学论点,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所有这些(以社会哲学的方式后续发展出的)关于被嵌入社会劳动结构中解放潜能的构思的反命题。虽然《启蒙辩证法》表达的是一种跟卢卡奇的马克思阐释相关的物化批判,但是在其范畴框架中劳动总体上丧失了一种解放性实践方式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劳动成为行为实践的基础以及统治的历史原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卢卡奇从商品交换的社会一般化历史进程中推导出的同一个物化过程追溯到行动主体跟自然一般的主动争辩。在他们看来,文明从自然强权那里的解放,只能在人的劳动活动中才能实现,劳动中对于外在自然的技术支配是与对内在自然的压制交叉在一起的;为了有助于从这种自然强制那里获得解放,与劳动相结合的认知成果从一开始就带有合理性特征,这一合理性在支配视角下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无差别地客体化。因此,人类的文明解放总是用一种工具理性的形成换来的,在社会进步过程的背面,人系统地扩大其对外在自然的控制,这一背面是一种社会的物化过程,其中人逐渐丧失了其内在自然,因为他将内在自然如同外在自然那样对待。(20)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 1969.对于改变的劳动概念也可参考Theodor W. Adorno, “Marginal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10/2, Frankfurt /M. 1977, S. 759 ff.
为了能解释这一社会物化过程的起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历史哲学视角下,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到人的社会文化原始条件,而这种历史哲学视角则从劳动行为中去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至今仍作为基础的所有塑造主体性的作用。劳动为此只能代表这样一种活动,为了能在操作上进入自然过程,劳动主体学着去塑造和控制其自身的驱动潜能;而一种整体上被主体的行为规划所操纵的、逐步阐明自身能力的劳动行为的可能性,则在理论上不予考虑。(21)这当然仅适用于批判理论的《启蒙辩证法》时期,遵从Helmut Dubiel的历史分期,即从40年代初的诸著作开始(Vgl. Helmut Dubiel,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lsche Erfahrung. Studien zur frühen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 1978, bes. S. 87 ff.)。由此,批判理论自然就陷入一种特有的论证强制之中,因为批判理论原则上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劳动哲学范式,即坚持一种仅被裁剪成改造自然的行为模式,那么它也只能将与社会物化关系相对获得解放的社会图像带入社会化的个体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之中。因为阿多诺哲学在范畴上将社会劳动重新解释为统治的行为实践基础,除被裁减为仅仅关涉自然的概念框架,阿多诺哲学甚至被放弃,被迫成为一种美学的哲学规划,这种美学在理论上勾画了一种非工具化的、模仿式地与自然打交道的可能性:如果对劳动中自然关联客观化把握总会造成社会关系在统治上的改变,那么一种在美学上与外在自然协作的状态也才允许对内在自然做无统治的解释。因此,以这一历史哲学视角拟定的批判理论的核心观念是一种“与自然和解”的动机。
《启蒙辩证法》的批判理论跟卢卡奇、马尔库塞和萨特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诸尝试,共享其行为理论的有关框架:社会劳动只为这些理论规划呈现了社会的实践维度,在此之上人类世界从自然的生活关联中产生并在社会文化上再生产自身。而表达出这个基本观念的范畴框架,是按照关系到外在自然的社会行为来设置的,他们的模型是在实践上关联自然环境的主体。因此,他们共同预设的行为模式迫使这些理论规划将社会解放的可能实现与一种意识形式结合起来,虽然这种意识形式形成于与外在自然的行为关联之中,可还是远离历史上经泰勒制劳动形式的普遍化所实现的诸劳动关系。一方面是一种理想化的、超个体的劳动过程的历史哲学构想,另一方面是一种无压制的、模仿性地与自然打交道的美学构思,它们都是试图解决问题的理论手段。哈贝马斯尝试用一种交往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基,才挣脱了造成这些概念策略的主体—客体模式。他从劳动概念的稀释中得出了最关键的结果,这种稀释在泰勒制劳动形式的经验之下影响了这一世纪社会哲学的概念构造。哈贝马斯学会了汉娜·阿伦特在回忆中引入的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制作的区分,以便让主体间沟通的行为类型提升到解放理论的地位,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劳动曾占据着这一地位。这种范式转换给哈贝马斯理论的整体建筑术打上了烙印——当然最终的代价是在范畴上遮蔽了自身锚定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中的诸反抗形式和解放形式。
三
马克思在解放理论框架中设想了一种社会解放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关联,而这一解放理论的历史基础自19世纪以来已经发生改变,即这个世纪批判导向的社会理论几乎没有一个相信社会劳动过程在经验上还具有意识教化的、解放性的力量。劳动形式的社会变迁似乎已经耗尽了劳动概念自身。在这一范畴张力中,马克思让劳动概念保持在异化和非异化劳动活动之间,保持在以手工业方式组织的对象加工和以机械方式分解的部门活动之间,而没有为进行中介的反思过程本身占有概念上的成套工具,这种范畴张力已经被逐步消解进这个概念的一个方面,即仅仅反映诸社会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劳动概念在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中已经丢失其批判的、超越已建立的劳动社会形式的意义。凭借“异化”或“抽象”劳动等范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而这些范畴几乎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哲学理论语言中消失,因为一种有关符合人的、也即非异化的劳动形式之文化上独立的标准似乎并不存在。同样,诸主体根据由科学上受过训练的企业管理层所设立的规则参与社会生产,而其行为要求和劳动观念对于新近的社会理论也已经失去意义:这些理论作为职业抱负沉浸在以经验方式进行的工业研究中——这些理论对于当前社会系统主要冲突的批判性诊断,几乎不再占据决定性分量。今天无论是马克思资本分析的概念实在论阐释,(22)Stefan Breuer, Die 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Frankfurt/M. 1977.还是一些在“占有”(Aneignung)主导思想下所进行的转换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23)这里主要指Andreas Wildt的文章《生产力与社会变革》(Produktivkräfte und soziale Umwälzung)。Wildt在这篇文章中建议了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转换,这种转换会使源自非暴力的、类感性的占有潜能之历史展开——也即(意识到)不再源自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框架——的革命社会运动解释成为可能。但笔者认为对这一概念的社会理论规定角度太狭窄:它既不以能结合实验性的—审美的行为方式的多样规范性内涵为主题,又不以能显现这种“占有力量”的社会结构上的冲突领域为主题。笔者也没有看到,这两个问题在维尔特粗略提出的范畴框架中应该如何得到解决(对此问题,原文注释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此处进行了删减,未完全展现)。都给出了在批判的社会理论框架内主题变动的例子。
在这一发展中,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占据着关键位置:批判的社会哲学将仅被设置成改造自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行为模式扩展成为一种适应主体间交流过程的行为模式,而这一批判的社会哲学之主体间性理论转向的优势也会被一种在行为理论上忽视诸社会劳动形式之冲突内容的劣势所取代。
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动机,来自阿伦特用《积极生活》中行为哲学分析所回应的同一个当代经验: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技术进步和社会解放之间差异的典型抹平,通过以目的合理方式所组织的行为体系,使交往上社会化的生活关系枯竭,这些如此广泛地规定和危害当前的社会体系,以至于哈贝马斯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集中到对这一发展趋势的阐释上来。对劳动和互动、工具性行动和交往行动的区分都服务于这一任务。在对马克思的批判中使用这一区分之前,哈贝马斯就在其认识论作品(24)Vgl. Jürgen Habermas,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in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M. 1970, S. 9 ff.; Jürgen Habermas, Gegen einen positivistisch halbierten Rationalismus, ebd., S. 39 ff.中提出了这一区分,这些作品为一种语用学的、偏离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批判做了准备。哈贝马斯并没有如同阿多诺接着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所做的那样,将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跟商品交换的抽象强制联系起来,而是将其追溯至思维操作上,而这些思维操作是被捆绑在对自然熟练改造之上的。工具性活动的实施意味着社会生产在文化上具有稳定的行为基础,而其实施规则在哈贝马斯认识论的语用学中占据着这样的角色,即伴随资本主义一起普遍化的交换行为的抽象规则在索恩·雷特尔社会发生学式的认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哈贝马斯的论证视角下,科学模式只能使这样的思维操作固定下来,也就是以前科学方式设置在支配自然的技术实践中的思维操作,而这一模式仅仅随着其在社会现实对象领域的扩张,才变成批判能力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当实证主义在科学理论上所表达的认识规则本身已经不存在时,实证主义那种与其解释模式相联系的普遍性要求在认识论上就是错误的。
这种首先只意图批判实证主义的思考,目前当然会激发人们在认识论上去定位人文科学:因为如果自然科学的理论建构在掌握自然的类历史过程中应当被确定下来的话,那么人文科学的理论建构必须回溯到一种前科学的经验过程,类正是透过这个过程在实践上再生产自身的。哈贝马斯将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追溯到“工具的”和“交往的”实践这两种行为方式的区分,(25)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n/M. 1968, S. 48 ff.;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 1968, Kap. I.从而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异以语用学的方式建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两面性的基础之上。正如自然科学依照引导认识的兴趣来支配自然一样,人文科学也被主体间沟通的保持和扩展的兴趣所主导,这一兴趣伴随着人的生活形式的语言化成为一种类所特有的生存的应当(Überlebenssoll)。(26)Vgl.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in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ldeologie”, a.a.O., S. 146 ff.这两种相互之间不可归因的行为准则——一方面掌控着工具性的对自然的改造,另一方面又控制着交往性的主体之间的沟通——确定了两个前科学的经验领域,而哈贝马斯则基于一种先验的语用学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绑定在这两个经验领域上;它们的区别同时开辟了认识论的道路,哈贝马斯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结构奠基于其上。
这一认识论的开端问题呈现了哈贝马斯首先展开其行为理论诸规定的框架。他最初对这样一些认知成就感兴趣,这些成就被系统地嵌入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实施过程之中。哈贝马斯在一种范畴高度上提出回答这一问题所需的行为概念,这一高度一方面以盖伦(Arnold Gehlen)的人类学行为理论为标志,另一方面又以继承米德的行为理论社会学为标志。在行为理论社会学传统中,社会科学的客体领域会被理解成一种现实性关系,而诸社会化的主体在社会行为中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这种关系。在他们彼此相互联系的行动中,解释其行为状况的诸社会成员创造了社会现实,而之后社会学才遭遇这一现实。社会学理论上的特殊地位,源自一种客体领域的特质,这一领域早已被诸行为主体的解释预先构造。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了这一基本预设,这种方式赋予他米德式的主体间性理论方法:这里社会行动被理解为一种交往过程,在其中至少两个主体通过符号主导的协调一致,使他们的目的导向的行为合乎一种共同处境的定义;一个符号中介的交互过程要求参与的诸行为主体不断地进行解释,在这些解释中,他们必须带着一种理解行为处境的目标,相互破译他们的行为意向。哈贝马斯在被语言分析哲学所采纳的重建交往言语行为的道路上继续探究这一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规定了其社会理论的范畴架构。他构想出有关这一行为类型的社会实践方式的总体谱系,以至于所有非沟通理解导向的、但却是社会指向的诸行为都转变为交往行动实践上的偏差。交往行为模式按照可能性揭开了社会行动的总体范围,在这个总体范围内,并不能被把握的人际间的诸行为过程,其数量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个社会的物化程度,也就是这样的规模——社会生活背景而非超越了沟通理解取向的行为协调于在社会结构中被强制的行为轨道上再生产自身的规模。由此,哈贝马斯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交往行动概念提升为规范性的和经验性的关键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概念以一定方式呈现了这一概念:它一方面有助于经验过程的分析,在这个经验过程中,社会生活背景只能借助这样的方式在文化上自我再生产,并在社会上自身整合,即这些关系至少允许交往的沟通理解过程进入社会行动的部分领域;另一方面,为在规范性上评估社会生活背景在其互动形式交往内涵上的自由程度,提供了分析的尺度。(27)Jürgen Habermas, “Einleitung: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die Entwicklung normativer Strukturen”, in Zur Rekonstruc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S. 9 ff.
交往行动概念在这一阐释中所获得的解放理论意义,对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来说,使得劳动概念的功能缩减了;在其范畴框架中,只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行为基底这一任务落到他身上,而交往上的解放过程是被这种生产力发展衬托出来的。哈贝马斯区分了保留在交往行为中——因为交往行为自身之中的目标乃是非统治的沟通理解——的道德—实践的合理化潜能和对自然的操作加工相关的技术合理化潜能,只有系统地利用劳动主体为了支配自然过程而培养的工具性知识,社会生活背景才能在经济上确保其持存。哈贝马斯将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分解成两个合理化维度,借助于这一区分,把批判的社会理论从解放理论的混乱中释放出来。而马克思理论的劳动哲学范式似乎导致了这种混乱,因为它让技术进步与社会解放的界限模糊了。“当工具行动同外部自然的强制相一致,以及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技术支配自然力的大小时,交往行动就同自身的自然压制相一致:制度框架借助于社会依赖性和政治统治的自发力量决定着压制的大小。一个社会要想从外界自然力量获得解放,需借助于劳动过程,即要借助于技术上能使用的知识的生产(包括自然科学向机器的转变);成功地从内在自然的强制中解放出来,要达到通过只受自由交往制约的社会交往的组织去替代暴力制度的程度;这不是直接通过生产活动,而要通过进行斗争的阶级的革命活动(包括反思科学的批判活动)来实现。社会实践的这两个范畴合在一起,才会使马克思在解释黑格尔时所说的类的自我产生的活动得以可能。”(28)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a.a.O., S. 71 f.本引文主要采纳了中译本翻译,个别地方略有调整。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实践—革命的变革过程——其中社会运动将社会从一种压制性的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是与道德—实践的知识相结合的,这种知识形成于对系统变形的相互作用结构的经验;规范的学习过程——其中行为主体自身共同协作逐步意识到沟通理解的目标,且这一目标内在于社会组织的交往行动,促成了旨在从社会统治中获得解放的诸道德洞见。哈贝马斯最终取消了马克思试图在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过程之间以范畴方式建立的联系:社会革命意识的形成内在地遵循另外一套不同于对自然进行社会加工的行为逻辑。哈贝马斯不再需要去应对一种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哲学所陷入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尽管这一哲学不信任实在的诸劳动关系的解放潜能,它还是在历史哲学上坚持劳动与解放的内在关联。劳动与交互作用的区分,使得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免受所有关于社会革命学习过程的工具主义的、被置于劳动行为模式的狭窄范畴运用的阐释的影响;但同时,劳动概念在其理论中居于一种边缘位置,以致这一理论将结合在工具行为之中的实践道德——借此劳动主体对一种资本主义彻底工具化的劳动活动经验作出反应——完全排除在其概念框架之外。
哈贝马斯在人类学的高度上吸收了劳动概念,盖伦的行为理论在这一高度上阐明了劳动概念。盖伦在其代表作《人类》中所秉持的基本思想是,(29)Arnold Gehlen, 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Frankfurt/M. 1971 (9. Auflage).人在身体上所装备的可塑的驱动系统、过度刺激的知觉与无外形的运动机能,强迫人作出一种具有目的的行动,而这一行动塑造了其需求、构造了其知觉并引导了其运动器官;人在具有生存风险的行为中会减轻自身的负担,而一种有缺陷的存在物的有机初始状况则给自己带来这种风险。现在盖伦用一种唯我论式的参考模式来解释这一被他理解为人类生命的统一组织原则的行为结构:在这个模式中,行动被设想为一个主体面向和借助事物的、在原则上孤立的操作。工具行动是对人来说从接口处显得有机的驱动生命的、知觉的与运动机能的系统不断地自我再组织。哈贝马斯利用这一人类学概念规定,完善了其行为理论有关描述自然客体指向的行为特征规定。正如交往行动概念之于社会互动诸形式,工具行动的概念也应把指向对象的行为方式回溯到一种在人类学意义上被确定的规则结构:在工具行为中,一个主体支配其活动以达成的成效,即他能够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处置事物;劳动行为依赖对技术规则的认识,而且技术规则是在与自然客体操作式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以经验的方式获得的。(30)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 a.a.O., S. 62 f.在现在社会劳动过程中,这一工具行为是在诸单个劳动主体之间、按照共同生产目的的合作规则协调进行的。(31)Jürgen Haberma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a.a.O., S. 145 f.
比哈贝马斯所利用的理论概念水平更进一步,工具行动概念明显保留了马克思赋予劳动概念的经济学和人类学意义维度。正如马克思那样,哈贝马斯使得源自一种类的有机配置的劳动自身变得清晰,这种类被强制在经济上通过工具行动再生产其生活。但是,哈贝马斯在缺乏范畴关联的情况下,将意识理论的意义维度从其工具行动概念中排除出去。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接着黑格尔将劳动行为阐释成人的诸能力和需要的对象化过程。在“巴黎手稿”中,劳动的外化模式的确规范性地承担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而在其理论的经济化过程中,马克思将这个外化模式转化为一种手工业劳动活动的经验图景,活动主体将其自身获得的经验知识自主且精湛地体现在对对象的加工改造之中;马克思从这一整体的劳动行为层面去除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抽空其劳动内涵并将其变得抽象的活动的极端情况。这样一种劳动行为的内在差异化在哈贝马斯那里并不存在。虽然工具行动概念也以一种活动表象为基础,在这种活动中,进行劳动的主体独立地控制和支配着在操作层面与劳动对象的打交道过程,但哈贝马斯并没有系统地利用这一概念内涵。他对人际间行为方式谱系的提升,在规范上所依据的乃是如下理论,即这些行为方式已然具有一种非强制的沟通理解行动的形态;然而,他仅仅是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区分社会劳动形式的历史谱系,而不是在这些劳动形式满足一种完好的劳动行为的诸条件的尺度上区分。(32)这在哈贝马斯阐释黑格尔早期作品时的劳动概念的方式中有对应。但随着泰勒制化的劳动系统的建立,资本主义积累压力下被推动的生产技术的劳动合理化达到了一个门槛,即大部分的工业劳动活动已经丧失了那种内在完整、自成一体的劳动行为特征。合理化过程将社会劳动分解成诸多工具性的部分操作,这些操作已变得不再依赖于伴随行为的控制和劳动主体的经验知识,即这些部分操作不再将一种劳动行为的结构真正地现实化。为了分析性地把握这个对工具活动方式的劳动内容的系统性消解过程,哈贝马斯牺牲了范畴手段,他将工具行动概念应用于20世纪那些社会哲学规划的传统中,而那些规划在规范上使劳动概念中立化,以致它们会将任何加工对象活动的实现形式都非批判地纳入劳动概念。
一种批判的劳动概念必须在范畴上包含两种工具行为之间的差异:在一者之中,劳动主体以自身知识循环地引导并自己主动将其活动结构化;而在另一者中,无论是伴随行为的控制,还是活动的符合对象的结构化,都不被赋予劳动主体自身。(33)尤其是为法国“劳动社会学”奠基的Georges Friedmann在手工业劳动模式上所展示的“劳动的完整性”的规划,必须在一种成熟的社会行为理论的框架内重新解释这样一种批判性劳动概念的重建。Vgl.Georges Friedmann, Grenzen der Arbeitsteilung, Frankfurt/M. 1959.显然,马克思的目标乃在于将劳动概念保留于其中意义上的差异,但他并没有在解放理论意义上恰当地使用它。而哈贝马斯却将自身限定在一种工具行为概念上,这种工具行为在每个操作性的对象关系中无差别地实现自身。
由此,这种以工具行动概念对经验上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层次差异的抹平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汇入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富有成果的区分。哈贝马斯利用在认识论层面发展起来的工具和交往行动的区分,以在进化论层面让解放的意识教化过程相较于一种技术知识的扩展过程凸显出来:在符号中介的互动行为结构中,一种道德知识从直观的行为主体的交往成果中产生出来,这一道德知识逐步意识到在反事实层面为社会行为领域奠基的诸沟通理解目标;与此相反,在社会劳动的行为结构中,符号式普遍化的对自然对象的操作经验将自身提高到一种扩大对外部自然控制的技术知识。这一区分承载了哈贝马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然而,如果哈贝马斯同样在范畴层面内部区分工具行动概念,正如他在规范上展开社会行为的谱系那样,那么他就必须想起一种道德—实践知识的类型,这种知识并不产生于对系统变形的交往关系的意识,而是来自在生产技术上受到破坏的劳动行为经验。但哈贝马斯就这样在范畴上完全隐没了社会不公正意识(Unrechtsbewußtsein)的谱系,而这种意识形成于对自身劳动的系统剥夺;因为只有当这一观念——即只有那种工具行为达到一种活动主体自身以循环的方式塑造和控制劳动行为的水平——是被允许的,在进行工业劳动的现实中,一种教化过程的可能性才会变得一目了然,而劳动主体在这一教化过程中系统地宣称其拥有控制劳动过程也即诉诸工具行为劳动特征的权利。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过程所设定的解放的反思过程,贯穿于一种在社会结构上歪曲的互动关系,以为了它固有的沟通理解目标而控诉其压制性的组织形式;如果这一论证至此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在社会劳动领域就会存在一种与这个反思过程相应的且具有道德取向的行为过程,这一行为过程透过劳动以统治方式建立起的劳动社会形式,去控诉工具行为的劳动内涵。其中得到表达的规范性要求,由一种道德的脆弱性(Verletzbarkeit)引起,它并不源自交往沟通方式的压制,而是来自对自身劳动活动的剥夺。在这样的经验上所形成的道德知识体现在,它们在外在规定的劳动关系本身的组织化现实中主张其自主性。在对工具活动方式的劳动内涵在生产技术上的消解的反应中产生了某种实践合理性,正是这种实践合理性赋予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劳动中变得日常的违背规范和反抗的做法以内在逻辑;它既不同于旨在对行为意向的理解取向之协调的交往行为逻辑,又不同于旨在对自然过程的技术支配的工具行为逻辑。因此,尽管不会以此来结合系统性的要求,我还是想暂时使用在法国劳动社会学中被用到的“占有”概念,以表明这一结合在工具行为实施过程之中却又决定着它的行为逻辑类型。
菲利普·伯尔努(Philippe Bernoux)在一篇题为《工人对合理化的反抗:劳动的重新占有》的文章[9]76ff.中报告了一项经验性研究,借助参与性的观察、标准化的询问和公开的采访研究了那种日常行为做法的广阔领域意义,而工业企业的工人们在这些日常做法中系统违反并破坏由企业领导所规定的、体现在技术的劳动组织中的生产规则。这一研究区分了四类实践上的,却并没有中断劳动过程的违抗规则的表现:一类持反对立场且尽可能自我决定劳动节奏的时间分配(“劳动时间的重新分配”);一类是个人的、协作的象征地呈现出的对劳动空间的占有(“个人和集体在工厂占有一定空间”);一类是劳动进行过程中自己主动发展的技术(“技术占有”);最后一类是无声的、协作的对企业管理技术的改革(“管理技术占有”)[9]77。在所有这四个维度上,工人们显然投入了一种整体性的劳动能力,这在某些情况下要比企业生产管理的科学知识更加重要。
伯尔努将这种被嵌入劳动进行过程中的反抗做法的谱系阐释成一种合作努力,即重新获得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我们的假设是,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来自其占有(l’appropriation)维度。他们每一个人都反映了如下意愿:组织和控制生产,将自身定义为独立自主的和朝向组织的群体,以及支配生产工具的权利也得到承认。”[9]80工具指向的行为过程尝试将不自主的劳动过程收回到一种自主规划和控制的劳动活动的视域中,在这一行为过程的广阔阵地上,劳动主体追索其活动所固有的要求。因此,在实践的规则违抗中得到系统体现的道德知识,并不旨在消除对交往行动的阻断,而是以从工具行动的封锁中解放出来为目标。
这一工业社会学研究使占有实践变得清晰,这种实践如此不引人注目地进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日常,以致它一直处于清晰呈现的门槛之下,而在这种门槛之上,社会学总体记录冲突行为和规范违抗的情况。因此,直到现在,这一实践反抗领域的文献资料还是被作为经验的社会研究文献。如果在那里被证实的经验以及在伯尔努的研究中所产生的结果并没有完全让人产生错觉的话,那么泰勒制化的、意义空洞化的工业劳动总是伴随一种反向运动的行为过程,在其中诸劳动主体试图以合作的方式重新获得对其自身活动的控制;那么,对异化劳动内含着未得辩护的统治这一点在实践上的回忆,对异化劳动来说乃是固有的。
为了掌握被应用于这一实践的批判形式中的道德知识,哈贝马斯在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所建议的范畴框架几乎是不够的;工具行动概念在哈贝马斯给它的说法中甚至在主题上遭到了剪裁,它自身都不会承认处于建立了的劳动关系的道德张力中。虽然交往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有其优越性,即敏锐关注到一种不再附属于特定阶级的、具有革新性的交往解放过程,但笔者在其中也看到了其范畴不足,即它一开始就这样设置其基础概念,就好像在历史上那种马克思所关注的对异化劳动关系的解放过程今天已成为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