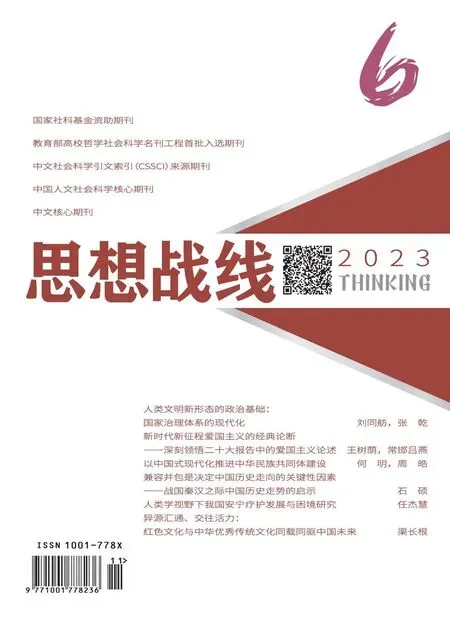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宋元经验
2023-02-25黄博
黄 博
宋元时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宋代中国境内各民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北方契丹、党项、女真相继兴起,建立了辽、金、夏等区域政权,在南方也有以白蛮为主体建立的大理,在西域则有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时期大一统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但随后蒙古的兴起,元朝的建立,一个新时代迅速到来,元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
事实上,元朝的大一统,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元朝纯属依峙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军事成功的结果。宋元时期四百多年,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各民族共同繁荣,从而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才是元代大一统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原因,而元代的大一统又反过来巩固了这一进程。宋元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过去的分科体系下,分属于不同的王朝史和民族史内容,如今从整体上全面梳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十分有必要。因此本文尝试从全局的角度,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出发,综合考察宋、辽、夏、大理、喀喇汗、金、元诸政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而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宋元经验。
一、宋元时期各民族语文的发展繁荣与多民族语文的交融并用
语言文字是创造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反映着思想文化本身的内涵。唐宋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主要依靠汉字表达和记录,从秦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都有着辉煌灿烂的表现,但在思想史领域却明显有些黯然失色。尽管匈奴、鲜卑等民族在汉唐之间近千年的时间里此起彼伏,曾经也盛极一时,但都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字(1)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实物遗存,匈奴人应该没有基于匈奴语创制的“匈奴文”,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没有争议。鲜卑文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点,由于《隋书·经籍志》录有《国语》《鲜卑号令》等书目,因此部分学者认为书写鲜卑语的鲜卑文字是存在的。但有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国语”著作或许只是用汉字记录的鲜卑语,不存在有真正意义上的鲜卑文。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目前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未见有鲜卑文字存世则是不争的事实。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1页、第374页。,自然也就没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存留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印记。唐代随着吐蕃、突厥、回鹘的相继崛起,藏文、突厥文和回鹘文开始陆续创制并行用。到宋元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多民族语文并用时代,除了此前已经行用的藏文和突厥文、回鹘文等外,又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一个全新格局出现:即从汉文化的一家独大到多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宋元时期多民族语文的繁荣,既是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获得加速发展后的人文成果结晶。如契丹大字的创制,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新五代史》记载,辽朝建立后,“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2)《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8页。,这批契丹文字,历史上称之为“契丹大字”。后来女真人也仿效契丹人,借用汉字的字形和笔画来拼写女真语,从而创造了女真文,《金史》记载,主持女真文字创制工作的完颜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3)《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4页。。党项人创制的西夏文,则更是在“造字”思想上深受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在形制、结构、表意和书写上都严格遵循了汉字的“六书”原理,西夏文字总数中约有80%的“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都是模仿汉字的“会意”与“形声”这两种构字法创造出来的。(4)有关西夏文的造字原理,参见史金波《西夏文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此外,除汉文化以外,契丹小字的创制,也深受回鹘文化的影响。《辽史》记载,辽朝初年,“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明可使。’遣讶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5)《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68~969页。。契丹小字在回鹘文的启发下,节选和改造汉字字形为契丹语的表音符号,从而实现了用一定数量的字符对全部的契丹语进行拼读,这就是所谓的“数少而该贯”。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畏兀儿文化(高昌回鹘),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就曾说,“因为鞑靼人(指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成吉思汗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儿文”(6)[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这种蒙古儿童所学的畏兀儿文,并不是真的畏兀儿文,而是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儿体蒙古文”,这种文字在经过改进后一直被蒙古族人民沿用至今。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多语文并用时代的出现,也孕育了一大批同时掌握多种语文的人才,为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上、文化上的交流与交融奠定了基础。当时,精通契丹文的契丹人,往往也精通汉文和回鹘文,精通西夏文的党项人更是对汉字的构字法了如指掌。各民族虽然都创制自己的文字,但在政府文书与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同时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在日常语文的使用中并不是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包括契丹人在内的辽朝境内的各族人民并不是只使用契丹文;同样,包括女真人在内的金朝治下的各族人民也并不是只使用女真文字;而西夏社会更不是只有西夏文的使用了。事实上,辽、金和西夏,汉字、汉文的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字上的共享共用也很普遍,比如传世的契丹文碑刻《郎君行记》就是书写并立碑于金朝统治时期,且除了刻有契丹小字外,也刻有同样内容的汉文。(7)《郎君行记》刻石于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因此在历史上长期被误会为是女真文。直到近代以来,随着学界对契丹文字研究的深入,才确定其上的非汉文部分乃是一通契丹小字的碑刻。参见牛达生《〈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契丹文在金代仍然十分流行,甚至《金史》中记载的精通契丹文的人,比《辽史》还多,其中提到说“通契丹字”的人,包括完颜璋、完颜布辉在内的有十五人,明确指出“通契丹大、小字”的人,包括完颜宗雄等在内的有九人。(8)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页。而西夏治下的河西地区,藏文的使用也相当广泛。日本学者武内绍人的研究表明,吐蕃王朝崩溃后,河西地区的藏语文的使用仍然相当普遍,不仅限于个人交流,也用于诸如宣誓、效忠之类的官方文件,且和汉语并用于各种文化典籍。(9)有关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藏语文使用的情况,参见[日]武内绍人《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杨富学译,《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
在语言文字上,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语文的掌握和使用上也可以说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语文共享共用的新格局。如一方面,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在造字上都有明显的模仿和借鉴汉字字形、笔画的痕迹。而另一方面,9世纪前期依据粟特字母创制的回鹘文,是一种典型的音素文字,契丹人在接触到回鹘文后,获得启发,在增减汉字的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创制了用来表音的字母——“原字”,再用“原字”拼写契丹语。因此契丹小字是一种介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10)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从13世纪初开始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儿文字体蒙古文,也是深受回鹘文的影响,甚至直接借用了回鹘文的字母。而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回鹘文本来是从右向左书横写,后来因受到汉字的影响,改为从左至右竖写,(11)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回鹘族)文字和文献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可见当时中国各民族在文字上的相互交融影响之深。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至宋辽夏金以来的分治割据局面,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元代一方面延续了多民族语文并用的现实;另一方面,元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实际,在语文上的反映就是国家通用语文思想的产生和实践。而通用语文尝试的另一个前置背景也是多民族语文的并用,在元代多种文字同时出现在一块碑里是很常见的现象。
据多种史籍的记载,早期的蒙古社会,有语言而无文字。据最早接触到蒙古社会的内地知识分子观察,“蒙古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2)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50页。,就连非常重要的军事行政上的信息传递,也非常粗陋,“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13)赵珙:《蒙鞑备录》,李国强整理,载《全宋笔记》第七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71页。。蒙古汗国建立前后,蒙古人开始大规模地接触和吸收畏兀儿文化,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学者曾奉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4)《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页。,即以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畏兀儿体蒙古文。畏兀儿体蒙古文此后成为元代蒙古人群体中最流行的通用书面语,无论文书行政还是树碑立传,都普遍使用这种形式的蒙古文。
元朝建立后,随着契丹人、女真人在整体上融入到汉人群体中,契丹文和女真文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汉字、西夏文、藏文、畏兀儿文、畏兀儿体蒙古文等多民族文字仍然在元代社会上广泛使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操不同语言、书写不同文字的各族人民,并没有因为多语文的并存而在思想文化交流上存在着工具性的障碍,恰恰相反,元代社会是一个多民族语文共享共用的时代,在元代多种文字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是很常见的现象。
由于多民族语文的并用,元代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掌握多语文能力的人群,他们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元世祖时期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吐蕃人桑哥,为“译史”出身,精通藏文、汉文以及畏兀儿文等多种语言文字。(15)《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70页。此外,元朝还创制了一种全新的文字,俗称“八思巴文”,这是一种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准备的新文字,这种文字借鉴了梵文和藏文的字母与拼写规则,试图为元代新形势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创造一种可以“译写一切文字”(16)《元史》卷二百二《八思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的书面语表达形式。当然这一尝试由于过于空中楼阁以致最终效果并不好,但这一基于多民族语文的通用语文体系的尝试,仍然闪耀着思想上的夺目光辉。
二、宋元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的加强与中华思想文化共享精神世界的形成
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的加速发展,增进和加强了各民族彼此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共享精神世界的形成。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建立后,契丹、女真、党项、白蛮等各族人民,在与宋朝的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开始大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成为他们各自民族创造他们各自的思想文化时的源头活水。
辽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大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各种中原汉人社会中流行的民俗文化。如《辽史》记载,辽太祖阿保机曾经询问身边的大臣应该崇奉何人,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其长子耶律倍则非常坚定地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得到阿保机的首肯,并让耶律倍以皇太子的身份每年主持祭祀礼子的“春秋释奠”礼。(17)《辽史》卷七十二《耶律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9页。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的思想精髓之一,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契丹贵族的亲睐。可以说,辽朝建立后,来自中原的思想文化已经在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此外,儒家思想在契丹贵族的教育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辽朝建立后,就下诏修建孔庙。之后,不断完善儒学教育体系,如在上京(在今内蒙古)设立国子监,在南京(在今辽阳)设立太学,让契丹贵族及官僚子弟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契丹贵族中有许多热心学习和精通儒家典籍的人,如史称辽兴宗“好儒术”(18)《辽史》卷十八《兴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1页。,辽道宗的身边“尝有汉人讲《论语》”,不但“心领神解”,还往往有不少自己的独见发明。(19)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四《耶律隆裕传》,贾敬颜,叶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6页。辽天祚帝年轻时也曾经抄写过《尚书》。西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甚至通过了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因而拥有“大石林牙”之称。在文学创作上,契丹贵族也接受了唐诗中清新雅丽的审美思想,辽道宗有咏黄菊的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金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秋风吹不去。”(2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6页。此外,辽道宗还有御制诗文集《清宁集》,其他的契丹贵族也多有汉文写作的诗文集传世,如耶律隆先的《阆苑集》等,不但以汉文作诗,且其中的情感也都与唐宋流行的审美情趣相近。(21)有关辽代契丹贵族的文学成就,参见别廷峰《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后,也开始学习并大规模地接受汉文化,不少女真贵族在思想风貌、情趣爱好等方面,呈现出他们的思想世界与中原汉人的思想世界已别无二致。如金熙宗会写诗和精于书法,喜欢穿儒服,日常生活中喜欢喝茶,喜欢焚香,喜欢下棋。史称金熙宗“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以致于在女真老臣看来,“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2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页。就连一向反对女真人说汉语、取汉姓、穿汉服,试图让女真人保持自我特性的金世宗,也大力拥抱汉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他命人翻译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女真文,认为汉文化中儒家思想,不是汉人专属的思想,而是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道理,是“仁义道德所在”。(23)《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页。因此,尽管族属不同,政权不同,但宋朝、辽朝、金朝治下的人民在思想道德上可以说是拥有共享的价值观的,这样就使得契丹人、女真人在精神生活上与汉人拥有的共同的思想情感。众所周知,元朝建立后,把留居在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都一律视为汉人,显然是因为他们与汉人拥有共同的、共享的思想文化特质。
党项人最初生活在甘、青、川交界地带,唐代开始逐渐移居到靠近中原腹地的陕北地区。党项人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大量接触和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党项人的思想中,经常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思想。西夏的建立,儒家思想发挥过至重要的作用,西夏统治者称帝建号,建置宗庙,设官分职,所践行的一套政治体制,其政治实践大多都基于汉唐以来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也是西夏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原则,西夏朝廷还命人翻译、刻印了大量传承和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24)有关西夏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吸收,参见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夏毅宗在位时,正当宋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他向宋朝派出使团,请求赐予儒家典籍,宋仁宗根据西夏的要求,一次性送给西夏使团《易》《诗》《书》《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等众多的儒家经典。(25)《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02页。夏崇宗时儒家思想在党项社会受到进一步的重视,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国学”,设置弟子员额三百人,“遵行儒教”,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夏仁宗时,不但把孔子尊奉为文宣皇帝,还在各州郡设立地方学校,将弟子员额由三百人扩容为三千人。并且参照唐宋科举制度,以儒学取士,设置了童子科、进士科等,选拔出以儒家思想为考核标准的官僚队伍,西夏末年的皇帝遵顼早年还曾以进士第一名及第而知名当世。(26)有关西夏采用唐宋科举制度的情况,参见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9~621页。
因为儒家思想的盛行,在党项人中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儒学人才。党项人斡道冲,八岁时以精研《尚书》考中童子试,成年后,精通《五经》。曾以西夏文翻译宋人所著的《论语注》,又自己撰写了《论语小义》《周易卜筮》等儒家经典的注疏类著作。(27)关于斡道冲生平的详细情况,参见虞集《故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进入元代以后,党项人中更是不乏大儒。元代初年的名儒高智耀就是一个西夏遗民。他在西夏末年曾考中进士,西夏亡国后,隐居于贺兰山,后被元宪宗召见,他向元代统治者大力宣传儒学,倡导“以儒治国”,得到元宪宗的赞赏,官至翰林学士。(28)《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高智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72~3073页。元代移居到中原各地的西夏后裔如余阙、朵儿赤、迈里古思等人,也大多醉心于儒学,热衷于弘扬儒家思想和学说,并以儒家大学者的身份闻名于世。(29)元代西夏遗民的儒学水平非常突出,详情可参见刘志月,邓文韬《元代西夏遗民著述篇目考》,《西夏研究》2016年第2期。
白蛮(今白族的先民)是以云南为中心建立的大理政权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统治时期,白蛮社会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元代初年奉命巡视云南的郭松年在所写的《大理府行记》中称,大理与宋朝,“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言行),略本于汉”。(30)郭松年:《大理府行记》,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四五,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可见宋元时期白蛮社会的思想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文化的一些基本内容影响到大理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存的摩崖石刻《护法明公德运碑》,刻于大理后期,是一篇优美的骈散兼用的汉文文学佳构。这虽然是一篇为当地文化精英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其中反映的思想竟与唐宋盛行的儒家思想如出一辙,如碑文中描写“碑主”的成长经历时说,“公自幼孤,久失庭训,不喜盘游。弱冠岁余,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温良五德□□,六艺三□,随而有之,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31)侯弘:《护法明公德运碑赞》,载张方玉主编《楚雄历代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页。无论是表达形式的用典手法,还是内容中所包含的家庭伦理秩序和道德才艺的追求,都是最为典型的儒家思想。
三、思想文化的相互吸收与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繁荣
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得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在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交往交融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内容。宋代以前中国古代各民族中,以汉族的思想文化最为繁荣,从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汉文化中的思想结晶,既是汉族人民在思想上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学习和吸收的精神养分。但宋代以前,汉族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创见和成就,就相形逊色得多。而宋元时期,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入,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如这一时期,汉族以外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积极吸收汉文化的优秀成果,既使是在传统汉文化范畴的思想领域内,在宋元时期汉族以外的中国各民族,也取得非常丰硕的成就,产生了足以与汉族文化精英比肩的、以汉文化为精神内核的思想和文化。以党项人为例,他们接受了汉文化传统主张的以天、地、人“三才”思想为基础构成的世界观,并且把这一思想贯注到他们教育思想中,以西夏文写作的儿童启蒙读物取名《三才杂字》。(32)有关《三才杂字》的成书情况和具体内容,参见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西夏文与汉文常用词语的双语对照词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编排规则,是以“天形、天相、天变”,“地形、地相、地变”以及“人形、人相、人事”三大类九小类的类型划分,(33)有关《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参见史金波《一部深度反映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奇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显然也是以“天、地、人”三大结构来认识和理解宇宙世间万物的。
众所周知,汉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人本思想”非常突出,而党项人的思想文化中,对于“人本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以西夏文写成的西夏社会的小型百科全书《圣立义海》为例,书中开篇就说,“人者,天下地上一切有情中之太初也”。汉儒对宇宙起源的认知,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分,“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34)黄奭辑:《易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圣立义海》的这一解释,借用汉文化中的宇宙起源论的“太初思想”,阐释了人是宇宙万物之始的观念。党项人认为,人之所如此重要,是因为人“上蔽覆于天德,下坚依于地藏”,“合天地德,阴阳调合,五行遮身,鬼神守护”,人的地位在党项人的观念中被如此强化,说明在他们的思想中,人本思想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党项人还从儒家思想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伦理价值,《圣立义海》中提出人本身应该具有的四种伦理道德属性,即“四正”:“有孝德心,仁之正也;解善恶心,义之正也,为廉让心,礼之正也;知真实心,智之正也。人因有此四正。”以孝德、善恶、廉让和真实对应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四大道德规范。(35)《圣立义海》是以典雅的西夏文写成的,文中所引内容是现代学者所作的译文,详情见[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西夏学者对儒家基本主张的进一步阐发,既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大旨,又不是简单复述孔孟之道的名言名句,而是在掌握了儒家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善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成就巨大,实现了共同繁荣,表现在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名家同时产生,经典集中涌现,而且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经典所具有的价值观日益趋近。这一时期汉文化的代表人物众多,从王安石、二程到陆九渊、朱熹,以理学思想为代表的新儒学从兴起到集大成,奠定了此后一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除汉文化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外,其他民族文化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民族都开始涌现出各自的思想家和文化经典。
如这一时期藏族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贡噶坚赞所著的《萨迦格言》,直到现在仍然是藏族文化的经典作品。《萨迦格言》用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如在政治思想上,《萨迦格言》宣扬“经常以仁慈护佑属下的君主,很容易得到奴隶和臣仆。在莲花盛开的碧绿湖里,水鸭都不唤自来”。(36)萨班·贡噶坚参:《萨迦格言》(汉藏合璧),王尧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反映了饱经吐蕃王朝崩溃后社会大乱之苦的藏族人民对仁政的渴望和对暴政的反对,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政主张不谋而和,表明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对仁政的追求,汉藏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高度一致的。此外,像儒家思想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好学深思、不耻下问等对知识的尊崇和渴望等内容,在《萨迦格言》中也有不少类似心意相通的金句,如贡噶坚赞经常将“学习知识”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强调学习是一种美德,“愚人以学习为羞耻,学者以不学为耻。因此学者即使年迈,也为来生学习知识”。(37)萨班·贡噶坚参:《萨迦格言》(汉藏合璧),王尧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萨迦格言》的流传,使得尊重知识、勤学好学的思想成为藏族社会的共识,清代初年成书的《西藏王臣记》认为,正是贡噶坚赞撰写的这些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的格言,为西藏社会开创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吾等蕃地能有传习五明(代指一切知识)之风,亦实赖此师之德也”。(38)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而维吾尔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众多流传于今的思想文化经典著作,其代表作品是成书于11世纪中后期、由喀喇汗王朝的大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所写的长诗《福乐智慧》。这部史诗级的巨著有着非常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体系,它渊源于回鹘古老的文化传统,吸收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各种伦理思想,兼收并蓄,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伦理学体系。
如早期喀喇汗王朝文化强调顺从精神领袖的意志,在他们早期所信奉的经典中,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忠”这样的概念并不存在。但《福乐智慧》中却有大量宣扬忠君报国理念的主张,如“为国君效力要忠贞不渝,建立了功劳,会百事顺遂”(39)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5页。,“忠贞的臣仆均系如此,不谋私利而利君王”。(40)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0页。并且创造性地树立起忠君的观念,提出拥有忠臣,对君主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价值。(41)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1页。《福乐智慧》对社会秩序中世俗政治的地位极为推崇,坚持“君主万世一系”,强调“父亲是君主,儿子天生是国君”(42)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60页。以及“国君天生是社稷之主”。(43)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喀喇汗王朝的政治思想中,一方面接受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要符合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用传统文化的规则代替国法,只有君主才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君主的责任——“如果国君不为民立法,不保护人民免遭不幸,人民将遭殃,国家将受损,社稷的基石将毁坏殆尽”。(44)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81~285页。
可以说,中国境内各民族在这一时期通过频繁的和高效的交往交流,在相互吸收彼此的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拥有自身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内容,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
结 语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曾经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4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15~216页。挖掘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走向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历史事实背后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经验,可以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互关系角度揭示出宋元时期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原因。宋元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都创造了各自灿烂的文化,呈现出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繁荣,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属于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内涵,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曾经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46)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14~215页。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正是中国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世界的思想基础。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创新,离不开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宋元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空前繁荣,恰恰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这才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宋元时期各民族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共同性的增强,各民族在立足于自身文化需要的同时,也将兄弟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结晶融入到自身文化之中,形成了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从而奠定了中国各民族共享共有思想世界的文化基础,在客观上打造了一个宋元时代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