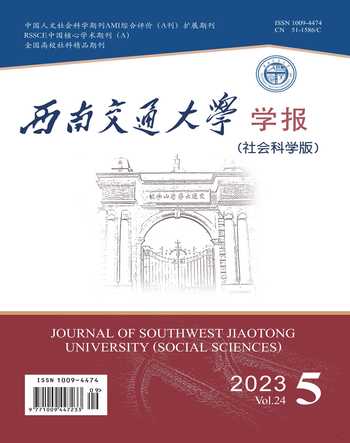从黑格尔到阿甘本:辩证法的虚无主义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2023-02-25陈琦
陈 琦
海德格尔曾提出,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阶段,是在黑格尔处发展至顶峰。虚无主义的典型症候是世俗与神学、虚无与合法化的不可区分,而黑格尔辩证法恰恰是对意识经验科学与绝对有神论的混淆。“‘上帝死了’……唯独没有‘不存在上帝’的意思”〔1〕,“自在的上帝”经历漫长的意识劳作过程转化为可触及的“自为的上帝”,于是绝对精神就作为一种存在的神学取代了上帝,它确证存在者之存在于主体面前的绝对显现,并要担保主体对世界对自身的解蔽能力。海德格尔说这种担保正是虚无主义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它使没有根基成为一种新的根基——它意味着通过对自我不断的抽离和挖空来重新占有自身,意味着一个对否定性进行肯定化生产的无限循环、辩证摇摆的过程:一方面设定了一个可支配、现成在手(Zuhandenes)的全面内在化的世界;另一方面,设定世界的意识机器因只在于维系自身运转的绝对可行性,所以注定沦为除自身以外别无他物实在的虚无的筹划、协商和计算。而这正是法国哲学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虚无主义时代现况的先声,旨在响应海德格尔的呼吁,即当前政治实践如要克服虚无化,需要重新审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阿尔都塞和阿甘本,他们指出黑格尔哲学起初恰恰是要克服二元论所带来的西方哲学的“虚空”。
一、黑格尔的虚无主义批判与辩证法的生成性转化
黑格尔早在其青年神学论阶段就对虚无主义的问题做过初步论述。他提出犹太教的道德律令是康德二元论的同谋,因它制造了生命体内外的对立和分裂,限制了生命力量的发展和统一。他也针对犹太教的法律法规及其惩罚手段做了剖析,指出这种法规是否定生命的异己客体、是至高无上的强权,它通过对惩罚措施的简单重复建构偶然性的正义;另一方面,犯人接受惩罚即他剥夺了别人什么东西他也将遭受同等苦难,这种惩罚非但不能使他与他者、与法规、与自我对生命精神的背叛达成和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那个异己的力量……这个敌对的存在一经惩罚了他便不复对他起作用……因为犯法者永远把自己看作犯法者……他的这种现实与他对于法律的意识是互相矛盾的”〔2〕。而后在《精神现象学》中他重提了这种强权逻辑,说这是一种主奴意识的暴力循环,是一种普遍伦理精神的毁灭,致使伦理共同体分崩离析成诸多为他的、被动的、“空”的个别性。“空”即是对虚无状态的描述,黑格尔也将其命名为“法权状态”,他在原子论那里找到了始作俑者。
黑格尔认为近代原子论和康德“物自体”共同的问题在于它们理论的根基处都存在一种“空”,而辩证法的工作正是要填满这种“空”。“空”是现成直观的自在之在,是完全外在于实体、只为实体运动提供环境条件而并不能推动实体运动的“纯粹空间”。这种观点是相对古代原子论的曲解甚至倒退,因为古代哲学家恰恰认识到虚空是万物运动的推动者,只不过这种认识尚且粗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lbst)……看起来似乎是在实体之外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实体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3〕。黑格尔说虚空是主体意识发展过程的必经环节,是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排斥而自我制造的虚空,是个体最初的直接规定性;在否定性运动将直接规定性不断外化并发展为规定性一般的同时,个体有限的意识行动也发展为无限的“行动一般”,并将其建立为自身的普遍性实存。这意味着作为推动力的虚空是主体或实体的自为之力,既是否定性的斥力也是建构性的引力,建构了个体对自身而言绝对的确定的“一”,并同时将自身展开为无限的“多”的共同体。所以黑格尔反对原子论,因为它导致实体运动受控于偶然决定论,丧失了意识与对象、主体与实体之间统一的可能性。辩证法对虚空的填满实际是对二元论的填满,通过虚空自身对自身的转化,将消极分裂的自在之“空”转化为积极能动的生成之“空”,是一种自我填满、自我充盈和自我实现。
阿甘本曾评价说黑格尔在这里使用的实际是一种时间的延迟机制,这种时间机制的雏形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阿甘本也将其概括为“时间化装置”或“语言学装置”:“它将存在划分成本质和实存,并将时间导入存在,这种装置是语言的工作。它将存在者主观化为主体(hypokeimenon),这是言说自行实现并让装置运转起来的根基”〔4〕。亚里士多德借由对行动概念的界定,即行动是对人伦理本性的“现实化”或实现(entelecheia),给出了“主体化=现实化”的理论雏形。该等式设定了意识对象是有待实现的可意识之物、是主体实在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它将康德意义上被动的既定存在物转化为能动的自我行动。这种行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是人的政治行动也是他的言说行动,言说是为声音锚定一个指称对象或开启一段话语情境的“命名”时刻,而“命名”实际是一种语言的预设结构、一种否定性的时间结构,它默认言说行动因为时间间隔永远无法切中实在对象,它永远在言说“已经不是”的东西。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时间间隔就被定义为虚空,它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运动转化为生成性的历史时间,并且只在终结的时刻才真正开启。
“借助时间的方式,实在被等同于本质。也就是说,存在与实在之间的同一性关系是一个历史—政治任务”。〔4〕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论建构了人如何行动以及何以为人的古典政治秩序,辩证法的转化工作也不外如是,“为了要使自己的潜在性成为现实性,意识必须行动”〔3〕,它强制性地规定了人必须行动,潜能即是为了在行动中耗尽自身,且行动的瞬间注定落入这个生成性的装置。这正是后来阿尔都塞进行黑格尔批判时的关键切入点,他指出黑格尔的初心是完成对“虚空”的生成性转化,但实际的情况是虚空只是被转化而未被消除、分裂被延迟而未被终结,于是虚空和分裂意味的死亡与暴力就不可能结束,且否定性、内在性的转化反而让人无路可逃。这种结构后来被阿尔都塞用来描述霍布斯的国家主权机器。
二、阿尔都塞论霍布斯主权机器与辩证法的虚无化倾向
后期阿尔都塞在霍布斯主权国家机器中发现了可对他前期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修正的权力构成形式。它不是封闭的“双重镜像”系统,要求承认或臣服于特定的大他者或“大主体”(Sujet),而是一套“去主体化”的主体化程序。这套程序最终帮他锚定了虚无主义的总问题。
居伊·德波曾用“景观社会”的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的典型症候。他提出“分裂就是景观的全部”〔5〕,这是说当下社会的再生产不是对产品或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是对景观的再生产;人已失去对产品的占有使用权,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因此人唯有通过消费即自我分裂和掏空的方式使自身作为景观展示的一部分,而无法从生产环节中获得自己特定的主体性身份,所以景观社会下的主体是纯粹分裂、去主体化的主体。阿尔都塞在霍布斯那也发现了这种主体,“给定的本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变,主体生产出了一种与自身相对立的秩序”〔6〕,其中个人不是被一个具体的主体化程序所控制,而是同时受到两股对立势力或两种假设的可能性的拉扯。程序是预防性和调节性的,是为了在两个对立的可能性之间取得辩证平衡,它的运作或许没有确定的结果,因其目的只在于为自身持续的辩证运动做担保。这恰好对应了早期阿尔都塞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发现的虚无主义倾向。
阿尔都塞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过程”的哲学,主体的绝对性只在它展开自身、显现自身的整个过程的绝对性当中实现,换言之,抛开整个过程它什么也不是,所以辩证法实际是一种“无主体的进程”:“这个主体就是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无主体的异化过程(或辩证法)只不过是被黑格尔认可的唯一主体”〔7〕。“无主体的进程”诚然是对超验性主体及其意向性结构所意味的自我特权的瓦解,早期阿尔都塞将其视为对传统主体哲学的颠覆。然而通过研究霍布斯国家问题,他发现现代国家机器恰恰是“无主体进程”的翻版,这台机器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反起源、反发生学和演绎学,它首先承认人理性的孱弱无力也即主体和主权合法性基础的不确定性——其中自然法不是真正的法则、不做定性,不要求对现实经验的绝对切中,它是以“假言命令”(impératif hypothétique)的形式对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进行计算的功能机制,而可能性就包括计算失败的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它意味着无论理性如何摇摆、内战是否发生,人最终都无法逃脱立约行动的必然命运。相应地,社会契约保障的也不是统一国家理性而是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条件,这导致现代国家主权沦为一种光学幻象,“主权者是演员(Persona)……这个人的统一性创造了被代表者的统一性”〔6〕,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唯有统一的代表权;社会契约仅在建立的一瞬间有效,人民即主权者处在不稳定的自然状态内,用霍布斯的话说,“议会一组成,人民就解散”〔8〕。因此主权机器所征用的即是作为“无主体进程”的辩证法,它的运作机制是一种语言的预设、表象游戏,无法真正切中现实,去主体化也去实体化。
阿尔都塞曾分析说这源于辩证法对人行动法则的规定。行动被黑格尔定性为一种“劳作”,而“劳作”的目标是为人类最初的罪行做赎还,这个罪行就是亚当夏娃吃下可以打开心眼的禁果并自此开启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事件。但阿尔都塞认为不是吃下禁果使人犯罪,真正的罪行发生在人伸出手的那一刻——伸手试图触及苹果的动作预设了知识的可触及性,即德里达《触感》(Le toucher)中所谓的“在没有对它有所触及的情况下要求着触及”〔9〕。黑格尔意义上的行动昭示着处在西方形而上学根基的“触感中心主义”(haptocentric metaphysics),它首先规定了对象和认识的分离,意味着人行动与自身存在之亲密性在最初的丧失——“既定物一旦成为被认识的对象,就会把自己显现为与自身相分离并且与自身相不同的东西……这个世界进入了分裂的状态”〔7〕。意识的漫长“劳作”无外乎是重复伸手摘取苹果,重复分裂与和解,以及对触及活动及可触及法则的强调。因此人与其生命分裂的罪行既无法从犹太教法律的惩罚活动中得到解脱,也无法在辩证法的内在性循环中得到真正的宽恕——循环保障的不是最终的和解而是这个循环的运行本身,而运行需要分裂的罪行作为支撑。阿甘本在黑格尔与阿尔都塞对原罪论的洞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辩证法虚无化导向司法暴力机制,其中行动被建构为一台自动运转的“人类学机器”并带来了“自主=自由”的假象,而要逃脱这台机器的控制,唯有开启全新的生命触感活动。
三、阿甘本对虚无主义的解决:行动机器的司法困境与“自我—触感”的突围
(一)辩证法的行动机器与虚无主义暴力——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为例
阿甘本依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行动法则作为“人类学机器”的初级形态。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以外在产品为目的的“制作”和以实现自身为内在目的的“行动”,而它们最终都作为一种“劳作/功效”(ergon)活动达成一致。阿甘本说“功效”是古希腊的一种权力装置,“一种分而治之(divide et imopera)的方式,让生命体成为结合了一系列功能性能力和层面的等级制关系体”〔10〕,它把行动区分成现实与潜能、灵魂与身体、主人与奴隶、属人与非属人两极,通过建构其间的生产转化关系实现整个人类生产生活系统的自动化运作。“自动”是兼有自动和被动两种属性、从属和统治两种正义、以己之动而为他物运动的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好的公民不仅要学会统治、也要学会服从,这与柏拉图从自我规训到规训他人的“治理术”一脉相承。行动中的人是“自主”的,但“自主”不是做自己的主人,唯有落入行动的法则系统,人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这发生在目的实现、潜能“现实化”并耗尽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一刻。也就是说,“功效”设定了一台必须持续运作的行动机器,行动的过程即是对普遍伦理规定进行生产和还原的过程,它给出了人类何谓的伦理学答案。
这台人类学机器奠定了传统共同体主义的内在性原则。个人的意识、实践和社会的政治、技术、经济同处在一个内循环的生产机制之下,完全透明且高度功能化,个人以对自我主体性的生产、分裂和规训来供社会整体的对他的使用和分配。今天内在主义和功效论是法国哲学思考的关键难题,而阿甘本认为它的肇因是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论和黑格尔悲剧论的改造。黑格尔说悲剧艺术是绝对伦理精神在具体生命存在中的实践形式,悲剧行动经历了自我扬弃、迂回与调停的漫长过程。《诗学》所强调的悲剧结构必备的“结”与“解”,被他描述为人类行动必然面临的冲突与和解,这导致:一方面,行动的主体注定是有过错(Schuld)的主体,行动就是为了犯错;另一方面,行动作为意识活动的外化和显现,“在作出决定和发出动作中对自己的内心生活始终是自觉的”〔11〕,所以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担责,这形成了一套“行动—意愿—归责”无尽轮回的装置系统,造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难题。行动的“原罪论”激发了这样一重吊诡的司法困境——既然人类必然有罪,那么他的罪行也就无所谓是否无辜了,“现在古希腊的悲剧人物……使决断成为不可能了。因他不能掌控自己的行动,无辜的罪行(innocent guilt)是一个享有影响力的面具”〔12〕,黑格尔为实现伦理精神合法性而构建的行动机器反过来抛弃了自身的合法性,使得人人都成了潜在的受害者和施暴者。这无疑也让正确认识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此类重大历史暴行成了难题。
阿甘本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是一种将行动的悲剧范式推演到极致的“紧急状态”(Befehlsnotstand),一个完全悬置法规却同时发挥至高法力的“例外”之地。在这个地带,主体与去主体化、行动的善与恶、无辜与罪过甚至生与死本身都已失去区分的意义——集中营是生产尸体的工厂,“死亡的辩证法”让纯粹的死亡不再可能,人是随时可生可死也是非生非死的“赤裸生命”。于是不仅用以审判奥斯维辛的法规是失效的,言说它的证词和见证行动也成为不可能,它完全超出了人类语言表达能力、认知符号框架的极限,“奥斯维辛的绝境即是历史知识的绝境:事实与真相之间,证明与理解之间的不一致”〔12〕。集中营内极端骇人的存在超出了存在物对它的指涉能力,中断了存在与被言说的存在物之间的语言学联系和辩证法逻辑,显示了历史不可言说、不可传递的虚无内核,以及意识在时间维度中自我展开的不可能。因此阿甘本指出,认识和言说奥斯维辛是一种绝境,但它也开启了全新的经验,“当我们消除了语言的预设性力量,我们才有可能让沉默的事物呈现出来”〔4〕,它让集中营内被当作生产条件的不可见的死去的生命重新显现,并让他们重新回归到自身的“纯粹死亡”,意味着“言说不可言说之物”与“见证不可见证之物”的解放行动。这一经验即是阿甘本所谓的“羞耻”。
(二)“自我—触感”,赤裸生命的“羞耻”经验
“羞耻”是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极端情境下的特殊体验,“将死之人不能在他的死亡中找到除了羞耻以外其他的意义……而唯有羞耻使人存活”〔12〕,阿甘本在这里采用了法国作家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所书写的一幅带有奇异味道的“羞耻”场景——一位被当众执行死刑的意大利年轻人在被德国军官从一行囚犯中叫出来并站在施暴者面前的那一刻面露“红晕”。阿甘本说年轻人瞬间的“羞耻”是列维纳斯所谓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赤裸体验,它是一种突然闯入的生命冲动,无法预料无法逃避,带着错乱的情绪而抵达理性意志和人类知识的极限,通往巴塔耶所谓的“非知裸露”的迷狂——正如“裸体”对自身全然的裸露一样,它恢复了人与存在之间原初的亲密性,“裸体是羞耻的,因它是我们存在和存在终极亲密性的显现……亲密性是存在对我们自身而言的……羞耻所发现的正是存在对其自身的发现”〔13〕。年轻人此刻站在囚犯和杀人犯之外一个不确定的位置,遭遇双重排斥而沦为一个不可言说、不可见证但可被任意凌辱屠杀的“赤裸生命”;与此同时,他也处于“蓄势待发”的短暂一瞬,一个将要成为但尚未成为被生产的尸体的时刻,此刻他身上涌现的是一种极度匮乏的需要、无自我的自我主义和无人称的主体——人同自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我没有落入一个预设的认知框架或辩证法程序,而是变成了与自身无限分离的未知者和陌异者。
阿甘本认为“羞耻”不仅是异质性的赤裸体验,也是一种触感体验。启发他的是源自斯宾诺莎而后由德里达、米歇尔·亨利等人发展的“自我—触及/触感”(auto-affection)。德里达说我们需要解除可触及法则对触感行动的限制,让行动重新向潜在的非—触即不可接触性敞开。他将这种颠覆性的触感模型命名为“自—触及你”(se toucher toi):“自—触及你既非单子式的……亦非双重、对称或相互的关系”〔9〕,“你”不是对“我”而言自明着的、映射着的对象,也不是与“我”相对立、为了回归“我”而需要否定掉的“他”,而是触感全然未知、永不可抵达的东西。因此“自—触及你”意味着触感内核的全然外露,是对接触的中断性、匮乏性与纯粹死亡的暴露,它不再按照权力生产系统的预设返回自我之在场性,而是“可不接触”、是转而走向陌异的远方的“自—触”。这种全新的触感模式被阿甘本挪用,他同时征引了米歇尔·亨利对内在性生命的定义,最终将其命名为“自我—触感”。
“自我—触感”指向这样一种特殊行动,在它发生的时刻,施动者与被动者、现实与潜能、行动与功效进入不可区分的地带,是亨利意义上无主体、无指示、无意向性的生命的内在性经验,是生命对自身全然质料化的使用。“质料化”是说生命将自身作为纯粹的质料和潜能,它如其所是的存在,围绕自身打转而不再等待灵魂赋予其形式化的未来,意味着一种无形式的、自指的运动,用斯多葛学派的一个说法来表达,就是“存在自己做着体操”〔14〕。正如舞者突然停滞的舞步,这一刻舞台上所展示的不再是主体与行动的关系,唯余趋向离散的舞者与纯粹姿势,一个内蕴着保存着无限潜能、无时间的、非生成的、行动的纯粹“占位”(localizzato),“内在自我是舞台而感官是观众,所有的分隔消失后……感官如实的品尝惊异的滋味”〔15〕。生命的“质料化”即“自我—触感”的体验寻求的是溢出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认识和言说行动的触感法则的设定,它最终开启的是身体感觉经验“非功效”(inoperative/ argos)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式的触感在德里达那里是跳动的心、身体和爱,顺着这个思路,阿甘本最终回归了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思想,“不仅是知识的光和遮蔽,而首先是对遮蔽和不透明的开放……在爱中,专有和非专有的辩证走到了它的尽头……爱是我们无法主宰、永不可触及却永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14〕,“本有”意味着爱之尽头的非专有性,意味着对专有之物的自由使用,即专有性和非专有性之二分的失效,而开启它的场所恰恰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尽头,即“绝对者”的时刻。
四、结论:虚无主义的未来,绝对异化的“专有者”与共同体
阿甘本曾说海德格尔的“本有”与黑格尔的“绝对者”概念旨在思考一种回归自身而可免除分裂的东西,即思想作为一种“专有者”(L’ appropriazione)的存在。只不过对黑格尔来说,这种无可分割是主体意识的无可分割,是意识自身无条件的确定性和自明性。海德格尔认为这是黑格尔失败的部分,因为他使自行发生、撤回、保存的物的经验和真理在经历对认识条件和认识工具反复的考验之下,扭曲为主体对认识对象绝对占有的权力意志。所以海德格尔说需要重新安放黑格尔“绝对者”概念的位置——“绝对者”恰恰是在它整个“劳作”、“触及”过程全然终结的地方真正开启,也唯有在终结时刻也即在无他者、无时间性的时刻,它才抵达自身并抛弃所有,包括对自我和他者的反复占有。这是一个绝对异化、绝对专有的时刻,它在抓住专有的时刻就抛弃对专有的执著了。阿甘本认为这个“专有者”就是连接黑格尔与海德格尔思想的界槛,他也将其描述为浸入激情的爱河而彻底狂乱的时刻,狂乱使人避免落入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的无尽轮回,是虚无主义的行动机器的不起“功效”、非“现实化”。它也是阿甘本所谓“羞耻”和“自我—触感”意味的异质性的生命经验。这是黑格尔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所留下的最为关键的思想资源——辩证法在终结时刻的自我献身解除了它对强权和虚空的眷恋,而为人们自由使用自身生命开辟了活路。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虚无主义的政治呈现出“一切皆为政治”的“去政治化”盛况。政治向日常生活全面推进、绝对敞开并绝对赤裸,但在门户大开的同时却不允许任何人真正进入甚至改写它,现代社会是丧失了自身实在的景观式的、博物馆式的社会。对此,学者埃斯波西托曾指出,需要重新提出一种“非政治”的范畴去抵抗现代“去政治化”和“超政治化”相互抵牾的两难境地。“非政治”不是“反政治”的意思,它和政治共享一个场所,要做的是消解政治借由主权机器与权力生产、再生产系统所设立的规定与边界,以还原政治纯粹而无可分的存在。既然虚无主义时代带来了传统历史国家论的终结,与其中诸种界限、范畴本身的相互侵越转化、不可区分,那么批判工作的立足点不应该是对这些概念进行溯源和求真,而是阻断计算、转化,即阻断辩证法的再生产逻辑、时间性的生成逻辑和专有性的财产逻辑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从而让无限运转的权力机器得以停歇甚至倒转。因此,虚无主义政治的未来召唤的是一种非功效、纯粹否定、绝对异化的共同体,“从这一角度看,共产主义标志着死亡的毁灭,即死亡他异性效能的终结,因为它使生命完全内在于自身之中”〔16〕。这种共同体的模型已在法国哲学诸学者那里给出了异彩纷呈的答案,而阿甘本所做的是将它定位到绝对受益的起点,即“异化”、“绝对者”或“专有者”,它们正是黑格尔虚无主义批判工作中最为卓越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