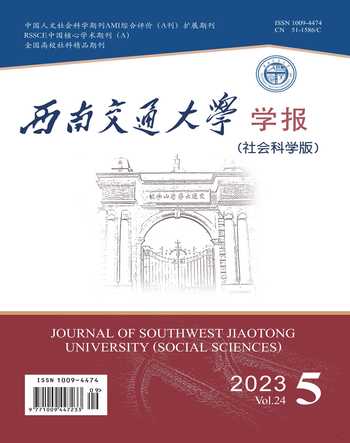厨房、闺阁与职场:论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空间
2023-02-25李燕妮
李燕妮
一、引言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1〕在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男性对应的是“生产的、公共的、城市的”〔2〕等优位空间,而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性对应的则是“生殖的、私人的、家庭的”〔2〕等劣位空间(1)该处对应的英文原文为:“production,public,male,city”(生产的、公共的、男性的、城市的)以及“reproduction,private,female,home”(生殖的、私人的、女性的、家庭的)。参见Jane Rendell,Gender,Space〔C〕∥Jane Rendell,Barbara Penner,Iain Borden,et al.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0:104.。针对父权文化对两性空间的此种有失偏颇的编排,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在《空间、地方与性别》一书中指出:“将女性束缚于家庭空间内的意图,既是对女性所进行的一种特定的空间控制,也是借此对女性身份进行的社会控制。”(2)此处对应的英文原文为:“The attempt to confine women to the domestic sphere was both a specifically spatial control and, through that, a social control on identity.” 本文将此句翻译为:“将女性束缚于家庭空间内的意图,既是对女性所进行的一种特定的空间控制,也是借此对女性身份进行的社会控制。”〔3〕为了抵抗父权文化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女性主义者开始了对女性空间的重新思考,她们“不仅仅是把性别和父权连接起来,而且开辟了压迫、剥削和臣服形式的一个更多中心的局面”〔1〕,更将女性“表征的生活空间重构为养育抵抗的场所”〔1〕。
纵观女性文学的发展长河,可以发现,女性对自身空间的反思由来已久。自伍尔夫以发聩之声呐喊要实现女性的解放与独立,须使女性“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并“始终在写作中强调女性的独特力量”〔4〕,对女性空间的批评与女性意识的生发、成长方骖并路;至桑德拉·吉尔伯特及苏珊·古芭以破晓之力摧毁父权禁忌封锁的幽暗阁楼,使苦于文化压迫与夫权折磨的“疯女人”激情归来,随着女性对自身自由空间呼吁的日渐强烈,女性的自省意识也日渐勃发;再到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性写作中,苦于其所、不得其位的女作家们在一处处自我涕泣、自我言说的女性空间里,以独立坚韧的主体精神、充沛昂扬的生命热情破除父权遗存的森严壁垒、敲碎礼法围城的铁壁银山。
徐小斌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她仍笔耕不辍,在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中,她对女性空间的书写颇具意义。她曾以《双鱼星座》一文在女性写作中颇得好评,而她的《羽蛇》《别人》《天鹅》等作品虽无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却同样体现着细腻深刻的性别思考、高度自审的女性意识及紧扣时代的批判精神。在揭示女性被男性霸权抹煞、代言的性别经验及生命价值上,徐小斌独辟蹊径,撷取厨房、闺阁与职场等女性空间,并经由这一片逼仄的天地,让被陈俗旧约压抑千年的女性经验浮出地表,从而在琐屑日常的累筑与柴米油盐的熏染中,打破男性霸权与女性无意识积淀赋予女性的磨灭才情、牺牲事业、无薪多劳的“灶下婢”、“枕边奴”与职场“边缘人”的形象。本文拟融贯性别地理学、叙事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在女性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对徐小斌笔下的“厨房”、“闺阁”与“职场”这三类女性空间进行系统地挖掘,以期深入把握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空间书写现象,并为当代文学中女性空间的批评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厨房:巧妇何须作羹汤
君子远庖厨,巧妇作羹汤,在男性主流秩序运作资本、男权价值体系评估空间的年代中,传统炉灶被认为是男性定义的女性空间:“炉灶的空间生产,其主角多半是女性,男性的进入代表着另外的意义,而这正是反映了对母职的期待。女性透过厨房炉灶获得属于女性的资源,发挥生育与母职的功能,但并不能逃过父系制度对其角色的分派与认知,使得‘女人的空间’具有特定的意涵。”〔5〕父系社会中,厨房这一空间的所有权被牢牢地掌握于男性手中,而厨房的使用权却被交予女性,厨房这一方寸之地也由此带有浓郁的阴性色彩,厨房里的光色流转与女性的家庭生活相伴相生。
在徐小斌的小说《双鱼星座》中,C城女编剧卜零与公司总经理韦之间维系着一段表面上风光无限、内里却缺情少爱的婚姻。卜零深知事业发达了的韦对自己已了无兴趣,但饱受委屈的卜零依然尽心扮演着好妻子、好厨娘的角色。在豌豆上市的季节里,卜零经常在距离韦下班还有一个小时时,就拉开架势剥豌豆,为韦烹制鲜嫩可口的素食小炒,以使吃腻应酬场上香槟大餐的韦大饱口福。但对于卜零在厨房内的操劳,韦并不曾心怀感激,他反而认为这是卜零应尽的义务。在卜零偶尔因身体抱恙、无法下厨时,韦便愠怒难忍、牢骚满腹。而厨房中的一切,哪怕是火柴的使用与摆放,都得以韦的意愿为尊。小说中写道:“韦觉得吃卜零炒的菜是一种享受,但是这种享受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刚性过程——完全不可逆转。偶然卜零没有按时做好饭,韦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韦明令点煤气灶的火柴不能丢掉,要码放整齐,在需要同时点两个灶眼的时候,就可以节省一根火柴。”〔6〕
韦对卜零未按时做饭的不满以及对厨房里火柴使用的规定等,都显示出男性对女性吊诡的厨房主权。实际上,卜零是一位独立优秀的知识女性,她理应享有与丈夫韦同样的家庭地位与权利,但遗憾的是,卜零迷失在厨房这一禁锢女性自由脚步的空间内,以厨房内的美酒佳肴犒赏韦的胃、笼络韦的心。与婚姻中迷失于厨房之内的女性相似,婚姻中的男性对自身的厨房主权也有着离谱的自信。恰如《双鱼星座》中所揭示的男性厨房主权,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十八般厨艺依然是男性考察女性是否贤良的标尺,男性也理所应当地成为厨房资源的监督者与厨房果实的享用者,厨房这一空间成为消弭女性主体意识、物化女性主体身份的囚牢。然而不无吊诡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厨房主权建立于男性攻城拔寨、为家庭提供物质基础与空间庇佑的年代,时至今日,多数女性早已实现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独立,而厨房依然是女性向男性表达爱意的古堡。徐小斌曾在自身的创作谈中表示:“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者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源于和女性缪斯的感性交往。”〔7〕诚然,当代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都享有较之以往更多的权力,但她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唯男性价值规范、审美标准马首是瞻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里,文化习俗中承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设定以及男权中心思想的历史存续,都使女性将来自于社会的、男性的“相夫教子、持家孝亲”等女性行为规范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主动选择,并使女性将外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自我潜意识中的压抑,进而使当代女性在厨房的虚假围城中徘徊陷落,几度出走却又几度回归。
徐小斌对女性从厨房中不断出走、又不断回归的这一吊诡现象思考颇深。小说《别人》中,被已故父亲以摔碎的喜字镜托梦的何小船得以从传统婚约中突围,顺利走出婚姻与厨房。可不幸的是,数十年之后,她又在宿命力量的裹挟下,在不惑之年里沦陷于与有妇之夫任远航的痴缠中,从不下厨的她为讨好情郎而“洗手作羹汤”。她不但悉心办厨,还描眉画眼,一改往日闭门谢客、不事梳妆的随意形象,化身为娇俏可人的美厨娘。但遗憾的是,在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及个人主义风行的当代社会中,道德律令已不再是人人奉守的圭臬,家庭关系也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金汤,男女两性靠一纸婚书维系的婚姻都尚难白头偕老,更遑论老姑娘何小船浪漫、冲动的婚外情。在何小船与任远航畸形关系的日渐恶化中,她曾向情郎表达爱意的厨房化作了一幅爬满蚁群的幻境:“她已经从一个过于旺盛的胖姑娘变成一个干巴巴的瘦女人了,感情的消耗实在是太可怕了……桌上的食物在那股蓦然而至的香气中变得酸腐,满屋都是搬运的蚁群……”〔8〕何小船与任远航的恋情最终在任远航事业的牵制与家庭的牵绊中结束,失落的恋情让何小船慢慢觉醒,也让她意识到她倾情所爱的男人是与她毫不相干的“别人”。徐小斌曾坦言:“无论这结论多么残酷,我们不得不承认性沟远远深于代沟——特别是在这个商业主义神话的时代。”〔9〕从人类学上来看,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长于感性的性别,她们“生活中的一些转变期引起了各种惊讶和忧虑,这些让她们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众所周知,女人特别易于患上歇斯底里症”〔10〕。相较于被感性与文化积习扼住咽喉、易耽于情爱的女性而言,处于男权中心社会和商业主义神话合谋时代中的男性,更倾向于把自身的才华、精力与热情投注于事业之上,爱情于他们而言大多只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调味品,这也就是在何小船与任远航的情爱拉锯战中何小船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
与《别人》中何小船失落的厨娘美梦相似,《双鱼星座》中,卜零也一度从凉薄的家庭中出走,却又在事业遭遇滑铁卢之际回归,试图以巧手办厨寻回婚姻的热度;但遗憾的是,卜零的厨娘幻想也殒落于韦的绝情之下。综观徐小斌的小说,可以发现这一幕幕女性爱无归处的悲剧,确乎是作家别具匠心的安排,汪民安指出:“厨房是接纳父权制的最佳场所,是社会结构刻写在家庭空间中的最深的痕迹。”〔11〕在徐小斌笔下,女性对“厨房”这一空间的认识由浅薄到深入、由模糊到清晰,被男权社会中无薪多劳的“灶下婢”形象折磨已久的当代女性,逐渐辨明了蕴含于“厨房”之中的有失偏颇的两性权力关系。于是,清醒之后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妇女要获得平等地位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摆脱厨房的琐碎管制”〔11〕。在徐小斌笔下,从厨娘之梦中觉醒的女性最终得以勘破男性吊诡的厨房主权、跳脱出无爱的家庭空壳,她们开始在厨房中进行自由的行为选择与情感表达。《双鱼星座》中,认识到丈夫韦的虚伪、势利与薄情的卜零,在幻梦中以厨房内的冰冻里脊为武器,完成了对韦的复仇。《别人》中,从伤筋动骨的情爱之痛中觉醒的何小船,把情郎任远航的照片与预卜爱情的塔罗牌一同铰碎扔进垃圾桶,她不再走入厨房、不再为所谓的爱情“洗手作羹汤”。
在徐小斌的小说中,“厨房”这一女性空间有着特殊的性别批判意味。女性在厨房内的出走与回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权文化积习与物化时代法则对当代女性独立与发展之路的掣肘,它们使得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犹疑不知进退、彷徨不知归处。但需要指出的是,伴随当下女性自审意识与自由意识的成长,女性在厨房内的犹疑与彷徨也必然只是暂时的,正如徐小斌笔下愤而反抗男性厨房主权的卜零及何小船,当代社会中充分觉醒的女性也必将反问自身:巧妇何须作羹汤?有朝一日,追寻自由与自主的当代女性,必然将厨房这一男性文化委派给她们的空间变成一间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屋子,厨房内美酒佳肴的不在场也将是她们冲决男性强权,并弃绝自身被男权物化、消费的客体身份的勇敢宣言。
三、闺阁:重重帘幕未遮灯
关于“闺阁”一词的涵义,最早见于两汉时期,此时的闺阁或作内室小门之意,或作宫禁之意。自唐以来,闺阁的词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用以特指女子的卧室;其后,闺阁一词又逐渐引申出妻室、妇女之意;近现代以来,闺阁更是带有了挥之不去的脂粉气,成为父权安置女性的深深别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福柯在《性史》中极为强调饮食伦理与性伦理之间互文共生的关系,他指出厨房与卧室是女性满足男性口腹之欲与床笫之欢的私密空间,从性别地理学来看,闺阁隶属于家庭空间,它包括卧室、浴室、阁楼等女性空间,同厨房一样,闺阁也带有挥之不去的阴性色彩,成为男性消费女性的另一场所。
在徐小斌的小说中,闺阁一方面显示出男权规约与文化禁忌对女性欲望的钤制。如《迷幻花园》中的芬,在鸡冠花与古旧饰物装饰的、颇具性讨好意味的女性闺房内向金交付初夜;《别人》中的何小船多次身着性感内衣、在体香萦绕的卧房里于任远航的情爱谎言中迷失。闺阁这一女性空间在此既带有女性向男性献媚邀宠的风月之色,又带有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约束甚至凌虐的性暴力色彩。另一方面,恰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花儿总在种子里。’这句令人赞叹的箴言说的正是家宅,正是以无法忘却的内心空间为特点的卧室。”〔12〕闺阁作为私密的女性居室,在观照女性欲望的同时,也反映着女性内心深处的情绪与思考,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女性对性别文化痼疾的反思。
闺阁之内,镜子是重要的意象之一,镜子的存在使闺阁中的女性得以观照自身的生命状态、审视自身的欲望诉求。《迷幻花园》中在青春泉内洗浴过的芬,虽明丽动人,却不得不在象征“青春”、“生命”与“灵魂”的三张纸牌中三选其二。抛却“生命”的芬大限将至,在生命的最后期限里,她焦灼地欣赏着自己以命相求的青春与美貌:“房间里找不到任何开关。无数玻璃镜在四周镶嵌,镜子拓展了空间……这时她看见墙壁上出现了幻象。一个美丽的女人幽灵般地走近……这时她才突然明白那女人就是自己。她惊疑不定,用挑剔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个’女人。确实很美丽,这样完美的女人走到哪里也会倾国倾城迷住所有的男人。”〔6〕闺阁中的镜子不仅映照出芬的生活世界,也映照出芬的心理空间,它是芬的真实欲望与隐秘情感的曲折反映,透过真幻交织的镜像世界,芬看到了被男性审美趣味塑造起来的、美得可怕的自己;也看到了生活于男权阴影下,思想与意识都残破碎裂了的自己。而又正是这残酷的镜像世界的刺激,使芬彻底认识到自己倾情所爱、追逐一生的男性金不过是一位精神与肉体都极尽丑陋、形似蓝田猿人活化石的男人,此时的芬也了悟到自己“为了赢得这个活化石的青睐,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美丽和青春”〔6〕的行为的荒唐。
小说《迷幻花园》一方面通过闺阁中女性渴求美、渴求青春、渴求男性青睐的镜像世界,反映出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恰如小说中三选其二的纸牌游戏,青春、生命与灵魂三者难以周全的选择预设,对女性而言本就是不公平的:抛却青春,那就意味着美人迟暮;抛却生命,那就意味着时日无多;抛却灵魂,那就意味着行尸走肉。在失之偏颇的性别预设下,女性的选择终究充满艰辛,而女性的悲情宿命,在商业主义神话与男权法则合谋的当代社会中,也更显沉重。在这样的时代里,需要女性付出的终究更多,她们在努力成长、孜孜求学的漫漫长路中,却要承受青春易逝、红颜易老的焦灼与惶恐;在体验爱情的同时,又要承担起流血、妊娠的风险与伤痛;在追寻事业的同时,还要肩负起持家、育儿的责任等……诸如此种,让女性苦不堪言。但另一方面,《迷幻花园》中闺阁内的镜像世界也映射出当代女性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认识已日渐深刻。面对爱情,她们不再是盲目扑火的飞蛾;面对男权,她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她们从逆境中获取生存的智慧,从苦难中磨砺生命的韧性,她们努力勘破生存迷雾、抗争现世难题,进而在努力找寻自我、建构自我主体性、实现自我认同的真实心路历程中,展现女性璀璨的生命之光。
此外,闺阁一定程度上也对应着女性身体的欲望。福柯将“身体”视作是权力规训与惩罚的对象,他指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3〕。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被视作是男权规训的对象,女性身体的大小、形态、欲望等都在男性权力的规训、塑造与惩戒之下,而“女性的欲望、饥饿和食欲在父权制社会中被看作极具威胁力因而需要控制的对象”〔14〕,故男权规训女性身体的首要任务当属压制女性的欲望。徐小斌笔下反映女性欲望的闺阁,一定程度上也见证着父权规训下女性欲望失衡的落寞与凄凉。如《玄机之死》中,感情受创、离家出走的鱼玄机,在青灯照壁、古佛伴身的咸宜观内带发修行;《羽蛇》中,有着懵懂、屈辱的性启蒙经验的若木,在往后的岁月里,于雪洞般寂寥的深闺内聊以度日。别尔嘉耶夫指出:“性是人的生活的隐蔽方面,在性里总是有某种令人羞愧的东西,人们不准许暴露性。人为自己受性的奴役而感到羞愧。”〔15〕在男性公共意识与价值规范一统寰宇的年代,“性”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女人言“性”尤为忌讳,在性爱中,男性攻城略地,多扮演霸权者与索取者的角色,而女性却是接纳者与驯服者的身份,女性自身的性欲望、性经验、性感受等则完全被置于男权家礼的遮羞布下无从言说,更难以发泄。
福柯在《性经验史》一书中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16〕男权社会中,被男性规训与塑造“身体”的女性,同样也以自身的“身体”作为对抗男性强权的有力武器。在徐小斌的小说中,女性在饱尝欲望失衡的苦痛后,开始摆脱对男性性爱霸权的依附与讨好,她们收回被男性代言千年的“身体”,自主探寻身体与欲望的言说方式,以闺阁控诉男性的强权,追寻女性自然合理的生命欲望。《迷幻花园》中初恋受创的怡将全副身心寄托于事业,同时以与闺阁之内的私密工具相伴的岁月来填补自身缺位的爱欲;《羽蛇》中的羽与同性金乌忘情欢爱,在金乌的引导下,向来拘谨的羽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秀美,并将自己自然饱满的欲望充分释放出来,她以浴池之中的黑色郁金香为秘密工具,与心爱之人共同享受肉身相亲的曼妙快感。闺阁之中的私密之物,成为女性探索自身身体秘密、释放自身合理欲望的端口与媒介,它将性爱关系中的男性一维彻底抹除,使女性由被动的性爱客体变成真正的欲望主体。
在徐小斌的小说中,闺阁这一女性空间不仅显示出男权规约与文化禁忌对女性欲望的压制,更体现出女性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真切认识、对两性权力关系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自身存在困境的勇敢抗争等。徐坤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现象时,借用北宋词人张先的“重重帘幕密遮灯”(3)徐坤在《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中指出:“当看到权威话语在谈到女性写作并得出结论时,都在近乎一致地提出要将女性写作提升到高度上去。只是不知,一直都在高度之中孜孜矻矻攀升着的我们,其内在和思想何曾与人类整体文明精神高度相悖离?如若没有悖离,那么究竟何处又是女性写作的灯?何处才有女性写作那烛照的光明?”在徐坤看来,90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并不失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思想,只是,90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尚处于男性文化与权威话语的包围之下,因此,彼时的女性文学写作还处于“重重帘幕密遮灯”的尴尬情境之中。参见徐坤《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刊于《作家》,1997年第8期。一语,追寻男性文化与权威话语包围下女性写作的“灯”与“光明”〔17〕。徐小斌小说中对闺阁这一女性空间的书写与批判,确切来说,更可谓是“重重帘幕未遮灯”。徐小斌笔下的闺阁充当着女性批判男权、言说自身合理欲望的媒介,闺阁这一空间某种程度上撤下了男权规约与文化禁忌加之于女性身体与欲望的达摩克斯之剑,它使女性在自身欲望言说的自由、自主中,寻觅到生命真正的独立与完满。
四、职场:但见道路阻且长
徐小斌小说对女性空间的反思与批判,除了体现在对厨房与闺阁的思考上,还体现在对出走后的“娜拉们”的职业空间的思考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8〕时代语境下,社会机制的向前推进、文化模式的包容多样与女性权利的逐步明晰等,都带来了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的重组复构,走出厨房、步出闺阁的女性也迎来属于自己的事业竞技场,但这是否又意味着女性业已享有和男性齐平的职业地位呢?答案依然不容乐观。
从性别本质主义出发,考察两性职业地位的失之偏颇可以发现,其根源依然存在于社会观念对女性的身体条件、性格特质、智力水平等的刻板偏见上。妇女学专家芭芭拉·维尔特曾对19世纪美国社会盲目崇拜的“纯正女性风范”(true womanhood)进行了反思(4)此处对应的英文原文为:“The attributes of True Womanhood, by which a woman judged herself and was judged by her husband, her neighbors and society could be dividided into four cardinal virtues—piety, purity, submisineness, domesticity. ” (纯正的女性风范,一个女人评判自己并被丈夫、邻居和社会所评判的特质,可以被划分为四种基本美德——虔诚、纯洁、温顺、顾家。) 参见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8, No.2 (Summer 1966), p152.,她指出,纯正女性风范倡导虔诚(piety)、纯洁(purity)、温顺(submisiveness)、顾家(domesticity)〔19〕。从芭芭拉的总结中我们不难发现,彼时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考评着眼于其对家庭的忠贞与奉献,他们所提倡的完美女性多为“家中的天使”,对于女性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他们罕有评论。近些年来,性别本质主义者在区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时,也指出女性气质的特征表现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男性气质的特征表现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思维分析思辨的〔20〕。于此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观念中对于两性气质的认识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也依然存在简单化、刻板化、模式化的倾向,时至今日,社会观念中关于男女性别气质的认识依然不免夸大了女性的家庭属性,弱化了女性的社会属性。
在徐小斌的小说中,一方面,女性在职业空间里多扮演男性上司的下属或雇员,她们也极易在职场的竞争与裁员中被淘汰,这确乎是作家有意为之的安排,借以讽刺当代社会中,女性因自身体力的短板、妊娠育儿的需要总是被安排于职场边缘的现象。诚然,时代发展到今天,两性关于性别特质、性别差异、性别分工的观念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但这些进步依然不足以消除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刻板偏见以及男性强权对女性的欺压与打击等。在徐小斌的小说中,大多数女性在职场中依然无缘高位,即便她们有了抛家别夫的勇气、不让须眉的才情与立业建功的决心,却依然不免在职场的勾心斗角与男权的倾轧算计中遗憾折戟。
小说《天鹅》中,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离异女教师古薇,因想让即将中考的儿子上个好学校,不惜放下自己一向坚守的清正之气,开办暑期作曲培训班,以改善自己和儿子困窘的经济局面。但久在象牙塔、不懂人情世故的她,却因教学严格得罪了颇有背景的学生孙路,面对学艺不精却极其狂妄的孙路,古薇不过是以严师的身份对他进行教育,期望能使他端正学习态度。然而古薇的诤言,不但没使孙路意识到自身的毛病,还将自己置身于职场内四面受敌的困局里,孙路的家长不但不感谢古薇对其子的严格执教,还责骂古薇毁了自己的孩子;平时笑面菩萨一样的学院领导因害怕得罪孙路的家长,不惜对冲撞权贵只为维护音乐学院尊严的教师古薇做出停课处理的重罚。这样的工作打击使古薇身心俱疲,但她并没有沉溺于工作失意的伤痛中,而是将这种前所未有的空无感与失落感化为创作灵感,如有神助般地创作出一首双主题的赋格曲。离异女教师古薇凭一己之力操持家庭、供养即将步入高中的儿子本就不易,职场中不辨是非曲直的倾轧更让古薇心碎。小说《天鹅》在揭示离异女性工作窘局、经济窘局与精神窘境的同时,也揭示出女性在面对职场打击时的精神韧性。
另一方面,因男性主流的职场地位与煊赫的权势地位,女性在职业空间里多只占据一方边缘之地,男性依然将女性视作职场潜规则命定的利用与征服对象,一旦女性表露出对既定规则的拒不融入态度,等待女性的就极有可能是事业的失败。小说《双鱼星座》中,电视台老板对下属卜零的姿色垂涎已久,无奈卜零不为所动,故老板在工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刁难卜零,对于质量拙劣、格调庸俗的剧本《南国红豆总相思》,卜零早就给出了“庸俗”的审稿意见,老板却对卜零迎头痛批,执意认为该剧符合群众趣味,并坚持与剧作家合作。而后,上级领导在审阅该剧本时,发现该剧本除格调不高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问题,故该剧本的投拍计划夭折在襁褓中。然而可笑的是,卜零的老板却在其后的尴尬局面中将所有问题全推给了卜零,使得单位中的其他同事都认为是卜零的组稿出现了问题,才牵累了老板。于是大家都在替老板鸣不平,而委屈的卜零却无处伸冤,在与老板擦肩而过时,卜零也试图向老板讨要说法,但她绝望地发现:“老板的眼睛像一片荒原一样一马平川,毫无内容”〔6〕。
如果说下属替上司担责已是职场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卜零老板用阴招诓骗卜零去献血,又以卜零献血之后因身体康复需要休假的时间太长为由将卜零从电视台革职,就充分体现了男性利用女性在生理条件上的弱势对女性进行欺压的行为之可恨了。卜零在工作中并无任何差错,她秉公办事、清正为人,在单位号召献血时,她也义无反顾、积极响应号召,本应成为单位嘉奖的员工,却因始终不为老板的淫威所动,而成为老板不得不拔的“眼中钉”。无独有偶,小说《入戏》中,不通“潜规则”的梅清风也是如同卜零一般的职场边缘人,她始终难以违背本心向觊觎其姿色的男上司献媚讨好,亦无法与擅于“走后门”的权贵达成合作,故梅清风不仅无缘职场高位,还因疲于事业忽略了对儿子的教导,以致自身陷入家庭、事业与生活的四面楚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卜零还是梅清风,都未在职场的打击中一蹶不振:卜零在看清老板的阴毒之后,挥别了C城的编剧一职,并计划远赴佤寨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梅清风在四面楚歌中,依然不忘初心,竭力抚平职场倾轧带给自身的伤痛,并继续追寻自身的职业理想。
诚然,女性走向职场,将千年来束之高阁的才情与梦想置于台前,与男性同台竞技、一较高下,这本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当代社会中,职场中的女性依然饱受男性霸权的压迫、性别分工的钤制与文化规约的束缚,对于出走后的“娜拉们”到底“何处是归程”?这恐怕不易回答,当代女性建构自身职业空间、求索自身职业地位的征程,依然不免是“道阻且长”!对于女性职业空间的深思与求索,主要集中在徐小斌21世纪以来所创作的作品中,此时的徐小斌经历了结婚、生子、工作、改行、离异等人生的重要事件,对于婚姻、事业、价值、理想、追求等主题,她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种情境下,她对21世纪中女性的职场人生进行了重新反思,但遗憾地发现,历经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社会并没有对女性真正大开方便之门,女性所面临的职场困境也并没有多少改善。与之相反,女性的工作与情感压力反而愈加繁重。但也正是因此,在职场困境中奋力拼搏的女性带有了英雄气,她们努力跳出家庭生活的平淡圈,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披荆斩棘、一展芳姿;她们以梦为马,在职业理想的引导下,不断攻克职场难题,竭力找寻那片确证自身生命价值的职业高地!
五、余论
综合考察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空间书写,可以发现其价值主要集中于文学与文化维度上。从文学维度上分析,徐小斌笔下的女性空间书写将“厨房”“闺阁”“职场”等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却又未被充分阐释的女性空间意象引入创作中,独辟蹊径地考察出这些意象所承载的女性意识,探讨其对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主体欲望言说、职业地位求索等方方面面的作用。
不同于同时期女作家残雪对梦魇空间的恣意捕捉,迥异于迟子建对黑土地上乡村世界的情有独钟,徐小斌笔下的女性空间涵括女性生活的点点滴滴,从素手煲汤的厨房,到对镜自赏的闺阁,再到披荆斩棘的职场,这些女性空间无一不弥漫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浸润女性安身立命的不易,也正是这样撷取自生活、渗透作家生命经验及性别感悟的空间才独具生命力,其所体现的价值思考也尤显真实。
从文化维度上考察,空间可以被视作是权力关系、文化法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反映。徐小斌笔下的女性空间书写是管窥社会多重关系、性别文化结构与时代中心法则的一方窗口,女性空间书写的深度展开不仅为反思历史遗留的性别文化痼疾提供了言说的渠道,而且有利于将被菲勒斯中心文化压抑千年的女性悲情宿命重置于历史的台前,从而真正找寻到当代女性的发展与进步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