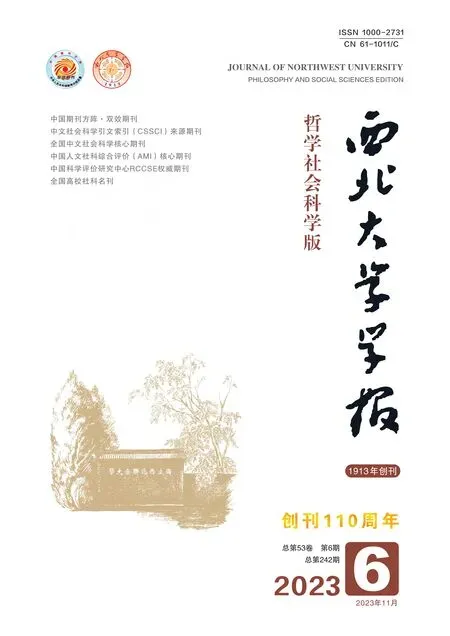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及其应对
——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维度
2023-02-24宋连斌武振国
宋连斌,武振国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制裁法是一项源起于古希腊的国家政策工具,其通过直接宣布某类合同无效,或是控制人、物、数据流动阻碍某类合同的履行,以达到限制特定交易的目的[1]。当交易可能违反制裁法时,如果企业遵守制裁法所设置的履约障碍,便需要承担违约风险;如果企业无视制裁法所设置的履约障碍,便需要承担制裁风险。为了从两难困境中解脱,国际贸易主体常常在交易中约定遵守制裁法,以做到企业合规。在此背景下,后续的争议解决程序是否承认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裁判者承认制裁法的法律效力,交易主体便可通过企业合规,从“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中解脱。如果裁判者否认制裁法的法律效力,交易主体仍需面对双重风险。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商事合同适用制裁法的研究比较有限,对制裁法的法律地位也呈现出相互分歧的立场。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认为,国际私法的建构基础是“法律关系”,其在本质上属于私法的延伸,外国公法不宜成为法律适用的对象[2]。而冲突法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构建基础是“政府利益”或“规制利益”,其在本质上属于私法的公法化或私法的社会化,故实体合同准据法中的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在符合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均有可能得到适用[3]。成功协调上述分歧,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正本清源,还可在企业合规的大背景下有效应对制裁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中国企业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
一、制裁法域外适用的理论分歧
作为一种强制性规则,制裁法可在属地层面发生公法效力,此点无需赘言。然而,外国制裁法可否引入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领域并发生域外效力,在学理层面则存在根本分歧。
(一)“法律关系本座说”对制裁法的拒绝及其局限性
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认为,国际私法的构建基础是民事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借由民事法律关系锚定民法的法律,国际私法应随民法被定性为私法,在原则上无法与外国公法相容。此观点之形成,源于私法自治和公法管制二分的基础理论。以任意性为主要特征的私法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可以由中外当事人凭借个人意志进行选用,天然便具有域外效力,可以进入合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而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公法属于国家管制的范畴,原则上只能在属地层面发生公法效力,不能进行域外适用,难以经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进入国际私法的领域。循此逻辑,在国际私法案件中,裁判者不能适用外国公法,也不能执行根据外国公法作出的裁决,至于本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则,也应当逐渐消亡以至于无。经过不断的发展,上述观点形成了国际私法领域的“公法禁忌”原则。显然,根据传统观点,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原则上对外国制裁法关闭了大门[4]。
“法律关系本座说”固然精妙,但实践的发展却与该理论的设计初衷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偏离。一方面,“法律关系本座说”通过公私法二分的方式将国际私法定性为私法规范,并预期其中的强制性规则将逐渐消亡。然而,在立法实践中,各国制定的强制性规则不减反增,甚至在条款的数目上有超过纯粹冲突法规范的势头[5]。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本座说”根据法律关系本身的性质在全球范围内形式化分配立法管辖权的做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被选择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质后果,也忽视了被选择法律与外国公法的潜在冲突,可能会在个案中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在实践中,为了避免被外国的强制性规则惩罚,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常常会约定遵守特定国家的制裁法。此时,即使“法律关系本座说”不承认外国公法的域外效力,外国制裁法也能通过合同条款的援引发生实际效果。这意味着,根据“法律关系本座说”所发展起来的“公法禁忌”原则,不能满足当下的现实需求,在部分领域甚至无法获得商事主体的普遍遵循[6]。
(二)“政府利益分析说”对制裁法的引入及其解释力
考虑到“法律关系本座说”仅符合形式上冲突正义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律适用背后的实质正义,最近一次的冲突法革命建议将法律背后的“政府利益”或“规制利益”作为国际私法的构建基础和适用标准,这便是“政府利益分析说”[7]。在该理论语境下,虽然国际私法的主要调整对象还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由于法官需要对法律背后的“政府利益”或“规制利益”进行综合评价和适用,国际私法实际上具有了独立于民法之外的选法逻辑,并随着“政府利益”的深度嵌入而具有了公法化或者社会化的色彩。显然,“政府利益分析说”能够有效解释国际私法中为何可以包括法院地强制性规则的问题,也能够为外国公法的适用铺平道路[8]。
随着“政府利益分析说”的传播,不少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已经注意到国际私法公法化或社会化的现象,逐渐允许在国际私法案件中适用外国公法[9]。在国际立法层面,欧共体1980年《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1980 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以下简称《罗马公约》)第7条和欧盟2008年《关于合同之债准据法的规则》[Regulation (EC) No. 593/200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June 2008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以下简称《罗马I》]第9条规定:“实体合同准据法以外的国家(下称‘第三国’)系合同应当或实际履行地点的,其颁布的优先性强制性规则可被适用。在考虑是否实施这些规定时,应对优先性强制性规则的性质、目的以及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10]462在国内立法层面,承认外国公法域外效力的国家也在增多。例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9条规定:“依照瑞士法律观念值得保护且明显占优势的当事人利益之要求,考虑本法所指定的法律以外的另一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如果案件与该另一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则可考虑另一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决定前款所指的另一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应根据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适用结果,是否符合瑞士法律观念项下适当的判决标准进行判断。”[10]380201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法院在根据本编规定适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时,如依照与法律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另一国法律,该另一国的强制性规则是直接适用的规则,则可考虑适用该强制性规则。此时,法院必须考虑此类规则的目的、性质、以及适用或不适用的后果。”[10]94除此之外,《韩国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第6条、1998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38条也有类似规定。而作为“政府利益分析说”的发源地,美国法院在处理外国法律的效力时,不会严格按照公法或私法属性区分其适用方式,而是在美国的冲突法框架内,通过政府利益分析和礼让原则一并进行处理[11]。
(三)“法律关系本座说”和“政府利益分析说”的关系
自巴托鲁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提出法则区别说以来,国际私法的构建基础至少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变动。第一次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将国际私法视为以法律关系为形式化选法基础的民法适用法,使得私法属性占据了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法禁忌”原则[12]。可以说,“法律关系本座说”能够很好地适应当时的时代背景。毕竟,在以低技术产品为主要交易对象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商品易于生产,交易主体的可替代性强,很难因为私人或者政治实体的原因发生供应链危机。此时,市民社会所进行的商业交往不会对政府利益造成明显影响,公法原则上无须适用于国际贸易,否则将影响合同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危及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随着交易对象转向高技术产品,商品的生产难度显著提高,一些关键领域供需失衡并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基于私人或政治实体的因素发生供应链危机的可能性显著提高。特别是在芯片等关键领域所进行的商业交往常常会对政府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国家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意图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公法规范[13]。此时,如果国际私法依然固守“法律关系本座说”的传统,拒绝将公法引入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显然是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典型体现。可喜的是,在国际私法构建基础的第二次革命性变动中,柯里(Bralnerd Currie)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将法律的实质内容及其背后的“政府利益”作为选法依据,不再对应适用法律的私法表象进行限定。该学说为公法的域外适用打下了基础,也使得国际私法具有了一定的公法属性。同时,该学说关注法律规范背后“政府利益”的重要性,无疑会导致国际私法从形式上的冲突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从一般逻辑上看,这种进化可谓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显然,随着国际贸易秩序的改变,“政府利益分析说”不仅更能适应当下国际贸易关涉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还是一种实质性的进步方案,无疑代表了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14]。
尽管“政府利益分析说”代表了国际私法的未来,但其与“法律关系本座说”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第一,“法律关系本座说”强调国际私法的私法属性,也就是合同法律适用受私法控制。而“政府利益分析说”并没有否认这一论断,只是将法律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公法领域,承认合同法律适用可以由公法和私法共同调整。
第二,“法律关系本座说”强调形式化的冲突正义,而“政府利益分析说”则借由法律背后的立法利益强调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本就相伴左右,在理想情况下理应浑然一体。
第三,“法律关系本座说”通过在全球层面分配立法管辖权的方式实现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而“政府利益分析说”要求分析立法利益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灵活性,确定性和灵活性本就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由此可见,在现阶段全然抛弃“法律关系本座说”并不可取,更务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冲突法规范的基础上,在个案中对公私法适用的政府利益进行综合考量[15]。
二、“政府利益分析说”语境下制裁法的适用路径及其限制
在“政府利益分析说”语境下,国际私法具有了一定的公法化或者社会化色彩,可以将其范围扩展到制裁法领域。然而,由于“政府利益分析说”尚未成熟,为了兼顾国际私法的确定性,制裁法适用的起点仍需借助于“法律关系本座说”所构建的形式化框架。按照制裁法与合同在形式上的联系程度,制裁法可被区分为准据法、法院地/仲裁地法以及“第三国法”三种类型。在上述情况下,制裁法何时能够发生效力,何时无法发生效力,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一)准据法中制裁法的适用及其限制
面对国际私法案件中的合同争议,裁判者应该优先适用实体合同准据法及其中包含的制裁法,只是制裁法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需要受到一定的实质性限制。根据“政府利益分析说”,在个案中具体制裁法的适用需要符合其背后的政府利益[16]294-326。
对于准据法中的制裁法,其背后的政府利益或规制利益可以根据立法意图进行判断。如果制裁法有意影响案涉合同效力,便具有进行法律适用的政府利益。如果制裁法无意于影响案涉合同效力,便不具有进行法律适用的政府利益。其中的差别,可以透过两起案例予以展示。在Arash Shipping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v. Groupama Transport案(1)Arash Shipping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v. Groupama Transport, [2011] EWCA Civ 620.中,法国保险公司与伊朗控股的石油运输公司之间签订了一份保险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遵守欧盟未来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法,否则保险人在案涉合同中的保险责任可立刻中止。合同签订后不久,欧盟出台了对伊朗实施制裁的第961/2010号条例,其中禁止向伊朗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对于本案欧盟法中的制裁措施能否得到适用的问题,需要结合其背后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欧盟第961/2010号条例出台的目的是禁止欧盟企业为伊朗公司提供保险服务,显然对法国公司和伊朗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具有规制利益。因此,在本案的准据法中,欧盟第961/2010号条例可以进行法律适用。而在“天津瑞福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公司海运欺诈纠纷案”(2)天津瑞福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公司海运欺诈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津高民四终字第77号。中,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在货代公司的介绍下,与伊朗海运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合同约定由伊朗海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运煤。在航次租船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2010)号决议,要求各国对案涉伊朗海运公司可能有助于伊朗核扩散的活动进行制裁(3)《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29(2010)号决议》第22条规定:“决定所有国家应要求本国国民、受本国管辖的个人和在本国境内组建或受本国管辖的公司,在与伊朗境内组建或受伊朗管辖的实体,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下属实体,以及代表它们或按它们指示行事的任何个人或实体,以及他们拥有或控制、包括通过非法手段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开展业务时,保持警惕,如果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认为这类业务可能有助于伊朗的扩散敏感核活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的研发,或有助于违反第1737(2006)号、第1747 (2007)号和第 1803(2008)号决议以及本决议。”。获悉此决议后,伊朗海运公司以其将被中国政府制裁而欠缺履约能力为由,停止履行航次租船合同,也拒绝返还中国能源公司预付的运费。中国能源公司遂以合同欺诈为由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通过仲裁和英国法律解决争议,但由于当事人接受了中国法院的应诉管辖,且在陈述时没有要求适用英国法,而是均援引中国法进行诉答,应视为当事人嗣后的选法合意已经变更为适用中国法。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929(2010)号决议的赞成方(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29(2010)号决议》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10年6月9日第6335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在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土耳其、巴西)、1个国家弃权(黎巴嫩)。,案涉制裁法应当嵌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但是,该制裁法能否在本案中得到适用,还需结合其立法目的进行判断。联合国安理会第1929(2010)号决议出台的目的在于禁止伊朗航运公司获取核材料或其他军事用品的能力,并不禁止伊朗航运公司运输煤碳等生活物资,难以影响伊朗航运公司在本案中的履约能力。同时,伊朗航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运煤的路线也不经过伊朗,不会造成伊朗核扩散。由此可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929(2010)号决议对于案涉航次租船合同没有规制利益,伊朗航运公司不能将其作为拒绝履约的理由。
(二)法院地/仲裁地的制裁法的适用及其限制
在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为了和当地的法律体系相容,法院地和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则往往可以直接适用[17]。但根据“政府利益分析说”,制裁法的具体适用仍需符合其背后的规制利益。
对于法院地/仲裁地的制裁法,需根据立法意图判断其在个案中能否得到适用。如果案涉争议属于制裁法的适用范围,制裁法可以得到适用[18]。例如,在Government & Ministries of the Republic of Iraq v Armamentie Aerospazio SpA et al案(5)Government and Ministries of the Republic of Iraq v. Armamentie Aerospazio SpA et al., Supreme Court of Cassation of Italy, Case No. no. 23893, 24 November 2015.中,意大利商人向伊拉克政府销售军用直升机,双方约定实体合同准据法为法国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660 号和第 661 号决议对伊拉克实施武器禁运,欧盟为实施联合国制裁也颁布了相应的制裁条例。鉴于制裁已经使得自身缺乏履约能力,意大利商人向意大利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终止合同。对此,意大利最高法院认为,联合国和欧盟的制裁措施属于意大利法律体系中的公共政策,可以优先于当事人选择的法国法得到适用。当然,制裁法在个案中是否具有适用的利益,还需结合制裁法的规制利益进行判断。联合国安理会第 660 号和第 661 号决议出台的目的在于禁止伊拉克获得战备补充、削弱其侵略科威特的能力,对于案涉军用直升机销售合同显然具有适用的政府利益。与之相反,如果案涉争议不属于制裁法的适用范围,制裁法便无法得到适用。例如,在SA T. v. Société N.案(6)SA T. v. Société N., Court d’appel, Paris, 3 June 2020.中,法国公司和伊朗公司签订了一份履行地为德黑兰的天然气储存合同,双方约定合同准据法为伊朗法,法国巴黎为仲裁地。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373号决议制裁伊朗进行核和军备活动,通过1747号决议对伊朗实施常规军备禁运,通过1803号决议制裁伊朗核活动所获得的金融资助,欧盟也据此出台了相关法律。获悉此消息后,法国公司通过仲裁程序寻求解除合同,仲裁庭则根据伊朗法认为合同未达到法定解除条件,法国公司欲解除合同需向伊朗公司支付项目解除费用。仲裁程序结束后,法国公司在法国巴黎启动的撤裁程序中主张:“联合国和欧盟的制裁措施属于法国法律体系中的公共政策,可以优先于当事人选择的伊朗法得到适用。”针对此项异议,欲探明仲裁地的制裁措施能否适用于案涉天然气储存合同,还需结合制裁法背后的政府利益进行判断。1737号决议仅对规制核和军备活动具有政府利益,没有扩大到天然气产业。1747号决议的限制对象为常规军备,也不包括天然气储存。1803号决议则关注于金融资助核活动的行为,同样不涉及天然气领域。由此可见,仲裁地实施的制裁措施,在案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均没有规制利益,无需得到适用,事后也不能成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三)“第三国”制裁法的适用及其限制
相较于准据法和法院地/仲裁地的制裁法, “第三国”的制裁法与案涉争议在形式上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密切。 如需适用,往往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政府利益”。 在“政府利益分析说”的基础上, 《罗马公约》和《罗马I》从目的、 性质和适用效果三个方面设置了一系列条件, 将可供适用的“第三国”制裁法称为优先性强制性规则。 据此标准, “第三国”制裁法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制裁法是实现合法目的的合理手段; 二是制裁法实施地与合同纠纷存在密切联系; 三是仲裁庭适用制裁法利大于弊[19]207-238。
第一,“第三国”制裁法的适用是实现合法目的的合理手段。《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和《罗马I》第9条第3款规定,在适用优先性强制性规则之前,须考虑规则的目的。对于“第三国”的制裁法,仲裁庭应该系统审查该措施的实施目的是否合法,以及为了实现该目的是否有必要实施该措施。就制裁法的实施目的而言,仲裁庭应该分别考察公开目的和隐藏目的,并从国际层面分析相关动机是否可以接受。例如,美国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但该制裁措施受到包括联合国大会决议(7)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8/8, 29 October 2013.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故该法的公开目的和隐藏目的均不具有合法性。就制裁法的实施手段而言,法院和仲裁庭应该对手段和目的的相称性进行考虑。也就是说,制裁法实施地必须对可预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行计算,确保制裁收益大于制裁成本。一般而言,综合性的制裁法可能对平民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并可能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一般不会被适用。而针对特定个人或实体的特殊性制裁法,例如旨在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武器禁运或贸易限制,其背后具有重大且迫切的政府利益,更有可能获得认可[20]160-198。
第二,制裁法实施地与合同纠纷存在密切联系。《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适用优先性强制性规则时,该规则的实施地与案涉争议之间须存在密切联系。遗憾的是,《罗马公约》本身并未对联系的性质和强度提供指导,这无疑赋予了裁判者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仲裁员可能遇到的制裁法一般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实体合同在制裁法的实施地履行,或者实体合同的履行过程与制裁法的实施地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这种情况一般也构成密切联系,因为合同当事人有义务遵守合同履行地的强制性规则。例如,在日本出口方与黎巴嫩进口方之间的合同纠纷中,虽然黎巴嫩法律不是实体合同准据法,但考虑到案涉合同在黎巴嫩履行,仲裁庭认为需要考虑黎巴嫩的进口限制(8)ICC Award n. 1859, 1973.。二是制裁法的实施地是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居所地、营业地或者国籍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密切联系,但仲裁庭需要针对个案进行谨慎评估。例如,在荷兰买方和奥地利卖方之间的销售合同纠纷中,仲裁庭便拒绝适用奥利地的强制性措施。案涉标的物产自荷兰,合同履行地位于德国,所使用的货币为德国马克,支付方式为通过德国银行付款。综合这些情况,尽管本案的卖方为奥地利人,但仲裁庭仍然认为该销售合同和奥地利之间不存在密切联系(9)Amsterdam Grain Trade Association, Award of 11 January 1982.。三是其他情况。对于制裁法实施地而言,如果缔约双方均不是该地的国民或居民(国籍标准),也不在该地开展业务(领土标准),双方的合同活动也不对该地产生影响(效果标准),更不会威胁该地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重要利益(保护标准),则案涉争议与该地不可能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Compagnie Européenne des Pétroles SA v. Sensor Nederland BV案(10)Compagnie Européenne des Pétroles SA v. Sensor Nederland BV, Arrondissementsrechtbank, The Hague, 17 September 1982.中,Sensor Nederland BV(下称荷兰公司)向Compagnie Européenne des Pétroles SA(下称法国公司) 交付地震设备,用于建造位于苏联的管道设施。其中,荷兰公司母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由于美国禁止向苏联出口设备,荷兰公司便拒绝履行合同。法院认为,荷兰公司股东的股东系美国公司的事实,与案涉合同联系过弱,不足以证明美国的制裁法与案涉争议存在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在制裁法实施地与案涉合同联系不紧密的情况下,制裁法的适用不仅没有重大的政府利益,反而可能会阻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往往不会得到认可[21]。
第三,仲裁庭适用制裁法利大于弊。《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和《罗马I》第9条第3款规定,裁判者须对优先性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后果进行评估,确保其实施能够产生社会效益。需要综合考量的利益包括当事人的利益、受到裁判文书影响的其他个人或实体的利益、制裁法实施地的利益和目标国的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例如,在Fruehauf Corporation v. Massardy案(11)Fruehauf Corporation v. Massardy, Court d’appel, Paris, 22 May 1965.中,两家法国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将60辆货车销售至中国。其中,法国卖方的大股东系美国董事,小股东系法国董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美国发布对华制裁禁令,美国政府要求“美国董事”不得履行合同,否则便对“美国董事”进行处罚。“法国董事”不愿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便对“美国董事”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如果法国卖方按照美国制裁措施不予履约,法国卖方将失去法国买方这一重要的客户(约占法国卖方年出口总额的40%),并将承担巨额损害赔偿,还将直接导致约600名法国工人失业。如果法国卖方继续履约,“美国董事”需缴纳的罚金要远远低于法国卖方的损失,而且“美国董事”被美国禁令处罚也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可能。考虑到公司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董事”的利益,法院决定,不应执行美国制裁法。由此可见,在适用制裁法所获得的政府利益间接而微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直接而重大的情况下,制裁法也没有适用的必要[22]。
三、“政府利益分析说”语境下制裁法的适用冲突及其消解
如果准据法所在地、法院地/仲裁地以及“第三国”之间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制裁法和反制裁法,就形成了制裁法的适用冲突问题。面对此种高度复杂化的情况,裁判者无须迷茫,可以根据柯里在“政府利益分析说”中提出的观点,将法律冲突区分为“无利益的案件”“虚假冲突”和“真实冲突”三种类型,通过衡量制裁法背后的政府利益对其进行区分处理。
所谓“无利益的案件”,是指任一司法管辖区的制裁法对于合同法律适用都没有政府利益的案件。在此情况下,裁判者无须考虑制裁法的适用,只需处理私法适用问题。在国际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法也无法确定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的,可以适用法院地法。在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法也无法确定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的,仲裁庭可以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法律[23]。
所谓“虚假冲突”,是指虽然合同涉及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制裁法,但实际上仅有一地的制裁法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政府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应适用具有规制利益的司法管辖区的制裁法。例如,在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案(12)See Hartford Fire Ins. Co. v. Cal., 509 U.S. 764 (U.S. June 28, 1993).中,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在美国保险市场因涉嫌违反《谢尔曼法》被加利福尼亚州提起指控,该英国保险公司认为其做法完全符合英国保险监管制度的规定,故美国法院应根据礼让原则适用英国保险监管制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分析两国的保险监管制度后发现,美国《谢尔曼法》只是在某些方面更为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法律之间存在真实冲突,毕竟英国公司仍然可以在不违反英国保险监管制度的前提下遵守《谢尔曼法》。考虑到本案仅有《谢尔曼法》具有适用的利益,故其能够进行适用。虽然本案并非合同法律适用案件,但其对制裁法的适用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所谓“真实冲突”,是指两个以上司法管辖区的制裁法和反制裁法都具有适用的利益,此时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制裁法的冲突问题。面对此种情况,裁判者必须对制裁法背后的政府利益作出更谨慎、更适当的解释,力求避免法律冲突的发生。如果裁判者经过反复确认,仍发现制裁法背后合理的政府利益存在冲突,在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之前,应该适用法院地法或者仲裁地法,毕竟保证裁判融入当地的法律体系才是裁判生效的基本条件。随着制裁法适用冲突的增多,立法机关需要对“遵从何种政府利益”作出明确指示,毕竟衡量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政府利益已经超越了裁判者的职责,属于一国对外关系法的范畴[24]。
四、制裁法引入合同法律适用领域的中国应对
随着制裁法引入合同法律适用领域的实践越来越多,中国如果仍然坚持公法效力属地主义的传统,并不利于企业在域外抵御他国制裁法所造成的冲击,可能导致国家利益持续受损。更好的做法,是直面制裁法域外适用所带来的挑战,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重构中国的国际私法体系,据此推进中国反制裁法的域外适用。除此之外,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利益分析说”的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规避制裁法所带来的风险。
(一)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推进反制裁法的域外适用
近年来,为了反击国际上日益泛滥的制裁法,中国颁布了包括2021年《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此类反制裁法的特点是从“法律关系本座说”出发,严守国际私法中的“公法禁忌”原则,通过惩罚遵守外国制裁法的本国公民和实体来达到阻断外国法律的效果。然而,在传统理论语境下,反制裁法无法发生域外效力,不仅很难阻止外国制裁法的域外适用,反而会加剧本国公民和实体同时违反两国公法规范的风险。从实际效果上看,中国目前的反制裁法体系所发挥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25]。
为了真正在域外阻断外国制裁法的适用,反制裁法需要借助于国际私法体系进行域外适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根据“政府利益分析说”对国际私法进行重构。也就是说,国际私法不再只是根据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形式化选法的法律,而是可以根据法律背后的“政府利益”或“规制利益”进行实质性选法的法律。在当前国际私法所提供的形式化选法框架下,司法者有权根据政府利益分析对冲突法规范进行个案检验。如果形式化的选法结果与政府利益分析的结果保持一致,自然可予以适用。如果形式化的选法结果与政府利益分析的结果发生冲突时,应以政府利益分析的结果为准。正是由于法律背后的“政府利益”分析占据了优先性地位,国际私法在性质上应随“政府利益”这一建构基础被定性为私法的公法化和社会化。随着国际私法性质的改变,具有公法属性的反制裁法也属于国际私法的适用范畴,并可借助冲突法规范产生域外效力。与此同时,在欧美国家进行的涉经济制裁类案件中,中国当事人应该积极运用《罗马I》和美国法中蕴含“政府利益分析说”的裁判规则,结合具体情况,论证中国反制裁法背后的政府利益比境外制裁法背后的政府利益更为重要[26]。
(二)谨慎选择法院地/仲裁地以避免制裁法的适用冲突
根据“政府利益分析说”,可能适用的制裁法包括准据法、法院地/仲裁地法以及“第三国”法,三者之间的适用冲突可被区分为“无利益的案件”“虚假冲突”和“真实冲突”。仅有在“真实冲突”的情况下,裁判者才需要通过谨慎解释的方式力求避免法律背后合理的政府利益存在冲突,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只能适用法院地或者仲裁地法,毕竟裁判本身不违反当地的法律体系是维持裁判效力的第一要务。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分析说”倾向于通过法院地/仲裁地法解决制裁法的适用冲突,故法院地和仲裁地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避免制裁法的适用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慎重选择法院地/仲裁地,尽可能避免其与准据法所在地存在真实的法律冲突。如果真实的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则当事人可以选择更为中立的法院地/仲裁地,以确保法院能够对不同国家的制裁法和反制裁法进行客观中立的利益分析,在最大程度上阻断制裁法的适用,尽可能实现案涉合同的效力[27]。
(三)预先置入免责条款以防范制裁风险
在“政府利益分析说”语境下,外国制裁法可以适用于合同的效力认定。在此情况下,为了从“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中解脱,交易双方可以作出合规承诺,将制裁法的适用约定为当事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免责事由[28]。
在国际商事习惯中,预先置入免责条款的做法也被广泛推荐。例如,国际商会的一份指南(13)国际商会(ICC)官方文件:Guidance Paper on the Issue of Sanctions Clauses in Trade Finance-Related Instruments Subject to ICC Rules,Document No.470/1238.中便列举了与制裁相关的免责条款,其具体内容如下:“银行遵守美国、欧盟和联合国所颁布的制裁法,对于制裁名单上所列的主体,银行不承担信用证付款义务。”在实践中,此类条款的效力也得到了广泛承认。循此推断,在“政府利益分析说”适用的条件下,如果制裁法的适用无法避免,企业预先在合同中置入免责条款,便可在遵守制裁的情况下摆脱违约风险[29]。
五、结 论
巴托鲁斯所开宗的法则区别说,要求裁判者根据法律本身的适用空间与性质进行法律适用,此时国际私法和民法的建构基础存在明显区别,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两层皮的关系。在此之后,国际私法的建构基础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萨维尼将“法律关系”作为选法依据,其目的是令国际私法和民法分享相同的建构基础。在该理论语境下,国际私法属于民法的范畴,能够很好地适应以低技术产品为主要交易对象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毕竟此时商品易于生产而难以发生影响政府利益的供应链危机。为了维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合同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公法非必要不得适用于国际贸易。但是,随着交易对象转向高技术产品,在芯片等关键领域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人为的供需失衡可能引发危及政府利益的供应链危机,国家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意图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公法规范。此时,如果国际私法依然固守“法律关系本座说”的传统,拒绝将公法引入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显然无法应对这一全新的问题。因此,借鉴柯里“政府利益分析说”所提出的革命性理念,国际私法的建构基础由传统上的“法律关系”转变为“政府利益”,便可以具有独立于民法的发展逻辑,且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制裁法和反制裁法都可以对合同法律适用产生影响,裁判者需要权衡法律背后的“政府利益”作出最合适的判断。结合“政府利益分析说”的特点,当事人需要慎重选择仲裁地和法院地,通过企业合规和免责条款提前规避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