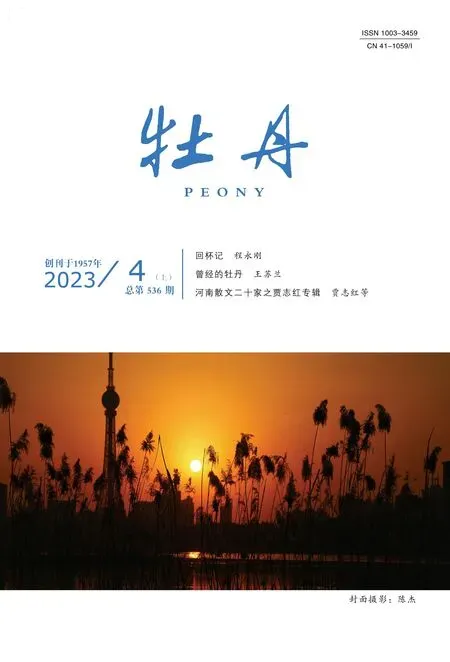证书丢了
2023-02-20王刚
王 刚
一
这一次,学校有三个高级指标,却有四个老师符合要求:我,老张,黄婷婷,龙伟。换句话说,我们四人得展开PK,干掉一位老师。为了顺利出线,我花钱发表了论文,升级了普通话证,评了市级优秀教师,完成了规定的继续教育,通过了计算机考试……总之,彻底扫除了通往高级的地雷。教育局下发文件后,我抓紧时间准备评聘材料,包括各种表格、计划、总结、家访记录、辅导记录、作业批改记录、述职报告等,脑壳都被搞大了。
简单点儿说吧,我这一次拼尽全力,只为拿下梦寐以求的高级。老师嘛,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只能靠职称吃饭,职称上去了,工资才能上去,养家糊口才有着落。不过,评职称可不像爬梯子,说上去就能上去。为了保证不被干掉,我绞尽脑汁,深挖文件精神,按照材料目录,将申报资料装订成册,可谓文图并茂,要内容有内容,要颜值有颜值。
下午四点,我忙完手中的活儿,打算去一趟学校,一是打印材料,二是复印证书。想到这个艰巨的工程终于即将完工,我顿觉一身轻松,吹着口哨向学校走去。保卫胡师傅拿着对讲机站在校门边,露出满嘴漆黑的龅牙,问我大周末的不休息,来学校干吗?我心情好,甩一支烟给他,挥挥手说,我要评中高,来学校搞资料。胡师傅满脸堆笑,按了一下钥匙,打开伸缩门,让我进去。我吹响口哨,在他惊异的目光中,大步向教学楼走去。可是,当我爬上教学楼,走进办公室,拉开抽屉时,不由愣住了。
抽屉里空空如也!
证书呢?我的证书呢?长腿跑了?插翅飞了?我有点儿发蒙,大脑一片混沌。长期以来,我的毕业证、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聘任证、获奖证、课时证等一直放在抽屉里,就像宝剑躺在剑鞘里一样。可现在,满满一袋证书,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定了定神,弯腰查看桌子下面,水洗一般干净。翻检桌上书本,什么也没发现。见鬼了?早知如此,应该把证书带回家,可谁知道会这样?学校三天两头让填表,为了省麻烦,我把证书放在办公室。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几乎所有老师都是如此。谁能想到呢,这个古怪的日子,我的证书竟然不翼而飞。
直起身子,扫视远远近近横七竖八的办公桌。学校办公条件差,十几人在一个办公室,显得拥挤窄逼。桌子上胡乱放着资料书,作业本,试卷。坐在我对面的,是满脸络腮胡的老张。老张教历史,上课用方言,土得掉渣。经常穿一套皱巴巴的西服,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花白如雪,像个老学究。学生们当面称他张老师,暗地里叫他古董。老张的办公桌与我的办公桌紧挨在一起,桌上摆满小山一般的试卷,还有一些大部头。我扒拉了半天,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拉了拉抽屉,纹丝不动;看了看,原来上了锁。
动手检查黄婷婷的桌子时,我迟疑了一下。这女人心细,如果动她的东西,她肯定会察觉。我仿佛看见她瞪着金鱼眼,皱着眉头,嘴唇翕动,吐出一串叽里呱啦的声音。黄婷婷是全校最洋气的英语老师,大波浪头,眉毛细长,嘴唇像花朵。这女人仗着有几分姿色,总以为自己是块儿肥肉,男人全是饿狗。我翻了半天,左看上看下看右看,没发现什么。
龙伟教数学,人高马大,喜欢健身,像个篮球运动员。这小子不太讲究,办公桌摆满书籍资料,还有两桶方便面,几个一次性杯子。我费了差不多半小时,才把桌上的东西清理完毕,却什么也没发现。我有点儿累,靠着桌子,看着紧锁的抽屉发呆,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证书会不会锁在抽屉里?
我真想找把扳手,把抽屉一一撬开。不过,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管怎样说,我还得在这里待下去,最好别干这种惹众怒的事情。
二
天色暗下来,窗棂上仿佛爬满了成群结队的乌鸦。我累了,叹了口气,坐在椅子上,茫然地仰起头,看着灰黑的天花板。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拉开门,原来是胡师傅。他拎着电棍,盯着我说,王老师,你在干吗?
我没好气地说,搞资料,你也要管?
胡师傅咧开嘴,露出满嘴龅牙,歪着身子挤进来,啪地按下开关,眼前立刻光明一片。他瞟了瞟办公室,用警棍扒拉着乱糟糟的书本,哑着嗓子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他的龅牙,说,我的证书丢了。
你不能这样干啊,如果上面追查下来,我该如何交差?
我的证书丢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胡师傅咧嘴笑起来,王老师,别生气,生气有什么用?
我一下子泄了气。不错,生气有什么用?我看着他的黑制服,手里的黑警棍,发亮的黑龅牙,油亮的光额头,笑笑说,胡师傅,我的证书丢了,请你帮个忙。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又不是警察。
放心吧,我只是想看看监控录像。
胡师傅松了口气,走吧,去监控室。
胡师傅打开监控视频,叫我自己看。真倒霉,办公室没装摄像头。当初,按学校领导的要求,所有办公室全装上了摄像头。这事引起了老师们的激烈反应,认为这种做法太过分,不把老师当人。想想也是,只要走进办公室,背脊上总有一只眼睛盯着,那滋味真不好受。由于反对的老师太多,学校领导做出让步,撤掉了办公室里的摄像头。不过,走廊过道装了摄像头,只要偷证书的人从办公室走出来,就会被摄像头拍下来。
胡师傅扔下我,出门巡逻去了。我坐在椅子上,用鼠标拖动画面,寻找该死的犯罪嫌疑人。我盯着大门,看高矮胖瘦的老师们陆续走出,再走过长长的过道。平时倒不觉得,一旦通过视频观看他们,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老张把擦了鼻涕的卫生纸揉成一团,偷偷扔到地上;黄婷婷的裙子后摆提了起来,露出半边屁股;龙伟跟在一个女老师后面,盯着她扭来扭去的腰肢;某位丰硕的女老师边走边理衣服,乳房忽隐忽现。
手机响了几次,是谢芬打来的,我懒得理睬,直接挂了电话。
看了半天,眼睛发酸作痛,画面逐渐模糊。我仰面躺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使劲吸了几口。胡师傅走进来,冲我笑了笑,又露出门板一样的龅牙。
我丢了一支烟给他,他接过烟说,找到了吗?
找个铲铲。我摘下烟头,丢在地上。
我扔下胡师傅,起身走出监控室。城市灯火辉煌,看看手机,竟然已近十点。我把手揣进裤兜,缩着脖子往前走,只觉天地一片茫然。证书丢了,高级咋办?这不是要人命吗?是谁暗里对我捅刀子?我拿出手机,打开教师微信群,往里面扔了一条信息:我的证书丢了,谁看见?若有知情者,请及时跟我联系。
等了几分钟,没有人吭声。我又砸下一条信息:到底是谁拿了我的证书?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走到派出所大门外。看看微信,没人放一个屁。我打开手机相机,对着派出所拍了几张照片,将照片丢进群里,补上一条信息:看来,我只能报警了。
仅仅过了一分钟,手机铃声大作。按下接听键,传来了马校长的怒吼声,你疯了?你想毁了学校?我告诉你,不要乱来,赶快给我滚回来。
我愣了愣,挂掉电话,在心中骂了他一句。
三
谢芬歪在沙发里,见了我不理不睬。虎子坐在地板上,抱着一辆玩具车,扯着嗓子嚎。我颇感诧异,这是怎么回事?谢芬平时对虎子可疼了,含着怕化了,捧着怕飞了。可现在,虎子哭得那么凶,她却置若罔闻。我抱起虎子说,儿子,乖,别哭?
谢芬瞪了我一眼,一句话也不说。
怎么?臭小子闯祸了?我冲她笑了笑。
谢芬哼了一声,扭过头去,盯着地板。
饿坏了,有吃的吗?我讪笑说。
想吃?自己弄。
你怎么回事?吃错药了?
我就是吃错药了,你要咋的?
我想了想,忍住了。记得某哲学家说过,一个女人等于500只鸭子,我可不想跟500只鸭子干仗。再说呢,一想起那些证书,心如猫抓一般,哪有吵架的兴致?虎子挣扎着,哼哼唧唧的,我拍拍他的屁股,抱着他跳来跳去。不一会儿,他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我把他抱进卧室,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走回客厅。谢芬仍保持着固定的姿势,脸色乌云翻滚。
别生气了,有话好好说。我在她的身边坐下,搂住她说。
她甩开我的手,眼睛瞪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我避开她的眼光,说,你到底怎么了?
她哼了一声,你咋不接电话?耳朵聋了?
我去学校搞申报材料,你又不是不知道?
搞材料?怕是搞女人吧。
别吵了,我的证书丢了。我提高声音说。
什么?证书丢了?她有点儿转不过弯来。
没有证书,我没办法评高级。
不能评高级?那你快找啊。谢芬失声喊起来。
到处都找过了,连影子也没看见。我低下头说。
谢芬一下子站起来,看着我说,你怎么搞的?是不是忘记放哪儿了?是不是被人偷了?谁会拿你的证书?你是不是得罪了哪个?证书没脚没翅膀,怎么会突然飞了?
我能说什么呢?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时间不早了,睡吧。
躺在床上,满脑子是证书。谢芬已经进入梦乡,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月光从窗户洒进来,斑斑点点,飘忽不定。谢芬说得对,证书没脚没翅膀,怎么会飞了?一定是谁故意整我。老张、黄婷婷、龙伟、小马,小王……谁是犯罪嫌疑人呢?谁都像,谁都不像。我是威严的法官,用各种问题盘问他们,试图把真正的盗贼挖出来。这些家伙很狡猾,谁也不肯亮出底牌。我跟他们吵了大半夜,搞得头昏脑涨,却没挖出一点儿有用的线索。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全消失了。我看见自己站起来,踩着铺满月光的大街,走到了学校门口。胡师傅提着警棍,笔直地站在值班室外,如一尊泥菩萨。我走进去,他仿佛没看见我,连招呼也没打。我懒得管他,径直飘进教学楼,飘进办公室。
风拍打窗户,呜呜直叫。办公室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我捡起铁棍,走到一张桌子前,三下两下撬开了抽屉。我赫然看见,抽屉里放着一叠鲜红夺目的证书。我赶紧伸出手,要把证书抓住。证书却动起来,噼啪作响,仿佛鸟儿拍打翅膀。一阵冷风破窗而入,嗖嗖有声。一张张证书随风起舞,长出了嘴巴,尖牙,翅膀,变成一只只大鸟,呼啦啦张开翅膀,撞开窗户,飞向辽阔的天空,眨眼间已踪影全无。
我一下子醒了,听见心脏扑通乱跳。
四
穿衣,漱口,洗脸,刮胡子,匆匆出门。周一要搞升旗仪式,七点前必须赶到,晚一秒都不行。学校安排了值班人员打考勤,晚到者扣分扣钱,作为推优评模的重要依据,与目标考核奖挂钩。老师们如装了发条,哪怕睡得比狗晚,也要起得比鸡早。
天空灰暗,飘着毛毛细雨。我冲出小区大门,看看手机,已经六点五十。我站在路边,使劲招手,打算拦一辆的士。附近站着几个面目模糊的人,伸长手臂,伸长脖子,像一只只鹅。几辆的士爬过来,我晚了一步,被抢走了。没办法,我只得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说我遇到点儿事,晚一点儿才能到校。主任说,算事假,尽快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抢到一辆的士。赶往校门口,耳边传来高亢的国歌声。灰色的天幕下,学生们齐整整地站在烟雨中,像一片湿淋淋的树。胡师傅提着电棍,带着几个保安站在伸缩门外,拦截迟到的学生。我快步走过去,悄声说,胡师傅,请开一下门。
胡师傅看了看,低声说,王老师,你怎么才来?刚才马校找你,脸色很不好呢。我的心咯噔一下,问,找我干吗?胡师傅说,不知道。我看了一眼黑压压的学生,说,胡师傅,让我进去。胡师傅低声说,王老师,以后来早点,我们挺为难的。
胡师傅按开门,我赶紧溜进去,跑到教师队伍的尾巴上。
升旗结束,我挤开乱哄哄的人群,快步往办公室赶。我恍惚觉得,只要像往常一样拉开抽屉,就能看见那些红红绿绿的证书。我第一个冲进办公室,拉开了抽屉。我失望了,奇迹并未出现,抽屉空空如也。
老师们陆续走进来。我像一根木头杵在桌边,看着一览无遗的抽屉。几个老师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低头收拾办公桌。老张走到他的桌边,敲了敲桌子,对我说,兄弟,怎么了?魂魄丢了?我吓了一跳,把抽屉推回去,连声说,没什么,没什么。老张问,证书丢了?我说是啊,丢了。老张笑笑,会不会把证书落在其他地方了?我说,怎么可能?证书一直放在抽屉里,从来没有动过。老张说,你的意思,这办公室有贼?
其他老师纷纷凑过来,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龙伟撇撇嘴,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谁会干这种事?龙伟的话引起了大家的附和,他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有人提醒我请个假,回家找一找。有人说我睡眠不好,会不会患了神经衰弱症。有个小女生甚至提到了老年痴呆症,说这种病很可怕,患这种病的人,会忘记所有的事情。为了验证她的观点,她跟我做了一个实验,我说说最近一个周做了什么事,让我一一列举出来。我努力想了又想,怎么也说不清楚。小女生笑了,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好去医院查一查。我拍桌子吼道,胡说,瞎扯,乱弹琴。
闹哄哄的声音沉寂下去。老师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诡异而尴尬。有的缩回座位,装模作样做事。有的打着哈哈,说不扯了不扯了,上课去。有的转过身,盯着手机,聚精会神玩游戏。我努力笑了笑,大声说,看来,我只得报警了。
此话一出,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反应。有的问出多少酬金,有的建议成立一个专案组,还有的搬出福尔摩斯、柯南、狄仁杰。黄婷婷抱着手,哼了一声说,你们不累啊,为这无聊的事情扯上半天?老张咳了几声,说,黄老师说得对,该干啥干啥。说着,拍拍我的肩膀,兄弟,几张破纸,谁会感兴趣?我愤怒地看着他,大声说,那不是破纸,是证书。
老张说,证书不就是废纸吗?别人拿去干什么?不能吃,也不能用。
有个男教师说,话不能这样说,证书对别人没用,但对王老师有用啊。
对啊对啊,王老师,你仔细想想,跟谁有仇?有人附和。
黄婷婷冷笑一声,杀父之仇?还是夺妻之恨?
上课铃声响了,大家如释重负,谈笑着走出办公室。
五
上了两节课,我拖着沙袋似的身体回到办公室,手机催命般叫起来。
几分钟后,我坐在了马校的面前。马校四十出头,比我小几岁,可他早就是高级了。他拿着一支铅笔,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像一尊弥勒佛。我缩了缩肩,笑着问,马校,你找我有事?马校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轻轻放下,看着我说,证书丢了?我说,丢了。马校说,听说你要报警?我竖起身子说,没,没这回事。马校哼了一声,是吗?可有人对我说,你要报警?我赶紧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马校笑起来,是啊,我想王老师也不会这么幼稚啊,学校是文明的地方,老师们都是有素质的,谁会拿你的证书呢?
我抬头看了看校长的笑脸,竟然无话可说。马校走到我的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你是老教师了,遇事要多想想,这样吧,抓紧时间找找。我答应一声,退出了办公室。
走过狭长的楼道,转角处冒出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同一办公室的小王。小王是90 后,下巴光溜溜的,像个高中生。我说,小王,有事吗?小王左看右看,低声说,王老师,你想过没有,你的证书丢了,对谁最有利?我愣了愣,问,什么意思?小王说,对谁最有利,谁就最有可能拿走证书。说完,不等我回答,忽然转身走了。
大老远,看见龙伟抱着手,站在办公室门外。我走过去,他把手指放到嘴唇边,嘘了一声,走,跟我走。我说,干啥?他以一种不容反驳的口气说,走,去足球场。
学生们正在上课,足球场上空无一人,显得格外空旷。龙伟不回头,甩着手往前走。刚下过雨,山峦格外碧青,就连足球场上的毯子,也格外青葱,仿佛是真的草地。
喂,可以了吧。我对着他的后脑勺喊道。
龙伟不说话,继续往前走,我只得跟着走。龙伟走到足球门边,停住脚步,抱着手,靠在门框上,阴沉沉地说,你怀疑我拿了你的证书?
我愣了一下,说,没,怎么会?
可是,你翻过我的桌子。龙伟盯住我说。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找到证书。
你翻过我的桌子,你这是怀疑我。
别这样,评中高的不只你一个。
龙伟笑笑,明人不做暗事,我如果对你不爽,根本不用偷偷摸摸,我会跟你真刀真枪干一仗。我跟你说了这些,如果你还怀疑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龙伟抬起手,指着球场说,来这儿,单挑。
别这样,何必呢?我们是同事,是兄弟。
龙伟掏出烟,丢给我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我们坐在球场上,使劲拉着烟,头顶飘起两缕烟雾。龙伟抽完一支烟,伸手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哥们儿,告诉你一件事吧,你的证书丢失的前一天,黄婷婷是最后离开办公室的。
我悚然一惊,说,你的意思,黄婷婷拿了证书?
龙伟笑笑,我可没这样说,你好好想一想。
可是,她为什么要拿我的证书?
这还不简单,为了干掉你啊。你可能不知道吧,黄婷婷没有省级优秀,也没有市级优秀,她能拿得出手的,只是一张优质课获奖证书,比你的条件差远了。
丁零零,耳边传来清脆的铃声。
龙伟起身,拍拍屁股说,走吧。
我看了看天,说,走吧。
六
黄婷婷穿着珊瑚红连衣裙,站在学校门口法国梧桐下,大波浪头发随风拂动。胡师傅站在伸缩门外,张着嘴看她,露出漆黑的龅牙,嘴角挂着两线涎水。我低下头,加快步子往前走。这时,耳边响起一个声音,王老师,王老师。
我抬起头,看见黄婷婷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王老师,一起走走。黄婷婷说。
黄老师,有事吗?我有点儿蒙,看了她一眼。
没什么事,找个地方吃午饭,聊一聊嘛。
黄婷婷与我挨得近,时不时碰一下,让我心跳加速。她身上散发出含混的香水味,一阵阵往鼻子里钻。我头脑发蒙,觉得手不是手,脚不是脚,只能机械地跟着走。五六分钟后,我们拐进一条清净的巷子。黄婷婷指着一家馆子说,就这儿了。
我点点头,跟着她走进去。
黄婷婷要了个小包间,点了辣子鸡火锅,两瓶生啤。包间很小,我感觉透不过气来。黄婷婷撬开啤酒,笑着说,当了这么多年的同事,还是第一次聚呢。我点点头,是啊是啊,大家都忙。她笑笑,确实忙,不过鲁迅说过,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会有的,以后要多交流啊。我没想到,她竟然知道鲁迅,使劲点着头说,是啊,是啊。她把一瓶啤酒递给我,喝一点儿。我摆摆手,不行不行,下午还要上班。
男人不能说不行哦,怕什么?她把啤酒递给我,笑着说。
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聊天。确切点儿说,主要是黄婷婷说,我听。黄婷婷口才不错,甭管什么事情,只要从她嘴里说出来,就会变得活色生香。我也想表现表现,但舌头不听使唤,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说是啊是啊,对啊对啊。
没多久,我们各自吹干了酒瓶。黄婷婷说,再来一瓶?
我大着舌头说,好啊,好啊好啊。
吃着喝着聊着,不知不觉中,上班时间快到了。在这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几乎颠覆我了对黄婷婷的看法。以前总觉得她高冷,尖酸,刻薄。现在看来,她完全是另一个人,能说会侃,风情万种。也许,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真该多聚多聊。
黄婷婷举起酒瓶,说再敬我一杯。碰了杯,干了酒,她好看的眼睛看着我,压低声音说,我叫你王哥,不介意吧?我赶紧说,叫王哥好,比较亲切。黄婷婷说,王哥,我把你叫出来,是想为你提供情报呢。我望了望她,什么情报?
你保证,不要对任何人提这件事。她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
我保证,谁乱说谁他不是人。我举起手发誓。
你的证书,可能是老张拿的。她看了看四周。
真的吗?你看见了?他为什么这样干?
我没看见,但我认为是老张拿的。黄婷婷好看的眼睛看着我,压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吗?按教育局的文件,普通话等级是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条件。
不错,是重要条件。
老张的普通话级别低,只是三级甲等。
可是,他资格老啊。
资格老有什么用?评职称主要看硬件。
可是,他为什么拿我的?
为了保险起见,提前清除对手。
想起老张油腻的老脸,还有土得掉渣的方言,我有点儿恍惚。
吃了饭,黄婷婷不由分说,抢着把账结了。
七
刚进家门,老张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说好久没聚了,叫我出去吃烙锅。我不想去,上了一天班,只想睡一觉。老张不依不饶,说他在“老城烙锅店”,叫我赶紧去。我说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帮忙照顾孩子。老张笑起来,叫我别扯犊子,赶紧过去。
包房里除了老张,还有四个人,一男三女。那男的以前见过,是老张的堂弟,开装修公司的。几个女的都很年轻,就像同一个模子出来的,细眉毛,红嘴巴,尖下巴。
老张要了两件啤酒,一人先发一瓶,提议先吹一瓶。众人齐声叫好,纷纷把酒瓶举到空中。我只得跟着举瓶,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不大一会儿,他们全吹完了,我还剩下大半瓶。真看不出来,那几个二十出头的小女生,喝酒如喝白开水。他们丢下酒瓶,催我赶紧完成任务。老张拍了拍一个女生的肩膀,说,小李,帮你王哥喝一杯。
小李把我的酒瓶抢过去,倒了满满一杯,嫣然一笑,王哥,我敬你。说完,举杯,张嘴,一饮而尽。我仰起头,把酒瓶塞进嘴巴,咕咚咕咚往里灌。由于喝得太猛,我被啤酒呛着了,发出吭哧吭哧的咳嗽,引起了一阵快活的笑声。
吹完第一瓶,老张提议大家自由发挥,爱咋搞就咋搞。大家拍掌叫好,划拳,碰杯,翻牌,人声鼎沸。起初,我还有点儿拘束,试图置身事外。不一会儿,禁不住几个小女生的轮番轰炸,身不由己陷入了混战。后来,我索性放开了,来者不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喝着喝着,头就变大了。放眼望去,人影晃动,墙壁晃动,楼顶也在晃动。
老张端着一杯酒,跟我碰了一下,大声说,兄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美酒美女,不醉不归。我大着舌头说,好,好,不醉不归。老张挥挥手,对小李说,小李啊,陪你王哥整几杯。小李坐到我的身边,举起酒瓶,笑盈盈地说,王哥,我敬你。
看着小李晃来晃去的脸,我举起酒瓶吼道,喝,喝,喝。
小李说了声干,我也吼了声干,两酒瓶碰在一起,发出垂死的惨叫。
醉意朦胧中,老张把我扶起来,走出了烙锅店。一阵凉风吹来,我感到肚腹里翻江倒海,赶紧丢开老张,跌跌撞撞地跑到一株树下,张开嘴巴吐起来。
吐过后,老张拿来一瓶矿泉水,叫我漱口。我漱了口,将矿泉水瓶扔到地上,连踢几脚,竟然没有踢中。老张把我拖到一幢高楼前,我们肩并肩坐在台阶上。天空忽高忽低,像一口摇晃的灰黄锅盖。路灯也跟着摇来晃去,如一只只萤火虫。
兄弟,你醉了?能听见我说话不?老张摇了摇我。
我哼了一声,示意他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你想过没有,是谁拿了你的证书?
要是老子知道,老子不弄死他。
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说,有什么不敢说的?
那好,我怀疑,龙伟拿走了你的证书。
我仰头大笑,为什么?凭什么?
很简单,他资历浅,条件软,没有过硬的拿得出手的获奖证书,如果硬拼,他根本没机会入围,只要把你干掉,他才能顺利过关了。
我看了看老张,觉得他说得有理。长期以来,龙伟瞧不起教语文的,说教语文的有股穷酸味儿,个个都是孔乙己。我也瞧不起他,说他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原始人。曾经有几次,我们还吵过嘴。在这评职称的生死关头,他会不会先下手为强,把我直接干掉?
可是,可是,他为什么不干掉你?我想了想,问老张。
只能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如此而已。
八
丢了证书,对我的影响显然易见。最直接的结果,让我丧失了申报高级的资格。老张、黄婷婷、龙伟,三人顺利晋升。想一想吧,换作是谁,这滋味好受吗?
事实上,丢失证书不仅让我错过了高级,还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按照职称进岗文件,我本可晋升一档,但因拿不出证件,只得干瞪眼。省里下发了关于成立名师工作室的文件,一旦申报成功,将给予资金扶持。我完全符合条件,但交不出证书,只能望洋兴叹。除此之外,诸如申报省级骨干教师、优质课评委、课题研究、校际交流活动等机会,我只能靠边站。在这期间,龙伟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黄婷婷申报了省级骨干,老张成立了名师工作室。就连那些嘴上无毛的小年轻,或搞了课题,或参加优质课比赛,或涨了工资。一句话,其他老师都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只有我被晾在沙滩上,成为一条发臭的咸鱼。
不错,没了证书,我成了一条死鱼。每天走进校园,我感觉脚杆打战,心里发虚;每次走进办公室,我低着头颅,脸庞发热;每次走上讲台,我弯腰缩脖,不敢直视学生,嘴唇哆哆嗦嗦,说话颠三倒四……总之,我像个冒牌货,没有半点儿底气。有几次,马校长拦着我说,王老师,怎么搞的?你的魂丢了?你看你教的班级,成什么样子了?听了他的话,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危机感:长此以往,我难保不会丢掉饭碗?不行不行,没了证书,我就不是我,我的魂就回不来。我下定决心,哪怕上天入地,也得把证书找回来。
我沉下心来,仔细梳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现漏掉了一个关键——那些上锁的抽屉。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得想办法打开抽屉,揭开里面的秘密。
好不容易挨到周五,临到下班之际,我溜进洗手间,反锁门,蹲于坑上。十几分钟后,我走出洗手间,办公室已空无一人。门已关上,办公室只属于我一人,再也不用看脸色了。我松了口气,坐在一张椅子上,打量一个个抽屉,准备天黑就动手。
暮色渐浓,对面的山顶上升起一轮月亮,像一枚硕大的夜明珠。按我的意思,没有月亮更好,安全性更高。不过,有月亮也不错,就像有人亮起了一把手电筒。我站起来,提起大号螺丝刀,走向老张的抽屉,将螺丝刀杀进缝隙,稍一用力,吱嘎一声,抽屉就被撬开了。我拉出抽屉,空空如也,水洗一般干净。
我提着螺丝刀,走向了一个又一个抽屉,龙伟的,黄婷婷的……吱嘎,吱嘎,吱嘎……持续不断的吱嘎声中,一个个抽屉被打开。空的,空的,空的,还是空的……
我丢下螺丝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喘气。
那些被打开的抽屉,像一张张大嘴,龇牙咧嘴地对着我。
我发了一会儿呆,忽然跳起来,奔向我的办公桌,拉开了抽屉。
一叠红红绿绿的证书跃入眼帘!
我愣了一下,伸出颤抖的手,抽出一张证书,赫然看见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定了定神,又抽出一张,还是我的名字。我不敢相信,对着月光翻开了所有的证书。不错,是我的,每一张证书上,都写着我的名字,熠熠生辉,光芒四射。
我那些不翼而飞的证书,莫名其妙地飞回来了!
我长吁一口气,把证书装进资料袋,打算离开办公室。门猛然被撞开了,胡师傅带着两个保安冲进来。他们穿着保安服,手里拿着高强度的电筒。我正要打招呼,他们却将强烈的电筒光敲到我脸上。我只觉得满眼白亮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王老师,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嘶哑的嗓音吼起来。
我听出是胡师傅的声音,赶紧解释,误会误会,请听我说。
这一次,我帮不了你,你去跟马校长说吧。
胡师傅,你听我说,听我说。
胡师傅冷哼一声,下令说,带走,带走。
几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电筒光从我脸上移开了。
我看见自己像一个犯人,夹在两个保安之间。
放手,放手。我喊起来。
别理他,带走。胡师傅跺着脚说。
这时,我又看见他满嘴闪闪发光的龅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