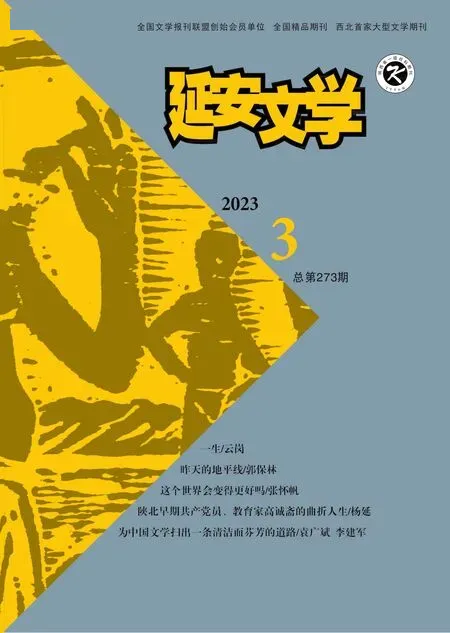膴膴周原
2023-02-20张凌云
张凌云
一
电视画面里,一片金黄色的麦田蔚为壮观,隔着镜头,也能感受到风吹麦浪的成熟气息,倘是不留意,这和中国北方的一处普通平原没有太大区分。但是,解说员的一个词,让我心中一凛,不由按下暂停键,并反复回放,久久凝视着那片金黄色的原野。
那个词,叫周原。
我终于见到了周原,见到了从诗经故事和上古传说里依依走来的周原。只是没料到,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见到不加任何标注或修饰的周原。
周原,是周部族兴起的地方,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这片方圆不过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像一个原点,将一部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回溯,回到最初的那个封面。
准确地说,现在所指的周原,称为周原遗址更合适些。它位于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公元前12世纪末,周部族的首领,周太王古公亶父率族人在这里营建城郭,开垦荒地,并定国号为周,开启了周王朝的雏形,此后历王季、文王、武王三世,周灭商。
我们熟悉的文明历史,肇始于周原。夏王朝太玄,可考的历史遗迹极为有限,商王朝太散,都城飘忽不定,即使盘庚迁都安阳后相对稳定,留给后人的文明财富也不多。只有绵延了800年时光的周王朝,特别是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作为有明确史书记载的年份开始,我们才对那些上古时代的文明碎片有了清晰的拼图。无论正史,还是《东周列国志》《封神榜》这些更加通俗、也更为吸引人的故事传奇,很大程度上,武王伐纣是我们认识一部真实意义的中国史的起点,而滋育了几代周人的周原,担当的是武王伐纣的序幕。
遗憾的是,周原如今对我们来说过于陌生了。这有客观原因。武王时期,西周定都镐京,在此之前,周朝的都城是丰京,二者毗邻,都离今天的西安不远。再往前,在文王晚年,即将都城由周原地区的岐邑迁至丰京,周原作为政治中心的色彩淡化。随着镐京的日益巩固,特别是周原由于不断遭到西戎入侵的破坏,终于在西周末年变成废墟,废弃不用。
屈指算来,周原地区的城池和遗迹,消失了快3000年了。上古的典籍记载既不翔实,更由于都城经常变换,对越早的记录就更加模糊,除了间断有文物出土外,周原对后人来说,最后印象就直接简化为两个汉字,静静躺在那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上。
那么,周原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二
《诗经·大雅·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为周原土地真肥沃,连苦菜都甜如麦芽糖。周原位于最早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关中平原西部,北依岐山,南傍渭水,海拔900米左右,这片平坦开阔的土地,在当时气候温润,草木葱茏,充满勃勃生机,的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诗经·大雅·绵》对古公亶父也不吝赞美之辞:“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溪水浒,至于岐下。”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诗经中的大雅,多是歌颂周代先祖及君王的叙事诗,这首诗明白指出,周人最早的发祥地,本在沮水漆水一带,是古公亶父早行赶马,沿着河岸一路来到岐山脚下。
为什么是岐山?我们先来简要梳理下周王室的世系表和迁徙图。
据《史记》载,周王室的先祖叫后稷,古公亶父是他的第12代子孙。中间的11代大多不出名,只有后稷的曾孙公刘比较有名。大雅中有两篇专门记述后稷和公刘的作品,《生民》与《公刘》,大学里曾学过,其中讲后稷的《生民》神话色彩较浓,《公刘》相对朴实,两首诗对这两位周部族的重要先祖教民稼穑,拓荒造屋的事迹都极尽赞颂,结合其他史料,可以推断出周人在他们带领下的一幅迁徙图。
周人最早的居住地叫邰。公刘时迁豳。古公亶父再由豳迁岐,即周原。
后稷作为农业始祖,邰是舜赐予他的受封地,在今武功县一带,同在关中平原,比周原偏东,自然条件同样优越,这样的一块好地,为什么要放弃呢,原因见《史记·周本纪》:“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是后稷的儿子,由于夏朝政治衰败废弃农师,不窋失了官职只好流浪到戎狄地区。历两世,公刘励精图治,将族人迁至豳,豳在岐山以北,黄土高原南缘,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濒临泾水,自然条件尚可,但谷地狭长,腹地有限,更由于经常受到戎狄侵扰,至古公亶父,终于“率溪水浒,至于岐下”。
这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是历经艰难险阻,重新回到水草丰饶之地的迁徙史。对于这片象征周部族真正勃兴的沃土,《诗经·大雅·卷阿》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宣言:“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也孕育了一个极富想象空间的名词,凤鸣岐山。
至此,周原大地升起了曙光。这道光,不仅照亮3000多年前尚处于蒙昧时代的一片旷原,也久久萦回在后人心头。
三
凤鸣岐山,多么美妙的字眼。虽然凤鸣岐山的典故通常指文王,如《竹书纪年》:“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鷟鸑鸣于岐山。”鸑鷟,传说中的鸟名,凤属,代指凤凰。我却宁愿相信自古公亶父“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下”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只凤凰昂首屹立在群山之巅,发出霞光一样金灿灿的啼鸣。于是,大地萌动,万物苏醒,所有隐藏的事物如万马奔腾,向着地平线汹涌而来。
这只凤凰有着巨大的翅膀。如果仔细查看中国地图,会发现关中平原西部有着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地名。扶风、岐山、凤翔、麟游、宝鸡、眉县、太白、千阳……这些光彩夺目,带着几分仙气的名字,犹如凤凰五彩斑斓的翅膀,翱翔在广袤的原野之上。
这是中国最美的一组地名之一。它们属于宝鸡,又称为西府的那片所在,当然,它们也属于周原。它们属于大周原的范畴,周原也不再局限于两县交界30多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而拓展到整个关中平原西部,包括宝鸡,以及咸阳、西安三市的各一部分。
可惜,它们实在太低调了,低调得让人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与周原有关的这组地名,除了左冯翊、右扶风的煊赫地位让人想起扶风曾经的辉煌,除了一碗岐山臊子面让人知道一座叫岐山的山,几乎很少有其他的声音了。它们都尽量把自己放低,低到尘埃里,低到古老而绵长的时光之河里。
周原同样低到了尘埃里。这片如今极少历史遗泽,只剩下村庄麦田的旷野,将它的胸膛紧紧贴住大地,不带一丝高蹈的姿态。就像那些谦卑的麦子,它们年复一年在地里分蘖,拔节,扬花,孕穗,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苍生黎民。
这是我喜欢的周原,也是始终抱有一颗初心的周原。凤凰啼鸣只是精神的放飞,低进尘埃却是它固有的姿态。
周是象形字。在甲骨文里,周就是一块方方正正长满庄稼的农田。顺着这个逻辑,才能明白《说文》“周,密也。从用口”的解释。生活在这里的周部族,将自己称为周人,正是因为他们热爱这方盛放汗水和耕耘的土地,这里有他们的情与爱,悲与歌,这里是他们一生的故乡,也是他们不变的乳娘。
于是我们回归到周的本义,同样也是周原的本义。周原,是中国农耕文明清晰的原点,古公亶父率领他的族人,将周部族祖先后稷教民稼穑的传统发挥光大,一圈圈蔓延开来,直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开满繁盛的丰收之花。
这不是夸张。周部族的确是善于农耕的,许多重要的作物品种,在这里都可以追根溯源。
所谓地下文物在陕西,这里的文物,除了那些建筑器物外,也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种子。
周原出土过不少碳化粮食。五谷中的稻麦黍菽稷,乃至泛指的百谷,大多都可以找到影子。考古专家曾专门对周原的土层进行研究,发掘了大量碳化的植物种子。其中包括粟,也就是小米,又称稷。黍,一种大粒小米,又称黄米。菽,即大豆。还有小麦。专家发现,这些碳化大豆明显要大于野生的大豆,还有源于西亚、对灌溉要求很高的小麦的大量出现,说明周原当时的种植技术已相当发达。此外,水稻虽暂未发现有碳化种子,但出土的产于西周晚期的伯公父簠上有铭文“用盛穛稻糯粱”,一连出现穛稻糯粱四种粮食,说明最迟至西周晚期,这片土地已开始种植水稻高梁。
难怪后人在《诗经·周颂·噫嘻》中会发出“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自豪的吟唱。重视稼穑的传统一脉相承,既开启了周王朝盛世太平的按钮,也夯实了整个汉民族社稷立国的基石。
四
低进尘埃的不仅是周人成熟的种植技艺,还有一串埋在土里的钥匙。这串掌握秘诀的钥匙,是青铜。
我对青铜器情有独钟。总觉得那些带着斑驳绿锈的器物,闪烁着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饕餮之美,是后代难以启及的范本。商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期。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堪称国之瑰宝,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制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不过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是礼器酒器,还有兵器,农具极少。普遍使用的还是各种木、石、骨、蚌制农具,如木耒,石锄,石铲,石镰,蚌镰等。
以善于农耕著称的周人,相比殷商时期,明显的进步是青铜农具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像翻地用的青铜铧,除草用的青铜鑮,收割用的青铜铚,都已出现。就周原而言,就出土过多件西周时的青铜锄,以及春秋时的青铜铧、青铜壁土等。虽说总体而言由于青铜珍贵,尚未替代石器得到普遍使用,但至少证明远在周原时代,我们的祖先已懂得使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在土壤里寻觅关于丰衣足食的更多奥秘。
如果说那些高高在上的国之重器离老百姓过于遥远的话,那么,更多走进普通家庭的青铜器皿,能让我们触摸到青铜荣光的真正温度。
周原所在的宝鸡市,是中国青铜器之乡。这里出土了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著名的晚清“四大国宝”,从汉代开始,宝鸡境内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宝鸡也被誉为“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应该来一次的地方”,而其中的扛鼎之作毛公鼎,正是出土于岐山周原。
我从参观博物馆的感受出发,对青铜器的主要类别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对卣、纍、瓿、觚、觯、卮、斝、盉、甗、簠、簋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乃至字都读不出的酒器食器进行了细细辨认,也对一些常见的国之重器如鼎彝,家用物什如豆盆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只是蜻蜓点水而已,并没有更深入的理解,只有离开灯光照耀下的被割裂的现代时空,回到3000多年前散发着原始气息的周原土壤,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周原出土过大量的食器炊具。如青铜甗,底下有几个出气孔,作用等同蒸锅,能够蒸出喷香的米饭。三个足的连档鬲,可以使食物平均受热,主要用来煮粥和菜汤。此外还有陶簋、陶豆、陶盘等,用于盛饭盛菜。无论是青铜器皿,还是陶制物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离开了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而用贴紧大地的姿态,氤氲出一幅最朴素也最隽永的农家康乐图。
这幅图里,我们可以看到男人耕种渔猎,女人缫丝养蚕,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点点绣出绵延了3000年的男耕女织、天下太平的生活理想。这幅图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点点垒出粮食和幸福,一点点堆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推动了有着大山般巨大影响力的农耕文明的基本形成。
于是,周原开始建宗庙,盖城墙,随着家族宗法制的建立完善和政权地位的日趋巩固,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功能已全部具备,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局面的开创,并最终以周代商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历史学家夏曾佑更是说:“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是周王朝重视制礼作乐,以礼乐制度逐步替代了从前的卜筮传统,将华夏民族从混沌蒙昧的状态摆脱出来,是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成为东方大国始终屹立不倒的精神之源。而这一切的上游,都可以看见周原的身影。
五
和许多消失的文化遗址不同,我不太关注周原考古的进展情况。诸如又发现了什么文物,岐邑故城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重要古建如何复原等等。
我知道,考古工作很辛苦,很专业,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窖藏铜器、建筑基址、甲骨卜辞,仅在遗址基础上建立的周原博物馆,就收藏各类文物上万件,直到本世纪20年代,这里还曾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考古学家的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步步将周原更真实、更丰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也许有些偏执,但我还是认为,无论有多少宗庙建筑被还原,形象有多高大立体,周原更像一片一望无际的原野,博大雍容、温柔敦厚的原野,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我们汉民族是没有英雄史诗传统的。尽管《诗经》雅颂里有几首歌颂周王朝先祖的诗篇,但还远没有达到史诗,特别是英雄史诗的范畴。相比之下,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江格尔》,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特别是《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其卷帙之浩繁,令人叹为观止。再看西方,除了早期的《荷马史诗》,中世纪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史诗,即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西班牙的《熙德》。这些欧洲主要国家在公元1000年后,相当于我国的两宋时期出现的史诗,虽以历史或神话为主要题材,反映的却是面对黑暗的中世纪,能够出现英雄人物改变世界的渴望。
双希文明,即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起源,而美与崇高,是双希文明中一对最重要的审美范畴。面对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或是整个雅典卫城遗址,我们会惊叹于那些气势恢宏的廊柱、穹门、石雕,包括已经坍塌的屋顶,残损的檐角,也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而希伯莱人虽然漂泊不定,没能留下太多的遗迹,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对承载精神之塔的某个地方的向往。如出埃及记的传说中,摩西带领族人,走了40年才到达故土迦南,数千年来,无论以色列人散居在世界任何角落,也无法浇灭他们想回归圣城耶路撒冷的热爱。美与崇高相互渗透,特别是崇高,能够让人产生巨大的悲悯或敬畏之感,面对无限和永恒,限入一种惊骇的喜悦,从而产生超越自我,努力向更高处延展的冲动。
这是西方史诗、建筑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他们保留了众多文明遗址的重要原因(当然也与建材多为石头有关)。他们需要那些矗立于高大的山丘或石础之上,让他们的灵魂得以皈依的建筑,即使是一根孤独的大理石残柱,也能成为联系天穹与人间的纽带。
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分野,华夏文明审美之维的核心是中和。中庸,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温柔敦厚。《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虽以孔子提出的仁为主要内核,却不能简单用中庸概括,而是兼具儒家之“和”与道家之“妙”,乃至儒道释三家共有的悦乐精神。所谓中和,既不张扬,又不鲁钝,反映的是华夏民族讲求含蓄平衡、和融智慧的价值观,无论对人,对事,对文学艺术,对宇宙万物。
回到主题上来。周原能充分体现并包容我们对世间万物的这种态度。它不突兀,没有那些高高耸立的殿堂塔尖,不悲悯,没有太多荡气回肠大开大阖的悲情故事,甚至是不显眼,那一片再普通不过的麦田,乍一看很难与赫赫有名的周原对上号来。但是,它坦露着博大的胸怀,与天地比寿与日月同光,数千年生生不息,滋育繁衍了一个民族,并将一直持续下去。它温和而坚忍,朴素而宽仁,始终像一位阅尽沧桑但不发一言的君子,微笑着看着它的臣民,它的子孙和后代。
某种意义上,周原就和我们的理想一样,以一尊温柔敦厚的肉身,努力道法自然,达到精神上的天人合一。
六
周原有着更丰富复杂的涵义。
周原是一枚永不褪色的钤印。周原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几千年的风雨沧桑与际会风云,并没有改变它本来的面貌。看上去,周原仍然是一片不带标签、再普通不过的原野,仿佛有一枚沉雄古拙的钤印,上面镌刻有周原二字,重重地按在大地之上,任凭岁月如何变迁,这片土地依然流着祖先的血脉,带着远古的芬芳。3000多年前,古公亶父和他的族人们,以愚公移山般的精神,一点点用锄头铲刀刨开蛮荒,用扁担箩筐挑起荆棘,把面前看不见的大山一点点移开,在荒原之上播洒出文明最初的种子。这枚钤印遇火不化,遇水不融,也不会随着现代文明的侵蚀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消减褪色,你见或者不见,你念或者不念,它始终都在那里。
周原是大地隐喻的原点。中国的几何中心是兰州。汉唐以前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西安。周原的位置,处于西安稍偏西、又离兰州更远些的一条中轴线上,这就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就地理面言,周原就像天圆地方居中的一个原点,于另一层意义上,尧舜禹以及商代文明虽然更早,但尧舜禹时代更像传说,没有确切的文明遗址,商代文明存在断代,只有以周原为源头的周代文明绵绵不息,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和基底。原,原道,本身有探究本原的意思,周原作为华夏文明的原点当之无愧。
我更想说的是,周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美丽童话,或者原乡。
周原不是虚构的神话传说,也不像西方的英雄史诗,而更像一朵美丽的童话,带着那些先民的歌唱,还有那些清澈的情感,盛开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这里,草木葱葱,平原漠漠,河泽盈盈,山川巍巍,是《尚书》《春秋》《国语》《左传》这些经典古籍雄伟的背景,是诞生《诗经》中那些优美的诗篇最初的温床。当我们吟颂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时,脑海里无处不在的是周原的影子。虽然这些诗句出现的时间要晚于周原兴盛的时代,地点也不局限于关中秦地,反映了黄河中下游乃至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我们仍会不自觉地想起周原,想起这片被渭水、千水、漆水河依偎包容的土地。我们仿佛在清晨掬起沁凉的河水,看荇菜浮萍缓缓地流过;在南山脚下悠闲地采集薇蕨,日过半晌不觉还没有满筐;在宜人的初夏里做着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游戏,空气中漫溢甜蜜的芬芳;在孤独的水中沙洲遥想起亲人,在每一个露重霜侵、雨雪纷飞的日子里反复唱着爱情的歌谣。
周原是一个开着不败之花的地方。这里有开不完的鲜花,结不完的果实,还有桃夭、甘棠、葛覃、苕之华、摽有梅这些有着鲜明汉民族特色的最早记忆。它们是文化版的植物学,也是人化的自然,是我们的祖先与养育他们的土地与生俱来的亲近与感恩,并深深影响了子孙后代,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学会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水乳交融的原乡。
总也忘不了苇岸说过的一句话:“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周原就是我们走不出的故乡。我的眼里常会出现一片广袤的原野,无论现代文明多么繁杂喧嚣,它依然是那么宁静,祥和,蓝天之下,随风飘舞着一朵野菊花。
一朵看似柔弱的野菊花,却是一座望不到顶的精神之塔。
七
要真正了解周原,还是要到实地去看一看。
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我踏上了周原之旅。来到陕西才知道,周原博物馆离周原景区相距有30多公里,周原景区又包括周城、周公庙、凤凰山几个部分,一天时间看不下来,而周原博物馆离法门寺很近,方便一起参观,于是决定先看周原博物馆。
周原博物馆位于扶风岐山交界,准确地说有两个,一个是扶风境内的宝鸡周原博物院,另一个是岐山境内的岐山周原博物馆。前者品级较高,系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限于时间关系,去了前者。
其实周原博物院虽说名义上在扶风招陈村,与岐山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原因是这一带发现了岐邑旧城和宗庙遗址,横跨扶风岐山二县,而周原博物院本来就在遗址基础上建立,除了室内的四个馆区,还有室外的两个建筑基址,尤其是岐邑旧城在岐山的凤雏村附近,所以很难、也没有必要将它们区分开来。
周原博物院黄墙红门,气象谨严,“赫赫宗周,万邦之方”八个大字,还有陈列的各类珍贵文物,使我顿时有了穿越3000年的感觉。我没有想到的是,整个博物院就处在一片麦田之上,除了一头毗邻村庄外,另外三面全是麦田。
仲春季节颇有凉意,天上还飘着小雨,但麦田都已返青,微雨中更显得几分青翠。伫足间,我觉得时光停滞了,这就是那个低进尘埃的不变的周原,再过数月,这里又将是风吹麦浪,遍地金黄,而遗址之上的周原博物院,只是一个忠实的麦田守望者罢了。
次日去周原景区。周城是近年来兴建的人造景点,以“古、土、乐、奇、巧”为构思,设有周王室、百工坊、诸子百家园、封神乐园、百鸟乐园、中轴文化展示区等六个主题区,宣传展示周文化。虽说是人造景点,但适应当下文旅发展需求,布局构造值得一观。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周原,既有古典陈设,也有场景演出,还有体验式的乐园,包括中轴线上,从进门处的天子六驾车马,到毛公鼎再到巨大的何尊,很好地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我去的时候可能由于天气原因,游人不多,据说上年国庆期间,人头攒动,盛况空前,还有举办一些主题日时,也会充分吸引人气。中国文化需要这种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大众更好地走近周原,认识周原,敬畏周原,让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拥有更广泛更强大的麦田守望者。
相比周城,周公庙是一处清幽所在。始建于唐代的周公庙,古木森森,苍苔浓荫,共有30多处殿堂碑亭,周公殿、姜嫄殿、后稷殿依次而列,“姜姬背子抱孙”的构建别具一格。踯躅流连后,穿过一道写着“天下归心”的牌坊,我径往后山而去。
将周公庙当作周原之行的最后一站,因为这里是我的终点。
我见到了一只金光灿灿的凤凰。这里叫凤凰山,又叫鸣凤岗,是岐山的一部分。在凤凰山顶,一只俊逸潇洒、展翅欲飞的凤凰雕像巍然耸峙,下面的基柱上,有凤鸣岐山四个大字。
这正是我心中的那只凤凰。它冲破岁月层层叠叠的束缚,向着我的脏腑和天灵呼啸而来。我的周围不断上升,再上升,直到汹涌成一片海。
山川河泽消失了,草木田园也消失了,此刻,它们在眼前统统化归为一个点,一个被尖锐的啼鸣擦得锃亮,并将在大地之上久久回荡的点。
那个点,是周原。那个点,是我们脚下走得再远,也一直连系的根。任前方的路再苦再累,任再多的烟尘遮蔽了眼睛,我希望能在心底听见一声嘹亮的凤鸣,沿着祖先走过的方向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