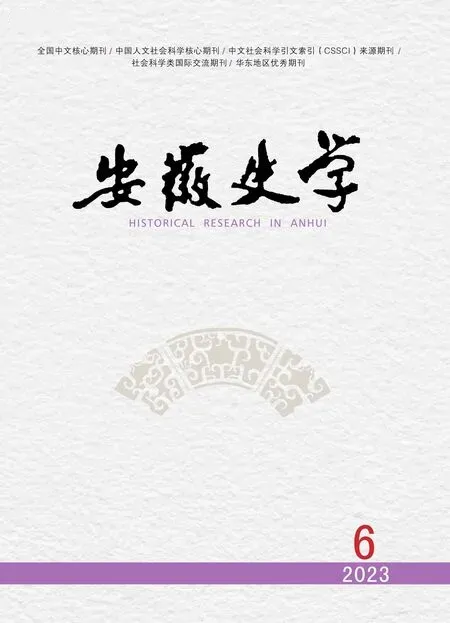苏区时期中共革命文艺的源起、衍化与组织化生产
2023-02-19任伟
任 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
借助文艺鼓动革命,是中共宣传的一大特色。井冈山时期,中共就开始有意改造士兵的娱乐活动,其后,革命文艺机制日益强化普及。全新的娱乐方式,不仅重塑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生发出一套有效的宣传方式。目前关于革命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度政策的梳理,侧重于文本描述,但较少关注实践形态。(1)参见周平远:《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周秦:《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戏剧》2022年第7期。其二,以某个人物或某种类型的节目为中心,探讨革命文艺的一些面相。(2)参见张军:《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贡献》,《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贾冀川:《论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顾楠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与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其三,从受众和社会影响方面,探讨革命文艺的功能与作用。(3)参见刘魁、江明明:《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王亚菲:《论苏区戏剧运动对当代戏剧形态多向度发展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这些研究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关照,不易呈现出革命文艺的全貌。本文拟从革命文艺的起源形态入手,力图把既往研究的几个方面综合起来——从制度起源看节目生产,从节目的内容和样式看观众反馈。
本文主要探讨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文艺节目的生产。中共以新代旧,倡导新式娱乐,红色演出一时间铺天盖地。但是,海量内容的生产并不容易,中共是如何完成的?此一问题既涉及到文艺的生产机制,也涉及到革命文艺本身的特点——即强烈的可复制性。第二,实践效果。后人观看革命戏剧,或感觉枯燥乏味,但对时人而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革命文艺都极具吸引力。第三,通常而言,娱乐应当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但革命娱乐却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导向性——观看者在嬉笑中深受教育。以后见之明观之,这样一种娱乐模式,深刻改变着大众的审美趣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限制,本文讨论的苏区空间,主要是以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
一、革命娱乐的制度化起源
苏区的革命文艺活动主要是指戏剧、歌曲、话剧等娱乐性表演活动,在当时又被称之为红色娱乐,或革命新剧等。苏区革命文艺的兴起与军事战争密切相关——主要为了是鼓动士气。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共一开始就有顶层设计的意识——后人视之为当然的制度,初创者可能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井冈山时期,红军整天东奔西走,四处游击,根本无暇顾及娱乐活动。士兵如何休闲,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当时的娱乐活动,多数只是在行军路上或战斗间隙唱些家乡小调,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注入,内容和形式基本囿于传统范畴。
事情最初起变化,源于军队中的“民间艺人”。他们根据作战状况,随性发挥,即时编造一些顺口溜,博众人欢笑。如1928年5月,红四军打败杨如轩,占领永新县城,就有人编了《杨如轩带花潜逃》,此曲唱词幽默诙谐,主要描述敌人丑态,凸显革命浪漫精神。6月,龙源口大捷时,有战士发明快板,借以弘扬士气。(4)邹耕生:《红军文艺的初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其他根据地也有类似情景,曾担任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的金如柏就回忆说:革命文艺节目最初没有剧本,“常常根据斗争情景,几个人一凑,编几句顺口溜,唱几支歌,就算演出了”;而且随着战斗频繁,此类节目越来越多,“常常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歌声”。(5)金如柏:《回忆红二方面军文艺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10页。可以看出,革命文艺活动之兴起,并不是领导者有意为之,只是“民间艺人”利用传统戏剧的形式结构,不断注入自身生活内容的结果。这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把日常生活随手拈来,整合进唱词,正是民间小调的惯有传统。
随着革命小调的增加,事情进一步发生变化。井冈山时期,虽然娱乐节目中有革命内容,但基本上是士兵自娱自乐,没有引导性机制,更没有规范性约束。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士兵娱乐活动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最显著的表征是机构设置。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行军途中设置“工农运动委员会”,娱乐活动开始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与历史上很多事情一样,架构设立并不意味着内容落地。1929年9月,陈毅向中央报告时讲,红四军士兵委员会内有娱乐科,纪念日时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新剧、双簧、女同志跳舞、魔术等,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6)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8、79页。向上级汇报,难免会多讲成绩;反而言之,面向下级讲话,就比较侧重提要求、找不足。同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向全军作报告时,态度完全不同。他说红四军中“革命歌谣简直没有”,“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可以看出,虽然是讲述同样的事情,但毛泽东与陈毅有显著差异。为何如此?与其说是判断不同,不如说是面对的情形不同。实际上,二人都把士兵娱乐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陈毅面对中央,重点讲成绩,侧重“有”的部分;毛泽东面对下级干部,重点是提要求,侧重不足的部分。但就事实层面而言,或可判断:通过娱乐活动培养士兵的革命意识,已成为中共领导层的内在自觉;但与此同时,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毛泽东才在古田会议上要求“充实士兵会娱乐部”。(7)毛泽东:《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0页。总体而言,古田会议前后,革命文艺已有萌芽,但尚需纵深推进。
其后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制度完善;第二,人员充实。就制度而言,古田会议后,与娱乐相关的机构普遍设立,最为重要者是列宁室。1930年10月,中央颁布《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正式设立俱乐部和列宁室,主要目的就是“有计划的切实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培养革命精神。其中,俱乐部以师为单位,是领导机关;列宁室以连为单位,是基本组织,具体推动各项工作。
首先看俱乐部,它是领导士兵娱乐的最高机关,总负责人由政治机关委任,下设晚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墙报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各委员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全面统筹检阅士兵文娱工作。从组织架构上看,俱乐部隶属于政治部,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列宁室归属俱乐部领导,是具体掌控、引导士兵日常休闲的直接组织。与支部建在连上一样,列宁室也是建立在连队上,共有6个组,分别是青年组、墙报委员会、识字组、体育组、游艺组、讲演组。其中,体育组下还分设球术股、劈刺股、田径股、武术股;游艺组下分设音乐股、化装股、杂耍股。(8)《列宁室组织法及工作条例》(1932年1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第1035页。不难发现,分门别类的组织机构,几乎囊括了士兵一切娱乐活动。
俱乐部、列宁室这一制度在部队推广成熟后,又逐步向地方复制。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各地设置俱乐部,规定县、区、乡、村必须都有相应的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如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集会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等。此外,中共对工作部署的细致,也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墙报中的文艺栏,主要刊载山歌、童谣、歌曲等,“登载这一栏,主要的是能代表下层群众的生活情绪,属于民间的文艺内容上,要避免小资产阶级不平的呼声”。插画栏,文字中配置插图,帮助识字少,或不识字的人看墙报。此外,为便于群众观看,还明确规定:墙报位置“高不得过人目一尺,底不得过人目二尺”。(9)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共掌控娱乐活动,不仅有严密的组织体系,而且有具体可操作的准则。如此一来,俱乐部很快遍地开花。1932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首次提出发展俱乐部,到年底就已建立712个。全中央苏区到1934年3月,发展到1917个,固定会员九万多人,各区、乡、村几乎都有俱乐部组织。(10)《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毛泽东在1933年在《长岗乡调査》中就讲,“全乡俱乐部4个,每村1个”。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且都有新戏演出,很能吸引群众。(11)毛泽东:《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41页。同年他在《才溪乡调查》中讲,上下才溪乡共有俱乐部2个,墙报数十处,工作人员一百多。(12)毛泽东:《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41页。由此可见,娱乐组织已普遍深入到各个层级的苏维埃体系之中。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文艺人员的来源。文艺活动在推广过程中,中共就发觉人才匮乏。解决困境的办法有二:其一,外派;其二,内部培养。在实践中,这两条途径相互补充。1930年后,党中央利用上海左联,不断输送文艺干部和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如崔音波、石联星、彭舜华、刘月华、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贾耀徳、沈乙庚等。专业人员的到来,不仅使得苏区文艺的品质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共以这些人为班底,组建了一大批文艺院校。如1931年中央苏维埃成立八一剧团,1932年扩建为工农剧社,其后各地纷纷效仿,成立分社或支社。据《红色中华》报道,截止1933年5月,汀州、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都建立了工农剧社,社员共计六七百人。(13)王永德:《苏区的一个重要戏剧运动组织——工农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54页。1934年,李伯钊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养一千多个学生。(14)傅钟:《红军的文艺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5页。总体而言,苏区专业文艺人才虽然一直不充裕,但中共通过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此一问题。其实,对于一项新兴事业而言,专业人员不足或是常态,只有伴随着制度本身的发展,人才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设计,牢牢掌握了根据地内的娱乐活动。但需指出的是,制度设计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实践细节完美无瑕。实际上,中共曾屡屡批评俱乐部的不足,例如1933年,中央苏维埃严厉批评俱乐部的工作,认为俱乐部组织不健全,有些地方没有建立。墙报内容大部分千篇一律,不能把党的中心任务与群众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晚会演出缺乏政治性,有些地方开晚会,只做老戏、打花鼓、唱京调,革命新剧不够等。(15)《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67页。一方面是成绩斐然,另一方面是不断的自我批评。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中共严苛的自我要求。其实,此类批评在革命进程中屡见不鲜,如征兵扩红、慰劳红军等过程中都出现过。但这与其说是制度的失败,不如说是中共在努力追求尽善尽美。毕竟,就总体而言,不论实践细节上有多少瑕疵,但党组织领导娱乐的意图最终还是得以实现。
二、革命节目的生产
就生产而言,苏区文艺节目的来源有四:其一,红军战士自己的创作;其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的创作;其三,留苏学生带来的苏联歌剧;其四,根据地内的民间小调。毋庸置疑,无论哪种创作,都必须遵循政治规范。
革命文艺节目的创作,必须体现政治意识,正如一位老红军所总结的那样:中央苏区文艺总的特点是政治第一。它所关注的不是个体的感悟,而是集体意识,根本目的在于鼓动,娱乐只是副产品。(16)《彭加伦谈中央苏区文艺》,《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297页。聂荣臻后来也说,红军的文艺活动,一开始就是要培养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17)聂荣臻:《红军时期的文化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5页。据潘振武回忆,红军早期演戏纯粹是娱乐消遣,传统花鼓戏盛行——战士扭扭捏捏上台,撇着嗓子唱几句情郎情妹,就可以博得满堂彩。1930年红四军攻占吉安,仍是类似表演。罗荣桓相当不满地指出:“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战士看了你们的花鼓戏,会想些什么呢?”众人沉默。在罗荣桓看来,革命本来就是反封建,因此不能老是演封建糟粕,要演文明戏。何谓文明戏?文明戏就是宣传革命的道理。把文明与传统对立起来,不是罗荣桓的独特看法,而是革命者的普遍思想。一位老革命文艺工作者后来就回忆说,“当时认为话剧是进步的东西,京、评、越、昆是封建落后的”,因此演出很少。(18)邵葆:《韩进谈中央苏区文艺》,《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302页。毫无疑问,在革命的映射下,传统戏立刻显得丑陋不堪。这倒不是因为它真的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不能提供革命所需要的价值。
总体框架确定后,进入到具体的生产环节,表现形式可以丰富多样。文艺节目的早期创作,很多都是旧瓶装新酒——利用传统戏剧的调子,填上新词。例如,鄂豫皖根据地非常流行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是由商城民歌《八段锦》填词改编;中央根据地演出的戏剧《骂蒋介石》,套用的是《昭君出塞》中的《骂毛延寿》的调。1933年蒋介石签订《塘沽协定》,红军据此编演《塘沽恨》,唱腔是套用旧戏《钓金龟》的曲牌。(19)潘振武:《战歌春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69、171页。如此种种,正如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刘瑞龙所言:“凡是民间的传统的文艺形式,我们能利用的都利用。”(20)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文艺工作略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55页。传统与革命交融,既彰显出传统强大的内生力,同时也说明革命的开放与灵活。中共之所以聚焦传统曲调,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专业性的音乐人才,短时间内谱不出曲子;同时,也因为民众对于传统曲调稔熟于心,张口就来,旧瓶装新酒,易于民众接纳。
当时,旧剧改造在苏区普遍推广。以兴国县为例,共产党进入之前,此地流传楚剧,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轮番登台,甚至还有一些色情戏。虽然几百年来的生活都是如此过,但在革命者看来,这些东西“封建”色彩浓厚,必须彻底改造。苏维埃建立后,各县、区、村成立俱乐部,专门改造旧剧。于是,大量打土豪分田地、送郎参军等具有革命色彩的楚剧诞生。(21)刘绶松:《老根据地文艺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26页。
在演出过程中,改造好的革命剧可以上演,但未经改造或改造不好的剧目则被禁止上演。1930年后,严控封建旧剧成为普遍趋势,各军区部队都有相关指示。1932年2月,红军占领赣州,总政治部明确要求,戏院准许继续营业,但须用新戏来宣传革命。(22)《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赣州工作给三军团政治部的一封指示信》(1932年2月1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第1169页。强调新戏,反过来讲,实际上就是禁止旧戏。1933年7月,湘赣军区明确规定,文艺内容不能违背政治教育原则,“如小调小曲有损害士兵精神的应禁止”,“游艺组的娱乐工作要与政治教育的目的不相违背,要表演激昂悲壮有革命意义,不应有萎靡士气的小调、淫剧和笑话,一切唱曲、剧本应经过政治部的审定”。(23)《湘赣省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决议案》(1933年7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
提倡革命新剧,禁止封建戏剧,是革命者的迫切愿望,而这一愿望的完成与落地,则有赖于组织保障。就此而言,工农剧社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于1932年9月成立,前身是“八一”剧团。从剧团到剧社,功能有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具有了审查权。剧团此前只是培养队伍、创作节目;剧社虽然也进行创作,但更重要的功能是审查节目。1934年中央苏维埃政府颁布《工农剧社简章》,对其审查职能做出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县分社及省分社负责指导下级剧社,并供给短篇剧本。中央总社负责指导省分社,并在理论及实践上领导苏区工农文艺。各工农剧社所编的剧本,以常务委员会为最初审查机关。如有争论或疑问,当报告同级教育部决定。最后审定权属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艺术局。(24)《工农剧社简章》(193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58、59页。
除工农剧社外,俱乐部、政治部、地方党委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审查职能。如俱乐部章程规定,群众创作的革命歌曲,传唱前,“须交政治部审核”。杂耍等娱乐表演,须删去封建性内容,以革命游戏,如跳高、跳远、单杠、劈刺刀等替代无意义的杂耍。(25)《俱乐部列宁室的工作决议》(1932年2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第1144—1146页。话剧的剧本要交当地党委审阅批准后,才可正式上演。(26)刘绶松:《老根据地文艺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28页。查阅当时的记录和后人的回忆,应该说这套规范在苏区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例如,活跃在鄂豫皖苏区的红日剧团,第一台节目便是“专门演给县领导审查的”,通过后,才大范围推广。(27)吴淑慎:《红日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37页。中央苏区曾就很多剧目能否上演,进行过激烈争论,如舞台剧《武装保护秋收》《谁的罪恶》等。(28)《提高我们在文艺思想上的政治警觉性——对于“武装保护秋收”的批判》,《红色中华》第115期,1933年10月3日;《“谁的罪恶”的演出与其脚本》,《红色中华》第102期,1933年8月16日。总而言之,中共关于革命文艺节目的规范与审查有一系列制度配套,并且得到广泛落实。
除旧瓶装新酒外,苏俄是革命文艺的另一源头。苏区时期,中共的很多制度政策都带有浓厚的苏俄印记。具体到革命文艺,1930年后很多人从莫斯科回来,他们带入的苏俄元素,极大丰富了革命文艺的多样性。例如,李伯钊在莫斯科学习时就是文艺骨干,到中央苏区后,她在八一剧团工作,兼任舞蹈教授,把在莫斯科学到的《海军舞》《陆军舞》《空军舞》搬上舞台,影响颇大。李伯钊的另一个贡献是从苏联带回了“活报剧”。这种剧目将跳舞、唱歌、话剧等融为一体,短小精悍,十几分钟演完,很有鼓动性。(29)邵葆:《韩进谈中央苏区文艺》,《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302页。苏联影响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例如有些剧目是从莫斯科直接照搬回来的,如江西苏区上演的《明天》《农奴》等,就是苏俄革命成功时,控诉旧社会的剧目。还有一些歌舞节目,是借用苏联的曲填上新词。最后,当时很多文艺学校都被命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从这一命名中,亦可想见苏俄对中共革命文艺的深刻影响。(30)李伯钊:《岁月磨不去的记忆》,《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304页。
三、革命节目的形式结构与内容效果
不论是在内容与结构上,还是道具布景上,苏区的革命文艺节目都有一套近乎标准化的规范。例如颜色运用上,当时多数节目都冠以“红色”二字,如“红色戏剧”“红色舞蹈”“赤色舞星”等——因为红色是革命的象征;白色是反革命的象征。革命者赋予颜色以内涵,从而深刻影响着舞台剧的装扮,红色后来成为革命剧的标配。除颜色外,其他如服饰、动作、语言等,形式上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据童小鹏回忆,革命戏剧之所以能够很快编排出来,一个关键原因是演员早已定型,如帝国主义戴纸糊的帽子,用棉花做的山羊胡子,还用面粉搞个高鼻子;资本家穿一身西装,挺个大肚子;地主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子等。造型标准化,不仅方便演出,而且深刻影响群众对“反革命”的认知与想象。童小鹏讲,演员一上台,群众就看懂了是什么人物。(31)刘毅然:《原战士剧社部分红军老战士座谈侧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79、180页。凭借装扮,就能知道是何阶级,就能联想到阶级敌人的罪恶,充分说明革命戏剧的角色设定完全被接受。若是以长时段眼光看,红军时期的舞台塑造,实际上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对“反革命”形象的认知。
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人物设定脸谱化,无疑枯燥乏味。但就当时群众的欣赏水平而言,简单的线条描述,反而易于理解。例如从苏联引进的活报剧,一般不讲话,类似哑剧,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清晰明了。如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就画一张东北地图,一个人扮日本鬼子,一个群众拿把斧头跟他斗。群众一眼就明白其中的意义。童小鹏讲,那时反对地主压迫农民,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人,反对国民党压迫士兵,基本都采取这种方式,很容易启发阶级觉悟。(32)刘毅然:《原战士剧社部分红军老战士座谈侧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79、180页。可见,“脸谱化”虽然被后人诟病,但在当时恰是优势。
如果不是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而是从实用性的角度理解,“脸谱化”实际上更符合传播规律。相较于幽深往复的探讨,简单直白的情节往往更容易俘获大众。对此,中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曾任红一军团俱乐部主任的潘振武就讲,如果从艺术的眼光看,革命戏剧相当粗糙,但是因为造型简单,百姓一看就懂,所以一直延续。(33)潘振武:《战歌春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62页。傅钟对革命文艺也有一个类似评价,他讲:战争环境中,文艺主要不是为了娱乐,而是革命宣传的武器。虽然艺术形式粗浅,但有作用,能影响群众。(34)欧阳雅、汪木兰:《开在红色土壤上的艺术之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20页。因此,从目的与手段的角度看,形式简化恰是革命剧的内在要求。1934年《红色中华》的一篇报道,很能反映这一趋势。文章借群众的口吻讲:过去的老戏打打唱唱,我们莫名其妙,“要读过满多书的人,满有才气的人才看得懂”。现在的革命戏,剧本说辞、角色扮演清晰明了,很接地气,一看就懂。理解之后,就比较容易引发共鸣。因此,很多观众跟着剧情“显露憎恶、喜欢、激愤、痛恨等各种不同表情”。(35)《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
如果说角色设定脸谱化,是革命文艺的一种特征;那么,内容上二元对立,人物活动的黑白分明,则是其另一重要特征。红军时期创作的剧本非常多,现无法一一描述,举其要者有:《红色间谍》,讲一个机警幽默的红军战士,奉命打入“围剿”的白军中,被敌人信任并提拔为班长,其后发动突袭,响应红军。《活菩萨》,描写地主土豪残余分子,在根据地内利用迷信造谣,进行反革命活动,结果被一革命青年揭破。《为谁牺牲》,描写革命根据地的一青年农民,早前被国民党白军抓走当兵,撇下老婆孩子,走了七八年,腿在战争中残废,最后被官长赶走。回到苏区老家,老婆是县妇委会主任,儿子是少先队长,相见之下,自己成了残废,政府还给他留下田地,感动得流下热泪。认识到过去自己究竟“为谁牺牲”。(36)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44、45页。不难发现,人物之间的黑白对立是革命剧情的重要特征。
但是,叙事结构上的一致性,绝不意味着单调重复。实际上,精细丰富是革命文艺的另一重要特点。中共根据场景不同,上演的剧目各有侧重,安排细致入微。例如,仅歌曲而言,就分为好几类。严肃正统的有《国际歌》《八一起义歌》《红军军歌》等,这些歌曲通常用于隆重场合。特别是《国际歌》,只有开大会时才能唱。鼓动性强的有《打龙岗歌》《高虎垴战斗歌》《少共国际师歌》《兴国师歌》等,一般用于战斗之前。激励民众的有《农民暴动歌》《送郎当红军》《慰劳红军歌》《帮助红军家属歌》《妇女解放歌》等,一般交给地方团体演唱。争取瓦解敌军的有《白军受苦歌》《白军十二月唱》《亡国恨歌》等,通常唱给俘虏听。(37)高励:《红一军团宣传队——战士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90—192、190页。此外,还很多剧本直接配合革命任务。例如,为响应扩红,中共组织编写《扩大红军》《送郎当红军》;为搞好军民关系,编写《送军鞋》《优待红军家属》;为教育士兵,创作《反对开小差》《拖尾巴》等。(38)高励:《红一军团宣传队——战士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90—192、190页。可以说,种类繁多,因材施教,是革命文艺的重要特点。
为达到良好效果,文艺表演者不仅细心裁量内容,而且相当注重舞台技巧。早期的娱乐表演,只是三五之人临时凑成草台班子,即兴演出,没有太多理论技巧上的自觉。例如,会场布置大多数是搭建野台子,偶尔用到庙里的旧戏台。舞台照明,一般是从山上砍些松油柴,点燃松明子,前台架起两堆,旁边挂两堆。化妆油彩很少,有时用墨画胡子,后来用羊毛粘。乐器基本上都是打击乐,多数从群众处借。(39)高励:《红一军团宣传队——战士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95、190页。自发表演虽然其乐融融,但是缺少规范。任何一种事物如成规模,必定趋向专业化、标准化。
1933年6月,中央对于戏剧表演做出明确规定。首先是化妆,规定指出:装扮必须要表现出阶级、性别、地方差异,不能随意涂画。其次,戏剧材料尽可能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要让群众一头雾水。第三,注意取舍材料。群众生活方方面面,不可笼统地搬上舞台,必须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明确。例如,如果材料是反对开小差,而开小差有各方面的影响,原因不同,“一定不能随便拿一部分或一概拿来”,要从全部材料中拿一个中心。第四,表演过程中,谈话要多于独自叙述,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自言自语的情况很少,“并且有对话才能表现各种复杂的关系,各种事情的波折,和各阶级的矛盾”。第五,注重戏剧结构,不可平铺直叙。表演一件事情要有起落,中间要有发展和转变。(40)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101页。总结而言,可以说技术性流程支配着革命文艺的方方面面。
革命者精心设计,那么观众反馈如何?应该说,革命文艺在当时颇具吸引力。红军行军路上,一般都设有文艺鼓动站,打一个胜仗,要演他几台戏。(41)傅钟:《红军的文艺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4页。演出的欢乐气氛,成为很多人一生的回忆。据潘振武讲,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住三天以上,总是首先找两间房子,把列宁室布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这里唱歌、排戏、跳舞、讲故事,特别是教唱歌,宣传队员教战士,战士教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就可以判断有没有部队驻扎。(42)潘振武:《忆红一军团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207页。
革命文艺活动完全主导士兵的娱乐生活,意义重大。首先是革命精神之灌输。不在现场的后人,可能已无法体会观看者的情感投入。实际上,演出内容的二元对立,以及煽情的舞台表演,非常能引起共鸣。据称,李兆炳编写的《血汗为谁流》,表现白军士兵修碉堡,饥寒交迫之下,还挨打受骂。俘虏观看时,嚎啕大哭,不禁高喊“打倒国民党”。(43)高励:《红一军团宣传队——战士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95、190页。鄂豫皖地区上演的歌舞剧《穷人调》,最后一幕是“逼租”,百姓沉浸其中,“整个会场都泣不成声”。(44)吴淑慎:《红日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339页。革命文艺强烈的情感渲染动人心魄。斯诺就注意到,中共把“艺术搞成宣传”,虽然把一切问题简单化,但这恰恰契合大众心理,“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外人看来是宣传的东西,但对于身在其中的人而言,“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45)[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其次,文艺活动制度化,使得士兵的空闲时间基本都被组织掌握。由此,赌博、嫖娼等传统军队恶习便没有滋生空间。1929年江西省委就注意到,国民党的士兵,没有正当的娱乐活动,“因此嫖赌之风,确实盛行”。(46)《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1929年5月4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本,第129页。士兵个人时间太多,就容易寻欢作乐。红军风气良好,同中共有效控制娱乐活动,应大有关联。
除军队士兵外,一般民众对革命文艺也有热烈回应。红九军团供给部长赵镕,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其参加演出的情况,为考察当时情景又提供了一个例证。1933年12月,赵镕从前方回到瑞金。第一个周末,即12月16日,他就主动跑到礼堂参加晚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林伯渠、张闻天、林彪等都已就坐。赵镕慨叹道:过去几年,野外作战,无日不在戎马倥偬之中奔波,年长日久,连星期天、节假日都忘了。现在回到瑞金,各界群众朝气蓬勃,忙而不乱,星期六晚上,大家欢聚一堂,谈天说地,交换意见,参加娱乐晚会,松弛脑筋,实在很好。
赵镕第一次观看正规剧团演出,就被深深吸引,此后每个周末,几乎都有参加。如12月23日记载,红色剧社的小演员们,在李伯钊同志的领导下,一个个精灵活泼,“装啥像啥”。不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工农群众,都表现的惟妙惟肖。12月30日记载,会上演出了几个活报剧,演唱了几首民歌。最后,李伯钊担任“拉拉队长”,大声喊:“请首长们唱一支歌好不好?”众人答:“好!”李伯钊接着喊:“周总政委前次唱得妙不妙?”众人答:“妙!”“请周总政委唱他从欧洲带回的国际歌要不要?”众人情绪更加激昂,齐声答: “要!”于是,周恩来起身,领大家齐唱国际歌。此后数个周末,赵镕从未落下。
从赵镕日记中可以看出革命文艺活动的几个特点:其一,演出极具吸引力,观看者众多,晚一步就没有座位。例如苏区二大召开时,工农剧社举行晚会,观众多达三千余人。(47)欧阳雅、汪木兰:《开在红色土壤上的艺术之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120页。其二,革命领导者热情颇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频繁出席。而且,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延安时期。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就注意到,红军剧社演出时,张闻天、林彪、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48)[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76页。其三,干部与群众互动热烈,体现并强化了红军时期的民主平等。前述周恩来与观众互动即是一例。事实上,罗荣桓、罗瑞卿、何长工等都曾参与过表演。上下级在欢快的气氛中,共同融入一个场景,很有助于增进情感。其四,演出频繁。赵镕只是记载了瑞金礼堂的每周一演,实际上当时的文艺演出应用于各种场合。如1932年5月2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学生毕业,晚上开演晚会,有活报、歌舞、新剧等。(49)《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学生毕业盛况》,《红色中华》第20期,1932年5月25日。1932年10月16日,红军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典礼,学生讲演完毕,由照相师摄影。“工农剧社即开始表演游艺,除双簧、京调、小女同志跳舞之外,还有三幕新剧‘到前方去’,寓意甚佳,助兴不少。游艺完毕,时已七时许。”(50)《红军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典礼盛况》,《红色中华》第36期,1932年10月16日。1933年3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晚上举行晚会,工农剧社表演歌舞、活报、新剧等,节目均极精彩,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喝彩,直至十一时,始尽兴而散。”(51)《马克斯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红色中华》第61期,1933年3月15日。其他节庆日时,晚会更是必不可少。赵镕记载,春节期间,李伯钊几乎每天都忙于组织娱乐晚会。(52)赵镕:《长征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文艺汇演铺天盖地,群众厕身其间,感受强烈。1934年《红色中华》报道,工农剧社演出时,“大家都准备叫哑了喉咙,鼓肿了手掌”,有些老同志带了老花镜,有些小同志依傍在妈妈肩膀,都带着极度的兴奋与热情。(53)朱华:《歌舞晚会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1934年2月3日。蓝衫剧团极受欢迎,每到一个地方,群众总不肯轻易放他们过去,恳求演几出。尤其是江口区,新剧团已经离开几十里,还派人去追。(54)《红军医院苏维埃剧团到处受欢迎》,《红色中华》第169期,1934年3月31日。胜利县群众自动给剧团送来猪肉、大洋等。(55)《胜利县热烈欢迎苏维埃剧团》,《红色中华》第169期,1934年3月31日。以后来的眼光看,革命文艺的宣教味道重,且不免模式化倾向,但当时群众显然未感受到其弊端,而只见其新颖。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文艺创作者确实能够贴近群众,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能理解的事例去表现革命意涵,切实做到了寓教于乐。第二,虽然以后来的眼光看,革命文艺的内容结构比较单一,但对当时百姓而言,它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并且与“文明”“先进”等连接在一起,具有相当高的尊崇性。中央苏维埃剧团巡演时,群众成群结队,相互招呼说:“大家去看中央来的文明大戏,蛮好看咯!”(56)戈丽:《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册,第81页。第三,革命文艺强调阶级斗争,充满崇高的反抗精神,不仅道德鼓动性强,而且有具体的、活生生的斗争对象,戏剧与现实密切相连,就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
结 语
中共革命文艺的成长是一个从“自发状态”到“规范状态”的过程。现有研究也大都注意到,革命文艺在起源之时与传统娱乐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传统向革命转化的过程中,节目的娱乐气质发生很大变化——政治性被一遍遍告诫,最后成为革命文艺最显著的标识。强烈的政治意识,深刻影响着文艺节目的生产。概而言之,政治引领娱乐使得文艺创作呈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其一,黑白分明、二元对立的模板化叙事结构;其二,人物造型的脸谱化。从艺术的角度说,这无疑损伤了文艺的丰富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革命文艺“政治色彩过于浓厚,革命宣传的功利性难免影响新剧的艺术水准。时间一长,容易使受众产生视觉和听觉的疲惫。”(57)刘魁、江明明:《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从长时段看,的确如此;但是回到革命文艺的起源状态,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中,也应该看到:“单一化”“简约化”的表演方式更能唤起群众的情感,而且在事实上也大获成功。因此,单向度的评价标准——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文艺的,都有失偏颇。事实上,在革命文艺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转化”与“消耗性的转换”同时存在。
政治引领娱乐是革命文艺的重要特征。它起源于苏区,并且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强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把文艺定位成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从理论上彻底奠定了革命文艺的取向。(5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此后,政治介入文艺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以后见之明观之,如何制定好政策,既能实现“文艺服从政治”,又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在相当大程度上考验着革命领导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