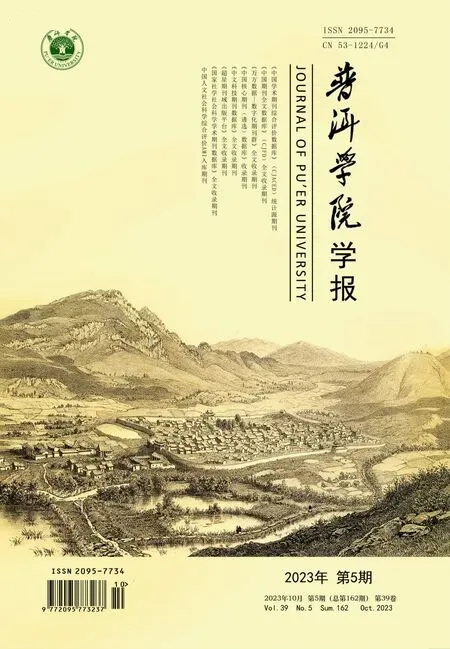从时间错位看《长恨歌》中的人物悲剧
2023-02-19施红丽李丹一
施红丽,李丹一
1.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2.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对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研究评论有很多,但就时间错位造成《长恨歌》中人物悲剧这一方面来说,研究的不是那么透彻。因此,从对时间的审视和解读来剖析小说中人物,因对时间的错位认识而导致的一系列悲剧,进一步揭示了小说中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一、怀旧:商业文化的另一走向
王安忆的《长恨歌》创作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自创作以来一直备受赞誉,缘于它绚丽细腻的笔法、跌宕起伏的情节,独特的视角等等方面。而人物由于对时间的错位认识而导致的一系列悲剧。
《长恨歌》的创作,是和它问世的时代息息相关的。20 世纪90 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所体现出的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对大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它几乎全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在物质上,人们显示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急切的渴望,现实欲望的满足和快感寻求成为一部分人生活追求的唯一目标。精神上,20 世纪90 年代的大众是“精神衰退”的一代,作为知识分子的许多作家也失去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精英意识,失去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继而转向了对过去的回忆。王安忆曾有过这样一段表白,“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1]。这显然是一种古典的传统“家”模式,也是当时怀旧的社会潮流。“怀旧在20 世纪90 年代成为大众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共同爱好,成为流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思潮”[2],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一道既迷人又老态龙钟的风景线。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即为怀旧文本的典型范例。她写出了一个程度不同的“怀旧病”患者的形象系列。尤其写出了王琦瑶这个生活在“上海弄堂里虽过着普通日子却骄傲、优雅的水一样永带着感伤和怀旧情调的女性形象”[3]。读完《长恨歌》,不能不被作品中氤氲始终的美丽而悲凄的氛围、感伤而深沉的意绪所感染,不能不被作品中温婉隽永的叙述风格、诗情画意的城市意象以及洁澈清雅直透心灵的语言和多声部回旋变奏的音乐性结构而赞叹。可以说,《长恨歌》是一曲繁华旧上海的挽歌,是一部对四十年来上海由沉潜趋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优雅坠入粗俗的“怀旧”感伤史,字里行间无不传达出一种对过去时间的迷惘追忆。
二、旧上海:时间的标本
在《长恨歌》中,许多的场景多为时间性场景:飞翔在上海屋顶上的鸽群,一代一代虽在替换,可作为总体,它们却是万物流变中的一个永远不变的物体、时间的化身、生命的见证。上海的弄堂、粉红缎旗袍、古木衣柜等,都打着时间的烙印,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时间仿佛依附在上面成为可触可感的实在性物体,在辽远的记忆里沉淀下来。而《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就是在这样一张网里以无限美丽又无限凄婉的神情为我们吟咏了一首苍凉伤感的歌,也是一首绵绵无期的“长恨歌”。王安忆要展示的也正是王琦瑶身上的“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流动时间与固定时间的对比张力”[4]。
王琦瑶是上海平常人家的女儿,可这上海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个人即便等得及,可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且有更大的破坏要来”[5]。从小说中排列的一些时间事件来看:
电影圈是1946 年的上海的一个进步圈,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1948 年的春天。这一年,内战烽起,前途未决。这是1957 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1960 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程先生是1966 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个。1976 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
这些强行楔入叙述过程中的年头,它的背后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劫后重逢。而王安忆也是通过这些事件来讲述王琦瑶与时间纠葛的一生。这给人一种时间匆匆,韶华易逝,人生变幻莫测的感觉。王安忆也曾透露小说最早起名为《四十年遗梦》,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覆盖上了苍茫的情愫。苍茫的时间跨度为人物凄迷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
三、怀旧者:时间错位下的悲剧命运
从《长恨歌》来看,人物悲剧都是由时间带来的。时间像一根魔棍,在不经意间搅动着人生,变幻着命运。而造成他们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时间的吻合和错位带来的种种悲哀及迷惘的怀旧”[6]。
怀旧,除了显在的对昔日的缅怀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潜在意蕴:对现状的不满。追怀过去的心理,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不如意的基础之上的。“今昔非比”的共同感慨,是频频震响在怀旧这一旋律中的最强音。
(一)王琦瑶:繁华梦中的痴情者
“‘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对于王琦瑶,繁华似曾有过,却只恍惚一刹那便从指间滑落;憔悴是憔悴,却又并不就此抱憾就此哀怨欲绝,这一身憔悴一身孤独竟也有些为那繁华一刻殉道的意味”[7]。然而,繁华来得快,消散得也快,瞬息之间,一切的风情与美艳便成为过往云烟。可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弄堂里娇羞乖巧的王琦瑶了,“时间的流逝是最使人感伤的,特别是当你还有希望,还在守望着什么的时候”[8]。
虽然时间将王琦瑶带入一个更为激进更为摩登的年代,可她的心却仍然留在上一个时代。她的笑颜戚容里,挥之不去的仍然是上一个时代的色与光,王琦瑶想用这一切来留住时间,对抗时间的流逝。可时间是让人无法抓住的,王琦瑶在生活中一直是清醒的。可旧上海的风情和逝去的繁华却成为她心目中一个永不磨灭的梦。她总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的回首遥望。到头来,时间仍是时间,历史仍在发展,生命的本身也只是一种梦幻而已,也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命运。
追根溯源,王琦瑶的悲剧不得不归结于她早年的风艳绮丽的生活,更是由于她的时间错位感。“她有一颗‘永远的上海心’,总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很仔细。只是她的人生没开好头,一路充满绵绵长长的辛酸”[9]。她“天真地把时尚与记忆倒置,把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当作时下的时尚,而这种天真的倒置犹如一股巨大旋风把她卷入了悲剧的深渊”[10]。再加上在两性社会中,女性对时间流逝的领悟有着比男性更深的感触。也正因为对时间的恐惧,没有哪一个女人的内心深处不渴望留住青春,不渴望永远拥有美好的往昔岁月。但是她的一生,在经历了太多的沉浮与聚散后,唱出了一首浮华斑斓的旧上海的挽歌,且这首歌是她自己作曲、自己填词、自己主唱,是“对人生错位的爱的沉痛悼歌”[11]。
由于对时间的错位认识而导致王琦瑶悲剧的一生。她喜欢缅怀过去,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格格不入的世间里能够找到一个避风港,喜欢在他人的身上找到过去的自己。可是上海已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上海,时间依然马不停蹄的在往前走,一味怀旧,只会让她找不到现实的乐趣,永远的活在那虚无的世界中,造成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悲剧。
(二)康明逊:自欺欺人的梦中人
“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12]。在新的社会里,“王琦瑶与‘遗少’康明逊的无望的恋情是一种‘向后看’的爱情,两个‘旧人’为了快要逝去的青春在尚可苟且的环境里做情爱的挣扎,却最终以怯弱收场”[13]。如果说王琦瑶遇到康明逊是找到一个过去的知己的话,那康明逊遇到王琦瑶只是把她当作对过去时光追忆的一个窗口。因此,当王琦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恰恰迎合了他的旧情,她只是使他有了一股失而复得的激动和欢喜。但“康明逊知道,和王琦瑶的恋情是不可能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尽管怀旧时慷慨悲凉也好,柔肠寸断也罢,而其最终的结局,仍只能是惊人的一致——除了幻灭,还是幻灭,正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4]。
(三)老克腊:追求“时尚”的寻梦者
书中的张永红是当年的王琦瑶, 是这个时代的精华,而作为怀旧与审美交织的“老克腊”,不啻是康明逊的翻版。王琦瑶是有旧可怀,有一生大起大落、坎坷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可是老克腊的“怀旧”实则就是“叶公好龙”式的,是矫情恋旧的。他的怀旧不是企图真正回到既定过往, 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一种在时间中某些东西被移植的感觉。
通常,时尚的先锋具有两种类型。他们或者标新立异、主持主流;或者标榜传统,维护往昔的荣耀。相对地说,前者体现出欢乐、肤浅同时又生气勃勃的风格,这种类型更多地以躯体活力、容颜和现钞为依据;后者都是怀旧的、体面的、精雕细琢的同时又是渊源悠久的。正因为他们把“怀旧”作为一种“时尚”,因此,当老年时代的王琦瑶和女儿一起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光里时,旧上海的繁华梦又重新焕发了她诱人的魅力。作为旧上海象征的王琦瑶,以旧上海的古典、绮丽、又不乏时尚,紧紧地吸引了女儿薇薇之类的下一代年轻人。王琦瑶的出现,为浮华热闹的现代生活加深了底蕴,增添了定力,追回了一份历史感。
如果说“王琦瑶是生活在新时代的‘遗老’,那么老克腊就是生活在新时代的‘旧人’”[15]。尽管他年纪轻轻,在叶公好龙式的刻意怀旧心绪中,“却又成了个老人,一下地就在叙旧似的。心里话都是与旧情景说的。总算那海关大钟还在敲,是烟消云灭中的一个不灭,他听到的又是昔日的那一响。”对于这样一个恋旧的人,与其说和王琦瑶在一起是爱上了她,不如说是恋上王琦瑶旧上海“三小姐”身上散发出来的那古木家具、木雕盒子、旗袍的气息,是爱上了和她在一起那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四、结语
人们终于发现时间是绵延的,过去如同流水一样总会从手指缝中消失,繁华如梦,一切都在再创造,没有什么需要保留下来。在《长恨歌》中塑造了一个王琦瑶,但这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她“不是一个人,而化开来弥漫和洋溢在空气中的一个灵样的东西。”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是一种生活形态,是以一种“强烈的符号化的个体介入到历史的进程之中”[16]。王琦瑶实则是一种代表,代表了那种经历过上个世纪繁华而最终因种种原因没落的人。在与时间的对抗中,他们的力挽狂澜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一切的悲剧只因对时间错位的认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