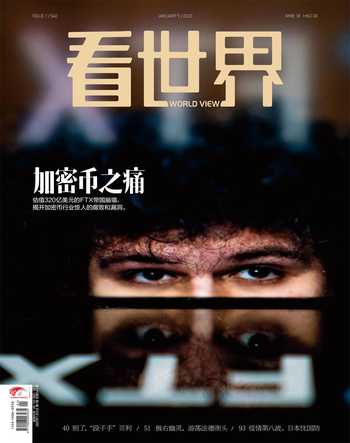欧洲流浪者,寻觅节日体面
2023-02-19菲力
菲力

2022年12月5日,英国伦敦,慈善机构Crisis展出一座4.3米高的流浪人士主题雕塑
大雪纷飞的平安夜,阴冷的墙角,“嗤”的一声,火柴燃烧起来……至于后面的情节人人都能够讲述:透过火光,女孩看见了壁炉、火鸡、烤鸭,尔后被亲爱的奶奶拥入怀中,去往那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痛苦的天堂。
安徒生写作的19世纪,是欧洲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社会贫富剧烈分化。借作家之眼,社会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流浪者”得以被全世界看见,并被赋予同情。但童话之所以是童话,一方面在于能够唤起人性之善,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单纯。
作家身后200多年,不仅阶级仍在,与之伴生的流浪汉甚至成为欧洲社会一个标志性族群。这一族群长期生活在下水道、地下铁等城市暗面,却如明镜一般,倒映出地上世界的“体面人”如何在善与恶的边缘,流浪。
“马铃薯不必成为松露才值得赞赏,马铃薯也能比松露更棒,关键在于你怎么想。”
流浪在伦敦
伦敦,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与其富庶的生活水平齐名的,是城市中超过30万的流浪人口—相当于每20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流浪者。但如果追溯其数量庞大的根源,就会发现,富裕与贫穷,有时根本就是今日英国的一体两面—权力机构选择牺牲一部分人的人生,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优渥生活。
二战之后,日不落帝国衰落,为填补人力短缺,英国从前殖民地国家向本土移民。1984年,“帝国疾风”号从加勒比地区搭载近500名移民来到英国,开启了此后长达23年的移民潮,加上这些移民在英国本土诞育的后代,总人数超过50万,被称为“疾风世代”。
这些移民劳工大多从事季节性工种,收获期内高强度作业,赚取微薄时薪。谁曾想当局过河拆桥,他们直至衰老也没能取得英国公民身份,而“黑户”是没有资格享受英国社会的教育与医疗福利的,最终,只能流落街头。
相比英国政府的失职,民间对待流浪汉的态度显然更贴近人性中善的一面。
在伦敦黄金地段,流浪老人再养一条狗的话,仅靠乞讨年收入高达3.5万英镑的传奇新闻也不是空穴来风。但圣诞节除外—这一天普通人家喝着热红酒吃着烤鸡,而流浪汉的居所,包括地铁站在内的大多数公共场所都停止营业。此时的户外,正是天寒地冻。
于是,2017年,英国铁路公司Network Rail发起了一场“感动英国”的圣诞晚宴,招募志愿者在平安夜打烊后,将Euston地铁大厅布置成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宴会厅。这一次,壁炉、火鸡、烤鸭没有如童话般幻灭,200多名流浪汉还在散场后获赠了一个装满日常用品的节日礼包。
受此策划启发,英国人开始思考利用城市中废弃的公共空间,为流浪者们提供体面的家园。比如,2019年Morris+Company成功竞标将约克街废弃的地铁站改造成旅社和联合办公空间;同年,一家伦敦的公司将淘汰的红色双层巴士改造成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这些项目试图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不再藏匿于城市暗面,而是正大光明地聚集在充满活力的社区。

2022年6月23日,英国伦敦,滑铁卢车站展出一座致敬“疾风世代”的雕像
这很意大利
在英国人通过捐款、改造旧空间解决流浪者基本生存问题的同时,意大利人表达善意的方式显然更具民族特色:吃顿好的!
早在1990年,意大利慈善机构“圣艾智德團体”就仿效《米其林美食指南》编制了一本专门面向流浪汉的口袋书《哪里》,不仅列出罗马市内80家室内外餐厅,还包括多家医疗机构的地址、可供栖身睡觉的场所,以及可供洗澡、剃须和理发的地点。这本“流浪汉版米其林指南”每年更新一次,最初仅在罗马和热那亚地区发行,后来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纷纷效仿。
不仅如此,体面地吃一顿,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其意义绝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事关身而为人的尊严。2016年奥运期间,一家坐落在里约破败社区内的“剩食餐厅”备受瞩目,其背后是当年收获“全球最佳餐厅”的意大利主厨Massimo Bottura,以及30多位米其林厨师;款待的对象,却是里约奥运期间因“有损市容”被政府驱逐的流浪汉。
尽管如此,餐厅从烹饪到服务,一切仍旧按照米其林标准,除了使用的食材来源于城市中每天因卖相不佳而原本要被抛弃的食物,比如他们居然用香蕉皮来制作甜蜜的冰激凌!餐后有流浪者这样感慨:“坐在这里,被无差别地对待,让我觉得可能我的人生还有机会。”
波兰社会有一种声音开始质疑,这些乌克兰人是否正拿着波兰纳税人的钱度假?

里约“ 剩食餐厅”的意大利主厨MassimoBottura

退休老人DinoImpa g l i a z zo(左一)与志愿者在准备食材
“马铃薯不必成为松露才值得赞赏,马铃薯也能比松露更棒,关键在于你怎么想。”Massimo的理念在意大利本土亦不乏同行者。比如,90岁的退休老人Dino Impagliazzo是RomAmoR(罗马之爱)协会的创始人,他从十多年前开始在自家厨房为流浪汉制作汉堡,渐渐地集结了300位志愿者参与进来。
Impagliazzo表示:“我们试图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罗马成为一个人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城市。”这一切都很意大利不是吗?
波兰的两难
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无家可归的人口就长期处于增长态势。但今年,规模最大的流浪者并不来自失业,而是战争。
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波兰和乌克兰居民关系天然密切,在历史和文化上较为相近,语言也几乎互通,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难民通过铁路、开车甚至步行进入波兰。

2022年3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乌克兰难民在难民营休息
不要质疑波兰人民的善良。波兰人口中基督徒比例占90%以上,而《圣经》写明“接待陌生人”是基督徒使命的一部分。NGO组织在倡议波兰民众款待难民圣诞晚餐的宣传片中就曾强调:“耶稣也曾是难民。”
更何况,这个本身命运多舛又在二战时期尝尽艰辛的国家,如何能不懂得“自己淋过雨,要给别人撑伞”的道理呢?
刚开始,波兰社会的确全员动员,大量志愿者帮助乌克兰难民寻找住宿、安排他們前往其他城市或国家的行程,洗衣店免费清洗难民们所使用的床单,餐饮公司也不会收取伙食费。更有数万户波兰家庭邀请乌克兰难民家庭入住,甚至与之同哭泣。数据显示,有70%的波兰人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为乌克兰难民提供庇护的工作。此外,政府也给予了乌克兰难民一次性补贴,并允许其合法居留波兰18个月—在此期间乌克兰难民可以工作,并获得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
一切都看起来很有爱,直到当超过250万乌克兰难民前来,这个东欧国家所处的道德和现实境地逐渐变得微妙起来。比较现实的问题是,愿意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家庭已达到收留上限,整个华沙人满为患。而且,由于战争期间乌克兰禁止成年男性出境,所以难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具备劳动力的老弱妇孺,但补助却做不到无止尽。
人们开始意识到,照顾一个难民家庭远远不止“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对方,提供一些帮助就好”,还有心理问题、健康问题、教育问题……随之而来的责任令人喘不过气。甚至,波兰社会有一种声音开始质疑,这些乌克兰人是否正拿着波兰纳税人的钱度假?
同时,波兰政府也开始就解决难民问题所需的融资,与欧盟展开拉锯。毕竟当初加入欧盟时,波兰期待的是有福同享,而不是有难一人当。
但联合国和西欧国家对这些压力显然并不感同身受,波兰反而被指责没有以相同的热情接待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和其他试图跨越白俄边境森林进入波兰国境的其他难民。
事实上,全世界并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站出来指责波兰此刻的各种要求。因为,作为一个东欧边境国力并不富强的国家,迄今为止波兰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接纳的总和。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