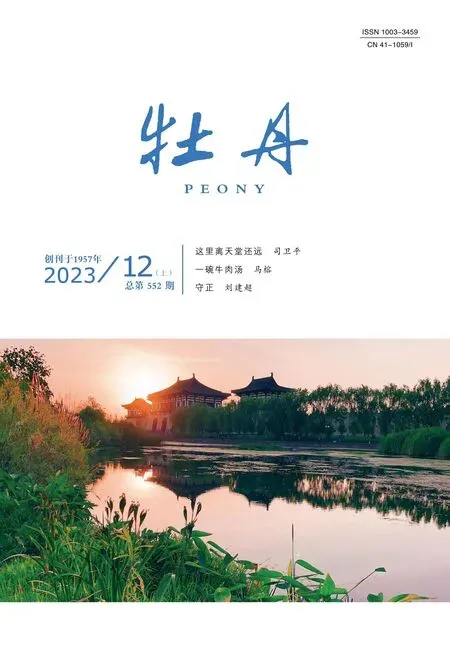蝶恋花
2023-02-16梁树欣
梁树欣
一
她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夸赞长得俊俏,大眼睛,双眼皮,鼻梁不高,但显小巧,眉毛浓淡相宜,像是颜真卿最擅用的长横。
每当过年走亲戚,她扎起辫子,搭在两肩,红绳绑在辫尾,一手挎着篮子,一手夹紧新做好的红棉袄,辫子随着脚步,在肩膀上蹦蹦跳跳。一路上,聚在瓦屋门前的长辈会不时传来一阵低语,说,这是老街东头家的闺女,你看长得多喜欢人。每当声音跃到耳畔,她会侧着头,小跑似的离开,红扑扑的脸颊,不知是害羞的颜色还是街口风太寒的缘故。
上学时,奶奶会给她扎起马尾。她最喜欢奶奶给她梳头。爷爷眼睛不好,是个高度近视的老知识分子,读书都要拿着放大镜趴在纸页上,手上的老茧也厚,梳头常常拿捏不好轻重,而奶奶不仅手暖和,而且会边梳头边夸她,夸她头发又黑又多,扎起后捧在手上,粗粗的,沉沉的,饱饱的,最后,奶奶把从县里带回来的蝴蝶结卡在她头上。她觉得自己是比露水还要新鲜的一朵鲜花。这是童年的她对幸福一词谙熟于心的理解。
她背着奶奶缝的挎包去了镇中心的学校。
她是班里人缘最好的,老师们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写字一笔一画、上课坐姿端正的女孩的喜欢。但人缘好不代表身边一定比别人热闹,男生们往往羞于在人前谈论她,抬头瞧她都要鼓些勇气,当她出现的时候,那些本就热闹的男生会变得更热闹,但他们不会设法把这种喧闹牵扯到她身上,只是不时有余光蜻蜓点水似的落在她身上,男生在看她是否因此抬头。女生看到她头上的新蝴蝶结,喜欢围着她询问来处,在黑绿蓝盛行的年月里,只有她身上常常会点缀那么几处斑斓,像是黄土世界里一抹新鲜的亮色。每周的升旗仪式,女生除了注目升起的国旗,余光总要落在她的蝴蝶结上,看看这次又换了什么颜色。当歌声渐隐,国旗飘驻于杆顶,女生便心安理得地观察起她的发卡,像是在端详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他们与她一同成长,可她常是漂亮而又新鲜的,衣服并不崭新,但洗得干净,像山林里的蝴蝶,生于此长于此,看着大方且得体,美得独特且祥和。
那时,人们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以及他们的父辈都在为在土地上盖起新房而耕作,人们刚刚知道去外地打工能挣大钱,但真正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人在一个镇上都屈指可数。不知不觉间,人们对土地逐渐埋下了一丝倦闷,人们喜欢用骂谁“土”来表达自己除了农耕外为数不多的攻击性。但男生不会说她土,除了她从不与人置气外的性格外,也和她家的住处有关,镇西的老街是每逢露水集时最繁荣的地段,而她家就在那条老街东侧。
在她上学的日子里,当然受过委屈,但校里校外从未与人置过气,有一次,奶奶擦着她头发上已经干硬的泥浆,拍着她脏兮兮的衣裳,问,阿珍,你这都不会生气吗?她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一边哭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黎明,天边的霞光初露头角,她跨上昨日黄昏便已收拾好的书包,辫子一跳一跳的,一如往日,干干净净地去了学校。早上的霞光并不刺眼,但升起得很快,黑夜尚未散尽,像彼时的黄昏一样欲拒还迎,她的大眼睛像是一面镜子,迎接阳光的同时也会折射阳光,她总会把自己收到的温暖倒映给旁人。不论这阳光似夏日那般盈余,还是如冬日那般稀少,她像大自然对待万物一样收放自得,容纳黑夜的同时会给黄昏留有余地,看到嫩芽后依旧会对枯叶一视同仁,她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人生中的风雨。她此后的人生中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风浪,但她赠给别人的彩虹早已不计其数。
她的气质与这个小镇大体相像,但总不尽相同,不像祖辈那样斤斤计较,也不似同龄人那般好大喜功,她的性格有着不言自明的颜色,不像土地一样紧绷,也不似井水那般松软,而是像雪花一样绵延跌宕,与湛蓝色的天空相得益彰。
高中毕业后,她没考上大学,在乡镇小学当了老师,在教书的第三年,经媒婆介绍,被一个穿着破衣服、推着破自行车后面还驮着个破柴锅的年轻人娶回了村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相亲,也是最后一次。男生大她四岁,中专毕业,头发有些自来卷,但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乱蓬蓬的像是个鸡窝。两个人一起去了镇北的油菜田,去了县南的城湖。几个月后,他们搭了一辆长途客车去了洛阳城,从黎明颠簸到傍晚,当她踩着发软的脚步下车时,看到了客车两侧溅满的泥浆。在龙门石窟,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山。
最后,他们回家去看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媒人。他们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嫁妆,也没有大操大办的酒席,男生买了新自行车把她驮回了五公里外的村庄。多年之后,村头那个苍老的媒人还常念叨这对顺风顺水的新人。结婚之后她依旧在镇上教书,男人去了外地挣钱,天南海北地跑过麦种,昼夜不停地跑过大车,既在城市的霓虹里卖过水果,也在一无所知中误入过传销,最后,从工程测绘员开始,一心一意地搞起了水利。
夏天的蝉一茬又一茬,冬天的雪一阵又一阵,立春前村口的寒风依旧刺骨,惊蛰后墙根的嫩芽准时破土。小满已过,夏日又长,林叶悠悠,秋后落黄。
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奶奶死了,刚刚在她锄地的时候,脸颊上似乎还含蕴着奶奶手掌的余温。她放下手头的活儿,草草盘起头发,在回娘家的路上已然泪如雨下,奶奶早已不能坐起给她梳妆,她月初回镇上时,还将奶奶的手心贴到自己的脸颊上,说下次赶集再来看你。她虽然早有预感,可以往那虚妄的预兆却坠破了如今真实的生活,那双松松垮垮的手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攥紧,到了娘家,尚未娶亲的弟弟站在屋外正擦着眼泪,她进了屋,看见奶奶的身体还躺在床上,本来静悄悄流淌的泪水,眨眼间泣不成声,泪眼蒙眬间,她看到,奶奶像蝴蝶一样飞远了。原来死亡就是永别的意思。丧事过后,她骑着婚时的自行车,回到了五公里外的村庄。
风吹麦田,麦子高低起伏,像正泛起波浪的大海,虽然她从未见过海。
二
自从她嫁到这儿,村里的人都夸这家老三娶了个俏媳妇,又漂亮又孝顺,还是镇上的。那年乡镇小学改革,学校把非师范的老师聚在一起,说交一万块钱就可以转正,她放弃了,觉得自己学历低,也不是科班出身,才不配位。
离开学校后,她便安心留在村庄里,陪着不识字的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总在人前人后夸她能干,说她除草耕田,养牛养鸡,洗衣做饭,干得比谁家媳妇都好。
第四年的深冬,墙头的老树刚刚抖落枝头第一捧雪花,她怀孕了。
妊娠前,男人从工地回来,她到县医院,生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这个八斤重的婴儿,衡量着她此前每一个朝暮重叠起来的重量,她的脚步从此不再指向自己的未来,而是踏在另一个生命前进的路上,她用此后那个寸步不离的身影来告别那个喜欢蝴蝶结、喜欢奶奶给她扎头的少女。
孩子出生后,男人的工作逐渐稳定,随着公司的迁移,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落了户,单位分了房,凑足了首付,稍作装修便赶忙让她搬来。第三年,她第一次坐上火车,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搬到了百公里外的这个家属院,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楼房。
家属院往北一公里是市中心,往东三百米就是京广铁路线,火车声在她的耳畔日夜不息。她开始以全职主妇的新身份来与这个城市互动,与自己的生命互动,与生命中的另一个小生命互动。很快,她能驾轻就熟地穿梭在菜市场和红绿灯之间,卖鱼的、卖肉的、卖鸡蛋的、她把各家小贩的价格了然于心,谁的质量好,谁的价格贵,几点的时候菜最新鲜,几点的时候菜农会把卖不尽的低价处理,她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比教师的职业更需要深入细致地学习,城市与乡镇比起来,在这儿的每一处生活都需要肉眼可见的开支,她开始记录一天的每一笔支出,百元的稀有,千元的罕见,本子上大多是一块四一把的生菜、三块五一包的十三香、八毛钱的绿豆芽,超市小票里的几分钱也不落下。除了儿子穿小的衣服和穿不上的鞋子,床头的几本日记就是她与生活朝夕相处的全部记录。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八年,八年后,六层高的家属院在拔地而起的建筑群的映衬下已经不算是高楼,儿子变成了初中生,她从全职主妇变成了小面馆的老板娘。
六个月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去了距家两个路口远的幼儿园,她开始拥有少许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买了辆自行车,到路南的烹饪学校学习做饭,从素菜开始,再到蒸煮焖炖,她都记在了笔记本上,不过,厨师教煎炸的时候她刻意回避了去,不是与接送儿子的时间相冲突,是她觉得油炸的东西不好。
华北平原上的四季,各地相去不多,只是那些在异乡和家乡两个概念的中折返的人,情绪不免此消彼长。夏季的闷热和冬天的刺骨逐渐被衬托得有所不同,相比于农村的淡烟流水,在城市里寻阴纳凉都成问题,相比于城市的见多识广,农村的不成体系也难值一提。她喜欢玫红和橘黄,先后买过一条红色的长裙和一件黄色的棉袄,她开始戴起发箍,她最喜欢那个两指宽窄、淡粉底色的布制发箍,上面有一圈透明小钻,小钻在太阳下跃起的阵阵光点,是她三十岁的见证。
昼短夜长,昼长夜短,从柳树缀出新芽,再到银杏面掩鹅黄,日落而息的生活已从她生活中淡去,她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日夜,不远处传来的火车声也不似最初那般刁钻刺耳。她送儿子上幼儿园时的动作不再那么紧张和僵硬,儿子松开她手掌的瞬间也逐渐变得稳健且果断。
日子像火车一样过了去。儿子上了小学,学校在离家三个路口处,她与这座城市的节奏逐渐变得如榫卯一样契合,厨艺也小有所成。她让儿子中午放学时和同学一路回家,要求儿子不能吃垃圾食品,但儿子时常会在到家之前把辣条或者冰糕吃完,有时一进门她便会闻到一股辣条味。她想了一个办法,闻不到味时就抓起儿子的小手嗅一嗅,儿子常会心虚,惨叫着把手缩回去,跑到卫生间洗手,接着耀武扬威似地把手重新伸回她面前。
周末她会带着儿子去半截河玩,初春时最为频繁,一早便骑着自行车,车篓里放着昨夜准备好的风筝和吊床,坐在后座的儿子唱起音乐课里学的歌,但他规矩地唱一会儿便觉得无聊,转而背起男生间口口相传的顺口溜。
到了半截河,自行车扎在一旁,她寻两棵间距合适的树把吊床系上,小男孩玩累了,在包里找出口琴,笨拙地吹起《两只老虎》。断断续续的乐声并不让她烦躁,她和儿子一同俯下身子,观察枯枝上透出的绿芽,半截河沿岸全是柳树,远看时,隐约间蒙着一层绿色,但到了近处,却发觉柳枝与入冬时模样并无二样。这似有似无的绿似乎是氤氲在树皮之下,像是即将长大的小孩,铆着一股劲儿在生机肆意的春天里博得自己的领先。一周一周的,渐渐地,儿子脱掉一层层的衣服,也看到了正绽放生机的万物,感受到春天来临时那静悄悄的步伐。夏天时,儿子在林中的小路上奔跑,对着那座有着南水北调标识的高桥呐喊,刺耳的蝉鸣给他和着节拍,儿子在河边打水漂,像她小时候一样。有一天,儿子把头枕在这座桥的栏杆上,两岸的柳树倒映着微风的模样,他挺直了腰,说,妈妈的头发像春天的柳树。
又过了几年,儿子到了小学高年级。有一天,她发现儿子在偷拿衣柜里的钱,想到自己先前不时会在家里找到一些玩具,她开始注意儿子背着她在学校门口买玩具接着偷渡到家的行为。那一天,早晨细雨朦胧,清早如傍晚一般昏沉,雨落得又急又密,像行人匆匆的脚步。儿子穿着五色雨衣,和她在入校的拐角处挥手告别,这条路名叫育才路,小朋友们会沿着这条路径直入校,她往往和其他家长一样在此止步,而这次她想看到儿子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她猜的没错,儿子不时回头,拐个身子进了路对面的小卖铺,她匆匆合上雨伞,三步并作两步,在儿子从雨衣兜里拿出被水微微打湿的一张五十元时,拧住儿子的耳朵,她抢过纸币,攥在手里,儿子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说,你站着干啥,现在给我上学去,回家再跟你算账。儿子走出小卖部,再一次汇入戴着红领巾的孩群中,儿子走得缓慢,背影像是要奔赴刑场。她注视着儿子越过保安身前,踏入校园,而后雨已将她的刘海尽数打湿,她撑开伞时,发觉纸钞已被她攥成再难展开的一团。
她的白头发似乎是从那一年开始长的。
后来,她又发现儿子偷拿她钱包——一个泛着黄斑和黑渍、皱巴巴的塑料袋子——里的钱,那晚,她把儿子在床底、被褥下藏的玩具悉数摆在客厅,各式各样的模型,有逼真的袖珍摩托,有兰博基尼和布加迪,问儿子买这些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儿子眼神躲闪,沉默不答,每当她音调升高,儿子胸膛总会一抖。她当着儿子的面,举着实木板凳,把一地玩具砸得四散而飞,儿子终是不忍心看着玩具一夜尽毁,说,妈,我再也不偷偷拿钱了,我错了,你别砸了。她看着儿子,把板凳扔到一边,在墙角处碰出噔嗵一声,跟疯了似的,把所有本该向儿子发的火一股脑地撒在自己身上,她好伤心,说,都怪我,没教好你,把你教成了个小偷、教成了个贼。说着一个巴掌扇到自己脸上,接着又是一巴掌,她打着哭着,儿子崩溃了,大哭着扑过去,撑住她扇向自己的手掌,大喊,妈妈你打我吧,你别打自己,你别打自己。儿子双手握住她的手腕,想让耳光落在自己脸上,可根本拗不过母亲惩罚自己的力气。儿子哭着跪下求她,她停下,将脸别过一旁,情绪上的抽噎依旧继续,胸口起起伏伏满有皱纹的眼眶已是通红,大眼睛里血丝连片,像是红色的蜘蛛网,儿子哭得喘不过气。她红色绒袄在腋窝处露出棉花丝,是她第一次去洛阳时买的,如今也染上了为人母的憔悴。
自那次起,她开始爽朗地给儿子零花钱,儿子对于钱的举止也逐渐落落大方。
三
儿子六年级时,刚刚在外地干完南水北调支线工程的男人回了家,本处事业上升期的他刚得几日清闲,工程验收时却出了问题,坍塌事故造成民工伤亡,上到分公司老总下到男人这种职员,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惩罚,几个主事的领导有的贪污受贿被抓进了监狱,有的因挪用公款而倾家荡产,有的因知情不报而受到牵连。男人算是幸运,也算不幸,被吊销了到手没几年的建造师证书,原本事业蒸蒸日上的他一下成了无业游民。
等到儿子小学毕业,男人和她商量,托关系把男孩送到市区边缘的一个寄宿制初中,一周回家一次,男人把这些年挣到的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买了一辆五菱面包车,一部分拿来租了个四十平方米的店铺,加盟了家热干面馆,算是开了个夫妻店。她的身份也从全职太太转换到了个体经营户,自她成了老板娘起,她头上只留下了两样装饰,一是黑色皮筋,二是白头发。
前两年,生意不可谓不红火,中午和晚上两个饭点,小店里挤满了顾客,她在外面记账收拾碗筷,男人在里屋煮面配底料,两人前脚赶后脚,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是夜里十一点还有生意,待到收拾好一天的碗筷,凌晨时能回家已是少有。每夜她都会把当天一口袋零钱瘫在客厅,数出一日的营业总额,再减去早晨的本钱,一天的收入便出来了。
那段日子,晚上男人总说起他的独到的眼光和明智的决定,饭店的生意来钱真快,没等男人说完,她便已沉沉睡去,男人也累,连夜里打呼噜的余力都没了。
小饭店能挣快钱,可快钱不意味着可以稳定增收,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小饭店所依托的有两类客源,一是对面中学的学生潮,二是附近百货批发市场的路人潮,然而中学在那一年改为食堂集体就餐。与此同时,电商出现,网购兴起,批发市场的客流再不似先前那般人满为患。
小面馆第二年生意便不如第一年,当男人看到面馆盈利的上限时,他对体面的在意逐渐从金钱的短暂夺目中闪出身来,一过饭点便回了家去,再不复最初的热情。晚上收摊时免不了抱怨这日薄西山的生意,身边的朋友听闻科班出身的男人正在以卖面条为生,话里话外都是说他屈才。男人的焦虑占据了饭点忙碌之外的所有细节。逐渐,小面馆里收钱和煮面都成了她一个人的事。
半年后,男人经朋友介绍跳槽到一家国企,进入事业的第二春,相比于男人上一份工作的坎坷,这次春天来得更舒展些。
这时,她七十岁的母亲去世了,听闻噩耗,她和住校的儿子打过招呼便赶回了家。
母亲患上脑出血已有七年,第一次脑出血之后便不能说话了,像一块喑哑的玻璃,后来情况恶化,头上数次开刀,左脑一侧有着明显的凹陷,看起来像是大雨过后被碾过的泥坑,摸起来像是一个蒜臼。随着病情的反复,玻璃上的裂纹已如蜘蛛网一样密集,母亲的死亡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如今,母亲呼出的最后一口气随着镜子碎裂的齑粉一同向远空荡去。她看着火化后的母亲被装在棺材里,用钉子钉固四周,埋入土里,成了华北平原上千万的千万坟头之一。坟西种了棵松树,坟东种了棵柏树,那棵万年松是她亲手所种,那棵柏树是她弟弟栽上又培的土,曾经母亲膝下的一子一女,如今的鬓角都已猝不及防地添上了白发。
她在家住了十天,直到丧事忙完,收拾好情绪,黎明一如既往地铺在眼前。
到了城市,她正式开始一个人经营小面馆。早上起来骑着自行车去面条铺买热干面,后面驮着硬纸箱,去菜市场买葱蒜,到店里,先虚掩卷帘门,把纸箱子卸下,在门口摆出禁止泊车的路障,再拖地擦桌子,配足能应付晌午客流的料碗,最后将卷帘门彻底抬起,打开门,迎接第一位客人。当她起身目送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收摊时,常常已是凌晨。因为店里只有她一个人,客人再少也显得手忙脚乱。
热干面馆来到了第三个年头,智能手机普及,扫码支付开始流行,彼时她还用着按键手机,思来想去终究没有下定买新手机的决心,只是将男人的收款码放在店里。她对这种新事物的兴起并不信任,可她口袋里能数出的收入越来越少,不知从哪一天起,她晚上不再细数当天的收入。
儿子擦着分数线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这是她开面馆的第四年。
这时,电商开始崛起,人们尝到了网购的甜头,周边饭店赖以生存的百货市场主顾们一个个另寻出路,市场里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自己的商铺尚且难以为继,租房做生意的小商小贩更是如坐针毡,她看着恒定且冷寂的房租,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大不如前了。
小饭馆的命运就是,越红火时越红火,越冷清时越冷清,刚开店时一早便会摆出去的折叠木桌,已荡上无心擦拭的灰尘,酒架最高层的那几瓶牛栏山依旧是那几瓶,空调的温度也没有先前那么精准,夏天不够凉,冬天不够暖,当店里没人时,她一人也不愿再开上空调,当人来时打开,空调的风尚未吹满屋子,客人便吃罢离开。
她是最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当她为门可罗雀的饭店而忧心忡忡时,疫情来了。
她在家里陪着即将高考的儿子,近半年足不出户,小饭馆的生意彻底停滞,每个月的房租却是一分不少。半年后,儿子成年,考上了大学。她把饭店重新开张,然而人们习惯外卖与网购,稀少的客源让她度日如年。
最后,在男人的催促下,她把面馆里的电器和餐柜一并变卖,当钥匙交回到房东手上时,房东说,你要是继续租的话,咱们房租可以降一降,她心里突然颤了颤,似乎有一肚子话想要急促地倾诉出来,可她不知从何说起,就像一根粗大的毛线找不到那处微小的针鼻,她匆匆换了话题,窘迫地与房东告别。
那晚,她从面馆里最后一次走出来,把卷帘门放下,没有上锁,扶好白天被风吹倒的自行车,踢起脚蹬,拿绳子把买菜的纸箱子拴在车座后,箱子里放的是她收拾出的最后一批杂物。
她朝着相邻的几家店铺顿了几下,一同做生意的街坊如今已经换了几茬,还留在那里的只有一家夫妻打印店和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饸饹面店。她最初的邻居是一家大脸鸡排,开店的是个胖乎乎的女孩,没生意的时候总会跑来笑嘻嘻地喊她姐,长得又可爱嘴巴又甜,她只能那么喜欢这个鸡排女孩了。
鸡排女孩和她相处久了,逐渐感受到了这个中年妇女的一尘不染,女孩嘴边最常挂着的话就是,姐,你咋那么好啊,我没见过比你还好的人。女孩常常跟她吐槽家里人又怎么数落她,一会儿说她没出息,一会儿说她嫁不出去。这几年,她帮鸡排女孩介绍过两个对象,不过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前年的一个中午,鸡排女孩给她掂了两份鸡排,说门面转让了,不干了以后,准备回家考县里的公务员,找个稳定些的工作。
她回过神来,眼睛有些干涩,打了个哈欠后,方才察觉风中已稍稍掺了些凉意,她告诉自己,以后再不开饭店,累死个人,就算有的那点好也都过去了。
想了一会,她似有似无地把刚刚的自己否定,心想,好什么好。
那晚的路灯把她映得忽明忽暗,影子起起伏伏,她推着车,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在后背一起一伏,马尾蓬起时,能看到后背上被汗沁透出了不规则的一块,在灯光下变了颜色。在脚步的一路探照下,她打开家属院早已紧闭的铁门,吱嘎一声,在深夜像火车一样悠远,像是有一滴水落在了她的眼睛里,眼神轻轻漾出几尾波纹,如月光一样空明。
到家后,打开灯,她意识到,小面馆和她老板娘的角色一样,再也不会亮起,她要告别这段人生,她在社会上唯一的身份湮灭在这一片黑色里。
干生意的那些年,她对经过耳边的火车早已不再有情绪上的起伏,火车早已像红绿灯一样平等地存在于她的生命中。儿子上大学,逐渐明白事理,时隔三年才给父亲道了歉。父子和好,是她抛开小面馆之外所获得的唯一圆满。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常常是几个月不回家,随着成年,他的骨架已经长开,后背和肩膀逐渐宽大了起来。男人四十而立,事业比之先前已经是有所为,单位从省会迁到天子脚下,她属兔的,想来也到了不惑之年,可这不惑之年却给她带来无止境的困惑。
饭店不干后,她赋闲在家,再次感到火车经过时床板和沙发的微微震颤,每每如此,她常会感到自己心里的不安,像铁轨一样,虽然坚固,但却颤颤巍巍。她不知如何向自己解释这一无是处的生活,这忧心实在是无稽之谈,只是隐隐觉得,她的不安似乎来得有理有据,像在肠道里不时渗出苦水,让她心神不宁。
她守着空家,其间找过零零星星的散工,工作并不繁重,但她一日下来总是身心俱疲。
这样的日子捱过了一年,她的头发愈来愈白,头发掉得越来越多,稀疏的刘海根部已经露出明显的滩涂,鱼尾纹和黑眼圈愈发沉重,沉重得每晚都把她拉入梦中,拉着儿子的小手,站在小面馆门前,向络绎不绝的客人一遍遍地解释今天饭店关门,歇业一天。
她早已告别年轻,或者说,现在就是她最年轻的时候。如今她依旧是美的,是不出彩的漂亮,是不显眼的整齐,是一种疏松的美,如她这半生一样,既没有灯光舞台所渲染的华丽身姿,也没有浓妆艳抹所铺陈的精致五官,大眼睛里虽然有了些杂质但并不浑浊。她能看到自己,是孙女,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是一个经过半生的自己。
四
入秋时男人回了家,趁着中秋节,开车带她和儿子回到镇上的娘家,昨夜到,明天走。
黄昏时她去到母亲的坟前,买了三刀黄草纸,拿百元钞在纸上比着压了压,拿指甲在黄纸表层理了理,引燃后,往火焰上三张三张地添,她不停地说,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妈,你妮儿回来看你了。
焰心一时旺一时垂,火苗一时高一时低,火舌像在吞吐着什么,不时传来枯叶燃烧的噼啪声。有的灰烬留在地上,有的灰烬漫在空中,像是一个女人飘荡着的凌乱白发,单从头发看,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样憔悴。
姐弟俩在坟头两侧各自种下的松树和柏树在夕阳的掩映下微微摇动,一同摇动的还有她现已稀疏的刘海,喷过啫喱水的刘海一绺一绺地曲在前额,看着畏手畏脚,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弟弟种的那棵柏树已经长得能供一人纳凉,而这万年松早已不是她最初种下的那棵,这些年里,万年松种上又枯死,枯死再种上,就是种不活,这棵万年松弟弟刚刚帮她种上一年,尚未见枯萎的迹象。
两棵同时种上的树如今却大相径庭,种不活的松树像是母亲对自己的惩罚,她望向四周的百亩良田。一马平川的田埂一眼可以看到天际,赤红的晚霞将视野尽头的座座坟包染成铁锈的颜色。看着别家老人坟前宽大的树荫,一派生机勃勃,像是秋收万颗籽的景观,她不由得悲从中来。想到妈妈生前吃了一辈子苦,死了也没有享福的命,她大哭道,妈,你不让这树活是不是怨我嘞,说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阿珍咋还不来?咋还不来哎?咋还不来哎?妈,你别生气了,我来看你了,你让它活吧……此时她像是一个请求母亲原谅的女孩,脚尖朝内,双手垂前,因为犯了错误而委屈地抹着眼泪,眼眶通红,眼球里的血丝像是在晚霞里浸了浸,眼袋像是装上了露水的重量,显得沉甸甸的。在她哭泣的时候,风把面前的松树吹得摇了摇头。
纸钱烧尽了,远处的残阳吐出最后一抹余霞,穿过树枝,越过田埂,在她头上织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最后,余晖散尽,坟前的最后一粒火星在黯淡的空间中隐去。
天空步入了夜晚,平原上处处困闲,人们一边相聚一边永别,目送着一道道血脉承转尘间,在与某种存在分离的同时,迎来某种心灰意冷的希冀。
晚上她睡在母亲曾长久卧病的床上,枕头里塞的是碎麦秸,一翻身就会有浅浅的声响。在梦里,她梦见头痛的母亲在深夜里磨牙,看到自己小时候睡觉的模样,身体里生长的骨骼正在悄悄作响,夜里总觉得发寒,似乎有露水下在她身上。刚入秋,夜变长了,但也没有愿想中的那样长。等天胧亮时,她终于把被窝暖热了。
太阳起得很早,一点一点地驱散露珠余下的寒气,母亲说她不疼了,她的骨骼也停止了生长,街上传来稀疏的鸣笛和轮胎的摩擦声。她起身做饭,一米六二的身高,和大腿高的压水井有着血脉相连的默契,几间苍老平房上跳跃着清晨的阳光,红底黑墨的福字将门框衬得更低了些。她侧着身子,提着晃荡但不溢出的水桶进了厨房,阳光还没投进屋里,暗涌的朦胧色正缓缓将她的背影隐去。
晌午要离开时,她匆匆忙忙地检查行李,检查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有什么话忘了说。男人边与岳父寒暄边打开车门,突然从副座飞出一只橘黄色的蝴蝶,拍打着羽翼,应是昨夜不小心飞进来的,在车里懵懵懂懂地徘徊了一夜。这蝴蝶飞过熙攘的一家人,忽快忽慢,像是心中七上八下,最后似要停驻在她的头上。男人见状,伸手赶了去。儿子注视着这只略显突兀的蝴蝶,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从未见过。她看着蝴蝶一点点飞远,看着它跌跌撞撞地飞来,又举棋不定地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