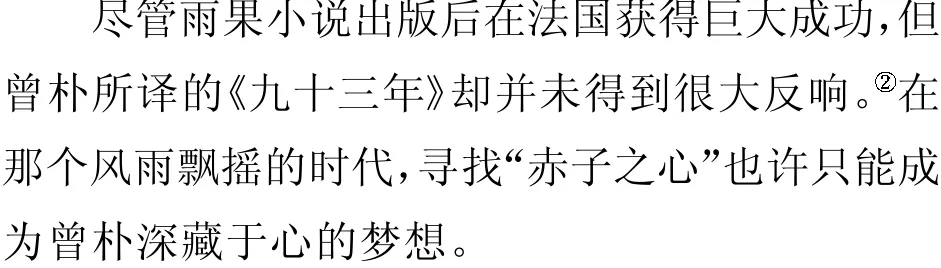缺失、渲染与隐形:曾朴译雨果小说《九十三年》的艰难抉择
2023-02-14张香筠
〔法〕张香筠
(巴黎大学 东亚学院,法国 巴黎 75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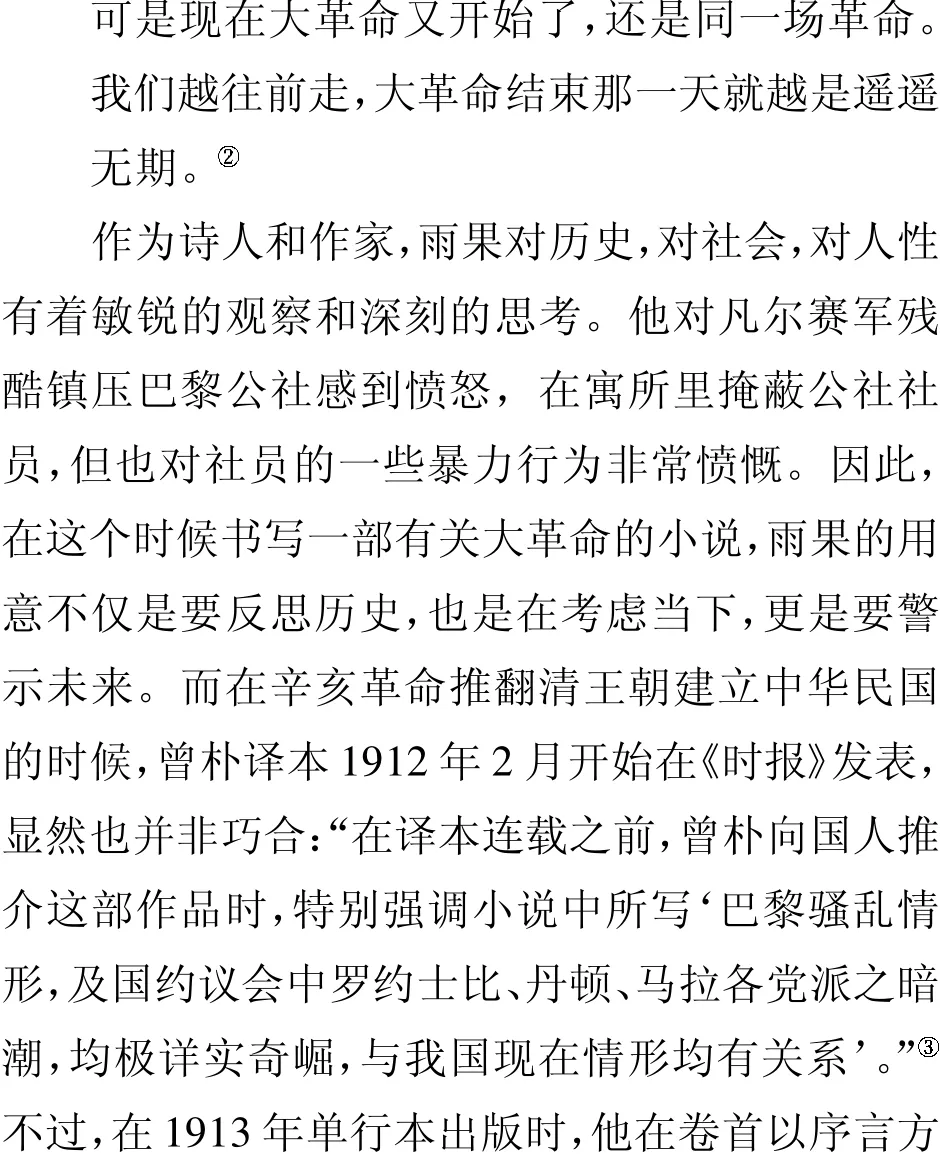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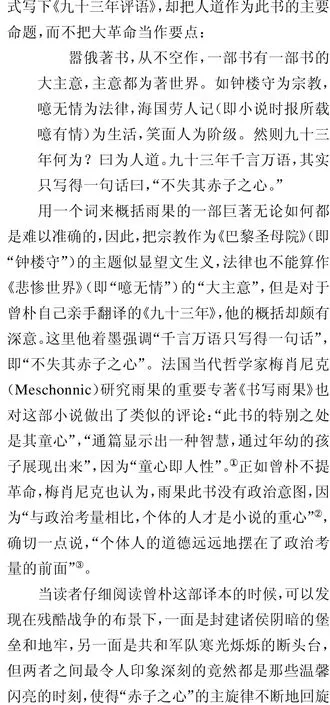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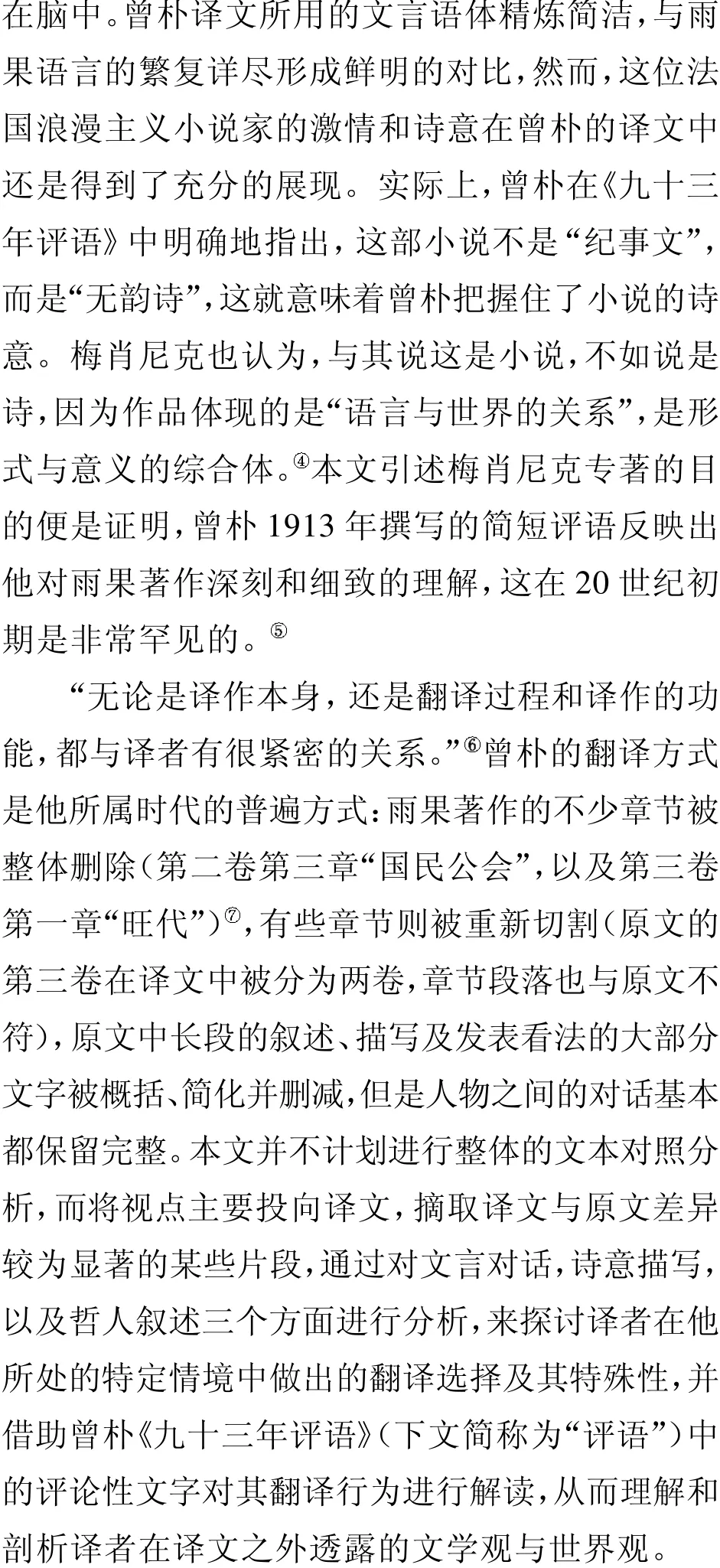

一、语言的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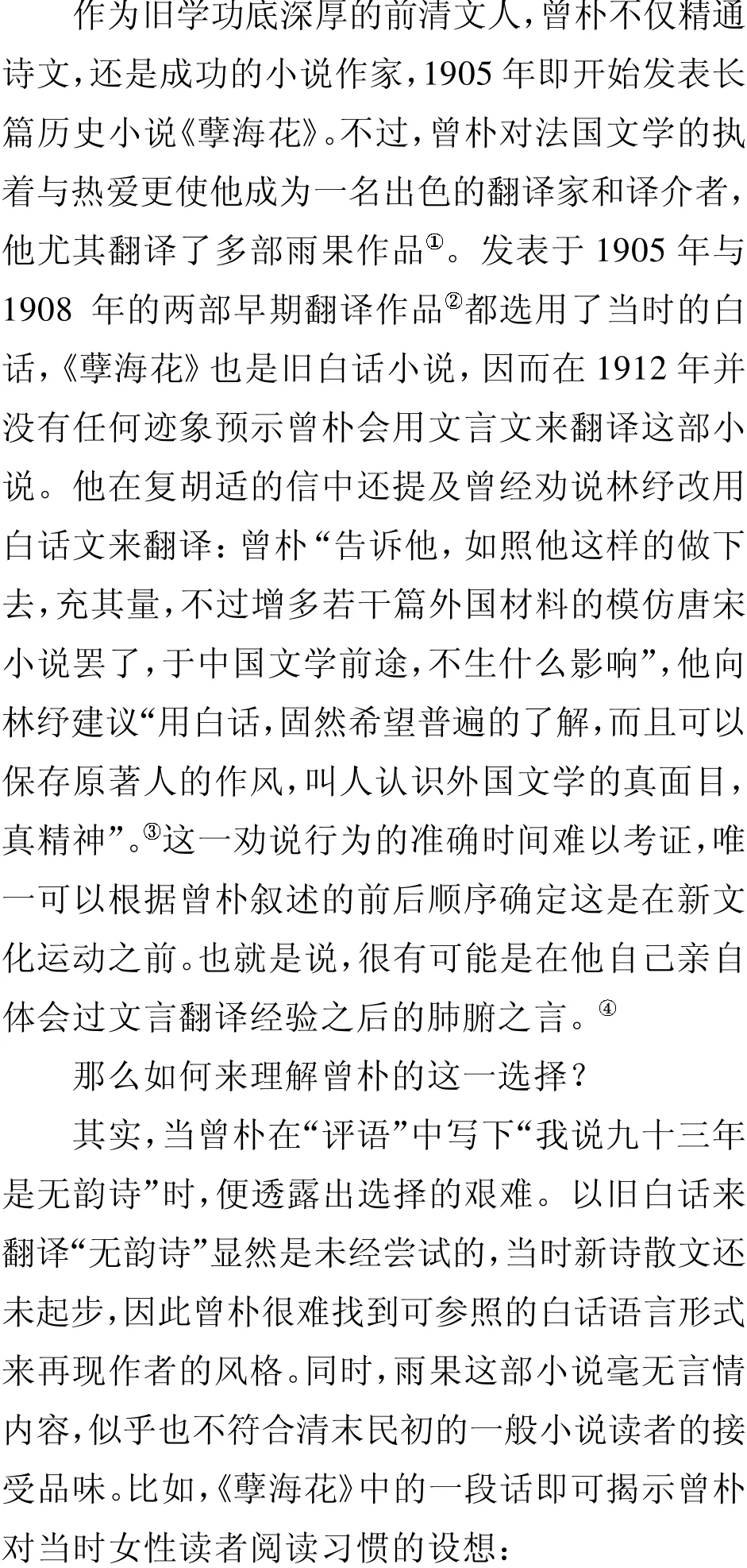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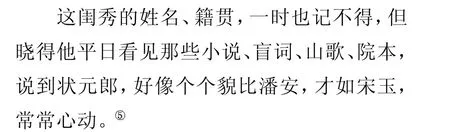


然而,这一选择却意味着悖论的产生。正如曾朴“评语”中强调,“九十三年何为?曰为人道。”因为尽管小说的题材涉及政治,但作者在书中塑造了好几个人物都对政治一无所知:如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农妇佛兰宣(Fléchard),还有她的三个孩子,以及乞丐戴麦客(Tellmarch),都像是战争场景中的局外人。在雨果笔下,他们代表着单纯的自然,与纷杂的社会、政治,甚至与书籍和文化都格格不入。而文言文作为一种只用来书写的语言,从本质上就是远离自然的,它象征的是书籍的世界,是政治与社会。因此,原文中生动活泼的童言,在译文中变得老成凝重,像一板一眼的台词。如三童嬉戏一节,当孩子们听到远处的铃声炮声链条的声音此起彼伏时,作者描述四岁的男孩仔细聆听,觉得很美,像天籁之声,他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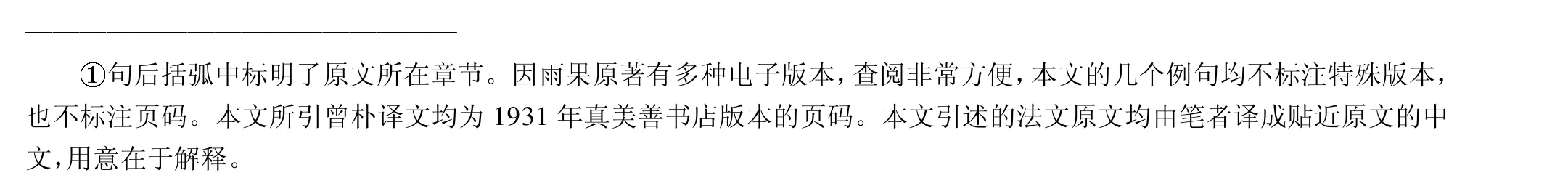
法文这一句不仅用词极为简单,最明显的是包含一个用词错误。Dieu(上帝)一般是作为专有名词使用的,但由于日常用语中人们常在各种感叹时说mon dieu(我的上帝),孩子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词,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于是说成了le mondieu(那个“我的上帝”)。这个错误是小说家有意呈现的,这使战火中无人照顾、无人教育的幼童形象更为真切可信,但这一点在曾朴译本中消失了:
若望且听且鼓其掌,欢呼曰:“是乃慈主作之,以悅吾曹者也。”(1931, 225)
孩子的文言句子极为完整,甚至添加了“以悦吾曹者也”来解释前半句“慈主作之”,使得前后逻辑严谨,而儿童的天真无知荡然无存。
稍后,雨果原文也对一岁半的女婴,咿呀学语的饶善德(Georgette)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尤其模仿了幼童的发音方式,强调孩子还不会组句。在译文中,此类词句有的被删除,有的则以音译的方式试图保留。例如饶善德听到窗外的军号声,喃喃自语“misique”,即为作者有意将musique(音乐)一词误写,以示幼儿发音不够准确。曾朴译为:
口中则唧哝曰:“妙!妙!西客。”盖其欲言密西克而伪其音。(“密西克”译言音乐。)(1931, 221)
由于采取了半音译的方式,就出现了“妙西客”三字,尽管将“妙”字重复了两次,似模仿幼儿说话的效果,但在中文语境中还是很难想象的。于是,后句“盖其欲言密西克而伪其音”,以及句后括号中的“密西克译言音乐”可以相当于译者的注解,来解释音译的两个词语misique、musique 的相近与不同。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对于曾朴来说,此处的幼儿发音错误模仿对于段落整体理解并不会形成障碍,鉴于文言的限制,翻译中做出如上取舍无伤大雅。
但是雨果在这一章节不惜笔墨地对年幼的饶善德再三进行刻画:不仅模仿了她的发音错误,也使用了某种句法错误。例如,在饶善德从小车里摔下来要哭的时候,哥哥告诉她摔倒的原因是她太大了,于是小女孩儿重复说“我太大了”,这里雨果便用“J'ai grande”来模仿法语儿童语言中一个常见的错误,即混淆助动词的现象。其实这一语言错误并不逼真,并非细致观察幼儿学语的真实记录,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不到两岁的幼儿很难使用代词“je”(我),而且话中重复的内容也与上句哥哥的话不太相似,所以此处对话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想象,但不可置疑的一点是,这一语言错误足以显示儿童话语的存在。可是,译文则完全无视幼儿话语的特征:
饶善德亦仰而踣,张口欲啼。若望即慰之曰:“令娘过长成,小车不能载矣!”饶善德曰:“我已长成耶?”言时,顿敛哭而笑。(1931,227)显然,饶善德重复了哥哥若望所说的“长成”一词,但改换了主语,并改换了副词“过”,代之为“已”,文言文的疑问助词“耶”更使得话语逻辑清晰,语意完整,不具有童言稚语的性质。
同样,雨果笔下的农妇佛兰宣,数月奔走寻子,历尽艰辛之后,看到三个孩子被困在大火之中,她发出绝望的呼号:
Oh!s’ils devaient mourir comme cela,j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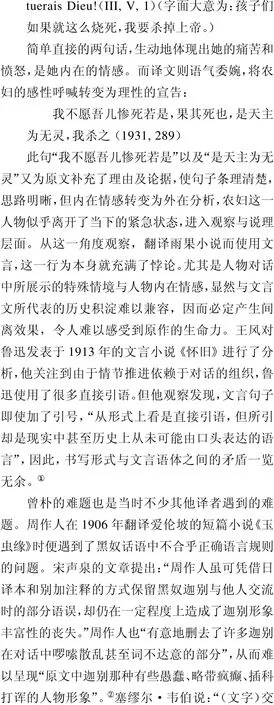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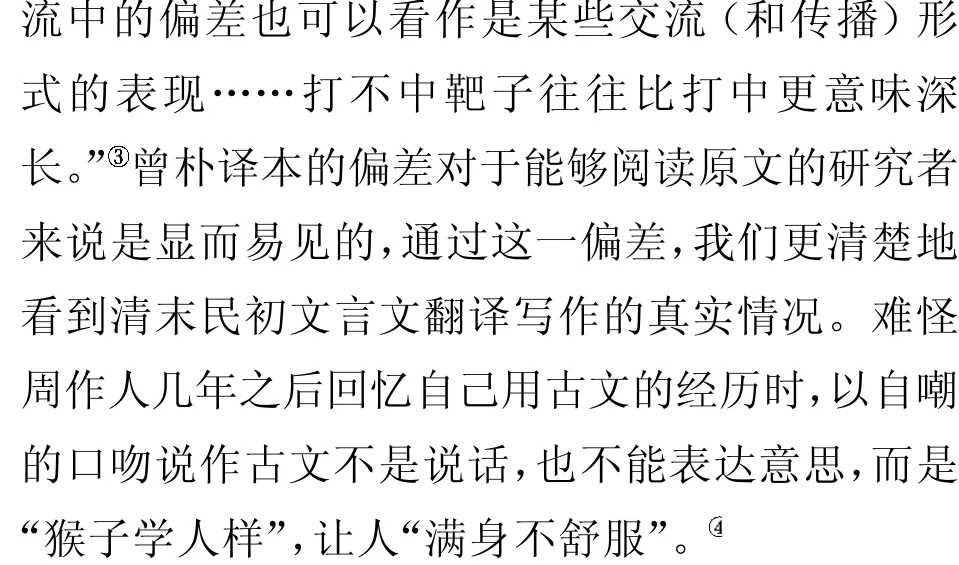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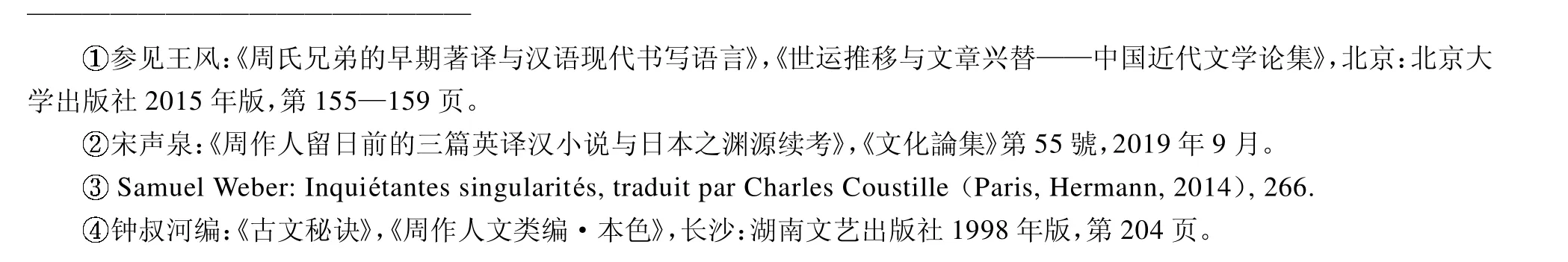
二、诗性与情感的渲染
尽管文言文翻译难以活灵活现地反映人物语言,但曾朴的译文却并不因此使小说落入死气沉沉的晦暗之中。因为正如译者在“评语”中已经表明,“九十三年是无韵诗”,雨果小说的诗性光芒是曾朴特别重视的,也是他从始至终尽力呈现的。
旭日升矣。童子醒矣。夫童子乃人类之花也。其睡也如花之合。其醒也如花之开。星眸乍展,恒若有冉冉温黁,渗漏于醇白之灵魂中,令人挹之不尽(1931, 217)。
此段描写节奏明晰,用词简洁,相比原文只有“花开”的一处比喻,译文添加了“旭日”“人类之花”“星眸”等多种图像,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一种大自然的明亮与美好,较原文更强调了孩子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使得这一片段尤为温馨。接下来的文字继续不惜笔墨地对孩子的纯洁无瑕进行描述:“然披体之外饰,去之愈净,而真体之光明乃愈弥满。”孩子是无“外饰”的“真体”,即“赤子”,象征着天然纯净,无忧无虑,未受到社会的污染。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不到两岁的女孩饶善德,曾朴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人物的喜爱:
然此时饶善德则胡知者,观面则微笑也,其口则微笑也,其两魇则微笑也,即此微笑之中,足知其无滓之婴魂,固深信造物之慈爱,阳光以煦我,长林茂草以育我,雕墙画栋以护我,固安然于不识不知之天然中,无忧无虑无惧。(1931, 218—219)
作者雨果站在超然的哲学家高度来进行大段细致的描写和深刻的评析。原文强调的是与战争残酷背景格格不入的无辜一切:frêle créature(弱小的造物),sans rien savoir(什么也不知道),sans rien connaître(什么也不了解),sans rien comprendre(什么也不懂),ne pense pas(不思考),说景物是honnête(诚实的),太阳也是innocent(无辜的)。译者曾朴则选择抛开原作客观的分析,而代以身临其境式的观察与刻画,使用三个“我”字(“煦我”“育我”“护我”),成为小女孩的“代言人”,也使大自然成为孩子的保护神,不仅拉近了距离,甚至改变了主次关系。同时,通过多个“也”“则”“之”及“以”的反复,寥寥几行,给此段文字带来了蓬勃的诗意,更突出了“赤子”的纯真与可爱,表达出他内心的呼声,也就是说,“无忧无虑无惧”的“赤子之心”是大自然珍爱的,更是人类最应该珍惜的。
除此之外,对于曾朴来说,原作的诗情也表现在革命者瞿文(Gauvain)的理性思考之中,因此也着重予以表现:
然一瞬之间,血战也,烈火也,残酷之老诸侯也,莫不如烟如雾,悉消灭于摇床前未成人者之目光中。此无他,以其未成人,斯未为恶,真实也,公正也,纯洁也,无罪者也。上帝之全德全能,悉寄托于无罪之童魂中,于是无罪者,遂得奏凯而旋。(1931, 301)
这段文字是对原文几个段落的概括,雨果笔下人物长段的内心斗争,以及对瞿文再三犹豫的描述都被简化了,但曾朴的语言节奏明快,气势磅礴,诵读性很强,而且把人物苦思冥想的正反两方面以简洁的字句表达了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其中几个词语的选择,“血战”“烈火”“真实”“公正”等,都响亮地叩击着读者的头脑,迫使其深思。
下面这一段则用了多个反问句,像是在质问每一个人:


此处文言短句砰然有力,字正词严,掷地有声,使瞿文的内心独白更像灵魂的拷问,投向读者。其实,译者曾朴就是在提出理性的警戒:革命的目的是为人的,是为家庭、为孩子的。这里,他的翻译已经超出了热爱文学的范围,更像是在传递一个政治话语。不过,此类话语的篇幅与原文相比已经大幅缩小;而另外一些段落却比原文长得多。实际上,译者最为欣赏的“人道”,虽然难以通过人物的直接话语来体现,但通过叙述者对人物的真实情感及其表达方式的渲染和描述,完全能使“人道”的主题跃然纸上。例如,曾朴非常重视农妇佛兰宣的母爱,即构成小说一条重要线索的情感,因而,当佛兰宣经过几十天的奔走寻觅,远远看到自己的孩子,而大火却正在包围他们的时候,他如此描述:
佛兰宣此时,已耐无可耐矣。奋身跃入壑中,荆棘满前,一步一蹶,勉达桥拱下,已发散衣裂,血涔涔如汗下矣。(1931, 293)
此处的“奋身跃入壑中”,“血涔涔如汗下”都是原文并没有描绘的形象,添加之后,译文把这位母亲的急切,绝望,不顾一切的情景更为生动精彩地表现出来。对于另一个人物,名叫赖杜伯(Radoub)的革命者,曾朴也着力刻画他的丰富情感。例如在小说开始,赖杜伯所在的共和军小分队遇到佛兰宣带着三个孩子,他观察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
此时哺儿忽离其母乳,徐徐回首以娇丽之目光直注赖杜伯蒙茸之面,冁然微笑。赖杜伯受此乳儿之微笑,较之利刃刺胸,痛乃愈剧,眶中急泪续续下,留须间如珠颗。(1931, 13)
原文对赖杜伯的描写较为简单,直接讲述他流泪;而译文中则增加了译者自己的解释,“赖杜伯受此乳儿之微笑,较之利刃刺胸,痛乃愈剧”,战火和炮弹并没有使这个男子汉惧怕,但幼儿的微笑却如“利刃”刺痛了他。在曾朴看来,雨果笔下的革命战士赖杜伯更因拥有丰富情感而使人敬佩信服,所以需要予以强调和渲染。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薛慕丹(Cimourdain),是投身革命的教士,雨果把他塑造为铁面无私的,从不表露感情的阴郁人物,举手投足都反映出某种远离俗世情感的教士身份,而他的心理则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的分析予以揭示。但是曾朴在简化人物分析的同时,一方面选取某些与人物情感有关的叙述着重译出,另一方面把分析内容的相关部分纳入具体的描述之中,从而把薛慕丹对瞿文暗藏的父爱通过叙述,也通过对实在的动作与话语进行描写来表现出来:
薛慕丹……独于桥阁,则亦未免恻然心动。彼念身为巴利尼小教正时,曾于此阁,授瞿文以读,嫛婗在抱,婉娈动人,娇口嘤咛,拼读字母,此景此情,宛其在目。今瞿文成人矣,且成为伟大之人矣,脱无此阁保卫其体魄,恶能发育其精神。因爱瞿文之心,不能不推爱于此阁,彼见瞿文舍桥而攻塔,彼已默会之而默许之。(1931, 209)
正如前文所述,原作的叙述和分析具有一种超然的客观性,不具感情色彩。在介绍薛慕丹对瞿文的情感时,只用了“élève bien-aimé”(他所爱的学生)和“le fils de son âme”(他的灵魂之子)来说明,而译文中则选用了“嫛婗”“婉娈”“娇口嘤咛”等多个“女”字为部首的词汇来描写瞿文童年的美好,无不明显地呈现出薛慕丹对那段时光的怀念。孩子代表着温馨和爱,曾朴夸张了对童年瞿文的描绘,以此来强调薛慕丹的情感,为的是证明他也是充满人性的。
薛慕丹徐徐蹑足前,昵坐其旁,摩抚其体殆遍,大类慈母之抚乳儿者。既乃徐举其手,就唇吻之。瞿文惊觉,于惨淡灯光中,审为薛慕丹,诧曰:“吾师,不意为汝也。我方梦一死人,吻我之手。”薛慕丹此时心大动,为语不能成声,仅微呼曰:“瞿文。”两人相视久,薛慕丹目眶中,已满贮泪潮……(1931, 324)
上述这一段发生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瞿文因放走敌人被判死刑,走上断头台的前夜,在地牢里沉睡,这时薛慕丹去看望他。这里曾朴以夸大动作手势的方法来强化薛慕丹的情感。“蹑足”“昵坐其旁”“摩抚其体殆遍”“满贮泪潮”都是原作没有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物的肢体语言,在故事情节的这一特殊阶段,显示了他的遗憾和矛盾心情,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具复杂性,更为丰满。
如果说曾朴翻译中采用的夸张和渲染并不符合作家雨果的书写风格,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依旧可以肯定,这种译法与译者在“评语”中所强调的“人道”为主线的小说思路是完全契合的。无论是纯洁的幼童,勇猛的战将,还是冷峻的教士或残酷的侯爵,人性的光芒都得到闪现的机会。雨果以长段的哲理性论述来阐明自己关于人类现实中善恶交错,光明与黑暗共存的思考;曾朴在大幅缩减此类论述的同时,尽可能以描述的方式来彰显原作的思想。
三、历史叙事与哲学思考的隐形
然而原作的思想的确远远不仅是“人道”。其实,如前所述,雨果的出发点是他的当下。为什么大革命的幽灵挥之不去?雨果的目光是多重的:哲学家的目光投向善与恶的分界与交织,政治家的目光投向民族国家与个体的命运,史学家的目光关注如何书写历史,而身为作家,他考虑如何把多向思考与多重观察编织成一个小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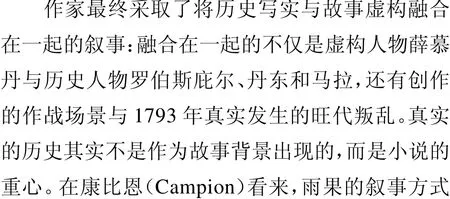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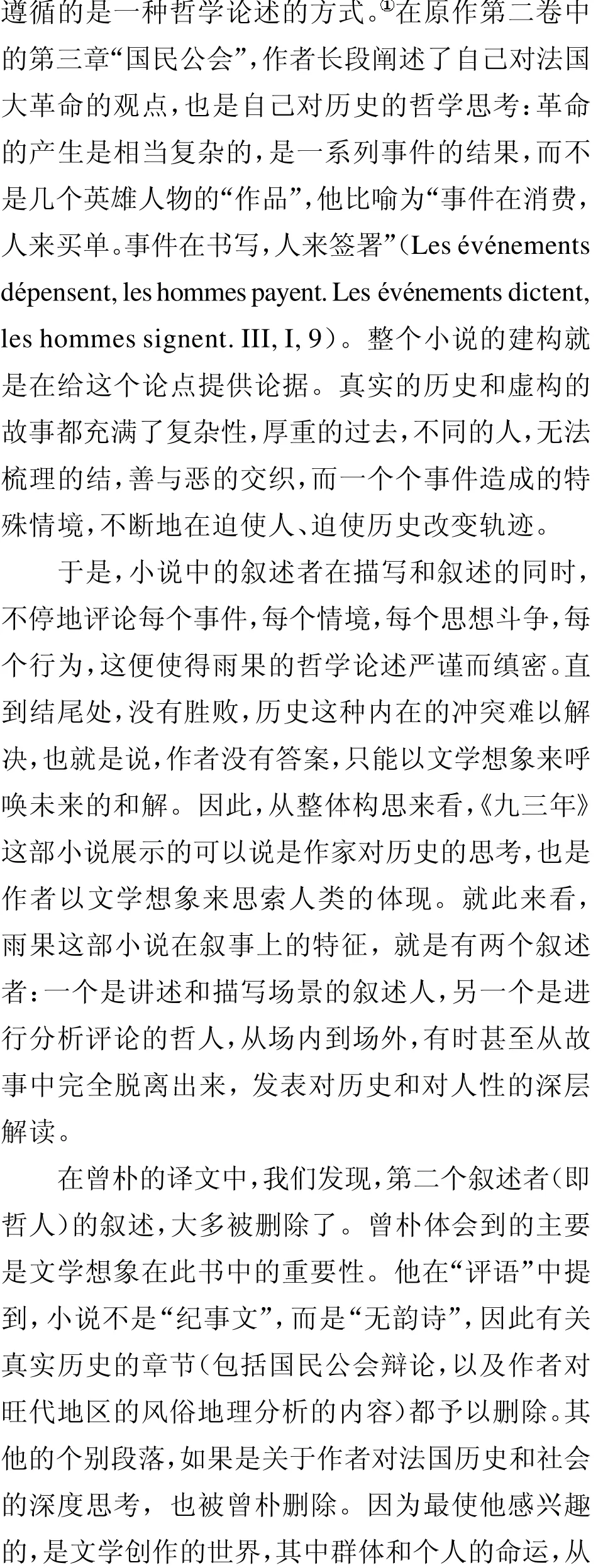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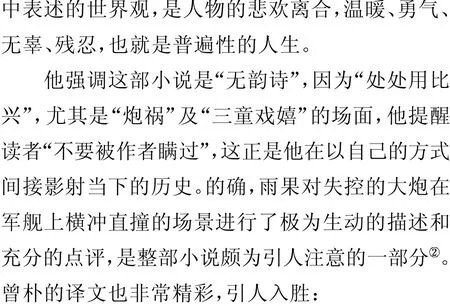

夫天下可恐之事,孰有逾于军舰在洪涛巨浸中,大炮忽脱其缰绳,此时之炮,不当名炮,乃成一莫可名状之怪兽:腾掷如豹,严重如象,轻捷又如鼠。波之流动,斧之坚利,闪电之迅疾,辅佐以行动便捷之机轮,往来进退,左冲右突,或伏焉,或跃焉,自船首以迄船尾,无不为其威棱之所届。……犬可驯也,蟒可诱也,狮虎可慑而致也,唯此无知觉之铜妖,杀之不可,捕之不能。(1931, 28)
篇幅尽管比原文小得多,但原文的主要比喻都保留了(豹、象、鼠、斧、闪电等),使得毁灭性的大炮形象清晰地展现出来。可是,他舍去了另外的几种联想,比如“似乎是永久的奴隶在复仇”(on dirait que cet esclave éternel se venge),“像墓冢一样沉寂”(la surdité du sépulcre),也删掉了雨果的另一部分哲学思考:大炮是杀不掉的,因为它是死的,但它同时是活的;这个恐怖场面的起因就是甲板的运动,但如何去跟倾斜的甲板作战呢?雨果的思想跳跃着,一边叙述一边引申到故事之外,他引导读者去思考历史,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然而曾朴看重的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法兰西的历史,对他来说,作者脱离故事所反思的内容并无必要,因而他舍弃了作者的评论,只把整体的隐喻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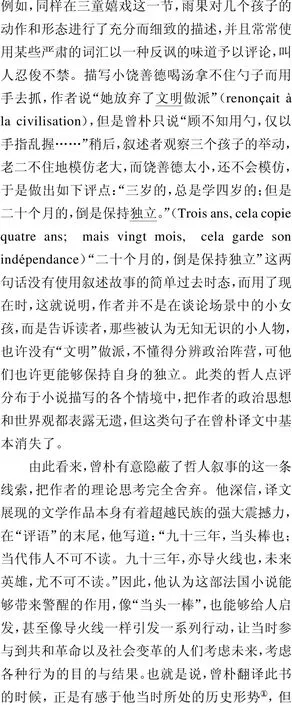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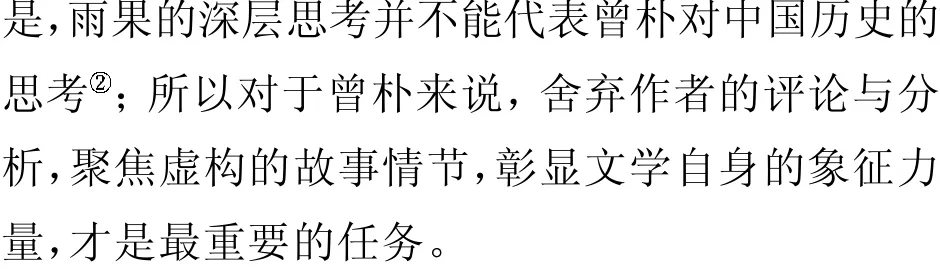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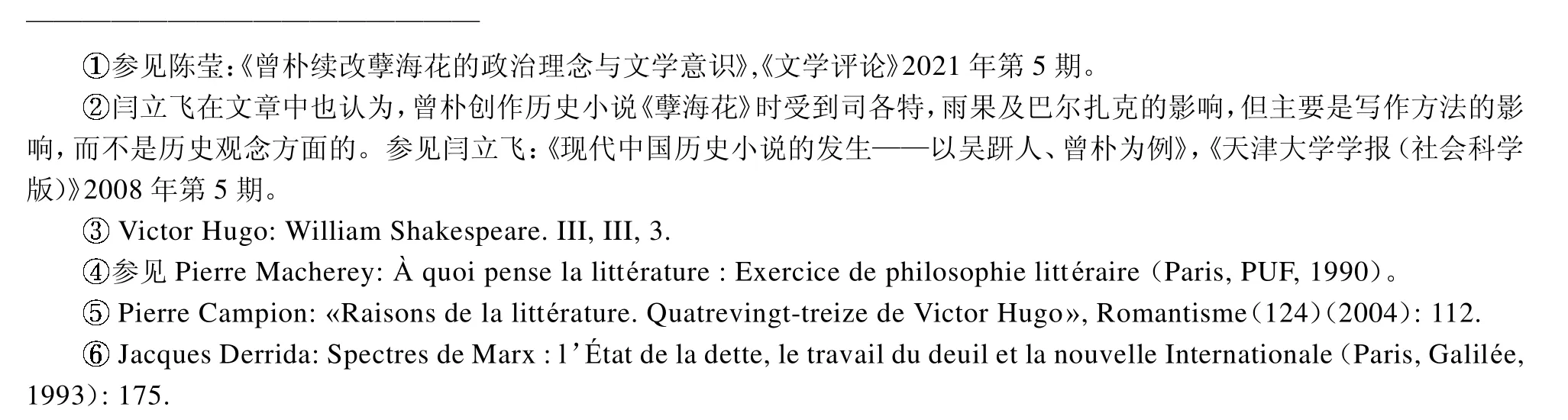
“此两灵魂携手飞升,一张光明之羽,一伸恐怖之爪,永永翱翔于浩荡之天空中,不复返矣。”(1931, 347)
这一句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图像,不具有真实性的图像,正像一个传说的神奇结局。的确,原文中雨果思考的不是善如何战胜恶,而是善恶和解的可能性,而译者苦于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颇显困惑。他于是添加了“不复返矣”,让美好的“光明之羽”与丑恶的“黑暗之爪”都远远离去,不再出现,小说以如此虚幻的图像结束,一方面增强了传奇色彩,另一方面则彻底地分开了理念的世界和真实的人生:瞿文和薛慕丹代表了两种概念化的理想世界,他们的虚幻世界“不复返矣”,而留下来的是重新团聚的母亲和孩子,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也许,曾朴在翻译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翻译这部小说来影射中国当下历史的目标并不是主要的,他在删除有关内容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视角,最终把“人道”,即摆脱了各类本质论和决定论的“人道”放置于小说的中心,并坦言:“九十三年千言万语,其实只写得一句话,曰不失其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