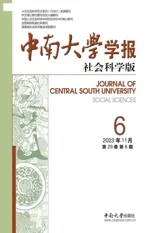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2023-02-13王逊
王逊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中晚明诗坛流派纷起,论调多元,或主格调而尚复古,或重个性而崇革新;同为格调论者,所标举的典范不一,至若情感之强调,又有“情真说”“情痴说”“情教说”等多种。彼此论辩攻讦,递相主导文坛,造就繁复面貌。中晚明诗学受多种因素之影响,就历史传统而言,则与严羽《沧浪诗话》一书有着繁复关联①。删繁就简,就大端而言之,“第一义”学说当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命题,尽管时人对它的态度或是认同,或是反感。至于何谓“第一义”,严羽有云: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1](7)
其以禅喻诗,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与第一义的禅法类似,具有最高典范价值,应当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取法对象。正如有学者所言:
学习的对象本身有高下之别,这种高下意味着真理性的高低,学诗者选择不同的学习对象,对于其所达到的境界具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学习对象的高下直接影响学习者水平的高下。[1](15)
就此来说,标举“第一义”,最核心的旨趣在于强调为文当确立最高典范,并积极取法。延及后世,因儒道思想资源影响、文坛现实格局、文人个体理解等方面存在诸多歧解,以致其内涵多有变化,突出表现在有关典范的确立(或拘泥于少数对象,或强调扩大取径)和取法典范的方式(或固守而不免偏狭,或灵活而鼓吹融通)等方面。但所谓的“异”,从根本上说并未偏离“第一义”的主导诉求,它们展现的是在总体原则指导下,围绕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和一般规律而进行的探讨和思考。故而考虑到本文系有关中晚明诗学问题的集中探讨,便有意搁置了有关“第一义”的具体考察(前贤郭绍虞等对此已有细致分析),专就其与诗学关系中的核心话题展开论述。
中晚明文坛虽众声喧哗,但以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为主要代表,“杂音”的存在并不影响总体的面貌。就七子派而言,其诗学主张无疑与“第一义”关联甚深,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云云,道尽个中滋味②。郭绍虞即指出“第一义之悟,则又明代前、后七子所常言”[2](317),譬如李梦阳,“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世人一般认为正是由于拘泥于“第一义”之窠臼,故而七子派视野狭隘,观念教条,以致因袭剽剥之弊肆意滋生,时人已多有批评,“或议其徒得声响,或讥其食古不化”[2](382),故而“第一义”学说以及复古之举广遭恶谥。
同样已被视为“共识”的,是“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567)。而袁宏道的核心主张与关键诉求,正可谓是对“第一义”的批判与突破。在他看来,“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4](709-710)古今皆有特定之“时”,理当各适其宜,不能强行划一,盲目因袭更是百弊丛生。这一理论提炼显然具有充分依据,他并举过往的文学发展历史予以充分论证: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4](710)
文中辨析了六朝以降诗歌创作的特征及得失,但其旨趣不在单纯褒贬评判,在袁宏道看来,不同时代有其特定的文学发展境况及相应的文学演进趋势,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创作思路与理念,造就了多元的创作面貌和风格,或法或变,或浓或淡,皆有其自足逻辑,不可一概而论、笼统视之。如此说来,每一创作个体最重要的任务便当是对当下、对自我的明晰判断和客观追索,而非盲目效仿某一典范,这便在前提上否定了“第一义”的合理价值。不仅如此,他还消解了作为典范的盛唐诗的尊崇地位,所谓“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至于被视为批判对象的宋诗,虽流弊无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时依然涌现出了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家,“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更重要的是,唐宋诗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七子派理解的那样截然对立,历史地考察,“盛唐—中唐—晚唐—宋”这一长时段的诗歌发展历程正符合他所说的“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宋诗依然从唐诗处取益良多,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唐诗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所谓“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此一来,取法“第一义”在具体层面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被推翻了。
两相对照,“第一义”自然更是难逃恶评。但以上论述看似明确清晰,就考察视域而言却不免粗疏,甚而某些“对话”是在错位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的思考宜进一步深入,“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间的复杂关联也宜进一步明晰。
一、典范与前提
究其实,“第一义”的丰富内涵中首先涉及的是对典范的仿效,如果换一种表述,这正是历来探讨甚夥的模仿与创作的关联性问题。其中又可以拆分为两个话题,一是要不要模仿,二是如何确定模仿对象。就前者论,不论基于何种立场,就创作实际而言,似乎谁也不能否认这么一个前提,即凡论及学习诗文写作的法门时,起始阶段总免不了对特定对象的模仿。七子派推崇复古之说,无论是为了正面立论,还是被动回应,都会对此一话题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末阶段,在总结前人经验、反思前人缺失的基础上,七子后裔就师古与继承、模仿与变化、师古与创造等问题皆有专门细致的深入考察。即使是被人广为批评的“形式”之模仿,他们也多有辩护与说明③。据此,清人有类同总结之声明,譬如姚鼐即称“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5](971)相关言论甚夥,兹不赘述。
既肯定了模仿之必要,自然要引出另一个重要话题,即模仿对象及范围之选择,其与“第一义”学说的关联似乎更大,影响及反响也更为深远。譬如说当我们论及七子派与“第一义”学说的关联时,首先想到的都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中透露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学习的对象有特定范围,系基于一定标准筛选出的“典范”,追根溯源,相关意识在严羽处早有直接、明白表述,所谓: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6](1)
李梦阳明显继承了严羽的主张,云“图高不成,不失为高,趋下者,未有能振者也”[7](1912),据此为其复古观点张目。自此以降,追慕者皆奉此为金科玉律。此等言论振聋发聩,但不由分说的价值判断和盛气凌人的强制说教或能产生震撼效果,却未必让人心悦诚服。譬如说,模仿为何要从最高典范做起?假使随意选择学习对象是否一定贻害无穷?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保不会令人心生疑窦。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七子派的选择是出于不得以的无奈。模仿是初学者的起步阶段,我们必须预先厘清头绪并确定目标,且从便于操作的角度考量,我们只能由部分或单一对象入手。历代文学积累丰硕,学人初入宝库,但见琳琅满目,惊奇欣喜固然有之,却也不免头晕目眩,若无先导开示门径,框定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以供学习,只怕不知所措。王世贞曾联系文学创作实际,对“第一义”之“效用”有生动阐释,云“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8](964)。此语道尽个中滋味,故而这一态度便不只是七子派的一家立场,时人多有同调。第二,七子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创作实践而来,如果说前文强调的是无奈,实则如此选择也(更)是出于必要与必然。自严羽以降,学人多强调“入门须正”,明确区分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反对随意选择取法对象。此一主张看似专横武断,极易招致争议,却也是经审慎思量后的结果。万时华论诗时以作画譬喻,云“今之为数君子诗者,大都学诗如名手临摹古画法书,初纸乍脱,尚自依稀,从临本转相传写,再四而后,渐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脱之,乃复佳耳”[9](265)。就同一作品而言,再好的临本也少了些神韵意趣,影响取法借鉴的效果,更不必说那些格调品格较差的作品了。因此,就模仿的对象而言,必须是也只能是那些经典作品。作画与作诗之间或存在必要差异,不可混为一谈,但从初“学”的角度来说,总有些经验和教训存在一定的共性,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文徵明的主张:“观宋人文,无若观唐文,观唐无若观六朝、晋、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极乎六籍。审能尔,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10](229)在他们看来,之所以面对庞大的文学遗产形成明确的区分态度,是对其艺术水准进行鉴定评判后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盛唐诗和秦汉文等成为最高典范系出于一种“必然”。或有人对这一结论要产生疑问,但许学夷指出,“学者闻见广博,则识见精深,苟能于《三百篇》而下一一参究,并取前人议论一一䌷绎,则正变自分、高下自见矣”[11](313-314)。而经其细致辨析,结论是:
《三百篇》而下,惟汉魏古诗、盛唐律诗、李杜古诗歌行,各造其极;次则渊明、元结、韦、柳、韩、白诸公,各有所至;他如汉、魏以至齐、梁,初、盛以至中、晚,乃流而日卑,变而日降。其气运消长,文运盛衰,正当以此别之。苟为无别,则齐、梁可并汉、魏,而中、晚可并初、盛也,诗道于是为不明矣。[11](317)
诸人皆言之凿凿,就逻辑而言,似未见严谨周密,但此类判断或结论历经文学史的沉淀,早已成为一种“常识”,获得世人的充分认同,若是有人质疑相关作品的典范意义反倒是咄咄怪事。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唯与七子派同调者,即使是那些对立面,如果详细考量他们的观点,也未曾完全摆脱“第一义”式的思维方式。譬如唐宋派,看似与七子派针锋相对、泾渭分明,但他们同样认可并强调秦汉文的典范地位,只是在具体取径或操作方式上有所不同,强调由唐宋而上溯秦汉,换言之,他们对七子派的质疑和矫正,只是操作层面的调整,并未触及总体思路的更张。再如袁宏道,虽对宋诗多有褒奖,且有“唐无诗”之说,但那不过是矫枉过正之辞,有学人指出,“袁宏道挑战李、杜崇高地位的真正动机,并非否认李、杜是伟大诗人这一事实,而是反抗16 世纪复古派所定立的权威标准”[12](152)。其弟袁中道出于纠偏的考量,更是明确标举盛唐诗的典范地位,云“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13](458)。就此来说,认可秦汉文与盛唐诗的典范地位是古人的共识,且这一结论并非贸然得出,实有充分的文学依据,即这些作品的文学成就及价值当得这一尊崇。因此,严羽等人的观点并非大言欺人,实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退一步来说,既然只能从单一对象的模仿开始,则必然要选取典范之作,否则这“取法”也失去了意义。清人对此做出了明确回应,姚永朴有云:
若夫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14](8)
桐城派的论文主张与七子派多有龃龉,但重视起点处的抉择却是他们的共识,并且都会依照一定的标准筛选出若干对象作为(最高)典范,所谓“撮其英华,去其糠秕”。可能的差别在于七子派的要求不免专断,表述也略嫌笼统,桐城派则强调学有统绪,每一步都应有明确规划,相较更为具体和客观。姚永朴为学文者重点推荐了《古文辞类纂》与《经史百家杂钞》这两部古文选集,且云“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矣”[14](9)。较之严羽和七子派,基本思想可谓若合符契。
综上,我们对“第一义”学说的合理价值已有必要彰显,但此举似乎并不能完全消除必要的疑问,甚而有人要指责其中忽略了一项颇为关键的问题,即取法最高典范虽有重要意义,但仅以最高典范作为效仿对象是否存在缺失。关乎此,我们不难获得一些答案。有学人指出,七子派取法“第一义”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此说强调了‘直截根源’,在择定了入门最高标准之后,其他作品皆被舍弃”[15](136)。依照“必”的思路,此举可谓理所当然,但偏狭僵化之弊也应运而生:
秦汉派觑定文学源头,奉之为最高理想,这本来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们一则截断了文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蔑视后世大家对前人学习的积极成果,从而也舍弃了有益的学古经验;再则由于秦汉文字本来与后世的轨辙备具、径路可循不同,往往篇章浑融,难以字分句析,这本属于文章发展的时代特征,但秦汉派遂以此为作文轨辙,在难以追寻篇章字句规则的时候,不免陷溺于摹拟声色以求逼真。[15](150-151)
这一层面或许争议更大,有关“第一义”的批驳主要与此相关,针对七子派主张的调整与纠偏也往往就此发端,甚至于我们有关“第一义”的主要印象及基本评价也都来源于此。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论述看似清晰明白,其背后仍不免有所遮蔽与混淆。譬如说,据上文分析,在“第一义”的名目下,包含了如何筛选典范、确立何种典范,如何取法典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排他性”的问题虽确实存在,却只针对部分层面,不能据此构成对“第一义”的通盘否定。且我们只是在严厉批判作为现象的“排他性”,却少有考察其来龙去脉,因此,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考量的必要,特别是细节的丰富与脉络的多元,其中的要义之一,即在于我们要开拓考察视野,将特定现象纳入历时发展进程中,明了其孕育环境、当下诉求与渊源流变,而非仅仅停留在共时层面,孤立、泛化立论。
二、处境与选择
以秦汉文与盛唐诗作为最高典范是时人共识,相关作品也确实当得这般尊崇,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文学判断,实则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他们强烈的现实考量。就前七子身处的文学境况而言,最大的问题或曰危机有二:一是自明初以来,日益形成了一种“重经术而黜词赋”的氛围,“包括诗歌在内的古文词生存与发展空间为之缩减”;二是其时的主导审美理想沦为一种淡缓柔靡的风格[16](122),时人多有检讨。譬如李开先有云,“国初诗文,犹质直浑厚,至成化、弘治间,而衰靡极矣。自李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材取软滑者,不惟诗文趋下,而人材亦随之矣”[17](916)。此类言论甚夥,“衰靡”云云,成为时人的普遍印象,故而纠偏祛弊、改弦更张成为一种强烈诉求,于是乎才有了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表彰。王九思即云“本朝诗文自成化以来,在馆阁者倡为浮靡流丽之作,海内翕然宗之,文气大坏,不知其不可也。夫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庶几其复古耳”[18](231)。个中的可能流弊他们并非全然无知,但在特定境况下,不得不矫枉过正,“责备者犹以为诗袭杜而过硬,文工句而太亢,当软靡之日,未免矫枉之偏,而回积衰,脱俗套,则其首功也”[17](932)。
循此角度,即充分考量相关命题的具体语境,我们的认识及判断当有不同。譬如说七子派和公安派,前者高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者则宣扬“纵心纵口”“独抒性灵”,彼此文学观念不同,价值立场有异。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独创、个性本就较之模仿、因袭更具强大吸引力,文学发展的动力也得益于扫除陈规、与众不同,加之七子派文学创作中大量存在剽剥蹈袭之弊,世人有此态度可谓理所当然。单纯就观点来看,公安派的主张似乎更为通脱、合理,但这种“单纯”的考察方式本身带有不可避免的缺失或遮蔽,其中的一个重要盲点就在于忽略甚至无视了我们此处提及的现实处境。
就七子派而言,秦汉文与盛唐诗的大力表彰与宣扬不仅只是一种文学类型或风格的喜好与采纳,而带有重新确立诗文地位、明确合理发展方向的诉求,正如有学人论及的:
李、何诸子极力倡导复古,本于尊崇古文词价值地位的立场……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以复古相尚,寻求别开蹊径,更主要的是其归向文学本位,在崇尚古典中实现了由重诗文经世实用性引向对它们本体艺术关怀一种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转迁。[16](56)
这是一种根本上和总体上的文坛格局重建。对于公安派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特别是基本的文学旨趣和审美理想已然重新确立的情况下,他们的任务已经从重建格局、确立典范转化为如何更好地建构审美理想④。就“重建”而言,难免矫枉过正,譬如七子派通过强调“必”来扭转局面,对于他们来说,确立目标是首要的,具体手段和路径难免空疏甚至偏狭,有时候甚至需要借助这些带有“缺陷”的手段来达成目的。但对后续建设者来说,他们不是宏观立论,而是要处理具体、直接的对象,此前的种种口号、论调因陈义过高或考虑过简,难免左支右绌甚至错漏百出,他们因之要有补充、完善甚至矫正、反拨之举。譬如说他们普遍认识到七子派复古之失在于泥、在于袭、在于拘求与古人同,结果非但未能靠近典范,反而失去了自家面貌,那么“针对复古摹拟之伪(如情感的过度文饰、形式的摹仿、情感的造作、诗情与人格的分离等导致的不够真实)”[19],而提出重视个性、鼓吹性灵也是理所当然。与此相伴随,文学典范也有所更张。譬如舍弃七子派直接取法秦汉文的路径,强调从唐宋文入手,又或者大力表彰宋诗的价值,但正如前述,此类言论并不构成对七子派“第一义”取径的反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鉴于前者之失,探求更为合理地接近典范的方式。由唐宋文向秦汉文上溯自不必说,鼓吹宋诗价值,针对的正是时人泥唐太过之弊,症结虽在“泥”上,但就事论事的批评和具有针对性的纠偏或许难以奏效,毕竟泥唐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让人无法轻易抽身,假使一方面仍以盛唐为典范,另一方面又强调自我和个性,世人极易由于“惯性”和“陈规”重蹈覆辙,那么唯有推倒重来,实现包括取法对象在内的整体改易,时人的思维方能有较大转变,即唯有造就全新局面,方能崭然有异。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部分思路也有待后续调整,譬如竟陵派就对公安派的主张多有扬弃⑤。
虽然七子派的诗学命题存在严重缺陷,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也并非全然允当⑥。更重要的是,后者对于前者的反拨甚至取代并不只是文学观念的简单对抗,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他们提出的命题上,更要细致考量背后的动机。毕竟一应命题并非凭空提出,这其中有社会环境与学术思潮的影响,但首先还是对现实文学状况的回应。我们在评价相关命题时,不应简单判断何者先进、何者落后,而需首先回答它们的提出有无现实性、必要性和针对性。就此而言,无论七子派还是公安派,他们种种理念的提出,都有其必要价值,至于后续流变,特别是种种弊端,虽与他们存在密切关联,但也不能就此否认其提出时的可贵价值。
“第一义”学说的推行是基于现实处境,那么随着现实的变化而调整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七子派对此显然具备鲜明意识并自觉求变。模仿或许确为写作起始的必然选择,但七子派亦有拟议以成变化之说,他们同样追寻由袭到创的升华与超越。前文提及了“排他性”,实则七子派对其可能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做出了深刻检讨与反省,从而实现对“第一义”的改造与完善。我们最为熟悉的或许是谢榛的主张,其云: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8](1189)
过往研究在处理谢榛与后七子的矛盾时往往左袒茂秦,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认为谢氏论诗圆融,较李攀龙等人高明,譬如李庆立即说:
李攀龙发起诗社,倡言复古,对持异议者,历来就视同异类,极力排斥。谢榛崇尚近体,力主“以盛唐为法”,但他并不是“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回到盛唐去;而是立志在继承盛唐的前提下创新,自成一家。这与李攀龙的主张小同大异。[20]
且在论者看来,“其他诸人,特别是王世贞、吴国伦,后来在自赎性反思中有所清醒,增加了对谢榛的理解和认识”[20],即他们经长期实践与反思,开始自觉认同谢氏的诗学主张。这一观点实出自钱谦益,其云“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3](424)。
类似说法陈陈相因,几成常识,但可能的误会仍有不少。与谢氏类似,后七子其他诸人亦有杂取众家、融会贯通的想法,譬如王世贞即云:
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8](964)
王氏此论,若将其归结为受谢榛启发或影响不免简单。结合文学史发展来看,这可谓是当时的一种共同态度,有学人指出,“将取法对象由杜甫推及盛唐其他诸家甚至初唐诗,是正德、嘉靖间复古诗论拓展最直接的表现。与此相联系,拓展模拟、学习诗风的范围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21](253)。进一步来看,取法范围的扩大还不止于此,“从诗学系统选择来看,六朝、初唐、中唐甚至晚唐时代的诗风,嘉靖前期都曾有人提倡”[21](256)。甚至更早一点,何景明鉴于李梦阳之失,就有“富于材积,领会神情”[22](575)的主张,这“富于材积”,强调的就是不主一家,多方借鉴。
扩大取径的主张或与个人的天分、学养有关,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探索和反思而得出。王世贞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最初觉得“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的主张过于偏狭,继而因下笔时有“驱斥为难”的烦恼,方才意识到李梦阳主张的可贵,但在大量实践中又发现“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故而才有多方取益、融会贯通的呼吁。因此,隔绝语境,单纯就理论本身做价值评判多少有些遮蔽,更重要的仍是需考量它们的问题意识与实际成效。
就此来看,谢榛等人广受赞誉的主张,取径的扩大确是矫正偏狭之弊的“良药”,“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诗歌领域师法于古的渠道,增强了复古话语的多样化,也为此阶段文坛格局的变通开辟了一条途径”[16](313)。但这种理论层面的完善,未必意味着实践层面的成功。譬如有学人指出:
主张习学古作的神气精魂而不拘字句的形似,自然是合理的,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题是,将这一原则性的宗旨落实到具体创作之中,就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何才算真正能“摄精夺髓”、“提魂摄魄”,可能会招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异议。在李、王等人看起来,谢榛的拟古之作就因为刻意强调合诸家之长,摄取神气精魂,未免无“法”可依,变得“绝不成语”。[16](344)
理论主张看似圆融,但置入实践环节,却让人无从下手,类似困扰无疑是真实存在的。这看似是操作问题,实则也是理论问题,清人的意见或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姚鼐云指出,“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5](971)。他虽提议要转益多师,但在操作环节,需要“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即每一阶段,只针对某一对象深入学习,通过一个接一个地细心模仿,最终实现融会贯通。谢榛所谓“历观十四家”熟读玩味之举显然是他所反对的,没有具体的、个别的学习作为基础,盲目寻求“脱化”,必然一事无成。前已提及,之所以要有“第一义”之标举,在初学者层面实属无奈,不如此便难以措手。谢榛等人的主张看似通脱,但对于初学者来说便是无从下手。某种意义上,起始处,必须有一“必”,以便入门;待到一定程度,再导之为阔大,如此方能发展。正如有学人指出的,“如果‘必自迹求’只能算作常人的摹习水准,那么‘广其资’、‘参其变’应该说就是克服这一状态的一种应对之策”[16](188)。不同的阶段,便当有对应的主张,此间次序不可随意颠倒。谢榛的理想固然完善,但用在初学者身上只怕并不能奏效,要么“驱斥为难”,要么变成随意拼凑的四不像。职是之故,我们在考察理论命题时,不能过于平面化和单一化,接受对象的层次与实践环节的变形等因素都需要充分考量。
三、立场与效果
七子派鉴于“第一义”引发的“排他性”之弊,提出了扩大取径的思路,但由于忽略了接受层面的实际情况,使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既有研究同样对其意义评价不高,但思路却与前文的分析迥异。在不少学人看来,扩大取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是基于某种策略性的需要……不过是宗尚的重心从一类目标移向另一类目标而已,更多是反映在习学的具体对象及方式上的一种调整,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于复古壁垒的突围”[16](313)。质言之,如果不突破复古派的理论框架,任何调整都无法真正应对当日的问题,他们欣赏的是对七子派的彻底反动和推倒重来,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主张之所以得到大肆表彰也与之相关。这一思路或有其合理成分,但同样存在遮蔽与曲解。
七子派与其反对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或在于对“法”的认识不同,与此相关引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三个重要命题,即古与今、时与法、因与革,七子派之失正在于未能合理认识和处理上述三者的关系以致流弊无穷,有学者即指出“一种文学样式,理应依循于一定的创作规范,但是,体裁格法毕竟是表现内容的手段,内容才是首要的。拟古派之偏颇,不在于重视古法,而是胶柱于古法,即无视世运迁流、风雅代变的事实”。与此相关联,“如何处理‘时’与‘法’的关系便成了区别复古派与晚明主张抒张自我性情的革新派文人的重要标志”[23](94-95)。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革新派,虽表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最终也不能完全弃“法”不顾,务实的做法是纠正前人胶柱于古法的缺失,寻求灵活法度的可能,特别是不能遮蔽了一己个性。有学人论及袁宏道的主张时指出,“法度并非固定而刻板,而是具有极大的弹性……诗人应当在法度之中找到个体自由,而非被其窒塞了一己精神之表达”[12](159)。
公安派的思路显然要更为通脱、合理,但正如我们在文中一再强调的,理论的“完善”并不能等同于效果的“完美”。第一,法度与个性的平衡始终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七子派固然有拘泥法度而抹杀个性的弊病,公安派也不无逾越法度的行为并饱受后人的抨击。第二,圆融的论调总不免有“蹈空”之嫌,很难落实到操作层面。对于后学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理论的多重内涵及高妙理想,便于上手的门道才是他们的迫切所需。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陈际泰所提到的情况:“效吾二三兄弟者,去其始造之意,已若立乎定、哀之间,以望隐、桓,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陈氏提倡豫章之文是为了让世人就此去体悟“圣贤之规旨与秦、汉以逮成、弘之义类”[24](458),而后学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番苦心,仅仅将模拟的对象由七子之文转变为豫章之文而已。如此一来,七子派因尊奉“第一义”而产生的弊端再度出现,只不过具体的典范由秦汉文变成了唐宋文乃至豫章文而已。至于袁宏道的效仿者们,“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13](462)。此处反映的自然是理论传播过程中的流弊,但也明白告诉我们,后学限于学力等因素,并不能很好地领会理论的精神内涵,他们往往“便宜行事”,旨在寻找一个便于操作的抓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越明确、越机械,则越是便利,至于灵活云云,反倒成了玄虚之论。公安派论诗提倡“时”与“创”,但此论无法真正回答有关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纵心纵口、独抒性灵之文或许是佳作,但若以为如此便找到了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则显然是妄论。正如邵晓林所说的“这种写诗的方式使诗呈现非诗的情态,诗歌的诗意被破坏,人文意义也不能得到保证。诗歌失去超越时空进入共享的可能,而有流为一时一刻一人之快的‘张打油’的危险”[19]。再如唐宋派,熊礼汇认为在如何创造新文风问题上他们有两点明显高于秦汉派:一是前者继承的是整个文学传统,后者则连“半截子散文艺术传统也没有很好继承下来”。二是前者重在继承古代散文艺术精神,后者则是临帖般的模仿;前者强调由“约以法度到超越法度”,后者则拘泥于法度⑦。从“约以法度到超越法度”确属应该,但如何超越?从倡导者的理念到追随者的实践,尚有一莫大距离或障碍,即如何执行,方法或手段为何。“悟”之提倡美则美矣,但不免玄虚,就后学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种种切实的规则和步骤。以此,反七子派诸家虽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除了一腔热情及高调言说外,却未能从根本上实现问题的解决。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有关诗文创作的探讨有两种模式:一种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另一种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规定,且强调的是自我和自主,反对拘泥于种种格套之中。换句话说,前者强调操作性,重视细节;后者强调灵活性,突出根本。学人在这两种倾向间明显倾向后者,但这种判断似乎不够客观。七子派的主张虽极易招致拘泥于形式或表面之失,并引发种种问题,但到底方便后学入手;公安派的追求虽有助于尽情释放和展现人的天性,但也容易遭致所谓“轻薄”“矜诞”等缺失,特别是后学,受此等精神感召,容易沦落至“今人议七子后,动称性情诗,问渠性是何物,罔所措矣”[25](128)。至承袭竟陵派者,甚而“以空疏为清,以枯涩为厚,以率尔不成语者为有性情,而诗人沉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26](554)。笔者在考察秦汉文与唐宋文之争时发现存在一个悖论,即视角太过细致,必然凸显差异,受门户之见的影响极易偏激并成流弊,至若矫正之法无过于忽略末节,强调大本,但所谓根本之法太过空浮,如何呈现仍需落实到细节,无论是“根本”还是“达末”皆属为难。可以这么说,偏于“悟”之一面,容易导致无所措手;落实到具体的体制规范,又会滋生僵化因袭之弊,这不仅是七子派的困惑,更是历来学人的一贯难题。即便如禅宗,为免文字障碍,强调明心见性、不立文字,但为了传承的需要,仍不免留下了诸多语录,也确实造成了迷障。或许桐城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答案,陈平原在论及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时指出:
注重“法”,则强调可操作性,适合于教学;注重“变”,则神龙见首不见尾,更适合于独自远行。相对来说,桐城教学有方,强调“法”的时候多,对“变”考虑得较少。这既使得桐城文派迅速扩张,声名远扬,也因其文章规矩太多,个人才情发挥不够,因而备受责难。带进“教学”这一角度,当更容易明白姚鼐及桐城文章的利弊得失。[27](225-226)
我们都知道古人极为关注诗文如何写作这一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宣扬一种理念,更要提示必要的尺度、准绳、方法和步骤,以期金针度人,某种意义上也是重视在“教学”,或者说,他们的理论表达方式及诉求都指向了“教学”。有论者指出:
古代诗话、文话除了辑佚诗文、记录诗事外,还有很多诗文理论的谈论,这些谈论往往源于创作实践,用于指导诗文书写。显然这些谈诗论文的话语主要源于书写的需要,时人对诗文如何书写的关注也源于现实生活的需求。[28]
七子派的思考方式及观念主张显然与这种倾向更为契合,但可惜的是,既有研究不免“偏离了七子派及诸诗文流派如何快速、高效提升书写水准的‘焦虑’以及从实践层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28]。当选择了一定的立场,采用了一定的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就需要承受可能得缺陷。任何的表述方式都难以完美,因此我们在审查相关现象时,便不应只顾苛责存在的问题,更该关注的当是它在“特色”一面贯彻落实的效果。
综上,“第一义”与中晚明诗学确实存在无可争议的密切关联,因“第一义”的推行而产生流弊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对此话题的审视不可过于拘泥,即仅仅考量创作成效一端。说到底,“第一义”学说在文学领域的敷衍和践行,始终是基于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实际境况的,它既具现实性,也具灵活性,但从理论表述到实际操作,由于个性理解的差异,言说方式的限制,以及接受过程的迟滞,总是难以完全对应,故而我们应从整体上有所把握,那么就当对此中甘苦有所理解,七子派的难得与难能便不会一味抹杀。否则,孤立地就任一方面考察、立论,虽不无发现,到底是片面的,甚至是偏颇的。
注释:
① 个中情形学人已有细致梳理,具体可参考雷恩海《〈沧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朴英顺《严羽〈沧浪诗话〉及其影响研究》(复旦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等。
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乃以笼统说法,廖可斌即指出,“对于学古应取法的榜样,前七子的看法基本一致,即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诗以盛唐为诗,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元以下则不足法”(见氏著《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127 页)。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相关创作活动指定了特定的典范,总体思路仍沿袭了“第一义”学说的要求。
③ 笔者曾就此做过专门探讨,详参拙著《明末学风与诗学》,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80-196 页。
④ 公安派与七子派的分歧自然不仅在于文学层面,思想文化因素或许更具重要影响,但这方面的话题学人多有探讨,无须赘述,倒是文学层面的观照较为稀少,本就应当有所突出。更重要的是彼时思想与文学命题系出于彼此夹杂状态,但学人往往只看重思想层面的突出影响,倒是对文学“思考”采取了不免忽视的态度。需知他们首先是文人,身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中,有特定的命题要回应,思想观念需施加在文学命题上方能产生影响。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文学”层面有专门关注,由此也能了解到他们的另一面。
⑤ 或有人认为,较之七子派,公安派的思想主张亦是一种颠覆,但这一立场并不影响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强调的只是不同理论主张有其特定生成语境,故而不可在“真空”状态下仅凭只言片语进行比较。
⑥ 余来明指出“公安派以抒写性灵为创作的内在机制,甚至不惜以牺牲诗歌技巧的锻炼为代价。如此作法,也遭到后世论者的批评,如钱基博认为公安派‘惟恃聪明,其尤甚者,轻薄以为风趣,矜诞以为吊诡’,确为公安派弊病之一”。见氏著《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267-268 页。
⑦ 熊氏的结论实与其对“传统”和“法度”的具体界定相关,详情参考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00-3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