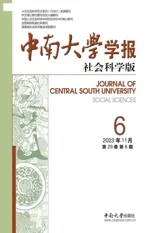直播戏剧的电影化叙事矛盾与元宇宙解题
2023-02-13张国涛丁阳
张国涛,丁阳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100024)
NT 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RSC Live(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Live)、Comédie-Française Au Cinéma 等将影院直播作为主要的放映形式,长期以来都是传统剧院的跨地区演出补充。然而,随着此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各国民众的线下文化娱乐消费被迫中断。在这种情况下,NT Live 等直播戏剧与Netflix 等影视平台共同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阶段,并开始转投线上影音平台进行文化消费。如NT Live 于2020年4 月2 日宣布推出“居家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 at Home)计划,旨在通过流媒体向全球观众进行经典剧目的公益性重播,以缓解各国大众不断积聚的观剧需求。该计划上线两个月期间,其展映的16 部戏剧在YouTube 平台获得了来自173 个国家900 万用户的订阅观看[1],并在腾讯艺术、优酷文化以及保利票务云上剧院等平台获得了超过500 万观看人次[2]。NT Live 的流媒体尝试揭示了其强大的商业化潜力,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百老汇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国内外剧院开始推动戏剧演出的线上转型尝试[3]。由此可见,在此前全球娱乐产业发展受阻的境遇下,直播戏剧显现出了愈加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
目前,关于直播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范式冲突的层面。索菲·迪塞尔霍斯特(Sophie Diesselhorst)与克里斯蒂安·拉考(Christian Rakow)等国外学者将直播戏剧的感官冲突聚焦于“时空同步性”问题上,他们认为只要观众能够与演出现场形成真实的互动反馈,那么在戏剧舞台上使用银幕(或屏幕)就是可行且合理的。此外,两位学者还认为这种反馈并不一定局限于现场事件本身(同空间的剧场互动),也可以仅以演出框架(跨空间的概念连接)为前提[4]。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等学者则更加强调“剧院演出的现场魅力”,认为演员面向观众进行的现场表演是内在“能量”的直接传递,并能够建立一种能被彼此信任的半公共“社区”,而直播戏剧却对这两者的依存关系造成了本质性破坏[5]。史册等国内学者同样将研究焦点放在“在场”问题上,认为直播戏剧是线下戏剧的“再媒介化”,观众的“身体在场”也在这个过程中转变为“身体化在场”。但由于当前的技术条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观众的虚拟临场体验也还无法被完全复现[6]。另外,国内也有其他学者提及了直播戏剧从舞台到银幕的“三度创作”现象,并用以分析电影化戏剧叙事的新型观演关系,不过其分析角度多以摄录技术层面为主[7]。因此,从国内外对直播戏剧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场”的概念是讨论戏剧舞台屏幕化现象时不可避免的。关于其在媒体范式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叙事矛盾,围绕“场”产生的叙事矛盾也主要集中在受众审美场域的重塑上,而对于媒介叙事冲突和蒙太奇范式矛盾等问题的理论剖析则相对较少。本文拟在分析直播戏剧当下遭遇消减戏剧叙事整一性和舞台艺术临场魅力困境的基础上,论述直播戏剧这一困境可望在元宇宙场景中得到解决并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可能性。
一、蒙太奇范式消解戏剧叙事的整一性
NT Live 这类直播戏剧作为传统戏剧和电影产业的融合产物,其最显著的特性即是观看媒介从舞台转向银幕,叙事范式也从“场”或“幕”的排演转变为片段式镜头的组接。这个由创作者所主导的镜头重构艺术被列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库里肖夫(Lev Vladimirovich Kuleshov)、费谢沃洛德·伊拉里昂诺维奇·普多夫(Vsevolod Illarionovich Pudovkin)以及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爱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zenshtein)等电影理论家称之为电影蒙太奇(montage),并认为其是“电影特性的基础”,是银幕表现力的根本来源[8]。而其于直播戏剧,将戏剧舞台银幕化的益处是观众能够透过镜头更加细致地欣赏演员的微表情与微动作,并极大地消解了剧院因座席距离而被强制划分的内容详略等级。并且,电影化的蒙太奇叙事也赋予了创作者更大的主导权力,主创团队能够利用各类景别镜头切换引导观众的观看视角,以更好地符合原本的创作意向,如叙事指向和叙事节奏。鉴于此,NT Live 大体上兼容了戏剧与电影的叙事优点,并初步构成了具有融合特性的创新形式。但就整体而言,电影化的蒙太奇镜头叙事方式却也消解了戏剧艺术原本的整一性叙事特征。
第一,直播戏剧的蒙太奇叙事方式削弱了人物行动之于舞台叙事整一性的核心地位。关于其整一性,谭霈生曾在《论戏剧性》中谈道,戏剧舞台上全部人物的行动都朝向一个明确目的发展推进,即这个目的将一系列角色以及动机贯穿起来。所有角色都在同一环境中按照各自的性格逻辑行动着,他们既不是彼此的陪衬,也不是主题的单向图解者,但却用独立且个性化的行为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丰富着那个统一的主题[9]。《北京人》作为一部设置了众多复杂角色的经典剧目,就直观地体现出了这双悬于舞台之上的整一化操控之手。具体说来,曹禺在固定置景中安排了十余人穿梭其中进行表演,但其高密度的限定空间却并未使人物线索陷入杂乱境地,而是依靠详略有致的平行式叙事手法展示出了众角色丰富而统一的行动设计。无论是代表传统父权形象的曾老太爷,代表教条反叛者的曾霆,还是代表失败实干者形象的曾思懿,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独特的个性在特定环境下展现着被赋予社会意义的个性化行动,并最终在多线索发展中汇聚成全剧核心思想。因此,正如谭霈生所强调的,戏剧舞台叙事的整体性效果来自独立人物之间有机互动关系,舞台之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无用或多余的,所有交错出现的人物行动都是总主题下有意义的分支[10]。
但是,舞台艺术的整一性美感却不可避免地被蒙太奇镜头所“拆解”。当各类屏幕取代舞台成为直播戏剧的展示媒介时,其叙事策略也必然需要按照电影化叙事原则进行重新编排。廖祥忠在分析电影沉浸性时指出,传统电影以二维画面将叙事时空聚焦于一个可控的影像中心,导演剪辑权掌握着故事情节的时间轴向顺序,并引导观众走进精心策划的情感预设。而戏剧舞台则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属性,多条由不同角色主导的行为故事线索在同一时空内并行,观众的关注焦点也自然无法被限制在特定场域内[11]。直播戏剧作为两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产物,复杂的蒙太奇镜头无疑打破了戏剧舞台多人物交错演出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戏剧舞台较为固定且精简的演出场景也在平面化的“降维”后显得“单调乏味”。这点在2022 年NT Live 推出的《尘埃之书:野美人号》(TheBookofDust—LaBelleSauvage)中得到了较为具象的体现,由于该剧根据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物质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小说改编而来,其夸张的奇幻世界观成为舞台视觉呈现的最大难题。也正因如此,创作团队的舞美巧思也构成了本剧最具创意与吸引力的创作闪光点,如将小说中占据大量篇幅的“灵兽”以纸艺形式搬上舞台,并由数位非主角演员进行手持表演以展现灵兽的肢体动作与对话。但是其在NT Live 的银幕呈现却极大地削弱了这一创意效果,蒙太奇镜头将灵兽表演剥离出故事叙事之外,并将其作为人类角色的“点缀”,零散地穿插于镜头间隙。虽然这样的影像处理方式更加利于突出故事主线,但灵兽作为舞台叙事的一环却并非仅是简单置景,而是时刻与主角表演保持同步的动作反应与情绪反应。此外,操纵灵兽的演员也并不只是“幕后”角色,他们在现场配音时丰富的神态与肢体表演也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量删减灵兽的戏份必然会对舞台的整体叙事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银幕前的观众也将失去了观赏“支线”剧情的应有体验。
究其矛盾根本,NT Live 这类直播戏剧自诞生以来就未对其杂糅性艺术表现手法进行范式上的统一。张庚在《戏曲的形式》一文中曾针对戏剧内不同艺术门类的融合问题提出了“表演中心论”说法,认为“各种艺术既然必须通过演员艺术,而且只能直接和演员艺术相结合,那么演员艺术所直接加于他们的限制自然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限制”[12]。也就是说,各类艺术部门与戏剧的融合必须要服务于舞台之上的表演,好的融合是使舞台表演得以增益,而不能削弱表演或是引发更为激烈的体裁冲突。显然,NT Live 的蒙太奇化创作方式更多是将戏剧内容作为供电影化剪辑使用的素材文本,而非以舞台表演为主要叙事核心。因为对于电影蒙太奇而言,影像表达题意的方式并不被舞台时空所限制,所以也无须只将镜头聚焦于演员动作,而是可以把一切能够引起观众直接观看或间接感受的事物都纳入其中。让·米特里就曾在《电影美学和心理学》(The AestheticsandPsychologyoftheCinema)中对不以演员表演为主的非叙事性蒙太奇如此评价:“尽管这种蒙太奇也推进叙述,但是这种形式侧重分析,而非描述。它的本意既是报道,亦是绘声绘色的抒情和墨酣情切的渲染,并且更偏重后者。”[13]这说明蒙太奇的杂糅性使电影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综合性艺术,表演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也并非全部。那么,以电影创作角度来重新审视NT Live 版《尘埃之书》,其对纸艺灵兽故事线的舍弃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可供主旨表达的局部镜头众多,演员也只是要素之一,那么作为辅助叙事的纸艺灵兽也就自然被置于更次级的镜头选择之列。由此而言,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舞台叙事与电影叙事之间的叙事差别:前者叙事效果取决于舞台空间内多人物行动的统一,合一场景的叙事意图表达并不能由舞台局部进行替代性叙事;而后者叙事效果则恰好主要依靠这种“局部”素材(画面)的组合拼接,是若干个精选镜头彼此碰撞所形成的电影情节“激情效应”[14]。
第二,蒙太奇镜头在压缩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导致了戏剧内容的信息损失和观看方式的切换“故障”。正如前文所言,戏剧舞台在三维空间内提供了一个更加个性化的自由视角,观众既能够专注于舞台核心位置的主角表演,也可以随心切换至其他角色应情而动的支线剧情。至于《不眠之夜》(SleepNoMore)这类没有固定主角以及演出舞台的沉浸式戏剧,其复杂的位置节点(五层楼90 个房间)与时间节点(3 小时)所交叉形成的故事网络,更是给予了观众更为自由甚至夸张的剧情选择权,并远远超出了电影蒙太奇的叙事能力。正如Punchdrunk 剧团在宣传《不眠之夜》时所讲的那样:“每个人的观赏体验都将是独一无二的。”观众在不同时间、不同位置所观赏到的内容,也就成为高度客制化的超验戏剧,而电影镜头无论聚焦于何处,都无法真正地完整记录舞台演出的所有枝节。虽然,这类沉浸式作品是戏剧艺术中十分特殊甚至极端的形式,但在此对比中,蒙太奇镜头对空间艺术的“压缩”局限性便凸显了出来。正如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等人所言,蒙太奇是“间断地描写和对事件的戏剧性地分解”[15],这种“时空不连续”概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蒙太奇艺术的固定内涵[16]。这就导致直播戏剧在对舞台表演进行摄录与剪辑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对戏剧内容进行不同程度的切割删减,从而无可避免地破坏其极为重要的舞台叙事整一性。具体到应用场景中,创作者会按照主观叙事意图使用各种二维景别(近、中、远景)来表现复杂的三维空间关系,但这种降低画面维度的平面剪裁必然会导致镜头画面损失舞台表演的大量信息。特别是当多个人物同时发生行动且处于不同舞台位置时,剪辑师通常只能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角度(人物)作为镜头内容,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戏剧舞台的整体感与叙事丰盈度。
可以肯定的是,现阶段NT Live 这类直播戏剧在叙事整一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表明戏剧与电影媒介的融合方式仍相对简单粗糙。以观众主观体验视角来看,NT Live 常会导致观看视角或观看心理上的切换矛盾,即“观众该以何种心理预设透过银幕进入戏剧情境之中”。对此,可以从艺术形式基本单位的角度来进行辨析,即电影镜头单位与戏剧“场”单位之间的不兼容性。具体说来,电影以镜头为最小基本单位,并且除常被谨慎使用的长镜头外,单个普通镜头本身难以独立承担完整的叙事任务,而是需要依靠一系列有机组合来完成叙事蒙太奇的最终使命[17]。对于尤其注重快节奏剪辑的动作片等商业电影,单位时间内能否容纳足够多的镜头数更是直接影响着电影的叙事节奏和叙事质量,但这也意味着单个镜头所能够容纳的叙事内容也将更为有限。而传统戏剧则以“场”作为舞台表演的基本单位,每一“场”都包含了所有同时起作用的要素,且是时间与空间的连续统一体[18],即场面(场)的概念以人物上下场作为整体叙事段落的切分尺度,并由此构成了舞台单位内的一段完整话语,也成为人物行动的连续体与统一体[19]。通过对比可知,镜头与场两者单位在叙事体量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并直接决定了观众截然不同的观看心理预设。正如简·费尔(Jane Feuer)在《话语渠道的重组》(ChannelsofDiscourse,Reassembled)中所言,每种媒介都拥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代码、惯例与期待”的观看系统,不同的内容也凭借差异化的实践路径与观众心理惯性形成了牢固的联结关系[20]。因此,当直播戏剧以碎片化的电影蒙太奇镜头展示连续整一的单场戏剧内容时,观众应该将其视为戏剧内容的电影镜头化再现,还是当作电影所记录的舞台故事,则成为必然存在的心理矛盾点。
由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主演的NT Live 独幕剧《伦敦生活》(Fleabag),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直播戏剧的特例来反向说明以上两个问题。该剧以女主角“邋遢鬼”自述其曲折经历为主要故事内容,且除一人一椅之外再无他物。另外,该独幕剧也仅由一个“场面”贯穿始终,在85 分钟总时长内未设置中场休息,并且也不存在时空切换以及演员上下场等舞台操作。因此,《伦敦生活》在舞台布景和人物设置上极为特殊的简洁特性,也就相应地限制了蒙太奇镜头的使用范围。其镜头形式主要以中景和全景为主,且极少使用近景与特写,同时镜头长度也主要使用固定机位长镜头,其目的是避免复杂的蒙太奇设计破坏唯一角色密集连续的台词输出。显然,这一弱化镜头存在感的处理方式,对于剪辑者而言是无奈之举,但其实际效果却恰好还原了剧场观众的观看视角,银幕前的观众也由此获得了趋于一致的临场体验。简单的舞台置景以及大量的中全景镜头,恰如其分地避免了电影化裁切对舞台现场造成的信息损耗,长镜头的使用也保证了前文谭霈生所强调的“舞台话语完整性”。此时,戏剧内容和银幕镜头在叙事范式上达到了相对平衡,并规避了戏剧“场”的概念与电影蒙太奇镜头之间的观看范式排斥反应。虽然对于大部分主流戏剧而言,复杂的舞美设计与演员间的多线索互动已经成为行业营销卖点,因此也就不可能常采用《伦敦生活》那般“不换场、少动作”的方式进行拍摄,但是当独幕剧较低的市场占有率与较高的媒介契合度呈负相关关系时,恰能说明NT Live 这类直播戏剧在进行媒介转译过程时所面临的普遍矛盾。
二、银幕媒介削弱戏剧舞台的临场感
NT Live 在早期发展阶段,主要采取同步“直播”形式,以满足超越剧场容量限制的全球观看需求。数字直播技术则有效地解决了“异地同步”问题,众多剧院、电影院和艺术馆等场所通过“分剧场”屏幕与主剧场在时间上保持高度一致,以此期望最大程度地保留戏剧舞台的现场参与感。但是,出于扩大传播广度以及增加经济效益等现实因素考量,英国国家剧院对放映方案做出了调整,仅将直播形式用于NT Live 剧目的全球首映,随后该剧目则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进行影院级加密录播回放。无可避免地,这种方式在时间维度上极大地削弱了银幕前观众的临场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使NT Live 与传统电影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加模糊。特别是当National Theatre at Home订阅制项目上线后,其与Netflix 等流媒体影视平台已无二致。由此可知,尽管NT Live 更利于戏剧艺术的全球化传播,但是银幕重新构建的媒介壁垒却显著削弱了舞台表演所特有的现场魅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 银幕壁垒阻隔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正如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所言的“一出戏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其现时性艺术核心恰恰揭示了戏剧舞台与电影银幕之间的重要差异,即前者存在于进行时态,后者则属于完成时态[21]。当置身于在场氛围时,观众会被舞台上现时且直接的表演所吸引,并会对戏剧舞台“再现”的角色行动做出同步反应[22]。相应地,观众也会成为戏剧表演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观众会随剧情起伏而展示出或激动或悲伤的临场反应,并成为烘托舞台气氛的重要环境因素,进而影响到台上演员的表演效果。换言之,舞台表演本质上乃是一种必须引起观众注意的即时活动[23]。特别是在戏剧发展早期,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直接互动更是作为一种演出常态而存在的,如各国都常采用即兴表演作为引发观众注意的主要方式。我国宋代的杂剧以及古希腊的酒神祭祀表演都强调舞台表演应当即兴、即景、即时地迎合现场观众的情绪[24]。根据《都城纪胜》与《梦粱录》的记载,杂剧已经专门设立“引戏”一职以迎合观众并进行适当解说,同时设副净和副末两人进行装傻揶揄以调动现场气氛,即“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浑”[25]。发展至明清传奇阶段,更是在副末开场时强化了角色与观众进行双向交流的规范化演戏程式。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知,副末在开场流程中可以根据演出现场实际情况跳脱出剧情同观众进行互动,其说词多为即兴发挥而非根据既有文本照搬照演[26],即所谓“做寻常熟事”以调笑乐[27]。
虽然,戏剧艺术在千百年演进过程中愈加注重舞台叙事的规整化,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戏剧艺术实践环境中,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基础的体验派戏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着相对主流的理论位置,强调演员应当在“镜框舞台”中进行“视若无人”的忘我表演,但是这种强调即兴的表演形式却并未消失,而是在喜剧以及实验性戏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大部分喜剧表演中,观众笑声为演员提供着演出效果的实时反馈,演员也需要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演出状态。甚至在实验性戏剧日益流行的当下,一些沉浸式戏剧(immersive theater)的叙事流程本身就是依赖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现场互动来实现。如亚历山大·赖特(Alexander Wright)在他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中就会邀请观众参加剧情内的舞会派对,观众的身份也从看客转变为群演,并成为整幕剧叙事结构的一部分。显然,这种不可复制与不可再现的即兴互动(交流)效果无法被电影银幕还原。或者说,银幕成为一道实质的“墙”,使得戏剧的临场氛围与观众相隔离。NT Live 银幕前的观众无法体验到真实剧院周围观众或激动或惊喜的情绪变化,也无法直接与演员产生情绪上的双向互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交流,并不代表观众需要参与演出中,也并非演员需与观众保持连续的正向反馈,而是指双方都处在一种共同但又相对独立的间离环境之中。周宪在《布莱希特的诱惑与我们的“误读”》一文中对此解释道:“即使是最自然主义的戏剧,最写实的‘当众孤独’式的表演,也存在着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内在)交流。”他认为布莱希特试图推倒的“第四堵墙”不应简单地与剧场的交流性形成对立,所谓的剧场性也并非指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直接互动[28]。所以,为要回归剧场性而打破第四堵墙,也不应当只关注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外在互动,而是要正视双方在剧场情绪(氛围)上更为普遍的内在默契。正如波兰著名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所强调的,只要观众与演员之间存在“观看—表演”的实质关系,就必然存在内在或外在的交流[29]。同样,周宪也认为这种非直接交流的剧场性存在于一切戏剧之中。这是因为,演员所表现的叙事意义会不断传递给观众,并根据自身期望和文化背景对其进行“解码”,从而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28]。或言之,演员与观众分居舞台上下,共同在无形的第四堵墙下沉浸于剧情,却又无比清醒地在各种笑料或感叹间展露出真实的情绪交换。所以,当直播戏剧银幕将这堵“虚幻的墙”实质化,观众的开声欢笑或者动情感叹也都无法透过银幕传递给演员,其剧场的多重交流性也便消失殆尽。不过需要补充的是,虽然电影镜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打破第四堵墙的效果,如在《安妮·霍尔》以及《刺杀肯尼迪》等电影中角色常会直视镜头与观众说话,但这是在电影概念上突破银幕边界并探入虚拟化观众视角中进行的单向诉说,而非是如剧场一样可以发生实质性的双向交流。
2013 年的NT Live 版《麦克白》(Macbeth)便生动地展示了现场观众与银幕观众在观剧体验上的明显差异。该剧的演出场地选在具有200 年历史的曼彻斯特圣彼得教堂,并且舞台上铺满了混有雨水的泥土以真实再现年代久远的故事环境。加之,该剧重新“解构”了观看席和演员间的舞台边界,将观众围在教堂内两侧的木栏后,使他们获得了类似于陪审团的近距离观剧视角。甚至在部分情节中,演员在打斗时会将泥土溅到观众身上,从而瞬间增强观众的故事代入感与参与感。然而,对于在银幕前观看直播的观众而言,特殊的舞美布置和临场惊喜都被简化为与己无关的纯粹背景,创作团队专为现场观众设计的沉浸化互动元素也因银幕的阻隔而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本剧真正的观众仅是那些位于教堂木栏两侧的人,除此之外的观众无论使用何种规格屏幕观看,都仅是获得了本剧的“影印”而非本体。也可以说,当现场观众成为银幕背景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在观赏NT Live 时就成为“观众的观众”。
(二) 银幕壁垒激化了戏剧与电影间的表演审美冲突
正如上文所言,戏剧舞台所呈现的最终效果,不但取决于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更是演出现场各种因素杂糅而成的综合性结果。这意味着世上并不存在两场完全相同的戏剧,观众的每一次现场观赏都是独立且全新的体验。因此,观众对于偶发因素的接受程度也就成为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又一审美差异。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在其环境戏剧理论(environmental theater)中明确指出,戏剧不应仅局限于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而应该在包括观众席在内的全体空间环境中展开,应当着重突出演员表演与观众观看之间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剧场元素都可以自由表达,无须为了凸显演员的表演而压抑其他剧场元素[30]。他主张在实际演出中,即便演员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角色的行为或言语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能通过表演使观众确信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仪式”中就足矣[31]。如他在作品《69年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in'69)中,就十分强调演员的真实表演反应与观众的即刻反馈。扮演狄奥尼索斯的女演员在排演时说出台词“我是一个神”后立刻笑场,因为她无法在演出时相信自己就是女神,但是这在谢克纳看来却并非失误。他告诫演员不必强使自己相信,而应该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说话。实际演出过程中,女演员的笑场引来观众一同发笑,现场氛围也并未尴尬反而十分融洽[32]。孙惠柱对此评价道,此刻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已被打破,双方在同一情境下形成了紧密的交流连结和情感统一[33]。不过谢克纳同时也认识到,虽然环境戏剧不赞同演员完全沉浸于角色中的斯坦尼式表演,但也反对演员脱离角色身份感性状态的表演认知,所谓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乃是在强调演员的“双重任务”,即演员不应当只是“演出来”而是要同时“做出来”,如此才能使他者相信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场”内以共情[34]。也就是说,只要演员所谓的失误是符合在场情境下的合理反应,那么就没有违反观众的主观观剧直觉,自然也就不会造成严重的出戏失误。
虽然演出现场的偶然性事件无法代表戏剧演出的常态,但其对于喜剧这类需要调动现场观众气氛的剧种而言,也确实经常成为重要的舞台幽默效果来源。如英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学者A.C.布拉德雷(A.C.Bradley)就对戏剧偶然性问题如此说道:“偶然事故所玩弄的把戏,往往构成了喜剧情节的一个主要部分。”[35]虽然布拉德雷所讨论的偶然事件主要指的是在剧作中推动事件发展的冲突设计,但是喜剧演出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也可以在恰当的处理下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一环。在观看戏剧时,演员笑场、道具故障或灯光错位等舞台失误时常发生,不过多会在演员娴熟的应变处理下被巧妙化解,甚至成为当场戏剧的独特亮点。例如在NT Live 版《天使在美国》(AngelsinAmerica)的演出过程中,演员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就在医院探望场景中出现了笑场失误,但与《69 年的狄奥尼索斯》不同的是,喜剧元素本身就在剧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一偶然行为非但未引起现场观众的不满,反而加大了此处情节的幽默效果,并意外地引发了比预期更加热烈的笑声。然而,当该剧在YouTube 以及哔哩哔哩等流媒体平台播出时,却受到了一部分观众的质疑。网友在留言区以及弹幕区留言表示:“加菲(加菲尔德)笑场了”,“怎么不把这段剪掉”,以及“现场的人不觉得尬,但我觉得尬”,等等。这说明,电影银幕对于现场偶然性事件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原本被剧场观众视为意外之喜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却变成了真正的演出事故。
这种表演审美上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两种艺术媒介对于“剧场性”的兼容差异,或称之为“在场”需求差异。因为电影相对更加注重镜头语言的叙事结果,即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影像设计。而戏剧则在叙事之外,尤其注重围绕舞台的在场氛围,而非单纯的演艺呈现。实验戏剧人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等认为,舞台、图像与音乐等都应为创造性动作本身而服务,其目的是调动现场观看者的情绪,而非只能以实质性叙事为首要任务[36]。特别是英国国家剧院近些年推出的诸多具有实验性色彩的剧目,若暂时抛开NT Live 的银幕录制需求,《裘力斯· 恺撒》(Julius Caesar)与《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等作品本身就极其注重舞台之于观众的调配作用。例如《裘力斯·恺撒》就几乎完全拆解了戏剧第四堵墙,该剧以Live House(Live Music House 的简写,中文释义为“现场音乐场所”)的形式将舞台设置于观众中间,并以真实的摇滚乐队演出作为开场。其间,观众的自由交谈、交杯畅饮以及剧场主持人的演出信息介绍,都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该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戏剧沉浸感与互动感都在此刻获得了极大的延伸。但是,当NT Live 版本在影院以及视频网站平台放映之时,开场多处观众冷脸发呆、接电话离场以及演员调琴失败等镜头,都不同程度地被部分观众批评,认为其观感粗糙且编排随意。显然,这些发生在演出现场自由、偶然且不受控的行为,仅属于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专属在场互动”,但却并不在电影所需的叙事镜头选择范围之内。面对银幕之上的NT Live 戏剧内容,观众自然会按照观赏电影的范式惯性来评价舞台现场的偶发性失误,并将其归类为无差别的演员表演事故或者剪辑制作事故。换句话说,银幕前的观众无法获得与舞台现场观众一样的临场体验,观看转播或录播让他们成为处于现场互动和意外笑料之外的“旁观者”。
三、元宇宙场景下直播戏剧的难题纾解与发展机遇
综合前文所讨论的NT Live 发展困境,可知其主要限制因素源于艺术媒介之间的兼容性冲突以及蒙太奇镜头带来的叙事差异。但可以预知的是,随着XR(Extended Reality,是AR、VR、MR 的总称)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播戏剧观众终将摆脱屏幕的限制并在虚拟空间内获得更为真实的观赏体验。需承认的是,作为元宇宙(Metaverse)底层基建的XR 技术尚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它们既无法解决沉浸场景下电影蒙太奇剪辑的叙事兼容性问题,也无法较好地实现电子游戏复杂的互动操作与符合人体工学的位移效果,而是仅能满足有限互动条件下的全景观看视角。因此,目前较为主流的娱乐文化产业仍未能融入元宇宙应用场景之中。不过,由于戏剧与电影、电子游戏这类近现代大众艺术形式存在着较大不同,其较低的媒介叙事技术门槛却正与目前元宇宙技术水平相契合。因为戏剧既无须银幕作为观赏媒介,也无须与文本保持即时的直接互动(强互动),所需要的仅是在固定位置以自由视角观赏演员的连续性现场表演,而这正是现阶段VR 技术最擅长的应用领域。由此而言,NT Live 因银幕而生的诸多叙事冲突也将在元宇宙场景中得以解决,并在文化产业领域成为一个更具实践意义的试验者。对此,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NT Live 在元宇宙中得以摆脱蒙太奇镜头叙事方式,从而获得与舞台现场趋于一致的观看视角。3D 电影作为当下最为普遍的沉浸式观影应用类型,依旧没能有效地解决其在影像技术上的兼容问题,即三维内容与二维蒙太奇剪辑在空间层面上的冲突,仍无法寻得合理的融合叙事范式。究其原因,蒙太奇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的、非连续的二维平面组接方式,所展示的内容也是对三维时空的降维与重构[37]。或者说,这种平面叙事策略是基于景别、角度、景深以及透视等摄影元素进行的有机调度,从而还原立体空间内的复杂位置关系[38]。然而3D 电影则与真实世界的时空向度保持高度一致,人类感官也就本能地趋向于真实环境的连续性认知原则。因此,当蒙太奇剪辑对3D 影像进行分割重构时,这种与真实世界连续性体验不相符的知觉错位就极容易导致观众产生排斥反应,即基于观看媒介惯性的思维认知与源于生理本能的感官认知之间的强烈冲突。甚至,部分电影中的高速切换镜头常会引发观众的视觉诱发晕动症(visually induced motion sickness,俗称3D 晕眩症),即视觉神经中枢面对大幅度、高频率、碎片化的“虚假运动”时所产生的自我保护反应[39]。由此可知,电影艺术运用3D 影像技术应符合人体基本的时空认知习惯,而长镜头无疑是最为合适的蒙太奇表现手法。如《阿凡达》(Avatar)中的高空骑兽飞行长镜头,以及《地心引力》(Gravity)开篇长达13 分钟的太空漂行长镜头,都以极强的真实感与沉浸感成为电影技术史上震撼人心的典型案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电影艺术对于长镜头的应用是极为谨慎的,因为限量过大、过程集中的长镜头必然会造成节奏拖沓与沉闷等叙事问题[40]。而戏剧表演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银幕化的“长镜头”艺术,这就恰显示出了其与3D 摄录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之间的互补性与契合度。
进一步讲,元宇宙XR 技术为NT Live 提供了相比3D 技术更为真实的双重立体视角,即观看内容的立体视角和观看环境的立体视角,以还原剧场观看体验。其一,观众在剧院中的连续性观赏体验被3D 长镜头完整还原,这既能够复现舞台内容的景深空间感,且不存在反直觉的立体画面高速切换问题。对此,若将直播戏剧的XR应用场景与现有的XR 电影相类比,可以发现虚拟空间内的电影叙事沿用了类似于戏剧舞台“场”的形式来取代蒙太奇剪辑,即单个电影镜头的演出时长与剧情时长大体一致[41]。如VR 动画电影《珍珠》(Pearl)全片时长5 分58 秒,却仅有36 处跨度时间剪辑,其目的就是以较长镜头来引导观众“浸入”叙事空间,并最大化减轻眩晕[42]。那么,前文所讨论的NT Live 版《伦敦生活》,其大量长镜头便可以从银幕媒介中的“异类”成为XR 新媒介中最符合观感的代表。其二,XR 技术以创造真实空间感为目的导向,这对于强调立体临场感的NT Live 戏剧而言,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数字化技术革新契机。XR 技术不但能够复原仪式化剧院的真实环境,而且还能够提供固定位置下的自由转换视角,观众也就得以从“人—银幕”这一单向且固定的观看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与剧院观赏几无差别的360 度临场体验。不过,由于直播戏剧的元宇宙应用与银幕空间应用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别,两者对于临场立体视角的还原要求自然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虽然在还原“观众—演员(舞台)”层面的临场体验时,二者的共同实践诉求是自由且连续的观看视角,但是却在“观众—其他观众(剧院空间)”关系上指向了全然不同的路径。这是因为当观众在电影院银幕前观看直播戏剧时,即使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与剧院观众处于同一空间,但是由于影院环境与剧院环境之间存在着合理的相似性,影院观众也同样处于多人观看的仪式氛围之中,所以直播戏剧在银幕空间内依然能够保有较大的“观众—观众”关系层面上的临场体验。然而在当下已有的元宇宙实践中,观众所处的观剧环境则是相对独立且简陋的虚拟空间,基于观众共同在场的观剧氛围也就无从谈起。不过,随着美国苹果公司于2023 年夏季推出混合现实设备Vision Pro,其“数字化身”(digital persona,或称作“数字化人物形象”)技术已经能够依靠成熟的生物扫描技术与动作捕捉技术,还原出使用者在现实环境中动态且自然(无遮挡)的面部动作与肢体动作[43]。加之这一技术已在Vision Pro 的虚拟FaceTime 会议功能中得到了初步实现,那么将其应用于虚拟剧院空间内以还原多人观剧环境,也就成为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技术解题路径。
第二,虽然NT Live 对还原临场感有明确需求,但却并未过度看重其参与性。究其根本,戏剧依旧是一门观赏艺术,而非纯粹的互动艺术。即使《玩味探险家》(TheGrandExpedition)、《黑衣女人》(TheWomaninBlack)以及《成都偷心》(StolenHeart)等国内外沉浸式戏剧日益流行,但其小众的先锋实验性表明它仍未能建立起独立且成熟的戏剧叙事体系,众多创作者依旧处在早期的摸索过程中。所以,传统戏剧仍然是发生在剧院第四堵墙之下的主流产物,NT Live 的媒介任务也仅是还原客座之上观众观看舞台表演的现场体验,对元宇宙的技术需求更多地侧重于视觉和听觉的全景式还原,而非如沉浸式戏剧或者VR 游戏一样直接参与剧情内容之中。加之,任何艺术形式若要实现内容创新都无法跳脱出当下应用技术的限制,只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优势才能最大化推动新内容范式的落地实践。例如XR 技术公司Magic Leap 长期无法将增强现实眼镜产品从概念转为量产,以及Meta 公司(原Facebook 公司)至今都无法基于Oculus 设备实现Horizon 虚拟社交平台的日常化交互操作,都在反证超出现有技术水平的产品概念无法实现真正的商业实践。多纳·L.霍夫曼(Donna L.Hoffman)与托马斯·P.诺瓦克(Thomas P.Novak)在1996 年将“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概念应用于网络研究时就曾指出,“心流”(flow,个人精神力完全倾注于某种活动上的主观感觉)在虚拟空间内的发生,取决于“挑战”(challenge)与“技巧”(skill)之间的平衡。若技术挑战太高,则会在不完备的成品中产生挫败感,太低则极其容易降低探索兴趣并失去创新价值[44]。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NT Live 还是3D 电影,它们当下不尽人意的观看体验,大多都是观看需求与媒介技术不适配的结果。而在可预期的未来,相比VR 电影或VR 游戏这类高互动要求与高叙事复杂度要求的艺术形式而言,NT Live 仅依靠成熟的摄录显示技术以及全景声技术,已然能够实现较为完备的戏剧舞台心流体验,进而成为目前最具有应用潜力的文化产业分支。
具体说来,一是,目前相对成熟的3D 与XR摄影技术已经具备全景视频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8K 分辨率的Micro OLED 显示技术也实现了近距视网膜级内容的输出能力。加之,120 帧高刷新率技术也从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BillyLynn’sLongHalftimeWalk)的影院级应用逐渐普及至寻常用户的移动设备屏幕,观众基本能够透过XR 设备还原现实剧场的高分辨率与高刷新率肉眼体验[45]。二是,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技术在部分高端院线中已经得到广泛商用,并在苹果(Apple Inc.)等科技公司的进一步改良下实现了“头部追踪”技术的消费级耳机设备下放。观众能够通过杜比全景声设备在自由转动头部时获得虚拟化的多声位效果,从而还原剧院观赏时的基本声觉体验。三是,虽然 Oculus 以及HoloLens 等XR 产品所具备的动作捕捉技术依旧不够完善,但是已然能够还原用户的简单肢体行为,NT Live 等内容提供方也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获取观众在观赏时的动作反馈,从而在直播戏剧内容中提供即时的简单互动。需要明确的是,NT Live 具有元宇宙商业化潜力的原因在于,前两者成熟的声画技术已经足以解决虚拟空间观剧的主要视听问题,发展仍未成熟的后者恰也是观赏主流戏剧的“弱需求”。总之,虽然当下元宇宙技术发展水平难以完成“复刻真实世界”的宏大任务,但是已经能为NT Live 等直播戏剧率先踏入元宇宙虚拟世界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撑,并为其他文化产业分支提供了借鉴基础。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NT Live 等直播戏剧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舞台效果折损。但在满足基本观赏需求与追求高质量观赏体验之间,显然前者是更为迫切的艺术普及任务。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存在着循序渐进的接受层级,无论是传统影碟介质还是在线流媒体,都被视为满足最基本欣赏需求的有效手段。在满足此基础需求后,观众才有可能接受更高一级的观赏方式,才会产生进入实体剧院体验舞台现场表演的内在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NT Live 成为全球范围内普及戏剧艺术的先驱力量,值得其他国家地区对这一传播形式进行参考。
综上,NT Live 这类直播戏剧仍会在互联网浪潮中保持进一步上涨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元宇宙技术不断革新的当下,其必将成为观众进行跨地区观赏优质戏剧的一个重要选择,这也为文化艺术产业创造了新的转型机遇。不过无法忽视的是,NT Live 在当前阶段仅能做好基本的观看功能,至于观众何时能获得与剧院相接近的欣赏体验,则需要在科技融合过程中进行更深层的叙事范式探索。在可预见的未来,NT Live 将于元宇宙虚拟世界中实现更加真实的临场效果,蒙太奇镜头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将被适时地解决。彼时,业界与学界将需要讨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即剧院是否真的会消亡,戏剧又将以何种形式被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