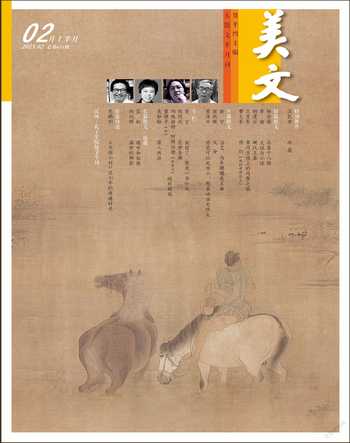传灯
2023-02-13曹文军
裴先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了,膝下似无儿女,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冬天裹条黑色的围巾。布鞋白袜,走路慢腾腾,很轻,总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苍白的脸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不怎么爱笑,颇有些落拓书生的样子。
裴先生早年毕业于名校,但何以到我们镇上教中学,不得而知。他那时教二个班的语文,最喜欢两个大文人:苏东坡和鲁迅。上课时,讲着讲着,就讲到东坡居士和迅哥儿那里去了。对于东坡,裴先生是引为知己的,课上经常为他鸣不平,颇有些“独夜有知己,论心无故人”之感。对于鲁迅,他极为敬仰,引用的时候,一字不漏,可见平时读得烂熟,“鲁迅先生说过……”总让我想到《论语》里的“子曰”,久而久之,我也爱看鲁迅,半懂不懂地读《呐喊》《彷徨》。
裴先生是城里人,但似乎一直住在学校。有时候,我去得早,会看到裴先生蹲在低矮的宿舍前面刷牙。许是牙口好,普通话极端正、流利,没有一点点方言的尾子。仅这一点,就足足让我们这些乡下的少年佩服不已了,因为在我们这边,说起话来,总是平翘舌混杂,“柿子”念成“四子”;“农”“龙”不分,“农民”常说成“龙民”。其实,在裴先生教我们之前,上课时,无论师生,没有人说普通话的。直到他来了,语文课才渐渐有了“语”和“文”的样子。
总之,裴先生就是与其他老师不太一样。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似乎还有些风度翩翩的感觉,这风度,也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我心中,就是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那时最得意的要算作文。因为平时爱看闲书,小学时就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四大名著。我的姨表弟王诚住在城里,他订阅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让我大开眼界。初中高中虽然学业紧张,但我仍偷偷摸摸读了许多小说散文。这些课外书让我受益匪浅,语文这门课,我不用花多少工夫,每次考试却都在班级名列前茅。现在回想起来,教科书许多都忘了,但那些课外书却像刻在脑子里。说来奇怪,裴先生竟是不反对读课外书的,他订阅的《人民文学》杂志,常常在班上传阅,而且允许我们到他宿舍借书看,我记得借过《三侠五义》《包法利夫人》和《唐璜》。这让我对他的钦佩又多了一层。
我总是满心欢喜地期待着语文课。
记得裴先生第一次布置我们写作文,写家乡的树,我就写了一篇柿子树,文章的构思模仿鲁迅的《秋夜》,开头便是:“我家屋前有一棵柿子树,还有一棵也是柿子树……”如此等等。隔了一天,作文批改发下来了,我先小心翼翼打开,看看究竟得了多少分。我想,裴先生如此博学,而且那样有风度,他肯定是识货的,他会不会给我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要知道,在裴先生任教之前,我的作文总在班上排第一。也许,下一节课,他就要在班上朗读我的文章了,用他那极为周正、流利的普通话。经过他抑扬顿挫地朗读,想必我的文章又会增色不少。
而这次,我只看见一个刺眼的“58”分,我不敢相信,但红笔写的分数,像块图章那样印在那里,赫然在目,确凿无疑。那是我自从上学写作文以来,绝无仅有的分数。那个博学而有风度的裴先生,那个说普通话像蝴蝶飞舞的裴先生,竟就这样无声地给我了一巴掌。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很烫,心仿佛跳到了嗓子眼。整整一堂语文课,裴先生像往常那样讲得抑扬顿挫,也许,比以前讲得还要好,他似乎又提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因“乌台诗案”下狱的苏东坡……我恍恍惚惚,挨过了漫长的一课。
放学后,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着作文本,硬着头皮敲开了裴先生宿舍的门。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裴先生临时住在那里。门前用砖瓦搭了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凤仙花,还有金鱼草,旁边是一棵很大的柿子树,果实熟了,高处无人采摘,上面停了几只啄食的鸟雀。
裴先生听我结结巴巴说明了来意,却不做声,只见他拿出上衣口袋挂着的钢笔,转身在旁边的纸上写了一个题目,用中指敲敲那几个字,然后点点头,盯着我。我立刻明白了,他要我现场重写一篇。我又羞又气,觉得自取其辱,但仿佛急中生智一般,打好提纲之后,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写完天已向晚,夕光从西边流进来,照在裴先生冷冷的脸上。他依旧不说话,却从窗前的方几上拿了一只火红的柿子递给我。我拿了,头也不回一直走,快到家时,才发现手上还捏着软软的柿子,已经裂开了,手上全是汁水,心头顿觉无名火起,一气之下,将那柿子扔得老远。
第二天語文课,我故意迟到了一会儿,及至推进门去,先吃了一惊,裴先生早已站在讲台前,他通常会稍晚到的。我低着头,故意不去看他。想不到,耳边忽然传来他那抑扬顿挫的嗓音,他喊住我,我以为又要挨批了,但也不再紧张,慢慢镇定下来。想不到,他很平静地说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在上课之前,先说明一件事,上次布置了一篇文章让大家回去做,这位同学的文章,我在批阅时以为是抄袭哪本书上的,所以给了不及格的分数,后来这位同学主动来找我,我当场命题,让他重写了一篇,待我仔细读了第二篇后,方才知道错怪了他,为此我向他道歉!”
说完,他竟对我作了一揖,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接受这样的古礼。接着,他将我那篇文章在班上当场朗读起来,读得声情并茂。我恨不得将头埋到书桌里。同窗轻轻碰了我一下,我不知道是因为心情激动还是没坐稳,整个人一下子跌倒在地,顺带把桌上堆得高高的书本全拉了下来……
那次误会之后,我却因祸得福,得以经常出入裴先生的宿舍,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下,我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学校板报上,有时还被作为范文贴在橱窗里。每每在天黑无人之时,我悄悄溜到那儿,借着路灯,瞅上一眼,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回去。毕业后,我总记得裴先生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临别时的嘱咐:“人不吃饭会饿得慌,人不读书会浮得很!”
离开学堂后,与裴先生联系并不多,但常常午夜梦回,想起他上课时,原本平静的神情瞬间被点亮的样子。目光炯炯有神,像是要穿透窄小的教室,走到极远的地方去。
工作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这都拜裴先生所赐。我常想起裴先生那堆满书的宿舍。他其实并不藏书,只是热爱读书,而且借给我们读。彼时,学校的图书室非常小,适合我们读的书并不多,而他的宿舍却似琅嬛福地,大部分都是我们爱看的文史哲,记得有好几个版本的《聊斋志异》,差不多半个书架的外国文学网格本,还有康德的哲学史、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梵高的画册等等。我时常在周日的午后,去拜访他,陪他聊聊天,或者一人一椅,坐在窗下,细读一个下午。
很多书上,都有他用铅笔写下的批注,不用说,这些书,他都精读过。有的书,他还会在扉页写上一整页的读后感。我日后也养成了裴先生的读书习惯,喜欢在书上写写划划。我工作八年后,有一天忽然收到裴先生寄给我的信,用毛笔竖排写在宣传纸上:
“文军兄:
一别数载,颇为记念。前阵子听人说起,兄这些年孜孜矻矻,前途一片光明。从前,我也曾有些美丽的梦想,但都破灭了,所幸得才而教之,这是老来唯以安慰之处。兄素为我所敬重,心地纯粹,嗜书如命。现在我老了,书也看不进去,亦成了负累,故请兄来一趟,把有些重要的书取走,一来留个念想,二来传给你,我也放心。此外,屋前的柿子树也老了,旁边恰有棵少壮,我过几日请人起出,一并赠与兄,即希察收为幸。”
我知道这些书在裴先生心目中的份量,现在他竟托付于我,令人既感恩又惭愧。我知道事不宜迟,隔日便开车去了母校。
时维深秋,一股熟悉的谷香飘然而至。远远地,我看到裴先生站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他已非常苍老,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话说不多久,嘴角便流口水,他準备了一方手帕,时时擦拭。我心里顿然明白,他早已不是从前那个“风度翩翩”的裴先生了。
那天,我装了满满一车裴先生的藏书,还有他托人挖给我的那棵柿子树,临走拎着沉沉的一袋柿子。回转头来,裴先生仍站在学校门口张望,秋风拂起他额前的白发,背后的枫叶正火一样在秋阳下燃烧。
彼时,我恰好在一个老小区买了套二手房,便将裴先生赠送给我的柿子树种在小区里,从书房的窗口,正好能看到。柿子树从青涩的果子开始,我便开始关注着它的成长。满树的柿子从碧青到淡黄,又渐渐变成桔黄和火红,不断变化的色彩使我生出了许多期待。霜降来临时,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吱吱喳喳地叫唤。我像裴先生从前那样,留一部分果子在树上不摘,每天清晨,我走到书房的窗前,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红红的小灯笼,朝阳斜斜射在上面,表面似有一层光晕。望着柿子树,我总会想起裴先生。
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柿子树越长越茂盛,结的柿子也越来越多,而我随着工作调动,早已搬离了原来的寓所。那天傍晚,回去看望旧日的老友,我看到巨大的挖掘机停在老楼下,柿子树连同旁边的桂花树和紫薇已被连根拔起。因为要拆迁,小区大部分人都搬走了。从前那棵壮硕的柿子树上孤零零地挂着三两只小小的柿子,在倾颓的树干上显得落寞无助。
那一刻,我忽而想起一晃好些年没有裴先生的消息了。我总以忙于各种杂事为由,久未前去探望。我也不忍看他衰弱的样子,太残忍了。前几年,我听说乡镇的母校因为合并,也全部拆掉了,而裴先生应该愈发衰老了吧。
一转眼,秋风起,桂子花落,梧桐叶黄,满目萧瑟。那天,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一棵茂盛的柿子树,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悬挂在枝头,引得我痴痴地凝望许久。
我忽然流下泪来。
(责任编辑:李雪)

曹文军 出生于江苏泰县(姜堰)。自幼喜爱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读书写作运动三部曲,现在基层某部门工作。曾在报刊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努力用文字留下岁月的光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