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
——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2023-02-13李孝迁
李孝迁
范文澜和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两位巨擘。范主张西周封建论,郭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的学术分歧在史学界众所周知。从1940年开始,他们就有过学术商榷,进入1950年代,彼此交锋更为频繁,互有影响。然而,范郭的论著多采取隐匿的论述方式,又经多次删改,使双方原本存在或明或暗的呼应文字,变得更加隐晦曲折,不易建立起关联,似乎他们只是各自平行地发表观点,没有往复论辩。既有研究也有意无意间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和谐”面相(1)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研究作品是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李红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研究古史分期问题的代表专著有:林甘泉等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这些著作均详尽概述各位史家的学术观点,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着力梳理各种观点如何在具体论辩中展开,看不到参与者原本论述中的对话情境。,淡化或遮蔽他们之间同样存在论争、分歧、争胜,乃至掺杂意气成分(2)“经过两人互相砥砺,互相帮助,认真学习,严肃考证,终于对殷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趋于一致,两人都断定殷代为奴隶社会。至于西周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两人继续进行认真地讨论,他们分别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各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又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在这方面,范老和郭老一样,足称模范。”(冯世昌:《百家争鸣的模范——读〈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札记》,《光明日报》1980年7月1日,第4版)此处所建构的范文澜与郭沫若的对话情境,或与实况略有出入。。这不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3)吕振羽承认:“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因而其相互间的争论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不只是在和敌对流派的斗争中,而且是在自己阵营内的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成长、壮大、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就是人民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真理愈辩愈明,问题愈辩愈深透。”(吕振羽:《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大力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60年12月24日,第3版)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家间原本潜在的各种论辩,一方面这是重建史实的工作之一,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可更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不仅是在和敌对势力论战中成长,也是在与阵营内部的各种观点交锋中走向成熟。。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准确理解论著中“说了什么”固然重要,而“为什么这样说”,尤其范文澜论著前后多次修改,意欲何为,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似更为紧要,过去对此关注不够。而若欲解答这些问题,重建史家间潜在的对话、较量和论辩的语境,不失为把握言说意图的一条可行路径。本文无意评判范郭学术观点的正误,而是通过比较范郭各种论著的学术观点、具体论述、细微修改,结合新发现的范郭未刊书信手稿,揭示他们在字里行间“你来我往”的隐微对话,动态展现两人论述古史分期问题的互竞辩难的进程,希望对他们“何以如此言说”有更进一层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虽聚焦于重建范郭的学术对话,但他们论著中的潜在对话者并不限于彼此,而是面向整个学术界的。
一、由显入隐:《十批判书》前后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学术交集始于1940年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订正版后记》,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第355页。。1940年范文澜初到延安,即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是他唯一一篇公开与郭商榷之文。他利用新接触到的权威理论《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1938年),作为正误标准(5)范文澜哲嗣回忆父亲:“为了写好通史,他在一本《联共党史简要读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章上写满了眉批,划满了圈圈杠杠。”(范元绶:《悼念先父范文澜同志》,《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1-42页)。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6)范文转载重庆《群众》(第5卷第4、5期合刊,1940年)时将“我党”改为“我们”。主张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范氏批评前者而支持后者。
范文澜先称道郭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尔后提出具体的商榷意见。关于殷代社会,范氏经论证得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备具,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至于西周社会,他认为“西周已开始封建社会。当然,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保留还是很多,但这些残余之能保留下来,只是由于传统及惰性力,不能再有所发展了。我们不应该误认残余为这个社会的本质,而忽视新因素的向前发展”。范还指出郭以《公刘》篇“取厉取锻”推论西周已有铁器,“是不甚有力量的”。对于郭氏把古公描写成一个穴居野处的野蛮人,骑着马走到岐山之下,嫁给姜女酋长作丈夫,范氏以为东周人还不知道骑马,“这未免近于文学而疏于考证”(7)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第16-18页。。范文最初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同年转载于重庆中共机关刊物《群众》,郭应该了解范的批评。此后,除了1951年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点名与范论辩之外,他们不再公开商榷,默契地转向以隐秘的方式在论著中不时向对方喊话。这种“玩法”,局外人或摸不着头绪,但当事人则能心领神会。
1944年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下称《自我批判》)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编》)有所批驳,可视为对当初范批评的一种回应。《自我批判》一文,矛头虽主要指向吕振羽和翦伯赞(8)详参李孝迁:《〈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但也包括范文澜。郭沫若解释“共和行政”:
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9)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第40页。
吕翦对此的认识与郭一致,唯范氏《简编》依据《史记》谓:“周公、召公共同执行国政,号称共和。”(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第33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者和年份,均指此版。郭氏口中的“近时的新史学家”“这样的朋友”,指的是范文澜。对于郭指控的“硬伤”,范并不以为误,《简编》订正本(1948年)和修订本(历年版本)一直坚信《史记》的观点。1953年范在《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始作自我辩护:“《竹书纪年》采战国游士的寓言,讹称共和是‘共伯和干(夺)王位’。……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如《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类,信口说来,不负责任,《竹书纪年》却误信寓言为真事,后人又误信《纪年》的误记为真史,一误再误,大概都是为了好奇的缘故。”(1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4-77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者和年份,均指此版。范氏所论并非无的放矢,正是答复郭氏对他的批评。
郭沫若《自我批判》指出同道所犯的错误,如误读“弇奴”“归矛”“帚侄”“臣在斗”“寇周”等,翦伯赞和吕振羽皆相沿不改。相较而言,范文澜在根本观点如西周封建论及其相关论证上虽与郭氏立异,但在某些细节尤其他不擅长的卜辞、金文释读方面,他的态度比翦吕二氏积极,愿意采纳郭的少许批评(12)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承认“甲骨文、金文多采王国维和郭沫若说”。,这从《简编》订正本“删”和“增”的文字中可寻暗痕。《自我批判》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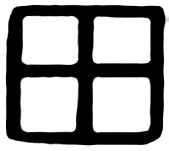
《简编》订正本修改“墨子及墨家”一节,与郭沫若《墨子的思想》《孔墨的批判》有直接关联。郭氏从未改变1923年以来的“非墨”观点(20)“墨子这位大师,我们如能以希伯来的眼光批评,尽可以说他是中国的马丁路德,乃至耶稣,然我们如以希腊的眼光来批评他时,他不过是一位顽梗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罢了。”(郭沫若:《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创造周报》1923年第7号,第6-7页)。《墨子的思想》指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21)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第8卷第15期,1943年,第423页。《孔墨的批判》又痛斥:“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前驱,是古代的鲍尔塞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22)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第101页。1940年代左翼史学界扬墨者居多,郭沫若的打击面甚广,不见得针对范著,但他的批评让范意识到原先论述或有不妥。《简编》延安版说:“墨家的政治目标,要改善人民生活,每个人都得工作,都得饱食暖衣,更进而得富裕的生活。……那时候如果墨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也许中国社会要提前改变它的性质。”(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77页。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原始共产社会的面貌。《简编》订正本不再把墨子思想比附成古代的共产主义,删除了这段文字,还将“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中的“政治解放”改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删除“墨子知道压抑最下层的庶人,不团结是不能希望解放的”,降低了墨子的政治觉悟。此外,《简编》订正本增添了对墨子思想的负面论述,如墨子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奢侈浪费,表现了庶民当时的要求,“但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实际上是叫庶民片面的去爱王公大人”(2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第160页。,这正是郭氏独有的见解,即“所谓‘兼爱’岂不就是偏爱”(25)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第8卷第15期(1943年),第426页。。
二、围绕《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论争

不过,郭宝钧还顺带说到周代殉葬情形:
殷代而后,此风稍戢。……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29)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第3版。
郭沫若对此判断相当不满,批评郭宝钧“缺乏马列主义的掌握”,“从旧史学的束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解脱。因此,他虽然抱着一大堆奴隶社会的材料,却不敢下出奴隶社会的判断。反过来,仅靠着一小撮单位不同的材料,却又下出殷周不同的大判断来了”(30)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第3版。。4月26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再次嘲讽“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智识”,“捧着金饭碗讨饭”(31)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第3版。。他担心“这样轻易的判断还可能使不假思索的人下出更进一步的轻易的判断,便是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不是。这个关系却可不小”(32)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第3版。。郭氏确有先见之明,果不其然,稍后范文澜、荣孟源就据此表示商周社会制度的不同。
1950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又举证郭宝钧《记殷周殉人的史实》,作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直接的材料”。至于周代是不是奴隶社会?郭沫若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因材料被湮没,或被歪曲,要纠正过来是不容易的,必须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来证明”(33)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光明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3版。。
范文澜对史学界讨论殷代殉葬和郭沫若北大演讲应有所关注,1951年春,他借在华北局检讨《简编》之机,主动向郭沫若隔空喊话,重申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期的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范文澜说:
今天不是专讲这个题目,无须多说,这里只说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根据地下发掘,商朝社会里阶级极显著的存在着,这是断定商朝决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批人殉葬。……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但殉葬就有这样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3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范氏也发现郭宝钧讲殷周殉葬不同,有利于西周封建论者,遂成为他口中“最简单的理由”之一。范氏关于周代殉葬的信息——“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系由何处得知呢?在范氏演讲稿发表之前,它没有出现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也不是源于《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如果比对稍后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信》中“百五十五墓,遇殉者六人”云云(35)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第5版。,可倒推范氏应在检讨《简编》前已从郭宝钧处获悉(36)1952年9月,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说明》交代:“本编有关考古部分,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夏鼐先生指正,避免了许多错误。”此外,本编插图也“承郭宝钧先生、贾兰坡先生推选并作说明,为本编增色不少”。说明范文澜和郭宝钧有所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在自我检讨之余,用相当大的篇幅为西周封建论辩护,且不点名地批评了郭:
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其基本论据建立在“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这个原则上面,依据《联共党史》所昭示,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土地不能当作生产工具。所以用“土地并非私有”来判断生产工具私有的不存在,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又略带讥讽地说:
列宁《论国家》中说:“剥削形式的变换,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度的国家,这是有极大重要性的。”列宁这样深刻的指示,某些历史学者熟视无睹,绝不理睬,对构成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劳动的人们也搁置一旁,不在话下,一味企图用一块铁、一把犁、一头牛来解决古代历史问题,真是太简单太机械了。(37)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第575-576页。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及2002年出版的《范文澜全集》,所收录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都是经删节的《新建设》版。《新建设》编者按:“本文是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记录。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记录,以供阅读《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参考。”
范文最初发表在《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日),被《人民教育》(第3卷第2期,1951年6月1日)和《新华月报》第4卷第2期(1951年6月25日)全文转载,但上引这段讥讽文字被删去了。
关于这篇演讲稿形成的背景,范文澜在给《新建设》常务编辑委员陶大镛信中有所说明。1951年3月31日,范给陶的一封信写道:
我的自我批评稿到现在收回的指教信还很少,一时恐怕出不来。那是一篇正式自我批评的文字,需要在《人民日报》上登载。这一篇是我在华北局的讲演稿,比起前一篇来是非正式的,是我个人的思想,有错误该我一人负责。现在送给您看看,是否可能在《新建设》发表。因为好多人(甚至山西、南方来信问自我批评何时发表)知道我要自我批评,都想看看,似乎可以先发表一篇非正式的。此稿系华北局同志整理,是否请您问问华北局是否同意。我对此稿发表还是不发表,把握不定,希望您仔细考虑,和熟悉出版规矩的同志商量商量,替《新建设》也替我个人考虑发表是否合式。将此稿提早寄给您,就是希望您有较多时间考虑它。
范所谓“自我批评稿”是针对旧本《简编》的检讨,有两种手稿:第一种原拟题目为“反动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改为“割裂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种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过第二种,并略作修改,建议范氏“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光明面’也提出一些,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38)转引自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第25-26页。按:赵庆云见过范文澜这部分手稿,其说可靠,与笔者所见的范信能相互印证。。第一种手稿就是范信中所提及的“一篇正式自我批评的文字”,也是他在讲话稿中提到的,“我要写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发表出来,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定本’”(39)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7页。,计划在《人民日报》发表,但此篇检讨最后并未正式刊出;第二种手稿是范信中说的华北局演讲稿,范接受了陆定一的意见,文末第二段确实补充了“古代历史的光明面”的论述。
范文澜主动把第二种手稿投给《新建设》,编辑部对文稿有所改动,又将修改稿反馈给作者审定。4月17日范给陶大镛回信:“胡绳同志把我的错误,似乎减轻得太多了,但我应尊重他的意见。稿中谈到西周封建问题,本不应占这样大的篇幅,因为有人(不同主张的人)在某些地方,说范文澜因主张西周封建,受了批评,要自我检讨,所以我想趁这机会约略提一提,但占篇幅不知不觉多了些。”此信透露了两方面讯息:其一,范文澜对于胡绳的删改并不满意。他在胡绳修改过的文稿基础上,恢复部分被删文字,如上引讥讽郭的一段文字,又将此稿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6月)。范氏此举的意图,明显就是要让郭看到这段文字。其二,范的讲话稿突兀地展开讨论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是为了回应“有人”散布谣言,他等不及正式检讨的定稿,先发表讲话稿,也是出于辟谣的考虑。范没有明说传谣者是谁,但从他文中刻意针对郭氏来看,此事或与郭有关。
郭沫若很快就看到了范氏《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不仅《新建设》,且《人民教育》《科学通报》上的范文,他也细读过(40)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4页,注三。。1951年6月17日,郭写了《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投给《新建设》,回应范的不点名批评。陶大镛收到郭文后,即转发范,6月19日范回复陶:
大镛同志:郭先生的文章,我同意登载,因为不登载,似乎有不让郭先生发言之嫌。但既登载后,我自应遵郭先生之命:“等待着严格的批评”,提出商榷之意见,一定要说到郭先生《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最基本的一点郭先生指出这是“中心问题”,即把土地当作生产工具,因而得出农民没有土地即没有生产工具,所以农民是奴隶。这种说法是不合常识的。我曾在发表的那篇文中暗示了这一点,此次郭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郭先生主张的“中心问题”。其他殉葬墨子说的是把秦殉葬扩大为一般,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不能说其中都是庶人之墓(除了三个以外)。一种制度必有残余,不能说周一个也不殉葬了。《诗经》我说《周颂》是西周初年诗,无人怀疑过,不是说其他的诗,也没有说大小《雅》是西周初年诗。等即使都照郭先生所说完全对的话,都还不是“中心问题”。如果那样正式提出来,我想,对郭先生是不利的。如果我被驳倒了,那是无所谓的,如果郭先生被驳得不利,是不是会引起其他枝节呢?这点请您和胡绳同志考虑。致
敬礼!
范文澜 十九日
6月20日郭又补充一些内容,当天陶就收到郭的《补记》。同日,陶一方面火速把郭的《补记》发给范,范当天即回复:“西周问题索性展开讨论,得出比较一致的见解,虽与今天无关,但前天的悬案能解决也是有用的,所谓‘火气’处不改也无所谓,因为在争论时,决不会因‘火气’引起‘火气’。不过改去当然更好。”另方面陶又赶快给胡绳写信:“关于郭老的稿子,我认为这期还是让它发表出来。文章写得有些‘火气’,似可改一些字眼,你看如何?范老看过了,给我一信,嘱我再同你商定。如果你觉得可以发表,是否仍可放在‘学术讨论’栏内?因为郭老写这篇东西,完全是‘商讨’的,我这样做,他不致责怪,同时,这样对范老也说得过去,你看如何?恳再指示,以便遵行。今将郭老原文和范老的信,一并附上。”并要求胡绳“如可能,敬恳于今天(廿日)下午四—五点将郭稿送还,我们还来得及送印刷厂”。但至晚上八点胡绳才收到陶信,故没有按时送还郭文。胡绳一开始主张对郭文“不要给做什么修改”,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改动了几处,让陶发给郭过目,并提出把郭文放在“学术讨论”栏目不妥。6月23日,郭给陶回信:“拙稿多经过朋友们看看是应该的。胡绳兄的删改,我完全同意。清样如能给我看看最好。”(41)以上所引范文澜、郭沫若、陶大镛、胡绳诸人的书信,均属手稿,不曾见刊于相关人物的全集、文集和书信集。
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针对范文所涉及的殉葬和《诗经》征引两个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范文澜引征《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奴隶与农奴的规定(42)“在奴隶占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奴隶主对于生产资料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一样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主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不完全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据此判定商朝殉葬和作祭品的人是奴隶,周朝废除用人殉葬和用人作祭品,因为农奴不能随意屠杀(43)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在范文澜向郭氏问难之前,王毓铨因见到1950年3月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订正本,于1950年6月10日撰写《周代不是奴隶社会》,也向郭氏提出商榷意见。有趣的是,王毓铨与范文澜一样,也注意到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经典定义,谓之“最明晰、最扼要、最中肯”(44)王毓铨:《周代不是奴隶社会》,《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19页。。范文发表在前,王文发表在后,故郭氏先回应范。郭沫若指出范引《联共党史》的规定,以能自由屠杀与否来判定奴隶与农奴,“那规定是正确的,但范先生的运用却不很正确。把视野专一放在人殉问题上,认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这应该是一种偏差吧?奴隶制度是最残酷的一种制度,封建制度要比它仁慈得多。假如周秦确是初期封建社会,那么当然的结论是周比商仁慈,秦比周更仁慈了。事实是这样吗?除开人殉制度之外,我可以举出几个残酷的例子。……这些所屠杀的俘虏虽然不是奴隶,可以说是奴隶的前身。此外,专杀奴隶的事,直到汉武帝时都还存在。……要说西周初年便已经废除了,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人,要从全面来看问题,从发展来看问题,才能够得到正当的结论”(45)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3页。按:此文收录于1952年《奴隶制时代》一书时有删改,引文“此外”之前的部分文字删改成“奴隶的前身是俘虏,大量屠杀俘虏在秦代前后都还盛行。我可以举出几个惊人的残酷的例子……”,郭氏或认为原先的反驳不够有力,故删去。。7月8日,郭氏在答复王毓铨的文章中再次谈到斯大林的说法,指出“王先生(其他的先生们也同样)从这里看到了有‘能屠杀’与‘不能屠杀’的不同,但却看脱了另外一点重要的区别,便是同一能‘卖买’,而在一边是“当作牲畜”,一边不是。这就是我所注意到的斯大林的说法是最有分寸的地方”(46)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年7月8日),《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21页。。括号里的“其他的先生们”,郭氏其实主要暗指范文澜。
此前,郭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并没有引据斯大林的说法,后受范文澜、王毓铨的暗示,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反驳王毓铨的文章中以斯大林的论述为标准,举证说明周代的生产者可以屠杀,也可以当作牲畜来卖买,故周代的生产者是奴隶。1952年2月17日,郭氏写《奴隶制时代》一文,“为了避免混淆”,又引征斯大林的说法,结论是:“在这样的认识上来看问题时,夏殷周三代的生产方式是只能是奴隶占有制度。”(4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3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者和年份,均指此版。郭氏此举似有与范唱对台戏的意味。范氏也不示弱,1954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再次引用斯大林的话,添加了一句“不切实根据这个定义,所说便缺乏可靠性”。这恐怕是有的放矢之言,批评对象或是郭氏。接着,范氏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看商周两朝统治者对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的不同,可以断言商朝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4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4-35页
范文澜举证西周反对殉葬的史实:“经书记载殉葬事,《诗经·秦风》有一条,《左传》有两条,《礼记》有两条,都是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儿子也决不敢反对制度。……孔子专讲周礼,连俑都反对,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49)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郭沫若反驳:“有反对人殉制的这些少数的例子存在,倒正足以证明人殉制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束缚力量。”进一步申论:如果我们能说“春秋时代有以人殉为‘非礼’者,故周朝没有人殉制度”,那么我们也可以仿照着这样说“美国的共产党员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故美国向来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或美国已经废除了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由此,郭氏评论:“范先生的论断,我觉得不很妥当,那是有点近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50)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2-33页。
郭沫若在《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补记——关于‘生产工具’的说明”部分,直接挑明“范先生的文章中有特别要我‘考虑’的一小段”,所以他先从《十批判书》征引一段文字(51)“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12页),特意提示读者,范氏“虽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但毫无疑问指的是我,因为‘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是由拙作中摘引出来的”(52)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7页。。1952年郭氏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录此文,但删去了有“火气”的“补记”,可见他顾及同道的感受,有意减弱论战的色彩。
对于郭沫若的公开应战(53)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王献唐不同意郭文的观点,如郭对“始作俑者”的解读,他指出“郭先生并没明瞭孔子说的语意,只是指范先生的文句小错,忘了自己连全文都未看通”(李勇慧:《王献唐著述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邓之诚于1951年7月24日阅读郭文,判定“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579页)。,范文澜为了避免引起“其他枝节”,没有与之正面交锋。范氏指导助手荣孟源写《周代殉葬问题》一文,从地下发掘、古籍记载、俑、用人为祭牲四方面逐条反驳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所提出周代存在人殉制度的证据(54)荣孟源:《周代殉葬问题》(1951年8月1日),《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荣文没有挑明针对郭,但若比对郭荣两文,则会发现存在明显的对话。郭文说:“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今天西周帝王的墓一直没有发现过,假使将来发现了,同样惊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们今天还不能断定它绝对不会有。”荣文应:“周王墓葬,虽然尚未发掘,无从推断一定没有殉葬,也无从推断一定有殉葬。但周初因为防止殷之顽民叛变,才封康叔于卫,为五侯之长,卫国的各种制度,应该可以代表周代。”郭文说:“周代的殉葬情形,《墨子·节葬》篇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扼要……这确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料,这就证明在战国初年都还有这样残酷的杀殉制度存在。”荣文应:“《墨子·节葬》说:……只据这一句话来说,好像春秋战国时期,殉葬制度确实普遍地存在着。可是读全篇文章,就不能这样了解。……‘天子杀殉’条不是指的周代,而是指的古代,所谓‘女乐’不是指的人,而是指的乐器。”
《周代殉葬问题》一文虽署名荣孟源,但完全代表范文澜的观点。如荣文谓“殷周两代前后相连,而殉葬制度就有这样大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发掘了一百五六十座周墓,仅仅发见三座墓中共有六个殉葬人”,若对比前引范文,不仅观点,甚至连文字都与范文相同或相近。《周代殉葬问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同期有郭沫若《墨家节葬不非殉》,这不是巧合。《新建设》编辑部了解荣文针对郭,故把该文发给郭氏征求意见。郭氏读后承认“荣文关于殉葬问题汇集了材料是可取的,虽然解释上有些问题”(55)1951年8月14日郭沫若致陶大镛信函。按: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未收。,于是他撰文就荣文解读《墨子·节葬》篇一处提出不同看法,如“《墨子·节葬》篇这几句话,有的朋友认为,所指的不是周代”,“有的朋友也说,没有包含着人。其实‘女乐’所指的就是人了”(56)郭沫若:《墨家节葬不非殉》(1951年8月20日),《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第16页。。郭氏此文虽没有点名,但所对话者其实是荣氏。
郭沫若虽写了《墨家节葬不非殉》,但他避重就轻,对荣文似无更多反驳的余地,毕竟对周代殉葬情况了解不详,于是继续向郭宝钧请教,为此他们面谈过两次。1951年8月24日,郭宝钧又以书面回复郭:“殷代殉人情形,前经函陈。周代情形,因搜集材料不多,尚无可供参考者,只前在濬县辛村发掘,得西周墓葬八十二;汲县山彪镇发掘,得战国墓葬九;辉县琉璃阁发掘,得战国墓葬六十四,合共不过百五十五墓,遇殉者六人,且都出诸侯阶级墓葬里。”(57)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第5版。此信发表于1951年9月1日《光明日报》,被郭收在《奴隶制时代》,但它并没有为郭氏主张周代存在人殉制度提供力证,反而有利于西周封建论者。
不过,郭氏的反驳对范文澜仍有作用。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原有一段文字:
其他如奴隶制度,被周朝基本上废除了(主要是释放农业奴隶为农奴),国王和贵族死后用人殉葬制,用人作祭品制,都被周看作非礼而废除了。(5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第44-45页。
范之所以作出该判断,正是基于郭宝钧告知他周代殉葬的状况。经过郭沫若的批驳,范最初以有人主张殉人“非礼”推论周代废除了奴隶制度,后来他或感不妥,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将上引文字改为:
周朝废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来屠杀,周朝废除这种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区别了。(5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9页。
范虽保留了周朝废除人殉制度这一结论,但与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相比,有两处退却:其一,不再说周朝基本废除了奴隶制度;其二,不再以“非礼”论述判断人殉制度的有无。
三、隔空对话:《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1954年范文澜发表长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60)《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最初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北京:新华书店,1954年),经过修改,作为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篇》绪言,1964年版《简编》对绪言又有修改,并不是如有学者所谓“除几处引文改用后来新版外,其他地方没有改动”(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其中第六小节《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预设的对话者主要仍是郭沫若。范氏在此近乎把《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复述了一遍:
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我想先把商周两个朝代作一比较。商朝社会里阶级极显著的存在着,这是断定商朝决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批的人殉葬;每年祭祀,还要杀若干人同牲畜一样作祭品。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祭祀不用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但当作国家最大的典礼和在精神生活上含有第一等意义即所谓孝道的祭礼与葬礼却有这样的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商周有不同的经济基础,所以有不同的上层建筑。(61)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第20-21页。按:这段引文反复出现在范文澜的各种论著中,但直到1964年版《简编》修订本才被删去,表明范文澜最终放弃了以人殉的多寡来判断商周社会性质的差异。这或与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黄子通和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诸文的批评有关。
从范文的进一步论证来看,有些论述是针对郭氏的。关于人殉问题,范氏以荣孟源的名义作了答复,而关于《诗经》问题,他在《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作了隔空回应。范解《诗经》多采毛亨、郑玄之说,谓“从来无人怀疑”(62)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但郭认为《诗经》经过先秦儒家的删改和琢磨,引用时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郭不同意范对《诗经》的解释,尤其指出“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引自《小雅·甫田》篇,“曾孙来止,以其妇子”等句同见《甫田》篇与《大田》篇,这两篇诗不属于“西周初年”的作品。在郭氏看来,范的《诗经》解释,是“全部肯定与随意解释”,“很难令人同意的”,所以他用教谕口吻说:“批判要严密,解释要谨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诗经》乃至一般史料所必备的基本态度。”(63)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4-35页。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范文澜在给陶大镛信中辩解:“我说《周颂》是西周初年诗,无人怀疑过,不是说其他的诗,也没有说大小《雅》是西周初年诗。”但如细看范文,他最初是如下表述:
西周初年,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我取其陈,食我农夫”又“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这里说的黍米饭,当然是农夫自备。(6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范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得出结论:“以上所举西周材料,都是从从来无人怀疑的《诗经》里取来的,除非有充足证据证明那些材料出后人伪造,否则就应该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65)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范所谓“没有说大小《雅》是西周初年诗”之说与他的文章所述自相冲突,郭氏并没有误读范文。事实上,郭的批评对范是有作用的。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举证上引《小雅》两句话,不再刻意强调是“西周初年”的史事,并说明“《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篇,《小雅》也是西周人所作”。此外,郭指出范文所引“食我农夫”有误,应为“食我农人”,1953年《简编》修订本也接受了郭的指正(6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第71页。。
1944年郭氏《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和《自我批判》,均认为《毛诗》“差不多全不可靠”(67)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3页。,“从时代来讲,《周颂》里面有几首诗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小雅》里面的几篇较迟,有的当迟到东迁以后。《七月》最迟,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68)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原》第1卷第4期(1944年),第8页。。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批评“把《七月》篇说成西周中叶或春秋中叶以后的诗篇,是缺乏根据的臆说。《七月》篇应如汉经师所说,是西周初年人追述周先公时农事,那时候周社会正经历着奴隶制阶段”(6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53页。。如果联系郭说,被范氏斥为“臆说”者正是郭沫若。1955年《简编》修订本上引文字有所改动,删去“臆说”二字,语气平和不少,并在“奴隶制阶段”前添加限定词“不发展的”(7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5页。。《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强调《七月》篇记载当时农夫衣食仰给于周君,没有自己的经济,定为西周人追述周先公居豳时诗,“我认为也是可以的”(71)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1954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页。。这正是对此前不少学者包括郭氏批评的回应。《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说:“《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们做的诗,而不是农夫们做的。(凡是大小《雅》里的诗都是采自贵族阶层的。)所以,那诗中的‘我’字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指农民。”范文应:“是不是可以说,《周颂》《小雅》所说不一定可信呢?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说《周颂》《小雅》作者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所以他们说的话不可信。这也不一定。”范氏认为诗义和训诂是有所本的,不能轻易改变,不点名批评郭的诗解“仅仅因旧说不合己意,轻率地别立新说”。1954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原有下引文字:
还有一种做法是名为翻译诗篇,实际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创作”了若干篇新诗。用自己的“创作”来证明自己的主观愿望的完全可通,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72)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5-26页。
郭氏《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正是范氏批评的“翻译诗篇”的做法。或因指向过于直白,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删掉了上引文字。
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说:“文献上的材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仰仗于地下发掘。……但中国的地下发掘,还仅在萌芽状态……一时还得不到结论,我看倒无须乎着急,只要证据充分了,‘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是永远存在着,不会被湮没的。”(73)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说:“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远在纪元前11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引以自豪呢?”(《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所谓“光荣事件”,范文澜或是套用苏联西莫诺夫斯卡雅的说法:“中国奴隶所有制度的发现乃是苏联历史学家以及中国进步的历史学家的光荣。”(《中国古代史的划阶段问题》,原载苏联《古代史研究通报》1950年第1期,钟元昭译文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10日,第6版)范文应:“是不是可以说,西周史料留存不多,需要等待地下发掘出新材料才能作证明呢?我想,等待地下发掘当然可以,不过,以发见的西周器物数量不算少了,从这些铜器铭文看来,奴隶是有的,但并不能证明西周是奴隶社会,反之,有些铭文却足以证明封建关系的确实存在。……在地下发掘得到确实可靠的相反材料以前,我们只能依据已有的典籍与器物铭文作出以上的论断。”(74)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7页。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画面隐约可见。
郭沫若一直热衷于讨论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器,《自我批判》认为铁的使用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是古代社会的转扭点的‘铁的证据’”(75)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52页。。对此,范很不以为然,1951年他提出:“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所以他对郭氏斤斤于生产工具颇为不满,批评“一味企图用一块铁、一把犁、一头牛来解决古代历史问题,真是太简单太机械了”(76)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郭著《奴隶制时代》仍强调“铁的作为耕器而使用,出现在周室东迁前后,这一重大因素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逐渐促进了井田制的崩溃,因而也就招致了奴隶制的崩溃”(7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20页。。1954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基础上增补说:“奴隶制度的转化,不在于出现什么新的生产工具而在于奴隶对奴隶主进行斗争,迫使奴隶主不得不变换完全所有制为不完全的所有制,而生产力也就在这个变换中发展起来。”(78)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7页。1955年版批判工具论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一方面肯定“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必须依靠制铁技术的进步”,同时又强调“生产工具必须与作为基本生产力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如果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这就难免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为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7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7-48页。。
然而,1956年郭沫若还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坚持铁器的有无是判定奴隶制和封建制界限的“铁证”(80)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人民日报》1956年9月8日,第7版。。与此同步,范文澜则继续加强批评铁器论的力度(81)据曾做过范文澜助手的卞孝萱回忆,当初范文澜与郭沫若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经常写文章交战,“后来上面就和范文澜打招呼说,当时郭沫若还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这样批驳他对团结民主人士不利。所以自此以后范老就没有写过一篇反驳郭沫若的文章,但是他的书每再版一次,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意思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放弃。”(卞孝萱:《冬青老人口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45页)。1955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增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章的观点——由野蛮转入文明是从铁矿熔炼开始,范文澜一开始没有评论(8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7页。,但到1964年版则添加了一句“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却还没有证明”,且批评道:“在封建社会初期,铁制农具很贫乏,经过二百年,铁器才开始有广泛的使用,铁器论将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可见封建制的发生自有原因,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生产力得以前进,铜器和铁器,固然不必过于拘泥,甚至使用残存的石器,也不妨碍封建制的发生。”推究封建制的发生,“首先应从剥削形式的变更上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效果上着眼。又可见铁的作用,既不决定原始公社制与奴隶制的交替问题(决定于金属工具),也不决定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问题”(8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6-47页。。范文澜批评铁器论者,靶点不见得仅有郭沫若,因为当年参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有不少特别强调铁的作用,但郭无疑是最具代表者。
自从1951年范文澜向郭沫若隔空喊话西周是奴隶社会“似乎是值得考虑的”(8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之后,双方多次往复论辩,且掺杂个人情绪。郭反驳范文一再出现“须得加以考虑”“那是值得考虑的”“更是值得考虑的”“那恐怕才是‘值得考虑’的”(85)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3、35、37页。,范文澜的回应也用“这是应该慎重考虑的”“需要慎重考虑的理由就是如此”(86)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6页。,事后双方又删改敏感文字,两人论辩的情形益跃然纸上。
四、“各表一枝”:凉山彝族社会性质
范郭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延伸到1950年代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古史研究者注意民族志性质的资料,以之印证中国古史问题,应受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郭氏较早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除了注重地下发掘,也留心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文献。1930年前后,国内民族调查数据不多,郭氏所知有限,但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仍能发现他探讨古史问题常举证彝族。例如,一般被支配阶级的民众或奴隶专称“黎”“黔”,郭氏推论中国古代原住民是马来人和四川彝族的祖先,因为马来人和彝族都是棕黑色的,“倮罗在四川又称为黑骨头”(8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136页。按:彝族在民国时期常被称为“倮罗”。,但当时他还没有想到用彝族社会印证西周社会性质。1944年《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始引征1935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1号《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有关彝族的七段叙述,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奴隶制,自然毫无问题,然而已经有土田的分割了!假使有土田的分割即当认为封建制,那么倮罗社会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吗?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事。……这些落后兄弟民族的现状正不失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了解得这些情形,回头再去读殷周时代的典籍,有好些暧昧的地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88)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原》第1卷第4期,第11页。。稍后,郭氏《自我批判》再次举证彝族,说明西周乃奴隶社会,他说:“我们为了要求得它的本来面目,最捷的途径是从今天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中的氏族社会里去找资料。在我国这种后进的兄弟民族是很多的,如像倮罗人,那毫无疑问是还停留在初期的奴隶制阶段的。”(89)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29页。
郭氏此时以彝族社会为例,推论西周社会性质,或与范著有关。其实,范文澜较早注意到民族材料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简编》叙述到传说黄帝后裔有少皞、颛顼、帝喾诸帝,“他们究竟作些什么事业,古史传述几乎全不可信。试取其他落后种族的记载,作远古历史的参考,倒可约略想见当时的情况”。范氏举《三国志》记载的乌桓习俗,印证中国古帝名号流传,“大概也像乌桓祭先世勇健有功业的大人一样”(9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9-10页。。当写到“周初生产方式”,范认为周初已开始踏上封建社会的阶段,即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的收获完全缴纳给地主,私田的收获为耕者自有。但这并不是说,周已完全废弃奴隶生产,只是说封建成分超过了奴隶成分。为了说明西周社会性质,范文澜举证:
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说,猺人男丁从酋长领得耕地,不纳租税,止服劳役。有罪受酋长裁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苗人酋长称为主户。主户计口授田给苗民,称为田子或田丁。领得的田,不许典卖。此外俘虏或买得人口,男女相配,给田耕种,称为家奴。农奴与奴隶并存,农奴数量比奴隶多,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9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7页。
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保留上引例证,将“农奴与奴隶并存,农奴数量比奴隶多,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一句改为“周国的封建制度,也许比洪、范二氏所记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显著的发展是在武王克商以后”(9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55页。。范之所以想到以苗人作旁证,或从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到暗示,而后又反哺于郭氏。《简编》曾以《中国历史讲座》为题连载于重庆《群众》,上引苗人例证出现在《群众》第9卷第11期(1944年6月15日),郭氏可能看到范著,遂仿范氏的论证思路,积极寻找同类证据,以支持西周奴隶说。
郭沫若非常重视彝族社会对古史研究的价值,1950年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第三次举证凉山彝族,重申“根据这个原始的奴隶社会,很可藉以了解殷周的社会结构”(93)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光明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3版。。1951年7月,他在与王毓铨商榷的文章中第四次举彝族社会的管家娃子,证明西周生产者是奴隶不是农奴(94)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年7月8日),《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24页。。1950年代,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学界有所分歧。1952年8月15日,胡庆钧给郭氏寄去《大凉山彝族社会》一稿(95)此稿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内部发行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1955年10月)。。郭氏阅读之后,于当月25日热情回信,断定彝族社会处在“奴隶社会的前期阶段”(96)《沫若书简》,《文献》1980年第1辑,第49页。,与他在《自我批判》中的观点一致。借《奴隶制时代》改版之际,1953年10月20日,郭写了《改版书后》,根据胡庆钧凉山彝族调查报告,“扼要地叙述一些,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以供读者参考”(9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76-177页。。概述彝族社会情况之后,郭的结论是:
白彝中比较享有自由的“曲诺”,他们的性质虽然有点类似农奴,甚至有的类似地主,但即使成为头人或“跟腿”,也不外是可以屠杀,可以贩卖的奴隶而已。白彝头人,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便可以成为外服的异姓诸侯。白彝“跟腿”,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便可以成为内服的王朝卿士。西周的社会制度,比起彝族社会的情形来自然进步得多,但在基本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98)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80页。
如联系之前范文澜说“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都是封建社会,那么郭的论述似有针锋相对的意图。郭氏对胡的彝族研究兴趣浓厚,明白彝族社会性质若能证成奴隶制,则可有力支援西周奴隶说,如同他关心郭宝钧所提供的殷周殉葬的史实一样。
郭沫若懂得阐明彝族或其他兄弟民族的社会情况,对“探讨我国的古代史上会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99)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80页。,范文澜也深知其中的利害。胡庆钧于1952年下半年第二次上凉山调查,回北京后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据胡庆钧回忆,1953年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准备前往凉山对彝族社会定性,行前征求了部分学者的意见,他先找了范文澜,范的观点是1949年前凉山彝族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而胡的观点是奴隶制(100)胡庆钧回忆自己写出彝族社会调查报告,认定民主改革之前凉山彝族仍然保持奴隶制度,所提出的等级划分引起了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及有关人士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1226页)。。1956年2月19日,胡庆钧在给郭氏的信中透露,他的彝族调查报告曾争取内部出版,但作为他领导的范文澜“表示须通过民委,不愿直接推荐,而民委又不能代为推荐,故未能如愿”。此事或发生在1953年前后。到了1956年,胡氏认为“现在的情况又和以前不同了,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各项工作迎头赶上,少数民族研究也不能例外。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已进行社会改革,大凉山彝区社会改革也即将进行,理论研究已不能长久落后于实际发展的后面了。听说民委领导上已开始考虑少数民族的研究报告可以公开的问题,我也极愿争取这个报告的公开出版”,于是他向郭氏求助,希望科学院与民委沟通,明确其调查报告是否能公开出版。同时,胡也向郭通报了调查报告虽暂时不能公开出版,但先行以“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为题在中央民族学院集刊内部刊行(101)中央民族学院集刊指的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胡庆钧的彝族调查报告发表在该刊第2辑,1955年10月内部发行。此前,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4年5月已油印胡庆钧以“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初稿)”为题的调查报告。,特向郭说明:
这些材料的本身对于彝族社会性质是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但是翦先生当时为了避免争论,不愿肯定彝族社会的性质,因此连“奴隶”的字眼都被删去。
翦伯赞主张西周封建论,与范文澜一致,故有删字之举并不奇怪。胡还向郭抱怨在近代史研究所“时常感到没有具体领导缺乏充分支持的痛苦”(102)《刘大年全集》第1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79页。,此处“具体领导”指的是范文澜。对于胡的调查报告既不能公开出版,又不能内部出版,加之范翦的上述做法,郭氏对此或有想法。1956年2月25日,郭氏将胡信转交刘大年,谓“请你看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征求范老的意见,同意他所写的报告,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103)《刘大年全集》第11卷,第77页。按:《刘大年全集》断定此函写于1957年2月25日,笔者疑有误,当为1956年2月25日,具体考订在此不赘。由于郭沫若把胡庆钧信转交给刘大年,所以此信现保留于《刘大年全集》。。但胡著没有得到范的认可,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事宜自然就没有达成。
1956年范文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胡庆钧有过一次正面商量。胡先作大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报告,翌日范作了“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的发言,论及:(一)彝族的阶级,(二)社会发展方向及阶级关系,(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四)国家与法律、前期与后期,(五)对彝族社会的估计,(六)试提一些意见。范氏依据胡报告中的材料和问题,作如下判断:
胡庆钧同志在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做了相当仔细的调查工作,收集材料很丰富,并且也做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得出一些假设性的结论。……要把调查工作做得圆满无缺,必须具备着若干必要的条件;而胡庆钧同志在大凉山工作的时候,某些情况使他无法作更深入的调查,这就限制着材料的准确性。昨天胡庆钧同志作报告,因时间不够充分,只能提供若干认为最重要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把各个方面都说到了,而且确是很重要,不过,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企图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来,还是困难的。(104)范文澜:《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未刊发言稿,第1-2页。按:笔者所见发言稿共31页,誊抄在标有“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会”字样的方格稿纸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范文澜的公开出版物,包括范文澜全集、文集和研究论著,都没有提及该文。
范认为胡的结论只是假设性的,并不可靠。他根据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规定,分析胡氏所提供的史实,得出彝族社会既处在奴隶制,又存在封建制,不过后者比前者数量大得多,处在统治地位,支配着彝族社会。范估计:“彝族社会大部分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前期,小部分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后期的最后期。由于奴隶主这个衰朽力量的强烈阻挠,阶级斗争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被压抑不能展开,因而形成在奴隶制统治下的极原始的封建社会。”(105)范文澜:《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未刊发言稿,第21-22页。
范文澜对胡庆钧的冷,与他对另一位研究彝族的学者刘尧汉的热,适成鲜明对比。1955年5月,刘尧汉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106)该文曾发表在《中央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年1月编印,内部刊物),内容略有变动、原正副题更置之后,又公开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将手稿寄请范审阅(107)《刘尧汉先生访谈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1956年5月24日,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激赞的文字《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他说: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108)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第3版。
范文澜与刘尧汉的学术观点一致,故愿意为学界推介,但与胡庆钧相异,他不仅“不愿直接推荐”,即便郭沫若出面干预也不让步。范撰文为刘尧汉高调背书的举动,似有意效仿郭在《奴隶制时代》改版向学界积极推介胡庆钧的做法,表明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变,与郭的学术分歧不仅在西周史,也延展至彝族社会。
结 语

范与郭的学术商量,双方均存“成见”,难以“虚心”正视对手所提出的问题,一味寻找对自身有利的证据,排斥不利的史料和观点。郭宝钧提出殷代殉葬的史实,郭沫若欢欣鼓舞,因为它可以印证殷代奴隶说,但当郭宝钧主张殷与周两代殉葬之风有别,郭沫若态度即变,因为此说与他所坚持的殷与周两代同为奴隶社会的观点相冲突,反而会被西周封建论者利用。范文澜就拿郭宝钧讲殷周殉葬的差异,作为判断殷代为奴隶社会而西周为封建社会的“一点最简单的理由”。但是,以人殉的多寡来判断社会性质遭遇诸多批评,最后范氏放弃了这项证据,但对西周封建论仍坚信不疑。同样的,范文澜对彝族研究者胡庆钧、刘尧汉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因学术观点有别所致。范郭皆深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极力证成各自的学说。范氏相信判断一个社会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不仅仅在于铁的有无,同时要注意阶级斗争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郭氏着迷于发现铁器痕迹,认为西周还没有出现铁制生产工具,因此不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从而不能产生封建社会。他们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导致彼此无法说服对方。
从范与郭的论辩史实来看,范氏扮演着主动的挑战者角色,1940年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公开与郭商榷,1951年《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又不点名批判郭。相反的,郭氏倒是被动的应战者,《十批判书》因同道的批评而写,《奴隶制时代》也是因应学术界包括范文澜在内的各种批评而发表的长短不一的论文集结。范虽是论争的发起者,但论辩中时常因郭的反驳而悄然修整论述,尽量减少破绽,完善论证,算是其“通达”的表现之一。不过范的核心观点始终未变;郭氏因《自我批判》获得了忠实学问、勇于自责的美誉,但事实上他很少接受批评者的意见。范郭论辩虽不尽是纯学术的商榷,意气之争间或有之,但他们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