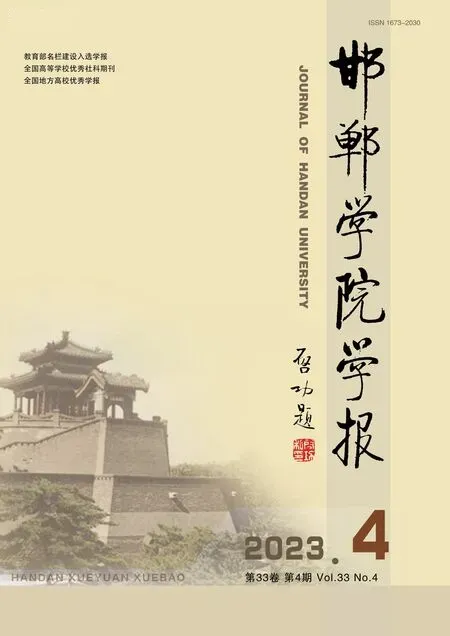荀子“天官”与“天君”辨正
2023-02-12陈迎年
陈迎年
(华东理工大学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7)
荀子“天官”与“天君”的辨正可以就“天”“人”关系而言,也可以就“心”“性”关系而论。这里关注荀子的“天人对扬”问题,它当然不能离开如上两个关系,但侧重却有不同,其核心问题是:“天官”“天君”等究竟在“人”还是在“天”?若“性”为“天之就也”,“伪”也是“性”吗?既是“天君”也是“天官”的“心”,与“五官”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最终的问题是,荀子为什么要如此辨说呢?①这是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前有《荀子的两心论辨正》,《现代哲学》2017 年第1 期;《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齐鲁学刊》待刊;后有《荀子“人论”疏议》等。
一、天人对扬
这里荀子的“天人对扬”是与孟子的“性命对扬”并列而言的。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牟宗三认为这是近人“不得其门而入,只是穿凿索解”的“性命对扬”。[1]147其实,荀子也有个类乎此的“天人对扬”:“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荀子·荣辱》),人也,有天焉,君子不谓人也;“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荀子·性恶》),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谓天也。只是可惜,孟子的“性命对扬”非常著名,而荀子的“天人对扬”则讨论者稀。
这并不是说,学者们很少关注荀子的天人学说。恰恰相反,荀子的“天人之分”一直就是人们讨论的重点和焦点。荀子自然之天的哲学史意义被把握为“解除神秘主义”和“突出理性化”,荀子的“自然观”隶属于其“道德观”“政治观”等也被拖带了出来。①参阅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第二篇《解除神秘主义——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1 年;《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附录一《“应之于治则吉”——荀子的〈天论〉篇与政治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只不过这里从天人对扬的角度看,关注荀子在什么意义上“谓天”,又在什么意义上“谓人”。
首先,“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星队、木鸣”等,是天,亦谓天,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形具而神生”时,有了人的好恶喜怒哀乐之情、人的耳目鼻口身等感官、人的辨知之心等,明明是人,可为什么荀子又谓其为“天情”“天官”“天君”呢?
或曰,荀子所言的天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天与人相区别,是“天行有常”的天,包括星辰、日月、寒暑、阴晴、旱涝、水火甚至珠玉等,即天地间一切除人之外的客观的自然现象自然物质,表示一种严格且必然的因果链条义,标明人之存在的“前提”或“所与”(the given),人就生活在此天之下。广义的天则并包天地万物,因而也及于人的身心,即所谓天情、天官、天君等。如此说来,明明是人,荀子却不谓人,而谓之天官、天君等,同样表示严格且必然的因果链条义。换言之,虽然人有自己的“神”“精神”或“神明”,但人的这种主体性、能动性等却不可能与物无对、天马行空,而同样有其客观义、因果义,只能是“所与”基础上的“自由任性”(volition)。
其次,众所周知,荀子严分了性、伪: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荀子·性恶》)
这里的“本始材朴”“生之所以然”“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不可学、不可事”“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等,都是在说人的“天性”(《荀子·儒效》),也即那种明明是人,荀子却不谓人,而谓之天的客观义、因果义。也就是说,荀子所谓的性,是在人却谓之天者。相应地,荀子所谓的伪,是在人而谓之人者。这样,就有了一个“天而天之”(天)“人而天之”(性)“人而人之”(伪)等的序列。这似乎是清楚而无疑问的。
但是,之所以“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所以“文理隆盛”等,却只是因为“心为之择”“心虑而能为之动”,而这个“心”,恰恰又被荀子命名为“天君”。“伪”因“天君”而然,岂非“伪”同样是人的“天性”?或者说,“人而人之”的伪,同样包括在广义的天之下,同样可视为人的“天性”,只不过性“谓天”而伪却“谓人”罢了?否则很难想象,人没有伪的“天性”却能够去伪,正如绝缘体没有导电的“天性”却可以导电一样。
在这种“谓人”与“谓天”的关联中,荀子一方面强调“器”“非故生于人之性”而生于“人之伪”,一方面又不能不区分“工人”与“陶人”的“天性”,因为“埏埴而为器”只能“生于陶人之伪”而不能“生于工人之伪”,“斫木而成器”只能“生于工人之伪”而不能“生于陶人之伪”。换言之,瓦埴固非陶人之性,器木固非工人之性,但工人不埏埴、陶人不斫木等却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最后,“谓天”与“谓人”的界线何在?何时说“广义的天”而何时又说“狭义的天”呢?荀子在此说“圣人”。“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即只有圣人才代表严格的“人而人之”,是真正的“天生人成”,或者说表示纯粹而完全的人(严格遵守因果律同时又呈现自由,有“具”且“具具”),其他所有的人其实都不过是部分为人(自由任性)部分为天(受因果律支配)的存在,严格说来是半人半兽的存在,还不可谓人。这同时意味着,荀子“天人相分”真实饱满的意指只有说到“天生人成”时方才实现,“明于天人之分”只是为了“能参”,或者说“分”让“参”得以摆脱原始先民天人合一的神秘与迷狂等,而走向平实和理性的天人合一。这里有人类走出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此即“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这或许是荀子或“谓人”或“谓天”的目的之所在。就此而言,虽然荀子特别强调“圣人之伪”与“人之伪”的不同,强调“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但究其实,最多只指示着平实和理性的天人合一之全粹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绝非是说圣人与人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换言之,荀子的圣人其实只意味着人的理想,同样是人自己生活自己创造出来的,而非指历史中的某个或某些现实的拥有与常人不同的天官或天君的人,因而“第一个圣人何由成”的问题只有在整个人类人文化成的过程意义上才是可以提出的。
总而言之,天官、天君等是人的,但却不谓人,在荀子的这种安排中,人既可以束缚自我,承认“天行有常”,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因果律,又可以解放自我,“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聘能”“理物”“有物”而“应之以治”,也即尊重主观观念,实现自由秩序(《荀子·天论》)。荀子区分了天人、性伪也即区分了自然与自由。天性表示自然,因果律起作用,客观世界、知识首出;人伪表示自由,意志起作用,道德、政治、秩序首出:如此就有了在因果律主宰的世界里人究竟有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性伪合、天人合则表示荀子立全粹之美,视自然与自由的沟通为必然,“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从而既能定之以因果律,又能应之以自由意志,而有所谓“成人”(《荀子·劝学》)。
二、天官五官
在以上的天人对扬中,天官、天君均“在人”而“谓天”。实际上,这种天人对扬还可以再继续细化下去,而表现为天官与天君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相对而言,究竟是天官还是天君更适合“谓天”?这里先看天官与五官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因《正名》而显。在《天论》中,尽管“耳目鼻口形能”是“天官”并不排斥“心”也是“天官”,但顺文脉认定“天官”即“五官”,而把“心”明确列为与“五官”不相类且“治”之的“天君”,还是更加顺适一些。但在《正名》中,“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之下,明确分目、耳、口、鼻、形体、心六条以论之,故“心”似与目、耳、口、鼻、形体并列而为“天官”,“天官”之数为六。但接下来的“心有征知”“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则似乎以“心”为“天君”而与“天官”对列。如此,也就当有“天官”之数究竟为五为六、“天官”是否即为“五官”的问题。①拙文《荀子两心论辨正》曾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参见《现代哲学》2017 年第1 期。
但一般说来,人们虽然注意到了荀子论天官与五官时的这些细微差异,但却并不以之为问题。比如李涤生一方面明确认定“‘天官’:耳、目、鼻、口、心、体。心是内感官,耳目等是外感官。‘缘天官’、因自然的感官”,一方面又认为“‘天官’、即五官,见天论篇”。[2]513,515这是随历代的注释而顺口说下来的。首先,杨倞注:“天官,耳目鼻口心体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前注紧扣文本,后注中的“心”却多少有些突兀。因此王念孙认为后一“心”字乃“体”之误,顺带着也认定前一“心体”当为“形能”“形体”“形态”。而俞樾竟不顾前面的“缘天官”,直谓“待天官之当簿其类”中的“天官”乃“五官”之误。最终,钟泰的如下说法代表了人们的一般看法:“天官,即五官,谓耳、目、口、鼻、形体,不数心也。”[3]415,418[4]894-899
认定天官只能是五官,严格说来并不符合荀子的原文。除了以上提及的《正名》“天官之意物也同”一段,《性恶》“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等文也表明,荀子既区分了天官与天君,但同时也把心与耳目等并列。也就是说,荀子的天官也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天官之数为五,仅指人的五官而不包括心,广义的天官之数为六,既包括五官也包括心。
狭义的天官也即五官对应的是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广义的天官则特别涉及感觉与思维的关系,包括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以及认识与欲求、实践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关系,荀子当然也有论说,如所谓“虚壹而静”等,但总体上来讲却是隐含的而非专题的。在西方历史中,对此的专题讨论可以追溯至比荀子稍早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把五官感觉作为了人类记忆、经验、技术、理智的基础,强调从感觉上升到知识的重要性。[5]1也就是说,技术与知识与官感既有分别也有联系。在《论灵魂》《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等文章中,亚里士多德对此分别与联系做了具体论述。简要言之,亚里士多德是从人与动物等生命的共同性的角度观察感觉的,强调感觉是首要的,感觉与躯体是不能分离的,感觉器官自然从躯体中就产生出来了。[6]32-33,99其次,亚里士多德也区分了五官,并强调“在五种感觉之外(我是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并不存在其他感觉”,但他却把感觉、意见、愿望、欲念、认识等关联起来讨论。[6]64,28,87最后,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后继者都潜在地包含了先在的东西”,如感觉能力包含了营养能力、欲望能力等,相应地,思维也就包含了感觉,这样就有了五官之间的排列“顺序”以及“营养、欲望、感觉、位移以及思维”等排列“顺序”。①亚里士多德说:“营养能力与欲望能力有联系,但前者更可以诉诸天,指一切‘有生’者自然而然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也有营养能力。位移即运动,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动物除感觉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本性’”。参见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6-37 页。这个排列顺序与荀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等说法若合符节。草木有生,也即草木有营养能力。禽兽有知,也即动物也有感觉,但却没有思维能力。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也讲到了水、火、气等。
到了近代,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等相关联,知识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感觉的研究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例如对洛克而言,他要划定“意见与知识底界限”,探求“人类知识底起源、确度(certainty)和范围”,以为人类建立思辨的知识和实践的公道等方面的“切实的普遍同意”,因为没有这种普遍同意人们便无法进入文明国家,而他给出的“地平线”正是五官感觉。[7]1-2,5,25,85简言之,洛克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认真甚至繁琐地论证了唯有客观世界的事物作用于五官所形成的经验,才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过,洛克虽然因此反对知识、法律、道德、宗教等所有方面的天赋观念论,但却并没有走到唯五官感觉论。在他看来,感觉有“由外面得到的”感觉与“内部的感觉”之别,前者是“物象刺激感官”并“传达于人心”,仍用“感觉”之名,后者包括“知觉、思想、怀疑、信仰、推论、认识、意欲,以及人心底一切作用”,而另外专名“反省”。[7]69也就是说,尽管认为人类的观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作为外部经验的“感觉对象”,一个是作为内部经验的“心理活动”,后者似乎能够脱离客观对象而有,但究其实洛克仍坚定地认为它最后是导源于感觉。或曰这是洛克哲学观点上的“二重性”也即“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但这样的安排有两个直接的结果,一是“良心不足以证明任何天赋的道德规则”[7]30,洛克要从五官感觉起建立善,而坚决反对一切直接的天赋的善,二是洛克没有因对五官感觉的基础地位的强调而走向定性众生论,而是在建立善的过程中承认心的其他作用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强调“习俗比自然的力量还大”[7]44。前者与荀子辟孟子的“唯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则不能不让人直接联系到荀子的“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荀子·儒效》)。
需要注意的是,洛克“感觉”与“反省”的区分一方面坚持了亚里士多德感觉与思维的排列顺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心”的作用。反省就不用说,即便五官感觉由“物象刺激感官”而来,但也一定要“传达于人心”。这意味着,虽然能够分别五官与心,但五官其实也属心,而有广义的天官。荀子说:“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荀子·正名》)又说:“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荀子·解蔽》)荀子的这类话语,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或者说,五官与心,其实都是属心的,而可总名天官,而天官虽然谓天,但其实还是人心。洛克的这一倾向被后来的康德更加直接而简明地表达出来了。康德的先验感性论,以时间、空间来论人们怎么就获得了感觉,而谓其为心的感受性,从而证明了外物的存在,去除了哲学上及人类理性上的污点。康德的先验逻辑论,以范畴来为自然立法,而谓其为心的自发性,从而高扬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将人类的人文化成安置在了理性的稳固道路上。其总思路可用如下一段话来概括:
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二种根本源流;第一,为容受表象之能力(对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为由此等表象以知对象之能力(产生概念之自发性)。由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8]72
这里谈及康德等西人,并没有数家珍的意思,意欲强调荀子无所不包、冠绝古今中西。荀子与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比如在荀子知识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目标,知识论只是被拖带出来的等。不过,从“普遍同意”或“共喻”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荀子关于天官与五官等看法与他们的讨论有能够相互发明的地方。现在可以就天人对扬而更加肯定地说,五官更自然,更接近天,更少人为,心则可以不论“物象刺激”而更多人为,天官则把五官的感受性和心的自发性结合了起来,既谓天又谓人。
三、五官天君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心”是荀子确定无疑的中心。“心”即是“天君”,又是“天官”,而且“五官”也不能离开它而有。“心”为“天官”而同于“五官”则谓“性”,“心”为“天君”而远离物象刺激则谓“伪”。这样,荀子“天官”与“天君”的辨正就进入了“心”“性”关系的讨论。
荀子心性关系也是人们讨论的重点和焦点,且“最为恼人”。①参阅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第三篇《性恶:一种必要的理论构想》和第四篇《“心之所可”与人的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1 年;《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附录二《性恶、情恶抑或心恶——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劳思光曾将其简明地表达如下:
荀子承认常人(涂之人)皆有一种“质”与“具”,能知仁义法正,能行仁义法正。则此种质具属性乎?不属性乎?恶乎?善乎?何自而生乎?若此种质具非心灵所本有之能力,则将不能说明其何自来;若此种质具是心灵本有,则此固人之“性”矣,又何以维持“性恶”之教?[9]254
必须承认,此一系列疑问是有坚强的文献依据的。一般说来,荀子认定人的天性就是好色、好声、好味、好利、好愉佚而疾恶。按上节已经指出的,这虽然是就天官而言的,但根底上还是与五官“并列”而说心,是心好色、好声、好味、好利、好愉佚而疾恶,此即“其心正其口腹”(《荀子·荣辱》)、“利心无足”(《荀子·非十二子》)、“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荀子·正论》。这样的人心,也可以说是情、欲、性,荀子谓之天。而此处“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的“质具”当然也是“心灵所本有之能力”,但它却是与五官“对列”而说心,心跃出而为主宰,是“知道”(《荀子·解蔽》)、“道之工宰”(《荀子·正名》)、“居中虚以治五官”(《荀子·天论》)的天君之心。这样的人心,不可以说情、欲、性,只可说知虑、治辨、决择,虽为“天君”,荀子却谓之人。
于是人们自然疑问:为什么同一心也,俄而与五官“并列”,俄而与五官“对列”;俄而“顺”五官,俄而“治”五官;俄而是自然的“天性”,俄而是自由的“人心”;俄而受物象刺激“感而自然”,俄而“出令而无所受令”。于是人们发现,荀子似乎偏爱二重性:心有二重性,一为是性的心,一为不是性而是伪的心;性也有二重性,一为情、欲、利的性,一为辨、知、伪的性。这确实恼人。但是,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之存在的“前提”或“所与”(the given)。人存在的基本事实就是“天生人成”,人的存在既是被规定的,有一系列不能不承认和接受的给定限制(天),又并非“定性众生”,在任何条件下都仍然能够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人)。
就此而言,劳思光的上述疑问并不意味着荀子的矛盾或错误,而恰恰只是因为他是站在孟子心性论的立场上而为言的。如何看待孟子的心性论超出了本文所设定的范围,但显然,以是否“违离”孟子心性论为标准来讨论荀子是不合适的。由此出发而欲“化解”荀子的“矛盾”与“不善巧”,或者“改善”荀子,而提出情恶说、性朴说、心善说或心恶说等等新说,一方面有其成立的坚强文本依据、事实依据和逻辑依据等,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深化了对荀子的理解,突出了荀子的某个或某些真实存在的面相,另一方面这些部分的拓展就荀子本身的系统而言又是不全面的,甚至因歧轻歧重而形成了对荀子的“违离”。
总之,就荀子本身的系统来看,天人对扬,于人心处必有心的二重性。心的感受性被荀子归于五官,与物象相摩相荡,感而自然,首先即是营养自己的倾向和能力,荀子对此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铺排。在此,五官其实是可以被归于肉身的,人与动物没有区别,而突出为欲望及其满足的重要性。不过,即便与动物相同,而可以本能谓之,但这里仍然不可谓恶。人们就此生疑,而提出性朴论等为荀子弥缝,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情还是欲等,在此都也不可谓恶。试想,若连营养自己的能力都归于恶,那么这种观念肯定是伤生害生反生的,因此情恶说并不能为性恶说弥缝。与此相应,心的自发性被荀子归于天君,与物无对,感而不能然,首先却是认识、分辨、选择及行动的意识和能力,荀子对此同样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铺排。在此,天君是纯灵的,是人独有的特性,而突出为抉择及其行动的重要性。善恶于是出现了,知道、从道、合道的选择和行动产生了善,相反就有了恶。在此可见心善说或心恶说的依据。
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执着地追问,究竟是心善还是心恶呢?或许,这一问法本身就“违离”了荀子。有没有一种可能,在荀子心既是善的也是恶的,正如康德的自由任性是两头通的那样?连带的问题是,五官之心是性,綦欲,却无善恶,天君之心不是性,治五官,却有善恶,而荀子却说性恶,这究竟是为什么?
四、心性之间
连植物都有营养自己的能力,动物在运动中增强了自己的营养能力,人的五官能力延续了动植物的这类本性本能,这是荀子首先肯定的。荀子说: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荀子·王霸》)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荀子·正论》)
两相对比,或以“心”当作“形”字,而强调天官不包括天君。不过,即便这里的“心”确实是“形”之误,也并不能否定《正名》天官意物的六指,荀子天官、天君、五官的整体关系并不因此需要修正。与此相应,一是荀子明确“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肯定人的营养能力及欲望等,二是荀子以五官为“具”,特别强调如何“具具”。
具,一为名词,器具,一为动词,具备。具具,一为主谓,器具具备,一为动宾,具备器具。这里的“养五綦之具具”为前者,(《荀子·王制》)“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为后者。不过,无论是“具备器具”还是“器具具备”,“具具”的意思都是明确的,即如何成就人的营养能力及欲望能力等,如何让人的五官成为人的五官。
“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人的五官难道不是随着人的存在而自然是现成的五官吗,怎么还可以说“让人的五官成为人的五官”呢?但这正是荀子“谓天”与“谓人”“谓性”与“谓心”等的关键之所在。对于动植物来说,营养、欲望、感觉甚至位移等能力都是现成的,是本性本能,随其出生而有,是既定的事实了。这里有生命力的健旺强弱之别,以及随之而来“弱肉强食”等“自然法则”。对于人而言,却有文明与野蛮之别,表现为洛克所说的“普遍同意”等问题,也即还须“考虑”到他者的营养、欲望、感觉和位移等,故人“爱其类”(《荀子·礼论》)要远超过一般的动物。换言之,人的五官既如动物那样是生而具有的,又不能不受到“内部的感觉”的影响而表现出对本性本能的某种超脱,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的原因,因此荀子强调“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礼义法度”“政令制度”“政教习俗”“道”(包括知识)等都是人“考虑”的结果,而“考虑”的过程是“长虑顾后”(《荀子·荣辱》)、“知虑取舍”(《荀子·君道》)、“修正治辨”(《荀子·荣辱》)等,“考虑”所依凭的“器具”则只能是天官、天君等。
也就是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不但要考虑到五官的满足,还要考虑到防范因自己五官的满足而伤害到他者五官的满足,只有同时“兼此而能之”(《荀子·君子》),才有所谓“具具”。而只有在“具具”中,五官才是人的五官,天君才成其为天君。两者在此是顺成关系。用荀子的话说,“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用洛克的话说,“能统治我们的情感,正是助进自由的正当途径”[7]237。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具具”,那么五官与天君“两者相持而长”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于是乎便不能“两得”而只有“两丧”(《荀子·礼论》)。“两得”之谓善,“两丧”之谓恶,善恶在此时此地方才出现了。
因此荀子性恶论既可以指五官性恶、天君心恶(不具具),也可以指五官性善、天君心善(具具),总之强调善、恶都是人自己的作品,若人放弃了自己的这种责任,不愿超出动植物,或者比动植物还动植物,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性恶了。所谓不愿超出动植物,是说不能肯定人类独特的知识、思维、习俗等观念,而宁愿如动植物那般感觉世界及在世界中存活。这是把人等同于一般动植物,不愿走出野蛮而进入文明。所谓比动植物还动植物,是说社会上流行的知识、思维、习俗等观念彻底抛弃甚至否定了“利”而“唯义之见”“唯义之求”“唯义所在”,那么众多“多余的利”便无法“共予”,而只能流入个别或部分人的“各特意”(《荀子·大略》)。这是说大部分人连动植物都不如,无法营养自己,其欲望成为不名誉甚至非法,而小部分人穷奢极欲,高喊仁义道德,但实际上却只有动植物的本能。这是把人等同于天使,借文明之名把人类陷入更加野蛮的状态。两者的表现虽不同,但前者只有五官而无天君,有感觉而无思维,后者只有天君而无五官,有思维而无感觉,总之都是割裂了人的心与性,因而无法“具具”,因此都陷入了野蛮状态的泥淖。
总之,如何“具具”的难题揭示了荀子为什么要如此辨说的原因。荀子无法否定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但这种“客观存在”的“具”又只有在“当下上手状态”[10]86中才能“具具”,也即成为真实的存在。换言之,“具具”是存在之事,是在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五官与天君、天与人、性与心等的外在相加。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若我们问的是人的存在,那么却不可能靠把肉体、灵魂、精神的存在方式加在一起就算出这种存在来;何况上述各种存在方式本身还有待规定。”[10]60这样说来,荀子的性恶论并不指示人的某种“既定事实”,而是说人类很容易、很自然就会心、性“两丧”,陷入野蛮状态的泥淖,因此人不能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解蔽》),以图“情文俱尽”(《荀子·礼论》),心、性“两得”“两有”。荀子曰“称情而立文”(《荀子·礼论》),亦曰“身尽其故则美”(《荀子·解蔽》),复曰“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