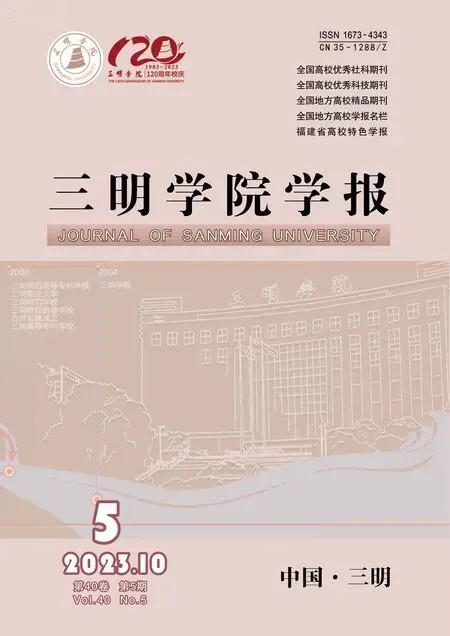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的情感文化透视(1946—2022)
2023-02-11邢成武
邢成武
(三明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爱情这一亘古永恒的主题,在东西方文学艺术创作中源远流长;当爱情与电影相遇,百余年的世界电影发展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一般而言,爱情电影表达的爱情主题内容,成为一种无异议的共识。然而,不同国别、时代背景下的爱情电影创作,其爱情的标准与爱情的表达也大相径庭。面对形态各异的爱情电影,从爱情的情感表达来透视其电影创作,成为观照爱情电影的主题表达、文化美学建构的关键核心。故而,从情感表达中透视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分析考察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艺术创作与彼时香港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交织图景,成为透视香港爱情电影情感文化变迁的镜像窗口。
本文对香港爱情电影情感文化的考察,以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为对象。虽然经过私人捐赠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搜集找寻,1945年之前的香港电影可看到的影片数量有所“突破”,如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研究者郭静宁说,“最兴奋的莫如竟然有十多部影片可看”[1]XV。但是,面对仍然“稀缺”的电影文本数量,要对1945年之前的香港爱情电影进行较为确证的研究,是较为困难的;而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无论是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是可见的影片数量,都较之前的香港爱情电影丰富。因此,本文以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为考察对象,并将具体的研究时期定位为1946年至2022年。选定1946年为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研究的开始,是因为经历1941年至1945年间日本的占领及战争影响,香港电影事业受到了极大破坏,香港电影制作到1946年才逐步恢复,到了1946年底才有了制作于战后并正式公映的作品。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本文考察的1946—2022年间的香港爱情电影,以普通话、粤语爱情电影为考察对象。香港电影存在粤语、普通话、厦语、潮语等多样化图景,其中,厦语、潮语电影“两者虽然都是在香港生产,却不以香港为主要市场”[2]34,并且“由于极少在香港上映,本地相应地较少文献记载”[3]22;对此两种电影的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的《香港厦语电影访谈》《香港潮语电影寻迹》,可谓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但相较于普通话、粤语电影的研究成果而言,仍然是十分匮乏的。此种情形,使得本文较难在文献及电影文本资料上对其做出相对完备的考察。故而,本文的研究并未涉及厦语、潮语两种电影形态。
根据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的发展演变,其爱情电影创作中的情感文化呈现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主要表现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期间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爱情受到较为显见的伦理道德束约,呈现出鲜明的“情感调控”特质;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爱情的自我表达更为鲜明,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约全面消退,呈现出从“情感调控”到“情感至上”特质的鲜明转向。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境下,香港爱情电影的情感呈现,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后情感主义”表达,呈现出“情感至上”与“后情感主义”的夹杂。此般“情感至上”与“后情感主义”夹杂的情景,在21世纪以来,伴随着CEPA协议签署下的内地与香港电影的深化互融情境,“后情感主义”的爱情表达逐步隐退,彰显爱情本真的“情感至上”的爱情创作愈发凸显,并成为时下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的情感文化的主导意涵。
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情感调控”特质
美国学者李海燕通过对我国文学叙事话语的分析,提出了现代中国爱情的3个谱系,即儒家、启蒙、革命的感觉结构。“如果说儒家的感觉结构执着于‘美德的情感’,那么启蒙结构则痴迷于‘自由恋爱’。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在1920年代愈演愈烈,但从大体上说,二者最终都被一种更具霸权性的模式所征服,即我所谓的‘革命的感觉结构’。”[4]16李海燕通过我国文学中的爱情话语提炼出的3种感觉结构,将文学上的情感与社会文化建构进行了对应。
借鉴其对我国近现代爱情谱系的划分考察香港爱情电影,则会发现她所言及的“革命的感觉结构”,不能说没有,但显然是最不凸显的一个。革命的话语,对于英国殖民当局而言,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注重防范的对象,无论是在抗日时期,还是在二战后的左右对峙中,对冲击或不利于殖民地统治的政治行为,都受到了殖民当局的干涉或禁止。比较而言,在近现代香港爱情电影的谱系中,“儒家的感觉结构”和“启蒙的感觉结构”是其爱情话语表征中的重要主体;它们体现出的对于爱情的自由追寻及其与伦理道德传统的关联,在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爱情电影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1946年12月15日公映的《芦花翻白燕子飞》,是二战后香港摄制的第一部港产片。彼时有影评指出:“故事是发生在战前的苏州,一直发展到复员后的上海,而龚秋霞更从一个乡村姑娘演到都市的交际花,情节曲折,大有茶花女的作风。”[5]10影片围绕着龚秋霞和王豪饰演的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展开,有两人的恋爱,亦有王豪饰演的爱国青年的抗战情节,同时,影片又套用了茶花女的情节,讲述了龚秋霞饰演的女角为了男主,忍痛离开,最后死亡的悲剧。
香港学者蒲锋曾指出:“《芦花翻白燕子飞》之后,香港的国语言情文艺片,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有不少受到《茶花女》影响的例子。”[6]16法国小说《茶花女》在19世纪末经林纾的翻译在我国出版发行,其表达的爱情主题内容,在20世纪初期我国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有着表征“个性解放、爱情神圣、恋爱自由”的现代性特质,然而却往往忽略了其情感表征与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有学者即指出:“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近代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渴望恋爱自由,要求婚姻自由是《茶花女》等这类作品风行的重要原因。处在新旧伦理交替之际的读者,的确对林译言情小说中排他的感情纠葛充满渴望,因为这也解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但事实上,至少是在最初阶段,中国人最早所接触的由恋爱自由所代表的西方的个性自由仍然首先是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的伦理责任联系起来的,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个人的幸福被家庭利益化解,正如马克和迦茵的结局。看来,西方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些所谓的个性解放还是与中国的家族主义和道德观念相连才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7]67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尤其是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的爱情电影,其反复演绎的茶花女式爱情,就鲜明地映照出了爱情的自我追寻与伦理道德传统之间的紧密关联。
此种茶花女情境,从爱情的情感呈现来看,又主要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如《芦花翻白燕子飞》般的爱情悲剧,较有代表性的电影有谭新风执导的《南岛相思曲》(1947)、蒋伟光执导的《怕见旧情郎》(1947)、李铁执导的《何处是侬家》(1947)、易文和张善琨执导的《茶花女》(1955)、秦剑执导的《一代名花》(1955)、陶秦执导的《不了情》(1961)等。此类爱情电影较为鲜明地呈现出了伦理道德束约与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之间的矛盾张力,即旧式家庭观念、阶级观念、父辈权威等,与爱情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冲突,在强大的伦理道德束约之下,男女爱情具有较为凸显的被抑制性与悲苦性。
第二种形态则是影片中虽然有较为鲜明的茶花女情节,但创作者在处理男女情感与伦理道德关联时,将两者进行了调和。此类影片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铁执导的《槟城艳》(1954)、秦剑执导的《何日君再来》(1966)。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彼时影片创作中常见的歌女爱情故事,它们既沿袭此类影片创作情境下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束约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了爱情男女的自主性。特别是影片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身上依然体现出是善良隐忍牺牲的传统女性特质,但创作者在塑造她们时,又展现出她们自立自强的形象,她们的爱情结局也一反同类创作的悲情性,而是通过与阻碍她们爱情追求的伦理传统的“和解”,走向了大团圆的情境。此类影片创作展现出的是与伦理道德传统的调和性,男女爱情的自我追寻与实现,并不是对伦理道德传统的决然反叛,故事的大圆满结局,并没有反叛伦理道德,而是将其与个人爱情自由追寻进行了调和,呈现出了一种情感表达上的调和性。
而与茶花女式爱情形成对照的,则是一种董夫人式的爱情。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爱情电影中,1970年公映的由唐书璇执导的《董夫人》,其闪烁出的浓郁东方意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此时期香港爱情电影衰落中的耀眼明珠。《董夫人》中的爱情话语,鲜明地体现为“董夫人为了女儿的幸福、个人以及宗亲的荣誉,终于拒绝了杨尉官的爱意,压抑了主仆之间的情欲,庄严地在鞭炮声中接受了贞节牌坊……所以《董夫人》探讨的是人性所受到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压力,也是个人感情和自由,相对集体价值观念的矛盾”[8]103。它和茶花女式的爱情自我追寻面临的强大伦理道德外力束约比较而言,表征出的是一种内生的伦理道德自我规约。此般情境下的爱情话语,虽然没有较为凸显的阶级家庭观念与父辈权威的外力干涉,但在男女感情的自我抉择上,一种内生的伦理道德自觉凌驾于自我之上,变成了抑制情感自由追寻的无形之剑,自我情感的追寻呈现出的依旧是一种被抑制性与悲苦性。
通过梳理与考察,从中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期间的香港爱情电影,无论是彼时电影创作中反复演绎的情感自我追寻上的被抑制性与悲苦性情境,还是其相对于爱情的悲苦性而言的大圆满结局,其爱情表达都与伦理道德传统指称的家庭观念、伦理秩序、美德精神等紧密相关,显现出了爱情的自我追寻与伦理道德传统两者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调和与被调和”的话语关系。从本质上看,此般情感表征体现出当时的创作者注重“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颂扬传统的家庭伦理观,体现儒家美德的精神世界”[9]40。也正是因为其显露出鲜明的伦理道德束约性,亦使得此时期内的爱情情感文化建构具有较为鲜明的“情感调控”特质,即“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追寻与实现上的被控制性与被调和性。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感至上”转向与“后情感主义”夹杂
学者张燕在分析香港都市爱情电影的历史与文化时指出:“就内在文化表达而言,香港都市爱情片经历了从移民文化到青春文化、本土文化、世纪末怀旧文化等的推进过程。……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年轻人开始逐渐有意识地探寻自我主体身份,香港逐渐由移民文化向本土文化认同过渡。”[10]108在香港由移民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过渡转型中,生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是其现代转变中的重要节点。此种文化意义上的转变,也使得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在进入80年代后,“情感至上”的表达成为显见的主流话语;同时,在80年代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中,还涌现出了一定数量的“后情感主义”表达的电影,与“情感至上”特质的爱情电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对照。从而使这时期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呈现出“情感至上”与“后情感主义”夹杂的图景。
(一)从“情感调控”到“情感至上”的鲜明转变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在分析我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时,曾指出我国的爱情崇拜遵循的价值观念,“如:个人内心平衡和社会平衡、自我完善和社会功能等,这一切的基础是建立在维护亲属关系和社会整体互补思想之上的家庭观念”[11]280。个体与家庭(以及由家庭紧密关联的伦理纲常)的二元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有着较为显见的表征;其鲜明地体现为前文所论及的伦理道德束约下的“情感调控性”,显现出的是个人情爱的被抑制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现代化带动的个体主义思想,一种更加讲求个体自由的情感文化随之鲜明显现。此种情感文化特质,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爱情电影过渡转变中可见端倪。
1979年的《纯爱》,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两人的爱情受到了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抑制,最后的悲剧成了必然。然而,这部具有鲜明的情感抑制性的影片,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市场反响。《纯爱》收获了18万港元票房,此等票房成绩排在了1979年度香港电影票房的末端,可见此类情感抑制的爱情,已然和彼时香港观众的接受有了一定的差异。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1980年上映的《喝采》,收获290余万港元票房,位列当年度香港电影票房榜第15位。《喝采》也是讲述青年男女的爱情,但和《纯爱》的情感抑制不同,它显现出的是对青年男女情爱欲望的洋溢与尊重。影片中陈百强饰演的主角,在自己唱歌的梦想以及爱情的追求上,虽然与父母之间有着代际的冲突,但影片显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肯定了青年人自我追寻的价值,影片最后陈百强通过歌唱比赛实现了梦想。虽然爱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圆满结局,但却留给了观众美好的想象,恋人的分开并不是一种悲情的结局,而是孕育着新生与希望。对比考察1979年的《纯爱》与1980年的《喝采》,它们在观众接受上的受冷落与受欢迎的反差,体现了香港社会文化的转变。爱情影片的情感文化自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与彼时的观众接受相匹配。
此种情感文化的变迁,与彼时香港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学者赵卫防指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产阶级晋升为社会领导者,标志着香港社会在思想文化上亦步经济之后尘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而使香港社会文化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这种自主性一方面反映在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自觉和文化觉醒较过渡转型时期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反映为对人之本体欲念的重视”[12]272。这种“对人之本体欲念的重视”,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上,集中表征为“关于现代人对真爱抉择的命题探索、对爱情的意义和本质的追问,以及凸显互相救赎的主题”[13]87。
如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以青年人爱情为表现主体的爱情故事,《喝采》(1980)、《柠檬可乐》(1982)、《第一次》(1983)、《少女日记》(1984)等,都将青年爱恋与自我追寻、自立自强等观念相结合,突出青年爱恋的“情感至上”特质;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表现中产阶级群体的爱情电影,《一屋两妻》(1987)、《七年之痒》(1987)、《开心勿语》(1987)、《呷醋大丈夫》(1987)、《一妻两夫》(1988)、《大丈夫日记》(1988)、《三人世界》(1989)、《再见王老五》(1989)、《小男人周记》(1989)、《相见好》(1989)、《三人新世界》(1990)、《小男人周记2错在新宿》(1990)、《老婆,你好嘢!》(1990)、《婚姻勿语》(1991)等。此类爱情电影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主要围绕着婚姻关系展开,即离婚、复婚,或是感情危机,此类涉及婚姻关系主题的爱情电影对爱情本身有着更为深入的观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九七的前途问题开始浮出地表,社会上普遍弥漫一股突如其来不知何去何从的迷乱感,因而纷纷出现了许多关于生活飘离与文化身份思虑的电影”[14]160-161,香港爱情电影也涌现出了此类情境下的爱情议题。如《胡越的故事》(1981)、《男与女》(1983)、《非法移民》(1985)、《美国心》(1986)、《秋天的童话》(1987)、《我爱太空人》(1988)、《八两金》(1989)、《人在纽约》(1989)、《爱在别乡的季节》(1990)、《浮世恋曲》(1992)、《风月》(1996)、《甜蜜蜜》(1996)、《玻璃之城》(1998)等。这些离散的爱情叙事集中生发于“九七议题”的时期内,使得这些文本标识上了独特的香港本土文化身份。同时,此类离散情境下的爱情叙事,往往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爱情的奇情性。如《甜蜜蜜》借由爱情有效串联起了离散与家国叙事,并在中美的辗转漂泊中,最终以爱情的传奇性相遇大圆满结局,寄寓了爱情的隽永与治愈性,凸显了爱与救赎的主题意向。此类离散情境下的爱情电影创作,它们在离散的两个中心,即家国与居留地之间,其家国之情的传达与建构,往往不太带有显见的意识形态性,其离散爱情叙事,可在相当程度上视为男女爱情叙事的烘托与见证,参与并形塑着爱情的恒久与情深。
从以上的分析考察可以看出,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前爱情男女受到的伦理道德的束约因素已全面消退,个体爱情的自我追寻及其价值实现成为情感表现的重心,作品中一再塑造的爱情神话,彰显出鲜明的“情感至上”特质。
(二)“后情感主义”的冒升与“情感至上”的夹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与“情感至上”彰显出的对爱情的赞扬以及爱情神话的塑造相对照的,则是一种可称之为“后情感主义”的爱情表达。“后情感主义”是美国社会学家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Meštrovic)提出的理论。然而,“梅斯特罗维奇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后情感主义概念,而是从多方面对后情感特征及其所涉及到的文化社会现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5]124,其中包括“后情感主义”中的情感与理性、文明的关联,情感与身份认同,情感与社会政治等内容。而要理解“后情感主义”,则需要明晰相对“情感主义”而言,其指称的“后情感状态”是什么。
学者王一川提出:“后情感主义建立在一种新的美学信念基础上:文艺可以替代、虚拟、转让或出售情感。其代表是后现代主义及大众文化浪潮。情感主义诚然也主张想象或虚拟,但它毕竟认定这种想象或虚拟可以传达人的本真情感及人类现实的‘本质’;而后情感主义则不相信本真情感及人类现实‘本质’的存在,洞穿经典情感主义的人为假定实质,转而索性把情感话语碎片用作日常想象、虚拟、戏拟或反讽的原材料,并且成批生产这种替代或虚拟的情感。”[16]7从中可见,“后情感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情感表征;其相对于情感主义而言,在一定面向上充盈着对“本真情感”的解构。以此种“后情感主义”观照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则会发现相较于“情感至上”所表征出的对自我情爱的追寻与实现而言,“后情感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情感至上”进行了解构与祛魅,形成了一种相对于“情感至上”的“后情感”表达。此般情景下的“后情感”表达,在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脉络中,或许最早体现于王家卫的电影创作中。
王家卫的电影往往被冠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此种后现代主义下的拼贴、碎片化、对意义的消解等,在1988年王家卫的处女作《旺角卡门》中有着较为不同的呈现。因为影片对人物主角情感的塑造(无论是友情、江湖义气,还是爱情),还算有着完整的故事建构,体现出的是一种较为遵从经典叙事的创作。而当王家卫的创作进入到1990年的《阿飞正传》后,完整的情感叙事好像就此“消失”,一种碎片化及捉摸不定的情感表达成为王家卫电影的常态。“王家卫热衷于事物的表象,平面化的表述,使观众在浮光掠影之后产生诸多疑惑。碎片充斥,使影片产生了强烈的断裂感。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断裂,王家卫采用了常规电影避之唯恐不及的手法——内心独白,而且是大量地使用内心独白,王家卫不依靠情节之间的张力而是凭借面对观众的自言自语实现碎片与碎片之间的过渡。”[17]10王家卫电影采用了常规电影较少运用的碎片化手法及内心独白,这在此前的香港爱情电影中的确是较少出现的。爱情电影的创作大多呈现出一种闭合性的叙事样态,无论是离散悲情还是圆满爱情,其都有着较为清晰的爱情“发生—发展—结局”的脉络,故事的建构亦大都遵从传统的线性叙事;而王家卫的碎片化爱情叙事,显现出了他的“另类”表达,并在《重庆森林》(1994)、《堕落天使》(1995)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爱情电影情感文化的透视,指称的“后情感主义”即是此种爱情电影创作,与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的爱情的线性叙事营建以及对爱情和自我本真情感的追寻形成鲜明反差。“后情感主义”是一种相对于“情感至上”特质的意义指称,在同期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此种“后情感主义”表达还显见于刘镇伟执导、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1995)中。《大话西游》对经典的解构,对其他作品的戏仿,在看似嬉闹的爱情故事中传达出一种对于自身情感无法把握的惆怅与无奈,亦传达出了较为显见的“后情感主义”特质。除了《大话西游》,香港青年导演的一些电影亦显现出了此种“后情感主义”特质,葛民辉执导的《初缠恋后的2人世界》(1998)、黎大炜执导的《超时空要爱》(1998),都是通过碎片化非线性叙事的运用,以及游戏性的嬉闹、反讽等手法,充满着对爱情的解构。
从中可看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冒升出的“后情感主义”话语,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美学特质息息相关。尽管后现代主义并无一个明确的理论界定,但其对于元叙事的解构,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怀疑,以及其反讽、戏仿、游戏等形式彰显出的混杂性、多元性特质,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得到了集中显现,这与彼时香港的社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香港社会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当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其已处于詹明信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时期,香港的文化多元主义表征得异常鲜明,现代主义的文化取向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取向混杂并存,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爱情电影的情感表达与文化建构上,呈现出的是彰显情爱追寻的本质主义的“情感至上”表达,以及与之形成文化对照的对爱情本真解构的“后情感主义”的夹杂。同时,此时期的“情感至上”与“后情感主义”夹杂,两者之间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情感文化上的并置,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爱情表征上的共融与互相对照。
三、21世纪以来的“情感至上”主导性与“后情感主义”的消退
香港电影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盛发展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步陷入低迷。“经历了多年影市萎缩后,步进二十一世纪,香港电影可说正陷进身份危机当中,处于十字路口之上,若要寻觅出路,香港影人应该坚持留守本土?抑或是顺势‘北漂’,投向如日方兴的国内市场呢?”[18]127坚守本土或是合拍成了香港电影创作者面临的新的时代选择。也正是在此历史情境下,香港电影创作者的北上,以及与内地合拍电影的现象,开始愈发凸显,并经由2003年CEPA协议的签署,使得香港电影的创作进入了合拍片的新情境之中。
21世纪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爱情电影数量激增。仅2003年,合拍的爱情电影即有《百年好合》《老鼠爱上猫》《新扎师妹2》《我的失忆男友)《炮制女朋友》《爱,断了线》《地下铁》《安娜与武林》,以上爱情电影占据了2003年度香港爱情电影创作数量的一半,此种情境在2003年以前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标志着香港爱情电影的创作自此进入到了合拍片的新阶段。此种合拍爱情片的火热情境,在2004年、2005年得到了延续。2004年的合拍爱情电影有《花好月圆》《大城小事》《2046》《七年很痒》《绝世好宾》《爱,作战》,2005年的合拍爱情电影有《后备甜心》《长恨歌》《千杯不醉》《挚爱》《神话》《再说一次我爱你》《如果爱》《情癫大圣》。
此般情境下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在爱情的情感展现上,基本上可划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喜剧爱情的样态,通过对爱情的浪漫化、理想化处理,展现出的是对爱情美好的期许;其二是文艺爱情的样态,在对非大圆满爱情的展现中,表征出的是对人物主体爱情及其命运的深沉关切,及其对爱情隽永、永恒追求的希冀。此两种形态的爱情表达,彰显出的依旧是对情爱本真的“情感至上”本质的探求。
而到了2006年左右,伴随着合拍片与香港本土电影制作的市场分众化,一种“叶念琛式”的“后情感主义”爱情电影创作,开始在新一代香港年轻导演的创作中集中显现。2006—2008年,叶念琛编导的3部爱情电影《独家试爱》《十分爱》《我的最爱》接续上映,收获了较好的市场反响,被称为“现世代爱情残酷物语”。3部影片都围绕着年轻人的爱情展开,亦大致采用了较为固定的演职班底,并由叶念琛本人编剧及执导,这使得作品具有风格延续及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叶念琛的爱情电影并非“传统式爱情至上、真爱无敌的爱情片,反而是外表美满、内藏暗涌的不忠爱情故事”[19]130。然而,此种爱情呈现,却在票房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亦折射出了香港年轻观众对此种非传统爱情观的一定认同。
类似于叶念琛爱情电影般对“情感至上”进行祛魅与解构的创作,在21世纪以来的香港青年导演创作中,亦体现在林子聪执导的《得闲饮茶》(2006),彭浩翔执导的《志明与春娇》(2010),麦曦茵执导的《前度》(2010),黄真真执导的《分手说爱你》(2010),曾国祥、尹志文执导的《恋人絮语》(2010)等电影上。此类青年导演创作的所谓贴合香港青年观众的“后情感主义”爱情电影,对爱情的解构、祛魅,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对传统爱情至上观念的一种自我怀疑以及对爱情再建构的无力与迷惘。相较于传统爱情的崇高与理性,他们展现出的爱情更多地显露出一种非理性下的呓语,尽管他们可能很切合时下年轻人的爱情观,但是此类影片并未对年轻人的爱情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案。他们基本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对年轻观众心理的迎合,但在爱情的意识形态表达及对现代爱情男女情感的深层次观照上,则明显匮乏。故而,此类所谓贴合香港年轻观众的“后情感主义”爱情创作,在2010年之后,不仅创作数量变少,而且在作品的影响力及市场反响上也明显消退。
与这种“后情感主义”爱情创作相对照的,则是在爱情的情感营建中,虽然亦表现爱情困境或是质疑,但最终依旧是相信爱情或是迎接自我新生的爱情电影创作,在2010年以来开始明显重新占据主流。此类电影有《单身男女》(2011)、《不再让你孤单》(2011)、《春娇与志明》(2012)、《单身男女2》(2014)、《哪一天我们会飞》(2015)、《纪念日》(2015)、《王家欣》(2015)、《失恋日》(2016)、《原谅他77次》(2017)、《春娇救志明》(2017)、《某日某月》(2018)、《幻爱》(2020)、《金都》(2020)、《阿索的故事》(2020)、《还是觉得你最好》(2022)、《缘路山旮旯》(2022)等。此类爱情电影创作,通过与年轻观众的情感心理的契合,达致商业娱乐与爱情梦幻的制造,并在大多数的影片创作中凸显出对传统伦理人情的回归。
如2015年刘伟恒执导的《王家欣》,通过成年之后的成人怀旧视角,传达着对美好青春爱情的渴求与怀想。有论者指出:“怀旧之于记忆,是带有过滤性的特质。然而,另一方面,过去使人痛苦的记忆,有时候又会在怀想的过程中担当净化和美化自我的作用,那是说人们透过对昔日痛苦的回想,肯定今日的自我,一个熬过艰苦而来的自我。”[20]62此种情境在《哪一天我们会飞》(2015)、《某日某月》(2018)中亦有所体现。此种怀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对过往香港的追忆,此种追忆往往是美好的,其与主角们现实处境下的爱情困境形成了对照。然而,通过对过往的怀旧与追忆,此类爱情叙事又都是以一种“圆满”的结局呈现,即直面自我或是对婚姻重提信心,从而走向一种以情感治愈现实的叙事情境。《春娇救志明》(2017)、《金都》(2020)、《幻爱》(2020)则从对爱情本身的怀疑与生存困境出发,在直面自身的精神困惑后,重识自我以及对爱情与人生重燃希望;《还是觉得你最好》(2022)则在兄弟伦理及爱情危机中,通过对爱和宽容的回归与肯定,实现了家庭的和谐与伦理的复归。
从中可见,在经历了一段“后情感主义”对情爱至上的戏谑、消解、质疑之后,香港的爱情电影创作又重回“情感至上”的创作表达话语之中。这些爱情电影创作,较为真实地关切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同时,它们又不陷入悲观、虚无的情感表达之中,而是强调情感的本真性,以及对爱情和自我的追寻与实现。
四、结语
通过对1946—2022年间香港爱情电影衍变中的情感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期间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其情感表达与伦理道德束约有着紧密关联,此种情感文化主导性,使得此时期内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无论是外显的伦理道德桎梏,还是内生的伦理道德自我规约,都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情感调控”特质。而伴随着香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自我主体性的凸显,香港爱情电影中的情感文化开始呈现出从“情感调控”到“情感至上”特质的转变,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爱情电影创作中表现得尤为凸显,其不同爱情电影样态一再演绎的爱情神话,表征出的是爱情至上的永恒信条;同时,与“情感至上”的文化表达相伴而生的,则是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显现出的“后情感主义”创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对本真爱情的解构与祛魅,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爱情电影显现出“情感至上”与“后情感主义”的文化夹杂。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面对香港与内地合拍爱情电影的新情境,表征爱情浪漫与本真求索的“情感至上”创作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期间虽然亦短暂冒升出如叶念琛式的后现代主义爱情创作,但此般“后情感主义”风潮在2010年以来很快消退,“情感至上”特质的影片创作占据市场主流,成为时下香港爱情电影的情感表达与文化建构的主导样态。
正如学者郝建指出:“爱情片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永不衰落的电影类型。它永恒的魅力来自人们对纯真爱情的永恒向往,这向往或是灰色生活里的一点亮色,或是感情沙漠中的一片绿洲。”[21]46二战后香港爱情电影衍变中的情感表达,爱情的营建虽然有着不同的时代印记及文化呈现,但爱情本身并不会因时代不同而褪色,也正是因为对爱情的永恒追求,才呈现出了如此丰富多元的香港爱情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