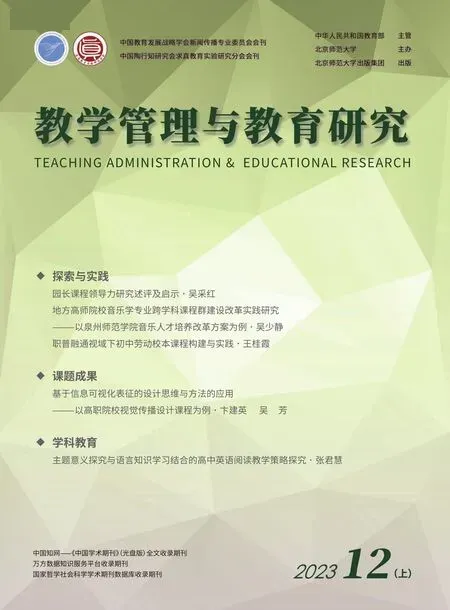跨学科视野下美术融合其他门类教学的实践研究
2023-02-11中央美术学院100105
陶 琪 (中央美术学院 100105)
美术既是空间的艺术,也是平面的艺术,它通过空间和平面的方式来展现美的存在,美术作品则是通过视觉来产生“美”的意义。从20 世纪开始,各门类之间的跨界开始崭露头角。美术不仅能与其他艺术门类跨界,甚至可以与各学科门类跨界。跨界的意义不在于猎奇,而是从学科跨界之中,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创造力。由美育出发,从审美角度重新观看各门类学科,不仅能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更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视野,由美术之美上升到学科之美。
一、意象与视觉之美的融合
语文,由“语”和“文”组成,可以理解为文本和语言的作品,其中也包含这个形成过程的总和。美术与语文的融合,在中国古代便就有所体现。例如,北宋时期徽宗就曾设立“画学”,画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正规的艺术家培养机构,考生通过画学的考核便能入校。画学考核的内容常与诗词中的诗眼和摘悉句有关,考生根据诗句来画出它们的意境,某种意义上与现在看图说话有异曲同工之意。以诗句来检视考生的构思与巧妙,从而考查考生的心性。如“踏花归来马蹄香”“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六月杖藜来石路,午阴多处听潺湲”等,以“景”和“趣”的诗句来考核绘画的同时,考查考生的文学修养,衡量的标准则是看考生能否通晓画意。
诗词通过语文表达情感,两者的方式虽有异,但两者又是指向同一处的。“画学”考试以文本为灵感,让考生创作美术作品,从而考查考生的思维创造能力,于今天而言,不失为一种文与美的跨界实践案例。通过诗词考查学生,教授学生,不仅能让学生理解古诗中的意象,更能感受到古诗的奥妙与韵味。
口述是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口语作品,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人与人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传达意象,而画面也是意象的一种。比如,在美术教学中,老师可以让一位同学讲一个故事,再让学生们根据这个故事来绘制一幅美术作品。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画面表达,在实践中通过口述故事的方法让学生创作作品,在提升学生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能激发出学生对绘画的兴趣,对故事的好奇,对于学生而言,讲出好故事也指向写出好的文章。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美术与语文相辅相成,从“文之美”到“语之美”,再到“画之美”相互交融。通过语文的意象美来引导学生创作美术作品,既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语文的意境,也能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诗画同源,甲骨文作为汉字的相对成熟形态,它既是画,也是书写,语文与美术的关系不是互相利用,而是互相成就,二者在学科跨界中指向的是学生情感表达的提升。
二、数理逻辑与美术的融合
数学被理解为人类对事物的抽象结构与模式进行严格描述、推导的一种通用手段。在数学教育中,常常使人联想到理性,但数学和美术的渊源却颇为深厚。画家达·芬奇的艺术作品观众中常有数学家出现,他也曾说能看懂他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数学家。众多科学家和艺术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共同探索数学与艺术的关系,论述了透视的重要性,他们将“黄金矩形”运用到绘画创作之中,得益于这样的研究才使得绘画开启了新的篇章。
20世纪抽象艺术的先驱康定斯基认为“一种伟大的、几乎无限的自由是现代艺术的特征”,现代数学基础的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尔认为“自由性乃数学的本质”。康定斯基把“结构”引入绘画,与著名的当代数学流派布尔巴基的“结构主义”不期而遇。1923年,康定斯基发表的《点·线·面》一书中对几何基本对象的艺术表现做了深入的分析,由此数学与艺术被再次联系起来,现代美术作品与数学的关系逐步升级。数学与美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属于抽象思维的结果,数学与美术的融合也必然水到渠成。
在抽象思维的影响下,又诞生了结构主义绘画、极简主义绘画等,其表现形式大多数通过融合数学和美术而被创作出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美术与数学的融合为美术教育提供可行性的蓝本。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点、线、面”式的抽象主义美学来对学生的创作进行引导,用美术来呈现数学的形象,由此开拓学生的抽象表达素质也未尝不可。此外,立体主义绘画、解构主义绘画等都与数学思维有些许渊源,从数学和美术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视觉艺术,使学生在扩宽美术视野的同时,又能从教学中感受数学抽象思维的乐趣。
美术既有数学思维,数学中也包含美术特色,两者融会贯通,互相成就。数学不仅了拓展美术的边界,更使艺术变得丰富多彩,美术也不断深入地诠释数学的内涵。例如,在数学的基础教学中,常常会使用到几何图形、点和线条,数学的点、线、面自然也可被理解为美术的点、线、面。数学与绘画的结合,既是科学严谨与美的体验相融合,二者对美术创作具有重要的创新作用。在美术教育中,美术与数学的跨界,不仅能使学生体会到数学的生动有趣,同时也能深化学生创作美术作品的内涵。
三、历史与美术的跨界
历史与美术的跨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画。历史画的概念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理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画被称为“故实”,古代中国绘画理论将教化劝诫的功能视为“故实”绘画的目的,例如,李唐所作的《晋文公复国图》,就是通过绘画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春秋时期的场景。此外,还有《清明上河图》《女史箴图》等名作。
三星堆是我国史前文明的产物,距今大约五千年,历史与美术之花也在其中传来芬芳。梁启超先生曾说:“少年智则国智。”三星堆文化如何被青少年关注,成为三星堆历史学习的难题之一。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青少年有太多的信息来源,获得信息的便捷反而使得学生无法聚焦,而历史课本中的图片信息又远不足以展现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鉴于此,三星堆博物馆推出了一本创意立体书,名为《神秘三星堆》。该书通过美术和立体书的结构,来讲述三星堆的故事,立体画面不仅包含视觉的震撼,还有解密的趣味。
从美术教育的角度出发,历史与美术的跨界并非是让学生做美术的历史考古,而是发现生活中的历史。例如,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家庭“历史故事”,单单一张画是道不尽的。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制作一本家庭历史书,或是一本家族历史书,通过学生与家庭的纽带,指向家庭与国家的纽带,历史并非事不关己,而是每一个家所组成的,每一个人所组成的,因此,由家庭历史绘本出发不失为学习国家历史的有趣的切入点。例如,中国传统纹样中的经典——缠枝。缠枝纹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其中不乏包含中国思维中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等思维。缠枝纹样暗藏在我国古代的众多器物之中,如瓷器、玉器、绸缎、糕点等,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器物中缠枝纹依旧保持着极高的生命力。在美术课堂上,学生大可绘制一幅“缠枝”思维下的纹样,无论是用于制作本子封面,还是玩具图案设计,它都指向了对中国传统图案设计思维的实践。
历史与美术的融合由来已久,无论是历史画、故实画,还是创意绘本和中国传统纹样,都显示出历史与美术跨界融合的可行性。学校美术教育与历史的跨界,不单是美术教育的革新,更是对文化的再解读,学生通过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其意深重。
四、拓宽视觉的新边界
20世纪的艺术家波洛克是“行动绘画”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行动绘画是指通过行为来创作绘画作品,又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抽象是指画作的视觉感受,表现可以理解为画家的行为和颜料的表现。具体可理解为画家围着画布带着节奏地走动,任颜料在画布上滴流,再将整个行为或创作过程通过录像和摄影记录,最后这幅关于画家与色彩关系的行动绘画便创作完成。行动绘画的概念或许是复杂的,但是在实施落地上却是相对简单的。落实到具体美术课程,教师可以采用连环画绘本的教学手法,在一张大画纸上,邀请每位学生共同创作,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记录这一过程,形成的视频即构成了“行动绘画”的一部分。再比如,通过调动学生的行为,比如跳舞、行走、记笔记等,在学生的落点处涂上颜料,例如,戴上涂油颜料的脚套行走在画纸上等,每位学生随机创作行动绘画,最后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也不失为有出处、有根源的艺术创作。
此外,20世纪50年代,波普艺术诞生,它是一种由可复制性而著称的艺术流派,其创始人之一的安迪·沃霍尔常常将报刊,甚至是一些品牌标志进行剪裁,拼贴和再创作。学生经过新媒体的技能学习后,教师可以拟定一个主题,让学生拍摄适合的照片,将照片打印出来。打印后的照片经过剪裁和拼贴形成独特的审美内涵。从20 世纪开始,艺术创作与科技和媒体逐渐展现出融合之势,美术创作作为艺术的门类之一,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的科技往往是青少年最乐意接触的,以此为兴趣,由兴趣出发,探索出美术的乐趣。
新媒体是依托新的技术支撑体系出现的新传播途径。它具备高效、便利和成本低的特点。在艺术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传授摄影、录像、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技术,建立艺术课程与社会生活的对话,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还可以拓宽学生的艺术表达渠道。
新媒体技术进入美术教育,不仅是教育方式的技术层面的革新,更在于技术和美术之间的跨界融合。今天新媒体与美术的融合在高校中已经有所体现了,如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于2022年成功申报科技艺术为本科新增专业,成为全国第一个具有科技艺术本科专业的教学单位。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崭新人类经验和社会问题,运用新的科技发展成果,以丰富艺术冲击力与感染力的实践和研究。此外,还有中国美术学院的跨媒体艺术学院等。面对技术变革,跨媒体就是用跨越媒体来激活当代艺术创作,重构科技社会的审美内涵。对中小学生而言,新媒体与美术的融合同样的意义非凡,它不再局限于工笔技法的绘画,对美术教育而言,延展出更多的可能性和“玩法”。新媒体、新科技之于学生,将不仅限于了解信息的工具或是娱乐的玩具,而是美术创作的一种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