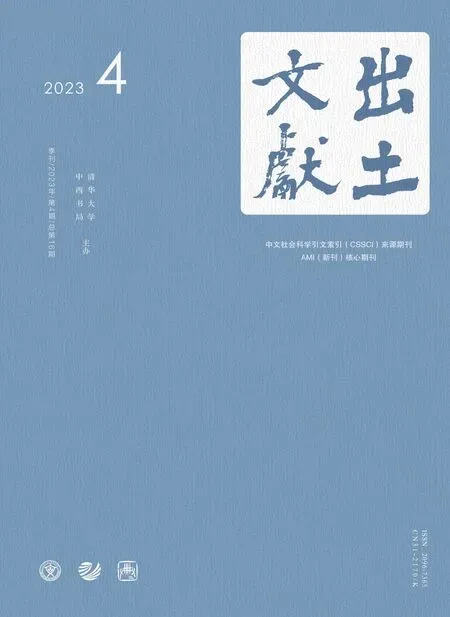物质文化视角下的早期中国书写*
——读麦笛《竹上之思: 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
2023-02-09肖清
肖 清
江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麦笛(Dirk Meyer)先生的专著PhilosophyonBamboo:TextandtheProductionofMeaninginEarlyChina中译本《竹上之思: 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以下简称“《竹上之思》”)已由中华书局(香港)于2021年出版,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倩。这本书最大的创新点在于作者将文本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meaningful object),以此提出了一套新的思考早期中国文本结构与写本文化的方法论。本文先介绍该书的研究背景,概述该书内容,再围绕其方法论问题展开研讨。
一、 背景介绍
麦笛博士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现为牛津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院士及中国哲学教授,牛津大学写本及文本文化中心创始主任,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汉学丛书”主编之一。麦笛专治早期中国思想史,并尤为关注口传与书写对早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本书就是其博士论文《战国哲学话语的意义建构: 郭店1号墓古文字材料探论》(Meaning-ConstructioninWarringStatesPhilosophicalDiscourse:ADiscussionofthePaleographicMaterialsfromTombGuodiànOne,2008)的修订本。(1)Dirk Meyer, Meaning-Construction in Warring States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A Discussion of the Palaeographic Materials from Tomb Guōdiàn One, Leiden University, 2008.除了这本专著,麦笛的代表作还有论文集《早期中国论证的文学形式》(LiteraryFormsofArgumentinEarlyChina,2015,与耿幽静〔Joachim Gentz〕合编)、《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 〈尚书〉成书与思想研究》(Originsof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y:StudiesintheCompositionandThoughtoftheShangshu〔ClassicofDocuments〕,2017,与柯马丁〔Martin Kern〕合编),学术论文《书写意义: 早期中国哲学话语的意义建构策略》(“Writing Meaning: Strategies of Meaning-Construction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格式化的意义: 对清华简〈汤在啻门〉和它关于中国早期思想生产告诉了我们什么的深描》(“Patterning Meaning: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Tsinghua Manuscript ‘*Tng Zi Chì/Dì Mén’〔Tng Was at the Chì/Dì Gate〕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Though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等。(2)https://orinst.web.ox.ac.uk/people/dirk-meyer, 2022-4-11.
自20世纪90年代湖北郭店《老子》写本出土以来,早期中国的出土文献吸引了大批国际简帛研究者的注意,促使许多研究者从这些珍贵的“原始”文献中重建早期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并由传统的文献释读,逐渐转向探讨早期文本如何在口传与书写共存的语境中生成、传递知识等理论问题。在这之中,研究书写问题成为了他们理解早期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通道。麦笛《竹上之思》的问世就依托于汉学界的这一研究背景。
从整体上看,国际汉学界对郭店《老子》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翻译与文献学方法论建构两个方面。翻译研究上,韩禄伯(Robert Henricks)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 郭店新发现文本翻译》(LaoTzu’sTaoTeChing:ATranslationoftheStartlingNewDocumentsFoundatGuodian)与安乐哲(Roger Ames)、郝大卫(David L. Hall)合译的《〈道德经〉让生命充满意义: 以新见郭店本为依据》(DaoDeJing“MakingThisLifeSignificant”:APhilosophicalTranslation)相对早出,顾史考(Scott Cook)翻译的《郭店楚简完整注释》(TheBambooTextsofGuodian:AStudyandCompleteTranslation)与《竹上之思》同年问世。(3)Robert G. Henricks, Lao Tzu’s Tao Te Ch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 Guod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Dao De 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Scott Cook, 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Complete Translation,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2.文献学方法论建构上,鲍则岳(William Boltz)与罗浩(Harold D. Roth)各自在美国达慕思学院1998年举办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古代文献整理的若干基本原则》(“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郭店〈老子〉对文研究的方法论问题》(“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GuodianLaoziParallels”)均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4)William Boltz,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 in 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 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39—51; Harold Roth,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Guodian Laozi parallels,” in 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 71—88. 两篇文章的中译可参艾兰(Sarah Allan)、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原编: 《郭店〈老子〉: 东西方学者的对话》,邢文编译,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4—58、59—80页。
《竹上之思》自2012年英文版正式出版以来就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关注,先后有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胡明晓(Michael Hunter)、陈慧(Shirley Chan)、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蓝悟非(Uffe Bergeton)等分别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ReviewInternational)、《通报》(T’oungPao)、《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ofChineseStudies)、《道》(Dao)、《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West)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书评。(5)Edward L. Shaughnessy, “Philosophy or Bamboo: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of Warring States Manuscripts,”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9.2 (2012), 199—208; Michael Hunt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98 (2012), 557—562; Shirley Chan,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9 (2014), 247—253; Franklin Perkins, “Meyer, Dirk,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Dao 13.1(2014),133—136; Uffe Bergeton,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by Dirk Meyer,”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5.1 (2015), 352—354.其中,夏含夷的书评还被译成中文,收录于其论文集《海外夷坚志: 古史异观二集》。(6)夏含夷: 《海外夷坚志: 古史异观二集》,张淑一、蒋文、莫福权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0—240页。此外,载于《物质文化与亚洲宗教: 文本、图像与实体》(MaterialCultureandAsianReligions:Text,Image,Object)中的论文《竹简与哲学生产: 一个有关早期中国书写与思想转变的假设》(“Bamboo and the Produciton of Philosophy: A Hypothesis about a Shift in Writing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a”)可视为作者对该书主要思想的简略概述。(7)Dirk Meyer, “Bamboo and The Production of Philosophy: A Hypothesis about a Shift in Writing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a,” in Material Culture and Asian Religions: Text, Image, Object, Benjamin J. Fleming and Richard D. Mann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41—58;麦笛: 《当文章成为实践: 阅读郭店〈老子〉》,刘笑敢、郑吉雄、梁涛编著: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 个案与方法》,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56—169页。
二、 内容概述
《竹上之思》原书除“导言”外,共十三章三个部分。第一至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分析郭店简《忠信之道》《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四篇“基于论述的文本”(argument-based text)的形式结构;第五至八章为第二部分,通过对比“基于论述的文本”与“基于语境的文本”(context-based text)在意义建构策略上的差异,分析了文本物质环境、写本文化、书写、意义建构、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第九至十三章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所涉写本的译注。考虑到将第三部分译回中文的意义不大,中文版只包括了前两部分。本文仅就译本所涉的前两部分展开述评。
麦笛认为,传统的早期中国思想研究通常仅将文本视为思想容器,却忽略了思想传递过程中物质载体的作用。因此他主张从文本物质性角度出发,假设“作为物质实体的文本能够解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本的重要信息”,以揭示早期“哲学文本的使用目的、使用者、在当时的思想交流中如何使用这些文本的相关信息”。(8)麦笛: 《竹上之思: 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香港: 中华书局,2021年,第2页。下文引述仅括注中译本页码。
麦笛将文本视为“独具意义的物质实体”的视角,主导了他对郭店文本形式结构的分析路径。在他看来,首先要在方法论上明确区分“文本”(text)与“写本”(manuscript)两个概念:
我将“文本”(text)定义为流传下来的思想实体。思想观念的表达,可以采用口头、书面两种形式,故而可以抽离于任何物质载体。文本可以通过老师、专家、谋臣,经由商路、市场,在人与人之间口头传播,从而独立于其物质语境。“写本”(manuscript)则是文本的物质体现,是文本在丝、竹、木等材质上的物理体现。混淆这二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单一归因的论述思维,从而扭曲历史事实的图景。(第11页)
在这种“文本”概念的基础上,麦笛进一步区分了“基于论述的文本”与“基于语境的文本”两种文本类型。这两种文本类型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作者基于战国哲学文本意义实践模式所做的形式化二分。相对于“基于语境的文本”,“基于论述的文本”的形式结构更具完整性与系统性,每一个结构模块在微观与宏观层面上都互相衔接并能够连续发展为一个封闭的“交叠结构”(overlapping structure)。譬如《忠信之道》,其形式结构就不仅在微观与宏观层面上形成了一套连贯的论证模式,还能够纵深地影响文本意义建构。而“基于语境的文本”的形式结构则相对松散,各结构模块之间没有系统化关联,相互孤立。
接着,麦笛比较了这两类文本在战国历史语境中的文本意义生成过程和作者问题。他认为,像《忠信之道》这种“基于论述的文本”,其高度平衡、有机连贯、结构封闭的形式特征形成了文本自身的“论述力量”,说明文本背后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作者”(proactive author)刻意为文,因此对应的传播方式可以脱离口传,仅以书面形式流传;而《缁衣》这种“基于语境的文本”由于仅在宏观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其意义建构主要依赖口传语境中“文本群体对各个思想单元内的阐释与语境化”,其文本意义传播过程是一个“文本、意义中介、信息接收者三方关系的结构”(第229页)。
全书最后两章讨论了书写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战国末年哲学话语意义建构的物质条件。麦笛援引法默尔(Steve Farmer)、亨德森(John Henderson)与维策尔(Michael Witzel)等人对古代世界各地文化中心(古希腊、印度、近东)的研究,说明轻便书写材料的广泛使用对哲学思想系统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时世界上所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中”(第266页),而郭店“基于论述的文本”所处时代恰好与这一世界性进程约略同时,因此主张将早期中国放在跨文化框架中进行平行比较。作者推断,轻便书写材料的广泛应用是战国中晚期的“创新”(第271页),在早期中国文本生成的历史进程中,“轻巧、易扩展、易使用、易携带的书写材料的普及,以及信息流的增加,促进了新的书写形式,进而促进了哲学的生产”(第279页)。
三、 批评商榷
欧美学界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有各科学者出于对社会知识传播与传媒技术的关注,参与到有关早期社会口传与书写问题的讨论中。这其中有两个长期相互对垒的学派,即“连续派”(The Continuity)与“大分野派”(The Great Divide)。“连续派”主张在早期社会中,口头传统处于中心位置并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早期文化,书写作为口传的等价物,作用也与其类似。其中的代表性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对比南斯拉夫乡村史诗的口头创作过程,从而印证了荷马史诗源自口头创作。(9)Milman Parry, “Studies in the Epic Technique of Oral Verse-Making. I. Homer and Homeric Style,”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41 (1930), 73—147; Milman Parry, “Studies in the Epic Technique of Oral Verse-Making: II. The Homeric Language as the Language of an Oral Poetry,”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43 (1932), 1—50.后来,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10)Albert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不仅使口头诗学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是辐射到古希腊之外的近百个古典及中世纪研究当中。而“大分野派”则主张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互相隔绝,强调书写对人类社会抽象逻辑思维与高级心理活动的划时代影响。尽管所论及的细节各不相同,持此观点的学者如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杰克·古迪(Jack Goody)与沃尔特·翁(Walter Ong)等都在其著作中尽力区分口传与书写之间的巨大差异,(11)Eric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Jack Goody,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er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2.透露出他们对字母文字的优越感和将“口传—书写”简单二分的思维模式。而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以及国际学界对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关系的全面理解,“大分野派”不断遭到批评。到了90年代后,詹姆斯·科林斯(James Collins)、布莱恩·斯特里特(Brian Street)等“新书写论”(New Litercay Studies)者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强调口传与书写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继而延续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12)James Collins, “Literacy and Literac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1(1995), 75—93; Brian Street ed.,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将这一争论延伸到古希腊以外的区域文明研究之中,促使其成长为国际知识界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
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学术对话中,《竹上之思》拓宽了西方书写史的研究视野,并通过关注书写如何推动抽象思维发展的问题,为国际学界的早期中国书写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传统的国学与汉学研究擅长将文本视为思想的载体,围绕文本的内容分析其思想大意或作者意图。尽管这种方法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主流且操作性较强,但同时也忽略了文本所属的历史语境及物质性特征,进而将历史建构为一个永恒的、虚构的、连续的传统。而麦笛强调要将文本理解为“有意义的实体”,通过分析文本及其各种意义建构策略,揭示早期中国哲学文本的使用目的、使用者以及在当时思想交流中如何使用这些文本的信息(第1—2页),这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都具创新性。在他看来,文本的物质条件(包括文本的形式结构及其在物理空间的传播、变异过程)对文本意义建构的影响超越了词汇层面,体现在文本的结构、布局和功能之中。可以说,麦笛突破了专注于文本内部的形式分析,将对文本形式结构的阐释与文本意义建构及历史语境相结合,来多方位地研究早期中国文本。
但美中不足的是,从后续的理论推演看,麦笛对文本物质性的分析完成度较高,而对于写本物质性问题,其研究更像是仅仅提出了一种假设,并未针对反面观点做出充分辩护。
首先是麦笛选取的对象文本数量较为有限。尽管作者明言这本书是“就如何处理早期书面思想提出一种方法论,而不在于描述书面哲学文本的所有特征”(第17页),但《竹上之思》仅就郭店简中5篇文本与相关平行文本进行案例分析,而不涉及诸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这些更具代表性的早期文献,就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了。
其次,麦笛对两种文本传统途径的分析,似乎未能完满地印证其开篇所提出的主张。麦笛分析,“基于论述的文本”高度系统化的结构看上去就像是“积极主动的作者”(proactive author)刻意为之的结果,而“基于语境的文本”则由于意义上的模糊性,依赖外部语境或权威的临场口头阐释。为此,他借用布莱恩·斯托克(Brian Stock)的“文本群体”(textual communities)概念,进一步分析了阅读、接触这些两种文本的不同群体(第198页)。不过斯托克所谓“文本群体”的理解前提是中世纪和早期现代书面文本不是简单地取代口传,而是在书写与口传之间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相互依存关系。(13)Brian Stock, The Implications of Literacy: Written Language and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可麦笛后面的论证却导向了“基于论述的文本”依赖书写,“基于语境的文本”依赖口传的二分。尽管麦笛在书中多处说明不能绝对区分早期口传文本与书面文本(第260、277、282页),但从其分析中暗含的前置设定看,他已将口传与书写理解为早期文本传播中两种独立的、互不干扰的传统,并因此忽略了口传与书写之间的复杂互动。特别是在讨论“基于论述的文本”的传播过程时,他认为竹简作为轻质书写材料有助于“基于论述的文本”的传播,却又将其衰落归因于仅限于书面传播,进而在外部口传语境中掉队,这种较为简省的归因方式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摆脱西方“口传—书写”研究的二分思维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明显地看到,很多时候麦笛借鉴了其他早期文明书写研究的经验,却未能对竹简作为轻便书写材料直至战国时期才广泛应用起来提供充分且直接的论证。特别是在讨论竹简具体在何年代才广泛运用于书写的问题上,他似乎只是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在《安阳书写与中国书写体系的起源》(“Anyang Writ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一文中,作者贝格利(Robert Bagley)类比两河流域与古印度等文明的早期文字书写研究,推测既然早期中国的书写系统已经相当成熟,那么那些刻写在竹简等易腐材料上的字词表可能只是失传了,并不是不存在。(14)Robert W. Bagley, “Anyang Writ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 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Stephen D. Houst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0—249.麦笛由此进一步推想或许这些易腐材料未必是竹简,也有可能是黏土等其他物质(第269页)。接着,他还根据沙加尔(Laurent Sagart)的上古音构拟,推测青铜器铭文所载“册”字或许不是专指竹简,而是“任何可以‘堆积’的物体”(第271页),但未能给出直接的证据。也正因此,海外的一些书评(比如夏含夷和胡明晓)就针对本书第二部分的论述,批评麦笛并没有为自己的立论提供充分的论证,质疑他以“与古代欧洲写本产生方式的类比”的方法,其言辞不可谓不犀利。(15)夏含夷: 《哲学还是竹子: 战国写本的写作和阅读》,《海外夷坚志: 古史异观二集》,第237—238页;Michael Hunt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98 (2012), 561。
从深层次讲,这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材料处理问题,而是理论视角的选取问题。国际学界在面对早期中国问题时有两种对立的视角,一个是普遍论视角,一个是特殊论视角。普遍论视角认为,中西文明之间总有相似相通之处,将研究其他文明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特殊论视角认为,中西文明是两种异质性文明,而且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语境和对象,因而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互释。从这个层面看,麦笛的研究一方面拓宽了早期中国研究的比较视野,使其充满了跨文化研究的阐释张力;但另一方面,如何摆脱理论话语的束缚,避免“简化”早期中国口传与书写的多重历史维度,也需要以辩证、历史的眼光进行考察。
小结
《竹上之思》虽初版于2012年,但在2021年中译本问世以前,尚未被国内学界广泛了解,唯有收入论文集《简帛思想文献研究: 个案与方法》中的论文《当文章成为实践: 阅读郭店〈老子〉》可视为对其研究思想的部分介绍。(16)刘笑敢、郑吉雄、梁涛编著: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 个案与方法》,第156—169页。而在国际汉学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伊维德(Wilt Idema)分别从物质文化角度讨论过书写形式的新变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但二人的研究都是针对整体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并没有专门着重分析竹简物质形式对早期文本传播与哲学思维的影响。(17)宇文所安: 《瓠落的文学史》,载《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伊维德: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物质性的思考》,丁涵译,《中正汉学研究》2013年第1期。从这一背景中看,麦笛的《竹上之思》对写本物质性如何影响到早期中国的文本传播与哲学思想的分析,应在汉学界是相当有价值的探索。
虽然上述内容是对麦笛方法论的反思与商榷,但《竹上之思》为学界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思考早期中国文本结构与写本文化的方法论,仍然是一部值得国内外学者细致解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