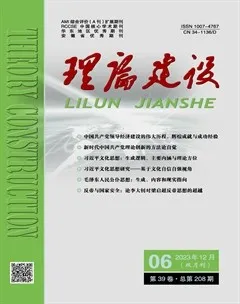反帝与国家安全:论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
2023-02-07李健
李 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李大钊与梁启超论反帝与国家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视作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1]。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国家安全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事实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构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要求,也内在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因此,对国家安全的思想史考察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已有学人作出了开拓性的努力[2-5],也有学者主张设立“国家安全思想史”二级学科[6-7]。
不过遗憾的是,除了少数研究[8]外,已有的“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几乎没有深入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国家安全思想,尤其是没有对帝国主义造成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困境予以足够关注。众所周知,对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来说,中国几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军事等所有方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挑战,可谓陷入“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危机”,中华民族遭受了重大的历史挫折。在所有国家安全威胁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逼总是构成了基本的历史背景,他们或是居于幕后,暗自操纵,或是现于台前,发号施令,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侵害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并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国家安全与民族发展的危害,几乎所有有心推动中国振衰起敝的仁人志士均将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构建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方面,围绕反帝展开了丰富的理论阐述。在他们看来,唯有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采用“反帝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视角,将有利于我们抓住中国近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的核心内容,进而廓清中国近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的大体面貌,推动“国家安全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在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史上,梁启超与李大钊为推进近代中国的反帝思想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作为对现实政治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者,梁启超与李大钊绝不满足于枯坐书斋之中的思维游戏,而试图回应彼时中国最为紧要的时代问题。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是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挑战,且近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并不具备基本的外部条件。本文将以梁启超与李大钊为研究案例,通过展示他们的反帝思想,论说反帝事业与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联系。
选取梁启超与李大钊为研究对象,还存在着更关键的原因:梁启超与李大钊之间具有真实的思想联系。当年少的李大钊于1905 年进入永平府中学时,便开始以梁启超的文章为媒介吸收新学,几乎手不释卷,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9]6;[10]5;但随着思想的深化,李大钊最终意识到了梁启超反帝思想的局限性,并通过提出自己的反帝思想理论而决定性地超越了梁启超。通过考察梁启超与李大钊的反帝思想及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我们能够清晰把握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者们在这一话题上的讨论与推进,以及这些讨论与推进如何促使一名青年思想者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主义,并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讨论梁启超与李大钊之间思想联系的成果较少,更鲜见从反帝思想的角度讨论二者思想关联的文章。除了讨论李大钊与梁启超借由《晨报》发生思想联系(李大钊曾担任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主编)的成果[11-13]之外,已有文献亦简要讨论了二者在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政治观点[14-16]。然而,与本文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仍较为少见。因此,本文的探索性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总体而言,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梁启超致力于向国民充分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危害,宣讲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一崭新的国家安全威胁及其具体呈现的多种形式,呼吁国民重视国家的主权独立问题,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然而,梁启超未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考察帝国主义的阶级属性,这导致其曾主张“民族帝国主义”国策,倡导以帝国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方针,亦曾采取改良主义的反帝策略,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危害,这些也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性。与梁启超相比,李大钊不仅洞察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坚决的革命态度,在反帝思想上超越了梁启超。
二、梁启超的反帝思想及其局限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为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历史贡献。正如其生前好友徐佛苏所论,“先生(指梁启超——引者注)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17]775;亦如萧公权所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以“爱国重群为个人不可少之公德”为核心宗旨之一,无愧为“开明之爱国者”[18]。面对构建与发展现代(1)国家的“时代之问”,梁启超在多个方面展开了思想与行动上的探索,反对帝国主义、建设国家安全便是其学术与政治努力的重要一环。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及之后进一步加速的帝国主义侵略极大地震撼了彼时国人的内心,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对摒除帝国主义威胁的努力造成了重大打击。1899 年,以政治犯身份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采用“哀时客”的笔名发表了《傀儡说》一文。此文尖锐地指出,戊戌政变及改革派被清洗之后的清廷政治,实质上便是遵循“光绪帝→西太后慈禧→军机大臣荣禄→沙俄政府”的“傀儡链条”。表面上慈禧囚禁光绪帝并以之为傀儡,其实背后亦被沙俄政府的代理人、军机大臣荣禄所摆布,成了沙俄政府的傀儡。在《傀儡说》中,梁启超向国人发出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郑重警告,呼吁国人重视帝国主义以傀儡的方式展开政治侵略的可能性。就彼时而言,帝国主义的威胁无疑是新的政治现象,因此梁启超的文章实际上向读者展示了国家安全的崭新议题,促进了国人对国家安全新领域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傀儡说》展现了梁启超对政治现实与世界前沿形势的敏锐把握,揭露了彼时中国的关税、铁路、矿务、厘金等国家权力均“握于人手”、主权沦丧的危险局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以“傀儡”实现征服与扩张的新实质:“今之灭国者与古异。古者灭人国,则潴其宫,虏其君也,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国。”[19]702-703从当代国家安全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国家安全思想具有深刻洞见。
忧虑国民的麻木不仁,梁启超在《傀儡说》发表后不久,亦发表了《瓜分危言》,更为充分地揭示了彼时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紧迫威胁。此文的署名仍为“哀时客”,延续了《傀儡说》对时局的悲哀之情,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招致“瓜分”的危险。此文认为,彼时的中国将遭遇双重瓜分——“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前者指领土的分裂,后者指内政外交诸权的丧失。梁启超尖锐地指出,“有形之瓜分”尚在将来,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等权力的褫夺则早已开始,不少国人对此竟仍“褒然充耳而无所闻,闻矣而一笑置之,不小介意”[19]716。此文细致地列举了帝国主义诸国对中国前述诸权的侵夺,并论说这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新现象,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夺其土然后夺其权焉;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夺其权不必夺其土焉,夺其实不必夺其名焉。”[19]725帝国主义仍乐于在表面上维持清政府对中国的形式上的统治,而在实际上榨取中国的核心资源、把持中国的核心权力、压缩中国的核心战略空间,具有极强的迷惑性。正如梁启超警告说:“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昵之。”[19]726梁启超希望促动其读者幡然醒悟,“中国之精血,瓜分已尽”,倘使中华民族仍不能自立自强,国家主权不能尽快收回,现代的国家安全体系不能从速建立,“中国自取瓜分”的现状便不能在根本上得以扭转,进而有陷于万劫不复的危险[19]716-736。
1901 年,梁启超用《灭国新法论》一文发展并总结了他在《傀儡说》与《瓜分危言》中的观点。《傀儡说》与《瓜分危言》所揭露的帝国主义威胁的新手段被梁启超精练归纳为“灭国新法”,展现出其对现代国家安全的明确思想关切。《灭国新法论》开篇有言:“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与传统文明不同,现代文明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崭新的特征。梁启超尤其强调“灭国新法”,即帝国主义征服与扩张的新手段、新形态,他认为这对现代国家安全的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梁启超旁征博引,运用埃及、波兰、印度、布尔、菲律宾等亡国之惨痛历史,指出“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直指国际政治的严酷现实,并充分揭示了主权国家安全可能在诸多方面遭遇的挑战。总体而言,在反帝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梁启超的国家安全思想表现出了明确的理论自觉与现代意识,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国民标定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新视野、识别现代国家安全的新领域、奠定现代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20]297-309。
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对现代国家安全的新威胁之后,梁启超势必要讨论如何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概而言之,梁启超采取的反帝“政略”是渐进的、改良主义的,他希望通过国民素质的提升(即其著名的“新民思想”)与民主政治的确立,来为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国民基础,进而赋予中国以抵抗外侮的力量。1899 年,梁启超以“哀时客”为笔名在《清议报》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指出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是“国民竞争”,依靠国民力量为后盾,并将国民的长远与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统一,鼓动国民在各个方面与别国展开全方位的、持续性的竞争,而不能如传统国家竞争那般,仅依赖君相的意志、能力与资源,并与广大国民无涉。梁启超认为,既然现代帝国主义的侵逼本质上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试图在对外扩张中实现利益欲求,其具有丰厚的国民基础,故而中国必须实现民主化、提升国民素质与政治认同,进而将中国国民转化为国家竞争的坚强后盾,若继续依赖传统政治“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的政治惯例,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无所“附丽”[20]206-210。
梁启超于1901 年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追溯至专制政治之“私”,呼吁近代公共性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建构,以内治促外交,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由弱转强、振衰起敝的治本之策。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有四大根源——理想、风俗、政术与近事,正是因为传统中国政治无法在政治理念上厘清国家与天下、朝廷和国民之间的关系,不能意识到构建现代公共性国家的重要性,一味致力于驯化、诱惑、奴役与监控国民,使国民性沦落为愚昧无耻,才导致中国不能回应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竞争的挑战[20]252-277。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十分重视其脍炙人口的《新民说》,并预料到部分读者认为以“新民”之策救国恐“缓不济急”乃至“避重就轻”的指责,论证“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近代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以近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基础,故而不再如传统帝国主义一般依赖于“一人之雄心”,而以“民族之涨力”为基础,以高素质的国民为国家竞争的后盾[20]529-532。因此,若要与近代的“民族帝国主义”相抗,便需要民主化,培养高素质的“新民”并将其在制度上转化为国家竞争的支持者。可见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中的观点是其《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观点的进一步展开。
概而言之,梁启超的反帝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重要的洞见:他出色地识别了近代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并论述了其对近代中国国家安全建设提出的崭新挑战,促进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现代转型;同时,他提出了反帝、建设中国国家外部安全的内治前提、将国民素质的提升与民主政治的建设视作维护中国国家外部安全的基本条件等重要思想。但是,梁启超的反帝思想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两点局限性。
第一,梁启超的反帝思想以中国国民性的提升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前提,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梁启超的主张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政治发展的要害,但考虑彼时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猛烈冲击,以国民教育与民主转型来逐步提升国家实力,进而回应帝国主义挑战的做法确实“缓不济急”,这一点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逐渐成为爱国者的共识。正如1924 年周恩来所著《革命救国论》所言:“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21]当然,梁启超曾一度倾向于快速革新的革命主义,他于1899 年发表《破坏主义》,主张“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20]71,但随着其政治立场的保守化,其改良主义的立场也越发僵化[22]。
第二,梁启超的反帝思想之所以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是因为他没有看清帝国主义的阶级属性,并未意识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必然会被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因而降低了其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态度。按照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资产阶级以经济垄断与政治扩张的帝国主义手段打造自身的市场势力范围,势必会遭受联合起来的各国无产者的反抗[23]。因此,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面前,帝国主义并不具备合理性,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梁启超未能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思考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导致其主要基于民族主义的视角,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帝国主义部分地具有合理性,甚至提出要采取“民族帝国主义”的“政略”,认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意图使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所用,以与同样奉行“民族帝国主义”的列强相抗[24]215。殊不知,一旦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恐会加大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甚至会与别国统治阶级共谋,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与国家安全及民族独立的目标相悖。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阶级属性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忽视导致了其在反帝问题上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从而不能切实地为近代中国的反帝事业提出可行的方案。当然,身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梁启超能够针对反帝问题提出上述洞见已然是重大的贡献,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能够提出超越梁启超的主张要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
三、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
作为近代中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通过其所创办的诸多报刊,如《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广泛地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25],以至于当十六岁的李大钊刚刚升入永平府中学之时,便能够借由梁启超的文章了解世界与中国的前沿情势,进而开始思考中国政治进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十七岁的毛泽东脱离纯粹的乡土社会、进入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学习的时候,他亦是通过梁启超的作品开阔了视野,开始思索现代政治及其基本原理[26]。然而,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李大钊愈发意识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反帝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促使李大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而超越了梁启超的反帝思想。
客观来说,李大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个历史过程。虽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早(大致可以追溯至他于1912年写作的一篇将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与释迦牟尼和卢梭相提并论为“人类一大救世主”的文章),但他最终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等到1919 年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1920 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时候[27]。在那之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李大钊早期思想影响很大,《隐忧篇》《民彝与政治》等文章充分体现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28]。李大钊与梁启超的思想关联便发生在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此一阶段。
1916 年5 月,李大钊由日本返回国内。彼时的中国正遭受袁世凯“洪宪帝制”之苦,梁启超与学生蔡锷正一同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的军事斗争,捍卫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正是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李大钊决定放弃他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毅然回国参加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积极参与反袁事业,并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深受汤的信任。8 月,在“宪法研究会”出资支持下,李大钊担纲创办《晨钟报》并出任总编辑。按照李大钊的设想,《晨钟报》应当“高撞自由之钟”,致力于“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为新创办的报刊起名为“晨钟”的意旨所在。在思想的大致方向上,彼时的李大钊与梁启超领衔的“宪法研究会”没有根本冲突,双方的思想存在较多共通之处。然而,随着反袁斗争的胜利、李大钊自身思想的变化,他与“宪法研究会”的思想冲突越发难以调和,李大钊决定与其分道扬镳,并于9月发表《李守常启事》,离开《晨钟报》。自此,李大钊与梁启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距离越发拉大,梁启超也最终成为李大钊要超越的对象[9]26-29;[10]24-30;[29]。
当然,1916 年李大钊与梁启超并不具有直接的政治联系,彼时的梁启超正在西南地区领导反袁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以及回乡为父守孝[17]475-516。李大钊主要与汤化龙和孙洪伊等“宪法研究会”的其他人物往来,因此其对“梁启超系”的失望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本人无涉。不过,即便如此,李大钊的思想已经开始具有超越梁启超的因素。在其于1917 年发表于《太平洋》的《辟伪调和》一文中,李大钊锐评“梁先生及其政团之所主张,既已全属幻想,空无是物,即或有之,亦非今世所宜,实现己所不能,持久又胡可得”,批评梁启超与当局合作、以图民主改良的策略只能沦为“翻云覆雨”乃至“为虎作伥”,并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30]230-232。而当1918 年与1919 年之交由《晨钟报》更名而来的《晨报》开始改版的时候,已然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李大钊回归并将《晨报副刊》改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阵地[11];[31]。
在反帝思想方面,李大钊超越了梁启超。与梁启超相似,李大钊也对帝国主义的危害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也呼吁国人尽早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李大钊于1917年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犀利地指出日本人打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号,表面上意在为日本乃至全亚洲的独立自主辩护,但实际上有“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的野心[30]154-156。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李大钊则明言,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在本质上“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唯有以旨在提倡“民族自决主义”的“新亚细亚主义”,才能避免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30]379-382。李大钊于同年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则有感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怒斥国际政治的强盗逻辑与帝国主义行径,倡导“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30]457-461。总体而言,李大钊与梁启超一样,竭力宣传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从民族的立场分析帝国主义的挑战及应对,他们都意识到了国家间竞争的民族主义基础。
不过,李大钊并没有停留在“民族”这一分析层面上,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入到阶级分析,这使得其“民族自决主义”带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民主与世界革命的意涵。在标志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的里程碑式文章《庶民的胜利》(1918 年)中,李大钊直言,一战的胜利者“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宣告了任何旨在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大……主义”(2)的破产和“民主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失败与“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向读者宣告,未来人类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归于“民主主义”与“劳工主义”,无产阶级将在各国内部完成民主革命,并将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帜插满全球,完成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消除帝国主义扩张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威胁[30]357-360。同年发表的《Bolshevism 的胜利》将“Bolshevism”与“多数政治”相联系,李大钊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双重期待[30]362-371。在1919年发表的《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中,李大钊提出,他提倡的“新亚细亚主义”在本质上以“自治主义”为前提,预设亚洲各地的民主化。李大钊在文末特地指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在“真正Democracy的精神”面前丧失了全部的政治合法性,“绝讲不出公道话来”[32]96-101。李大钊为应对帝国主义威胁而提倡的“民族自决主义”,预设了无产阶级在各国内部与世界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世界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李大钊的帝国主义研究带来的崭新洞见。
依照李大钊的逻辑,倘使无产阶级不能在各国内部与世界范围内完成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颠覆,便无法根除帝国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既然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源于列强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逐利的扩张欲(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中,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32]100),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自然成为反帝的题中之义。也正是在这个方面,李大钊决定性地超越了梁启超。正是因为李大钊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他才能在反帝的问题上具有更为彻底的革命性,而不会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相较而言,梁启超仅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与国民基础有笼统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扩张实际上标志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因此,梁启超仅从提升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论说反帝事业的路径,甚至一度寄希望于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以“民族帝国主义”的“政略”对抗列强的帝国主义,忽视了本国资产阶级借帝国主义国家机器压迫与剥削无产阶级的现实性。梁启超之所以会在反帝问题上采取改良主义的方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帝国主义的合理性,是因为其缺失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完成了对梁启超的超越,在反帝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革命性。1925年,当李大钊在为五卅运动积极部署,推动反帝爱国运动走向高潮,明确打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旗帜之时,梁启超也在四处奔走,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为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辩护,但其渐进改良的主张却招致了诸多批判,进而深陷舆论重围[9]179-183;[33-35]。
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李大钊的“庶民政治观”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梁启超的“新民政治观”。“庶民政治观”发现了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下层群众的历史主人翁地位,将国家政治进步的重担托付给国家真正的“多数”,而“新民政治观”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析意识,即便在其脍炙人口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在普通国民“自新”还是依赖精英阶层启蒙的问题上也是犹豫不决的。《新民说》第二节有言“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然而《新民说》第十九节又说,“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国民需要“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的启蒙[20]530,659。因此,当《庶民的胜利》明确地举起“庶民”这面旗帜时,“新民政治观”势必要退至历史舞台的边缘[36]。与之相应,当李大钊在1919 年接续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讨论时,他实际上为这一主题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32]66-70。当李大钊于1921 年底在北京中国大学发表演讲时,他指出人类政治发展出现了“由平民政治(democracy)到工人政治(ergatocracy)”的崭新趋势,这也说明他在识别政治进步所能仰赖的革命性力量的问题上取得了新进展[37]。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陷入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危机”,彼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复杂多变,而诸多国家安全危机又均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侵逼的阴影之下,因此反帝实属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安全体系的前提。考虑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全面且持续的威胁,中国难以获得渐进改良所需的国家安全环境;而帝国主义又具有明确的阶级基础,故非通过广泛而坚决的阶级斗争不能铲除,任何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均有可能造成现代国家安全体系建构进程的中断,已有的现代国家安全体系建构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很好地说明了反帝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结 语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围绕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仍相对付之阙如。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总体性危机”,而帝国主义便构成彼时国家安全挑战的基本背景,故而可以从反帝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考察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面貌,本文于此只是抛砖引玉。
作为近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梁启超与李大钊在反帝与国家安全方面有着重要而充分的论述。通过论述梁启超与李大钊的反帝思想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我们在说明反帝构成了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基本主题的同时,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一论题的历史贡献。虽然梁启超是反帝思想的先行者,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故其反帝思想具有明显的改良色彩。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展开亦曾受惠于梁启超,但李大钊最终完成了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展开了积极的反帝斗争。
当下考察梁启超与李大钊的反帝思想,也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思索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风高浪急,世界范围内“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暗流涌动、风云变幻,对我国新安全格局的构建提出了艰巨挑战。我们要正视外部环境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识别安全挑战,积极制定战略对策。
注释:
(1)由于中文“近代”与“现代”均对应英文modern,故本文对二者的具体内涵不作区分,仅根据习惯选用。
(2)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用“大......主义”指代诸如“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旨在为强权扩张服务,并导致冲突乃至战争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