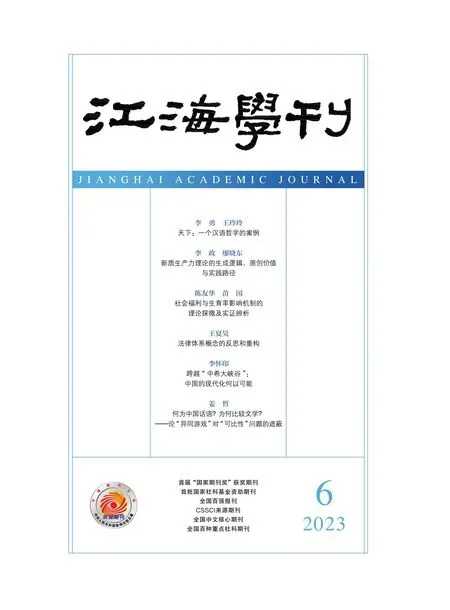论罗钦顺的“心学似禅”
2023-02-06吕花萍
吕花萍
罗钦顺穷毕生精力于程朱义理之学,断然持论“心学似禅”,其鹄的固然在于“卫道”以屏“邪说”,然其卫道的方法主要还是取道于学理辨析。(1)参见胡发贵:《罗钦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本文致力于廓清罗钦顺“心学似禅”的内在理路,力求为理解罗钦顺思想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心学“以心为本”似禅
罗钦顺首先从本体上揭示了陆象山及其后学所谓“以心为本”的禅学性,认为“天地之变化,万古自如”,(2)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6页。其固有的规律,不能用人的主观精神亦即“人心”去决定。
尽管象山自言其学得于孟子,但通过对孟子心学思想的分析,罗钦顺认为象山误读孟子,象山之学与孟子旨意有着根本的区别。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告子上》)“大者”指“心”,而“小者”则指“耳目”等感官,本心确立了,则事无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夺。由此可知孟子的“心”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认知之心,“耳目”等感官容易受到物欲的蒙蔽,而“心”则是天所赋予的能思之官,能思则得理,故物不能蔽;二是道德之心,即四端之心。此心“并非仅只是以理性判断为内容的道德思考能力,更是道德情感,后者乃是道德行为得以生发的动力因”。(3)廖晓炜:《如何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兼与周海春先生商榷》,《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陆象山依据孟子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告子上》),认为“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辞逊处自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则无所用乎思矣”。(4)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45页。象山在这里更强调孟子的道德之心,他还提出此“心”是永恒的,与宇宙同在:“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5)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3页。由此观之,陆象山的“本心”原出孟子,但却将孟子之“本心”提升为宇宙本体之心和人伦道德的本源。他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都发于此心,人的伦理道德也源自此心,此心即理。
罗钦顺认为孟子之心主要是指认知之心,“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6)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45页。在罗钦顺看来,孟子更强调心之能“思”的作用,只有心才能进行抽象的思辨活动,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反求诸己和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耳目感官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孟子才要“先立乎其大”。故孟子“吃紧为人处,不出乎思之一言”。(7)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45页。思则理得,不思则不得理,如果没有经过“思”这个过程,听由心的感应而任其西东,就会陷入“猖狂妄行”(8)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49页。之中。基于这一立场,罗钦顺一针见血地指出陆象山无所用乎思的“心”,有违孟子之旨而与禅学一致,进而点明象山之学的实质是不理解心与性的区别,由此通往禅学。“尝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则性果何物耶?……谓之禅学,夫复何疑!”(9)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45—46页。就陆象山将“本心”视为世界万有的本源而言,其与禅学确有相似之处,罗钦顺以象山之学为禅学也并非完全是毫无理据的排辟。但熟加推寻,便可发现罗钦顺的偏失在于没有体察到陆象山的“本心”概念承袭孟子,“四端”是其“本心”的题中之义,由此注定了陆象山的心与禅宗之心在本体论上名同而实异。
罗钦顺不但判定象山之学似禅,而且指责象山贻误后学,导致象山后学也都走上了通向禅学的不归之路,杨简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10)参见赵忠祥:《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罗钦顺通过具体比较杨简之学与禅学,认为两者都是说万事万物来自内心,杨简自认为已达到定慧不二的圆明境界,罗钦顺觉得这正是禅学的不逊之处。(11)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9页。“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义也。”(12)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3页。《楞严经》认为一切世间诸法,都是菩提妙明元心之形象,杨简的说法正是来自《楞严经》,先天完满具足的心,被规定为世间各种现象的根本。(13)参见赵伟:《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罗钦顺指出杨简的中心思想是以心法起灭天地,终至混淆儒佛于一窟:“以慈湖之聪明……而以心法起灭天地,又任情牵合,必欲混儒佛于一途邪!盖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14)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5页。杨简继承了陆象山以“心”为本的思想,故在他看来,吾心广大无际,宇宙中的变化不过是我或我心的变化,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我的现象。罗钦顺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愚常谓:‘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非臆说也,乃实见也。若谓‘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范围天地,则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谓之知道,可乎!”(15)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5—106页。罗钦顺认为杨简所谓的“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势必导致理气一元的世界歧出一个“心”,(16)陈来老师指出,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罗钦顺与朱熹的理气观有很大差异,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发展(参见陈来:《宋明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23页)。胡发贵老师认为罗钦顺为强化并突出“元气一本论”,特别着意在理气关系上证成“理气为一物”(参见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166—194页)。钟彩钧老师提出,罗钦顺主张“理气浑一说”,并判定其为理的哲学与气的哲学的折中形态(参见钟彩钧:《罗整菴的理气论》,《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郑宗义在《明儒罗整菴的朱子学》里指出罗钦顺理气关系与朱子并无二致,罗依气本论言理气一物,是用圆融说的理气一反对分别说的理气二(参见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103—153页)。罗钦顺强调“理气为一物”,故准确来说为理气一元论。形成二本。“如果说世界万物皆是‘心之灵’的投影,‘心’涵摄宇宙,这就会导出‘心大而天地小’的结论,而且还会必然推出‘天地是有限’的判断。”(17)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228页。罗钦顺认为就本体而言,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是一物,但人心各有所感,如果说吾心可以范围天地,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这是对主客观世界的颠倒。
罗钦顺进而指出儒、佛之间最为典型和根本性的区别:圣人本天,佛氏本心。“慈湖所引经传,如‘范围天地’‘发育万物’等语,皆非圣贤本旨……程子尝言:‘圣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见,万世不易之论。儒佛异同,实判于此。”(18)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5页。罗钦顺所谓的“佛氏本心”即指佛氏以虚灵明觉的心为本体,纵观《困知记》,“罗钦顺视为论敌的佛学主要是禅宗,而且是偏重于慧能一系的南禅顿教”。(19)秦晋楠:《从作为中介的禅宗看儒佛交涉问题——以罗钦顺对佛教的批判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6期。慧能深得拈花微笑的正法眼藏,以明心见性之顿悟法门为本,故罗钦顺说“禅学本心”可谓契其奥旨。罗钦顺指出杨简对于经传中“范围天地”“发育万物”等语的理解,都违反了圣贤的原意,混儒禅于一途:“盖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与焉!……藐然数尺之驱,乃欲私造化以为己物,何其不知量哉!”(20)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6页。世界生生不息,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使然,人是不可能对之加以干预的。如果说“此心可以范围天地”,(21)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05页。那就是贪天功为己有。在罗钦顺看来,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只认真际(本体),而否认实际(现象),而由于真际(本体)又是虚、空,故世界流为幻化,从而将不可分割的关系硬性撕裂,舍现象而言本体,导致体用截然分开,终至以人生为幻。
基于此,罗钦顺有针对性地透过佛教经典对禅学的“心识”进行分析。他说:“《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语心品’,良以万法唯识,诸识唯心,种种差别不出心识而已,故经中之言识也特详。”(22)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3页。八识之中,最重要的是阿赖耶识,称为根本依,有了这一识,前七识才能有所依,才会有所作为,此一识在《楞伽经》中称藏识、识藏,乃真妄和合心。罗钦顺指出:“藏,即所谓如来藏也,以其含藏善恶种子,故谓之藏。其所以为善为恶,识而已矣,故曰藏识。藏识一尔,而有本有末。”(23)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8页。藏是善不善因,所以为本;藏与七识同为识,所以又为末。藏之为本,曰“真相”“真识”,藏之为末,曰“业相”“妄识”。故论藏之体,本无生灭,超然自足,永恒不变;论藏之相,相续和合,刹那生灭。“迷之则为妄,悟之则为真”。(24)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8页。本为真,末为妄,同一“藏”以本末分为两截,同一识又以迷悟定真妄。对此,罗钦顺认为其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佛氏分本末为两截,混真妄为一途,害道之甚无过于此……以此观之,本末明是一物,岂可分而为二,而以其半为真、半为妄哉!”(25)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9页。罗钦顺认为,“藏”之本与末的关系,犹如目视、耳听、口言明是一物,怎能分为二呢?在现实世界中,“夫目之视,耳之听,口之言,身之动,物虽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无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26)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9—70页。倘如佛氏所言,“则方其未悟之先,凡视听言动不问其当然与不当然,一切皆谓之妄;及其既悟,又不问其当然与不当然,一切皆谓之真……当去者不去,当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灭矣”。(27)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70页。罗氏认为佛教“心识”理论夸大了心的作用而贬低了感官的意义,混淆了真与妄的标准,判断世界真妄的标准全在于主观唯心的“悟”,这就必将导致“人欲肆而天理灭”的严重危害。
实质上,罗钦顺揭露象山及其弟子之学为禅学,不但对象山后学具有警醒作用,其暗含的深意更在于,以此佐证日渐成为显学的阳明心学之于儒学正宗的异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阳明心学而言,实有釜底抽薪的学理意义。(28)参见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164页。在他看来,心学的着眼点在“心”,这种心本体论近于禅的“以心法起灭天地”,“理”在心学中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而其严辨儒、禅之异,恰恰认为儒家以理为本,因而,罗钦顺将心学判为佛禅之学并力辟之。“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29)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心、性、天是同质同层的,故圣人本心即是本天。心学的“本心”是仁义礼智之所从出的超越根据或曰“本体”,心能生发仁义礼智的理,依循心学的进路,儒者深刻体认到本心除了作为道德根源外,还具备“寂”“虚”“空”等特性。但严格地说,仁义礼智等道德价值是本心的内容特性,而“寂”“虚”“空”等是本心的形式特性。(30)参见郑宗义:《明末王学的三教合一论及其现代回响》,吴根友主编:《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81—233页。罗钦顺以本心本天来分判儒佛堪称切中肯綮,但他立足于心学本心的形式特性,将心学一概归为禅学则失之偏颇。
心学“以知觉为性”似禅
继对陆象山、杨简“本心”的批判之后,罗钦顺词锋直指王阳明的“良知”,从性论更为深入地厘清心学的禅学性,认为心学“以知觉为性”似禅。
“良知良能”出自孟子。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向善的能力,运用这种能力自然会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即良知。王阳明把此心的良知视为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3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9页。罗钦顺曾多次辩驳阳明的良知学说:“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实良知良能之说,其义甚明……正斥其认知觉为性之谬尔。”(32)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92页。罗钦顺未及就良知学说和王阳明进行直接论难,但与秉承阳明心学的阳明弟子欧阳德的辩论,直可视为与阳明的间接辩论。
欧阳德卫护师说,首先申明“良知即天理”的基本立场,然后区分良知与知觉。他根据孔子、孟子、子思、濂溪等人的言论进行考证,再与佛家《楞伽经》等进行比较,指出知觉和良知名似而实异:知觉以外物为对象,是感于物而动的生理知觉,其本身并不具有道德意涵;而良知是本心自发自感的活动,具有道德意涵和创生规范功能,而不仅仅是体验层面的认知感官作用。(33)参见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221—222页。罗钦顺则在回信中予以反驳:“足知贤契不肯以禅学自居也。然人之知识,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虑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谓别有一知也。”(34)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54页。他认为孟子的“良知”之所以成为良知,是因为不虑而知,所以“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的趋善弃恶的良知和佛家的“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的知觉,其实是一个“知”。罗钦顺所谓的“知觉”包含三层意涵:一指心能知觉性理(如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之道德知觉;二指认知事物之定理的见闻知觉;三指心能知觉外物(如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的感官知觉。在他看来,道德知觉、见闻知觉、感官知觉并无区别,同属于知觉的范畴,是人的认知能力,即所谓心的“妙用”。故他弱化了“良知”之“良”的道德意涵,将“不虑而知”理解为心之直接性的作用。据此,“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的良知与“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的知觉,都是不虑而知之知,人皆有之,人皆能之。故良知与知觉同出于心而异名,名异而实同,良知或知觉仅属心的经验作用,不能用作客观之理的规范。
在欧阳德看来,凡知视、知听、知言、知动都是知觉,是一般心理生理活动的发出者,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属于后天的知觉活动;良知则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一如孟子所谓“四端”的发出者、知觉者,是天赋自明的先验道德理性,并呈现本然之善,本然之善以知为体,不能离知而别有体。(35)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王阳明将心本体化,特别强调良知既是先天道德本原又为是非之心,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与评价体系,良知即体即用,“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36)张怀承导读、注译:《传习录》,岳麓书社2020年版,第188页。良知与知觉的本质区分也可以上溯自宋儒张载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37)参见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德性之知是由心的作用而获得的超越于感官经验的认识,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所获得的认识,而通过目见、耳闻所获得的认识是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不依赖于感官见闻并超越于见闻之知,是对于生活世界的根本认识。知识与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知识的增加并不等同于道德水准的提高,知识的缺乏也不等于道德的低下,良知不同于见闻知觉而又必须通过见闻知觉的活动来表现。良知与知觉是不离不杂的关系:不杂意味着知觉与良知是异质异层的概念,知觉由形气主体感于外物而发,属于后天的经验活动。良知则是德性主体自感自发的活动,是先天道德意识的自然流露与发用;不离意味着良知与知觉经由动态辩证发展的过程,成为间接的体用关系——良知是体,知觉是用。另外从天理来说,它首出的意涵是当然之则,良知之活动即是天理之存有,良知不仅是主体,也是实体、本体,用宋明理学的术语说,良知既是心体也是性体。据此,欧阳德一再申明良知即天理,良知即实体,可谓完全符合阳明之旨。
客观而言,罗钦顺未契良知之旨,坚持认为良知只能描述人心的天生自然能力,它本身不具有一定之理。例如,爱其亲、敬其长的行为,只是心之知觉作用的体现,而为什么要爱亲、敬长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应有其必然的理论依据,这部分属于天理或事物定理的范畴。事物之理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诉诸个人主观意识的知觉。(38)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92页。罗钦顺虽然也承认“良知”的特殊性,良知是“人心之妙用”,但是依他来看,活动的“心”与不活动的性理确为二物,心的妙用只是天理的外在表现。故罗钦顺消解了“良知”的超越性。(39)参见王振华:《良知与知识之辨——理学视域下良知与知识的关系考察》,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7页。换言之,他固守朱子的“心具理”,在他看来“良知即理”就是心学“以知觉为性”的有力证据:“《传习录》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又云:‘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皆以知觉为性之明验也。”(40)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70—71页。罗钦顺在解释“人之知识,不容有二”后指出,如果按照欧阳德的说法而加以区分,良知与知觉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楞伽经》中所谓的真识和分别事识之间的关系。“惟《楞伽》有所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三种之别,必如高论,则良知乃真识,而知觉当为分别事识无疑矣。夫不以禅学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终不免堕于其说”,(41)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54页。《楞伽经》所明三种识,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真识为第九识为一心,变现出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为现识,展现众生与外境,而七识下的有情六道众生,在此平台上,又依不同心识变现出不同的别别虚妄境,也就是说八识中除阿赖耶识外之其他七识,与色、声、香、味、触、法诸境相对,而起虚妄分别为分别事识。见赖永海释译:《楞伽经》,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良知与知觉本来同一,若加以区分,那就和禅学的“真识”无二。在他看来心学的“心即理”与禅宗的“作用是性”没有本质差别。(42)在罗钦顺思想体系中,性是理,理属于形而上的终极法则,对气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它是知觉运动背后的所以然之理,知觉运动等生理机能属于形而下的气的层面,因此认为运水搬柴是知觉运动,当它“运得水搬得柴”也就是当它受理的指导时,才能神通妙用,佛教不肯定理对行为的指导,只以知觉运动为性。依罗钦顺之意,“性理”与“知觉”是区别儒佛的关键所在,对“性理”的肯定,意味着对世俗伦常的承认、遵从与践行,由此罗钦顺将心学的“良知”推向了禅学。
罗钦顺概括了《楞伽经》的四个主旨,“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识’,曰‘二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43)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2页。由此认为“凡此诸法,不出迷、悟两途”。迷是无所觉,“迷则为名、为相、为妄想,为妄想缘起自性,为人、法二执,而识藏转为诸识”;悟是有所觉,“悟则为正智,为如如,为成自性,为人、法无我,而诸识转为真识”。真识、妄识以“觉”而定,“佛者,觉也。而觉有二义,有始觉,有本觉。始觉者,目前悟入之觉,即所谓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及其至也,始觉、正智亦泯,而本觉朗然独存,则佛果成矣”。(44)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2页。罗钦顺认为佛家的“觉”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人的认识能力而言的“始觉”,另一种为离人而言的超越精神实体“本觉”。本觉是众生自有之性德,心体本自清净,离一切妄相,即如来之法身;众生本觉被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所障蔽,迷而不觉,依靠后天的修治忽起一念趋向本觉而显发本觉,是为始觉。本觉是始觉之体,始觉是本觉之用,从根本上说,本觉、始觉一体不二。罗钦顺解释本觉是众生所本具足,此就共性而言;始觉是个人的修治之功,始觉显本觉是成佛之道,始觉消泯而本觉朗然独照时,则佛果成。由此可见罗钦顺对本觉、始觉关系的认识极为透彻,但在《困知记》中罗钦顺却每每以“知觉”称呼“觉”:“佛氏之所谓性,觉而已矣。其所谓觉,不出乎见闻知觉而已矣。”(45)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1页。很显然,罗钦顺是用“始觉”来代替“觉”,他把禅学的“性”视为闻见知觉,闻见知觉对朱子学而言都是心的虚灵妙用,还不到性理层次,这在以理气生生为本体的罗钦顺看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盖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实见,禅学之有得者,亦是实见,但所见者不同”,(46)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51页。禅学所见是虚灵知觉的神妙,因而猖狂妄行,永远触及不到客观世界事物的性理。“然又有谓‘法离见闻觉知’者,岂见闻知觉之外别有所谓觉邪?良由迷悟之不同尔。”(47)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1页。对于禅学的“法离见闻知觉”,罗钦顺认为禅学并非要人不见不闻,而是在见闻中不因分别而生攀缘。“所谓觉,不出乎见闻知觉”,(48)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61页。是指法不是凭空而有,乃是因缘和合而生。故法不离人的主体知觉,或说空性不离知觉而有,所谓的即物言空,而非物灭而后体空。罗钦顺驳斥禅学“以知觉为性”,其最终目的在于证明陆九渊、杨简、王阳明等心学皆流于禅,并为程朱理学正名。故他等视禅学的性与心学所谈的性,认为其异于朱子学所谈之性理,为此他引《论语》里的“义之与比”来佐证:“昔有儒生悟禅者……使吾夫子当时若欠却‘义之与比’一语,则所谓‘无适无莫’者,何以异于‘水上葫芦’也哉!”(49)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82页。罗钦顺所认为的“义之与比”,是人要依于客观的理而行,而不是人的本心的呈现。纵使没有人的知觉,这性理还是在物身上,所谓的物物各具一太极,所以要格物穷理以知之,尽心知性。(50)参见蔡家和:《罗整菴哲学思想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他认为“义之与比”的“义”是天理、性理,与物理一致,而不是依心而有的,心的功能只能觉知它。
相较于程朱理学,阳明所谓的良知具有新的含义,溢出了朱子、罗钦顺理气、心性理论的范围。“良知不只是一个光板的镜照之心,而且因其真诚恻怛而是有道德内容者,此即阳明之所以终属儒家而不同于佛、老者。”(51)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39页。就理论的内涵而言,“良知”源自《孟子》与《大学》的良知、致知的概念,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发出者、知觉者,故在具体内涵上“良知”不同于禅学的“灵觉”。禅学的心是清净真如心,而“见性成佛”乃指此真如心见空寂性或空如理以成佛,这种收摄于超越的真如心上说的空性或空理,不是一种自然的性能,不是知觉。罗钦顺“力斥良知”主要是针对当时阳明后学“主寂”“主静”“喜静厌动”的学风,实际上是在呼吁和提倡一种平实的治学态度。(52)参见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139页。
心学“局于内而遗其外”似禅
在罗钦顺看来,由于心、性的相似,落实到为学方法和修养工夫层面,心学的易简、格物“局于内而遗其外”似禅。在工夫论上,罗钦顺和朱子一样认为有内外之别,应内外相和而并举,即外在之“理”与内在之“心”合二为一:“惟是圣门《大学》之教……外此或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遗其外。溺于外而遗其内,俗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53)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43页。在这里“内”就人或人心而言,“外”就心外之物而言。罗钦顺“强调内外之别,并非就是将二者孤立隔绝,而是……心物的互证。”(54)赵忠祥:《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第94页。“凡吾之有此身,与夫万物之为万物,孰非出于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于内外乎!”(55)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42—143页。一方面,万物外于吾心,“自我而观,物固物也”;另一方面,“吾”与万物都是气化所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
在为学工夫上,罗钦顺主张“吾人为学,必须循序渐进,范我驰驱,如行万里之途,决非一蹴所能到。其或好高欲速,有能免于差谬而得所归宿者,鲜矣”。(56)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29页。故他对陆象山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只向内心求而可能导致的学风的玄禅化深为警惕:“有詹阜民者,从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象山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盖惟禅家有此机轴。”(57)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46页。另外他对陆象山影响后世学者不复专心读书,专务坐禅求道也深怀忧虑:“自陆象山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言……相将坐禅入定去,无复以读书为矣。一言而贻后学无穷之祸,象山其罪首哉!”(58)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94页。从明心的角度分析,禅宗认为心生万法,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59)尚荣译注:《坛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页。陆象山和禅宗都强调个体内心,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象山要求人们反求诸己,其发明本心的路径是单一的。禅宗的识心见性,并未明言运用何种固定方式来获得证悟。从禅定的角度分析,陆象山提倡静坐,日以继夜地用力操持。而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修行要义,为了断却众生的执着心,否定了坐禅的固定方式,提出“外离相即禅,内不乱为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60)尚荣译注:《坛经》,第84页。若能做到外离相而内不乱,即是禅定;若执着于打坐,牵挂于念佛,那样也是挂碍,也不能算是坐禅。
在修养工夫上,罗钦顺的理论基石是万物外在于人心,故格物应物我兼照,内外俱摄,察之于物理与照之于身心融为一体。(61)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第331页。在他看来,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与禅学的明心之说实无区别。王阳明对《大学》格致做了解释:“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6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9页。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把格物解释为正心。他提出格物的“物”就是“事”,事即意之所在,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格”就是“正”,正其不正,以去恶归正,(63)参见任仕阳、许至、渠彦超:《“宗儒排佛”——罗钦顺佛教观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故所谓“归于正”就是“为善”。(6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7页。他用内在的“心”和“意”笼罩了所有的外物,用对“物”的内在意念性的解释来消除其客观外在性。对他来说,由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格物致知就是正心中之物,致心中良知,所以“无内外之分”。(65)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216页。针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心”“格心”“物者意之用”的观点,罗钦顺认为这与佛家之明心说实无区别:“世顾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绪论,以阴售其明心之说者,是成何等见识邪!佛氏之幸,吾圣门之不幸也。”(66)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5页。他认为“‘格物’既是外向的实践,也是‘致知’的开始与知识的本源”,(67)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117页。所格之物无疑是世界上的一切。罗钦顺尤重视工夫,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才能内外合一,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68)参见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5页。人心作为一物,格物的同时也包含格心,故不能把格物等同于格心。此处罗钦顺并未明确批评王阳明,但无不暗指王阳明的做法必然使格物的工夫完全变为禅宗反省内求的方法,“局于内而遗其外”似禅。禅宗的核心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里的心指的是内心、真心,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觉悟内心的佛性,度己度人,才能到达彼岸。的确,禅宗的“即心即佛”(69)尚荣译注:《坛经》,第105页。与阳明的“心即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阳明将外在普遍之“理”、禅宗将“佛性”纳入人的内心,都认为“心性不二”,从这点来看,罗钦顺所言不无道理。朱子的格物论不仅肯定客观外物的独立价值,还试图探寻外在的格物穷理和内在的道德体证两者之间的津梁,即如何“转识成智”或如何完成“异质的跳跃”。(70)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504页。罗钦顺的格物论基本上遵循了朱子格物论的理路,所穷之理不仅包括“存在之理”,还包括“形构之理”。(71)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79页。牟宗三认为“理”分为“形构之理”与“存在之理”,认为“形构之理”为自然义、描述义、形下义的“所以然之理”,即作为形构原则的理,言依此理可以形成或构成一自然生命之特征,亦可以说依此原则可以抒表出一自然生命之自然征象,此即其所以然之理,亦即当作自然生命看的个体之性,就是指把形下的实然的现象总括起来,以一个理由说明之,归纳普遍化之理,是知识论、见闻之知的万理;“存在之理”则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体论的、推证的、异质异层的,此理不抒表一存在物或事之内容的曲曲折折之征象,而单是抒表一“存在之然”之存在,单是超越地、静态地、形式地说明其存在,不是内在地、形式地说明其征象,故此理亦可曰“实现之理”,即道德实践的德性之知,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
因此,罗钦顺和王阳明只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立场,他们的格物致知虽有差异,但都要求通过格物致知而发明本心固有的“理”,自觉地按照儒家伦理规范去行。二家通过证悟所确立的皆是具有伦理道德内容的本心,在重视日用之功的基础上发明本心,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而禅宗将万法都归结为自心,肯定众生之心即清净佛性,故只能向自己心中求,转迷开悟,以明心作为修行的起点,将现象世界看作心的幻影,把远离幻象世界叫作悟后起修。其修行的目的在于去除执着,显发般若智慧,从而照见诸法实相,最后得到解脱。阳明心学和禅学一样也看到一切都是“心”的作用,但阳明心学以明心作为终点,反过来研究如何用“心”来驾驭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去更好地实现修齐治平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心学和禅学亦判然不同。
结 语
罗钦顺因宗奉程朱理学而持论“心学似禅”,对心学后学具有警醒作用。“从学术史的意义来看,则钦顺的固守宋学立场,客观上既继续推进了程朱理学,又丰富了其时的学术形态。”(72)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289页。但心学与禅学毕竟是不同的思想体统,我们基于历史同情之理解,在揭示罗钦顺“心学似禅”之论确有不能周洽之处的同时,也当顾念其“尊信程朱,培护正统”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