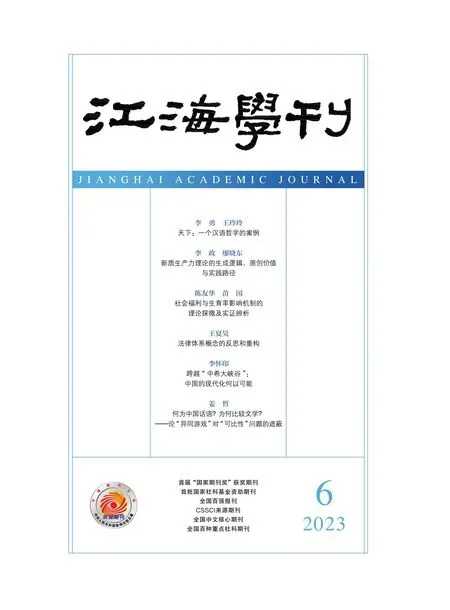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
——以G.A.科恩的意见为线索
2023-02-06李娴静
李娴静
G.A.科恩在《什么的平等?论福利、善和可行能力》一文中曾提出,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实现了一场革命,却错误地描述自己成就的思想家。之所以说是一场革命,是因为森倡导在平等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的关注点应从商品及效用转到个人状况上,他据此提出的可行能力视角在对平等问题的分析上超越了功利主义、福利主义以及罗尔斯的基本善,被科恩称为“对这一主题的当代反思的一大飞跃”。(1)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in Martha Nussbaum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10.与此同时,科恩认为,森用可行能力来描述个人状况是错误的,因为可行能力概念没有穷尽拥有商品之后、产生效用之前的所有个人状态。科恩提出“midfare”(2)国内学者对“midfare”一词有三种译法。龚群将其译为“中介性好”,高景柱将其译为“中间福利”,段忠桥、常春雨将其译为“中间状态”。本文直接使用英文midfare,上述三种译法或有益于读者理解该概念。的概念用以替代可行能力。“我把商品的非效用性效果称为‘midfare’,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处于商品和效用之间的。”(3)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18.具体来讲,midfare是“由商品引起的个人状态构成的一种异质性的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了商品可以为人们所做的三个异质层面的事情:第一,商品赋予人们能力——人们能够用商品做什么的能力;第二,商品促使人们运用这些能力展开有价值的活动,达到可欲求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用商品做了什么;第三,商品直接导致进一步欲求的(不需要人们运用任何能力就享有的)状态,例如,当母亲为婴儿穿上衣服,婴儿不需要运用任何能力就享有保暖状态。在科恩看来,可行能力只是midfare的一部分,因为,森的可行能力概念是具有竞技性特征的主动性的概念。(4)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p.24-25.森曾对科恩的观点直接做出回应,“可行能力从来没有竞技性,尽管科恩显然被我使用的‘可行能力’和‘实现’等词误导了”。(5)Amartya 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Martha Nussbaum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pp.43-44.
关于科恩对可行能力的“意见”,学术界一度有所争论,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从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森的自由观与共和主义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自由与不依赖之间的联系,因而佩蒂特肯定甚至推崇可行能力所展示的自由维度。佩蒂特从决定性偏好(decisive preference)与决定性选择(decisive choice)的角度为森辩护,他认为科恩对可行能力的误解源于他没有厘清偏好(preference)和选择(choice)的区别,简单地概括决定性选择与决定性偏好的区别,即选择的行使与选择的倾向之间的区别,“G.A.科恩错误地认为,森对功能性可行能力的关注来自美好生活的竞技性形象,因为科恩没有看到可行能力需要决定性偏好,而不是决定性选择”。(6)Philip Pettit, “Capability and Freedom: A Defenc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17, 2001, p.17.另一部分学者则赞同科恩的观点,例如段忠桥认为,科恩“指出了森的‘能力平等’存在的缺陷,强调平等主义者还需关注那些与人的能力运用无关的合意状态”。(7)段忠桥:《论科恩的“优势获取平等”主张》,《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段忠桥认为,森将商品为人们做的三类事都归到可行能力名下是错误的,可行能力只归属于第二类(人们实际上用商品做了什么),因此当森“以能力或功能来描述他所关注的对象时,后者却被不必要地收窄了”。(8)段忠桥、常春雨:《G.A.科恩论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哲学动态》2014年第7期。本文将基于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既有研究,对科恩的“可行能力需要用midfare代替”这一判断做分析,从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的概念、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的关系、自由的多层面、可行能力的优势与不足等方面探讨可行能力,进而证明,科恩的意见源于对可行能力的误解,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的概念
1979年,在以人类价值为主题的“坦纳讲座”中,森发表了“什么的平等”之主题演讲。演讲中,森对功利主义的边际效用平等、福利主义的总效用平等、罗尔斯的基本善平等逐一进行了批判。功利主义追求人们的边际效用平等以求在总体上获得最大效用,但是功利主义的平等观漠视人际差异性、漠视分配,因而显得偏狭且不合理。福利主义追求总效用平等,但这种平等观存在漠视利益得失的量值、漠视所涉及人数等问题。把功利主义对功利总和最大化的要求和总效用平等结合起来,也不能弥补其信息基础的狭隘性:它们存在忽视欲望根源或性质、忽视非效用信息的重要性等弊端。罗尔斯的基本善平等超越了功利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平等观,但其不足在于,基本善的设定无法解决跛脚人等弱势群体的问题,忽视了人际差异性。同时,森还指出,“罗尔斯的框架中存在着某种‘拜物教’的因素”。(9)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in Robert E. Goodin &Philip Petti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ress, 1997, p.483.在此基础上,“基本可行能力”(basic capabilities)的概念被提出,森将其定义为“一个人有能力做一些基本的事”。(10)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p.484.例如,人们有充足的营养,有必要的资源可以购买衣服和住宅,可以参与共同体生活等。以基本可行能力平等作为参照标准,可以克服上述三种标准所具有的困难与不足,为道德中涉及平等的方面提供一个更加充分的基础。
基本可行能力与基本善及其效用的区别在于:虽然基本善的清单包括各种权利、自由、机会,以及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但是,基本善不关心这些事物对人有什么程度的影响。效用关心事物对人们有什么影响,但它只关注人们的精神反应。森提出基本可行能力平等,“本质上是罗尔斯方法在非拜物教方向上的扩展”。(11)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pp.484-485.这种扩展的具体表达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关注点,乃是罗尔斯对基本善之关心的自然扩展,即把注意力从有益事物转向有益的事物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12)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p.484.这种转向正是科恩肯定森实现了一场革命的地方。
森对可行能力的反思与推进体现在对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概念的引入与诠释中。在“汉尼普曼讲座”中,森批判了以个人财富来评判个人福利的方法。在森看来,我们不能把个人福利简单地理解为他有多富有,因为财富只是实现个人福利的工具,商品的性质并不会根据拥有它的人的不同特点而改变。例如,自行车的特点之一是它是一种交通工具,这种特点并不会告诉我们,拥有它的人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和一个残疾人,即使各自拥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自行车,他们能用一样的自行车做一样的事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一个人的福利时,我们明显需要转换到‘功能性活动’”,(13)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即一个人可以成功地运用商品做什么。
“功能性活动”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森对可行能力思考的重要推进和深化。“一项功能性活动是一个人的一项成就(achievement):他或她能够做的事情或者能处于的状态。”(14)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7.之所以强调活动和状态,是因为人们把物资转换成个人功能性活动的能力,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因素。例如,一个人的营养状况会受到诸如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新陈代谢率;(2)体型大小;(3)年龄;(4)性别;(5)活动程度;(6)医疗情况;(7)享有医疗服务的机会及运用它们的能力;(8)营养学知识及教育;(9)气候条件。(15)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17.因而,当我们评论一个人过得怎么样的时候,必须关注他实际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他可以成功地做什么或者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功能性活动反映了一个人的活动(doings)和状态(beings)。
在这个阶段,森对功能性活动的界定是:它发生在拥有商品之后,在人们获得效用之前。例如,骑自行车这项功能性活动发生在一个人有一辆自行车之后,在他因骑车获得快乐等效用之前。功能性活动被森视为一个人的状态的一部分,福利(well-being)则是对功能性活动的评测。当功能性活动的含义被解释清晰后,可行能力就有了明确定义:可行能力反映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不同功能性活动的各种组合”。(16)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9.森通过对功能性活动与商品及效用的对比,突出功能性活动在评价个人福利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进而以人们能达到的功能性活动的各种组合诠释可行能力,使得可行能力的内涵更加丰富、清晰,这一诠释是森对可行能力研究的重要进展。
森对可行能力的再次推进体现在1984年以“福利、主体性和自由”为主题的三场演讲中。在演讲中,森分享了他对可行能力的最新研究成果,即“探究一种道德进路,可以从福利和主体性两方面看待人们”。(17)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2, No.4, 1985, p.169.森指出,在评价一个人的福利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他所选择的或业已实现的功能性活动向量,还要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可行能力集上,“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可以被定义为他或她能达到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18)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2, No.4, 1985, pp.200-201.亦即,我们要关注人们享有多少“机会”、享有多少“选择”。在这个时期,森认为可行能力与“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s)(19)在《资源、价值与发展》一书中,森也将可行能力诠释为积极自由,具体可参见Amartya Sen,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310-316。但是,森后期的作品不再强调这种区分,因为他认为积极自由包含了不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的限制,也就是说对消极自由的违背必然是对积极自由的违背(但反过来不成立)。相似,即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的自由。这种以自由定义可行能力的观点,森在1985年以生活水平为主题的“坦纳讲座”上,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与辨析。首先,“一项功能性活动是一项成就,一种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达到这项成就的能力(ability)”。(20)Amartya Sen, et al., ed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6.而跳出“一种”,用普遍的视角来看,可行能力是“有关自由的概念”,是“有关你可能会过上的生活的实质机会”。(21)Amartya Sen, et al., ed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p.36.可行能力涵盖了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并指向人们享有的可以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机会。在《再论不平等》一书中,可行能力有了清晰完整的定义:“可行能力代表了人们可以达到的不同的功能性活动(个人状态和活动)的组合。因此,可行能力是一组功能性活动向量,它反映了一个人过某一种生活或者另一种生活的自由。”(22)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0.自此,可行能力的概念便在森的著作中定型。
从可行能力的提出,到森对可行能力逐步完善的思考与诠释,我们可以明晰,可行能力反映了人们的实质生活状况及实质自由。科恩所提出的“midfare”概念,实质上与森称为“功能性活动”的概念相对应,而并不与“可行能力”概念相对应。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既密切相关又有显著区别,如果把功能性活动比作一个点,那么可行能力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众多点的集合,这个集合彰显了人们可以享有的过上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机会和自由。一言以蔽之:“可行能力进路,从广义的定义上来讲,并不仅仅关心一个人从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束里选择了哪一个功能性活动集合,还会从与自由相关的这样一种合理且丰富的角度来看待功能性活动本身。”(23)Amartya Sen, et al., ed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pp.37-38.从概念上来说,科恩对可行能力的理解,忽视了可行能力在机会与自由层面的指向。
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的关系
科恩对可行能力质疑的核心是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主动性及其导致的“竞技性”:“我所不能接受的是相关的竞技性,这体现在森所说的‘福利的核心特征是达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24)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25.这一部分将从个人福利入手,通过复盘福利的核心特征是可行能力的推演逻辑,来考察科恩的判断是否具有合理性。
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well-being)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涉及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福利?对“well-being”最为直观的理解就是being well,不过,我们需要区分富裕(being well off)和享有福利(being well or having well-being)两种不同的理念。富裕,指向的是“一个人对外在事物的控制力”,(25)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195.例如,她有多富有,她能买什么物品或服务等;状态良好,指向的是“她所达到的内在于她的东西”,(26)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195.例如她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她成功地做着什么事情或者成功地处于什么状态等。说一个人享有福利,指向的是一个人运用外物达到的内在于自身的东西。
我们在寻找通往福利的路径时,往往会遇到两种歧途,一种是功利主义路径,即完全基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从主观的视角看待福利;另一种是纯粹客观的视角,例如斯坎伦所指出的,“客观的标准,是指独立于一个人的品味和兴趣的,为评价一个人的福利提供基础的标准”。(27)Thomas Scanlon, “Preference and Urgenc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2, No.19, 1975, p.658. 斯坎伦在《选择与迫切需要》(“Preference and Urgency”)一文中,通过迫切需要与效用之间的对比,证明了道德判断中的福利标准之客观性。亦即,评判一个人的福利水平的客观标准 “与一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无关。”森认为,纯粹主观的及不考虑个人差异的完全客观的标准都是不可取的。富裕与享有福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际差异性使得富裕与享有福利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森主张,我们应在不失客观性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特点作为测评的参数,那么,功能性活动就是个人福利最直观的相关项——人们的生活由一系列相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组成,功能性活动展现了一个人所达到的内在于他的享有福利的状态,人们在福利方面的成就可以用“功能性活动的向量”来表示。不仅是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也与个人福利密切相关。
例如,有两个人享有共同的功能性活动向量:挨饿。A挨饿是因为他很穷,B挨饿是因为他在斋戒。A和B的区别在于,B有选择不挨饿的自由,但是A没有。由此,我们必须区分“做某事”与“自由地做某事”这两种情况,可行能力正是在这一区分上凸显了机会与选择的重要性。在测评人们的福利水平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已经被实现的功能性活动,还要注重考量实现福利的自由。关注人们可选择的机会与自由,才能更好地分析已经实现的功能性活动——它们是人们从原始功能性活动集合里通过选择实现的。因而,在森看来,一个人所能达成的功能性活动——他能做什么活动或者处于什么状态——是一个人的福利的首要表现特征。把功能性活动按照一定标准排序,看一个人达到的功能性活动在排序中的位置,是个人福利的第二个表现。而个人福利的核心特征是“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ability)”。(28)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200.在这里,森用“ability”区分于“capability”,“capability”在森的著作中特指可行能力,亦即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多种功能性活动的各种组合,其本质是选择的机会或者说实质自由。“ability”表示才华、能力,这种能力指向将商品转化为功能性活动的能力。在森看来,把物资转换成功能性活动的人际相异性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把食物转换成营养良好这种功能性活动会受到的九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有所论述)。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对男性和女性营养状况的对比往往采用测量食物摄入量的方法,但食物摄入量很难反映个人福利,而且这种方法还会帮助掩盖这些贫困国家中妇女所受到的剥夺。这些政策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可行能力的忽视。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科恩的“我所不能接受的是相关的竞技性,这体现在森所说的‘福利的核心特征是达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29)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25.这一判断至少有四点值得推敲。首先,科恩如何定义福利?如果依循森的划分,一个人对外在事物的控制力(例如他有多富有等),较为容易与“竞技性”的能力相关联,但是一个人运用外物达到的内在于他的东西,与人际差异性直接相关,而非竞技性。每个人想要的生活是不同的,人们要达到的目的不同,所选择的功能性活动束不同,起跑线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谈竞技性。科恩将森所作出的“福利的核心特征是达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之判断作为可行能力具有竞技性的表现,其逻辑让我们推测出他对福利的理解应当与森对福利的定义不一致。其次,科恩所说的“竞技性”批评指向的是可行能力(capability),而他引用森的原文所显示的概念是能力(ability),这里科恩要么混淆了这两个概念,要么没有将两个概念的关系厘清。再次,森突出强调,人们把物资转换成个人功能性活动的能力(ability),会受到个人、社会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科恩将森所强调的人际相异性理解为竞技性,忽略了社会和自然等影响能力的因素,这种理解“能力”的方式颇为武断,把“能力”推及(涉及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就更显片面。最后,笔者认为,科恩并没有理解森所表达的可行能力与福利的关系。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个人,均身患绝症,一个人因治疗费用超出其可承受范围而放弃去医院治疗,另一个人完全可以承担医疗费用,但因他信仰巫术而不去医院治疗。最终,两人呈现出的midfare是一样的:都处于身患绝症且未得到医院治疗的状态。但是,他们所享有的可行能力却完全不同。
那么,可行能力与福利的关系是什么?个人福利与可行能力相关,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如果说已经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组成了个人福利,那么实现这些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亦即人们在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中选择的自由,将构成人们拥有各种福利的实质机会,亦即福利自由。“功能性活动是个体福利的构成要素,而可行能力反映了一个人可获得个体福利的自由度。”(30)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49.森指出,这种福利自由与伦理分析和政治分析直接相关。例如,在有关社会状态的良善程度的描述中,人们各自享有的福利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要素,福利自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东西,从这个视角看,“一个良好的社会同样是一个自由的社会”。(31)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41.个人福利与可行能力相关的第二个层面是业已实现的个人福利本身取决于实现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这个层面又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能够做出选择,这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在重大的选择项中真正做出选择的生活可以被视为是更富足的生活”。(32)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41.因而,对个人福利而言,有一些可行能力有直接的贡献。第二,当个体福利并不取决于可选择的自由的程度时,可行能力所扮演的角色是工具性的,可行能力集合提供了各种功能性活动向量的信息,功能性活动是构成个人福利的要素,因而可行能力对于个人福利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行能力不仅与可实现的个体福利的自由有关,还会影响到已被实现的个体福利水平。功能性活动是一个点,而可行能力是这些点的集合,“可行能力集”被森定义为“个体可享受的、追求她自身福利的全面自由”。(33)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150.在进行人际比较时,可行能力关注的信息焦点已经从商品或者基本善等手段域转向了与人们的生活状况直接相关的功能性活动域,并且,它注重人们从不同的功能性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
通过对以实质自由看待可行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对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的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森的可行能力,并不能(如科恩所说的那样)被视为midfare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仅仅从midfare的角度看待可行能力,“我们可能就要如同为挨饿的穷人担忧那样而为斋戒的富人担忧”,(34)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45.实际上,虽然挨饿的穷人和斋戒的富人都享有挨饿的功能性活动,但是其背后,他们可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却是完全不同的。从实质自由的角度理解可行能力,我们才能看到享有同样功能性活动的人们的异同之处。也正是因为自由的视角,可行能力在人际比较与社会分析中才具有重要性、全面性与优越性。
自由的多层面
Midfare的最初形式是“获取优势”(access to advantage),(35)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28.虽然“优势”这个概念在科恩的论述中有点模棱两可,但是“获取”这个概念是明确针对森的可行能力(之不足)而提出的。“我使用‘获取’是指,一个人只有当他既有机会(opportunity)又有才能(capacity)获得他没有的某物时所享有的对它的获取……即使‘可行能力’(capability)在一般意义上不同于才能,它也仍不包含‘机会’(一个没有机会去游泳的人也许有能力游泳),由此可以推断,我所说的获取比森所说的可行能力要求更高,因而我们对于平等的解读也是不同的。”(36)G. A. 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虽然科恩在同一篇文章里指出,森的可行能力有时候也包含着机会,但科恩认为,可行能力与机会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森对可行能力的定义和诠释都是摇摆不定的。关于可行能力的定义、提出背景、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以及机会在可行能力概念中的“角色”,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详细讨论,科恩有关“可行能力不包含机会”,以及机会与可行能力之间的关系模糊等判断,源于他对可行能力的错误理解。
科恩提出并强调“获取”(access)不同于可行能力的重点在于他想向人们阐明,一个人实际拥有的东西(无论是否运用能力而得到)都是他获取的:“这种对获取的特殊解释的动机是,平等主义者必须考虑一个人的某些状态,这些状态既不是由这个人造成的,他也没有能力造成,这些状态属于midfare的第(3)类……”(37)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28.笔者认为,科恩有关“应以midfare代替可行能力”的论断,源于他把可行能力理解为一个完全主动性(38)科恩认为,森所说的“人们从商品中得到的”这句话里的“get out of”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取出”,从商品中得到某种东西代表了一种可行能力的运用;另一种是“收到”,从商品中得到某种东西不需要可行能力。在科恩看来,只有第一种是与可行能力相关的。的概念,“森打算让可行能力具有一种竞技性的特征(athletic character)。他把可行能力与马克思有关一个人通过能动性实现他的潜能的思想相联系……”(39)G.A. Cohen,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p.24.基于对可行能力的这种能动性的理解,科恩认为,可行能力忽略了商品可以直接导致一种合意状态的情况,例如,杀死害虫的杀虫剂可以让人们不运用任何能力,就享有害虫被杀死的状态。本文第三部分将以自由的多层面为主题,从自由的视角对可行能力概念进行再剖析,试图证明,“可行能力是完全主动性的”是一个错误命题。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明晰,森所讨论的以自由为本质的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以及个人福利自由直接相关。然而,人们还会追求个人福利之外的其他价值或者目标,譬如说,一个人的目标是祖国独立,这样的目标就不能仅仅从这些成就能为他个人带来多少福利来测评,还应该从这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评价。这就涉及主体性成就(agency achievement),“主体性成就是指一个人有理由追求的目标或者价值的实现,不管它们是否与她的个人福利相关”。(40)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56.森把主体性成就分为“已实现的主体性成就”(realized agency success)和“参与性的主体性成就”(instrumental agency success)。例如,一个人的价值目标包括祖国独立或者消除饥荒,这些目标一旦实现,他的主体性成就就得以实现,不需要考虑个人在实现这些目标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已实现的主体性成就”。而强调个体在实现价值目标中的参与性的是“参与性的主体性成就”。与主体性成就相对应的是主体性自由,我们首先要梳理的是,福利自由与主体性自由的关系。
在森看来,福利自由“聚焦于一个人拥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向量以及享有相应的福利成果的可行能力”。(41)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203.这种自由有别于“主体性自由”,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指的是这个人“追求他/她认为重要的任何目标或价值的自由”。(42)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203.也就是说,主体性自由更加具有普遍性,它并不受“追求什么目的”(例如福利)的限制。当然,对目标的认真评估对主体性自由来说很重要。例如,A把不会游泳的B推进河里造成B溺水而死。在这个例子中,A作为一个有责任的道德的主体是非常失败的。(43)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219.因而,森所说的具有主体性的人首先得是负责任的道德主体。从这个层面上讲(主体性的重要性是对那些可以负得起责任的主体来说的),对于一些年幼的孩童和精神上存在疾病的人士来说,主体性方面的重要性就弱很多,评估这类人群时,他们的福利成就更值得被予以关注。
对主体性自由而言,开放的条件性(open conditionality)是其特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决定去追求福利,那么对这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评估就要包含他的福利自由。但是,这种包含并不是一贯的、绝对的。例如,森给出这样一个情景假设:在一个惬意美好的春天,A在河边享用三明治,此时,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溺水了,因为溺水的人与A有数百英里的距离,所以A不能做任何事情去帮助他。又假设,这个不会游泳的人就在A面前溺水,那么此时,A的主体性自由就提升了,A可以选择扔掉三明治,冒着生命危险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去把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救上岸。如果A这样选择并且这样行动,那么他的个人福利(综合考虑)非常有可能在减少。同时,他的福利自由也在减少,因为A不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有在河边吃三明治的机会。这个情景假设告诉我们,在主体性自由(可选择的机会)增多时,福利自由有可能降低。因而,虽然主体性自由的范围比福利自由广泛,但是主体性自由并不一定能够把福利自由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
主体性和个人福利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对个人福利的追求是主体性自由的一个方面,同时,作为能动的个体,如果没有达成非福利目标会使他感到受挫,他的个人福利也会因此降低。因而我们在分析主体性和个人福利时,既要注意到二者的差异,也要注意到二者的联系。主体性方面和个人福利方面谁更突出一些,需要依情况而定。“福利在评价一个人的个人优势时是重要的层面,而主体性在评价一个人在他的善观念下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是重要的层面。”(44)Amartya Sen,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p.206.也就是说,从主体性层面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决策者和行动者;而从福利层面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受益者(与个人利益和个人优势相关的受益者)。有时候我们必须在相互冲突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但是选择一项并不代表着否定另一项的意义。例如,要生活美满还是事业有成?无论选择哪一项,该选项都不会使另一个选项变得不重要。以此为例,我们很容易理解,不论我们是否将主体性目标中的非福利目标看得比个人福利更加重要,都不影响个人福利的重要性。
总之,可行能力进路要求我们从福利和主体性两方面看待人们,即使我们分析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社会不平等)时,首要关注点在个人福利及个人福利自由上,我们依然要关注人们的主体性,因为人们对福利自由的运用依赖于影响他们做出实际选择的主体性目标。
明确了福利自由与主体性自由的关系,我们再来辨析一下主体性自由的两个层面,以便更清楚地判断(科恩所认为的)“可行能力是完全主动性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森把主体性自由分为“作为控制的自由”(freedom as control)和“有效自由”(effective freedom)两个层面。“有效自由”是指一个人达成他选择的结果的自由。有效自由并不关注机制和程序上的控制,同时,一个人的选择是如何执行或者如何实施,对有效自由并没有影响。有效自由具有的意义之一是它可以注意到反事实选择——现实中并未实现但如果一个人可以控制结果的话他意愿做出的选择就是反事实选择。与有效自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控制的自由。控制是指程序的控制(procedural control),一个人是否成功地达成他做出的选择对自由的程序控制这一方面没有影响。森认为,当代政治哲学对自由的关注多是关注其程序控制的一面,并且作为控制的自由往往会和基于限制的进路(在一些事物上不要干涉其他人的控制性自由)相结合。
为了说明作为控制的自由和有效自由的区别,森在以“福利、主体性和自由”为主题的“杜威讲座”上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一个朋友在一场事故中受伤并且失去了意识,医生说有A、B两个治疗方案,两个方案的有效性是一样的,只是A方案会让人少受一点罪。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朋友如果处于清醒状态时,他的选择会是方案B。因为治疗方案A涉及动物实验,朋友完全不同意在活着的动物身上做实验。如果为朋友选择治疗方案B,我们选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他的福利(A方案更有利于朋友的个人福利),而是因为他的自由(他达成他选择的结果的自由),这里体现的就是有效自由的一面。由此可见,我们如果只从控制的维度看待自由,会忽视当人们自己不能控制一些情况时对自由的要求。
又如警察维持街道秩序的例子,“警察在街上防止犯罪的行动可能对我的自由有好处,因为我不想被抢劫或粗暴对待,但在这里,控制权不是由我行使,而是由警察行使”。(45)Amartya Sen, “Liberty and Social Choi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0, No.1, 1983, p.19.我们都不想在街上遇到抢劫,这时我们寻求的是有效自由——达成我们选择结果的自由。由谁来执行控制与达成我们选择的结果相比,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有效自由和作为控制的自由这两个层面对应着森对机会层面的自由与过程层面的自由(不受干扰地自由地选择)(46)在《理性与自由》中,森认为,自由包含有两个不同的特征:“(1)它有助于我们获取在我们各自的私人领域,例如个人生活中,想要选择去获取的东西(这是自由的机会层面),(2)它让我们得以直接掌握私人领域中的各种选择,无论我们是否会去实施(这是自由的过程层面)。”的区分。可行能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人们已经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的测评以及人们在不同的功能性活动之间选择的机会的测评,而其劣势是对自由的过程层面指导较弱,“可行能力的理念虽然在测评自由的机会层面具有可观的优势,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完全处理自由的过程层面,由于可行能力是个人优势的测度标尺,因而它在过程平等(公平)层面缺乏对人们的充足的指导”。(47)Amartya Sen, “Human Rights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6, No.2, 2005, pp.155-156.当我们在估价机会的时候,我们应关注人们的可行能力,而自由的机会层面不关注程序上的控制,亦即,可行能力并不仅仅是主动性的,他人的选择、公众的行动、公共政策的影响都会使人们的可行能力得到增强或削弱。因此,良好的社会安排——制度设计、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对个人可行能力的大小有着直接影响。
基于自由视角的分析,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森对科恩观点的回应,“以一个人所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可以得到他人选择的巨大帮助,如果仅依据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来考虑成就将是错误的”。(48)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44.如果我们理解了“有效自由”(与“已实现的主体性成就”相对应)和“作为控制的自由”(与“参与性的主体性成就”相对应)这两个自由层面,理解了福利自由与主体性自由的关系,就会明白并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即“只是当我们亲自动手去消灭疟原虫的时候,才能让我们具有过一种免于疟疾的生活的可行能力”。(49)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p.45-46.
小结与评价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结合学术界的相关讨论,尝试对可行能力的优势与不足作出评价,继而对文章的主要论点进行总结。
森通过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维度,来定义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关注的焦点既不限于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也不限于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它集中关注的是一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的机会(无论他是否会选择使用该机会)。亦即,可行能力反映了一个人在各种生活可能性之间的选择自由。
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可行能力对各种价值要素均加以考虑,既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福利的关注,也能满足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和行动自由的关切,还能保持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对个人自由权及对实质自由所需要的资源的集中注意。“这种方法所专注的信息,可以深刻地影响对于社会及社会制度的评价,而这正是可行能力方法的主要贡献。”(50)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3.可行能力作为一种评价方法,在适用范围的广度和判断敏感度上都具有优越性。同时,可行能力理论也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例如可行能力的测量与评价是非常不易的工作。
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在针对森的《再论不平等》所写的书评里,批评了可行能力的不可操作性。(51)Robert Sugden, “ Welfar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 Review of Inequality Reexamined by Amartya Se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1, No.4, 1993, pp.1947-1962.他认为,由于功能性活动的无限宽泛性以及可行能力方法对自由、机会的评价信息的宽泛性,我们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运用可行能力对社会生活中的事务进行评价。因为功能性活动清单并不是一个“闭合”的存在,按照可行能力方法,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参考的要素太多、太不固定,以至于我们对一个人的整体优势及劣势根本无法做出判断。伍尔夫·盖德尔(Wulf Gaertner)在对森的《可行能力与福祉》一文的评价中,提出有关可行能力的可测性问题:“像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或成年人的识字率这样的基本功能性活动是相对容易测量的,甚至可以根据一个基数尺度来测量。但是诸如获得自尊、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工作中感到快乐这样复杂的功能性活动应该如何测量呢?”(52)Wulf Gaertner,“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Martha Nussbaum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p.63.笔者认为,盖德尔所提出的问题切中了可行能力理论的要害。虽然可行能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会因信息获取的限制而对现实有所妥协,但可行能力并不是乌托邦式的设计,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依据可行能力理论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53)这份人类发展指数参见: http://hdr.undp.org /en.现已成为一种标准的关于发展的评价方法。人类发展指数的制定,正是可行能力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应用的事实证明。但是,在依据可行能力拟定全球人类发展的测评指标时,被集中关注的是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就业率等人类基本可行能力,这些内容相对容易测评。然而,人们的可行能力不仅包括充足的营养、健康的体魄,还包括生活幸福、有自尊地生活、体面地参与社区活动等。各种更加高级、更加综合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应该如何测量?
森曾提出,当我们测度可行能力的时候,有三种资料来源:市场所获得的资料、调查问卷的统计、对个人状态的非市场的观测。对个人状态的非市场的观测对于可行能力的测评十分重要,但在具体测度中会受到信息来源不充分的限制,在“汉尼普曼讲座”上,森对测评可行能力的数据获取方面给出的回答是,“我恐怕没有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神奇的办法,但是不管我们在实践中使用什么折中方案,首先要意识到的是我们对一种满意的解决方式的需求”。(54)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32.数年后,森对可行能力路径的思考日臻成熟,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克服其在实际评估中面临的数据获取的困难,“即使是在实际应用中接受了获取数据的有限性并迫使我们无法全面描述可行能力集,也要对眼前的数据保持一种基本的分析动机并将其视为在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实践性妥协,这一点很重要”。(55)Amarty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p.53.科恩没有讨论midfare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根据科恩对midfare的相关讨论,midfare并不具备弥补或化解可行能力测度困难的能力。
综上所述,科恩提出的midfare概念,与森提出的功能性活动概念相对应,而不是与可行能力概念相对应;不仅是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也与个人福利密切相关;只有从实质自由的角度理解可行能力,才能看到享有相同的功能性活动的人们之间存在的真实差距;可行能力并不是一个完全主动性的、具有竞技特征的概念,他人的选择、公众的行动、公共政策等都会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因此,科恩针对可行能力所提出的意见,源于他对可行能力的误解。可行能力具有广泛的信息基础,这种优势也导致了其测量与评价的高难度。Midfare不具备可行能力所具有的优势,也弥补不了可行能力理论所具有的不足,以midfare代替可行能力的提议,在理论证成的层面上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