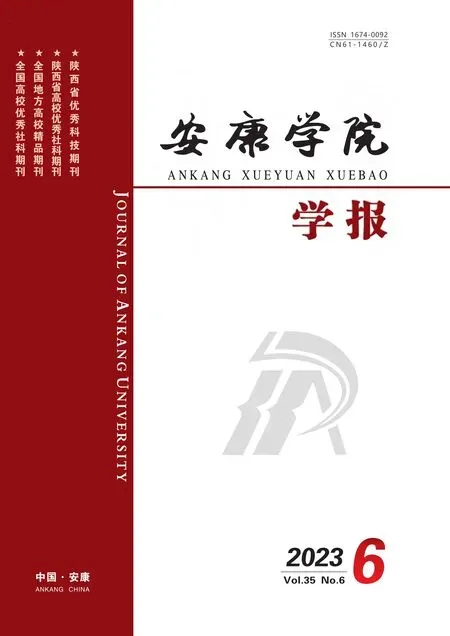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
2023-02-06韩国良
韩国良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在中国文论史上,王国维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游戏说”的提出,二是“境界说”的发明。“游戏说”的提出主要是西方观点的照搬,而“境界说”的发明则深深扎根于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王国维之所以称“境界”而不称“形象”,称“不隔”而不称“直观”,称“真”称“自然”称“情兴”称“赤子”而不称“客观”称“模仿”称“再现”称“形似”,可以说处处都与“言志说”主导下的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质密切相联系。
对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前人已有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但是其侧重点一般都放在中国文论的现代化上,也即放在“境界”与“形象”的统一性上,认为王国维以西方美学发明中国文学,大大凸显了中国文学的可感特征,开拓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视野,提升了中国文论的理论层次,可是在王国维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改造方面,关注却是远远不够的。王国维的成功并不仅表现在对异域文化的借鉴上,也表现在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上。可感乃审美的基本属性,也是中西文学的共同特征,可是由于中西文学对“言志”“摹仿”的不同侧重,也使它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形象直观”只是可感不隔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与叙事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向以抒情言志见长,因此它的可感特征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果一味强调“形象直观”在实现可感性上的唯一性,那实际上就等于是一种“形象霸权”或“形象专政”。而王国维之所以称“境界”称“不隔”称“真”称“自然”称“情兴”称“赤子”,而避免称“形象”称“直观”称“再现”称“形似”,可以说正是对以主客分离为背景,以认识论思想为基础的西方“形象霸权”理论的大胆突破。换言之,也即是其“境界说”的本根还是深植于以天人合一为背景,以心性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国“童心崇拜”泥土中的。所谓“童心崇拜”,一言以蔽之也即崇尚以诚感人,以真感人,它与中国文学的“言志”传统高度相一致。作家看重的乃是触物之切,感物之真,体物之诚,写物之挚,诸境众象都弥漫着他的血气情绪,这样的作品才叫有生气。它与西人所反复强调的“形象直观”并非一回事。由王国维的成就不难看出:欲求开新,必先固本,坚守中国本土立场,尊重华夏民族精神,这实为进行一切学术创新的重要保障。
一、对“境界”“不隔”概念的选择
正如学者所说:“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其说是‘叔本华美学思想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倒不如说是康、叔美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晶。”[1]“(王国维)‘不隔’的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美学思想中强调艺术直观特性,及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是总结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产物。”[2]487“(王国维)虽然穿着西学的鞋子,但在思想上其实是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3]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深受西方“形象直观”说的启发,但却并未照搬西方“形象直观”说的概念,而是巧妙选择了更切合中国传统的“境界”“不隔”二语,来揭示“形象”“直观”所要表达的美学精神。也就是说“境界”“不隔”虽然与“形象”“直观”的所指对象颇有差异,但是它们的本质精神却是完全相通的,它们所强调的显然都是艺术创作的可感性问题。再进一步说,“形象直观说”所面对的乃西方以“模仿说”为指导的叙事文学,而“境界不隔说”所面对的乃中国以“言志说”为指导的抒情文学,两种文学虽都要求高度可感,但其可感性的表现却颇有不同:前者侧重客观形象,后者侧重主观境象。既是如此,则它们所适宜的概念术语也自应有异。所以王国维的做法正是对中国文学特殊性的兼顾。它充分说明王国维的“境界说”虽然借鉴了西方的理论,但他却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
关于“境界”也即“意境”的形象学意义,有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李泽厚说:“艺术最基本的单位是形象,‘意境’的基础首先就是‘形象’。要诗、画有‘意境’,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意境’必须通过‘形象’出现。”[4]张文勋说:“所谓‘境界’,就是作家借助于典型化的方法,在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5]张少康说:“意境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2]483但是对于这种艺术形象的特殊性,我国学者似并未给予特别重视,以致直到目前为止,也还有不少学者仍把王国维“境界”“意境”概念的具体所指,与西方的形象化观念完全等同起来。如:“王国维的诗学基本与传统诗学没什么关系,他是将源于西洋诗学的新观念植入了传统名词中,或者说顺手拿几个耳熟能详的本土名词来表达他受西学启迪形成的艺术观念。”[6]或又谓:“把形象看作诗歌本体的观点并不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共识,而是近代西方美学的产物。从20世纪初年,准确地说,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这种观念才输入到中国,并逐渐占据了权威和统治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形象本体’论充斥着中国各种各样的理论著作和文学教科书,甚至连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毛泽东也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任何一种理论话语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体制和知识实践,西方的‘形象本体论’也不例外,它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而是一种与复杂的历史关系相纠缠的权力话语。”[7]161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王国维的成就,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王国维以“境界”(有时也用“意境”)代替西方的“形象”,完全考虑到了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文学由于以抒情言志为主,所以它并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取胜,也不以人物性格的典型鲜明见长,它的可感性主要是由那些细碎零散的诗歌意象,诸如人生片段、生活细节与自然景象等来体现的。这样的诗歌意象所组成的诗歌群象,往往都带有十分浓厚的情绪化特征,而其形似性、可视性、完形性却并不鲜明。也正基于此,只能将其视为心物交融的艺术境象或艺术情境,将其称为偏重人物、偏重客观的艺术形象就颇嫌生硬。也就是说较之“形象”一词,“境”字于中国诗文显然更相宜。王国维之所以将其名为“境界”“意境”而不名为“形象”,其最根本的缘由也正在此。
与“境界”“意境”之称相联系,王国维对中国文学的尊重还表现在对“隔不隔”之说的提出上。通览王国维的现有论著不难发现,在《人间词话》前他对文学可感性的形容都是用“观”或“直观”一词来表达的,如其《〈人间词话乙稿〉序》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8]24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说:“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9]《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说:“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而无概念杂乎其间”“美术上之所表者,……在在得直观之,如建筑、雕刻、图书、音乐等,皆呈于吾人之耳目者”“诗歌(并戏剧小说言之)一道,虽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与否。”[10]但是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经过再三思考,最终还是放弃了“直观”而改用“不隔”。
关于这一点,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明就是“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它的原文本作“语语可以直观,便是不隔”[11]。“语语都在目前”是个笼统的说法,它的实际意思乃是语语都可直觉。如果一定要紧扣字眼,把“都在目前”理解为所写境象都是视角境象,这是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如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说“大家之作”有三大特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12]14。“如在目前”显然是将此三者都包括在内的。而“直观”一词就不同了,由于它是个外来词,人们还未来得及将其泛化,所以它的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还是统一的。西方学者所以喜用这一词汇,这与他们的摹仿学说、叙事传统是有密切联系的。而中国文学乃抒情文学,它的可感性乃体现在一系列意象上,体现在可视性并不是那么强烈的艺术境象,也即艺术情境上,因此“直观”一词与此显然不相合。可以说艺术境象一定是可感的,可以直觉的,但是并不能说一定是可直观的,所以两相对照,将“直观”改为“不隔”显然更准确。因为顾名思义,所谓“不隔”乃包括各个方面,眼耳鼻舌身心各种器官都涵盖在内。以这一词汇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可感性特征,显然是更为恰当的。
然而有不少学者似并未看到这一点,他们仍将“不隔”与“直观”等同起来,如云:“‘不隔’说和西方的‘形象’概念,坚持的是同一种视觉优先性,或用米切尔的话说,一种‘图画的专政’”[7]149。“‘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在原稿中本为‘语语可以直观,便是不隔’。这一处改动告诉我们,王国维提出‘隔’与‘不隔’,尽管采用了陌生的说法,却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就本于叔本华的‘直观说’。所谓‘不隔’就是‘可以直观’;所谓‘隔’就是不能直观。更重要的是,它透露给我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视作‘意境’(境界)本质的‘能观’,就直接来源于叔本华所谓的‘直观’。”[7]67-68十分明显,如果采用这样的观点,那王国维“不隔”说的创新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王国维为适应本土文学所付的努力也几乎全要被抹杀了。以这样的态度看待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这对深入认识他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一定会产生不利影响的。
二、对实现“不隔”途径的确立
中国文学乃言志的而非摹仿的,乃抒情的而非叙事的。与此相应,其形成“不隔”的途径也自应有别。西方文学侧重客观的形似,形象的逼真,而中国文学则侧重主观的真诚,境象的情化。古人每每说“不诚无物”[13]、“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4],可以说把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示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如此,中国文艺也同样如此。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曰:“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15]《文心雕龙·情采》曰:“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16]538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尝读相如、蔡邕文,了无所动于心。屈子则渊源理窟,与《风》《雅》同其精蕴。陶公、杜公、韩公亦然。可见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诚身、修辞,非有二道。试观杜公,凡赠寄之作,无不情真意挚,至今读之,犹为感之。无他,诚焉耳。”[17]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序》曰:“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18]王国维对诗文“境界”的可感不隔,也同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如上所引,其《人间词话》在“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之后紧接着说:“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12]14。“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正是就作家创作对审美对象的感受真切,至诚无伪讲的。类似的表述如:“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2]4-5“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12]13-15。类似的论述还见于他的《文学小言》:“‘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屈子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感,殆与言自己之所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也”,“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8]24-25。像这样不厌其烦,反复阐述情感之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这与我国的“言志”传统显然是高度相契合的。
对于王国维的“隔”与“不隔”形成的原因,前人向有三种认识。一以朱光潜为代表,如其《诗论》曰:“以我们看,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面见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凌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显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19]48。二以叶朗为代表,如其《中国美学史大纲》曰:“从王国维自己的话来看,‘隔’与‘不隔’的区别,并不是从意象与情趣的关系上见出,而是从语言与意象的关系上见出。作家所用的语言能把作家头脑中的意象(‘胸中之竹’)充分、完美地传达出来,并能在读者头脑中直接引出鲜明生动的意象,如‘池塘生春草’,就是不隔。作家所用的语言不能充分、完美地传达作家头脑中的意象,也不能在读者头脑中直接引出鲜明生动的意象,如‘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便是隔”[20]。三以叶嘉莹为代表,如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曰:“静安先生所提的‘隔’与‘不隔’之说,其实原来就是他在批评之实践中,以‘境界说’为标准来欣赏衡量作品时所得的印象和结论。如果在一篇作品中,作者果然有真切之感受,且能作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致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不隔’。反之,如果作者根本没有真切之感受,或者虽有真切之感受但不能予以真切之表达,而只是因袭陈言或雕饰造作,使读者不能获致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隔’”[21]。仔细对比以上三家的看法,虽然说前两种看法也不算错,但是由于他们对王国维所说的“所见者真,所知者深”都强调不够,所以相比而言,还是要以叶嘉莹之说更周延。
当然,对于“真”的强调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西方文化对“真”也很重视。不过,两相对照,还是各有偏重的。具体一点说,西方之“真”主要指客观事物的真理、真相、真实,中国之“真”主要指主观情感的真切、真诚、真挚。王国维的阐述显然与中国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由“诗言志”出发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如王夫之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22],对此昭示得就极清晰。对于王国维之“真”的情感蕴涵,有不少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陈洪曰:“‘境界’的要义在‘真’。这个‘真’并非客观事物的真象、本质,而是精神、心理上的真切感受、体认。”[23]马正平曰:“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真’,并不是艺术的‘真实’‘真实性’问题,而是讲的是一种‘真挚’和‘真切’的感受、感觉。”[24]这样的见解对准确把握王国维“境界说”的民族特色显然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三、对“自然”“情兴”范畴的肯认
受传统文化与“诗言志”观念的影响,王国维把诗文创作的可感不隔,最终还是落实在了人的内心情感的真切深挚上。那么,在什么情景下产生的情感才算真切深挚呢?有关这一点王国维也同样呈示得很明确。具体说来,也就是只有那不假思索,倏然而生,发自肺腑,难以遏止的“自然情兴”才是最真挚的。
首先来看王国维对“自然”的强调。其《人间词话》曰:“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12]20“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2]13“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村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12]22“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12]14这样的思想在《宋元戏曲考》中也有体现,如该书《元剧之文章》曰:“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25]160。《元南戏之文章》曰:“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25]183该书《余论》评汤显祖之不足曰:“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然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25]192
基于对“自然”之情、“自然”之语的高度肯认,王国维对那情由中出、不假思索的乘“兴”之作特别青睐。这在其相关论著里展现得也同样很明白。如《人间词话》曰:“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今不如古,……须伫兴而成故也”,“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12]18-20。“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12]23尤其是在《宋元戏曲考》之“元剧之文章”一节里,王国维对“自然”与“情兴”的关系更作了直接宣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25]160-161。
十分明显,在王国维看来那些不假思索的乘“兴”之作,乃触物起情,情起文生,物到情到,情到文到,所以只有它们才是最自然的,也只有它们才能切实做到不计善恶,不计美丑,情由心出,发于肺腑,表达出最深挚、最真诚的切身感受。由于这样的作品字里行间、各个意象都弥漫着作家的血气情绪,所以也只有它们才称得上真正的可感、真正的不隔,使人如临其境,如历其情,从而在内心产生最强烈、最持久的共鸣。
王国维对“自然情兴”的高度肯认,也同样是对中华文化悠久传统的继承。虽然“自然”概念乃道家首倡,但其实儒佛二家对它也同样很喜爱,尤其是在儒释道合一的魏晋之后。儒家常说“天理自然”,佛家常说“万法自然”,都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尊崇。既然提倡“自然”,也必然钟爱“情兴”,因为“情兴”本来就是“自然”在情感领域中的展现。那么,在古代文论里我国学者会那么热衷咏歌“自然”,褒赞“情兴”也就毫不足怪了。前者如阮籍《乐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26],《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65,李德裕《文章论》:“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27],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28]963,谢榛《四溟诗话》:“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29]。后者如孙绰《兰亭诗序》:“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30]1808,《颜氏家训·文章》:“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31],李白《江上吟》:“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32],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也哉?天也,斯谓之兴”[28]817,袁黄《诗赋》:“感事触情,缘情生境,物类易陈,衷肠莫罄,可以起愚顽,可以发聪听,飘然若羚羊之挂角,悠然若天马之行径,寻之无踪,斯谓之兴”[33]。
不难看出,我国古人对“自然情兴”确乎非常之陶醉,他们所说的“情兴”其侧重点也确实在作家情感的酣畅淋漓,率然而出,无所拘忌,不可遏止上。贾岛《二南密旨》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34]可以说将“兴”的意义揭示的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尽管古人对“情兴”极为重视,酣畅淋漓的“情兴”也一定是真诚的,发自肺腑,充满血气,可感不隔的,但是古人对这种可感不隔的特性却罕有论及,好像它完全是自明的似的。也正缘此,王国维把诗文的可感不隔与作家的“自然情兴”联系在一起,这在理论上也同样是一巨大突破。由这一突破可再次看出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现代化,在王国维的思想体系里实是高度相融合的。否定其中任何一方,对王国维“境界说”的认识都将是不全面的。
四、对“赤子之心”的揄扬强调
王国维对“赤子之心”的揄扬强调与他的真切不隔思想也密切相关。依照王国维的逻辑,文学创作要做到可感不隔,那就必须有真切的感受、真切的表达,而要实现感受、表达的真切,顺从自然,乘兴而作,不假计虑,言由中出,显然乃是其最佳选择。而若想做到自然、乘兴,就必须有一个清净无染的心灵。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受到世俗社会的是非善恶、功名利禄的太多影响,那就好比一面明亮清洁的镜子布满灰尘一样,它对外物的映照就一定不会再那么清晰,那么明了了。所以从这一角度讲,保持内心的清净,对于文学创作的真切不隔来说也是极重要的,甚至把它视为基础也不为过。王国维之所以特崇“赤子之心”也正是从这一维度考虑的。
对于“赤子”的揄扬强调,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反映,但是相对来讲,远没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展现得那样凸出,无论在儒家或道家思想中都是如此。《老子》20 章曰:“我独泊兮未兆,若婴儿之未孩”[35]47,28章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35]74,55章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35]145。《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6]556,同书《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年龄稍大),无不知敬其兄也”[36]897-898。也正由于儒道先贤对“赤子之心”都特别重视,才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坚实地位。受其影响,在古代文论里,借“赤子”立说也一直是一极重要的话题,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明代提倡“童心说”的李贽。另外,如“公安三袁”与袁枚的“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说”,徐渭的“真我说”,龚自珍的“尊情说”,梁启超的“少年说”等,也同样都是很有名的例子。不过,比较而言,还是李贽表达得最完善。其《童心说》曰:“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那么,“童心”既对人如此重要,人们又为何将其丢失了呢?对这一点,李贽也同样有明确的回答:“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那么,“童心”既失,又有何后果呢?对此,李贽进一步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37]98-99。虽然李贽所说并非专对文学而发,但是显而易见这一表述对文学创作无疑更具指导意义,王国维的思想可以说也是沿着这一理路走的。
其《人间词话》曰:“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12]19,又曰:“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其《文学小言》曰:“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又曰:“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其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而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8]25。由以上表述不难发现:王国维对“社会上之习惯”“文学上之习惯”对于作家思想、创作的不良影响,其认识实是极深刻的。
盖也正因如此,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即:“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12]4。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观点,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意见,如有的学者说:“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这同阅世深浅并无关系”[38],还有学者认为:“以王氏之论推之,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性情愈真则赤子之心愈纯,赤子之心愈纯则愈可产生好词章。设使此说得以成立,则后主最为感人之作不当出于被虏之后,而当出于被虏之前;后主赤子之心经臣虏生活后必当破损,其全真之时定为养尊处优之日。然‘词话’论及后主词的十余处中,其意所指似皆为后主囚后之词,正是这些佳制,博得了王氏的盛赞。对此,王氏将何以解之?”[39]
对于前人的这些否定也有学者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王国维说主观诗人不可多阅世,不是说绝对的不阅世。这表明阅世多少只是相对而言的”,“主观诗人以抒写胸中郁积、表达强烈情感为目的,对情之真切与纯粹的要求远比客观诗人更直接更重要。为了不破坏心中纯情而能任性而发,阅世相对少些,无甚大碍。相反,被世俗污染同化,尤其不利于主体真诚品格与率真感情的培养。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恰恰为其成为一位主观诗人提供了隔离作用”[40]。如果在其亡国前,他已是一久谙世习,摸爬滚打的老手,那么面对亡国之变,他就未必能成一卓绝千古的词人了。彼此对照,不难看出:较之上文那全盘否定的意见,这一看法显然要更公允。
再进一步说,所谓主观诗人,也即抒情诗人,主要是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对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抒写固然也离不开对外物的依托,因为它也需要寓情于物,托物言志,借景烘托等,但是相对而言,与那些客观之诗相比,也即与那些戏剧、小说相比,它所需要的客观材料、外在凭借毕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较之客观诗人,主观诗人并不需要太多的素材储备就能写出非常优秀的诗歌。也正缘于此,对于那些主观诗人来说,保持内心的纯净无染,避免世俗观念的侵扰眩惑,拥有一颗赤子之心,这才是他们更需要的。只有确保这样的赤心,当他们面对生活事变时,才能产生真切的感受,作出真切的反映。而那些客观诗人,由于他们的创作主要是通过故事叙述以塑造人物的,因此深入生活,丰富阅历,积累素材,增广见闻,以为其写人叙事服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虽然说保持自我童心的纯真,不受世俗观念的侵染,对于他们来讲也同样很重要,但是由于人物塑造、故事叙述的需要,比较来说,他们对生活阅历的丰富,社会经验的积累,现实人生的体验,其要求无疑更迫切。并且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随着生活的深入,阅历的增加,客观诗人掌握的素材,积累的故事,熟悉的人物固然加多了,但他们对世俗观念的抵制,对不良风气的抗击,其任务也同样变得更艰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客观诗人的多阅世,多经事,实为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如果不是文学创作所必须,如果不是人物塑造无法凭空想象,那么,在王国维心里恐怕连客观诗人的多阅世也是不必要的。
总之,文学创作的可感不隔乃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而主观之诗“言志”为主的特点又决定了它并不能像注重形象塑造的客观之诗那样专求形似,因此如何确保内心情感的真切深挚,如何使读者充分体验到作家的血气情绪,也就成了这类文本实现可感不隔的最主要的凭借。要使内心情感真切深挚,血气情绪流于行间,保持内心世界的童真,不受世俗观念的侵污,显然乃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据此足见,王国维的“境界说”,它的本根确乎还是深植于以天人合一为背景,以心性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国“童心崇拜”的泥土中的。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王国维对“赤子之心”的强调固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浸育,但与我国古代的“童心崇拜”也是有差别的。最起码李贽等人对文学创作的可感不隔,其认识远不如王国维这样清晰。如果说李贽等的“童心崇拜”主要展现的是一种个性独立,精神解放的思想倾向的话,那王国维的“童心崇拜”则主要指向文学创作的可感不隔。他们的思想基点并不完全相一致。
五、结语
显而易见,王国维的“境界不隔”说虽系受西人“形象直观”说的启发,但它的得名以及王国维对“真切”“自然”“情兴”“赤子”等一系列概念的强调,显然又使它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烙印。一方面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新走向,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里程碑,然另一方面它的这一新的走向、新的转换又是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的。它并不是对西方“形象直观”说的直接移植或简单照搬,而是针对中国心性文化与言志文学的特点,无论在概念的选择上,还是系统的重构上,都对西方的“形象直观”说做了积极的改造。也正由于这样的改造,才使“境界说”既保持了与西人“形象直观”说的相通性,又增添了丰富的截然不同于西人的新内容,使西人那深受“摹仿说”影响的形象化、直观化理论,最终也得以在以“心性论”“言志说”为主导的中国文学环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衍变为一种涵蕴丰富,饱含生机的新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国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论现代化的奠基者,也是西方文论本土化的开先者。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程度上,其“境界说”都堪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而在他之后迅速崛起,急遽膨胀,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的形象化、典型化学说,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中国文化的本色。
虽然说自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对王国维的历史价值认识已越来越深入,对他的“境界说”的评价也越来越公允,但是无可讳言,主要着力点仍放在他对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引领上,放在他对中国文论的开新上,而他对中国传统的尊重,也即对于他的如何固本,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说“可感”乃一切审美的基础,也是中西文学共有的属性,但中国文学既以抒情见长,则它就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王国维正是仅仅抓住这一点,才建构起以“境界说”为旗帜,以“不隔说”为核心,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的文论大厦。也正缘此,王国维这种既勇于开新,又不忘固本的学术理路,对于我国目前的文化重建极具借鉴意义。一方面固然要广纳并蓄,开阔视野,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失去自信。这种新旧兼顾、华夷相辅的学术理念实为当下进行一切学术探索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