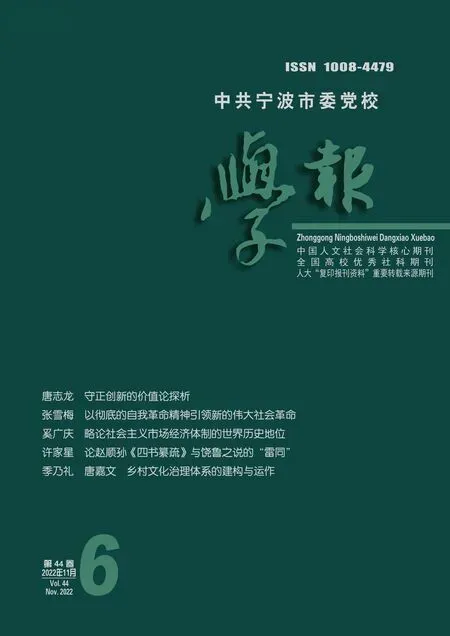梁启超历史哲学刍议
2023-01-25郭勇健
郭勇健
梁启超历史哲学刍议
郭勇健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梁启超的史学有历史哲学的维度,他将佛学的某些观念运用于历史问题,上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史学的批判。为超越旧史学,前期梁启超以自然科学为新史学的方法样本,以进化论为新史学的理论武器,后期梁启超放弃了科学的诉求,转向佛学,这使他的新史学不再执着于历史科学的定位,而是增加了历史哲学的维度。佛学对梁启超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引进业力、共业、心力、因缘等佛学概念和理论,并使他拒绝英雄史观,质疑历史的因果律,调整历史的进化观。
佛学;史学;梁启超;历史哲学
梁启超有历史哲学吗?这是个问题。一个史学家,当他不限于研究某一处、某一段和某一专题的历史,进而反思历史本身和历史研究本身时,往往会进入历史哲学的论域。梁启超当然有过这种反思,如他的“新史学”构想、他的“历史研究法”。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清浅明晰为特征,少有哲学思辨,缺乏形而上学的深度,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中有历史哲学之维度。有两种历史哲学,一种是下降式的历史哲学,作者本身就是哲学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并将其基本观点运用于历史学,成就了历史哲学;另一种是上升式的历史哲学,作者首先是历史学家,未必有系统的形而上学,但他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达到哲学的高度,也能成其为历史哲学。上升式的历史哲学,可以借用他人的哲学立场、视角和观点。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属于后者,他借用了佛教哲学,将佛学的某些观念运用于历史问题,上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关于梁启超之“新史学”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将梁启超的史学坐落于佛学基础之上加以考察,则比较少见。本文试图初步描述梁启超的基于佛学的历史哲学。
一、从佛学到史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p99)这也可视为梁启超的夫子自道。但我们不能因为这句话就认定梁启超的史学一开始就“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成稿于1920年,此时梁启超已深入研究佛学有年。大体上,梁启超与佛学之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康有为影响,得以接触佛学;第二阶段受谭嗣同、杨文会的影响,开始研究佛学;第三阶段出于自己对文化和人生的反思,主动深入佛学之堂奥,完成了《佛学研究十八篇》,并尝试学以致用,将佛学观点运用于新史学。
据其自述,梁启超19岁列于康有为之门墙,已开始接触佛学。“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2](p11)那时的梁启超还想参加科举考试,大体上是孔孟信徒,满腔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对于出世的佛学不免有些隔膜,因而“不能多所受”。其后,“(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1](p99)其时梁启超对于佛学已是“好焉”,但还“不能深造”,至于在论著中“推挹佛教”,恐怕还要等些年月。的确,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写过《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但正如文章题目所示,佛教不过是达到“群治”的工具,作为工具,佛学与小说并无实质差异。我们知道,梁启超在1902年还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要借助或利用佛教信仰的力量,一如他要借助或利用小说感染的力量。此时的佛教对于梁启超而言,并不是“佛学”,更不是“佛教哲学”。
一般说来,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思想主要是儒家,掺杂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可谓“内儒外西”。前期梁启超的思想可以《新民说》(1902~1908)为代表,此书呼吁改造国民性,一时振聋发聩,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方案,并不见得多么“新”,甚至还是传统儒家的那套思想:“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3](p210)就此而言,梁启超与鼓吹“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并无本质的区别。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立志从政治转向学术,大约以此为界,进入其学术思想的后期,也进入他与佛学之关系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梁启超断言西方“科学万能”的迷梦已经破产,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趋于没落,而东方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拯救”之方,因而需回归传统文化。但此时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已不限于儒家文化了。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的演讲中,梁启超断言:“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4](p27)明确强调“国学”的构成在儒学之外还有佛学,恰好表明梁启超自己的学术思想已是“融合佛儒”了。就是在这个阶段,梁启超开始尝试将佛学观点运用于史学。
梁启超于20世纪的头几年提倡“新史学”时,尚未把佛学运用于历史研究,因此那时梁启超的史学基本上还只有“历史科学”,而没有“历史哲学”。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传统史学的批判。在1902年前后的论述中,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旧史学实际上把历史视为帝王的家谱,因为“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5](p133)其二,旧史学总要标榜“正统”。梁启超批评道: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津津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赴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6](p189)
显然,无论是把历史“家谱化”还是持历史叙述的“正统说”,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所以梁启超说“千余年来陋儒津津于此事”。儒家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君臣”,儒者以“臣民”自居,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下,历来并无“国民”或“公民”的观念。因而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实即批判儒家史学。他要突破围绕着“君”的史学,代之以围绕着“民”的史学;要突破朝廷史学,代之以国家史学。1921年梁启超写出了较为系统的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深化对旧史学的批判,把矛头指向旧史学的始作俑者孔子,他认为,旧史学“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7](p34)
突破和推翻旧史学的儒家思想框架,需要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史学。1902年前后,梁启超把目光投向西方,主要是以进化论为新史学的理论武器。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原本是一种生物学理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将它扩展为一种伦理学。1898年,严复编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名之为《天演论》,一时洛阳纸贵,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天演论》的命题也成为20世纪初中国学界趋之若鹜的“真理”。梁启超是率先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学者之一。《新史学》中的《史学之界说》,对历史学有三个层层递进的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8](p139)“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8](p141)“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8](p142)所谓公理公例,也就是客观的规律。梁启超此时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而历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进化”和“规律”这两个关键词,说明梁启超当时所畅想的“新史学”,是一种以科学为样本、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史学,可称之为历史科学。
但以科学作为历史学的榜样,将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这在欧洲主要是18、19世纪的思路,不妨把这一思路名为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主义挟着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伟大成就之声威,认定自然科学是世上唯一的真理,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一切学问。19世纪末期,以新康德主义者为先锋,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纷纷质疑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主张历史学的独特性,进而创建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以历史学为中心的人文科学。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对“科学万能”的质疑,可视为中国学者对科学主义的一种批判与超越。20世纪20年代,在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第二年,梁启超读了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深受启发,史学思想为之一变。他说:
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卡儿特(按:即李凯尔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7](p138)
这里所说的“因果关系”,乃是自然科学的命脉所在。然而,梁启超的自我批评过于严厉,“完全错了”的说法也有所夸张,因为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虽然用了“因果”二字,这因果实与科学的因果貌合神离,与其说它是科学的,不如说它是佛学的。
总之,为了突破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旧史学,梁启超一度求助于西学,试图采用进化论的观点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一门新史学,这是梁启超的前期史学。但进一步的探索使梁启超发现,进化论的观点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历史领域的适用性比较可疑,甚至与历史学扞格不入,于是他放弃了科学的诉求,转向佛学。他的“新史学”,也变得更丰富了,不再执着于历史科学的定位,而是增加了历史哲学的维度。
二、业力与共业
梁启超历史哲学的首要概念,就是“业”,这是一个佛教哲学的概念。梁启超认为,“业”是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他在一封家书中强调,佛教阐发的“业”和“报”的道理,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9](p75)。所谓“报”,亦即“业之报”或“业之果”,“业”所带来、所残留的结果,就是“报”。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也不会得瓜。有业才有报,报是业的结果,因此“业”是首要的概念。
那么,何谓“业”?“业”的梵语为karma,音译“羯磨”,意为“造作”“行为”。简言之,业就是所作所为。佛教把业分为身、口、意三种,身、口、意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造业”。“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多么微细的小小事件,必定会在我们的身、心、未来境遇中留下痕迹。”[10](p121)譬如心理活动或思维模式会反映在身体上、面相上。古人云“相由心生”,这便是业的作用。业的作用,亦即“业力”。正如自然科学有“物质不灭”的定律,佛教哲学也主张“业力不灭”。对此,梁启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业”是什么呢?我们所有一切身心活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飞奔过去,随起随灭,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动一次,他的魂影便永远留在宇宙间,不能磨灭。勉强找个比方,就像一个老宜兴茶壶,多泡一次茶,那壶的内容便生一次变化。茶吃完了,茶叶倒去了,洗得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来什么也没有;然而茶的“精”渍在壶内,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渍下的茶精便起了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茶精是日渍日多,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将壶打碎。这叫做业力不灭的公例。在这种不灭的业力里头,有一部分我们叫他做“文化”。[4](pp1-2)
文化是一种“业”或“业力”,历史亦然。在梁启超看来,一般史或普通史也就是文化史。
不过,梁启超在《说无我》中又说:“佛说法五十年,其法语以我国文字书写解释今存大藏中者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无我’。”[11](p72)在《佛教心理学浅测》(1922)中也说:“倘若有人问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能用一句话包括他吗?我便一点不迟疑地答道:‘无我我所。’再省略也可以仅答两个字:‘无我。’”[11](p346)前面说佛教七千卷经典说的只是“业”的道理,现在又说佛教八千卷经典说的只是“无我”的道理。两说置于一处,冲突立起。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成道后初转法轮,言说“四谛”,“苦”是第一谛,集谛、灭谛、道谛都建立在苦谛之上;“一切皆苦”是原始佛教“三法印”之一。佛教的根本目标,乃是解脱或超越人生之苦。佛教主张无我,正是为了釜底抽薪,在思想上和践行上彻底取消体验苦的主体——无人体验的苦自然不再是苦。但是,业或业力,必有造业和受业的主体。所谓“自业自得”,正因为有“自”或“自我”,业的理论才得以成立。倘若“无我”,那么造业和受业的是谁?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轮回的又是谁?如此,“业”和“无我”的思想,岂非发生了冲突?其实,这一冲突是佛教思想本身的内在冲突,佛学家吕澂曾批评释迦牟尼的思想:“他一面否认自我存在,同时又肯定业力的作用(肯定业力,是他无法解决现象是什么决定的这样一个问题)。婆罗门的业力说,是同轮回结合的,释迦既否认了轮回的主体,那么轮回还有什么意义?这是释迦学说的内在矛盾。”[12](p22)
我们无法断言,梁启超是否意识到了这个“内在矛盾”。所幸在梁启超的史学中,并不曾发生类似的“内在矛盾”,这是由于他对“业”有进一步的限定。佛学主张“无我”,只是要消解个体的我。换言之,尽管“小我”消灭了,“大我”仍然存在。而梁启超历史哲学的“业”,恰好绕过了“小我”,注目于“大我”。他将“业”分为“别业”与“共业”。别业是个体的所作所为,共业是群体的所作所为。文化属于共业。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文化并非“我”的文化,而是“我们”的文化。历史也是共业,也是“我们的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历史,并非个人的历史,而是社会的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说:
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立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7](p2)
在《历史统计学》(1922)的演讲中梁启超也指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13](p134)。举例来说,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实即清代学术简史,此书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思潮”的概念,“思潮”即是一种“共业”。一个人,哪怕他是天才、伟人、英雄,充其量能“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但仅凭他一人不可能形成“思潮”。梁启超指出:“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1](p1)由此可见,有群众,有人类社会,方有历史可言。“民族”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单位,故而历史往往表现为民族史。因此,历史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启发民族自觉,培养“民族心”。民族史是共业,世界史就更是共业了。“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7](p113)
梁启超在史学中引入佛学的“共业”概念,基于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从“破”和“立”两方面加以考量。第一,从“破”的方面,或是从学术论争的角度看,“共业”说首先还是为了反对旧史学。旧史学以帝室为中心,沦为“帝王家谱”,而新史学“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7](pp1-2)所谓帝王家谱,当然并不是只描述帝王一人或一姓,而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叙事的中心,用西方史学的话语,旧史学的立脚点在于“英雄史观”。而梁启超的共业说主张历史是“全社会之业影”,根本上质疑了“英雄史观”。第二,从“立”的方面看,“共业”说造成了对历史之主体的新看法。“历史的主体”,梁启超称之为“历史的人格者”。那么,“历史的人格者”是谁?按照“共业”说,造业或受业的主体,并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作为共业的历史,其主体并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广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7](p122)
梁启超的以上言论表明,他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只是过去的现象,已不再适合于现代,“历史即英雄传记”的史观,也随之而俱倒,因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明确反对人物传记式的旧史。这种观点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1902)一文也有鲜明的表述,在那里他强调英雄退出历史乃是“世界进步之证验”。梁启超自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认为,个性须扩充为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总的来说,梁启超拒绝了英雄史观。然而,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略论梁启超的史学》(1985)一文中却断言,梁启超持有“个人英雄史观”,文章说:“他的个人英雄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着比较系统的发挥。”“把历史归结为英雄与群氓,认为左右历史发展的只是少数英雄,而群氓则只配扮演一种消极的角色,这种英雄史观在此书中得到比较系统的阐发。”[14](pp190-191)这一判断,并不妥当,必须纠正。
梁启超的以上观点,与西班牙历史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Gasset)依稀相似。奥尔特加在名著《大众的反叛》(1929)中指出:“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15](p25)这与19世纪以前由少数精英领导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奥尔特加称之为“大众的反叛”“大众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历史动向。有评论云,奥尔特加此书,一如卢梭《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马克思《资本论》之于19世纪。马克思反对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梁启超的史观也若合符节。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已成不刊之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固然有关,与梁启超的影响也未必全无干系。然而梁启超的历史观,并不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也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奥尔特加其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出版比《大众的反叛》早7年)。要说影响,佛教哲学当然是首要因素。佛学的“无我”说和“共业”说,在梁启超的史学中表现为英雄的淡出。
三、因果与进化
关于历史学的两大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和历史规律的问题,恰如保罗·贝克(Parl Bekker)所言:“研究历史的关键不在于陈述历史事件,而在于挖掘其中变化的规律和动力。”[16](p4)在梁启超史学中,动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历史和文化是人类的共业,那么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业力,具体地说,则为“心力”。“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7](p119)“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7](p128)所谓“心力”,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或即是佛教的概念。梁启超写过一篇随笔,名曰《惟心》(1900),阐明佛学“境由心造”“三界唯心”的道理。但梁启超有时也用西方学术概念来表述“心力”,此即“自由意志”。换言之,在梁启超看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乃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之为自由意志,就在于突如其来,不可预期,无缘无故,完全偶然。如此一来,历史是否有规律的问题,或曰历史的因果律问题,便成为梁启超史学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但凡研究问题,要言之,无非就是问个“为什么”,也就是求其原因,知其所以然,研究自然如此,研究历史也当不例外。例如,研究秦朝历史必要追问其灭亡的原因。一般认为,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所以一开始梁启超也并不觉得“历史的因果律”是个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界说历史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7](p1)明确规定历史研究要“求得其因果关系”,大致相当于司马迁要在历史写作中“原始察终”(《史记·太史公自序》)、“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毕竟不同于司马迁的“旧史学”。若问如何“求得其因果关系”?那就要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梁启超指出:“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4](p9)当时梁启超还做过一场《历史统计学》(1922)的演讲,顾名思义,“历史统计学”就是尝试将科学的归纳法用于历史学。但是,哲学家牟宗三指出:
有人说他是用科学方法讲历史,这句话是不通的,科学方法不能用在历史。什么是科学方法?归纳法。历史是不能归纳的。文字的材料可以归纳,但历史本身是不能归纳的。现在念历史的人,他研究的不是这个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材料。……历史是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归纳的。比如说昆阳之战,王莽有百万大军,还有狮子老虎巨人,汉光武有多少军队呢?他只有数千人!但是他却把王莽打败了。你敢说汉光武那时如此,你今天也一定可以如此吗?他打胜了,你就一定能打胜吗?这是没有一定的,不能归纳的。这不能用科学方法,当然也没有科学方法中所发现的因果法则。[17](p9)
牟宗三这段话的观点,梁启超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约1922)的演讲中,梁启超也强调归纳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只及于整理史料而止。正是在这篇演讲里,梁启超质疑了历史的因果律和历史的进化观。但这种“修补及修正”是否说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观点是站不住脚且没有价值的?显然不能。事实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已经对“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抱有怀疑态度了,他指出: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历史之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7](pp119-120)
将这段长文悉数引用,因为它对于理解梁启超的历史哲学,相当重要。梁启超的说法表明,历史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是有区别的。
什么是因果律?因果律的最简单表述就是“凡事必有原因”,因与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故而,因果律就是“必然的法则”。自然是一个受必然法则支配的领域,但历史是自由意志的造物,并不受必然法则管辖。不过,梁启超以佛教哲学的“共业”理论解说历史,而“业”的理论,却是肯定必然性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就是必然性。按照佛教“业力不灭”的理论,众生所造之业,永不消失,必然报应。因而有人认为,佛教哲学主张一种宿命论——尽管未必准确。历史的发展,也显示出某种必然性。《三国演义》第一回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天下大势”,亦即历史的必然性;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则道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受必然规律控制的铁一般的历史,那还是历史吗?自由意志说与业力或共业说,不会发生矛盾吗?
为驱逐这一疑团,我们必须澄清:“心力”或自由意志发起之后的必然后果,与“心力”或自由意志的发动本身是不同的。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据说隋炀帝铺张奢糜巡游江南造成了隋朝的灭亡,但若非由于当时的修龙舟之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造福后世的功绩,直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隋炀帝铺张奢侈,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长此以往,隋朝必然灭亡,这就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样。但隋炀帝之铺张奢侈,与其他帝王之铺张奢侈有所不同,比如他并不造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开运河、造龙舟,完全出于隋炀帝个人的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出于他的自由意志。由此可见,自由意志说与业力或共业说是可以并存不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主张“造因”,“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18](p22)通常所谓“历史不能假设”,这是着眼于“果”,着眼于历史的必然性;为了改变历史,只能着眼于“因”,亦即发动自由意志,创造出新的“因”。唯有“造因”,才能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梁启超的造因说,后来为胡适所继承。
回到原初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说没有,那是由于“规律”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在历史学中并无立足之地。说有,那是承认历史的发展自有一种“必然性”在。梁启超断言“以因果律绝对适用于历史”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这正是由于他看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他又强调历史研究“不谈因果”为“断断不可”,这却是由于他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照此看来,不论有无后来的“修补及修正”,梁启超史学中的“因果”,都已与自然科学的概念貌合神离。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因果”,不如说是佛教哲学的“因果”。所以梁启超说:“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梁启超用了“因”,还用了“缘”,他说:“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有果必有报”,“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7](pp131-135)这些都是佛教式的表述,并启用了原始佛学中的“缘起论”。“缘起论”又可称为“缘起说宇宙论”,它认为,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而存在的。“因”和“缘”就是条件。梁启超在《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中指出:“宇宙何以能成立?人生何以能存在?佛的答案极简单——只有一个字——‘因缘’。”[11](p56)而在他看来,“史迹”也是因缘所生的。
基于佛学的历史哲学,有异于科学,也有别于进化论。大约自黑格尔以来,“进化”便隐然成为统治西方学界一种历史观。经达尔文生物学进化论的推波助澜,“进化”几乎成了历史的代名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在这个国家“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9](p123)。这正是以“进步”或“进化”作为衡量有无真正历史的尺度。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1902)中也有类似的判断:“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8](p141)但是,黑格尔和早期梁启超的观点都是很成问题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绝非如黑格尔所言“从无任何变化”。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变化未必都是“进化”。变化有两种,一是“进化”或“进步”,一是“退化”或“退步”。进化是历史,退化也是历史。斯宾格勒(Windham Press)的《西方的没落》(1918),也许可视为“退化史观”的代表作。以“进化”衡量中国历史,不如以“退化”描述中国历史。这虽是今人的看法,古人其实也已这么看了。譬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这显然是一种“退化史观”。老子如此,庄子亦然。梁启超认为道家思想比较消极,并不采纳,他采纳了含有积极因素的佛教思想。但与道家相似,佛教的宇宙论与其说是“进化”的,不如说是“退化”的。把佛教的宇宙论用于历史,必会得出轮回史观或循环史观来。前引梁启超所言,“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这“当然之程序”,就是循环。循环史观与进化史观之不同,以视觉形式表达,前者为圆圈,后者为直线。但佛教认为宇宙的变化并不是画一个圆圈就结束了,而是一圈既了,一圈再起,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于是,从整体看是循环,从局部看则是退化。换言之,在每个循环阶段,都是退化。退化经历了生、住、异、灭四个阶段。宇宙如此,历史亦然: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为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1](p2)
前期梁启超信奉“进化主义”,也信奉自然科学。科学必然带来进步,这是严复引进进化论之后风行中国的观点。“进化主义”与科学是捆绑在一起的,将它们捆绑在一起的则是现代性。科学是现代性的主要力量,进化或进步则是现代性的主要观念。后期梁启超欧游归来,意识到“科学万能”只是现代欧洲人的一个迷梦,发现了进化或永远进步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幻觉。这种思想转变表现于历史哲学,使他认识到进化史观未必没有局限,而旧史学的循环史观未必全无是处,因而将自己的进化史观做出了调整。尽管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中,梁启超提到旧史学的循环史观仅以孟子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为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哲学在他的思想转变中没有发生作用。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 梁启超自述[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3] 梁启超. 新民说[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4] 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5] 梁启超. 中国之旧史//梁启超集[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6] 梁启超. 论正统. 转引自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 梁启超集[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9] 梁启超家书[M]. 林洙, 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10] 庭野日敬. 《法华经》新释[M]. 释真定,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1]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12] 吕澂.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3] 梁启超演讲集[M]. 贾菁菁, 编选. 上海: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14]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5]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M]. 刘训练, 佟德志,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6] 保罗·贝克. 音乐的故事[M]. 马立, 张雪燕,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17] 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8] 梁启超. 自由书[M]. 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19]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B259.1
A
1008-4479(2022)06-0076-09
2021-11-03
郭勇健(1973-),男,福建福清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艺术哲学。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