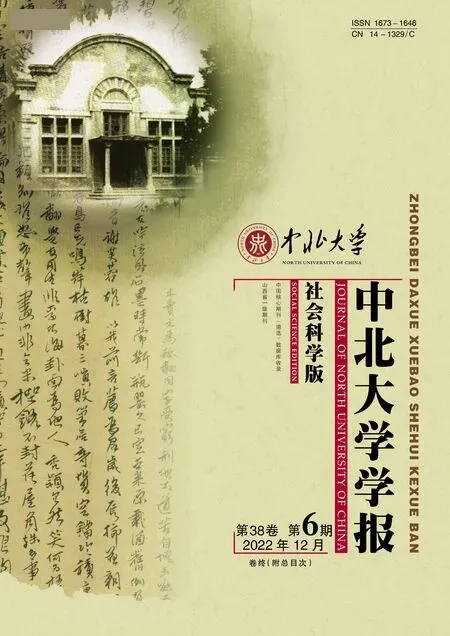传记电影的虚与实:约翰·罗斯金形象勘误*
2023-01-25石琪琪黄芷熠
石琪琪,黄芷熠
(1.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2.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0)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位卓有成就的理论家,他不论在艺术批评还是在倡导社会政治改革方面都对时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被同时期的人誉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圣人”“美的使者”“先知” 等。“他是第一个有同时代的作家,他的同龄人们成立学会研究他的作品的人,第一个罗斯金学会于1879年在曼彻斯特成立,随后在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地也相应成立,1887年,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分别成立了他的研究会,并出版了一份研究他的杂志……美国各地也组建了许多研究罗斯金的团体和俱乐部。”[1]248西方国家的罗斯金研究一直都是一门显学,国内学界对他的关注也起步较早,20世纪初期,李大钊、李叔同、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就曾对罗斯金的思想进行专门的译介、阐述,比如李大钊就曾从罗斯金的情感、美术、经济等角度为其作小传,将其思想与我国社会改革现实结合讨论。由于历史语境的原因,该阶段学者重点关注的是罗斯金所提倡的经济、劳动、社会改革等领域;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十余年),国内学界再次掀起罗斯金研究的热潮,当前的罗斯金研究很少再重点关注他在社会改革层面提出的思想,主要探讨其作为艺术家、大批评家所提出的理念。
罗斯金作为艺术史中一位伟大思想家,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自从他的自传《往昔》和他传《约翰·罗斯金的一生》出版以来,以罗斯金为传主的传记电影、纪录片、短片,以及改编的小说、戏剧层出不穷,多媒介语境中的罗斯金影像不再重点阐述传主作为“伟人”的身份,而是具象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形象。颇为奇怪的是,影视媒介中向我们传达的罗斯金基本都是歪曲了历史真实之后的形象再造,或借助罗斯金的伟大艺术家身份暗示、反衬导演和编剧意欲表达的主题思想。于2014年上映的关于罗斯金的两部传记电影《透纳先生》《艾菲·格蕾》却极端地扭曲了传主的真实形象,扭曲历史真实的程度远超电影艺术所应有的自由。从社会公众层面而言,传记电影往往是大多数人认识传主、了解史实的重要方式,“从最早出现的电影到制片厂时代结束,电影的发行在有规律地增长,传记片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一直为公众构造着历史”[2]2。为了使公众可以相对客观、真实地认识这位杰出思想家,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一定的辨析。
1 传记历史片中的“他者”形象
传记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门类之一,具备传统电影艺术范畴内的相关特征,虚构性、故事化、再创造,同样也是传记电影的核心叙事方式。杨正润先生将传记电影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记历史(文献)片,另一种是传记故事片。历史片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内容是叙述传主一生的主要活动(通常以活动地点为叙述背景)……尽可能对传主作出完整、直观的介绍。”[3]470传记历史片强调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客观描述,对传主的叙述要求横跨整个人生,不再重点关注传主在某方面的突出特质,强调史实的广度而非深度。
以艺术家作为传主的传记电影一直都是该类影片的重要选题,这类影片大都通过传主一生中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作品受到的推崇/批评,去塑造作为伟大艺术家形象的履历。在塑造传主形象或凸显故事的冲突性时,往往通过设置某些“重要的他者”(1)关于“重要的他者”,参见W.J.T.Mitchell提出的“Significant Other”,意指每一种艺术大都依靠与他者的对立来描述自身。纵深所塑造对象的经典性,这种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为所塑造形象提供某种恰当的深度,使之更具张力。近些年上映的艺术家传记电影《雷诺阿》(2012年)、《透纳先生》(2014年)、《艾菲·格蕾》(2014年)、《我与塞尚》(2016年)等作品尤为强调这种叙事手法,这几部电影中的尚雷诺、罗斯金、塞尚等形象正是作为“重要的他者”而存在。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领域的研究学者基本都将透纳与罗斯金视为一对互相成就的伟大画家和伟大批评家,并将两者对自然的观察视角作为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点。电影《透纳先生》中关于罗斯金的情节安排,正是起于两人互为表里的艺术理念,但编剧通过设置两者的理念冲突反衬透纳的杰出形象,更多地是利用了罗斯金作为大批评家的身份,并未深入这种身份应有的艺术认知能力。据笔者了解,两人对绘画的观念却是早年的罗斯金对透纳作品的维护并未受到晚年透纳的认可,以及晚年的罗斯金对早年自己维护透纳的观点及对透纳晚年创作的作品(尤其是女性裸体绘画)更多持存疑的态度。然而,影片在形象塑造时却完全没有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传主与“他者”。
作为电影艺术,我们必须认可导演和编剧通过某种特定的视角或手法去塑造传主的典型形象。在《透纳先生》中,虽然罗斯金的存在只是作为透纳人生当中的一段微小经历,只是一种被涉及的“他者”形象,但笔者却无法苟同电影借助演员的形象、语气、态度等行为的演绎,将罗斯金塑造为一个内外不一的小矮人、伪君子,这完全是对传记人物真实性要求的无端干预。《透纳先生》中涉及罗斯金的剧情总共有三段幕次,分别为:第一幕,在透纳家中的画展室中,罗斯金父子评判、意欲购买《贩奴船》(1840年)、《暴风雪—汽船驶离港口》(1842年)与透纳产生的对话;第二幕,在罗斯金家中的会客室,多位杰出艺术家共同讨论海景画中的影像技术;第三幕,在罗斯金的家庭晚宴中,镜头聚焦透纳和艾菲之间略带神经质的对话,并以罗斯金张扬的声音作背景音。前两幕主要涉及透纳与罗斯金对艺术的认知差异,即透纳不认可罗斯金对这两幅画的解读,以及反讽罗斯金没有站在历史的角度公正地评价克劳德的作品。
透纳的这两幅作品,其实是他晚年结合自身观看自然的视角去实践歌德《颜色学》中提出的关于光、影、空气的理论。歌德提出颜色理论的初衷是对牛顿光学理论的拒斥,他强调主观色彩与客观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颜色学的关键在于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所以我正是从属于眼睛的颜色开始。这样我们在一切知觉中就经常可以分清哪种颜色是真正在外界存在的,哪种颜色是本身主观产生的。”[4]115透纳对该理念的实践正是“以艺术的力量和效用去赞叹真实的自然,以对自然的知觉去鉴定自我的艺术”[5]71。罗斯金是认可透纳的这种突破的:“人眼本是天真单纯的,由于后天的经验,使我们接受了知觉对象的意义,因此失去了这种单纯性、朴素性,似乎‘看’只是看我们所知的东西,只有恢复眼睛的这种天真单纯性才能产生绘画上技巧的力量。”[6]他们同时强调视觉的主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但透纳却没有认识到“罗斯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快速观看后得到的简单结论,他的分析把隐含的道德与审美结合了起来”[7]。由于罗斯金为透纳辩护投给《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一篇文章没有被透纳允许发表的确是历史史实,仅就这个层面而言,电影中的透纳借拍打青蝇暗讽罗斯金对这幅作品的评判就像苍蝇一般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但这一幕却通过演员的演绎将罗斯金表现得极为自负,甚至盛气凌人,结合第二幕与透纳、斯坦菲尔德、琼斯、罗伯茨等人谈论影像艺术中的水域和海洋时比之更甚的骄狂自大,导演在这里借助乔什·麦吉尔的演绎否定克劳德的成就,也正是彻底否定罗斯金对艺术的认知能力;通过演员的言辞对话与表情动作,将罗斯金凸显为一个矮人般的伪君子形象更是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
第三段幕次,暗示了各类涉及罗斯金影视剧中重点戏谑的那段未完成的婚姻。剧情发生在罗斯金的家庭晚宴,导演不仅将罗斯金与艾菲的座位安排在完全斜对角的位置,甚至罗斯金的画外音也在责备艾菲对艺术没有任何天赋;艾菲在电影中就像提线木偶一般,自始至终都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这完全与她作为一位精明“女画商”的形象相悖(嫁给米莱斯后,他的画作很多都是艾菲在打理)。当然,这里或许是为了反衬罗斯金的清教徒家庭氛围对艾菲的“迫害”,并通过透纳与艾菲的对话明确表现出来,透纳混混沌沌的以巫师预言式的口吻对艾菲说:“它就要来了,罗斯金夫人,他就要来了,爱情”,这里很难明晰编剧是意欲表现晚年透纳的精神状态,还是特意为了表现罗斯金的家庭氛围。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了然罗斯金在这段婚姻中的负面形象。
总而言之,《透纳先生》中对罗斯金与透纳之间的关系建构与对罗斯金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具有争议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电影艺术的部分特质对这种不真实的现象进行一定的理解,但我们必须要认清这种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在公正地认识电影所要展示的传主的同时,也必须审慎地思考传主之外的他者形象是否具备同样的客观性,在通过“形象的他者”去巩固传主的卓越性时,两者互为烘托或许可以更好地凸显传主的经典形象。
2 传记故事片中的“自我”虚构
在电影艺术的娱乐功能及经济效益的诉求下,传记故事片相较于历史片则成了传记电影的主要载体。“故事片的镜头主要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影片就是讲述他的故事,同时也是在讲述一段历史,”[3]470它强调建立在对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之上的故事化处理,并根据编剧的审美诉求对传主进行相应的形象塑造,这种审美诉求不仅受到编剧本人的单向影响,甚至受到潜在读者和观者的审美移情与期待的干预。据笔者观察,以罗斯金为传主的传记电影、纪录片、短片基本全都关注到他那段未完成的婚姻,这正是编剧为了迎合观者追求新奇、趣味、探究隐秘,迎合观众对公众人物的隐私、八卦等不为人知的事情的想象。
1912年,无声黑白电影《约翰·罗斯金的爱情》(TheLoveofJohnRuskin)开创了罗斯金影视剧的先河,之后有BBC于1975年播出的《爱情学院》(TheLoveSchool)、1994年的短片《约翰·罗斯金的情欲》(ThePassionofJohnRuskin)、2009年BBC的6集连续剧《绝望的浪漫主义者》(DesperateRomantics)、2014年的电影《艾菲·格蕾》(EffieGray)和《透纳先生》(Mr.Turner)。其中,《艾菲·格蕾》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影响最大,同时对罗斯金形象的误导也最为严重。这部电影通过聚焦艾菲和罗斯金6年的简短婚姻,并截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段情节冲突,前期通过婚后与罗斯金父母共同生活作铺垫,反衬与婆婆共同居住的沉闷、压抑,到中期与罗斯金同游威尼斯加强两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在罗斯金邀请米莱斯为其作画时,与艾菲一同前往爱丁堡演讲途中将矛盾完全爆发,并结束婚姻。整体来看,如果仅就电影叙述的历史事件而言,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历史史实,即罗斯金与艾菲因婚后6年未完成婚姻而离婚,以及罗斯金宗教主义的苦行僧式成长环境。
该影片所要传达的主题显然不仅仅在于表现历史事件,它重点凸显的历史事件背后的隐含主题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罗斯金是一位巨婴式的成年人;其二,罗斯金是一位性无能者;其三,暗示了罗斯金的恋童癖。如果仅就演员的外在形象塑造而言,参考现存各类罗斯金的画像与照片,《艾菲·格蕾》中的罗斯金影像最具代表性,但这部电影的核心却是通过相关情节编造,成就了一部纯粹女性主义立场的家庭婚姻关系的道德说教片。为了将罗斯金塑造为女性主义视角中的“理想”形象,编剧以远超电影艺术所赋予的自由粗暴地诽谤传主,电影叙说的这三个主题扭曲了历史事件本身。其实,“在威尼斯的时候约翰并没有单独把艾菲留在那里……罗斯金在爱丁堡演讲时也并未让艾菲和米莱斯单独在一起(两人都一直跟随着),更没有威胁如果不服从就要毁掉艾菲的名声,甚至在床上背对着艾菲手淫更是无端地捏造,这些场景都是一种故意蔑视的表现”[8]。对于电影中这类被歪曲的情节,编剧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借助具体事件的真实性,对事件的细节进行一定的再造,恰恰是这些被歪曲的细节堆砌,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被歪曲的罗斯金形象。
编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一些重要情节的藏匿,看似公正地塑造了罗斯金的形象。首先,我们对电影将传主塑造为巨婴的形象给予一定的认可,罗斯金在自传中对此也有所叙述:“童年时期的灾难式经历,使我没有任何想去热爱的东西或人;也没有任何可以让我持续坚持或容忍的人;也没有人教我严谨地做事和举止得体;我判断是非的能力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培养。”[9]35-36自传中关于父母、感情等关系的类似叙述还有很多,这种经历造成了他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的情感问题,以及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使他难以拒绝来自母亲对自己感情经历的安排,甚至与艾菲的婚姻也完全出于双方父母的强求。这一点正是该电影所塑造“巨婴”的出发点,但笔者以为影片对罗斯金的这种定性过于片面,日常社交中的罗斯金并非没有自己的决断力,也没有完全依赖父母,他对父母的顺服来源于他的个性,以及他认为“来自于父母的照顾是一种小小的荣耀,我会觉得欣慰而不是感到羞愧”[9]187。他在人生各阶段与各阶层人的接触更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罗斯金的思想和行为真正卓越之处在于,他经常可以脱离自身的环境与其他阶层和时代之外的人对话。他是一位思想深刻的道德学家,观点也非常虔诚,他尝试做的事情是为了整个人类而非自己。”[10]8其次,《艾菲·格蕾》的编剧粗暴地借法官之口宣布两人婚姻的未完成是因为罗斯金性无能、阳痿,完全是虚化历史,她掩盖了两人婚姻的缘由以及罗斯金对情感的真实态度。关于两人婚姻的初衷,在罗斯金的父母看来,他们认为罗斯金经历了两场无疾而终的感情,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艾菲“已经长成了一个完美的苏格兰女性,她的健康和精神足以弥补人们对他那孤僻、病态性格的成见”[1]70。在艾菲的父母看来,“协议的一部分是,当约翰和艾菲结婚时,约翰·詹姆斯·罗斯金不会带来嫁妆,而是交给艾菲一万英镑”[11]39-40。《艾菲·格蕾》中虽然也借艾菲的言论表达了她的父母很需要他们的资助,但这种表述在电影的情节安排中几乎完全可以被忽略。或许正是双方父母的“功利”心态,罗斯金在婚后并没有履行这场婚姻,这场“丑闻”双方唯一的公开观点是罗斯金在一份法律声明中称“艾菲因父亲的经济问题而心烦意乱,在新婚之夜,她因这种痛苦而显得非常虚弱、紧张”[10]105。结合艾菲婚前已有的婚约“艾菲已经告诉另一个年轻人,当他从印度回来时,她会嫁给他,而这个约定似乎在艾菲的圈子里已经知道了,但也并没有被更多人知道。艾菲要求约翰为他们的订婚保密,他同意了。”[10]103李大钊先生对此问题的总结最具综合性:“罗斯金之前有两段感情,但都是悲剧。罗斯金因其母亲勉强撮合,与Grey(古雷)订婚,然其结果又加上许多悲剧。此错误三方面必须负责。一、其母为安慰其子之悲哀计,不问其是否合意,勉强撮合;二、罗斯金顺从其母命,勉强允许;三、Grey又不审慎,因之结果不佳。”[12]236-237结合罗斯金虔诚的宗教道德信仰或许可以解释婚姻未完成及双方父母都未参加婚礼的原因。不论如何,这场婚姻存在某种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段婚姻未完成的原因,各类传记以及传记短片也都进行了一定的猜测,包括《艾菲·格蕾》中的描述,总体上可以指向一点,即罗斯金对女性裸体的欣赏完全来自于对古典风格的女性裸体雕塑的赞美,以及古典主义绘画大都视裸体为纯洁、神圣的指向。所以,他在面对艾菲的裸体时无法接受真实与理想间的差异,由此出现由惊愕到厌恶再至默默离开的场景。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基本可以明确《艾菲·格蕾》中塑造的罗斯金形象只是借助史实表现编剧的女性主义观点。但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尝试对罗斯金这段婚姻关系下某种定论,只是针对电影中对传主形象的极端扭曲进行一定的辨析。
对隐含在电影背后的恋童癖,这个主题并不是重点要突出的问题,但结合该影片的叙事视角及思想主旨,我们可以显然明白剧情中人物设置的目的。这个问题的迹象,主要表现在被杜撰出的艾菲未成年的妹妹,以及罗斯金认为童年时期的艾菲就像亚当的夏娃,而现在却成了沉溺于放荡与快感的妓女;结合对罗斯金影响很深的几段情感经历,不论是早年的阿黛尔还是中年时的罗斯,她们都是在未成年时期吸引到了罗斯金。而且,这两段情感经历显然比与艾菲的婚姻对他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罗斯金一生中,与艾菲的婚姻或者未再婚的插曲虽然损害了他的声誉,但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损害。相比之下,他与阿黛尔和罗斯的关系几乎完全是他想象中的关系,这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10]199-201由此,罗斯金的情感倾向更多在于未成年的女性基本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艾菲·格蕾》对罗斯金在这个问题上的塑造却是通过混淆“恋童癖”的现代意义,意欲表达他对未成年女性的性想象,无视了罗斯金出于宗教主义立场对未成年女性的“纯洁”特质的赞美。
我们需要注意,“在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女性导演们毫不回避女性自身的欲望,大胆地在影片中表现出女性欲望,以此来彰显女性的主体意识”[13]113。《艾菲·格蕾》在塑造传主罗斯金的形象时,正是在于借助罗斯金这段“婚姻的未完成”表达导演/编剧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我们从中或许可以得到成年人不论在生活还是精神层面都应该脱离父母的“掌控”,或者与之相关的道德说教主旨,但该影片与《透纳先生》同样通过虚化,污化了这位杰出艺术家的真实形象,甚至比之更甚。
3 传记异本中的形象弥合
以上两部典型影片中对罗斯金形象的扭曲,我们可以通过各类相关传记文本和传记片中的叙述进行一定的弥合。相较于传记电影,传记文本对传主的关注更为全面,我们可以从更多历史事件中综合认识传主,可以明晰传主思想成型的流线,而非影视剧中对传主人生的短暂聚焦。
传记文本在论证传主形象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需要注意区分不同传记在塑造传主形象时的差异。笔者搜集到的关于罗斯金的传记文本基本可以分为标准传记和现代传记两类,标准传记对传主人生的叙述较为详细、客观,而现代传记则是传记作者借助材料论证出的传主形象。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关注视角更多受到作者个人知识背景的影响,在塑造传主形象方面不再完全遵守标准传记的写作方式,“生平、个性和解释是传记构成中的三个要素,解释则是现代传记的主要追求。”[14]4现代传记不再强调对传主人生的简单叙述,它成为对传主思想或历史事件研究的一种范式。由安德鲁·巴兰坦所作的传记《约翰·罗斯金》和苏珊·法根斯·库珀的《模范妻子:艾菲·格蕾、罗斯金和米莱斯的激情人生》就是典型的现代传记,传主的人生在这类传记作品中不再成为重点,传记家的关注也偏向于自我对传主思想的研究,比如作为大批评家的典型形象、伟大艺术家的“三角恋”关系,等等。对于罗斯金的大批评家形象,他传作者重点参考了罗斯金的代表性专著《现代画家》系列,《建筑七明灯》《威尼斯之石》等作品的创作历程,更加强调的是对其中提出的艺术理念的论证,诸如“如画” “情感误置” “哥特艺术”等艺术理论术语的进一步阐发。现代传记的作者更多只是在借传记的文体形式论述自己对传主较感兴趣的方面,这依然可以为我们展示出传主的典型形象,且在表现传主的艺术评论家形象方面更具深度。
标准传记较为详实的整合关于传主人生各阶段的各类材料,力图客观、公正地展示传主的真实形象。相较于现代传记,它虽然没有明显塑造某种典型形象的倾向,但我们依然需要注意到作者在选择材料时潜在的意识。比如在《约翰·罗斯金的一生》中,阐述罗斯金婚姻的内容就非常少,主要随着传主人生时间轴线的发展结合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简短的叙述。这无疑表现出一种立场,即传主的这段婚姻经历在整个人生阶段是无足轻重的。各类传记电影特意从这段婚姻中截取出的罗斯金形象显然具有片面性,意欲表达的那三个主题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宣告。有学者认为,“在罗斯金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幻想和审美的天性以及严格的、清教徒式的教养强加给他的压抑之间徘徊。”[15]通过阅读各类罗斯金传记,尤其是他的自传《往昔》,这个问题的确很明显地贯穿于他的各个选择之间,同时,他频繁地否定过往岁月的一些做法更是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注意,不同传记文本在表述同一历史史实时的差异。罗斯金在他的《往昔》中仅有一处提及妻子艾菲,“在圣马丁堡,我们离开父母后,因为我准备去夏蒙尼峰和采尔马特进行地质研究,我的妻子严重警告我:我是一只冷血动物”[9]419-420,自传中的这句叙述只是罗斯金在旅行途中一句简单的表述,并未进行其他任何解读,现代传记的作者则对这句话进行了多重解读,他们认为艾菲完全无法理解写作对罗斯金而言的重要性,也完全不懂创作需要的孤独和专注。“罗斯金的这种行为与艾菲所说的自私完全不同,她无法理解他给我们最大的遗赠正是他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对罗斯金来说也一样),这是他生命的意义。”[10]117作者以罗斯金的创作冲动为出发点,回应艾菲对罗斯金的评价,并将罗斯金预设为伟大艺术理论家的身份,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罗斯金与艾菲之间的本质差异,证实一位普通女性和伟大艺术家之间的对立。在以艾菲为传主的传记中则认为:“约翰狂热的继续学习,艾菲尽力的紧随其后。但约翰无法理解她对此的疲倦、无聊、焦虑,甚至是因此流泪。”[11]50通过这种简单的比较,两人之间的志趣差异很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他们之间短暂婚姻结束的更本质原因。
在笔者上述几部关于罗斯金的影视剧中,仅有《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这部作品中的叙述相对真实、客观,情节也较为完整,并没有明显对电影中某一形象进行绝对的单面塑造。这部6集电视剧主要以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奋斗为核心,罗斯金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在一定意义而言也是作为一种“形象的他者”,但他的存在并非纯粹作为一种对立或烘托的意义,更强调的是一种参与。虽然拉斐尔前派运动并不是受到罗斯金思想的启发,但他对他们后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拉斐尔前派发展的前三年是属于他们自身的,但接下来的三年实际上是属于罗斯金的。”[1]87影片明确了罗斯金作为伟大艺术批评家的形象,但也描绘出家庭中的罗斯金绝对服从于父母的软弱形象;米莱斯也并不像《爱情学院》,尤其是《艾菲·格蕾》中塑造的不论品格还是外在形象都十分的节制、完美,通过贪图广告费、不顾模特生命安危将他的贪婪、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艾菲也不再是各类电影中古典、柔弱、凄凉的弱者形象,将她流连于各类社交圈、拜金,甚至与不同人的暧昧也隐讳地表达了出来。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都通过较为客观的立场进行塑造,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相对公正,虽然也重点关注了罗斯金的那段“丑闻”,但叙述立场却没有明显偏颇。
通过综合比较罗斯金的自传及各类他传,我们或许可以明晰传主的形象并非简单的单面形象。我们必须要审慎地认识《艾菲·格蕾》和《透纳先生》中片面塑造出的罗斯金形象,尤其要注意结合罗斯金的杰出思想对人类认知自然的推动。虽然无论自传还是他传都难以绝对脱离传记作者的某种视角,但传记文本对传主形象的塑造基本都是通过众多历史事件及人生选择的梳理,并没有直接向我们展示出作者观念中的传主形象,我们可以从阅读过程中认识到符合历史真实的传主形象。笔者在这里并不反对传记电影对艺术家传主形象的“再造”,并认为电影艺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也是一种创作范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应该更加有益于我们理解艺术、认识事件,即使需要通过设置某种距离以增加陌生化效果,也不应该对历史史实进行无端捏造,甚至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变相“攻击”。对于众多历史语境中的艺术家影像,基本鲜有影视剧传达出的单面形象,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历史以实现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