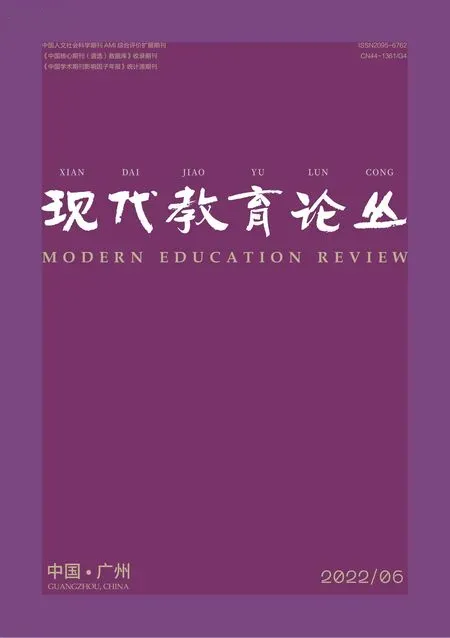学生全球流动是重塑人类共同未来的重要想象
——评《全球化时代学生流动能力研究》
2023-01-24汪卫平
汪卫平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202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第41 届大会上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乃至2050年的教育。报告提出:“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这一契约源于一种共享愿景,即教育具有公共目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能够将人类联合起来,通过集体努力,提供所需的知识和创新,帮助我们塑造面向所有人的可持续和和平的未来,维护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
作为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塑造全球教育共识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全球领域的流动能够帮助人类在面对未来诸多不确定情境中构建共同的认识和目标。虽然,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在前期的确重挫全球学生的跨国或跨区之间的交流,但随着各国政府有力措施的实施,学生的全球流动正在逐渐恢复。毫不夸张地可以比喻,在疫情危机频仍、疫苗研发与病毒变种赛跑的形势下,跨文化争端在逐渐消磨人类共识和合作动力的情况下,全球范围内学生海外学习与交流是当下除了跨国贸易外最重要的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接触的主要形式。
虽然学生全球流动和海外学习经历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不能归类为新近的主题,但基于中国本土情境考察大学生全球流动能力以及宏观层面政府、高校的配套政策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推及到更广泛层面,与本科生海外学习、跨文化交流、全球流动的相关中文研究十分匮乏,一些零散的学术论文也缺乏一定的系统和理论建构的贡献。欣慰的是,深耕于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杨启光教授,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对相关领域文献和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进而写作出了《全球化时代学生流动能力研究》。一本能够及时回应当前理论界对学生全球流动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呼唤,在实践领域有力地回应了全球化时代和面向2050 人类重塑教育社会契约的努力方向的前沿专著。
在文章结构编排上,作者的独具匠心与严密逻辑的组织使得读者可以对学生跨国流动主题有更全貌的了解。在导言部分,作者介绍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内涵、风险挑战以及纵深发展的战略。第一章,作者从全球化、学生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读者展示了学生跨文化流动的背景主题。第二章,作者努力地向读者呈现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从而铺垫好了本研究试图着眼的突破方向。在第三章与第四章,作者敏锐捕捉到了学生全球流动的不公平问题以及流动争议的理想目标。在第五章,研究者尝试构建了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学生全球流动能力的框架指标与内在结构。在第六章,研究者将视角转向了现实部分,基于丰富的学生样本调查数据,研究者描摹出当前国内学生全球流动能力的问题与改进建议。在对中国本土进行考察后,研究者在第七章基于全球比较的视角,综述了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俄罗斯、葡萄牙等主流国家学生跨国流动的现状及相应政策。在第八章,作者考察了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是如何支持学生跨国流动,尤为珍贵的是作者还呈现了新中国70年以来学生全球流动政策的变迁。而在第九章,作者则从院校研究的视角指出学校在推动学生全球流动的应为与可为,并以国际留学市场最具代表的澳洲高校进行案例分析。在第十章,作者又将读者从微观的前述研究中抽离出来,转而去直面学生全球流动的伦理问题及其指导框架。最后,在结语部分,作者向大家展示了推动学生全球流动的前景,扩大学生参与、坚持全球开放信念、建设命运共同体等。
正如作者本人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迈向“纵深发展时代”,一个有关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正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研究者并不拘泥于已有研究仅仅关注海外学习不平等的个体层面,而是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试图挖掘全球化时代交织在个体与宏观机构多重因素下的流动不平等。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理论上的演进,基于罗尔斯正义论和比较教育学“空间正义”的视角,建构出基于“流动正义”的学生全球流动能力框架。至此,作者对学生全球流动能力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抱负开始真正地展露出来,并且还具有弥合理论与实证的理论雄心。建立在前文构建的能力框架,他通过对全国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学生的调查,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学生全球流动能力的自画像。这种数值上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纷繁复杂的学生跨国或地区流动下的认知、行为、情感,甚至是流动收获的结果等维度的现状。
更让人惊喜的是,研究者似乎从来就不会给人留下读罢就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实证部分之后的论述更是让读者对该主题的认识和思维有进一步的升华,而这是当前教育学领域实证研究很难做到的。他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出了域外的实例,以政府支持的政策工具将个体的学习选择与宏大的政治叙事相结合,基于增能赋权理论的“个体增能”视角介绍了高校层面如何激发学生的流动能力和获得,基于流动伦理的视角将跨文化交流和接触送到了道德和伦理层面。种种逻辑严密和思维衔接的章节设计,将学生全球流动能力研究真正做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尤其是,“个体增能的视角”也支持克缇加斯特(Kortegast)等人研究的结论,“海外经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学生的学习成果,只有为学生提供结构性机会的分享平台,才能让学生真正获益”。
人们曾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的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巴别塔,来比喻全球化时代人类共识对于社会秩序和规则的重要性。诚然,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流是否能够真正带来共识的建构和重塑依然存在争议,但就算是《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作者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也无法否认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学生跨文化接触与交流对共识重塑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跨文化交流往往强化国家认同,加深人们之间的差异意识,激发相互的恐惧,而不是培养共同社区意识”,然而谁又能够否认高等教育全球学生流动不是促进了教育社会契约和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建构呢? 或是,谁又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促成这种契约的达成呢? 毫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全球流动是重塑人类共同未来的重要想象。而这也更呼吁未来有更多研究像该本专著一样持续聚焦学生全球流动、跨文化交流、海外学习等经历。新冠疫情对全球社会跨文化理解和认同的撕裂效应似乎并没有随着疫情减弱而有所减弱。但我们好像能够期待学生跨国流动,能为促进全球理解的融冰之旅提供稳定的动力与更有启发和创意的解决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