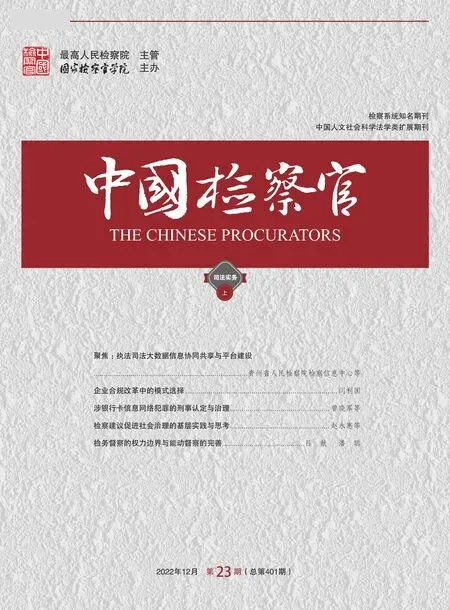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的界定
2023-01-23周力/文
● 周 力/文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意指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违反民法规范的同时,亦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情形。在此意义上,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包括两种类型:违反知识产权民法规范的同时又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案件、虽然违反民法规范但是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存在疑问的案件。前种事案无疑属于典型的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至于后者,尽管经过最后的评判可能认定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属于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范畴。之所以得出该种结论,是因为其行为本身具有构成犯罪的表象,且得出不构成犯罪结论的过程中亦需适用刑法对该种行为作出刑法评判,故亦具有刑民交叉的性质。
一、界定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的意义
民法与刑法都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相应规定,但民法与刑法的使命、规范范畴及规制方式等存在显著差异,对当事人的影响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均有所不同,故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应注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边界的探寻、突出知识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
首先,民法与刑法规范目的不同。“刑事责任同民事责任各有其目的,前者在于对行为予以报应,并防止将来侵害的发生,后者在于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平复过于侵害的结果”。[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其次,民法与刑法的规制范畴存在差异。民法以普通民事违法行为为规制对象,但刑法却以犯罪为规制范畴。具体到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普通危害性的民事侵权行为由民法规制,但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则必须由刑法规制。再次,民法与刑法的规制方式不同。民法以令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等民事责任作为规制方式,而刑法却以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规制方式。相对于民法法律责较为温和的规制方式,刑事责任以刑罚为主要内容。最后,刑法与民法的法律后果不同。作为民事违法的后果,民事责任主要以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调整为主要方式,当事人意志在民事责任的追究中往往占据重要地位,例如是否追究民事责任有赖于当事人一方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才能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并且在民事诉讼中,只要不违背国家强制性规定,原告可以撤诉、原被告亦可自由达成和解。与此相对,刑法的法律后果以追究刑事责任为主要内容,法院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人依法适用刑罚。刑事责任相对于其他法律责任的关键区别在于,其具有处罚的严厉性与超强的强制性,不仅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以剥夺人身权利为内容,死刑甚至以剥夺生命为内容。
由此可见,合理划定犯罪圈大小,把握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对于平衡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创新发展两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既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惩治力度,有效阻遏侵权行为,又要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制度限制公平竞争,有效规范市场秩序。此外,界定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对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界定的疑问
鉴于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过程中无疑应注重探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然而,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复杂性致使案件在罪与非罪的界定上存在诸多争议。
(一)侵犯知识产权危害行为的判断存疑
众所周知,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犯罪行为的确定,是判定犯罪成立的前提。若能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体条文中的危害行为作出科学解析,无疑有助于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法条文的罪状描述虽然整体上较为明确,但是部分条文中危害行为的内涵解读及司法认定通常存在疑问。第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部分危害行为的描述过于简洁,如何正确解读及认定存在疑问。以刑法第216条所规定的假冒专利罪为例,其对危害行为仅仅描述为“假冒他人专利”,但是何为假冒他人专利没有具体明确,例如,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标注他人的专利号,是否属于“假冒他人专利”?又如,将所销售产品上的某种专利号换成他种专利号,是否属于“假冒他人专利”?第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危害行为的范畴划定存在疑问,即侵犯知识产权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包含何种具体范畴,部分场合难以认定。例如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是否所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都属于该种行为范畴存在疑问。第三,侵犯知识产权部分行为要素的理解和认定存在疑问。例如刑法第217条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包含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许可”等要素,2008年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26指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指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或者伪造、涂改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的情形,但是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涂改了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文件并达到法定数量(数额)标准便一律认定构成犯罪显属不当。
(二)侵犯知识产权危害后果的认定存疑
鉴于刑法以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规制对象,故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条文往往对危害后果作出限定,只有“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数额较大”的,才具有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尽管司法解释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条文中作为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违法数额较大”等作出了较为明细的规定,但是在具体案件的“销售金额”“直接经济损失”“非法经营数额”等认定上还存在不少疑问,而且包含了“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兜底性规定,何为“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往往存在争议。
三、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犯罪边界的具体探寻
司法实践中,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判决无罪,甚至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一审被判决有罪,二审甚至再审又推翻有罪判决宣告无罪。或者相反,有些案件一审宣告无罪,经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或者再审又被认定有罪。该种犯罪评判结论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一方面表明了部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界定确实存在疑问。另一方面,包含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若不注重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则会导致犯罪判定结论的疑问与混乱。这不仅会对涉案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并且也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严肃性、公正性。针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考量。
(一)重视挖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法条文的实质处罚理由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的划定,固然应以刑法条文的表述为根据,同时适用司法解释的办案标准。但是,检察机关若仅拘泥于刑法条文的形式化表述,忽视犯罪处罚实质理由的考量,则会导致犯罪边界的划分存在疑问。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之所以被列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在于其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的现实而紧迫的实质危险。尽管司法实践中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通常对法益造成了一定侵害,但是通常并不等于必然,也并不一定达到实质危险的程度。若特定行为人侵入信息管理系统非法获取某商业秘密,单纯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并且随后将其删除,并不存在刑法上值得处罚的理由与根据,因此不能成立犯罪。可见,“司法机关应当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即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2]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过程中,应坚持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不可对刑法条文作过于字面的形式化解读,因为“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是形式的,形式的解释没有任何意义”[3]张明楷:《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实质解释倡导在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以行为具有的实质法益侵害危险或者社会危害程度作为评判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准。也即,只有具有“值得处罚的违法性”[4][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才具有构成犯罪的可能性。
(二)探寻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应贯彻刑法谦抑性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通常存在犯罪成否的争论,还涉及到刑民交叉案件的谦抑性问题。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实务中,忽视知识产权民法规范基础的现象较为常见。有见解即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既是立法原理,也是指导司法工作人员解释刑法、适用刑法的原理,但它不是处理个案的规则”[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48页。。但是,既然承认谦抑性也是适用刑法的原理,那么它无疑也是处理个案的规则。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的划定,除了需遵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之外,刑法谦抑性的贯彻亦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个案犯罪成否的争议表明了犯罪判定的复杂性。部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往往存在争议甚至难以下结论。在此状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中行使审查起诉职能的专门机关,应坚持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案件过滤作用,审慎评判。只有在确认通过民法等基本法律规范无法作出有效规制的场合,才具有认定成立犯罪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此,检察机关应深入研析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同时加大对同类事案的分析和研判,以实现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把握的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