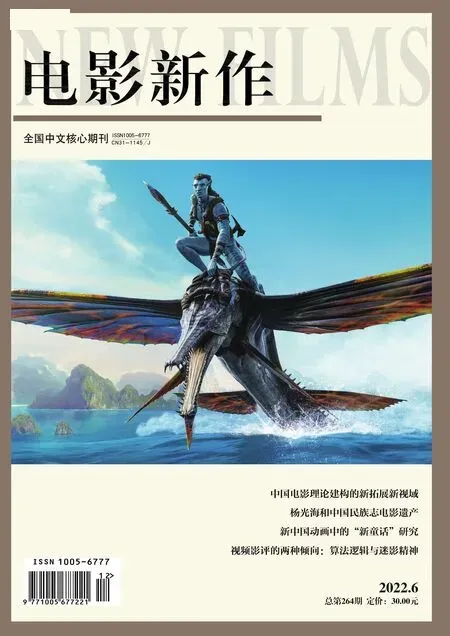被复兴的吸引力与数字影像实践
2023-01-21杨天东
杨天东 王 婷
“吸 引 力”的 概 念 最 早可追溯至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对戏剧的分析。在爱森斯坦看来,戏剧应该由一些吸引力蒙太奇组成,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沉迷在“幻觉叙述”中的观众关系。吸引力就是要让观众臣服于“情感上或心理上的冲击”,要“点燃”观众,撩拨观众的感官。早期电影研究学者汤姆·冈宁(Tom Gunning)深入挖掘了电影的这一机制,将其概括为“惊诧美学”。彼时的电影与杂技、魔术等表演被看作同一战线的流行物。电影破坏了现实生活的“静止”状态,运动影像以前所未有的逼真性与写实性为观众献上了最震惊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最原始的、强调速度的、直接的运动冲击力形构了该机制,使其始终发挥效力,“被火车吓得四下狂窜”的传言也由此让众人信服。简而言之,奇观令吸引力美学在早期电影中得以施展魅力,在惊诧中点燃观众,使幻象在观看中实现与心理的缝合。这是“吸引力电影”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电影历史,与电影的整体历史一样,已经以叙事电影为主导进行了书写和理论处理。1然而,吸引力电影与叙事电影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以主导性的在场彰示了某方的相对胜利。汤姆·冈宁认为,吸引力电影与叙事电影意味着不同的电影讲述模式,从电影出现伊始到1906年,吸引力电影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到1913年,吸引力电影与叙事电影开始角力,叙事电影逐渐大放异彩,而叙事也成为电影讲述的典范。从早期以技术革新为核心的吸引力电影,向以成熟的电影语言为核心的叙事性电影的转变,是电影从懵懂走向成熟的过程,电影史维度的叙事性霸权亦因此建立。不过,吸引力电影并未被不断宣示主权的叙事化所俘虏,而是转入电影的另一重讲述模式:以先锋派的姿态再次证明了奇观的魔力,同时也潜入叙事电影中,作为某种成分得以呈现,这被汤姆·冈宁称为“被驯化的吸引力”。2在汤姆·冈宁的论述基础上,弗兰克·凯斯勒(Frank Kessle)追蹑电影发展的脚步,将这两种讲述模式概括为“叙事整合电影”与“吸引展示电影”3,进一步深化了两者的复杂内涵。在此后的电影发展进程中,伴随着从短片到长片的流变、声音及色彩等元素的出现,吸引力与叙事在彼此的竞争与融合中相处。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自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引领了全球数字电影风潮,进而重新将吸引力电影拉回到电影产业与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这是一种由数字技术所构筑的奇观,被称作“斯皮尔伯格—卢卡斯—科波拉电影效应”。420世纪90年代以后及至21世纪的数字电影时代,以灾难片、科幻片、怪兽片为代表的好莱坞视效大片更是以“感官刺激压倒了叙事,声音压倒了影像,娱乐压倒信息”。5由此,照相写实主义时代影像的认识论价值被“拟像”的奇观所取代,吸引力在“后电影”时代迎来了复兴。
在新媒体、新平台兴起并主导运动影像生产与传播的当下,“后电影”的概念指向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表征的数字运动影像,它们以各种屏幕为载体肆意流转,对传统的影院电影电影形成挑战。“后电影”的具体形态,既包括由计算机图形技术、游戏引擎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生成的数字电影,也包括由各种新媒介技术生产、流媒体技术传播、具有强交互性的影像,比如VR电影、游戏电影、互动电影、交互式纪录片、弹幕电影,等等。6总之,“后电影”一改传统的媒介特性的固执,转而支持一种“泛影像”的观念,其逻辑在于:当一切媒介形式的生产和流通都服膺数字技术(都是由计算机生产、互联网传播);当银幕失去了“灵韵”,不再优先于各种自发光的屏幕,媒介间性的意义便已丧失。无论我们是否乐于接受电影汇入影像的汪洋之流,数字技术的“抹平”效应正在我们眼前发生。
被复兴和强化的吸引力携带着新的技术参数与变量塑型着电影的模样,赋予了电影新的解释空间。法兰西斯科·卡塞提(Francesco Casetti)指出:“电影一直是灵活的‘机器’,对于各种革新改良采取开放态度,同时专注于自身的平衡状态。整部电影发展史,都在挑战电影部署,不断把新元素引入,以及不断实验新的可能性。”7也正是在持续的装配与重置下,电影一直面临对自我的审视、怀疑和确认,在“不再是电影”与“又再是电影”中游走、徘徊与调适。对此,法兰西斯科·卡塞提给出了一种解释:“电影在调适的过程中,总是会遭遇某种惯性。当电影的特性发生变化时,它倾向于吸收差异,或至少把这差异归于‘其他类’电影,而这些‘其他类电影’仍旧是‘电影’。”8于是,电影一直面临着终结的危险,却从不曾终结。在数字技术无处无在的时代,吸引力美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又一次呼应了人们的心灵渴求,揭示了电影的当下面貌。凭借数字吸引力的百变造型,数字影像持续地回应着当代人的心灵扩张。
一、告别绿幕,开启虚拟制作
2009年,《阿凡达》(Avatar)横空出世,震撼的视觉冲击力令此前标榜视觉特效的影片黯然失色。《阿凡达》作为电影制作技术的革命性成果,首次使用了V R、A R等虚拟制作技术,掀开了电影虚拟制作(Virtual Production)的历史。《阿凡达》中令人惊艳的视觉特效使电影业内人士与观众意识到虚拟制作的魅惑与强大。之后,在数字技术的不断赋能下,虚拟制作持续推进。2019年,迪士尼原创剧集《曼达洛人》(The Mandalorian)上线,虚拟制作又一次受到广泛性关注。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的电影业陷入危机,“虚拟”作为一种方法成为2020年以来电影业的关键词。也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越来越多的电影选择这一制作模式,继而推动了虚拟制作的脚步。随着技术的介入,虚拟制作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调整与变动。它是指一种虚拟场景与现实制片相结合的制作方式。具体而言,它是“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与CGI和游戏引擎技术相结合,使制作人员能够看到场景在他们面前展开,仿佛这些场景就是实景合成和拍摄的”9,即“所拍即所见,所见即所得”。
从技术层面而言,虚拟制作可大致划分为表演捕捉、电影视觉化技术、混合虚拟制作和实时LED墙四种类型。表演捕捉是一种主要应用于动画电影的2D转描机技术,捕捉片中演员的面部表情,将之套用在其他角色上,如《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2019)和《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2011)等影片便是这一技术的典型代表。电影视觉化技术是指在进入规模化制作前,对部分镜头或全部镜头进行可视化呈现,分析并探索故事的创意,以便于测试后续的技术实操性。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如今的电影视觉化技术已不再限于前期的使用,包括视效预览、技术预览、特技预览、虚拟采景、后期预览等都已运用这一技术,如《疾速追杀3》(John Wick: Chapter 3 - Parabellum,2019)中玻璃办公室的场景便通过虚拟采景完成。混合虚拟制作,顾名思义,强调一种“混合”的功效,指的是通过摄影机的实时追踪,将绿幕前的摄影元素与CG元素合成,这一合成可以方便摄影师进行实时预览,也可在后期环节中进一步完善。混合虚拟制作分为实时制作与后期制作两种类型。前者的功效类似于“虚拟演播室技术”,常用于体育、新闻等节目;后者方便后期视效的制作与合成,如《奇幻森林》(The Jungle Book,2016)在拍摄绿幕时仍保留了传统的制作方式,“演员在幕前表演,只有部分或者几乎没有实物背景和真实对手。后期制作类型的虚拟制片可使用摄像机跟踪数据为镜头内实时合成图像提供依据,实时合成使用代理分辨率”。10混合虚拟制作技术确有开拓性意义,不过仍存有绿幕溢色等环境画面的问题。由此,实时LED墙出现了。作为时下最为先进的技术,它比绿幕更胜一筹,解决了绿幕溢出的问题,并呈现出高精度的影像,演员可以更加自然地进行表演,摄影师的取景工作也更加顺利,避免了此前绿幕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曼达洛人》就充分使用了这一制作方式,“将传统的电影制作工具与LED幕墙、虚拟现实和游戏引擎等新兴技术相结合,通过将游戏引擎实时渲染生成的画面显示在LED幕墙上的方式,将演员表演和现场搭建的场景与实时渲染生成的画面相结合,得到近乎真实的场景动态照明和环境光效果,并且在拍摄现场直接得到摄影机机内合成的高质量画面”。11
总而言之,与传统的制作方式不同,虚拟制作的优势便是“后期前置”,制作思维从“留待后期解决”转向“在制作中解决”,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在传统的制作方式中,各部门和各环节相对孤立,最终效果得不到保证,后期的修改往往代价高昂。虚拟制作则使各部门与环节的关系更加紧密,推进了制作进程的协作化、高效化与非线性,从而使电影创作更加专注于想象力与创造力,提高制作效率与效果。当然,这种制作方式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比如,《曼达洛人》在制作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一个虚拟艺术部门,这一部门包括摄影指导、视觉特效指导、布景设计师、游戏产业的美术设计师、模型师等人员,他们会根据视觉预览,讨论动画模拟所呈现出来的灯光、运镜、布景等问题。这些工作在传统的电影制作流程中并不会出现。所以,这对电影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人文艺术的思维,进行知识的更新,以满意电影工业发展日益数字化、技术化的要求。
追随电影工业整体的蓬勃态势,国内虚拟制作技术的发展亦令人惊喜。作为国产电影中第一次完整使用虚拟制作技术的影片,《刺杀小说家》(2021)标识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重要节点。影片通过“数据及信息收集”“动作捕捉与虚拟拍摄”“现场拍摄与虚实结合拍摄”以及“后期视效制作”四个模块12,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虚拟制作流程,拓展了虚拟制作的本土化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有效地应用于《外太空的莫扎特》(2022)、《独行月球》(2022)等影片中,推动了虚拟制作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建构。
二、观察者的技术:被扩延的类型与被扩增的影像
在愈加被强化的技术之外,媒介融合或融合文化12下的电影扩张持续性地释放出吸引力的多重层次。这一扩张以游戏电影、互动电影、VR电影、弹幕电影、桌面电影等众多互动影像为代表,提醒着电影的再次部署与装配。某种意义上,影像的互动性返归了叙事的原点。人类在古代说故事时,通常是根据听者的反应适时调整和变化说故事的方式、内容及长短。从电影出现后,这种双向互动的叙事以一种不容辩驳的姿态被打破,就像鲍里斯·格洛伊斯所指出的,“在不同媒介互相对抗的漫长历史中,电影当之无愧地成为世俗化现代性的标志”,然而,当电影从新领域转为传统领域后,“它本身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偶像破坏姿态的打击对象”。14这种破坏的策略包括录像、电视、电脑、DVD等新技术的介入,还有影像内部的破坏。伴随数字技术的日益深入,不断革新的互动影像一再彰显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偶像破坏的互动性策略大约始于1967年的《自动电影》(Clovek a jeho dum,又名《一个男人和他的房间》)。这部由捷克导演拉杜兹·辛西拉(Radúz Cincera)创作的剧院式互动电影描摹了该类型的雏形。在这部剧情片中,每当一本胶卷放映至尾端,银幕会停在分隔的画面,此时角色会走上舞台,向观众征求剧情的发展方向,多数观众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会直接影响剧情的走向,也就是——下个胶卷的选择。很明显,稚嫩的《自动电影》获得并复兴了叙事的原本意义。此后,以光盘为存储介质的互动影像也曾一度受到欢迎。但是,它普遍地走进大众视野则是近年来的事,《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2018)是重要的分水岭。有了《黑镜》系列的珠玉在前,2018年的剧场版《黑镜:潘达斯奈基》以互动的面貌与观众见面。在十秒钟为他人的命运做出每个选择的新体验里,该片真正开启了互动电影的元年。也是在同年,索尼公司推出了《底特律:成为人类》(Kara),主角由真人出演,讲述了AI女机器人卡拉的故事。两部作品分别呈现出宛若游戏与宛若电影之感,模糊了电影与游戏的界限。
在此之前,尽管电影与游戏的互相借鉴并不鲜见,不过大多仍旧停留在改编的层次,真正将互动的概念成功引入影视的作品还是少有的。传统影院的观看方式是基于一对多的关系,而游戏则是一对一的互动,因此,《自动电影》在当时无法被推广与普及。流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私人观影的方式建立了一对一的互动基础,在成熟的技术介入与各种设置的完善下,用户可以通过触屏、鼠标、遥控器等来控制剧情的走向、进度的快慢、人物的选择、最后的结局等。其中的叙事线复杂交织,重重“分叉选择”的设置同构了这一复杂性,将更多的自主权交付于用户,鼓励他们不断探索其他情节和结局。值得思考的还有互动电影中“我”的位置。无论技术再发达,故事再复杂,终究不得不面临对“我”的追问。《黑镜:潘达斯奈基》的成功不仅在于成熟的互动体验与具有吸引力的故事,还在于它激发了用户对自身主体性和自我意志的思索。当影片中斯蒂芬发出“究竟是谁在控制我?拜托,真有人的话,给我个讯号好不好?”的质问与“分叉选择”同时出现时,便将斯蒂芬与影片外的“我”连接起来,提示了自我的觉醒。
在交互性的意义上,互动的另一面是沉浸感,与之亲密的虚拟现实与VR电影登堂入室,走进历史的舞台。当虚拟与现实相遇,意思似乎相悖的两个词会发生怎样的奇妙反应?法国戏剧家翁托南·阿铎(Antonin Artaud)在《剧场及其复象》(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2010)中提出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概念,并指出“精神的复象,可以帮助观众、参与者进入另一种精神的世界内”。15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虚拟现实逐渐更具实操性,沉浸感亦如梦如幻。作为技术性的产物,电影与虚拟现实的结合在近年大放光芒。2016年是VR元年,IT行业纷纷试水,宣布了多个有关VR技术的项目,而一向对沉浸感不懈追求的电影工业也开始与VR紧密联结,提供了一种新的影像形式,再次叩问了影像的本质。
在《观察者的技术》(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2017)中,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认为,19世纪的观看与传统观看出现断裂,原因在于从“暗箱”到“立体视镜”的变化,这一过程引发的沉浸性给予了虚拟现实的效果。16经过立体视镜、3D等技术,如今VR技术将这种沉浸感持续扩增,产生主观性的在场,使得“我看故我在”成为可能。更为关键的是,VR技术消解了传统电影的边框,身体作为中介成为观看与被观看的中心,物理性距离由此消失,成为“感知的创造性替身”。17在这个意义上,VR电影愈加趋向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是对电影真实的再次定义。
无论是观看方式还是观看内容,V R电影都是对影像的“谋反”。2016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曾与美国企业VRC合作项目“专注VR”,表现出对VR技术的兴趣。2018年,由他执导的电影《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观影热潮。《头号玩家》在制作理念上与VR技术高度相关,也预示着VR时代的全面抵达。不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VR的看法带着些许警惕。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项被称为虚拟现实的危险媒介”,“我之所以认为它危险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赋予观众许多新的观看空间,不再遵从说故事的人的指示,观众可以选择自己要看哪里”。18与互动电影的性质相似,说故事的主体不再唯一。对于电影,VR技术的介入同样是一项偶像破坏的行为。在传统的电影观看中,观众在观看时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而使画框消失的VR电影制造了更多的观看空间,观众可以任意选取观看的视角和内容。2017年,首部华语VR电影长片《家在兰若寺》由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执导完成,并入围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R单元的最佳VR电影。《家在兰若寺》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和视域,不同于刺激惊险的VR印象,接续了蔡明亮一贯以来的“凝视”特质。当戴上VR眼镜的那刻,观众便进入熟悉的蔡式长镜头中,去到电影中的任何角落,极致地感受另一种人生。在谈到执导该片过程时,蔡明亮表示:“VR的特性很好玩,就是单纯为了一个观众而生,观众可以选择看场景,也可以选择看演员。因此,这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大挑战,片中女主角尹馨就认为,拍摄VR电影时的表演难度更高,没有固定的镜头可以看,要让自己直接成为空间的一部分,这也会比较类似剧场的表演方式。”19恰是这样的特性,影像谋反了特有的所指与单一叙事,建构了独立的影像美学。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VR单元中,《家在兰若寺》作为展映影片出现,此时的影片已从4K升级为8K,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8K立体声影片,细腻可感的画质使沉浸感得以扩增。
新技术步履匆匆,姿势纷繁,VR电影也在经历持续的变化。2022年7月,纪录片《我们在虚拟现实中相遇》(We Met in Virtual Reality,2022)在HBO播出。整部影片在VRChat上拍摄制作,讲述了五个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彼此联系以及与外界交往的故事,复现了虚拟世界中的爱情与友情。VRChat是一个虚拟现实的社交平台,用户可以用自己定义的虚拟角色来搭建个人的虚拟世界。因此,充分发挥了元宇宙概念的《我们在虚拟现实中相遇》也被认为是全球首部元宇宙纪录片。某种意义上,新冠疫情的肆虐令虚拟现实的概念得以广泛传播与实践。影片中动漫式的虚拟人物与真实的情感呈现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映,又一次昭示了吸引力的美学特质,导演完全使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是直接电影与VR的一次结合,将席卷全球的元宇宙世界影像化,展示了虚拟世界的情感与生活。
三、流媒体与数字传播语境
数字技术获得了神奇的在场和实践感,解构了传统的媒介格局、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生存方式,建立了新的秩序,应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那句名言——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乃是一种解蔽方式。20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进一步强调,“媒介不仅仅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而且‘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媒介非表意,媒介即存有;媒介是人的‘存有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21置身“万物媒介化”的时代,电影的生态亦因应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媒介为电影制造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观看路径。这一实践既存在技术层面,也包含文本建构的层面。只有在开放的解读空间中,我们方能从宏观地、多层面地端视与领略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传播语境。
2022年9月,西班 牙《先锋报》刊文称,伍迪·艾伦(Woody Allen)完成正在拍摄的电影后,就正式退休,不再拍电影。随后,伍迪·艾伦发布声明——自己并非宣布退休,而是考虑要停止拍摄电影,因为拍摄一部用不了多久就会登上流媒体的电影,对他来说并不那么享受,他是一位死忠的电影院信徒。22这样一种抵抗的姿态来自于新技术与新媒介的普及和传播。有意味的是,拥抱新技术与新媒介同样寄予了对电影的某种忠诚。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曾说,之于电影艺术,流媒体是比声音更大的革命。2019年,由他执导的电影《爱尔兰人》(The Irishman,2019)选择在大银幕与Netflix平台同时上映,再次掀起一场关于“影院派”与“沙发派”的对峙。当年,Netflix在一部分安卓手机用户中测试了包括倍速播放在内的功能,遭到众多好莱坞从业者的抵制。于是,那个持续的追问再次登场,即:流媒体是否正在杀死电影,当电影彻底拥抱流媒体,是否意味着电影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终结。
电影的历史揭示:新媒介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怀疑。流媒体在较长的时间内不被传统电影从业者信任。与电影院的典范地位不同,流媒体意味着某种边缘、不专业与不正统,很难在电影生产的过程中获得认可。以成立于1997年的Netflix为例,从最初的DVD租赁业务到后来的视频点播平台,其发展规模始终受到限制。其声名鹊起始于2013年,一直游走于产业链下游的Netflix试图向上游发展,开始介入内容生产环节,打造了系列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2013)。随着《纸牌屋》的全球热播,Netflix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此后,它开始自制电影,并采用了网院同步发行的新模式。Netflix不走寻常路的操作自然遭到了不小的抵制:当“蛋糕”被“他者”分走,无论是院线从业人员还是电影出品公司,都感到了莫大的危机。如果说2020年之前,业内相关利益方对Netflix的态度仍有保留,传统的影院派与流媒体之间势均力敌,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作为一个契机打破了这一态势。根据数据显示,2019年,在全球电影市场中,院线市场第一次不敌流媒体的数字发行,但两者之间的比例相对平衡。2020年,流媒体以绝对强势的姿态对院线形成威胁。根据Conviva最新公布的报告《串流媒体现状季报》显示,2022年第二季全球流媒体市场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与2021年第二季相较,收益率为14%。23与此同时,像Disney+、Amazon Prime Video、Apple TV+、爱奇艺、friDay影音、catchplay等流媒体都直接提供数字用户线上媒体服务。可见,世界范围内的流媒体已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于主流话语体系中摆出更具声量的姿态。
不应忽略的是,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还是80年代的录像机,原本的市场对新媒体通常从最初的敌对姿势走向和解。这种“化敌为友”的过程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循环。于是,我们看到,在角力的过程中,流媒体逐渐被主流电影界接纳和认可,2017年,由Netflix出品的《玉子》(Okja,2017)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2019年,Netflix投资的《罗马》(Roma,2018)收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三个奖项。2022年,在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由Apple TV+出品的《健听女孩》(CODA,2021)获得最佳影片,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流媒体电影,这历史性的一刻标志着主流话语对流媒体的敞开与认可。
流媒体的转型,在美学、产业、文化等诸多方面改写了传统的电影生产与消费模式。24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先进的流播技术,流媒体培育了新型的互联网电影观众。比如,流媒体的倍速播放与慢速播放、只看Ta、发送弹幕等模式,使得流媒体的观看超越了图像观看,进入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由此,用户的观看行为本身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性。如果说传统的影院电影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流媒体的文化则是私人化的、趣缘性的。对电影的理解,需要更多地关注观看实践的变化,并由此提出数字时代的新的电影本体理论。由此,对流媒体美学和文化的深入考察,可以打开对数字时代电影的多面理解。
结语
作为技术与艺术、产业与文化、逼真与假定、造型与运动等特征的复合载体,电影发展至今已然被赋予了多重本体性指认。时至今日,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裂变更为电影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参照。某种意义上讲,数字技术的成熟重构了电影的内涵,也再造了电影的生成、传播与接受语境。“后电影”时代,电影成为“总体屏幕”的一部分,在众多装置、多媒体与艺术创作中变身25;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平板等装置已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当代人提供形式繁多的“震惊性”体验,持续影响和改写着人类感知世界与自我的方式。总之,数字技术续接了电影在诞生时的魔法效力,被复兴的吸引力一再释放自身的能量,昭示出吸引力美学的特质,并作为一种“惯习”26建构着整体性的文化结构、认知系统与社会意识。对吸引力美学的进一步总结和思考,是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技术数代的首要和根本性问题。
【注释】
1[美]汤姆·甘宁.吸引力:它们是如何形成的[J].电影艺术, 2011(4):71-76.
2[美]汤姆·冈宁.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J].范倍译.电影艺术,2009(2):64.
3[荷]弗兰克·凯斯勒.吸引力电影作为装置[J].王苑媛译.电影艺术,2019(5):84.
4同1.
5陈犀禾.虚拟现实主义和后电影理论——数字时代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观念[J].当代电影, 2001(2):84-88.
6杨天东.数字吸引力:“后电影”的美学与文化[J].当代电影,2022(5):170.
7[美]法兰西斯科·卡塞提.卢米埃星系:未来电影的七个关键词[M].陈儒修译.台北:一人出版社,2021:173。
8同7.
9斯大凌.虚幻引擎发动,电影已进入虚拟制片时代.公众号“深焦”,2022.5.13.
10杨玉洁.从《奇幻森林》到《曼达洛人》看虚拟制作的演化[J].影视制作,2020(6):15-23.
11吴 悠.《曼 达 洛 人》与StageCraft影片虚拟制作技术分析[J].现代电影技术,2020(11):6-12.
12徐建.《刺杀小说家》:中国电影数字化工业流程的见证与实践[J].电影艺术,2021(2):131-137.
13亨利·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已不能准确描述媒体运作的现实,融合文化则把学术性的媒介研究从单一媒体平台的角度上升到考量不同媒体平台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层面。参见[美]亨利·詹金斯.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于人民的选择——数字时代的叙事、文化与社会变革[A].常江,邓树明编.从经典到前沿:欧美传播学大师访谈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15-216.
14[德]鲍里斯·格洛伊斯.艺术力[M].杜可柯,胡新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82.
15[法]翁托南·阿铎.剧场及其复象[M].刘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1-57.
16[美]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M].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4-25.
17柯宜均.感知的创造性替身.“台湾数位艺术网”,2017:12-18.
18曾靉.在叙事与虚拟之间:VR如何影响影视产业?.数位时代,2017.7.24.
19曾靉.“我重新拍剧情片是因为VR!”蔡明亮携手HTC拍首部VR电影《家在兰若寺》.数位时代,2017.7.18.
20[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140.
21[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9.
22伍迪艾伦的媒体代表向IndieWire网站发布了一则声明:“伍迪艾伦并没有说过他将要退休,或是正在撰写另一部小说。他是说他正在考虑要停止拍摄电影,因为拍摄几乎立刻或等一段时间就会登上串流平台的电影,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有趣,他是一位死忠的电影院信徒。目前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并非常期待能够前往巴黎拍摄新片,也就是他的第50部作品。”见https://news.agentm.tw/235164/.
23Conviva的报告显示,2022年第二季全球串流媒体市场实现两位数成长。见智慧电视和Roku在全球观看方式中占主导地位.“businesswire”,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20909005106/zh-HK/.
24常江.流媒体与未来的电影业:美学、产业、文化[J].当代电影,2020(7):4-10.
25Jeffrey Shaw,Peter Weibel.Future Cinema: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M].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2003.
26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