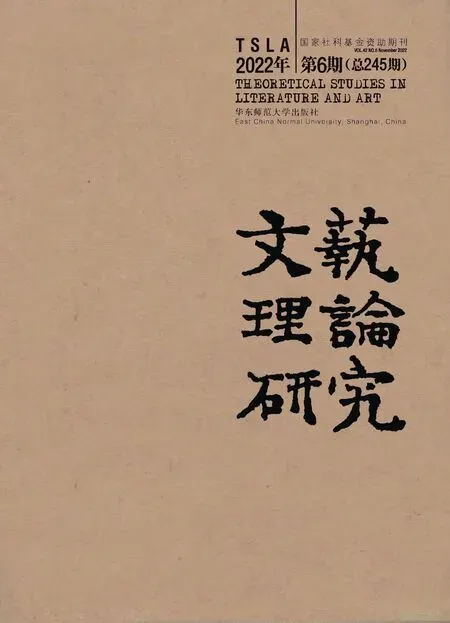问题与方法: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及其可能性
2023-01-20宋石磊
宋石磊
二战后,相对于此时国内中国艺术史研究界的“沉寂”状态,海外艺术史研究掀起了中国艺术研究热,尤其关注中国的晚期绘画问题,进入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鼎盛时期。一大批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陷入了“方法论热”。当然,新的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尚且悬而未决。但是,这也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文艺复兴以来那种发端于欧洲的传统艺术史研究,即停留于风格分析和图像解读的研究方法是否还适用于中国艺术。尤其是将这种研究方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艺术研究之上的“跨文化借用”的方法,已然不适用于随着时代语境变迁影响下的中国艺术。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下,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尤其是美国的东西部两大学派开始崛起。
近几十年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史学科的观念模型,并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美学、考古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不断侵入,海外艺术史研究的边界不断延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体系,逐渐分化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三种路径:一是艺术史“外向观”(Outward-looking)——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视觉分析”;二是汉学“内向观”(Inward-looking)——方闻(Wen C.Fong)的“结构分析”;三是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新趋向——柯律格(Craig Clunas)的“物质文化和考古视觉图像材料分析”。尤其是高居翰在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五对概念”和李格尔(Alois Riegl)“艺术意志”的传统的风格学和形式分析基础上所推进的视觉分析,与其说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毋宁说带来了一种“他者”的全新观照视野,以及艺术史阐释的另一种可能。而方闻领衔的普林斯顿学派的“结构分析”对于中国艺术品考古文献和汉学功底的重视,以及柯律格对于物质文化和考古视觉图像材料分析,都启示了对于“物质材料”和视觉图像证据的重视。乃至于国内近十多年以来的历史图像学研究①和“图像证史”②的研究方法的流行也可从中找到影响的痕迹。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使发端于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路径,创造性转化为适用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范式。正如王一川先生所指出的:“随着中国艺术学理论下艺术史学科体制的确立和持续运行,被质疑的悬而未决的艺术史有可能逐步开放其学术空间或可能性。从美术史专家自觉面向艺术史开放和拓展的事实,可知中国式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及其路径正在打开。”(王一川38)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要想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势必在西方“他者”的参照之下,从中国本土艺术史的艺术本质和艺术经验中提出问题,继而寻找一种中国本土艺术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问题、方法、研究路径及其可能性。
本文从“汉学与艺术史”之争谈起,通过对二战后影响至今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所分化出的汉学学派、艺术史学派及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新趋向这三种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路径的梳理,管窥其各自不同的语境及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悬而未决的可能性,以期以海外艺术史的经验总结,为当下中国艺术史学科建构和讨论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启示。
一、从一场论争谈起:“汉学与艺术史”之争
二战后,海外艺术史研究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汉学与艺术史”③(Sinology and Art History)的激烈论争,所直接导致的是海外艺术史学界汉学学派与艺术史学派两大阵营的对峙。1947年,在纪念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两百周年而召开的“远东文化与社会”(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研讨会上,与会者就“纳尔逊孝行石棺”(The filial-son Stone Funerary of Nelson-Atkins)的真伪鉴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纳尔逊孝行石棺”之所以引发论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纳尔逊孝行石棺”之真伪鉴定对于重构中国早期绘画——古代六朝绘画具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具体表现为乔治·罗利(Georg Rowley)与亚历山大·苏泊(Alexander C.Soper)的论争。罗利因为一来不懂中文,二来缺少汉学的文献功底,仅仅依据“纳尔逊孝行石棺”的风格形式分析就将其断定为赝品,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正如苏泊针对罗利的艺术史研究路径的批判:“仅借英文资料的西方学者”在掌握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中国艺术品所下的赝品断定,难免有失之偏颇之嫌。这成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自二战以来根深蒂固的派别论争。海外艺术史此后的诸种论争,究其源头,都可以在“汉学与艺术史”之争中找到线索。这场论争之所以发生,与海外艺术史的整体转向相关。20世纪上半叶,大量中国的青铜器、佛造像、壁画、书画与瓷器等流失海外,带动了弗利尔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博物馆的勃兴,由此带来了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热,引发一系列问题:如何研究这些中国艺术藏品?以何种艺术史方法来阐释中国艺术?以往第一代汉学的研究方法如何修正?由此带来了汉学与艺术史两大阵营的方法论之争。
论争的焦点集中于风格史与形式分析的方法是否具有一种艺术史的“普遍性”。中国艺术的核心问题是断代划分与真伪鉴定,所不同的是研究方法的区别,是风格分析还是文化史阐释?如对于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的研究,后者是通过文献学和考古佐证展开的;前者却是西方风格学与形式分析的艺术史专业训练。如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的弟子罗樾(Max Loehr)对于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纹样分类,基于风格类型的断代划分,以“风格连续性”形成不同年代的风格序列。而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lgren)则专注于青铜器的铭文、文字和形象作纹样分类,进而阐释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味。研究方法与路径的分歧显然是“汉学与艺术史”之争的关键所在。
前者是正统的文献考证与断代划分,所运用的是文本、青铜器铭文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中国艺术所生发的整体文化史的把握,从艺术品的铭文、印章、题跋、画论和日记来重构一个时代的文化史,进而指出这是对艺术品的断代划分和真伪鉴定的重要证据。长期以来,在汉学与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对峙中,汉学家们倾向于强调文献学的重要性,将一幅艺术作品还原到整个文化史的背景中,旨在作一种意义和内容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阐释。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一个理念: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所谓“风格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而言,源于德国,属于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因而不适用于中国艺术的分析。
从渊源上来看,后者的理论来源属于沃尔夫林传统。风格学与形式分析的研究方法自文艺复兴始就一直是“显学”,艺术品本身及其形式是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从“时代风格”和“风格的连续性”的再现的形态(the Code of Representation)来把握一个时代风格的实质性因素,试图通过一个时代的普遍性风格来建构一种艺术史的“风格共相”。风格史研究往往倾向于从强烈的风格观感切入,而不是一整套理论的套用。在沃尔夫林系统所编织的艺术史坐标上,横向指向各种不同的形式风格,纵向则是找寻一个普遍的“风格共相”,以此串联起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寻找一种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普遍性。早期风格学研究者受到了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西方艺术史专业系统的训练。巴赫霍夫指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汉学家以题跋、印章等画面附属的二手材料作为真伪鉴定的证据,这很有可能是后世的伪作,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画论则大多是文人的个人喜好等主观成分书写,因而不可信。尤其表现在文人画方面,巴赫霍夫指出文人画作为业余的游戏绘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非艺术史的界限。他坚持认为艺术史学者应从绘画自身风格出发,以画面作为主体研究对象,重艺术本身的风格分析,这是把握艺术史的可靠的第一手文献。将中国艺术风格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剥离出来,相对于外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坏境而独立的风格史,不同时代的视觉艺术语言串联起一个时代的艺术史的风格演变。
二、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三种路径
“汉学与艺术史”之争所形成的汉学学派与艺术史学派之间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分歧,其实质却是海外中国艺术史学界对于中国艺术研究如何走向纵深分析所日益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汉学与艺术史”之争所形成的汉学和艺术史两大学派的对峙,一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的柯律格,出现了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新趋向。大致来说,近几十年的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经历了由“外向观”到“内向观”后融合的路径转向,汉学与艺术史分界与融合的演变历程也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当然,这并非指向绝对划分,而是试图从艺术史的阐释进路中找出一种研究脉络,形成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三种路径。
(一)艺术史“外向观”:高居翰的“视觉分析”
二战后,海外艺术史研究界掀起了中国艺术收藏热。1949年,法国收藏家杜伯秋(Jean Pierre Dubose)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席克门(Laurence Sickman)共同策划了“明清画展”。这成为影响海外艺术史整体走向的一次重要的艺术史事件,引发二战后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重心从宋画转向了明清绘画。高居翰(James Cahill)正是在“明清画展”的启发下,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明清绘画之上。长期以来,因对于模仿再现(Representation)系统的重视,美国学界过分偏爱自然主义写实的宋画,进而忽视了明清绘画的创新性。高居翰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展开了对于明清绘画革新的再发现,进而影响了学界对于中国晚期绘画的整体认识。
高居翰所持的是一种“风格即观念”的研究理念和“绘画只有通过画史才能进入历史”的绘画通史观。在沃尔夫林传统风格分析的框架内,高居翰以“视觉分析”作为切入点,结合史学、文献、考古,以及思想和文化等因素,对绘画作品予以重新定位。高居翰所开创的全新方法论给海外艺术史研究带来了生机。但也因其研究方法与传统艺术史处理模式存在巨大差异,一时引发了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于高居翰的“生活方式与风格倾向”(Life Patterns and Stylistic Directions)对应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的模式和方法。④具体表现在高居翰对于浙派和吴派的评价。高居翰抨击浙派对于前人技法的过分因袭模仿,导致其创作陷入了一种“僵化”模式。高居翰的问题在于先验地将浙派与吴派对立,在行家或利家的指称背后有着明显褒吴抑浙倾向。这一观念很快便受到了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韩庄(John Hay)和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的批判。尤其是普林斯顿学派出身的班宗华指出高居翰过分重视方法论的创新而恰恰忽视了艺术本身。针对这一批判,高居翰迅速展开反驳,其理论依据便是传统风格分析仅仅停留于谈论画的层面,而他所探求的是一种社会史和历史语境下的艺术。这场论争表面看来指向艺术史的评价与书写,实则是长期以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界根深蒂固的方法论之争,即:“汉学与艺术史”之争所积淀的结果。
从学术史的进路来看,高居翰的“视觉分析”属于艺术史的外部考察,李维琨率先指出高居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属于“外向观”(李维琨20)。这种“外向观”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史发展的某种必然逻辑。过去传统艺术史持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假定“有一个在跨越时间和地点的无限连接和变化中证明多少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它’艺术”。而艺术史学科的任务便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追溯这种艺术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艺术社会史学者的方法则关注符号的不同作用,而这些作用正是由同时产生、持续和反映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中的艺术作品所造成的”(普莱茨奥斯240—254)。高居翰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以往传统艺术史的风格学和形式分析是否还适用于现代艺术史的研究语境。尽管风格学有其优势,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纯粹风格形式分析太过强调不同时代风格的“分类”,过分关注时代风格的总体概括,缺少一个“对应关系”的分析模式,致使难以凸显画家个性,这显然与高居翰所主张的晚明绘画“革新论”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在这一层面之上,高居翰重新审视艺术作品生产和接受的艺术风格变迁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关系,转而从外部输入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批评等话语体系。因此,高居翰借鉴了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时代之眼”(Period Eye)⑤,摆脱了以往西方艺术史学者的传统风格分析的既定框架,转向社会史与历史语境下的艺术,以期对“时代风格”(Period Style)作一种艺术史的实质性判断(Exercising Critical Judgement)。对于高居翰而言,艺术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时代的图像证据。正如威廉·瓦特逊(William Watson)对高居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式”的评价,指出高居翰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偏重从“外因”考察艺术作品风格革新的时代、地域、背景,以及社会、心理、经济与政治等原初历史语境。高居翰致力于开拓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旨在将研究边界的外延不断扩大,力图建构一种多维视野下的“大艺术史”研究框架。具体到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继而展开丰富复杂的论述,诸如地域、经济地位、对传统所持的态度,等等。“对艺术家生平、分析画家作品,将他们置身于特定的时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语境。”(高居翰1)以及借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术语,如“赞助人”“收藏家”“职业画家”“业余画家”来处理浙派与吴派、行家和利家的关系。高居翰充分展现了他全新的“视觉分析”的学术理路:“如何通过细读画作和作品比较来阐明一个时期的文化史而作的一次尝试。”(高居翰2)如高居翰对于遗民画家弘仁如何从安徽画派的线性的刻板结构演变为黄山个性化书写的典范。他将萧云从的黄山书写与丁云鹏的传统风格比较,同时辅之以安徽画派线性版画与绘画的双重影响倾向,层层剖析了弘仁笔下的黄山如何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从传统的窠臼中突围出来。高居翰充分展现了扎实成熟的风格分析,开创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
高居翰反潮流的艺术史书写带来了二战后美国艺术史的范式转换,同时,他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居翰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乃至于他所收藏、引证、研究的中国艺术作品,就范围而言,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地,唯独缺失了中国大陆本土所收藏的中国艺术作品这一块。研究对象与材料本身的不完整,无疑使他的判断失之偏颇,以至于出现了一种“艺术史的偏见”。高居翰虽然精通日语,但是却不懂汉语,缺少汉学的知识积淀,所以才会出现中国文化阐释的“鸿沟”。1999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董源《溪岸图》的研讨会上,高居翰指出《溪岸图》为张大千伪作。一直到2012年上海博物馆所举办的“翰墨荟萃”国际研讨会,针对董源《溪岸图》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的美国收藏古代名作展,高居翰仍坚称《溪岸图》是伪作。这无疑都是高居翰“知识盲点”的后遗症,也是他颇受争议的原因。这与二战后罗利与苏泊在“汉学与艺术史”之争中的问题是一样的。罗利的问题也正是源于不懂汉语,加之汉学功底的缺失,表现为一种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的通病。这显然是时代影响所致,文化历史语境决定了艺术史阐释的限度。二战后,因受到海外艺术史“方法论热”的影响,高居翰重视方法论的创新,而忽视了中国艺术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但这在一定层面上也启示了艺术史研究需要必要的汉学及文献考证的知识背景。因此,艺术史与汉学的融合成为时代所趋。
(二)汉学“内向观”:方闻的“结构分析”
艺术史研究的“外向观”所直接忽视的是艺术史的本质问题,这一问题愈来愈引发艺术史研究界的焦虑,一些艺术史学者开始将研究重心放在艺术史学科的反思之上。首要的便是重新反思艺术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转而关注艺术的本质和意义。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下,沉寂许久的汉学内部研究重新焕发生机。事实上,早期海外汉学所秉持的就是一种内部的艺术史观。二战后,方闻领衔的普林斯顿学派所持的“内向观”成为与高居翰为首的沃尔夫林传统之“外向观”相对峙的美国艺术史学界东西部两大阵营的分野。方闻的“结构分析”研究方法重回艺术史的本质问题,即克莱因鲍尔(W.Eugene Kleinbauer)所指出的艺术史家的意义:“艺术史家渴望通过识别艺术品的材料和技法、制作人、制作时间和地点,以及意义和功能——简要地说,它们在历史图式中的位置——来分析和阐释视觉艺术。”⑥(qtd.in Mandelbaum299-377)这种“图式(Scheme)-历史(History)”的框架,正如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所指出的:历史有一套符码(Code)的观念,即年表的图式。⑦
在方闻看来,研究中国艺术,必须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从绘画的模拟与再现分析,进而还原艺术品生成的“原境”。方闻基于形式分析、符号学、文本学、物质文化等方法论的大量分析,结合自身对中国艺术的深刻体悟,所阐释的是如何以中国书画的视觉迹象来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化史,所直接回答的是“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的问题。方闻所强调的是基于作品的“结构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文献整理的层面,并进一步指出远离作品的研究表现出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滞后性”。这无疑切中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命脉。海外中国艺术史的治史方法虽然参考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将艺术置放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但是这种传统艺术史处理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仅靠手上有限的材料来推断一种艺术史的风格变迁,这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绘画理应生成的这一偏虚假的期望之上的。同时也使得艺术史研究陷入了一种停留于史料整理层面的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艺术史研究虽有考古研究和文献分析,诸如王国维的以地下出土文物之考古来考证文献材料证据的“二重实证法”,但传统的中国画史却停留于将文物来作为文献的佐证。鉴于当时中国艺术史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方闻所持的是一种“艺术史的普遍观念”,方闻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绘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表现方式的独特性。“中国艺术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想确立其学术界碑,必须首先始于对其视觉符号‘基本要素’(诸如线、面、画面等)的阐明,继而分析其‘视觉化机制’的构成。”(方闻30)具体表现在他对于石涛的“一画论”的精彩解读,“一画”与石涛早年佛门生活经验有关,石涛深受旅庵大师对于“一”的禅悟影响,“文彩已彰”(郑拙庐49),所隐含的是一个冲突中见和谐的妙悟,暗合明清易代鼎革的语境。“一画”之所以贯穿石涛的创作,在于其生命与艺术的浑融为一,于外在明清易代危机的生存困境与混乱中渴望重建和谐秩序。
在方闻看来,作品的“结构分析”是判定一幅绘画作品的时代风格与年代归属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此建构一个整体性、时代性和区域性的风格序列的普遍性共相。即从对每一幅作为“物质文化”的绘画作品的“线条、空间、画面”的形式分析中,探讨其生发的“视觉化机制”。同时,方闻也强调鉴定学,基于大量的文献证据和艺术作品的视觉证据分析,才能生成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因此方闻对于那种传统的“艺术史普适方法”⑧和“普适体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不同时代的历史际遇之差异,势必需要从不同研究对象本身所处的原初语境出发。即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视觉语言及其文化表征,为获得一个可资观照的普遍性研究视野,需要建构一种共同的现代分析和阐释模式,如方闻的著作《〈夏山图〉:永恒的山水》(SummerMontains:The Timeless Landscape)对于北宋山水“视觉化”样式的解读。方闻基于画家如何以一种移动的视点抑或一种平行透视法来观看山水,立足于分析视觉语言与构图的发展变化,以手卷的形式从右向左打开,以一系列不同的深远、平远和高远的移动视点展开,这一“视觉化”的样式成了方闻鉴定此画为屈鼎手笔的关键性证据。
方闻的“结构分析”的生成是基于他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的反思。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不再关注研究对象本身于何时、何地,以及由何人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接受美学的视野,考察此艺术作品在后世的递藏和接受情况。即以一种后世收藏者的眼光来定位,这势必产生一种阐释的缝隙。这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显然是方闻基于中国艺术研究的“滞后性”所作出的判断。
(三)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新趋向:柯律格的“物质文化和考古视觉图像材料分析”
方闻所指出的艺术史研究的“滞后性”,促使海外中国艺术史学界进一步反思这一问题。20世纪初,德国考古艺术史家亚多尔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在《艺术考古一世纪》(ACenturyof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一书中所强调的考古艺术品本身的视觉分析可谓异曲同工。在传统考古学家的金石研究和文献佐证之外,米海里司强调考古艺术品本身视觉形式分析的重要性。相较于以往传统艺术史立足于一个假定式框架的分析模式,米海里司转而强调考古艺术品本身的线条、空间和色彩所组成的画面结构形式的重要性。米海里司认为考古艺术品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图像证据,而是重视考古艺术品本身的视觉形式分析。即:“艺术品有它自己的语言,艺术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对之加以理解和诠释。”(Michaelis304-340)
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下,柯律格得以脱颖而出。柯律格自始至终秉持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史研究视角,进而形塑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艺术史概念,带来了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海外汉学新趋向。
与前人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献学与鉴定学等融入中国艺术研究路径相比,柯律格基于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进行中国古物研究的15年艺术经验,致力于还给作为物质材料的艺术品一个真实的“原境”。这显然是来源于巴赫霍夫“艺术史的知识生产有其内在的逻辑”的研究启示。与高居翰相比,柯律格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海外艺术史的学科训练。⑨与方闻相比,柯律格也没有中国书画的功底和深切体悟。与其他汉学家长期在中国工作也有所不同,他甚至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仅仅于1975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过一年。但是柯律格却在对于博物馆的“物质材料”的观摩中,获得了一种“古”的眼光。也正是他对于中国物质材料的熟悉,使其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东方学和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所指出的“后殖民主义”艺术史书写的意识形态中突围出来。20世纪80年代,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陷入了一种艺术史的危机,1982年,美国学院艺术协会主办的《艺术杂志》冬季刊直接以“一种艺术史学科中的危机”为题做了一个专辑。艺术史的危机之所以发生,首先要反思学科研究的对象,即由一种“风格的历史……(正像)在假定的艺术自律中建立一种叙述的或偶然之链的企图”所体现的“深刻的矛盾”(普莱茨奥斯241)。这显然是学界基于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史学困境的反思,同时也面临着“新艺术史”的挑战。这促使柯律格进一步反思:“一件往昔之物它真正意味着什么?”(柯律格,《长物》10)柯律格以“物质文化”为艺术史编织的脉络,立足于中国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梳理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品,并进一步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重构这些艺术品生成的“原境”。在1991年出版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一书中,柯律格所运用的“物质文化”的艺术史新方法,便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具象化,既促进了汉学与艺术史的融合,也带来了海外汉学的新趋向。在《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一书中,柯律格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路径,以图画(pictures)串联起了明代从绘画、印刷、工艺、器物,到历史、文化,乃至于日常生活的图像,“以此来带出中国关于图画制作的长久而复杂的历史”(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7—8)。在带来了“跨文化的艺术史”的研究启示的同时,又极大地延展了中国绘画的阐释空间。
柯律格的“物质文化和考古视觉图像材料分析”,从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史研究视角,打破了艺术史学科的边界,表现出了一种“艺术史的洞见”。正如乔迅(Jonathan Hay)所评价的那样:《长物》所带来的汉学与艺术史融合的新声音,源于柯律格没有受过艺术史的训练,反而带来了一种新鲜感,尤其是汉学的文本细读功底。(Hay308)柯律格的意义在于:在既有的艺术史范式之下与汉学融合的新突破,尤其是创新性地阐释了中国晚期绘画与西方绘画面临“艺术终结论”的相似境遇。
这些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极大地延展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边界,带来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转向,拓展了学科的深广度,体现了艺术史方法论的前沿性和探索性。
联系当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以下几点启示:
1.高居翰、方闻和柯律格的不同主张,大致代表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路径和方法论的差异,尤其是高居翰和方闻所代表的美国东西部两大学派的对峙。
高居翰的“视觉分析”代表的是一种“大艺术史”视野,体现了一种建构“世界艺术史”的野心。方闻所代表的汉学“内向观”,是海外艺术史上以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代汉学家所持的观念,方闻坚持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强调一种可资观照不同民族的艺术史的普遍性和公共视野。而高居翰力求一种艺术史的深度,因受到19世纪“新史学”的“大历史”(Universal History)叙述的影响,高居翰秉持一种“大艺术史”的“大叙述”(Meta-Narrative):基于大量中国绘画作品的视觉图像的形式分析,从以往对于明清绘画的“误读”和“偏见”中抽离出来,转而从外部探寻,这种“外向观”致力于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史和历史语境下来把握艺术史。高居翰尤其注重挖掘新材料,将以往被文人话语所长期遮蔽的职业画家、宫廷绘画、世俗绘画和民间绘画重新纳入了艺术史的书写。这便与传统画史文人所长期主宰的话语空间大大地拉开了距离。在反拨文人话语权的同时,又拓展了艺术史的版图。从学术的进路来看,前者立足于艺术史的外部考察;后者着眼于作品为主体的风格阐释;在研究方法上,后者运用考古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归纳,相对比较具体客观。而前者立足于风格史的逻辑推演,难免有失之笼统的判断。二者分歧更多指向的是研究路径和方法论的差异。
具体到柯律格的艺术史阐释,在融合海外汉学和艺术史的基础之上,柯律格又极为审慎地看待西方“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所固化的意识形态书写,表现出一种对于海外艺术史生产机制的深深怀疑。因此,柯律格借鉴人类学的“物质文化”这一概念来重构中国艺术史上的画家和作品,进而重新阐释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史,这种“跨文化的艺术史”带来了新的维度,体现出一种海外艺术史研究的新趋向。但是,柯律格的艺术史阐释模式挑战着传统的艺术史方法和叙事模式,无疑又会带来新一轮的艺术史论争。
2.来源于方法论的启示。
二战后,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方法论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方法。如艺术史的“结构-语言”模式,将社会与经济理论移用于艺术史;以及后来“新艺术史潮”(The New Art History)代表诺曼·布列逊(William Norman Bryson)借鉴文学研究的“符号学”理论应用于艺术史研究;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借用印度裔学者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混杂理论(Hybridity Theory)来处理中国艺术,并以圆明园和清代艺术作为证据来进行艺术史阐释;等等。从艺术史的脉络来看,方法论的更新无疑是艺术史发展的某种必然逻辑,以往整个艺术史的有关画家传记、思想、证据、意义和内容的基础性考证工作已近乎完成,因而势必走向一种精深的批判性分析和因果阐释。但是这也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艺术史阐释的限度问题。如高居翰借用西方社会与经济的术语所提供的“赞助人”模式,以及依据画家的文人身份的“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的划分。在尚未弄清是谁所画,画面分析尚未到位,乃至于掌握的作品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文献学功底的缺失,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建立在中国绘画理应发生这一偏于虚假的期望之上。这种艺术史阐释模式的另一重危险还在于,极大地忽视了外部的社会状况、时代语境,乃至于文人题跋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性内涵。在基本汉学知识缺失的情况下,再好的艺术史阐释模式也终究是失效的。相形之下,中国本土艺术史研究因外在社会状况而导致的“断裂”,在艺术史自足性的演变下缺乏研究方法创新的自觉。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下,国内学界加快了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译介。21世纪以来,尹吉男主编的“开放的艺术史”丛书、范景中主编的《美术史的形状》与李军主编的《眼睛与心灵:艺术史新视野译丛》成为国内学界了解海外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持续升温,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巫鸿、郭伟其的《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牛克诚、杭春晓、张南南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第一辑)》,李淞、彭锋主编的《西方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译丛(第一辑)》,范景中主编的《海外中国艺术史译丛(第一辑)》,等等。但是也要汲取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经验教训,尤其要警惕另一种现象:过分沉溺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忽视研究对象本身。在参照海外艺术史阐释模式的同时,也要注意那种背离中国绘画“主体性”的现象,正如朱良志先生多次提及的艺术史研究的“西方化”问题。对于具体的艺术史问题,需要回归原初的历史语境考察,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考察一种艺术史方法的有效性应根植于本民族文化语境,在新的视觉材料和历史证据的理论阐释中产生新的认识,进而丰富艺术史的经验和规律。真正出色的艺术史阐释模式是让人看不到理论框架套用的痕迹,但是却阐明了事实本身。
结 语
海外中国艺术史的路径转向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使发端于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路径,创造性转化为适用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史建构的观念与范式?如何修正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如何将中国艺术史纳入世界艺术史的话语体系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要想在世界艺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势必在海外“他者”的参照之下,从本民族自身的艺术经验出发去提出问题,继而寻找一种中国本土式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性。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是基于“问题-方法”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展开的。与中国艺术史进步的、历史的、渐进的演变形态有所不同,海外艺术史的每一次范式转型都伴随着激烈的学派论争。新论争聚焦新问题,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不断递进与更新,加之方法论层面的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史学科的观念模型。海外艺术史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所创造的,在参照西方来对中国本土艺术进行阐释之时,不能将海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全盘照搬,而势必进行一种“创造性转化”。那种将海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之上,所谓一种文化强制另一种文化的路径,以及中西二元对立的局势,都是需要警惕的。
在当下的中国艺术史讨论中,海外艺术史研究“他者”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中国艺术史研究要想突破长期自足的“自律性”,势必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而研究路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无论是高居翰的“绘画只有通过画史才能进入历史”,抑或是方闻的“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以及柯律格的“物质材料”的历史性,都强调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历史意识,画家与作品在历史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中去界定二者的关系。艺术史的发展永远处于一种流动之中。这需要从中国的历史语境、社会状况、绘画创作和观看经验本身去提出问题,进而寻找一种中国本土艺术史的阐释框架。近年来,尹吉男教授的“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史”、李军教授的“跨文化的艺术史”、朱良志先生的“文人画的真性”的美术史重构等都是国内艺术史的有益尝试。在具体的阐释路径上,王一川先生以北京大学的艺术史学科为个案,进而指出四种研究路径——实地调查与纵深分析汇通、艺术观念思考与艺术家作品体验汇通、文化史与艺术史贯通、跨国艺术史比较研究视野,从而为综合类大学艺术史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借鉴。彭锋教授立足于中西方艺术史的比较视野,从中国社会状况出发所考察的中国当代艺术没有走向欧美的后历史的“艺术史终结论”,而是具有不断演进的历史。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风格分析和图像解读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艺术史研究语境,而应该从当代普遍流行的艺术史观念所生发的“原境”来对其重新审视,进而提供一种艺术史研究的新视域。不断打破学科边界和学术壁垒,借鉴多学科理论的新趋势,进而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一种流动的艺术史中建构各艺术门类多元互动的中国艺术史“大叙述”。这种大艺术史的建构旨在以本民族文化特质来重塑海外艺术史,在一种历时性的互动中展开中西方开放对话。中国本土的艺术史学科模型建构亟须一种开放的跨文化视野,立足于大艺术史的整体研究之下,重新反思艺术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性。
注释[Notes]
① 2018年10——11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图像学”方法论系列讲座:图像何以“证史”?——“历史图像学”的方法论问题。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应邀主讲《历史研究的图像学“转向趋势”》《“图史互证”的问题与方法》《“历史图像学”研究中的“刺点”与“难点”》三讲。尤其是关于“图史互证”的方法,他引用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讲述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进而指出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其“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是文化、政治、物质等一系列多元的背景下考察。2019年5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办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立足于图像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葛兆光、李公明、金光耀、李军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图像作为史料进入研究视野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
② 曹意强是国内较早关注“图像证史”方法论的学者。参见曹意强:《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新美术》2(2004):7—13;曹意强:《图像证史与图像撰史——关于历史画创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美术》11(2006):109—111;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2005):24—38;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二)》,《新美术》1(2000):61—77。
③ 关于“汉学与艺术史”的论争,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在《汉学还是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笔记》一文中,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之争做了详细梳理。参见Pope,John A.“Sinology or Art History:Notes o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X 10(1947):388-417。
④ 关于高居翰的“生活方式与风格倾向”对应分析的模式和方法,及其渊源和来龙去脉,笔者另撰高居翰专文做了详细探讨。参见宋石磊:《高居翰的两次艺术史修正》,《读书》4(2022):151—159。
⑤ “时代之眼”是巴克森德尔研究15世纪意大利绘画时所使用的概念,大意是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史的材料,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图像证据。参见Baxandall,Michael.PaintingandExperienceinFifteenth-CenturyItaly:APrimerintheSocialHistoryofPictorialSty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⑥ 克莱因鲍尔界定艺术史家的任务加以比较(qtd.in Mandelbaum 299—377)。参见Mandelbaum, Maurice H..History,Human,&Ration:AStudyinNineteenth-centuryThought.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⑦ 参见Levi-Strauss,Claude.Lapenséesauvage.New York:Harper & Row Press,1966。
⑧ 葛兰巴提出了“艺术史普适方法”(Universal Approach of the History of Art)这一观念。简单来说,葛兰巴认为艺术史家的意义在于发现特定视觉语言中蕴涵的国族或种族的文化的本土性意义,而非将此意义并入一种所谓的“普适体系”。从艺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葛兰巴的这一理念尚处于艺术史研究的早期,只适用于一般的艺术史阐释层面,对于一些复杂的艺术史情境,诸如中东艺术的多次殖民化及其变迁显然是无法阐释的。参见Grabar,Oleg.“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History of Art”.ArtJournal4(1982):282。
⑨ 柯律格不但有博物馆的工作经验,同时还有文学的背景。他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硕士和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攻蒙古文学,并于1975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一年。
⑩ 常宁生提出中国艺术史研究应警惕中西二元对立的问题。即:“艺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艺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参见常宁生:《艺术学的建构与整合——西方艺术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艺术史研究》,《文艺研究》10(2007):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李佩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Cahill,James.TheCompellingImage:NatureandStyl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esePainting.Trans.Li Peihua,et al.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
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Clunas,Craig.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Trans.Huang Xiaoju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1.]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洪再新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SuperfluousThings: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China.Trans.Gao Xindan and Chen Heng.Ed.Hong Zaixin.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
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和结构分析研究》,李维琨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Fong,Wen C.ImagesoftheMind:SelectionsfromtheEdwardL.ElliottFamilyandJohnB.ElliottCollectionsofChineseCalligraphyandPainting.Trans.Li Weikun.Shanghai:Shanghai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1993.]
Hay,Jonathan.“Review ofSuperfluousThings: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China.”TheArtBulletin94.2(2012):307-312.
李维琨:《美术史方法的差异与对象的差异——〈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读后》,《新美术》4(1989):59—61。
[Li,Weikun.“Differences in Approaches and Subjects of Art History:Review onTheBarnhart-Cahill-RogersCorrespondence.”NewFineArts4(1989):59-61.]
Mandelbaum,Maurice H.History,Human,andReason:AStudyinNineteenth-CenturyThough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
Michaelis,Adolf Theodor Friedrich.ACenturyof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Trans.Bettina Kahnweiler.London:John Murray,1908.
多纳尔德·普莱茨奥斯:《当代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40—254。
[Preziosi,Donald.“A Crisis in,or of,Art History.”TheEndoftheArtHistory?:SelectedWorksofContemporaryWesternArtHistoryandPhilosophy.Ed.and trans.Chang Ningsheng.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240-254.]
王一川:《艺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文艺理论研究》34.4(2014):38—45。
[Wang,Yichuan.“The Possibilities and Paths of Art History.”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34.4(2014):38-45.]
郑拙庐:《石涛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Zheng,Zhuolu.AStudyofShitao.Beijing: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