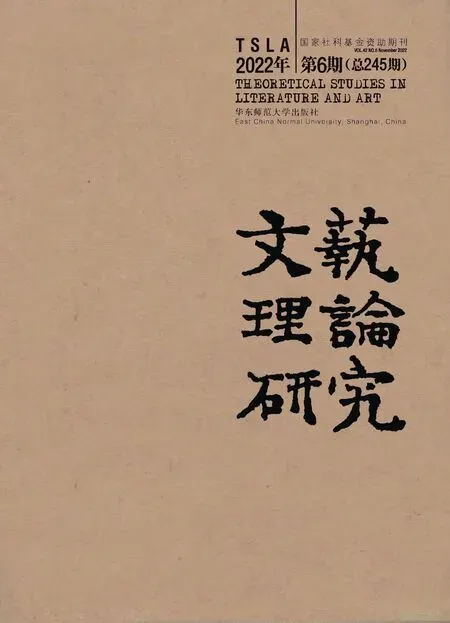“人力车夫”形象缺席左翼文学考论
2023-01-20康馨
康 馨
1926年3月27日,梁实秋在其《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中讽刺新诗中的“人力车夫派”,说“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同时又以为劳动是神圣的,觉得人力车夫值得赞美”(梁实秋62)。所谓“人力车夫派”并非文学史上的既成概念,但非常敏锐地概括了“五四”的文化氛围。新文学中出现了不少憨实勤奋的“人力车夫”形象,形成了一股“人力车夫题材热”。①“人力车夫”可谓“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形象化表达,也是当时泛劳动主义思潮的审美符号。胡适不仅把“人力车夫”当作新文学取材来源(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301),还用来指代亟须研究的社会问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1版)。
“人力车夫”承载了“五四”知识界的整体关怀,但被新文化运动哺育的一代左翼青年并未在30年代延续此题材的先锋意义——“人力车夫”被定格在“五四”而断裂在了左翼文学中。以文学潮流之自然演进来解释“人力车夫”的退场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左翼文学显性的革命话语与隐性的启蒙关怀不可能毫无依据地裁汰任何一种“大众”形象。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代印象之下,已有很多研究从作家思想转向、作品思想资源以及上海政治与商业环境等方面为这个宏大主题添上了历史细节,②但以人物形象讨论左翼文学特质的研究则比较单一,大多集中于对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等左翼文学既“有”的形象进行解读。本文则采取逆向思维讨论左翼文学所“无”的“人力车夫”,并从文学形象之“无”推论左翼作家的文艺观,试图解释左翼作家因何抛弃了这一曾经颇具时代意义又本应该符合其革命关怀的文化符号,一方面为左翼文学的思想史特征添上一个注脚,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大众化”之不彻底性填充一些历史细节。
一、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劳动者”的阶级化流变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强调“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蔡元培)。这里将体脑力“劳工”与“特权者”相对立,打破了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当时以“劳动”划分社会层次的文化民粹主义思想。③在从传统“士”过渡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知识界认同于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平民理念,产生于内省式的精英自觉。在无政府主义观念中,“劳动”已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具有道德完善作用并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革命手段。通过让知识分子参与劳动以及为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价值均衡,抹杀智识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阶级差异,是无政府主义者颇具道德理想主义的革命规划。在这个进程中,个体要逐渐摆脱从家庭到社团组织的各种“特权”,在平等劳动、平等受教育的社会关系中走向平等主义的大同世界。
神圣的“劳工”是现代知识分子为了重新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知识范式而进行的社会解释。但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旨在通过教育追求健全人格、通过劳动构建互助关系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逐渐远离了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中心。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平民”主要指与统治者相对的劳动者,那么在马列主义传播于20年代、“智识阶级”被驱逐出“劳动者”范畴后,“平民”就变身为阶级属性更鲜明的“工农大众”,活跃在30年代左翼革命话语中。
1919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以阶级话语重述“一战”,将“劳工”概念窄化为“体力劳动者”,这可视为无政府主义“劳工神圣”到苏俄式“劳工主义”观念的一个转捩点(李双 杨联芬124—131)。1921年12月15日,李大钊在中国大学演讲时,首先引用列宁的话将“德谟克拉西”分为中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还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认为社会党人从事的只是中流阶级的、半有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党人从事的才是劳工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运动(674—680)。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智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无产阶级已被完全分开;第二,劳工阶级/无产阶级的人群成分中几乎没有提到农民而主要指工人。李大钊一改之前“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的判断(180),将“劳工”的群体指认从“农民”转为“工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资源中无政府主义的减弱与列宁主义的增强。
梁实秋以“人力车夫派”讽刺的社会平等观,虽然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但二者南辕北辙的革命策略,决定了“劳动者”在两种革命设计中的差异化面貌。无政府主义式的“劳动者”主要是将体力劳动和文化教育相结合来推进社会革命的泛劳动主体。而20年代马列主义式的“劳动者”则是将“智识阶级”排除在外的体力“劳动阶级”。劳动者在实际生活中的并不神圣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心劳力者”的阶级化阐释,④使“劳动”的悲剧色彩愈加浓厚,成为阶级斗争逻辑的情感铺垫。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因排斥任何形式的权威而拒绝组织化的革命原则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动员力,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可能消灭阶级压迫。因此,“教育”只能作为阶级革命的辅助手段而不再是建构从个体到社会之理想人格的完满方式,“劳动”也不再有道德崇高性而成为压迫与异化之表征。
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说是“压迫”。⑤虽然“大众”作为“无产阶级”的同义词代替“劳动者”成了左翼文学的政治主体,但热烈讨论着文艺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并未真正进入大众所在的农村和工厂。通过提炼革命理论,左翼作家找到了一种将阶级意识注入文学形象的表达模式,那就是渲染个体劳动之“苦”来推导群体革命之必然,所以左翼文学中的主人公往往始于压迫终于革命,“无产阶级”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审美性的能指范畴。1931年,丁玲的《水》被视为普罗文学的重大突破,冯雪峰明确将“集体行动的展开”而非“个人心理的分析”视为该作品的一大优点。群像的宏大性遮蔽了个体人物之鲜活,在“指明出路”的固定动作中阉割掉了“劳动”本身的革命意义。由于无产阶级大众尚未开口说话,劳动者主体意识只能被并不劳动的作家们以崇高的道德虚位形塑出来。而与道德美化同时产生的,便是工农大众的景观化——飞速奔跑的人力车夫只是无产阶级大众之一种,阶级革命视野中的人力车夫,没有拉车租车的行业生态,没有红白喜事的日常伦理,只有脱离劳动现场的阶级身份。1935年,胡风批评小说《新客》在其“知识分子欺骗车夫”的故事中几乎没有表现车夫的生活,仅仅围绕知识分子进行书写,车夫的出场似乎只是为了塑造“受害者”形象而在承受着“抽象的痛苦”(顾封112)。胡风所期待的,是具有个体生存逻辑的劳动者,然而作者只是在社会印象方面抓取了车夫与工农大众的最大公约数。不仅是人力车夫,这也是所有“劳动者”在左翼文学中的共通状态,因为“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引出“革命”的前情提要。
随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阶级化转向,“人力车夫”与“劳工神圣”的退场亦步亦趋。当左翼文学将“写人生”的主体从道德理想主义“劳工”转为意识形态“大众”时,普世性“平民主义”退场后的干瘪文本却并未因阶级意识的填充而获得更为厚重的时代价值。而“人力车夫”在左翼文学中的边缘化,除了时代思潮原因,还可以从30年代工人运动中撷取某些社会学依据。
二、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力车夫:工人运动边缘的非典型“大众”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人力车夫不仅充当了重要交通网络,而且是街道上非常常见的无产劳动者。到30年代中期,上海市的人力车夫已约8万人,直接间接赖以生活者约30万人,占沪市人口的百分之九(蓝思勉984)。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左翼文学中却只是革命“大众”的一员,既不是“工人”典型,也没有“五四”那般引人注目的题材效应,这首先是因为人力车夫并未真正参与到30年代上海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同时也并不符合左翼文艺观念中的“大众”形象而被放逐到了真空地带。
国民革命时期澎湃发展的人力车夫工会,在30年代遭到了行政制约。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⑥将工厂监督、工会运行到罢工管制悉数纳入“合法化”进程。1931年3月,上海等地发出的人力车夫工会筹备申请遭到拒绝:
兹悉训练部以人力车夫虽系体力劳动者,但非基于雇佣关系,提供其劳力,车夫租赁车辆,其与行主之关系,如房东房客,非一般雇佣与雇主可比,且人力车夫作业无定时、工作无定所,若组织工会,转有影响其工作之处,经函市执委会将该人力车夫工会筹备处撤销,并闻训练部对于青岛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及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之同样请求亦经以此意分别解释。(《人力车夫不得组织工会》第5版)
此令明确否定了人力车夫组织工会的权利,故此群体的斗争始终零散而被动。1931年,上海黄包车夫被日军打死后引发的追悼活动是以上海总工联的名义对全上海车夫工友发出反抗倡议的(《关于日军打死沪西黄包车夫的特别报告》504—505),租界人力车夫也只能以“人力车夫代表”的名义发出请愿,而无自己合法的行业组织。此时期的人力车夫不仅没有工会,而且在自身罢工运动中也并不完全主动。由于人力车行业存在着公司、车主、承放人等多方权力关系,层层剥削便使得链条末端的人力车夫困苦不堪。而且车主、承包人与车夫乃是一种家长式关系,车夫反抗雇主的积极性也因此大大减弱。1934年,法租界人力车夫配合车商的号召举行罢工,但不少车夫却在罢工后恢复登记时因为担心手续之烦琐引发意外而纷纷返乡暂避(《不甘登记 人力车夫纷返原籍》第11版),可见车夫的罢工并不会直接利好于自己,甚至会沦为当局与车商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如果说前述权力结构是民国各城市人力车业的共同点,那么上海市人力车业还因其政治格局而更显复杂。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的车照种类与车辆换班时间各不相同,市政管理方案也各自为政(《黄包车释意和黄包车夫的等别》8—11)。针对人力车业的社会问题,上海市政府组织了人力车问题研究委员会并发布了调查报告书;公共租界工部局组织了人力车委员会,并于1933年成立了“人力车夫互助会”,但看似完备的救济方案只是华而不实的表面工程(杜重远401);法租界则由于公董局实行的人力车夫登记制度可能削弱车商利益引发了车商组织车夫进行的大规模罢工。
国民政府与租界当局的行政法规一方面瓦解了人力车夫“组织起来”的可能,另一方面还因为限制了赤色工运的发展而进一步间接降低了此群体的政治活跃性。彼时中国的工会可依据政治倾向大致分为赤色与黄色工会,黄色工会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原则,赤色工会则在1927年之后遭到重创,很多地下工作者只能分散进入合法工会并伺机领导罢工运动(宋钻友 张秀莉 张生219—228)。而包括人力车夫、娼妓、码头工人等组织性较低的非技术性劳动者,还往往通过加入帮会寻求集体庇护(裴宜理62—70),要有效动员这个群体,赤色工运不得不熟悉帮会结拜盟誓传统与运作规则,因此便更难动员散落在工厂之外的劳动者群体。
除了工人运动的政治生态,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也使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缺乏纪律意识的潜在革命群体非常警惕。早在20年代,知识界就将经济学领域对“有业”与“无业”的区分与政治上的军阀、兵匪问题结合起来,对“游民群氓”产生了负面评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将就业问题解释为资本家压迫下的平民求生难题,并试图唤起全社会阶级意识的产生(蒋凌楠158—161)。由于土匪成分降低了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共产党对“流氓无产者”的革命策略也曾在30年代初“左”化。⑦一个客观现实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主要是个体劳动者而非工厂工人,个体劳动者又往往出身于农村,成为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游民群体。30年代上海的人力车夫主要是苏北破产农民,身无长物的他们十之八九是文盲,也谈不上“阶级觉悟”,⑧可以说正是左翼文学所不屑的“流氓无产者”。这类人物虽然会从“反饥饿”的本能中升华出“反压迫”的行动主题(杨程145—148),但是既非先进生产力也非觉悟群众的人力车夫,毕竟不是左翼文学期待的人物形象。
当然,很多左翼作家并非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自觉淘汰“人力车夫”,他们笔下的“革命”或者依赖都市感觉,或者生套政治口号,只是在认同革命伦理的同时进行了正确的想象而已。“无轨列车”上迸发出的力量与速度、形形色色的都市与机械符号、挣脱传统认知的意象群落,构成了“左倾”现代派文艺的先锋美学。这类作家以物质享受感受资本主义之罪恶,用习得但并不一定理解的话语塑造倾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蓄势待发的劳苦工人,这便是那群摩登青年眼中的“革命”了。例如在《火山下的上海》中,作者段可情塑造了两种人力车夫形象,一种是冬日晚上在舞场外等候客人的车夫,他们为了取暖进行的“跳舞”与舞场内的“跳舞”形成了鲜明对照;一种是躺在马路上休息的人力车夫,在睡梦中实现了过上等生活的幻想,醒来后在黄粱一梦的失落中忽然间“眼望着有几点寥寥晨星的天空,渐渐由黑暗变成光明了,一轮如烈火般的红日,已出现于东方来了,催起这些奴隶们,去替有钱的主人翁们,作一架运动的机器,来供给主人们的需要。但是这机器,有时是要爆发的”(段可情36)。这里在都市景观中更显贫苦的“车夫”至多也就是“被压迫者”的符号表征,左翼作家无法提供比“五四”更“先进”的人力车夫形象,更无从想象在党派政治中带有阶级意识的人力车夫是何模样,毕竟人力车夫在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的边缘化位置以及在阶级社会中“流氓无产者”的尴尬身份已经使其失去了文艺典型性。
三、左翼革命逻辑对“人力车夫”现代性问题的失语
“人力车夫”虽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角,却是现代性问题的集中场域。自20年代便已出现于各地的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已经体现了该群体建立革命正当性之难。而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针对人力车夫进行符合革命逻辑的现代性评价则是更为困难的事。
与农民和工厂工人不同,人力车夫是交通现代化链条上的中间环节,这一行业的必然消失与这一群体的生存利益构成了尖锐矛盾。1934年7月,上海工部局为发展机械动力交通而提出限制车夫数量并逐步取消人力车的规定,引发了车夫持续数月的罢工风潮。人力车夫的救济、整改与行业发展问题,“从本质上看是滞后的行业治理结构与制度和所谓文明社会形成巨大反差在经济伦理层面的反映”(马陵合108)。有人将人力车夫视为中国发展畸形之体现,因为欧美和日本的交通已发展到机械动力时代,而中国却徘徊在人力动力水平并伴有诸多社会矛盾(谷士杰1—14)。在同情“人力车夫”之余批判“人力车”之野蛮,暴露了后发国家的自卑心态。在现代化的链条上,“文明”应该如何在物质进步与人道关怀中得到落实?
倾向于援引英美社会学资源的学院派学者,主张通过制度主义立法途径改良劳工问题。由于交通与社会失序状况频出,30年代上海的人力车夫调查报告大多本着调和劳资矛盾的原则将其作为社会治理问题予以学理分析。几乎所有整改建议都认为裁汰人力车行业不能采取提高车租、限制从业条件等强硬方式,而要通过提高车夫生活水平、提供教育机会来帮助其脱离车夫行业,优化车夫们的社会参与方式,将车夫问题与社会经济结构挂钩,有人甚至提出了将社会救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经济振兴结合起来的综合方案(吴平115—131)。然而,这些提高工人待遇、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在左翼眼中只是不彻底的改良主义。30年代以社会学名义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劳工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颠覆国家制度,实现工人阶级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掌控,通过革命寻求社会问题的“一次解决”。遗憾的是,这种宏大叙事并未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整改方案,在车夫罢工非常集中的30年代中期,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回应几乎可以说没有——乌托邦想象对于缓解眼前的贫困毕竟毫无助益。
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承认机器代替人力的进化公式,⑨他们也并没有反资本主义经济的俄国式民粹观,“谷贱伤农”与“丰收成灾”的农村小说大多是为了揭示破产农民必然走向革命。不仅如此,在道德层面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作家其实是极为依赖都市感觉的,茅盾就将“紧张”概括为现代生活的基本精神,同时也称赞这是因为现代人正在以大无畏的精神创造新的世界(茅盾19)。左翼作家眼中的“都市”,既是进步的表征,也是罪恶的渊薮,既是勃勃生机的现代化场域,也是斗争与反抗暗流涌动的情感闸门。都市景观与无产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给作家对待经济与道德伦理不完全一致的人力车夫群体提出了难题。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性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但不是一个可确证的“客观现实”,因为急于跟上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并没有后视条件对现代性采取完全敌对的姿态(李欧梵162)。如果说“五四”的“人力车夫”是劳动主义、平民主义符号,那么30年代上海的“人力车夫”便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象征。佝偻的脊背不仅是民族伤痛的隐喻,也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体现。在物质与精神现代化之间陷入两难已经是“现代性”的内生问题,而左翼革命伦理却不承认在社会治理层面落实“人道主义”救济的必要性,这进一步暴露出左翼话语在面对社会现实与完善自身逻辑时候的双重有限性。
四、出走的“骆驼祥子”:左翼的“革命语言学”
从平民主义“劳工”进化成无产阶级革命“大众”的人力车夫,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包裹下转化为“阶级人”。然而彼时致力于自身意识形态工农化的左翼作家还未能真正在创作中消化革命伦理,由于很少进入生产现场观察劳动者,他们很难写出形象饱满的工农大众。幸而老舍用《骆驼祥子》接续了现代文学谱系中的“人力车夫”,为读者追溯二三十年代北平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样貌提供了具象模特。30年代上海的革命氛围固然不可与北平的政治环境同日而语,北平的黄包车夫“包括了相当比例的市民——旗人、当过警察的人、商贩、失业匠人,与上海车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情况不同。北京匠人也不生存于包租制之下,境况要好得多,受教育程度、娱乐活动也比其上海同行要好不少”(裴宜理318)。但革命上海与市井北平的空间差异并不能为左翼缺少祥子式的人物提供充足理由——祥子的生命过程已将老舍触摸社会脉搏的非阶级思维展露无遗。正因为老舍是从文化层面观察底层市民的生存逻辑的,所以才能够写出日常劳动着的“劳动者”。
努力谋生却屡屡失败的“祥子”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当家作主的机会,从革命年代走来的“人民”成为新政权的政治主体,而绝缘于革命的祥子则需要一番洗练才有资格进入“人民”之列。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后记中,老舍检讨自己只看到社会的黑暗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删去“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在劳动人民翻身的今天“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老舍78—79)。1958年梅阡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给祥子安排了一个具有革命意识的工友小顺子,并且在结尾暗示祥子也将走上相同的反抗道路。原作中的消极沉沦一扫而光,祥子也成了劳动人民之光辉理想的代言人。反观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劳动者书写范式,只想顺利融入既定社会秩序而不思革命的祥子,其实从一开始便没能跻身左翼“大众”。
早在20年代末“革命文学”论争之初,甘人就认为从作家意识的角度出发,“人力车夫文学”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因为“第一第二阶级的人,不懂得第四阶级的心肠[……]即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甘人1405)。⑩这段话意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携革命话语“假革命”,批评革命文学论争中显现的激进主义话语形态。然而“人力车夫”作为一种“五四”符号,却在之后的历史中进一步被激进主义思潮所裹挟,继而与“人道主义”一起被“污名化”,受到左翼阵营的激烈批判。30年代初,瞿秋白将“五四”文学贬为“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认为这类文学是“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这种创作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洛文艺所不需要的”(史铁儿33)。而越发激进的作家出身论和不断强化的“五四”断裂论,应当也是“人力车夫”再未获得左翼文学青睐的重要原因。
梁实秋之所以讽刺“人力车夫派”,是因为觉得此派的“人道主义”“乃是建筑于一个极端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人是平等的’[……]吾人反对人道主义的唯一理由,即是因为人道主义不是经过理性的选择。同情是要的,但普遍的同情是要不得的。平等的观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的”(梁实秋62)。梁实秋出于古典主义的社会理想承认文明乃天才所创造,所以人的自然权利是平等的,社会地位则理应有别,故否定“人道主义”平等观念的过分理想化(李怡382)。左翼同样否定“人道主义”,理由却是人道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心理会麻痹大众的反抗意志而无益于阶级斗争,所以断然没有通过社会救济缓和阶级矛盾的必要,唯有壮大无产阶级力量,才能将眼前的苦难铸就为终极的解放。
左翼“以未来论当下”的乌托邦宣言,本质上是如何以革命时代的语言描述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语言学”问题——乌托邦语词化的困难造成了以革命的名义“偷换概念”并制造二元结构的表达乱象。“人道主义”因阶级论的介入而失去了“普世价值”,“人性”也因为违背了群体化原则而成为“阶级性”的对立面。每个被左翼批判的词语,都是因其普泛性所指范畴存在着窄化可能而被选中的,因为阶级论提供的是一种对人类群体进行拆分重组的新方式,所以从大范畴中抽取阶级小范畴就是构建一个完备革命话语体系必要的技术支持。激进表达并非阶级思维之单向结果,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失去了非此即彼的表达结构,革命理论的呈现将更加步履维艰。由于表达前提的迥然差异,左翼口中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信仰的“人道主义”原本就不在一个意义轨道上。被革命“征用”的词语本能地排斥非秩序性情感,并且以更加极端的方式为革命意志加持,“一次解决”有多么极端,这套革命话语为了实现对未来世界的承诺就会消耗掉多少“现社会”常规词意的合理性。
革命语言进入左翼知识分子的表达系统并不困难。如果说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是一种终极关怀,那么“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叙事就是将“人类”概念以阶级论思维揉碎重组而产生的新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得以成立,是因为阶级斗争理论编织了一幅极具冲击力的未来愿景,而“人力车夫”经历“五四”知识界的风流云散来到革命的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工业化格局中亟需人道主义救济的非革命群体,不仅外在于工农革命队伍,而且散发着消解革命认同的改良主义信号,其在左翼文学形象谱系中的悄然后撤,可以说也是革命文艺观与革命语言学裁汰机制运行之必然。
注释[Notes]
① 相关作品例如,诗歌:胡适《人力车夫》、沈尹默《人力车夫》、刘半农《车毯》、陈南士《走路》、顾颉刚《春雨之夜》、圣陶《人力车夫》、晴霓《人力车夫》、周恩来《死人的享福》、徐志摩《谁知道》《先生!先生!》、闻一多《飞毛腿》《天安门》等;小说:鲁迅《一件小事》、郁达夫《薄奠》、刘一梦《沉醉的一夜》、陈南士《走路》、舍我《车夫》、汪敬熙《雪夜》等;剧作:陈绵《人力车夫》、欧阳予倩《车夫之家》、于伶《银包》、洪深《贫民惨剧》、陈大悲《平民的恩人》等。
② 例如秦林芳:《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与“五四”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9(2017),150—158;姜振昌:《裂变与再生:作为左翼文学先声的“革命文学”辨争》,《鲁迅研究月刊》1(2015),41—48;张丽君:《论1920年代中国文学的左翼化》,《文艺理论与批评》1(2012),78—85;陈国恩:《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学习与探索》3(2008),190—194。
③ 有研究者根据精英意识的强弱程度将“民粹主义”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民为粹”的民粹观,即视人民为精粹,崇尚人民的力量与智慧,确信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种是自认为“民之精粹”的民粹观,在承认人民进步性的同时对其愚昧落后表示怀疑,坚信人民大众的力量需要知识分子的指导才可真正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39—45。
④ 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中说现在要将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倒过来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6(1920):42—43)。这里的“劳心者”,指的是包括智识者、军阀、官僚地主等在内的所有非做工者,与体力劳动者构成二元对立,通过控诉劳力者的“劳而不获”实现劳心者与劳力者之社会价值的倒置。
⑤ 翻阅关于劳动问题的30年代报刊,可以发现倾向于协调劳资矛盾、缓和阶级冲突的文章大多将讨论范畴限制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国计民生”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关心分配胜于生产,强调组织斗争胜于调查研究。
⑥ 例如《工会法》《工厂法》(1929年)、《工会法施行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施行条例》(1930年)、《工厂登记规则》《工厂检查法》(1931年),参见张廷灏:《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劳工法规详解》,法政学社编,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
⑦ 古田会议后,闽西红军对收编的土匪武装进行了思想与组织改造。1930年6月上旬《流氓问题》决议案指出,“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红军当前最严重的任务,表明红军极为重视并极力改造游民无产者思想意识方面的落后因素。1930年7月,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检讨了过去对土匪成分的宽容政策,认为一味拉拢土匪并无条件收编为赤卫队的做法过分估量了土匪的革命性,一定程度上使党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参见张雪英 苏俊才编:《闽西统战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82—98。
⑧ “此次以车夫能否认识马路名称为标准,其中又分全能认识,略能认识,及全不认识者三种。结果全不识者占半数以上,能全识者仅占百分之八·五五,由此益信人力车夫教育程度之浅薄矣。”[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一)(附表)》,《社会半月刊(上海)》1(1934):107]
⑨ 茅盾在《“现代化”的话》中对中国农村出现洋水车代替人力的现象和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场表示欢欣,认为这是中国的进步。(茅盾:《“现代化”的话》,《申报月刊》7(1933):105—110)
⑩ “若说人力车夫文学便是革命文学,即是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说有人力车夫文学总比没有好,我即不敢开口。但是我仍旧要腹诽,这是虚伪,比住在疮痍满目的中国社会里,制作惟美派的诗与描写浪漫生活还要虚伪。”(甘人140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元培:《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Cai,Yuanpei.“Labor Is Sacred.”PekingUniversityDaily27 Nov.1918.]
杜重远:《替人力车夫说几句话》,《新生周刊》2.20(1935):401。
[Du,Chongyuan.“A Few Words for the Rickshaw Puller.”NewLifeWeekly2.20(1935):401.]
段可情:《火山下的上海(续)》,《创造月刊》3(1928):26—36。
[Duan,Keqing.“Shanghai under the Volcano(Continued).”CreationMonthly3(1928):26-36.]
甘人:《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北新》2.13(1928):1403—1417。
[Gan Ren.“Miscellaneous Writing:A Response to Li Chuli.”Beixin2.13(1928):1403-1417.]
顾封:《读〈小说〉创作专号》,《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文学10》,郑振铎主编。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109—114。
[Gu,Feng.“Reading the Special Issue ofFiction.”Hongzang:CollectedProgressivePeriodicals(1915-1949),Literature.Vol.10.Ed.Zheng Zhenduo.Xiangtan:Xiangtan University Press,2014.109-114.]
谷士杰:《中国的人力车夫问题(续完)》,《劳工月刊》5—6(1936):1—14。
[Gu,Shijie.“The Problem of China’s Rickshaw Pullers(Continued).”LaborMonthly5-6(1936):1-1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4(1918):289—306。
[Hu,Shi.“On the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NewYouth4.4(1918):289—306.]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
[---.“More Discussion of Problems,Less Discussion of ‘Isms’!”WeeklyReview20 July 1919.]
蒋凌楠:《20世纪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史林》2(2019):158—161。
[Jiang,Lingnan.“The Entanglement and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Working Class’ in the 1920s.”HistoricalReview2(2019):158-161.]
蓝思勉:《上海市的人力车夫问题》,《新人周刊》1.49(1935):984—985。
[Lan,Simian.“The Problem of Rickshaw Pullers in Shanghai.”NewPeople’sWeekly1.49(1935):984-985.]
老舍:《〈骆驼祥子〉后记》,《老舍序跋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8—79。
[Lao She.“Postscript toCamelXiangzi.”CollectedPrefacesandPostscriptsofLaoShe.Guangzhou: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1984.78-79.]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Lee,Leo Ou-fan.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Trans.Mao Ji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1.]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李大钊全集》编委会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Li,Dazhao.TheCompleteWorksofLiDazhao.Vol.3.Ed.The Editorial Board ofTheCompleteWorksofLiDazhao.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ress,1999.]
李怡:《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
[Li,Yi.TheHistoryofWordsandtheEvolutionofThought:QuestioningtheConceptofCriticisminModernChineseLiterature.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2013.]
李双 杨联芬:《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探索与争鸣》12(2019):124—131。
[Li,Shuang,and Yang Lianfen.“From ‘All Four Classes Are Workers’ to the ‘Working Class’:Formation and Semantical Transmutation of the Idea of ‘Labor Is Sacred’.”ExplorationandFreeViews12(2019):124-131.]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晨报副刊》1926年3月27日。
[Liang,Shiqiu.“The Romantic Tren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ontinued).”MorningPostSupplement27 March 1926.]
马陵合:《近代人力车业治理的理念与制度困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2019):101—112,159。
[Ma,Linghe.“The Conceptual and Institutional Dilemm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Modern Rickshaw Industry.”SocialSciencesinChineseUniversities2(2019):101-112,159.]
茅盾:《现代的——》,《东方杂志》3(1933):19。
[Mao,Dun.“Modern—.”OrientalJournal3(1933):19.]
——:《“现代化”的话》,《申报月刊》7(1933):105-110。
[---.“Words on ‘Modernization’.”ShunPaoMonthly7(1933):105-110.]
《人力车夫不得组织工会》,《时报》1931年3月27日。
[“Rickshaw Pullers Shall Not Organize Trade Unions.”TheTimes27 March 1931.]
《黄包车释意和黄包车夫的等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月刊》10(1931):8—11。
[“Rickshaw’s Meaning and Class Difference between Rickshaw Pullers.”FortnightlyJournaloftheDepartmentofSociologyatFudanUniversity10(1931):8-11.]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Perry,Elizabeth J.ShanghaionStrike:ThePoliticsofChineseLabor.Trans.Liu Ping.Nanjing: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1.]
史铁儿:《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1932):8—42。
[Shi,Tie’er.“Real Problems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n General.”Literature1(1932):8-42.]
《关于日军打死沪西黄包车夫的特别报告》,《上海工会联合会》,上海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504—505。
[“Special Report on Japanese Army Killing Huxi Rickshaw Pullers.”ShanghaiFederationofTradeUnions.Ed.Shanghai Archives.Beijing:Archives Press,1989.504-505.]
宋钻友 张秀莉 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Song,Zhuanyou,et al.AStudyoftheLifeofShanghaiWorkers,1843-1949.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11.]
《不甘登记 人力车夫纷返原籍 南市车辆搁置不少》,《新闻报》1935年8月13日。
[“Unwilling to Register:Rickshaw Puller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Many Vehicles in Nanshi Have Been Put on Hold.”News13 August 1935.]
吴平:《农工衰败与人力车夫》,《劳工月刊》2—3(1936):115—131。
[Wu,Ping.“The Decline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Rickshaw Pullers.”LaborMonthly2-3(1936):115-131.]
杨程:《新感觉派的身体审美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Yang,Cheng.AstudyoftheBodyAestheticsofNewSensationSchool.Wuha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