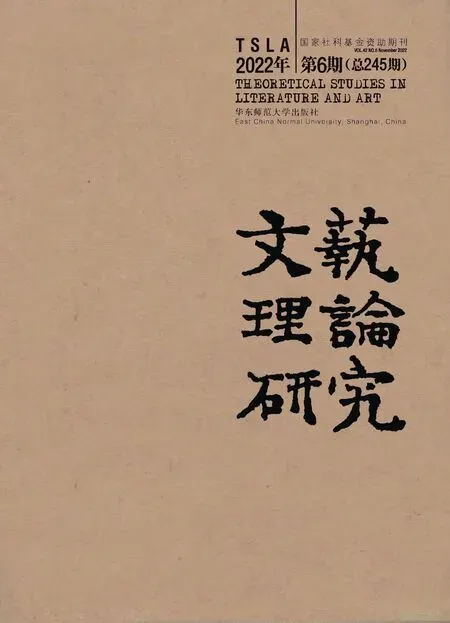叙事学对话与“中国声音”
——1997年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23-01-20江守义
江守义
自袁可嘉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以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兴趣,到1997年,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如火如荼。综观1997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翻译、介绍和运用。1997年杨义《中国叙事学》的出版,向学界展示了一个和西方叙事学不一样的“中国叙事学”,国内叙事学的研究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阶段。此阶段国内叙事学研究多头并进,不少研究可归入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之中,有些研究还尝试建构自己的叙事理论。对话和建构让中国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仍有不尽如人意处。
一、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
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叙事学研究进入了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国内学界的叙事学研究也出现了多头并进的情况:既有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又有对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关注和建构。译介、运用和1997年以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一是从介绍到梳理。梳理包括对具体术语演变情况和内涵变化的梳理以及对叙事学关注问题的梳理,前者如《外国文学》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栏目,对“叙事学”“叙述”“视角”“叙事性”“叙述距离”“不可靠叙述”等经典叙事学术语加以梳理和评述;后者如孔海龙、杨丽的《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围绕某一问题,将经典叙事学和诸多后经典叙事学派别的观点放在一起加以对照。二是从搬用到化用。化用主要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对西方叙事学理论加以必要的调整。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将叙述者分为“史官式”叙述者、“传奇式”叙述者、“说话式”叙述者和“个性化”叙述者;在叙事视角下专门讨论“编辑型全知视角”,就是依据古代小说的叙事特点来化用西方叙事学的相关理论。
对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关注和建构是1997以后新出现的情况(下文多有涉及,此处不赘述),它伴随着本阶段译介中的述评和运用中的化用,使得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态势。杨义《中国叙事学》出版后,国内叙事学研究慢慢出现了一股和西方叙事学对话的潮流。对话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体研究中含有对话精神,另一类是研究形式呈现出对话姿态。
第一类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中西叙事比较研究,二是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三是在评述、参照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时含有对话精神。
中西叙事比较多种多样,有宏观理论方面的比较,如方汉文《历史语境视域:中西小说的文类学比较》、王成军《神话·虚构·纪实——中西小说叙事诗学的思考》;有具体叙事形式的比较,如刘婧《试论中西方空间叙事异同》、王燕芳《基于语言结构的中西小说叙事模式差异研究》;有具体小说类型的比较,如吴琼娥《中西意识流小说主要差异——以〈酒徒〉和〈达洛卫夫人〉为例》;有小说研究路径的比较,如江守义《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单篇论文侧重于具体问题的比较,相对单一,著作的比较则复杂得多。吴家荣等人的《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2011年),从中西神话、中西戏剧文学、中西小说,中西叙事学四个方面展开比较,中西叙事学比较从西方叙事学的形式研究出发,从叙事人称、叙述聚焦、叙事方式、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五个方面展开。该书由于涉及问题过多,论述显得不够深入。将中西叙事比较推向新高度的是傅修延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按照傅修延的设想,该项目由七个子课题构成,前两个为“总论”,分别为中西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中西叙事思想比较,后五个为分论,分别比较神话、小说、戏剧、诗歌、民间叙事五个方面的中西叙事传统,研究时既要有全球化眼光,又要有本土立场(傅修延,《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论纲》1—6)。撇开分论部分的比较不谈,总论部分的两种比较,对话的意味就很明显。“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可以进一步深化《外国文学》梳理术语的专栏,让中西叙事传统在术语使用的差异中形成对话;“中西叙事思想比较”更是从叙事思想上让中西方叙事展开深层对话。
中国传统叙事研究表面上看和西方叙事学研究各行其是,但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取得的成绩,对西方叙事学有所补充,也能折射出西方叙事学的不足,可视为一种潜在的对话。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史传叙事研究。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和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可为代表,前者对“征引”模式和“君子曰”评论模式的探讨,后者对历史叙事本质的思考,都显示出叙事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这对西方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显然是一种反拨。同时,对史传叙事的关注,可以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倾向作一注脚,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反复出现的伦理教化与史传的治世抱负息息相关。传统叙事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关注,显示出西方叙事学忽视了一个事实:小说不仅是艺术,也是人生的写照。(二)援引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古代小说。除了上文所说的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外,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对古典名著的叙事学分析,如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王彬《红楼梦叙事》、刘绍信《聊斋志异叙事研究》、罗小东《“三言”“二拍”叙事艺术研究》。这些分析虽然都援引西方叙事学理论,但其目的是解读古典小说的魅力。相较之下,西方的经典小说叙事研究专著比较少,像热奈特《叙事话语》那样专门研究《追忆逝水年华》的做法,实属罕见。这意味着,西方叙事学从叙事形式的建构出发,经常选择一些叙事特点明显的小说,来说明某个叙事理论,反而忽视了小说经典的魅力。(三)对小说叙事某一方面的深入研究。如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小说评点彰显出中国小说叙事的特色,西方叙事学没有专门论述这一点,说明他们在建构叙事理论时考虑不够周全(西方小说中也有类似评点的情况,如卢梭《新爱洛伊丝》中经常出现“作者注”);《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显示出中国古典小说写人重于写事,对人品的关注超过对事件逻辑的关注,这既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叙事逻辑来判断古典小说叙事的成绩,也意味着西方叙事学过于注重人物的“功能性”特点是失之偏颇的。(四)梳理中国叙事传统。如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赵炎秋主编的三卷本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含熊江梅《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李作霖《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赵炎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认为中国文学有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两大传统各有自己的主要载体,这就使它们与文学体裁(文体)和文体学发生了关系”(董乃斌500),古文论、史传、诗词、乐府等都是构成叙事传统的有机部分,在梳理两大传统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文学史理论、诗学与叙事学等层面,与世界对话”(董乃斌532)。这种开阔的视野显然是西方叙事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意识到西方叙事理论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其目的是在“整理中国古代叙事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本土叙事理论”(赵炎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1)。指出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可谓对迷信西方叙事学的当头棒喝。(五)研究传统叙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对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那里也有,但主要是从作品内容中发掘出意识形态内涵,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探讨叙事观念。对叙事形态和物欲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西方小说研究中出现过(如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但在以文本为基础的西方叙事学研究中基本上付之阙如。换言之,西方叙事学对叙事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忽视,让西方叙事学在精细分析叙事作品的同时,却难以解释这些叙事作品何以形成。(六)图像叙事研究。如赵宪章主编的8卷10册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乔光辉《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当前是图像时代,西方叙事学主要通过电影研究来关注图像,对传统的版画、插图研究得较少。赵宪章等人从语图关系、文图关系出发来研究图像,无疑是对西方叙事学的有益补充。
某些对西方理论的评述或参照西方理论的研究,虽然没有打着中西叙事比较的旗号,但骨子里含有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精神。具体表现有三:(一)在介绍西方叙事理论时对其加以评述,进而形成对话。申丹可为代表。后经典叙事学的很多情况是由申丹首先介绍到国内的,她在介绍的同时还有所评述,有时还对西方的理论加以修正,体现出一种和西方平等对话的姿态。在介绍费伦修辞性叙事理论的时候,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由于没有认清“人物模仿功能的实质,费伦有时混淆了人物的模仿性与结构性或主题性之间的界限”(申丹,《多维 进程 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6);在介绍“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以及二者之争的时候,既指出认知至少有三种——以叙事规约为标准、以作者为标准和以读者为标准,三者之间相互对立,又认为试图调和修辞和认知(建构)的“认知(建构)-修辞”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涉及两种并行共存、无法调和的阅读位置。一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的阅读位置,另一种是‘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138)。无论是关于某个人的理论还是关于某个问题的讨论,她都发表自己的看法。(二)就西方叙事学的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或借用叙事学方法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总体上超越了西方现有的水平,让该研究完全有底气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刘阳《叙事逻辑研究》、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可为代表。不妨以龙迪勇的研究为例。他在弗兰克研究的基础上,将空间从文学叙事拓展到历史叙事和图像叙事,显示出一定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会导致他的研究成为叙事空间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西方叙事学的相关研究也需要从中汲取营养。此外,如赵毅衡在《空间叙事学》“序言”中所说,对空间形式的追寻,不仅“是一个‘故事发生在哪里’的故事”,也是一个“以何种方式生存于世的故事”,这就涉及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魅力(赵毅衡,《序二》6)。换言之,涉及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对话。(三)从中国叙事传统入手,参考西方理论来建构中国叙事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可为标志。他不满于中国叙事学界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意识到中西叙事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行原理”,所以“返回中国叙事本身”(杨义,《中国叙事学》10),从“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入手来研究中国叙事学,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从文本结构出发来研究叙事学形成研究路径上的差别,进而论述了中国叙事学独有的“意象篇”和“评点家篇”。这其实已经是在和西方叙事学进行对话了。随着思考的深入,在《中国叙事学》增订版中,他明确提出“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把握中国叙事形态”(杨义,《中国叙事学(增订本)》21)。从传统叙事入手来进行叙事学研究,并不是从杨义开始的[赵毅衡早在《苦恼的叙述者》(1994年)中就有这方面的尝试,但淹没在当时跟风西方叙事学的潮流中],但他是拥有建构“中国叙事学”雄心的国内第一人。杨义是在现代小说研究和古典小说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中国叙事学的研究的,他对西方叙事学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其研究更多的是展示一种对话姿态。
第二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会议上中西方学者的交流,二是国内出现了专门的叙事学期刊。
就第一种情况看,历届“叙事学国际会议”,都有西方学者参会。中西方学者共聚一堂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自然是一种对话。会议的交流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交流,但由于参会人员的复杂性,“叙事学国际会议”的“对话”氛围比一般的国内会议要浓厚一些。具体表现有:(一)大会发言中的“自由讨论”。由于中外学者学术语境的差异,对很多问题相互之间有隔膜,会议特别安排了“自由讨论”的时间。“自由讨论”阶段,惯例是外国学者的报告,中国学者提出商榷,中国学者的报告,外国学者提出商榷,然后报告者再加以回应。会议对报告时间有严格的安排(超时会自动掐断),对“自由讨论”的时间则宽松一些,会议的“对话”意味也由此多了一些。(二)大会“点评”中的“对话”。大会“点评”往往是礼节性的赞同,但有时也蕴含了中西叙事特点的对话。2015年,在昆明举办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奥沙利文作大会报告,他以西方的电影电视作品为例,讨论“系列叙事的六要素”,认为“系列叙事”将会是21世纪“一种重要的出版类型”(奥沙利文76)。傅修延在回应中指出,这种“系列叙事”的情况,在中国的明清长篇叙事作品中早就有所体现,《西游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回应式对话,虽然三言两语,但至少向西方学者传递出一个信息:你们现在觉得新鲜的叙事情况在中国古人那里早就有了。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叙事不必在西方叙事艺术面前妄自菲薄。“西方系列剧和中国传统叙事不谋而合的‘巧合’,勾勒出的是中国传统叙事在经历‘西学东渐’遭遇‘迷茫’后,又在当代与世界的接轨,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叙事蓬勃的生命力。”(卢普玲13)(三)小组交流中的讨论。参加小组交流的人,所学专业不一样,外国文学研究者对西方理论一般持赞同态度,文艺学研究者对西方理论有时持审慎态度,讨论有时会形成“交锋”。2015年的昆明会议,詹姆斯·费伦的大会报告是关于叙述可靠性的几种变化情况(费伦87—92),这显然是费伦对自己既有的叙述不可靠研究(契约型不可靠、疏远型不可靠)的补充。小组讨论时,有外国文学研究者认为,费伦的这个补充显示出对过程性不可靠的重视,有文艺学研究者就反问:难道契约型不可靠、疏远型不可靠不是从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吗?这种交流虽然是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但多少也有点中西“对话”的意味。
就第二种情况看,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之后,国内出现了三种专门的叙事学期刊。首先出现的是傅修延主编的《叙事丛刊》(2008),该刊第一辑就是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的论文选。“发刊词”说:“与国外叙事学研究潮流的复兴相呼应,目前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呈如火如荼之势[……]为了呼应目前的叙事学研究热潮并反映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创办此《丛刊》(傅修延,《叙事丛刊》1—2)。不难看出,《叙事丛刊》的宗旨是展示中国的叙事学成果,其用意就是和西方叙事学对话。事实上也是如此,除第一辑因为是会议论文选而收录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文外,此后只有第三辑上有一篇美国学者加百利的论文(因“空间叙事”专栏需要),其余的全是中国学者的文章。同一年的5个月后,唐伟胜主编的《叙事·中国版》问世。该刊借助美国《叙事》期刊在国际叙事学界的广泛影响,用“中国版”的标识来表明中国叙事学界融入国际叙事学界的用心。该刊的对话体现在其宗旨和栏目设计上。该刊的创办宗旨即交流对话:“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唐伟胜1)该刊的栏目有五个:一是“焦点”,每一辑有一个焦点话题(如第一辑是“不可靠叙述”、第二辑是“病残叙事研究”);二是“《叙事》最新论文选译”;三是“经典文本的叙事学阐释”;四是“国内学者论坛”;五是“书评”。前三个栏目都刊登国外学者的文章。由此看来,《叙事·中国版》主要是展示西方最新叙事成果,但从三个方面看,该期刊也具有“对话”意义:一是“中国版”所体现出来的对话色彩,二是“国内学者论坛”体现出来的对话和回应,三是“书评”栏目中同时包含对西方叙事学著作和中国叙事学著作的书评,这种对照也显示出一种对话精神。2019年,《叙事·中国版》和《叙事丛刊》合并为《叙事研究》,傅修延任主编,唐伟胜任执行主编,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的会刊。《叙事研究》设六个板块:国外来稿、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理论研究、叙事作品研究、跨学科叙事学研究、书评与会议简报。从“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并置来看,对话意味明显。第三种期刊是尚必武主编的《叙事理论前沿》,2014年出第一辑,该刊在栏目设置上,除了有“二十一世纪叙事学:西方视野”“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形成中西并置外,还有一个“西方叙事学在中国”,梳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接受的过程多少带有对话的色彩。就论文使用的语言看,“西方视野”中的论文是英文版,其他栏目则用中文版,也有点对话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是和1997年以前的研究比较而言的,不是说1997年以后的研究,都是从“对话”出发的。由于从事叙事研究的学者成分复杂(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各个领域都有),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其学术眼光和学术兴趣各异,其叙事研究的出发点也不一样。粗略地看(每个学者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无法一一讨论),外国文学研究者主要是介绍西方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并用相关理论来解读西方作品;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主要是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来解读现当代叙事作品;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主要是在理论阐释和比较过程中寻找中西叙事理论的差异;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情况较为复杂,有些研究者不屑于西方理论,专心用传统的考据、文献梳理、“知人论世”的方法来从事叙事研究,有些则比照西方叙事理论来突出中国古代叙事的特点。
二、叙事学的“中国声音”
上文所说的国内叙事学和西方的对话,已然发出了一定的“中国声音”,但它们夹杂在学习西方叙事学的潮流之中,所发出的“中国声音”还不明显。仅仅有这些对话,国内的叙事学研究还很难像现在这样,从众多的西方文论中脱颖而出。在对话的基础上,国内一些叙事学学者还建构了自己的叙事理论,在某些方面推动了叙事学的发展,从而在叙事学界发出了和西方平等的“中国声音”。“中国声音”的构成,大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二是对西方叙事学在方法上或范围上加以拓展,三是从西方叙事学入手的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彰显出中国特色。
第一个方面的“中国声音”,其前提是需要得到西方的承认,这无疑有很大的难度。申丹的“隐性进程”就是在西方叙事学界发出来的“中国声音”。申丹一直活跃在国际叙事学界,一直在和西方叙事学对话。她的《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研究》《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均可看作对话的产物。“隐性进程”也是在对话过程中产生的。它是申丹在阅读西方小说时发现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显性情节的一部分,也不是显性情节隐含的深层寓意,而是与显性情节相互独立的叙事暗流,二者并行发展,形成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共同表达作品的主题(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22—25)。就对话而言,申丹辨别了“隐性进程”和很多容易混淆的西方概念(如莫蒂默的“第二故事”、沃茨的“隐性情节”、马什的“隐匿情节”、艾伦的“隐匿叙事”、罗尔伯杰的“深层意义”)的区别。在隐性进程的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了双重叙事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问题。“隐性进程”获得西方叙事学界的认可,有一个过程。2013年开始,她在《今日诗学》《文体》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2016年,在劳特里奇出版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和修辞: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2017年,在欧洲叙事学协会双年会上就双重叙事动力问题作大会主旨报告。这些意味着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界已经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声音”。2019年底,法国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详细介绍了“隐性进程”这一术语,这意味着中国人所创造的“隐性进程”术语已被西方叙事学界正式接受。2019年11月,美国的《文体》杂志邀请她撰写以“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为题的目标论文,编辑部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加以回应,然后再由她对这些回应加以回应,目标论文和讨论的成果均于2021年初刊出,这意味着中国人首创的这一理论在叙事学界起到了“国际引领作用”(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325)。“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至此已不再是申丹个人的“中国声音”,而是被西方学界公认为推动叙事理论发展的“中国声音”。
第二个方面的“中国声音”,是在和西方叙事学对话的基础上,另辟路径对叙事学研究进行拓展,进而建构自己的叙事学理论。主要有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和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赵毅衡很早就开始进行叙事学研究,《苦恼的叙述者》(1994)借助结构主义叙事学来研究“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中国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关系”(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3),对话的意味很明显;四年后出版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有些内容与《苦恼的叙述者》重复,但该书有一个副标题“比较叙述学导论”,直接点明该书的意图在于中西对话,同时,作者在悉心梳理叙事学的过程中总结出“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1)这样一条叙述学基本公理,并指出:“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3)就赵毅衡对叙述公理的总结和对小说之外的叙述的关注来看,他显然不满足于西方叙事学建基于小说叙事研究上的既有成绩。有感于叙事转向导致很多以前不认为是叙事的体裁现在被认为是叙事体裁,他开始寻找各种叙事体裁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赵毅衡,《广义叙述学》12),于2007年开始了“广义叙述学”的相关思考,①2013年,《广义叙述学》出版。广义叙述学从符号学入手来研究叙述学,是“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述学”(赵毅衡,《广义叙述学》4),思考的是符号学原理在叙述学中的应用。简言之,广义叙述学即符号叙述学。它“研究所有可以用于‘讲故事’的符号文本之共同特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6),将所有的叙述按照再现类型和时向-媒介类型两条纵横轴线加以定位,然后从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间与情节、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四个方面展开。相对于已有的研究,广义叙述学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有所推进,如借助言语行为理论来讨论意动叙述、将叙述框架和人格性人物视为叙述者二象、叙述框架中的人格填充的多种方式、将(文本外)观众的实际时间纳入演示类文本叙述时间的考察范围,等等。此外,广义叙述学与当前叙事学的跨媒介研究以及多学科叙事转向的趋势保持一致,是随着叙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这自然将以小说为中心的西方叙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赵毅衡提出“广义叙述学”,是对中国学界习惯于学习西方而没有勇气超越西方感到不满,《广义叙述学》出版前,他曾在文章中感慨,他构建广义叙述学的想法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原因倒也简单:西方叙述学界尚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真的必须留在一百年来的旧习惯之中,只能让西方人先说,我们才能接着说、跟着说吗?”(赵毅衡,《广义叙述学:一个建议》150)赵毅衡的感慨固然是一方面,毕竟西方的有些研究说穿了也没啥意思,比如说,玛丽-劳勒·莱恩讨论电脑时代叙事学时提到的递归、堆栈、推进、弹出等(赫尔曼68—72),对小说叙事研究来说实在意义不大,在中国的聊斋系列小说中,类似情况早已出现。但更重要的是,似乎是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门槛太高,它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叙述学,又涉及多种艺术,一般人对符号学都未必懂,也很难同时熟悉多种艺术,更遑论兼有二者的广义叙述学了。同时,广义叙述学将叙述定义为“有人物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这一定义抽去了西方叙事学对叙述“过去时”的限定,更符合中文习惯,就此而言,“广义叙述学,理应更符合中国文化的需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19)。就赵毅衡的感慨和对叙述的定义看,他是想通过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广义叙述学》出版后,有一些回应,有人甚至认为广义叙述学开启了叙事学研究继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之后的第三阶段(方小莉7)。广义叙述学的“中国声音”已然发出。
和赵毅衡从跨学科的叙述现象来建构广义叙述学不同,傅修延没有选择这种宏大路径,而是另辟蹊径,从听觉入手来研究叙事。在寻找中国叙事传统来和西方对话的《先秦叙事研究》中,他已经谈到先秦的“记言艺术”,初现听觉叙事的萌芽。对文学叙事而言,听觉叙事算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但傅修延的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语音学角度来研究听觉,而是通过语音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听觉。对以前忽视听觉的叙事学研究而言,强调听觉叙事就暗含对话的意味。由于现实生活中视觉挤压了听觉,叙事文学的阅读主要通过视觉而不是听觉,这些导致了听觉钝化,但随着人工智能语音提示的流行,听觉在未来可能要比现在重要一些。就此而言,《听觉叙事研究》是一本面对未来的书。同时,人类在有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声音,一般人对声音也远比对文字敏感,每个人都可以听故事,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故事。口头叙事远远早于笔头叙事和镜头叙事,而且笔头叙事和镜头叙事中不乏口头叙事的成分(只是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笔头叙事中的情节和镜头叙事中的画面),就此而言,《听觉叙事研究》又是一本为过去纠偏的书。全书正文从“释‘听’”开始,通过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探讨(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33—139),论证了叙事文学可以书写人类倾听,听觉叙事因而有了强大的叙事文本支持。然后结合叙事文本,对音景、聆察、幻听、灵听、偶听、偷听等展开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听觉和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以示听觉叙事与人的主体性息息相关,叙事接受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进而理所当然地讨论听觉和叙事接受的关系。在具体讨论中,该书提出的语音独一性、聆察、灵听等术语,均是结合听觉叙事而创造出来的术语。总体上看,听觉叙事研究是以往西方叙事学所忽视的。此外,书中还援引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的判断,多少意味着听觉叙事可以作为中国叙事区别西方叙事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就听觉叙事研究填补空白而言,还是就听觉叙事是中国叙事的特色而言,听觉叙事研究都已在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第三个方面的“中国声音”,是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彰显出中国特色。上文曾分析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形成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但这种对话是潜在的,且基本上在国内古代文学界,很难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声。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本来已经发出了一定的“中国声音”,但由于两个原因,它主要显示的是一种对话姿态,其“中国声音”并没有引起西方的关注。其一,当时学界处于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狂热期,《中国叙事学》淹没在学习西方的热潮之中;其二,《中国叙事学》的五个部分“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意象篇”“评点家篇”中,前三个部分搬用西方叙事学,“评点家篇”对应西方叙事学的叙事接受,但具体论述时又和西方叙事学没什么关系;“意象篇”可谓中国特色,但杨义的论述,只是最后一部分“意象的功能”和叙事有关,其余部分与叙事关系不大。总体上看,杨义从中国叙事本身出发来梳理其特色,但梳理过程中,很少涉及西方叙事学的具体情况。搬用西方框架又在框架内自说自话,对西方叙事学而言,其中固然有“中国声音”,但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话姿态。要想在某个领域发出西方能理解的“中国声音”,需要从这个领域内部出发,有所突破和创新。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显然没做到这一点。相较之下,傅修延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叙事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早年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其用意在于用西方叙事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参照”(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294),这只算是对话。1999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从先秦叙事中来探究中国叙事之源,对西方叙事学而言,也属于自说自话。但到2015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就已经不再是对话,而是发出了“中国声音”。原因有三:一是在“导论”中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谈起,将中国叙事学纳入国际叙事学发展的轨道之中;二是该书“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的论述,表面上看是“自说自话”,但其骨子里始终遵循西方叙事学的形式分析路数,如“初始篇”联系虚构世界来研究神话,“器物篇”是对青铜器纹饰、瓷器颜色和瓷绘的讨论;三是该书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打破“外来影响的遮蔽”(傅修延,《中国叙事学》20)。总之,从西方叙事学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中国叙事传统,可以让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学大体处于同一语境中,而不是语境各异的自说自话。同一语境中的比较,自然可传递出“中国声音”。
三、反思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当前的叙事学研究在国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能及时了解西方叙事学发展动态,在多方面和西方叙事学进行对话,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发出了“中国声音”,推动了国际叙事学的发展。相比较其他的西方文论,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可谓成绩斐然。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国内叙事学的成绩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叙事学界的弱势地位。国内虽然有申丹这样国际叙事学界的佼佼者,有尚必武这样年轻的欧洲科学院院士,但总体上看,国内叙事学还没有走出去。就代表“中国声音”的叙事学研究而言,除了申丹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动力”受到国际叙事学界的肯定外,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和中国叙事学建构,虽然通过“叙事学国际会议”传给了国外同行,但其影响主要还是在国内。反观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则要好得多。比如说,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学”,关注的是反模仿的虚构叙事,主要是后现代叙事中的一些情况,其用意是拓展既有的叙事理论。这当然有价值。但究竟什么是“非自然叙事”,理查森并没有讲清楚。他将叙事区分为非虚构叙事、模仿虚构叙事、反模仿的非自然虚构叙事,表面上看起来很清晰,但问题在于非自然叙事就存在于前二者之中,这样看来,非自然叙事只是叙事文本中的一种现象。作为现象,非自然叙事究竟要讨论哪些问题,理查森也没说清楚,或许是因为后现代叙事的特点导致他说不清楚。但理查森既然将非自然叙事称为“理论”,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就应该清晰。就此而言,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远远不及《广义叙述学》和《听觉叙事研究》,但它在国内颇受欢迎,这或许和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跟风西方乃至膜拜西方有关。叙事学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西方叙事学,而是适用于一切叙事艺术的叙事学,但由于它是西方首创的,西方的强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历届的“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学者发言结束后基本上不参加中国学者的讨论,在不缺少翻译的情况下,这就显示出一种高傲的姿态。西方学者也很少像中国学者虚心学习西方那样来关注中国的叙事艺术(浦安迪等汉学家不是西方叙事学的主流)和叙事研究,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研究似乎就应该是弱势的。
其二,要理性对待西方叙事学成就。后经典叙事学已打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藩篱,表现出多种研究趋势,但有些研究趋势未必是后经典叙事学所独有,譬如说,叙事学的跨国界研究,西方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转向,实在值得推敲。因为经典叙事学时期,叙事学就开始跨国界了,国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叙事学研究就是叙事学跨国界的产物。罗兰·巴特在叙事学兴起之初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年)中说:“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2)经典叙事学所归纳的种种叙事形式,本来就没有国界限制,又何来跨国界之说?此外,西方叙事学是基于西方叙事艺术的实践而来的,未必适合中国叙事艺术的实际情况,我们接受时也需要理性。不妨以叙述可靠性为例,西方叙事学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文本中心主义。从文本出发,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一致,为可靠叙述,不一致为不可靠叙述,看起来似乎很清晰,没什么问题。但结合中国叙事的实际情况,问题就出来了。在《前七国孙庞演义》中,孙膑在不知道庞涓的阴谋之前,处处被庞涓算计,在知道庞涓的阴谋之后,处处都能防患于未然,还能预知事件走向进而算计庞涓。孙膑和庞涓的本领都没有变化,先是孙膑被庞涓算计,后又是孙膑算计庞涓,叙述是否可靠呢?从行文看,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不仅是可靠叙述(因为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始终一致),而且是小说意图实现的关键。小说主旨是通过孙膑仁义、庞涓奸诈来宣扬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小说中的矛盾现象源于人物的道德品质。这样看来,西方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来理解叙述可靠性,就值得推敲。
其三,后经典叙事学阶段,不可抛弃结构主义叙事学所采取的形式分析方法。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结构主义藩篱,对文本形式的归纳转为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是否不需要形式分析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后经典叙事学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和以前的小说研究的差异主要就在于对形式的重视。后经典叙事学也需要文本形式的分析,它虽然不归纳出某种形式,但却以经典叙事学已经归纳出来的形式为分析基础,即使在分析某一作品的文化内涵时,也需要从形式入手来加以分析,而不是脱离形式,随意发挥。赵毅衡很早就意识到,“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282—283),只有通过形式分析走向形式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才能避免掉进形式分析的陷阱。梁冬丽、曹凤群的《通俗文学‘有诗为证’的生成与流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全书从史学背景、诗骚传统、程式化过程、流变、海外传播与影响几个方面对“有诗为证”这一常见的通俗文学形式进行文化学考察,全书围绕“有诗为证”展开,又超越其形式层面的分析,考察其形成背景和过程,将形式分析和形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宗教等因素结合起来,它是形式研究,但又超越形式研究。西方虽然有分析某一阶段小说形式变化的专著,但还没有针对某一形式的专著。梁冬丽等人的这本书,虽然不被中国叙事学界所熟知,但不容忽视。
其四,加大向国外同行译介中国叙事研究的力度,同时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申丹的“隐性进程”之所以有国际影响,是因为她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系列英文论文。对研究者来说,只要某个观点能真正推动研究进展,都会受到重视,但国外叙事学研究者一般不通中文,这就需要国内加大翻译的力度。国内叙事学界不乏翻译人才,但多是将西方理论翻译到中国,少有将中国的研究翻译到西方的。尚必武在西方期刊上发了一篇主要是介绍性的《经典叙事学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与变异》,就让西方学者愿意就自己的研究和中国学界进行对话。吕克·赫尔曼和巴特·维瓦克在他们合著的《叙事分析手册》的“中译本前言”中表示,他们正是从尚必武的这篇文中了解到中国叙事学界的一些情况,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国有所反响。这意味着西方也有人意识到要和中国叙事学界进行对话。但对话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只有多翻译一些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和西方的对话才能多一些。翻译中国叙事学成果,是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的一种方式。此外,学界还应该多关注一些本土化研究,目前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的专著,除了一些中国小说的叙事学分析外,只有王瑛的《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这一本,和诸多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著作相比,远远不够。
其五,加大中西叙事比较的力度。如上文所说,中西比较研究已经有一些,但从对话和“中国声音”的角度看,还要进一步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叙事的特色。罗怀宇的《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以西方经典叙事诗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2016年)通过叙事范畴和概念来进行中西比较,但该书用力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对中西叙事思想差异缺少必要的总结。赵炎秋将中西叙事和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勾连起来,指出中西叙事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赵炎秋,《文化与文学》1),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中西小说观念和悲剧观念的差异。这是2022年叙事比较的最新成果,但这种比较是宏观的,具体深入的中西叙事差异的比较尚不多见,在比较中如何彰显中国叙事特色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六,用力于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五四以来,中国的叙事艺术多少受到西方的影响,真正代表中国叙事特色的是传统叙事。只有将中国传统叙事研究深入下去,才能总结出中国叙事的特点,进而修正西方叙事学总结出来的形式规则;才能寻找出叙事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中国叙事和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才有可能让国内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处于真正的对等地位。上文所说的叙事学本土化、翻译和叙事比较研究,都绕不开传统叙事研究。如上文所说,传统叙事研究的成绩是多方面的,对西方叙事学多有补充,按理说应该在国内叙事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但由于古代文学界重视考证和叙事学界追随西方的原因,传统叙事研究在叙事学界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研究[谭帆等人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可为代表,该书虽然没有普林斯《叙述学词典》涵盖面广,但对每个术语的梳理要深入得多。此外,通过对传统叙事中“‘事’的多义性”和“‘叙’的多样化”的梳理,谭帆还指出“叙事”一词的古今差异(谭帆83)],应该对叙事学研究有所帮助,但这些研究主要在古代文学界产生影响,叙事学界几乎没有反响。要想通过传统叙事研究彰显中国叙事特色,打破学科壁垒势在必行。后经典叙事学提倡跨学科,文学内部的古代文学和文艺学、外国文学之间都壁垒森严,显然不符合跨学科的理念。如果叙事学界能吸收古代文学界的成果,用叙事学路径总结出传统叙事的特色,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将会踏上一个新台阶。
概言之,1997年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可以和西方对话,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出了“中国声音”。但总体上看,西方叙事学仍处于强势地位,要想改变这一态势,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加大翻译和中西叙事比较的力度、加强传统叙事研究都是可供选择的途径。
注释[Notes]
① 虽然方小莉在访谈中说,赵毅衡2008年提出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的构想(方小莉8),但在2007年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上,赵毅衡提交的论文《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就已经对“广义叙述学”展开思考,该文中提到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向度,是“广义叙述学”对体裁分类的基本依据之一。另外,赵毅衡倾向于称“叙事”为“叙述”。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2—42。
[Barthes, Roland.“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Trans.Zhang Yinde.AStudyofNarratology.Ed.Zhang Yinde.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9.2-42.]
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Dong,Naibin,ed.AStudyoftheNarrativeTraditioninChineseLiterature.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2.]
方小莉:《符号叙述学的兴起:赵毅衡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16):5—14。
[Fang,Xiaoli.“The Rise of Symbolic Narratology:Interview with Zhao Yiheng.”EnglishandAmericanLiteraryStudies2(2016):5-14.]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Fu,Xiuyan.AStudyofAuditoryNarratolog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21.]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ChineseNarratolog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论纲》,《学术论坛》40.2(2017):1—6。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AcademicForum40.2(2017):1-6.]
——主编:《叙事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ed.JournalofNarratology.Vol.1.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8.]
——:《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
[---.TheSecretofStorytelling:LiteraryNarrativeTheory.Nanchang: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2020.]
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Herman,David,ed.Narratologies.Trans.Ma Hailia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2.]
卢普玲:《中国传统叙事与批评的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6年8月15日。
[Lu,Puling.“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and Criticism.”GuangmingDaily15 August 2016.]
肖恩·奥沙利文:《系列叙事的六要素》,舒凌鸿译,《叙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论文集》,谭君强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67—77。
[O’Sullivan,Sean.“Six Elements of Serial Narrative.” Trans.Shu Linghong.NarratologicalStudies:ReviewandDevelopment—CollectedEssaysoftheFif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NarratologyandSeventhAcademicConferenceofNarratology.Ed.Tan Junqia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7.67-77.]
詹姆斯·费伦:《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一种修辞诗学》,王浩编译,《思想战线》2(2016):87-92.
[Phelan,James.“Reliable,Unreliable and Understatement:A Kind of Rhetorical Theory.” Ed.and trans.Wang Hao.IdeologicalFront2(2016):87-92.]
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Shen,Dan.AStudyofDualNarrativeProgress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21.]
——:《多维 进程 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2002):3—11。
[---.“Multi-Dimensions Progress Interaction:On Post-Classical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of James Phelan.”ForeignLiteratures2(2002):3-11.]
——:《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4(2006):133—143。
[---.“What Is ‘Unreliable Narration’?”ForeignLiteratureReview4(2006):133-143.]
谭帆:《“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3(2018):83—96。
[Tan,Fan.“On the Semantic Origin of ‘Narrative’:Also on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LiteraryHeritage3(2018):83-96.]
唐伟胜:《前言》,唐伟胜主编:《叙事·中国版》(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6。
[Tang,Weisheng.“Preface.”EssaysonNarrativeinChineseTranslation.Vol.2.Ed.Tang Weisheng,Guangzhou:Jinan University Press,2010.1-6.]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Yang,Yi.ChineseNarratology.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7.]
——:《中国叙事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ChineseNarratology(RevisedVersio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9.]
赵炎秋:《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2):1—8.
[Zhao,Yanqiu.“Culture and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hought.”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1(2022):1-8.]
——:《明清近代叙事思想》。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NarrativeThought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andModernTimes.Changsha: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Zhao,Yiheng.GeneralNarratology.Chengdu: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13.]
——:《广义叙述学:一个建议》,《叙事·中国版》(第二辑),唐伟胜主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49—160。
[---.“General Narratology:A Suggestion.”EssaysonNarrativeinChineseTranslation.Vol.2.Ed.Tang Weisheng.Guangzhou:Jinan University Press,2010.149-160.]
——:《序二》,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6。
[---.“Preface 2.”SpatialNarratology.By Long Diyo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4-6.]
——:《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TheTroubledNarrator.Beijing: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1994.]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WhentheSpeakerIsSpoke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