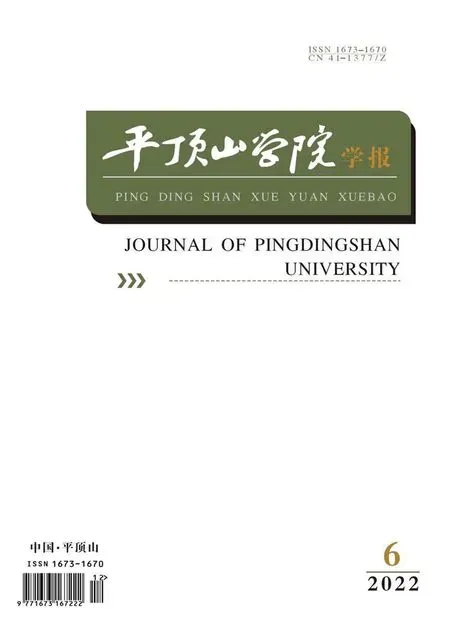从王国维之避而不谈柳永词看其学术品格的分裂
2023-01-20陈莹
陈 莹
(浙江大学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王国维《人间词话》是词论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它以传统词话的形式,点评百家词作,字字珠玑,精妙隽永,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词学理论。依照这套标准,柳永的词作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人间词话》定稿六十四则,提及柳永的不过寥寥几处。王国维似乎有意不谈柳永,原因何在,值得深入探究。
一、柳词符合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人间词话》提出了几个主要的评词标准,如“境界”“真”“自然”“隔与不隔”等。柳永作为宋词名家之一,其词作符合王国维所言的“境界”,不造作,直抒胸臆,情真意切,极少用典或代字,并且词作数量庞大,家喻户晓,不应被排除在王国维的审美视野之外。
(一)柳词有“境界”
“境界说”是王国维评词的核心理论。《人间词话》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又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1]1秦观“杜鹃声里斜阳暮”,固然意境可嘉,却不免令人思及柳永的“断鸿声远长天暮”[2]35。这悲歌寥落的壮阔长天,怎就不及斜阳冉冉、杜鹃啼血的暮色?柳永词此类苍凉意境甚多,如《八声甘州》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词中气象万千,意境苍凉萧瑟,深远阔大,苏轼赞其“不减唐人高处”[3]183。又如《雨霖铃》之“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4]18,意境开阔,如不系之舟。南国天地,暮霭沉沉,孑然一身,哀鸿凄惶,此境可谓极矣。再如《少年游》之“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4]245,胸中有无我之境界方可为之。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柳词符合王国维所钟爱的审美境界。
(二)柳词言“真”
“尚真”是王国维的审美追求,也是其文学批评实践的原则,它是王国维判断诗、词是否有“境界”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与“境界说”成一体系。《人间词话》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2柳永性情率真,表达方式多为直陈。他即事言情,直抒胸臆,多用白描写景状物。俗字俚语信手拈来,绝无雕琢之态,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花枝》《秋夜月》《忆帝京》《两同心》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如《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4]384
这是一首羁旅相思词,柳永少时离开家乡,流寓江南,夜夜买醉。此词作于一次孤眠惊梦之后,平白直叙,造境凄清。“今宵”“昨宵”,景况如一。次句一个“又”字,传达出极不耐烦的情绪。小饮虽无意趣,却“初更过”才归,可见愁闷之深。中宵惊起,但见“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满腔幽怨跃然纸上。“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对上片所略过的情事作了补充,原来梦里与情人同衾共枕、欢洽入眠。相思情切与好梦难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寸心万绪,咫尺千里”,无限惆怅。“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由自己的思念联想到对方的思念,深入一层。结尾重复修辞,意境浑然,耐人寻味。全词前后照应,层次清晰,清新质朴,凝炼生动,是谓真情感、真语言、真境界也。
又如《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4]18
此词作于柳永因作词忤宋仁宗,离开汴京,与一位恋人惜别之时。柳永充分利用《雨霖铃》长调声情哀怨的特点,写凄恻的离恨。上片融情入景,暗寓别意。时值暮秋,萧瑟阴沉,寒蝉凄切。一二一的句法结构,幽咽顿挫,有力地表达出凄凉的况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称其“曲处能直,密处能疏,鼻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5]。全词在章法上不拘一格,自远及近,疏朗清远,声情双绘,奕奕动人。自是缘情而发,情真意切,断人肝肠。
柳永作词,感情真挚,平白晓畅,正是《人间词话》所激赏的抒情风格。然而,尽管王国维后来甚至对工于雕琢的秦观、周邦彦词的评价有所改观,对柳永却一直回避不提、态度隐晦,与他论词、做人皆倡导的“真”性情相去远矣。
(三)柳词极少“代字”
宋代作词,使用“代字”的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沈义父《乐府指迷》言:“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筋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沈氏所揭示的这一修辞现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最先称之为“代字”,此说被后世学者延用至今[6]。
王国维反对用代字,《人间词话》云:“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1]8秦观“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13个字,仅仅描绘了一个人骑马经过楼前的情景,便是“意不足、语不妙”的表现。高明的词作,无需代字。又道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1]8。王国维显然不认同沈伯时的主张,作词如果按图索骥,对照类书所列的字词用典,这样的词作如同工具书一般,意义何在呢?反观柳永作词,极少用代字,感情真挚,语妙意达,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屑代,不必代,不暇代,与典故泛滥的文人词判然有别,这正是为《人间词话》所推崇的语言风格。
(四)柳词“不隔”
除此以外,王国维还非常强调作词“不隔”。何谓“不隔”?《人间词话》道: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1]9
在言简义丰的《人间词话》中,以这么大段的文字谈“隔”与“不隔”的问题,足见王国维对“不隔”的重视。这段文字历数从东汉到南宋的知名诗词,惟独“隔”过了柳永。殊不知柳词最是“不隔”之词,柳永最是“不隔”之人。比如柳永的歌妓词,与其他词家相比显得别具一格。如《鹤冲天》:
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弹。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4]137
再如《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少年、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抵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著,如何是。[4]42
两首词均以歌妓的口吻将人前的光鲜和人后的落寞娓娓道来。这样的作品于柳词中不在少数。多数词人作艳词,津津乐道于歌妓的容貌、体态、服饰、技艺,他们模仿女子的口吻,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情感的摹拟、揣度、臆测,只是为了消遣助兴。歌妓多数情况下只是取乐的对象,作词者并没有真正表现她们的内心世界。柳永却在科举屡试不第的困境中,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境同情她们的命运,是歌妓们的“知心人”。于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词能触动歌妓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愿望,在教坊乃至民间社会广为传唱,正是以真挚、“不隔”取胜。
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柳永词讳莫如深——不直接地鉴赏,也不明确地否定,而是尽量不表达、不评议。《人间词话》几个主要的评词标准,如“境界”“真”“自然”“不隔”等,皆是柳词的风格特点。王国维为了阐释“境界”说,甚至借用了柳永的名句(虽然不提出处),由此可以推知王国维在审美上对柳词的真实态度。所以,王国维避而不谈柳永词,原因并不在词作本身。
二、王国维有意不谈柳永词
夏承焘在《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一文中有言:“好的选本实际上是选者自己的一种创造,好的选本是一个有机体,贯注在中间的是选者自己的见识、议论。”[7]其实不止选本如此,选评本也是如此。评论家在评论之前,已有自己的选择:首先是评谁不评谁的问题,其次才是评价高低的问题[8]111。王国维有意不谈柳永词,正是他根据内心的某些标准做出的选择。
(一)“屯田轻薄子”
“三境界说”是王国维评词的核心理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1]6
王国维对第二重境界的阐释,引用的正是柳永《蝶恋花》中的名句。以一句道一境界,可见该句在王国维审美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之高。然而,王国维却一口咬定这首词是欧阳修所写。在这里,他把词人“人格”的优劣与作品的高下混为一谈(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王国维无意犯了个小错误,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王国维是在有意抹杀柳永的文学史地位)。他判断作品归属的唯一依据是作者的品行。《人间词话》道:“《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1]26王国维还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柳永的鄙夷,如“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间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1]26。又一次提及了柳永,直指他“凉薄无行”,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下如此判断。
北宋之时,文人流连于秦楼楚馆乃是常事。即便是被王国维高度赞誉、品行端方的欧阳修也有不少风流韵事。如《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
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9]85
欧阳修在词中自比为与宰相之女偷情的韩寿,并自命“天赋与轻狂”“长是为花忙”,词中隐喻之意甚为不堪。此类内容的词作还有《玉楼春》《忆秦娥》等,“轻薄之意”未尝逊于柳永。宋朝文人狎妓成风,欧阳修在扬州做官时,与众美姬日日笙歌,通宵饮酒作乐。张先八十五岁纳十八岁的小妾——“十八新娘八十郎,一树梨花压海棠”被传为文人风雅的佳话[10]12。同样是作艳语,在王国维眼中,柳永是轻薄无行,欧阳修却是“虽作艳语,终有品格”。王国维为什么对两个词人采用双重评价标准,值得深思。柳永与欧阳修,一个是科举屡试不第、浪迹民间的落魄才子,一个是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走上儒家“学而优则仕”之路的官僚知识分子,王国维抬举欧阳修而贬低柳永,恐怕并不是因柳永品行有“瑕疵”,而是柳永偏离了儒家士大夫“仕途经济”的传统理想追求。
(二)崇尚道统,不喜狷狂
王国维不谈柳永,还因为他不欣赏逸出儒家道统范畴之外的“狂者”。柳永喜用“狂”字来表现纵情笙歌醉舞的不羁情怀。“狂”是柳永词的一大特性。纵览柳永《乐章集》,含有“狂”字的作品共有25例。如:“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4]151(《如鱼水》)“洞房饮散帘帷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4]340(《昼夜乐》)“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凭谁去、花衢觅。”[4]367(《征部乐》)“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4]269(《倾杯乐》)它们或追忆少年漫游的情景,表现耽于玩乐的心态,或表现虚掷光阴的苦闷,寄托出世游仙的遐思,偶尔流露出仕途不第的失意。“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4]148塑造了自己怀才不遇,淡泊名利,笑傲江湖的狂者形象。
朱熹认为:“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11]135“狂者”固然恃才傲物,但是抛弃了儒家正统的社会进阶道路。他们对自身和社会规则都无法认识清楚,于是容易碰壁,一腔热血转为一蹶不振,或愤而离去,隐居避世,或浪迹教坊,饮酒作乐,落拓不羁。以上种种,皆是儒家道德理想不提倡的。王国维对于“狂者”并不是一味地批判,相反,他非常欣赏儒家价值理想范畴之内的“狂者”。以他对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的评判作为例证。王国维常以“狂”“旷”“豪”等词语来评判苏辛二人,称他们“雅量高致”。这样的评价是建立在人格基础之上的。“东坡、稼轩,词中之狂。”[1]31“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1]30王国维欣赏的“狂者”,是忠君爱国、心忧社稷的君子,而不是放浪形骸的浪子和侠客。人格标准无疑嵌入他的审美观中,以致他对柳永、贺铸等人不置可否。
(三)意图标举儒家理想人格
叶嘉莹先生从王国维各个时期的词作、书信、批评文章中,推断出王国维有“一意追求儒家士大夫完美人格”的倾向[8]113。王国维生于清末浙江海宁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饱读诗书,七岁起入邻塾,师从潘紫贵、陈寿田先生,接受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在时局动荡的晚清,社会道德滑坡,许多人可以为了蝇头小利不顾原则。目睹这一切的王国维深深忧虑,想以儒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情怀转变世风。因此,他对那些行为符合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特别是有家国情怀的词人大加推崇,如辛弃疾、陆游,甚至亡国之君李后主。对于行为偏离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词人,如混迹教坊的柳永、豪爽行侠的贺铸、寡妇再嫁的李清照,均避而不谈,迫不得已提及一二处,亦颇有微词。对歌妓、狎客也持鄙夷态度,因此对此类题材也有所贬斥。王国维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柳永词的价值,他在《人间词话》未收稿的15则中提道:“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1]20肯定了柳词的艺术水平,并将《八声甘州》和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并举,给出“格高千古”的评价。可见,王国维心中是有一杆秤的。但是,他出于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偏执维护,故意视而不见,移花接木,企图消解柳词的地位。在学术与人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把人格标准凌驾在学术原则之上。
三、性格弱点导致学术弱点
王国维曾评价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12]18。他体弱多病,四岁时失去母亲,缺少爱护,形成了忧郁的个人气质。中年时期,妻子和父亲相继离去,他失去了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变得更加沉默寡言。49岁,长子病逝,一个月后又同挚友罗振玉绝交。一年后,政局动乱,50岁的王国维投湖自尽。动荡的时代、坎坷的人生造就了王国维悲观的性格。他不仅思想中充斥着浓重的悲苦情绪,还对忧郁的词人、凄凉的词调尤其偏爱。他心理脆弱,行事偏执,看人待事易钻牛角尖。这些人格弱点,也被他带入了学术之中,成为学术弱点。
(一)多病才子的忧郁情调
王国维自己的诗词,常带有一种看透世相的苍凉和莫可名状的孤独。23岁时便咏出“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13]137这样的句子。病弱之躯和敏感的内心强化了他悲观厌世的情绪。王国维从哲学中寻找精神慰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特别吸引他。王国维读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拍案叫绝,称其“思精而笔锐”,悲观厌世的思想深深契合了他“性复忧郁”的内心,对他此后的学术风格有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对气质忧郁、思想悲观的词人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如他盛赞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4在他看来,生于深宫之中的李煜有一颗不染世俗的“赤子之心”。但想写出“眼界始大”的词作,必让这颗心经历一番血泪折磨,王国维因此称李煜词为“以血书者”“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5,将李煜词上升到无与伦比的高度。事实上,王国维的个人处境和忧国之思让他对李煜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才让他发出了这样的激赏。王国维同样激赏的纳兰性德、冯延巳等,都是气质忧郁的多病才子。相比之下,柳永之词就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般,令王国维那颗忧生忧世的心倍感厌恶。
(二)极端化的偏执认知
王国维对同一个词人、同一类作品的评价常有偏执化的倾向。例如,王国维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真”,《人间词话》对于“真”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1]5,感情都不真的人,观物怎么能真?观物都不真的人,境界怎么会高?境界不高的人,怎么能写出高水平的词句?可见,王国维对“真”的追求达到了偏执的程度。“真”固然是一种至高、至纯的境界,却不等同于主观论事,一味地自我抒发。王国维却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1]4试问除了襁褓中的小儿,谁能不涉世、不阅世呢?即便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1]4的“赤子”李后主,也经历了亡国之痛和沦为阶下囚的凄惨生活,焉能谓之阅世浅?可见,王国维对词人人格之纯“真”的要求,几乎苛刻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成了一种偏执的完美主义信条。这种“真”的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人能达到呢?在“真”的信条下,王国维非常赞赏民歌风格,对用词直白、内容露骨的牛峤《菩萨蛮》,大赞其“情真”。王国维又对《古诗十九首》里赤裸裸的思妇情欲描写大加赞赏,认为这表达了“真性情”。相比之下露骨程度远不及此的周邦彦词却被王国维刻薄地比作娼妓,鄙夷之情溢于言表:“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1]7此后王国维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对周邦彦词的评价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盛赞其为“词中老杜”[14]423。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心态有两极化倾向,常先有偏颇之词,后又矫枉过正。
(三)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早年的作品,带有很强的个人偏好和主观色彩,其中的一些观点王国维自己在晚年已经不再认同。不论是前后矛盾的评价,大相径庭的态度,还是随处可见的双重标准,都指向王国维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各种原则相互碰撞,学术标准、审美风格、道德规范、价值追求相互分歧、对立、冲突。王国维仅在一处捎带提及柳永时进行了正面评价:“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才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14]423这一则将柳永在词中的地位等同于白居易在唐诗中的地位,评价非常之高。可见王国维并非自欺欺人之辈,他虽然鄙薄柳永,对柳词还是有一个公正的定位。王国维一方面明知柳词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又偏执于内心的种种观念,不愿承认柳词的价值,于是只好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使自己不必直面内心的冲突,陷入两难困境。多重标准的相互碰撞,造成了他学术品格的分裂。
四、结语
柳永的缺席是《人间词话》的一大缺憾。王国维将柳永词排斥在《人间词话》之外,既是读者的损失,也是他个人学术上的损失。王国维学术造诣很高,陈寅恪称赞其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2]11。一向冷峻的鲁迅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5]417。然而,王国维对完美的偏执造成了自己学术上的不完美。柳永被略去并不是孤例,贺铸、李清照、王安石、吴文英、张炎等也遭到了冷遇,原因不尽相同,但都与王国维内心的某些偏见有关。王国维因个人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将多位在中国诗词史上成就不凡的词家排斥在《人间词话》之外,着实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