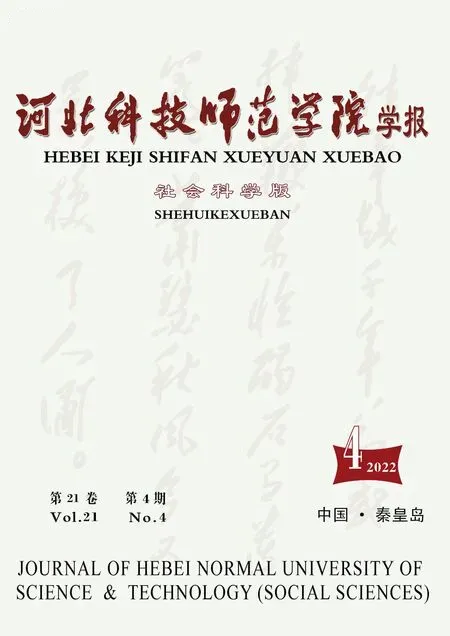钱澄之《屈诂》的文本阐释与注释特征
2023-01-20张启惠
张启惠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文献侧重:《诗》《易》为主
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术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苑》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1]90可见传统儒学以经治世的思想由来已早,经学阐释的传统也从未断绝。出身经学世家的钱澄之,在此环境的熏陶中经学笃实,《屈诂》自然显示出鲜明经学阐释的特征。钱氏在注释中征引经典文献,其中包括《诗经》《周易》《春秋》《国语》《史记》《礼记》等;在经典文献中,以《诗》学、《易》学内容为最主要引用对象。钱氏治骚时转相发明,将《诗》学、《易》学思想用在阐释屈原作品之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直接征引《诗》《易》词句,解释字词之意;再次是征引《诗》《易》文献解释句意;最后用《诗》序、《易》学思想来阐释屈原作品与屈原思想乃至屈原形象的构建,从而进行义理申说。
(一)屈骚词意
钱澄之秉承“以骚继诗”的诗学宗旨,征引《诗》《易》文献来训释屈骚字词之意,这是最基本的训释手段。钱澄之在选录《楚辞集注》基础上精简释文,对基本字词出阐释,如 “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中对“鹈鴂”的解释,钱澄之引《集注》释云:“鹈鴂,即《诗》‘七月鸣鵙’之鴂,声相近,阴气至,则先鸣而草死也”[2]175;《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中解“九”之义,云“九阳数之极,所谓之九天”[2]222,用易之阳爻为九,来阐释天之九重;《天问》“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中“承辅”解释,钱氏诂云:“承辅,则官而不名,《商颂》‘阿衡’是也。”[2]251“阿衡”出自《诗经·商颂·长发》,《长发》篇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即“伊尹”,天降之卿士,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贤臣,故曰“承辅”,可见钱氏引《诗》释骚的正确性。
(二)屈骚句意
钱澄之征引《诗》《易》文献,解屈骚章句之意,大体是为了演绎《诗》《易》之思想,恰巧印证自序中“窥其大旨之所在”“诗学易学之义也”[2]4。《离骚》篇中多次引用《诗》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四句,钱氏诂曰:“开章诉陈氏族,见己为国宗臣,无谊可去。古上下通称朕,谦辞也。朕者渺小者之称,胎中初有微形称朕,犹云兆耳。《诗》:‘维岳降神’,原曰吾以降,其自命不凡矣。”[2]143“维岳降神”出自《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篇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3]669钱氏用其阐释“帝高阳之苗裔”,把握住其自命不凡的意味,对于屈原自我审视有着正确的构建;对于屈原所处政治环境恶劣的解读:“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身亡兮,终然夭乎羽之野”,钱氏诂曰:“原自信心不可惩,忽述女嬃之詈,通国唯一之姊关切耳。言女嬃知原‘终鲜兄弟’,此身关系非轻,故深虑其夭死也。”[2]158用《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一句表明屈原所处环境之恶劣,正如原诗中所诉“纷独有此姱节”“孰云察余之中情”等,举世朋党,屈原孑然一人矣,与《郑风·扬之水》中“终鲜兄弟,实为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女”[3]198正相符合。
《天问》中“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迎班禄,不但还来”四句,钱氏诂云:“王者家天下,季德也。该秉,谓父子相承;恒秉,谓亦世相守,虽失之,必思中兴也。朴牛,指浇。《易》所云:‘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以喻元凶也。言少康有中兴之志,焉得此元凶授首乎?”[2]242“恒秉季德”四句叙述少康中兴之事:田猎获禽,遂以灭浇,钱氏用《易·明夷卦·九三》之意,即“贤明的诸侯或君主趁着南征狩猎的时刻,灭掉昏君”,这与少康中兴事迹完全符合。此句历来多解,但钱氏之解亦可备一说。再者如《九章·怀沙》:“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钱氏诂曰:“自惟事业无成,存此志于万世,可也,志之有像,《易·蛊》上爻所云:‘志可则也’。”[2]286即引“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表其将以清虚高尚之志为法则。
(三)屈骚思想
征引《诗》《易》来解屈骚思想,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离骚》“求女”解读与屈原形象的自我构建。首先《离骚》“求女”的解读,钱澄之采纳吸收汉儒后妃之德的思想融入到对于“求女”解读,将“思得淑女”意旨比附到“求女”这一虚拟活动上,并反复强调“女”之重要性,为何要求女?《离骚总诂》云:“乃为帝阍所拒,不得见君,然后叹息于举世之溷浊好蔽美也。不得已而思求女,盖君而又贤妃在内,不致小人尽惑已甚。上官、靳尚与郑袖比,犹皇甫七子‘恃褒姒为奥援’也。《车辖》之诗,恶褒姒乱国,思得贤女以内助,所以拔其惑本。屈原犹是意此。”[2]186钱澄之在《离骚总诂》认为屈原见君受阻,乃是小人在内,惑乱欺君,因此思得贤女拔出惑本;并以《小雅·车舝》中“娶妻以德”意旨,比附屈原“求女”,亦渴望如“高山景行”之季女;紧接着钱氏又阐释求得贤女的重要作用,《天问》“登立为帝”四句曰:“自桀伐以下,皆言女德。桀得喜以致殛,舜因二姚以受禅;妲己宠以璜台而亡商,女娲生而有骇形而王天下。”[2]239可见“思得淑女”诗学思想对钱澄之的影响极为深重。其次是对于屈原人物性格的再塑造上,用《易》中思想来丰富对于屈原的解读。钱澄之构建屈原人格,基础是儒家传统解读:忠臣孝子,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四句,钱氏诂曰:“美人,自况是为。臣之于君,犹女之于夫。故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2]145引《文言》“地道”“臣道”“妻道”一说,凸显屈原追随楚君忠贞之行,并在自序再次提到,《庄屈合诂自序》云:“吾观庄子述仲尼之语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曰:‘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思?’而终勖之以‘莫若为致命’。夫庄子岂徒言其言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义命自处也,审矣。”[2]4钱澄之认为孝子之侍亲为命,忠臣事君为义,二者既不能懈怠于心,又不能逃避与天地之间;二者之最高境界则是行事而忘身,舍身而取义。
二、文构辨说:“文无次序”之矛盾
(一)概说:“文无次序”辩证继承
王逸《楚辞章句》就屈原作品结构称其文无次序,钱澄之在其基础上,秉承“性情说”诗学观,对于屈原作品阐释以情感为基础,提出“意至而词至”。《楚辞屈诂自引》云:“以屈子之忧思悲愤,诘屈莫申,发而有言,不知其为文也。重复颠倒,错乱无次,而必欲以后世文章开合承接之法求之,岂可舆论屈子哉” “吾尝谓其文如寡妇夜哭前后诉说,不过此语,而一诉再诉,盖不诉不足以尽其痛也。必谓后之所诉异于前诉,为其徇其次序、别其条理者,谬矣”“则见其情绪之感触:有无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至,忽然有词。词同而以不同,则未尝无次序无条理也。”[2]139总观钱澄之对于屈辞篇章结构之论,似乎是矛盾的,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其论述是在注释中不断变化发展的。首先钱澄之认为屈原之辞乃是忧思悲愤郁结而作,故有重复颠倒、错乱无序之表象,因此不能用文章之法牵强对比,如果强为其次序是谬矣;进而提出屈原乃是因意而构,意之所至发而为词,若是理清屈原复杂的心理活动,就能够大致描摹出屈原作品结构,即钱澄之所谓“未尝无次序无条理也”。
(二)辨说:《天问》结构论述
《天问》篇章结构划分,能够代表钱澄之阐释屈骚作品的矛盾心理,首先是钱澄之按李陈玉《楚辞笺注》将《天问》总体划分为三部分,大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问天:首句“遂古之初”至“何盍何晦”四句,共44句,是问天上许多不可解之事。其中从天地之形何人营造、何人传之、何人识之,再到日月星辰,何列何属,大都是天地初形之未可解之事。
第二部分——问地:“不任汩鸿”四句至“鲮鱼何在”四句,共68句,问地上许多不可解之事。其中包括鲧禹治水、昆仑悬圃、烛龙雄虺、黑水玄趾、鲮鱼鬿堆等,大都是地上怪异之事,屈原一一列而问之。
第三部分——问人事:“禹之力献功”至“何试上自予,忠名弥章”,共261句,问人间许多不可解之事。人间世事又分为三小部分,笔者暂且为其划分:首先是问夏之事,自“禹之力献功”至 “帝乃降观”四句;其次是问商之事,自“简狄在台”至“何圣人之一德”四句;再之是问周之事及春秋杂事,自“稷维元子”至文末。
钱澄之虽按李陈玉之法为《天问》划分了大体结构,但是在训释过程,钱澄之所透露的观点是复杂矛盾的。首先是《天问》解题,钱澄之诂曰:“文无次序,只是就壁上所见,随发问端,不必求其伦次。先儒谓原杂书于壁,楚人集成之,理或亦然。”[2]221“后儒欲一一详对,以释其疑,亦愚矣。”在解题时钱澄之认为其无次序,有两种可能:一是仅就壁上所画,随发问端,不必特求其次序;二是屈原之辞杂书于壁上,楚后人集之而成,因此无次序;并且对前人进行辩驳,即仅事诂释,而不是强一一对之;紧接着又再次强调其次序仅仅是壁上所画,“白蜺婴茀”四句钱澄之诂曰:“胡为此堂,言画此事于此堂。……只此数章,忽及羿,忽及鲧,忽及仙人,皆就壁上画所见而问。本无伦次,而注者强为穿插承接,固矣![2]236可见钱澄之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不能为划分次序而次序,否则就是顽固愚蠢,甚至可笑!“何试上自予”四句,钱澄之又曰:“小序甚明,因祠堂壁上画有种种奇怪故事,随‘其所见,一一呵’而问之。或相承,或不相承,或喻己意,或据彼事,本无伦次,仍其荒唐。注者为之考据载籍,分别章句,辩证其是非,大似像痴人说梦也。”[2]255
总观《天问》中无次序申说,虽与文中划分篇章结构所矛盾,但是却与其注释原则“力戒穿凿”相一致,钱澄之《庄屈合诂自序》云:“于屈不敢强事穿凿,以求其悲愤,惟是依文释义,使学者章句分明以进窥其大旨所在。”[2]4《楚辞屈诂自引》又道:“吾盖深恶夫牵强穿凿,以探其前后之贯通,故以诂名。”[2]140因其深恶牵强穿凿,所以阐释篇章结构时,更倾向于“依壁而发问”无次序之论,同时又在文中自然引用李陈玉对于《天问》的大体划分,仅限于从天、地、人事三部分,而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只是为遵循其“章句分明”“力戒穿凿”训释原则。
三、文情体悟:以情注骚
明代中晚期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却异常繁荣,在此双重作用下,晚明社会产生剧烈的变化,整个社会风气由循规蹈矩的古典生存方式,转变为物欲膨胀的庸俗人生[4],在这种时代潮流下,一方面人们极力想要冲破原有的秩序,另一方面则是人欲的放纵(或者对于天理的蔑视,对于人欲的承认和肯定)。从王阳明本是以“拯救世道人心”而发起的心学,再到其后学李卓吾等高扬其个性解放的呼声,逐渐演变为对天理的蔑视,对于至情的肯定。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众多文人深受“主情”意识的影响;钱澄之虽然经学世家,但在经历了晚明腐败黑暗的政治、抗清等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之后,钱澄之对于屈原情感体悟应该是更加深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屈原之人评价,性情之正;二是对于屈原作品的解读,以情贯之,更能贴近作品本旨,典型的“以情注骚”,以及以情注骚的理论基础,即“性情说”的诗学传统。
(一)解屈原:性情之正
首先,钱澄之在《田间易学》曾对“性情”做过阐述,认为性乃一体之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即“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5]193,并且提出与个性解放社会思潮相一致的性情理论,“天下无无情之性,若情槁则性灭矣”[5]193。可见钱澄之对于一体性情的重视,并且将性情之说用到屈原之人的解读上。钱氏在明末“主情”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于屈原之人之事的评价及阐释,体现着“性情”的主要特征。钱澄之《庄屈合诂·庄屈合诂自序》云:“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2]3可见钱氏对于屈原之人之事是以包容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认为“性情深至”;肯定其忠君念国,却因谗见疏,并且对于否定屈原之人的论调发出反问之辞:“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意即凡伯家父等人(家父《诗经·小雅·节南山》、凡伯《诗经·大雅·板》)怎与屈原相提并论。
此后钱澄之又在《屈诂》进一步完善“性情深至”阐述,《庄屈合诂自序》云:“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也。吾谓《易》本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之为也。庄子之性情,于君父之间,非不深至,特无所感发耳。诗也者,感之为也。若屈子则感之至极也。”[2]4显然钱氏在 “以屈继诗”“以庄继易”基础上,认为 “《易》本乎时”“《诗》本乎性情”,因此在时的影响下,二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即“潜”“亢”之别;并且钱氏将道的感悟与个体“性情”联系在一起,认为至性之体方可悟道,悟道后才能做出死节之行。那么何为性情?何为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性情”有详细说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6]221;对道与性情的关系阐述引谢氏之语道:“学者于此二者,可见性情之正也。能识圣人之性情,然后可以学道。”[6]92可见钱氏对于性情的认识来源于此,因此屈原人格中“性情”与明末“主情”意识下的性情,即屈原性情符合孔孟“君子”之性情,可称之“性情之正”,在钱氏的诗论中也可以寻到蛛丝马迹,《叶井叔诗序》道:“诗也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准礼义以为情,则情必本诸性。可知三百篇以下,惟汉为近古。魏晋以还,情亦少杂矣,然其诗犹沉绵曲郁,而不至于放,则犹有礼义存焉。至六朝,而情荡矣,所述者大抵皆艳冶之私、靡丽之习,其事至褻,其声极新,令闻之者心志滔淫而不自持,卒至于溃防裂检,风俗横流,国随以亡,皆情误之也,是岂知有性情者乎?”[7]258-260,钱氏在诗序中表明性情应符合“礼义”,并批评了六朝靡丽放荡之情乃是“情之误”,是“不知性情之正”表现;因此才有:识性情,然后学道;体道后,方可死节。性情之人,体道;体道之人,死节。显然,钱氏对于屈原接受,融入一己之志,将屈原阐释为“性情之正”体道之人,屈原沉江而死乃是存道之行,这符合钱澄之所秉持的遗民价值体系,或者说符合其内在的遗民意识,即典型“存道以救世”。在《九章》中诂云:“以命则死不可逃;以义则死不可让,《论语》所云‘当仁不让师’也。愿勿爱者,即以自勉,又以勉后之君子也。后之君子,有不获于君者,勿萌贰心,惟以吾为类耳。是故屈原之死,非为愤激,所以作万世之忠之榜样也。”[2]288钱氏强调其“非为愤激”,引《论语》“当仁不让师”,忠于君而不萌贰心,屈原之死乃为万世之忠的榜样,虽然这将阐释落入传统忠君之俗套,但是正符合钱氏所说的性情之人体道,体道之人死节。
(二)解作品:以情贯之
屈原曾在《九章·惜诵》自述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由此观之,其作品饱含着屈原难以诉说的情感,原悲愤不能自已:悲其身不见用,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反复缠绵,前后诉说其情。然历代学者,自汉以迄清,对于屈原的主要研究都是附属于时代之学(如汉代之经学、宋代之理学、明代之朴学),望其或 “厚人伦,美教化”,或辅成王道,然而对于理解屈原的情感却无所裨益。虽然主流研究沿着时代之学轨迹在发展,但是从朱熹开始,“就诗论诗”,以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屈原及作品,再到明中晚期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蓬勃发展,“主情”意识深入人心,对于文学作品的情感体悟更是高涨,使文学作品回到其本身,这也印证了“诗缘情”的本质。钱氏在崇情思潮下,对屈原作品的理解,自然是更接近“发愤以抒情”之本旨。如对《九章·怀沙》“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四句的阐释,钱氏诂曰:“任重、载盛二句,与《小雅》‘不输尔载,终逾绝险’同义,指党人用事者言,怀瑾握瑜,自命也。” 这里钱氏直接道明“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与《小雅·正月》“不输尔载,终逾绝险”同义,即贤能辅国方能度过危险,否则就会“陷滞而不济”,《正月》中抒情主人公孤独、愤懑、忧伤的情感与屈原可谓是一致的,异代同感。钱氏在对于屈原其人的阐释基础上,其“性情深至”“至性至情”,认为其作品有感于“事于君父”,乃“感发之极也”,对于其作品也是在“性情”的特征下,注重体悟屈原心中情感,因此能够体会到屈原文辞背后“情不能自已”深邃的情感。钱氏在《离骚总诂》提到对于情感的体悟:“原疏而宪令亦废不行也!原所悲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之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故一则曰‘哀民生之多艰’,再则曰‘相观览民之计极’,而终之曰‘莫与为之美政兮’,则原情可见矣。”[2]187钱氏感悟到:屈原被谗见疏,宪令废而不行,美政理想无实现之日,亦哀国事日非、民生之多艰,原悲愤之情不能自已。
(三)析文论:性情说
钱氏以情注骚,论人也是以性情观之,这都源于钱氏的文学观“性情说”,即“诗以道性情”,诗最主要的的任务就是抒发一己之性情或是志趣。首先是是的本质,诗本性情,在钱氏的文集中曾多次提及,《庄屈合诂自序》曾言:“诗也者,性情之事也。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2]3钱氏清楚地认识到诗人内感于物,发而为诗,诗的本质乃是言志;钱氏在《田间文集》言:“政以人情为本,达乎情,斯可以达于政耳。诗也者,情之至也,吾达吾情,亦因以达人情,政不外是矣。”可见,钱氏准确把握了诗歌的本质,乃是一“情”字,只要以情达情,用诗人的情感去体悟原诗作品,便能把握住诗之本旨。但其性情强调符合礼义,其中《田间文集·叶井叔诗序》道:
“诗以道性情。而世有离情与性而二之,是为乌足与语情乎?诗也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准礼义以为情,则情必本诸性。可知三百篇以下,惟汉为近古。魏晋以还,情亦少杂矣,然其诗犹沉绵曲郁,而不至于放,则犹有礼义存焉。至六朝,而情荡矣,所述者大抵皆艳冶之私、靡丽之习,其事至褻,其声极新,令闻之者心志滔淫而不自持,卒至于溃防裂检,风俗横流,国随以亡,皆情误之也,是岂知有性情者乎?”[7]258-260
其中钱氏明确表示自己秉承传统儒家诗教:首先“诗者,性情之也”,“无情不诗”的性情论的主张,其次要止乎礼义,因此对于汉诗之后的艳冶之私、靡丽之习是强烈批评的,认为“国随以亡”,是纵情之果;并且指出“其诗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云”,屈原显然符合其标准,或者就是其作诗的楷模。因此,再回顾楚辞篇目的选择上,必然是要符合儒家诗教,注重文学作品的真情实感。
其次,是构成诗之性情的重要因素:真,或者说是作品中的真情实感。钱氏《田间文集》言:“夫性情之事,盖难言之,难于真而。譬如优孟登场,摹写忠孝节义之事,一笑一啼,无不酷肖,而人知其言之皆妄,以其皆沿袭之言,而非自出之言。自己出者,有诸己而后出,所谓真性情也。”[7]309无论是平和还是激越,只要是出于一己之怀,都是真性情的表现。当然这也是钱氏推崇屈原作品的原因,尤其对激越之诗的评价,更是表现出不俗的文学观。《田间文集》钱氏言:“吾诗悲,非世所乐闻,其声往往激楚也。”“诗有音,感而成音。彼吴锁干而吟者,无情之音,不足听也。是以论诗者当论其世,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钱氏谈到自己“激楚”之声是所处时代与社会现实所造成的,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这正如屈原辞赋作品,屈原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遭受的困厄与磨难,是屈原忠于内心以及现实生活所创作出来的,是无法变得温柔敦厚。因此,钱氏以情达情,才更好地体悟屈原作品怨愤激越之情。
四、文本注释特征
(一)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钱澄之诂屈,贯彻着“不牵强附会”“实事求是”的方法,又继承朱熹《集注》的体例,基本是以四句为一小节作注,有些章节依据文意则是六句、八句一注,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具体格式:先标注字音;次引《集注》解释字词、句意,或先酌采前代诸家之说;最后“诂曰”,乃是始叙作者之意:训释词语在前,观点在后;或总结章句旨意,或阐发义理;诂的征引的情况在某些篇章中即可诂,也可不诂,即可引,也可不引,其条例是较为宽松,在统一体例之中有着变化和发展。因此这样的注释原则会使其注释不拘束于体式,更加顺畅清晰。总体观之整饬划一,层次分明,条例清晰,字义、读音、章句义理兼顾,显然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离骚》“朝吾将济白水”一节为例:
朝吾将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阆,音郎。緤,音薛,一作绁。)
《集注》:“《淮南子》言:‘白水,出昆仑之山’,阆风,山上也。女,神女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佚女”“三姚”,将遍求也。
【诂】曰:昆仑,天柱、悬圃、阆风皆在其上。自悬圃上升,反于阆风,盖兴尽而反也。反顾,南顾楚地也。反顾流涕,无端哀高丘之无女,是时楚宫南后、郑袖并宠于王,秀与靳尚辈表里惑君,后之不问,谗于嬖比,此王所以终不悟也。故思得贤女,正位宫中,以废嬖而沮谗。高丘,楚地,疑襄王前既有阳台神女之说,故以寓言。[2]167
从上述条例来看,在继承《集注》基本注释体例下,《屈诂》优势是极为明显的。与汉宋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相比,继承了这种体例的《屈诂》,其层次清晰,更让人一目了然。并且与明清时期一些注本相比较,钱氏这一体例选择上更胜一筹。
(二)兼采诸家,融会贯通
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1]90正如《经学历史》概述言之,钱澄之“诂屈”遵循着实事求是、以意逆志的方法和原则,取前代诸家之说,择善而从之。其间酌采林希逸、张凤翼、黄文焕、汪瑗、李陈玉等宋明诸家观点,以严谨开明的态度征而有名,以求融会贯通整个注释系统,避免穿凿附会。
以《离骚》训释为列: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予以假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览,一作鉴。余下无于字)
集注:“皇,皇考也。”“揆,度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而。《礼》:‘生子三月,父名之。’‘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故字虽朋友之职,亦父之命也。”○汪瑗曰:“五臣以正则为释原名,以灵均为释平字。”○张凤翼曰:“言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和天地中正,故始赐以善名。”
【诂】曰:初度,犹初生也。览揆,揆度也。犹今初生推测福命也。意其生有异于常儿,故名以平而字以原。高平曰原,高而能平,所以勖之。故原因君之见疏,而转念亲之赐名之义。[2]143
本句注屈原名与字。钱澄之先录《集注》释原由平中来,正则、灵均分别对应平与原,是美称。紧接着引《礼》中记载古时命名之习俗,亦强调父之命名的重视。后则引汪瑗、张凤翼之说,尤其是张氏之说,似有些自命不凡的味道。之后钱氏自诂与上大体一致,演绎集注之意;与之不同的是:结合屈原自身因君见疏之事,来解释此句安置的特殊意义,即“异于常儿”因以赐名。再如《天问》训释: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为兹何功?孰初作之?(圜,与圆同)
《集注》:“圜,谓天形之圆也。则,法则。九,阳数之极,所谓九天也。”○张凤翼曰:“言天之九重,求而知之乎?又谁之功力初作之乎?”○黄文焕曰:“问九重从何一重作始也。”[2]222
在训释 “圆则九重”这四句上,钱澄之首先录朱熹《集注》解字词之意,后分别引张凤翼、黄文焕注解章句之义,连续流畅,并无强拉硬拽之感,使得整句注释完整如己出。上述释文中,钱澄之虽引用朱熹《集注》、黄文焕《楚辞听直》、汪瑗《楚辞集解》等诸多参考文献,但不是毫无标准的采纳,而依据文本之旨,根据实事求原则,严谨开明的态度,按照释文体例的需要,酌情采纳,使得诸家之说能各归其位,各释其义,无赘尤之嫌疑。
(三)平正通达,富有诗韵
钱澄之《楚辞屈诂自引》云:“吾盖深恶夫牵强穿凿,以探求其前后之贯通,故以诂名。”其训诂旨在前后语句之贯通,使后人读之章句分明。在体例上,继承《集注》体例,四句一释,先注音,后解字词之义,之后串讲句意,阐发义理。注释以疏通前后文意为主,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简洁利落,段落之间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对于章句之间的解释连贯舒畅,或先录集注,或兼采诸家之说,或直接表明一己之寄托,一气呵成。从而在阅读上是平正通达,无凝滞淤堵,或牵强生涩之感。以佶屈聱牙、难以理解的《天问》训释为例: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集注》:“问往古之初,未有天地,故未有人,谁得见之,而传道其事乎?”[2]221
真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瞢音蒙。闇与暗同。冯音平。)《集注》:“此承上问,时未有人,今何以能穷极而知之乎?”[2]222
明明闇闇,何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此问: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为乎?阴也,阳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为本?何者为化乎?”[2]222
上文三章问天地之初形成之事,其注解虽引《集注》,但仔细观察,钱氏省去了朱熹“一一答之”的义理繁琐阐释,而是直接采用章旨的解释,因此钱氏的注释更加连贯通畅,通俗易懂,更不会使楚辞文本再添加上一层“理学迷雾”,读者也会望而却步。
再看《九歌》《九章》篇目训释:
广开天门兮,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纚尘。(涷,音东,从水)
【诂】曰:“天门开,神将降也;乘玄云,巫往迎也。司命,天上星神。其来也自天,其去也冲天。篇中两君字指神,两吾字皆巫自称。先驱、清道,皆作巫语,所以迎神也。”[2]203
鸟兽鸣以諕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畞兮,兰茝幽而独芳。(諕,音豪。苴,音祖。比,音比。薺,一作苦。茝,一作芷。)《九章·悲回风》
【诂】曰:“万物各从其类:鸟兽以同群而号,草苴以不芳而比,鱼龙不逐队而行,荼薺不同畞而生,秉性各殊,臭味自别。此兰茝所以幽而独芳也,则君子岂能与小人并世乎?当今之世,非吾世也,惟早自決而已。”[2]304
观炎气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霜雪之俱下兮,观潮水之相击。(液,音亦。)《九章·悲回风》
【诂曰】:“观炎气而窺烟液,悲霜雪而听潮水,自言其魂气所之,随时即境,无冬无夏,无不可以寄其情也。”[2]310
览其上述释文,除平正通达,简易流畅之余,钱氏似乎也注意形式工整对称,即“天门开,神将降也;乘玄云,巫往迎也”,语言雅致优美,即“万物各从其类,鸟兽以同群而号”“观炎气而窥烟液,悲霜雪而听潮水”等,这类语句使其注文平易通达,又富有诗韵。总体来看,钱澄之的《屈诂》既没有像汉代王逸《章句》逐句作注,也没有像宋代朱熹《集注》中掺杂义理,或者《补注》中大量的名物训诂,也没有明代心学影响下空疏注释臆说的学术风气。钱氏吸取王、洪训释优点,但不是逐句作注;依《集注》体例,但却没有繁杂义理,也无“一一对之”的牵强;因此其注释显得更为平正通达,语义流畅。并且作为诗人学者的钱澄之,其注释的语言也讲究形式,富有诗韵。
结 语
《屈诂》分量虽不如《诗学》《易学》,但其注释精简扼要,平易流畅,兼采诸家,又融会贯通,集中体现钱氏治学特色。钱澄之文献征引在经学阐释的基础上,偏重诗、易文献的征引;文构阐释在文无次序的基础上,融入以情体意的重要方法,并且在《天问》结构阐释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前后变化;文情的体悟则是在明末主情意识的思潮下,明末遗民共同的文学观:性情说。因此,钱氏贯穿着以情注骚的原则,并且抓住了屈原内心复杂的情感活动以及志趣,从而把握住屈原作品的整体脉络,用诗人的情感不断揣摩变化的感受与情思,使其在清初遗民楚辞学中争得了宝贵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