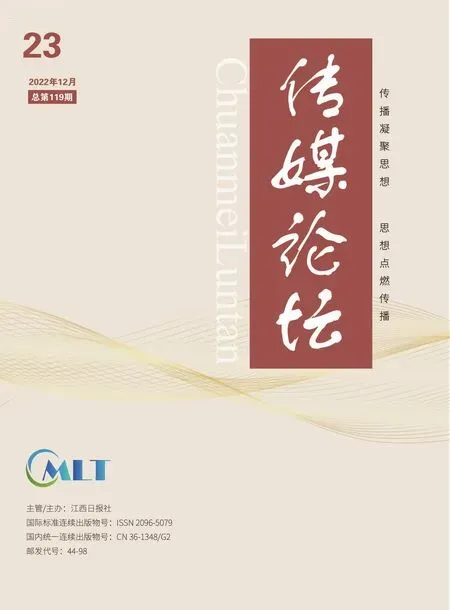侠情、悲歌与产业嬗变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美学风格呈现
2023-01-20王大留朱旭辉
王大留 朱旭辉
电影《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创造了中国IP系列电影的票房纪录,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相较前者,《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战争场面更加紧凑,场景更加恢宏,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业制作的天花板,而其在美学风格上的尝试与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与参考价值,为电影美学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电影美学理论体系。
一、暴力美学:直观凛冽与武侠风格呈现
暴力美学是战争电影艺术创作中美学呈现的永恒话题,是电影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激发情感的桥梁。电影创作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暴力美学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表现形式渗入到电影产业中[1]。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暴力元素直观且逼真,通过毫不避讳地展现战场的血腥画面使观众直面战争的残酷。同时,经过徐克导演艺术化的处理,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元素。直观凛冽的场面塑造加之浪漫化的武侠风处理,使电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暴力美学风格。
《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暴力美学风格呈现出直观、逼真的特征,气势磅礴的宏观战争场景与硝烟弥漫的近身肉搏场面相配合,直观刺激的影像效果和逼真强烈的音效技术相统一,将暴力美学的情感张力与情绪宣泄推向极致。影片在影像层面充分使用了“燃烧”带来的冲击力,正如片中战士在谷底清点牺牲人数,燃烧弹的热浪侵袭而来,红黄色的光带着炙烤的热气在志愿军脸上掠过,火光袭去,一半的山体变成焦炭色,震撼人心的场景画面使死亡的阴影弥漫在整个山谷,并在观众心底埋下直观、恐惧的心理投射。影片中多次呈现志愿军牺牲在熊熊烈火中的骇人场面,比如许多战士被喷火器活活烧死,在烈火焚身之际仍坚持向敌人开枪;何长贵上一秒还在部署工作,下一秒便被坦克的炮弹击中,身体被炸裂成碎片,消失在一片火光中,场面突发、直观且血腥,揭示了冷酷、血腥、残忍的战争本质。受众在观看此类暴力画面时所带来的痛感、刺激感以及震撼感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同频共振的审美体验,在激荡与惨烈中寻求同化与共鸣,在审美再创造中实现对暴力元素的理解与认知。此外,影片中飞机枪弹旋转着打下来把山谷几位战士扫射得粉碎,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碎片继而消失,只剩雪地里的一摊血水,这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处理手段也是对中国电影暴力美学的一次尝试与创新。扑面而来的子弹、被血染红的雪地、遍地残存的衣服与肢体的碎片,使观众在惊恐的同时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惨烈,这是对中国电影暴力美学内涵的一次丰富与拓展,正如黄建新导演所说:“在电影美学里,这是电影最强烈的效果之一。”[2]
除去直观凛冽的特征,影片的暴力美学还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侠风格,对武侠类型元素处理的游刃有余的徐克导演将自己独特的暴力美学理论体系与知识建构运用到电影实践之中。《长津湖之水门桥》在运镜上传达出徐克导演洒脱的武侠风格和娴熟技巧。如伍千里怀抱炸弹、背垫铁板从雪山上滑落进入被美军重重包围的桥面,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洒脱飘逸,运动镜头紧跟拍摄主体移动营造出一种动态的坠落感,并且通过镜头带来的紧张、暴力、刺激的画面传达出视听一体的美学质感。另外,影片多次在主角牺牲时运用了升格镜头、定格画面以及类似于动画动态延伸的子弹轨迹特效来丰富和渲染武侠风格。在谈子为牺牲时,镜头定格在弹片穿过其腹部的一瞬间,画面宛如油画一般祭奠着这位英雄的消逝,人物被弹片击中的定格画面与画外音叠加赋予了这位英雄忠勇侠义的武侠气息。在三炸水门桥时,伍千里被一连串子弹击中,在掉落下桥的最后一刻定格,随即他开出最后一枪,子弹擦出一条银色的长线击中桥面上的炮弹,此处画面、情节颇具侠情与浪漫主义风格,人物凌空的定格画面与濒死前的闪回镜头相结合塑造了侠骨柔情的人物形象,徐克导演大胆地采用一些超越电影类型维度的综合性力量将暴力美学做到风格化、浪漫化的有机融合。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暴力美学实践是纵深维度的技术发展与演进呈现,同时也代表了艺术形态、审美方式、美学观念等不同维度的技术迭代与美学嬗变。在愈发多元、开放的创作环境中,暴力美学也由此有了不同深度的阐释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影片敢于直面战争场面的残酷与血腥,在除去传统英雄熠熠生辉的主角光环后,一个个鲜活而平凡的英雄典型形象拔地而起,对暴力元素直观的呈现更能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惜与对未来的展望。除此之外,《长津湖之水门桥》糅合了浪漫主义风格的武侠元素,对不同元素和风格的创新与尝试也为电影暴力美学的发展、演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悲剧美学:以情动人的“崇高美”
王德峰教授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卡塔西斯”论证:在所有审美活动当中,最高的愉悦叫作悲剧美。从新中国电影创作伊始到新时代的电影艺术都在美学形态和美学风格中体现出了对“悲剧美”的推崇。其中,战争题材电影尤为注重推崇和渲染“悲剧美”,借助悲剧美反衬出主旋律影片中英雄的崇高之美与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长津湖之水门桥》在悲剧美学意蕴中表现出庄严、崇高的影像色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审美对象通过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美”更具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并由此展现出艺术作品的道德教育与心灵净化作用。
“‘崇高’的概念经过康德、黑格尔的阐发,转引为对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命价值的描述,用来指人在精神思想品质和风貌上的巨大性与超常性。”[3]在悲剧美学的范畴中,崇高感主要是指当主人公面对难以战胜的困难或命运时仍然迎难而上并与之进行反抗斗争,最终造成生命的牺牲或理想的消逝,由此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能量与人格魅力,使观众享受到审美愉悦。《长津湖之水门桥》以志愿军的牺牲贯穿全片,出征时157人的连队最后只剩1人,每个个体生命的消逝都激发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崇拜与敬仰之情,表现出悲剧美学中独特的“崇高美”意蕴。
英雄悲剧最易产生崇高感。《长津湖之水门桥》虽以平凡的小人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对于历史和人民来说,他们每个人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影片所表现的英雄群体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为了宏伟的志向与远大的抱负而无私奉献、负重前行。平河作为一名神枪手,牺牲前最先被轧断手臂,被坦克反复碾压却坚定地让伍千里开枪引燃炸药包,这种誓死完成革命任务的牺牲使影片弥漫着庄严、悲壮的悲剧氛围,久久难以消散;梅生心心念念回家教女儿算数,最后嘴中叼着烧的只剩一半的女儿的照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面前,梅生毅然决然地牺牲了个人与家庭利益,个人与国家的取舍为人物赋予了古典主义悲剧美学色彩;九连仅剩的几人拿着最后一颗手榴弹坚定的地冲向敌人,却被重火力拦截,手榴弹只能在手中爆炸,血肉之躯难以抗衡枪支炮弹,影片通过个人与强大力量的抗争来塑造高大伟岸、气势磅礴的个体英雄形象,衬托出志愿军们崇高的爱国情怀。结尾伍万里喊道:“第七穿插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孤独却倔强的背影屹立在火车前,曾经有一百多位战友与他并肩作战,如今连哥哥的尸体都只剩下一捧黄土。遗憾残缺更能触动观众,庄严壮烈更能引发共鸣,悲剧结局以更加深刻的艺术感染力深化了影片的爱国主义主题,为影片呈现出崇高美的悲剧内涵。
《长津湖之水门桥》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每一位志愿军、每一位中国军人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正如谈子为所讲:“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由光影到现实,看到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国富民强,幸福与憾动在观众心底油然而生,这种最直观的审美愉悦便是崇高感。悲剧美学中的崇高内涵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可以使其达到空灵、纯净、升华的境界,而对于观众来讲可以起到以情感人、净化心灵的作用。
以情动人、歌颂真善美,是《长津湖之水门桥》所体现出的最本质的艺术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念,“艺术创作是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4],借此推崇艺术作品的道德观判断与净化宣泄作用。悲剧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承载着艺术教育的作用。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长津湖之水门桥》正是通过残酷冷冽的“毁灭”给予观众强烈的撼动。结尾伍万里抱着骨灰对着幻想中的哥哥说“哥,我特别特别想你”,与《长津湖》开头呼应,出征前哥哥捏着他的脸庞溺爱地叫着“包子”,回乡后却只剩自己孤身一人。这种撕碎式的悲剧感使审美主体在二次同化中感受到审美对象的痛苦与艰难,悲哀与磅礴,在艺术体验中感受共鸣与升华,在哀婉中反思进而实现心灵的净化与启迪。影片借悲剧美追求一种自强不息、扬清厉俗的艺术教育理念,在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之间的冲突中发掘人性的真善美,注重表现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电影最后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随风飘动着的那条红色围巾是悲剧的体现,更是象征着中国军人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给予观众以精神层面的教育和启迪。
《长津湖之水门桥》再现的是民族抗争的悲剧历史,也是彰显民族精神与国家威望的正义之战。对于这些志愿军们来说,相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个人性命已无足轻重,由此塑造出一个个高大伟岸的平民英雄形象。《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悲剧美学理念创造出的是正剧的感染力,一方面真实而直观地描绘悲剧历程,一方面呈现向死而生的力量,闪耀着高尚的人性光芒与道德光辉。
三、工业美学:作者性与体制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统一
电影工业美学是伴随着电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是电影工业化的产物。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电影创作团队水平提升以及观众审美需求多样化,电影制作越来越朝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大制作”影片层出不穷。“大制作”意味着大规模、大投入、大产出,使得电影制作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成为具有流水线制作模式的产业项目。《长津湖之水门桥》以宏大的战争场面为主要拍摄内容,演员之多、电影内容涉及的空间场景之非常复杂,都意味着拍摄时的场面调度和资源调动是非常复杂的,是当之无愧的“大制作”。按照学者陈旭光的定义,“电影工业美学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5]电影工业美学强调削弱导演在电影中的支配作用,弱化电影作者性的观点与风格,强调合作与制约、规范化与产业化,将工业模式引入到电影制作全过程,在注重艺术性与作品质量的前提下讲究市场回报与商业利益。战争题材的“重工业电影”最能体现出电影工业美学的气质,《长津湖之水门桥》致力于作者性与体制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和谐统一,影片对这两组关系的处理体现出多元化、建构性以及创新性的特点。
《长津湖之水门桥》对于作者性与体制性的关系处理表现在导演的合作模式方面。影片采用了多位导演通力合作的新型电影工业模式[6],电影由徐克导演主导,陈凯歌和林超贤联合担任监制并负责部分导演工作,又邀请到黄建新导演担任总监制,为影片保驾护航。制作团队阵容强大,三位导演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徐克导演擅长打斗场面,近身搏斗的动作设计及镜头组合富有浪漫主义的武侠气息;擅长宏观巨制、偏爱惊险刺激风格的林超贤导演负责部分宏大场景拍摄,爆破、空投及使用直升机拍摄总攻等宏大场面呈现视觉震撼的奇观效果,彰显气势磅礴的战争氛围;哲学思维与浪漫主义观念并存的陈凯歌导演负责文戏,为紧张刺激的战争场面适当融入温情气息。三位导演各自发挥所长,为电影注入多元化的生命力,并且导演风格之间相互制约,削弱了电影的作者性,做到了体制性与作者性相制衡、相统一,成就了电影制作的产业化模式。
影片对于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也进行了创新性实践。电影在演员阵容方面集中了老戏骨与年轻演员,老成持重与新鲜活力并存,流量与质量并重,宣发推广与深耕内核共生。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地加工制作,将艺术性与商业性完美融合。影片中多次体现了导演的戏剧化处理,比如伍千里在水泵房身受重伤难以脱身仍能一枪瞄准平河身旁的炸药包;最后一次炸桥任务中伍千里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关键时刻一击命中炸弹炸毁了桥;伍千里牺牲后与伍万里冻在一起,美军用喷火器燃烧了伍千里的尸体,火焰的温度融化了伍万里。关于这些想象性、戏剧化的情节设置,黄建新导演作出解释:当观众的情绪代入到叙事创作中时,绝大多数观众的意愿与希望就是叙事合理性的重要条件,即观众希望这样,就能接受这种设置[2]。导演将电影艺术性与观众意愿相结合,通过适当采取商业性、迎合大众审美判断标准的方式将主旋律作品真正做到大众化。《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不仅体现在艺术思维中,还体现在技术实践中。电影拍摄过程中运用了飞猫摄影、无人机摄影,甚至还在拍摄兴南港戏份时用到直升机拍摄,影片中许多场景用CG技术搭建,宋时轮站在山顶、志愿军走在结冰湖面上的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的,体现了大投入、大产出的工业化制作模式,同时也为电影的艺术质量做出了保证,最大程度平衡了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体现的作者性与体制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电影工业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丰富拓展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同时这部电影的摄制实践也在技术层面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创新与发展,也为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商业化制作、工业化生产提供新的参考范例与创作启示。
四、结语
《长津湖之水门桥》从电影美学方面进行类型化整合,在视听语言、叙事逻辑以及情感宣泄等多维度体现出创造性的实践与突破,为战争题材电影发展提供了主流电影创作的文化坐标、时代精神与逻辑意义,实现了主流意识、艺术诉求与商业发展的三位一体模式,构建中国电影美学发展的新态势与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