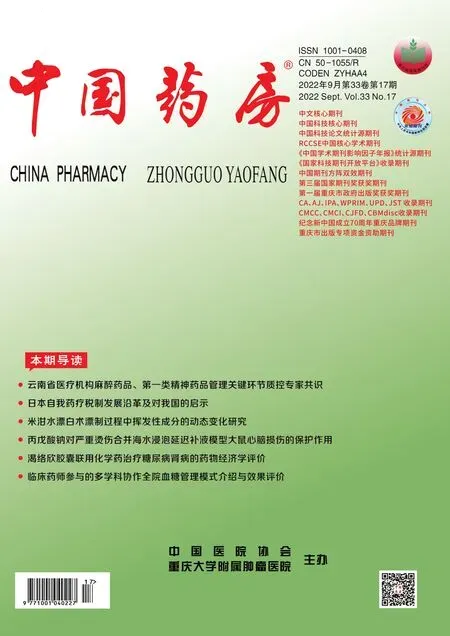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体系构建Δ
2023-01-11徐敢罗卫花王玉伟郭冬梅叶桦孙昱庄伟朱文涛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088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00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北京000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北京0005
徐敢,罗卫花,王玉伟,郭冬梅,叶桦,孙昱,庄伟,朱文涛#(.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088;.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 00;.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北京 000;.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北京 0005)
药物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用有限的药物资源达到最大程度健康效果的交叉学科[1]。药物经济学评价及其证据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制定/修订、药品集中采购、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等都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如何评价中药在防治重大慢性病中的药物经济学优势”在2020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确定为中医药领域的3项重大科学问题之一,受到行业内外的高度关注[3]。中成药在防治重大慢性病中的药物经济学优势研究是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研究体系和达成行业共识。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评价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优势的理论框架,探索可用于评价中成药药物经济学优势的理论、工具、方法,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药物经济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中成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近年获得了一定发展,研究数量和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与国际水平和国内化学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相比,我国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缺乏规范性指导和标准,尤其是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潜在优势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未得到体现[4]。
1.1 中成药潜在优势不能得到全面评价
现有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对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中医药治疗进行了多维度评价[5],但在相关研究中,中药组、中西药联用组或者化学药组具有经济学优势的结果都有出现[6-7]。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整体上的辨证论治,而不仅仅是考察机体的局部特征。中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及中成药不同于化学药的作用机制及特点,决定了简单套用化学药的经济学评价指标及技术很难真实、全面地评价中成药的价值。没有按照中医药规律和中成药特点开展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使得中成药的很多潜在优势得不到体现,部分瑕疵甚至可能会被放大,有些生搬硬套经典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使中医药疗效和优势评价出现了“削足适履”现象,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技术和方法难题已经成为提供高级别证据的瓶颈问题[8]。
1.2 评价的理论、方法、工具需要创新和完善
现有的针对如何系统评价中成药在防治重大慢性病中优势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系统反映中成药特点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尚未形成。现有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理论、工具和方法尚不足以支撑系统评价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潜在优势所需的学科体系发展和实践应用要求,尚需完善[9]。这是因为:第一,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研究时限不够长,时间控制不够严谨,研究方向过于狭窄,不能充分展现中成药治病的特点。尤其是在治疗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时,中成药的疗程通常较化学药长,其优势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有数据表明,在我国已发表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接近70%的研究时限在1个月以内,持续时间在1年以上的仅占1.08%,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治疗周期相对较长的慢性病,研究时限较短导致所得结果无法完全体现中成药的优势[10]。第二,目前采用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相对单一,大多采用成本-效果分析,较少采用效用和效益指标;多数采用有效率或治愈率等单一疗效指标,采用综合指标的较少,同时,“早防早治”的指标体系难以确定,使得中医药优势难以得到全面反映[10]。第三,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多数采用回顾性的病例对照研究[4],前瞻性研究设计在中成药的临床试验阶段没有开展或者无法开展,并且外部有效性较低。第四,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设计往往与真实世界有一定差异。已发表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文章,大多以某中成药(中药组)与某化学药(化学药组)或者与该中成药加化学药(中西药联用组)进行回顾性研究或者前瞻性研究,观察每组药物的疗效和经济学评价结果,得出治疗药物的经济性。但是,真实世界中仅有较少的中成药治疗方案仅采用某单一中成药进行数个疗程的治疗,因而相应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虽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1.3 评价所需的高质量证据有限
数据质量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基础,没有真实可靠的研究数据,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便无从谈起[11]。我国中成药品种存在先天安全性指标缺失、后天安全性再评价工作推进不力等现实问题[12]。中成药联合化学药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缺乏说明书数据支持和效果指标评价,中西药联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评价还缺乏体系构建和方法学基础设计。从药物经济学评价角度丰富中成药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助力中成药综合评价,已经成为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之要务[12]。由于中成药的使用缺乏较高质量的评价数据、指标和标准,因而目前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普遍照搬化学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模式和指南,没有充分体现中成药的特色,总体评价质量偏低,高质量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较少[13]。在医保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践中发现,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质量参差不齐、规范性差,相当比例中成药产品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报告没有提供支撑数据,无法证明其与药物经济性相关或临床具有成本-效果/效益优势,总体水平亟待提高[14-15]。因此,提升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水平、规范数据源、提高研究数据质量,使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更客观、公正、科学、准确,并把客观的评价结果应用到药品谈判以及其他政府决策中,是业界、学界、政府及医疗机构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16]。
2 构建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药物经济学评价框架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开展了广泛的分散性评价研究,但还存在理论、方法学创新的提升空间,需要加强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学研究,提升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质量和能力,为科学评价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17]。
2.1 系统思考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内涵和价值
2.1.1 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特有属性分析 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评价中成药防治慢性病优势的前提,是清楚中成药的经济学基础指标、特点和发展规律。中成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我国中医药资源配置机制下,具有区别于一般商品和化学药的经济学特征和属性。现有研究从药物经济学评价角度比较关注中成药的使用成本[17],假设性地认为中成药与化学药具有相同经济学属性。后续的中成药经济学评价,有必要利用西方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经济学分析方法,有针对性地对中药资源稀缺性、资源配置方式、供需规律,以及中药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等一般经济学规律和特征进行研究,科学解释和丰富多种中成药联用和中西药合用相关理论。只有准确界定中成药的经济学属性,才能对中成药进行更科学、综合的经济学评价。
2.1.2 中成药“治未病”和发挥人体自身调节作用的价值分析 中医药突出“治未病”,针对机体危险状态“未病先防”,可以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同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长期生存的希望和更高的生命质量。中医药的主要特色和优势综合表现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以及慢性病和康复治疗中的核心作用上[18]。如果忽略中医药“治未病”和发挥人体自身调节作用的价值,简单地将中成药从调节人体整个系统平衡状态的功能与化学药“对抗式”医疗模式做对比,就会忽略中成药的部分临床价值和经济学价值。
中医治病注重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遵循2个原则,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因此,有必要依据上述原则构建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特征和属性指标,综合分析中医优势病种的中成药临床应用经济学特征和最佳健康产出指标;将诊断明确的属于中医优势病种的患者,在得到其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转为中医药治疗;根据临床实践结果进一步丰富卫生经济学和药物经济学评价内容,完善疗效的证据链,建立起既符合中医药规律又能被国际医学界认可的疗效评价体系,让中医药的独特优势评价立得住、被认可、可推广。
2.2 遵循中医药规律评价中成药治疗慢性病的优势
《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2020》的发布对规范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成药治疗慢性病的经济学综合评价和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制定,需要在参考借鉴《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2020》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医遣方用药的基本原则,统筹考虑中成药药物经济学在研究设计、研究角度、目标人群、干预措施和对照选择、研究时限、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特殊性[12]。评价体系不能完全按照西医学的生理、生化和影像学指标来评价,而是需要尊重传统中医药的认知模式和相关指标,结合传统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评价理论和方式来综合评价,并建立起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系统的评价逻辑[12]。
2.2.1 研究设计 药物经济学评价中的前瞻性观察研究,可以反映真实世界中干预方案的成本和效果,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较高;其还可以借助临床实践开展药物经济学干预研究,通过前瞻性收集患者成本和健康产出等信息的临床研究,为卫生决策和医保决策提供依据。另外,由于针对中成药自身特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平行研究数据相对于化学药而言十分有限,故建议制定中成药临床研究方案设计规范[19]。该规范应充分考虑和体现中成药的特点,并将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前瞻性观察研究方案考虑进去,最终为患者的临床决策提供更多高级别的中成药循证医学证据。
2.2.2 目标人群适应证 中成药的适应证既有以中医疾病、证候为主者,也有以西医疾病为主者。目前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研究中,若以中医疾病、证候为主要适应证,并且中医病证与西医病名相对应者,往往采用西医相应疾病的疗效判定标准及观测指标作为参考,以相对成熟的西医疗效进行判定;若中医病证与西医病名不对应,则会选用适宜中医证候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若中成药的适应证是以西医疾病为主时,则可以首先考虑采用西医的疗效判定方案,再辅以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20]。但是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这种评价方式可能将中成药彻底沦为辅助用药。尤其是对于既有西医适应证又有中医适应证的中成药,如果只采用西医相应疾病的疗效判定标准及观测指标作为参考,容易反映疾病的局部病理变化,从而可能忽略中成药在改善证候和患者整体状态方面的经济学价值。因此,对于具有多种功能主治的中成药,在目标人群的选择上,除了需要兼顾西医适应证以外,还要考虑其中医证候疗效对应的经济学价值。另外,为充分反映中成药的经济学价值,建议对纳入《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的标准化项目,在经过诊断和评估之后,在医保体系中可优先纳入具有经济学优势的中医药治疗路径,用中医药思维来界定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中成药的经济性。
2.2.3 干预措施和对照选择 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选择的干预措施一般是针对获得国家批准且已上市的中成药,具有明确的适应证、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对照措施一般是选择与干预措施有相同适应证的常规治疗或者标准治疗方案[12,21]。在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中,要想获得全面的经济学评价结果,在干预措施或对照措施的选择方面,应着重注意联合用药尤其是中西药联用方案。为了准确、合理地评价联合用药的效果,需要研究者根据药品说明书明确所研究的中成药在联合用药中的定位,即属于基础治疗药物还是辅助治疗药物或其他情况,并在报告中说明该定位,并且还需对其合理性作出解释。
2.2.4 研究时限 研究时限不足是已发表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普遍存在的问题[21]。中成药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尤其要注意选择足够长的研究时限,以收集研究所需干预方案产生的成本和健康产出[12]。重大慢性病的研究时限原则上要求更长,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临床试验数据有限、无法获得更新的临床疗效数据或者数据不适用等多种困难。对此,可以依靠建模方法和真实世界研究的实际数据来弥补和完善。
2.2.5 评价方法 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证实中成药相对于化学药的临床综合价值,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多元化和优化提供依据。中成药的特点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和协同调动机体功能而发挥治疗作用。相对于化学药,中成药的功效主要体现为整体健康结果的改善,而非临床指标或症状发生短期显著变化。成本-效用分析是比较适宜于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方法之一。对于慢性病和缓解期疾病,建议尽量采用以健康效用为指标的成本-效用分析法进行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5]。
2.3 药物经济学评价工具和方法创新
中医药防治重大慢性病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要求。大部分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时限短、研究方向过于狭窄,使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优势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无法得到很好的体现。这需要通过运用模型得到长期的研究成本和产出数据,以及采用真实世界研究法,才有利于更好地评价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优势。
2.3.1 药物经济学系统建模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模型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药物经济学评价使用的模型主要包括决策分析模型、马尔可夫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其可对无法实现的试验进行合理预测,还可模拟并延长研究时限、外推试验结果等,从而为最终决策提供科学而合理的依据与解释[5]。针对慢性病防治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长期观察或获得较长期的产出结果,模型法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模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模型本身容易偏离疾病发展的真实过程[5]。此外,模型法还包括一种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其从系统内部的机制、微观结构入手,通过剖析系统进行建模,并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来分析系统内部结构与其动态行为的关系,从而寻觅解决问题的对策[22]。虽然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在药物经济学评价领域的应用还不够普及和成熟,但可能为系统评价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优势提供新工具和新手段,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3.2 优化健康产出和健康量表 中成药的产出指标包括中医证候及其改善的主要症状指标。如果能采用生活质量量表获得患者的效用值来进行相关的中成药药物经济学评价,并对效用值不确定性进行敏感性分析,就能更好地评价中成药的价值。我国目前应用于中医药疗效评价及卫生经济评价的普适性生命质量量表主要有欧洲五维健康量表、六维度健康调查简表和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等,但这类量表对中医药干预的生命质量相关指标和关注点体现不足,且其并非基于中国人群健康偏好设计。国内基于中医理论疾病专用的中医生命质量量表约有40个,但主要偏于对症状和中医证候的描述,且大部分没有相应的效用积分转化体系,也未开发配套的健康效用积分体系,一般仅适用于反映中药治疗的效果而非效用[23]。要想客观表现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的药物经济学特点,需要制定利于患者自评生命质量且能体现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证候量表。202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中医生命质量评价量表》。该量表基于中医理论框架和中医健康观,可用于评价经中医药干预前后的生命质量变化[23],将成为中医药干预患者生命质量的健康效用评价和开展中成药防治慢性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测量工具,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及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2.3.3 真实世界研究 要想全面、准确地研究病因复杂、多脏腑受累的慢性病治疗效果和患者整体功能、状况的改善情况以及进行多维度结局评价,还可引入真实世界研究方法,从大数据分析中收集真实世界证据。真实世界研究是一种运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真实无偏倚或偏倚较少的人群中,对某种或某些干预措施(包括诊断、治疗、预后等)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的研究[24],可更系统地反映和评价疾病治疗效果、药品不良反应以及健康产出。真实世界大数据分析已成为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研究方法[25-26]。
3 结语
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从医学价值出发,进一步创新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适宜中成药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中成药治疗成本、治疗效益、患者满意度、外延效益影响、社会公平性等,通过大样本量的中成药临床评价和高质量的中成药系统评价报告提供科学的临床研究数据,使更多中成药的疗效和特点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和展现。完善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药物经济学评价体系是一项需要多学科齐头并进的工作。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创新方法与技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突破。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要与中医临床个体化疗效评价动态指标体系构建,中医临床个体化诊疗信息智能采集与评价方法创新以及中医慢性病诊疗优势专科/专病遴选等多学科、多技术协同推进[27]。通过系统诠释中成药防治重大慢性病优势的经济学评价理论和方法等,可助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和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的落实和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