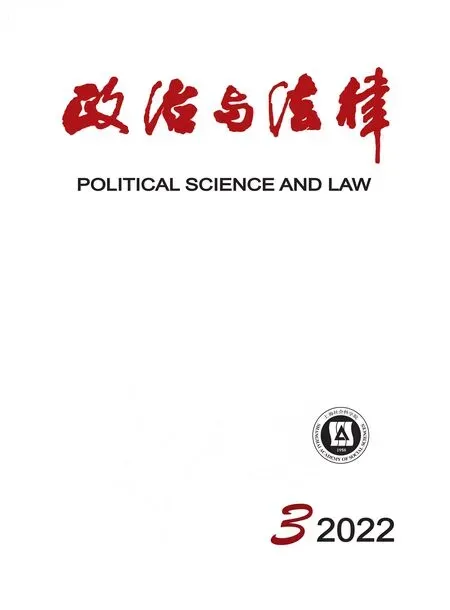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
2023-01-08鲁晓明
鲁晓明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 510320)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即计划生育制度的放松乃至废止,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就法定婚龄与生育及人口结构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就适应老龄社会的法定婚龄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定婚龄与人口生育之密切联系
法定婚龄,又称禁结婚年龄,或允结婚年龄,系法律承认的当事人自主缔结婚姻之最低年龄;也系法律不再加以禁止,而交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低年龄。若称禁结婚年龄,盖指在此年龄前不得结婚;若称允结婚年龄,则指满足这一年龄以后可以结婚。
现代民事活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遵循其自身意愿。婚姻事涉个人重大利益,应充分体现个人自主意思。近现代以来,以追求个体自由为目标,婚姻法学界高举婚姻自由大旗,反对任何形式的包办和强制婚姻,学界经常在“‘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人权、男女平等、反封建’等语词构成的语境中”〔1〕徐静莉:《婚姻自由原则背后的矛盾冲突——抗战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分析》,载《晋阳学刊》2006 年第3 期。解读婚姻。故对于自然人而言,是否缔结婚姻、与谁缔结婚姻、在什么年龄缔结婚姻纯属私益,系属个人自主之意思。法定婚龄,恰恰是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限制,即通过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对于未达到法律规定年龄的当事人之结婚意愿施加限制,以达到某种公共政策目的。
婚姻是人口生产的前奏,生育历来是婚姻重要的目标和内容。由于婚姻与生育直接关联,社会对人口再生产的干预主要通过婚姻制度实现。〔2〕参见顾鉴塘:《论婚姻家庭的人口再生产本质》,载《人口与经济》1989 年第12 期。法定婚龄作为调节人口生产的重要政策手段,以保证人口生产与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法定婚龄作为国家婚育政策的直观反映,与人口结构存在密切关联。当人口少、劳动力匮乏、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国家往往降低法定婚龄倡导早婚以鼓励生育;反之,当人口过多时,往往提高法定婚龄,通过倡导晚婚以达到减少生育,延长代际传承周期的目的。近代以来,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新生儿夭折率低,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在一些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为避免人口增长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给环境造成过大压力,于是将法定婚龄由促结婚年龄变更为禁结婚年龄,强制提高结婚年龄下限,以达到延缓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相反,当社会陷入少子化、年轻人口增长缓慢、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不足、社会负担不断增加之时,则降低法定婚龄,通过放松对于民事主体婚姻年龄的限制以提高人口产出率。
此外,作为一种婚姻制度,法定婚龄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成年人保护、社会秩序维护与利害关系人保护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一,防止发育不成熟者过早陷入婚姻,损及身心健康。性是婚姻的基石。两性差异和两性关系,是婚姻的生理学基础。〔3〕参见林葆先:《婚姻良法的伦理标准》,载《河北学刊》2014 年第2 期。“在婚姻中,所谓的强烈感受往往与‘性’密切相关”,〔4〕吴玉军:《责任感与忠诚感的回归——社群主义视野中的婚姻家庭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 年第3 期。“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5〕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95 页。婚姻虽非以性为全部,但性无疑是婚姻之重要目标和内容,两性结合首先就源于性的冲动。婚姻对于当事人的生理学意义,就在于性行为在配偶间的常态化。而性的常态化则以自然人生理获得充分发育为前提,若发育不成熟之人经常性地进行性行为,则必然会耗及精力,因超出身体正常承受能力损及身体健康。故为维护自然人健康计,法律设定结婚年龄限制。唯达到一定年龄,身体发育成熟,能够承受性行为常态化后果者方允许缔结婚姻。
其二,防止心智不够成熟者过早进入婚姻而陷于纵欲之境地。婚姻以性为基础,而性则是动物的。人类特有的情感与动物本能交织,演化出人类特有的性爱。基于原欲的满足与交媾欲的满足,性对于婚姻当事人的诱惑几乎无处不在。心智不成熟者在巨大的感官刺激面前往往缺乏基本的抵御能力,极易沉迷于感官刺激中不能自拔。纵欲不仅损及行为者身体健康,而且使其颓废不思进取。故即便生理发育成熟,若精神未达到理性对待性诱惑的程度,亦应加以限制。唯在自然人自我判别力和控制力达到较高程度时,始得允其缔结婚姻。而必要的年龄限制,显属确保自然人正常成长的必要手段。现代社会禁止童婚,即在于儿童既难以抵御性之诱惑,亦不足以承受性行为日常化的后果。
其三,保护婚姻当事人后代的利益。即防止不具备抚育能力者过早生育,陷后代于抚养困难境地。婚姻的意义之一,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为了“保证生出来的孩子不但有母而且有父,于是有婚姻”。〔6〕费孝通:《生育制度》,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第39 页。性不成熟者过早涉足婚姻,易孕育不健康的子女;心智不成熟者过早孕育子女,则难以承担起抚养教育重任,而陷子女于无人照护之危难境地。故法律设定结婚年龄限制,以保护其子女利益。
其四,维护利害关系人利益。婚姻是整体主义的产物,夫妻系共同体观念在婚姻领域的体现〔7〕参见郑玉双:《婚姻与共同善的法哲学分析——兼论同性婚姻合法化困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 年第5 期。。夫妻双方通过组建家庭,形成稳定的共同关系。家庭以夫妻为核心成员,集生活、生产功能于一身,承担着生活、生产和生育的使命〔8〕参见邢铁:《我国古代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周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5 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共同生产关系存在弱化的趋势,但家庭的生产功能仍相当程度上存在。作为婚姻共同体,配偶双方既共同进行生产劳作,又共事繁衍生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归入夫妻共同体,夫妻互具日常生活事务代理权利,夫妻共同养老育幼,日常支出共同负担。家庭不仅意味着对外进行有组织的民事活动,而且意味着核心成员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的责无旁贷。心智不成熟的自然人不具备基本的履约与民事责任承担能力,放任其过早组建家庭并成为交易的常态化参与者,势必对交易安全构成冲击。故各国通常与民事行为能力一体考虑设置禁结婚年龄,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不允许结婚,即便个别情况下允许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亦设置特别限制,如须经过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以确保其具有相应意思判别与责任履行能力。
二、控制生育系我国法定婚龄的突出功能
我国法定婚龄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47 条。该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定婚龄尽管兼顾了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但人口控制无疑是其突出主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事行为能力仅是民事主体成为适格婚姻主体之前提,并不以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已足,而是要在成年以后再增加一定年龄
《民法典》第17 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第18 条第1 款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行为。将法定婚龄规定为男满二十二周岁、女满二十周岁显然考虑到了发育成熟的成年自然人才合适从事婚姻行为这一现代社会基本准则,而将发育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排除在外,防止过早进入婚姻损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显系考虑因素。
然而,我国法定婚龄虽以自然人成年为必要,但并不以成年为已足,而是于成年后再增加一段不得结婚的年龄。与十八周岁的成年年龄相比,男满二十二周岁、女满二十周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了两年至四年。之所以男女存在差异,则是因为发育周期存在差异,女性比男性发育成熟时间一般要早两岁。
于是之故,尽管婚姻行为属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未达法定婚龄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却不得为之。从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到达到允许其结婚的年龄,存在二至四年不等的距离。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婚姻不仅是当事人之间人身关系的结合,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因而系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婚姻行为能力系特殊的民事行为能力〔9〕参见邓丽:《论民法总则与婚姻法的协调立法——宏观涵摄与微观留白》,载《北方法学》2015 年第5 期。,故实施婚姻行为除满足民事行为能力一般要件之外,还须满足法律的特殊规定。此一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难言自洽。因为行为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不同,一些特殊复杂事务需要行为人具有更高的意思能力,故法律上或有设置特殊行为能力之必要〔10〕参见高晓春:《论自然人的行为能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 年第1 期。。且将婚姻行为能力解释为特殊行为能力,意味着未达法定婚龄者并不缺乏婚姻权利能力,唯在达到法定年龄之前不得行使之。故即便未满法定婚龄者之婚姻并不通归无效,而属从事与其年龄不相适应的行为,可以比照《民法典》第145 条第1 款后段的规定,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在当事人成年且孕育子女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解释后果。然而,一方面,我国法律上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却并没有任何关于特殊行为能力的规定,将婚姻能力解释为特殊行为能力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047 条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系在此年龄前禁止结婚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此时,对于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行为,循行为能力理论与依《民法典》第1047 条性质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除此,以婚姻行为承载较多社会功能为由将其从一般民事行为中抽离也缺乏充足说服力。毕竟,任何民事行为均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只是程度存在差异而已。婚姻行为虽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本质上仍是私事,其社会性并非显著多于其他民事行为。
(二)我国法定婚龄鲜明地体现出对于较低年龄之成年人婚姻自由的限制
1.我国法定婚龄的功能是限制低龄成年人婚育自由
低龄成年人亦属成年之人,生理发育业已成熟,并无科学依据显示性行为日常化将损害其身心健康。通过提高婚龄,限制年纪较轻的成年人婚姻意愿,使其不能过早实现结婚目的,明显不是以保护其身心健康为目标,而是基于公共政策目的。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尚没有明晰的婚育政策,法定婚龄也相对较低。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 条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11〕该规定没有规定岁的标准为周岁还是年头,无论是男满20 周岁,女满18 周岁,还是男第18 个年头,女第18 个年头,均可结婚,实质是照顾中国民间“虚岁”和“实岁”的年龄计算习惯。这一规定较之现行法定婚龄男女均早了两岁,且不要求满周岁。按照当时民间普遍采用“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实质上男子的最低婚龄只比十八周岁成年年龄晚一年,女子的最低婚龄比成年年龄还要早接近一年。
其次,现行法定婚龄是晚婚晚育政策的法律表达。晚婚晚育政策最早提出于1973 年12 月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12〕此次会议提出“晚、稀、少”的控制人口政策。其中,“晚”即晚婚晚育。。之后,相关政策不断清晰。至1980 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晚婚晚育并要求党团干部带头,晚婚晚育政策最终形成。有关法律的修订正是这一政策直接推动的结果。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明确将“晚婚晚育”与法定婚龄挂钩,将法定婚龄规定于第5 条前段,而将“晚婚晚育”规定于第5 条后段。一方面,将法定婚龄提至二十周岁以上的极晚年龄;另一方面,鼓励达到法定婚龄者延迟三年以上才结婚。虽然形式上,《婚姻法》将晚婚晚育规定于法定婚龄之后,意味着晚婚晚育存在不同于法定婚龄的独特意蕴;但极严格的法定婚龄本就是晚婚晚育的体现。换言之,“晚婚晚育”政策实质上通过两个层次体现于《婚姻法》之中。一是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法定婚龄;二是倡导性的“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之表述。
2.我国法定婚龄对于婚姻自由的限制极为严格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属于最严的法定年龄限制。虽然西周时期曾经存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13〕《周礼·地官》。的礼仪性初婚年龄,但这一古礼婚龄并未被遵守。〔14〕参见王跃生:《近代之前初婚年龄的制度类型及功能考察》,载《晋阳学刊》2013 年第6 期。相反,我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实行早婚早育制度。男性结婚年龄除西周、春秋时期部分诸侯国〔15〕春秋时期,主要是齐国和越国规定了二十岁的结婚年龄。参见《墨子·圣王篇》、《韩非子·外储》。、北齐、唐贞观元年短暂地存在二十岁的政策婚龄外,自唐以来一直维持在十六岁〔16〕“岁”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概念,中国古代关于“岁”并不存在严谨的表述。“岁”既可以是“虚岁”,亦可以是“实岁”。周岁,则指实际年满,即“实岁”。本文所指“周岁”,均系年满一定岁数。在内涵不是特别确定,或文献来源使用“岁”时,则使用“岁”概称。以下的极低水平,仅于清末有所回升〔17〕对于政策婚龄,为唐十五岁,宋十五岁,明十六岁,清十六岁,《大清民律草案》提升至十八岁。;女性结婚年龄则更低,从未超过十七岁,多数时期是在十六岁以下。〔18〕在可查阅的资料中,仅春秋时的越国及西晋为17 岁,其他均在16 岁以下,以15 岁和14 岁为最普遍。参见《新唐书》卷2,太宗纪;《诸子家礼》卷3,议婚;万历《大明会典》卷69,庶人纳妇;《钦定大清通礼》。且这些年龄基本为促结婚年龄,即达此年龄者需履行结婚义务,而非对于结婚年龄的限制。事实上,关于结婚年龄的最低限制,在中国古代少有规定,而基本交由当事人及其家庭自主决定,中国古代“童养媳”盛行就是可资佐证的例子。相较而言,无论是从促结婚到禁结婚的转向,还是男满二十二岁,女满二十岁的结婚年龄起始规定,现行法定婚龄对婚姻当事人意思的限制无疑最为严格。
其次,在比较法上亦属于最严格的年龄限制。一方面,综合而言,我国法定婚龄晚于其他国家。法定婚龄的设置,既涉及生理发育事宜,又与婚育传统、婚育伦理等直接相关。现代医学、生理学等业已证明,男满十六周岁,女满十四周岁,即基本发育成熟〔19〕参见邓希泉:《青年结婚年龄的国际比较研究》,载《北京青年研究》2017 年第4 期。。年满十八周岁,则已具备正常的识别与自我控制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行为。因之,世界各国均围绕十八周岁的成年年龄,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设置法定婚龄。或直接以之作为法定婚龄,或结合本国婚育传统、婚育伦理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在一定年龄幅度内浮动。总体来看,采二十周岁以上法定婚龄者寥寥。而要求男女均年满二十周岁的,则只有我国。我国法定婚龄不仅远高于十八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也远高于一般国家男满十八岁,女满十六岁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法定婚龄标准单一,缺乏必要的缓和。为兼顾个体差异,使法定婚龄制度更契合当事人实际,各国通常设置特殊制度柔化法定婚龄,使其更具张力和包容性。“外国法在规定法定婚龄的同时,大都具有一种特许制度,即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低于法定婚龄的情况下,向法定机关申请批准结婚的制度。”〔20〕巫昌祯:《婚姻法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4 页。比如,《日本民法典》第737 条规定:“未成年的子女结婚,应经其父母同意”;《德国民法典》第1303 条第2 项规定,家事法院可以依申请作出许可结婚的决定;《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581 条第2 款规定,埃塞俄比亚皇帝及其指定的人如有充分理由,在不超过两岁的幅度之内,可以授权特许结婚。我国《民法典》则仅于第1047 条对法定婚龄做出刚性约束,即在此年龄之前不得结婚,而没有任何缓和性的例外规定。国家单纯基于人口控制目的而严格限制过早结婚,对当事人及其父母等家庭人员的意志施加统一限制,是我国法定婚龄的鲜明特点。
显然,在自然人发育年龄不断提前,法定婚龄降低具备坚实的生理学基础的情况下,我国一反数千年鼓励生育之早婚传统,而规定极其严格的法定婚龄限制,主要不是基于自然人生理发育因素,而是在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膨胀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公共利益考量,通过强制推迟结婚以达到少生育、进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的。
1949 年后,我国人口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4 以上〔21〕参见宴月平、黄美璇、郑伊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趋势研究》,载《东岳论丛》2021 年第1 期。,人口短时间内急遽膨胀。从1960 年至1980 年短短二十年间,我国人口数从66207 万遽增至98705 万,人口净增加超过三亿二千万。〔22〕https://data.stats.gov.cn/search.htm?s=%E6%80%BB%E4%BA%BA%E5%8F%A31980,2021 年5 月6 日访问。本文人口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处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人口增速远超社会承载能力,造成资源与环境的高度紧张,因而直接导致了控制生育政策的出台。自1971 年7 月国务院《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23〕参见贾志科、沙迪、赵英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年婚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兼述政策效果及未来方向》,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5 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便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目标。由于认识到“青年的初婚年龄,特别是女性初婚年龄的迟早,对人口再生产影响很大”〔24〕谢恩荣:《治理早婚早育环境,建立晚婚晚育新秩序的思考》,载《人口与经济》1989 年第5 期。,“平均生育年龄每增加1 岁,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作用大致等同于将‘一胎率’的比率提高8%”〔25〕陈俊鸿:《谈谈晚育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作用》,载《南方人口》1988 年第1 期。,而初婚年龄的推迟可以使两代人之间的间隔拉得很长等原因,实施晚婚晚育政策,规定较晚的允结婚年龄以达到控制婚育目的,成为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极高的法定婚龄使婚育周期拉长,使适婚男女减少,生育率降低。极高的法定婚龄与提倡青年男女推迟婚育有机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其制度意蕴,均是控制人口增长。《民法典》第1047 条删去“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表述,虽表明在老龄少子化背景下,婚姻法不再明确将“晚婚晚育”作为倡导性价值,但由于沿袭了“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的极晚婚龄,至少意味着《民法典》没能承担起转变婚育政策的重任。《民法典》保留了体现“晚婚晚育”理念的既有法定婚龄制度,据此,自然人在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之前,即便生理成熟,当事人意愿强烈,亦一律禁止结婚。即使通过改动年龄等方式获得结婚登记,亦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26〕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㈠》第9 条,在未达法定婚龄而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以请求确认婚姻无效。从实施效果来看,严格的法定婚龄制度也确实达到了晚婚〔27〕参见王跃生:《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立足于“五普”长表数据的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6 期。及控制人口生育之目的。
三、老龄社会法定婚龄应以促进生育为目标
一国婚育政策的确定,唯立基于本国人口实际方具有合理性。个体婚姻生育本是民事主体私事,除非事涉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原则上不宜干预。晚婚晚育政策是对意思自治的重大限制,应视为特定时期因应严峻人口形势的权宜之策。
老龄化的背后是深刻的人口结构变化。〔28〕参见都阳、封永刚:《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载《经济研究》2021 年第2 期。经过几十年晚婚晚育的宣传教育,我国生育观念不再以多生育作为目标,少生优生已成为占绝对主导的生育观念。相应地,少子化与极低生育率已成为老龄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之事实,婚育政策变控制生育为促进生育,通过提高生育率增加年轻人口数量和比重,以优化人口结构也就理所当然。
(一)老龄社会人口形势已由人口膨胀变为增长失速
从年轻人占绝对多数的年轻化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人口结构的颠覆性变化。社会老龄化不仅意味着长寿化,亦意味着少子化。正是因为少子化,新增年轻人口数量减少,方会凸显老龄人口占比过大问题,而使社会呈现老龄化特征。经过长期的“晚婚晚育”及少生优生宣传,晚结婚少生育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观点。适龄夫妻生育亦从高生育率迅速降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且不断深化。至二十一世纪初,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5 以下的极低生育水平〔29〕参见尹文耀、姚引妹、李芬:《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 期。,至2010 年时仅为1.18,2015 年更跌至1.05。〔30〕参见穆光宗:《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战略取向》,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 年第1 期。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远低于2.47 的世界平均生育水平,也低于1.67 的高收入经济体生育水平。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我国不仅不会出现人口增长,连保持正常的人口代际均衡都不可能。据专家预计,我国将在2025 年至2030 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31〕参见林宝:《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的关系》,载《人口研究》2020 年第3 期。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情况来看,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期极可能提前。困扰我国的现实国情,已由人口膨胀转为低生育所致的人口急遽减少。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再是老龄社会的突出矛盾
社会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长寿化。长寿化意味着高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长寿化作为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医学技术水平发展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直接体现。这一点,从国家统计局关于寿命与人口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我国人均寿命仅为49.3 岁。截至2015 年,人均寿命已提升至76.34 岁。相应地,65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占比不断提高,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32〕参见林宝:《中国人口老龄化:2000-2010》,载张车伟主编:《中国人口年鉴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9-213 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65 岁以上的人口仅为2248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15%。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 年60 岁以上人口达到26402 万人,已占总人口的18.70%。〔33〕参见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2021 年12 月19 日访问。
随着人口结构的急遽变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与生命力旺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处于生理周期的萎缩期。年龄越大,物质消耗的需求越小,生活空间也越小。因此,老龄化社会必然是低欲望、对资源环境低索取的社会。老龄化越深,高龄老人占比越重,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也就越小。虽然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但无疑将小得多,至少将不再是社会突出矛盾。即使存在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亦与人口生育没有直接关系。
(三)解决老龄社会新的矛盾需要采取促进人口生育的政策
老龄社会新的矛盾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代际人口严重失衡。
由于特殊生育政策的原因,我国从生育率高企到进入极低生育水平,并非渐进式推进,而是断崖式下跌。此种不正常的剧增剧减导致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老年以后,年富力强的成年人急剧减少,后果就是代际人口严重失衡。“未来数十年,我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34〕易富贤:《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载《中国经济报告》2018 年第5 期。家庭户持续趋向小型化,家庭内部人口代际失衡严重。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家庭户平均尚有3.44 人,由核心家庭、没有孙辈的直系家庭和不完全家庭中的夫妇一方与未婚子女构成的二代户还是我国家庭户的主要形式〔35〕参见王晓慧、肖鹏峰、康国定、杨萌萌:《中国分代家庭户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载《南方人口》2012 年第4 期。。仅过了二十年,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家庭户平均人口下降到仅2.62 人,由单身家庭、同辈人构成的一代户以49.5%的占比成为最主要的形式〔36〕参见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版,第8 页。。老人单身居住的空巢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缺少交流,老年人普遍缺少精神慰藉。当其身心陷入疾患或行动障碍之时,亦难以及时获得来自晚辈的照护。人口的持续发展面临威胁,老有所养亦难以实现。
2.扶养压力急剧增加。
社会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难以维系。一方面,家庭中长者的数量成倍增加。在成年夫妻同时还是职场生力军、抚养小孩之当然责任人的情况下,只要一位以上的老人失能失智,或部分老人身体欠佳,整个家庭将无喘息之机;另一方面,家庭小型化使得家庭养老能力下降,家庭已承担不起日渐沉重的养老压力。养老不得不从家庭走向社会。这一点,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2000 年,日本亲属担任监护人的比例高达90%以上,到2020 年则下降至19.7%;第三方担任监护人的比例则由10%迅速增长至80.3%。〔37〕参见张继元、晏子、税所真也:《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成年监护服务:日本的经验与启示》,载《学术研究》2021 年第5 期。
社会老龄化,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序列,转而进入受赡养者行列,亦意味着享受社会保障人口的比重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压力将越来越大。我国社会的老年抚养比,1953 年时仅为7.4%,2019 年时已提高到17.8%。〔38〕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2020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版,第8 页。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筹集制度下,随着养老金缴付人数的下降和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供求失衡所致的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乃势在必然。到2050 年,我国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4 亿,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15%。〔39〕参见杨舸:《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 期。届时,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
3.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深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下降。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 年达到9.98 亿的峰值以后逐年减少,年均减少超过三百万人〔40〕各年度就业人口数据可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著的2016 年至2020 年各年度《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年均减少数据系笔者以后一年度劳动年龄人数减去前一年度劳动年龄人数之和除以被统计年数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老龄社会整体需求低,难以支撑需求拉动型经济。总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欧盟和日本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的过程〔41〕参见易富贤:《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载《中国经济报告》2018 年第5 期。。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相当占比的人口进入低欲望低产出年龄段,整体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威胁。相关预测显示,受老龄化影响,正常情况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将由2019 年的6.3%逐步下滑至2035 年的4.41%,2050 年的2.67%。〔42〕参见翟凌云:《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潜在经济增速影响的估算》,载《上海金融》2021 年第8 期。
在老龄化背景下,反映晚婚晚育政策的现行法定婚龄,对于成年人婚育实施过于严格的限制,恶化我国人口结构的风险不容忽视〔43〕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十分复杂,人口政策、城市化、教育水平、生育成本等多种原因均可能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毋庸讳言,相对于其他国家生育率的逐步下降,晚婚晚育政策显然是我国生育率快速降低的重要因素。。依照我国目前的人口走势,预计在2033 年前后,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将超过20%,达到联合国超级老龄社会的标准〔44〕联合国关于老龄社会的标准,参见1956 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含义》对老龄社会类型所做的划分。。如果仍然实施晚婚政策,我国代际人口失衡将更加突出,不仅加剧养老负担,而且激化各种深层矛盾。除此之外,过晚的法定婚龄违背生理发育规律,使发育成熟、具有婚育意愿的青年人需要经历较长的婚姻等待期,不仅造成人为禁欲,对公民权利形成不必要的克减,而且导致非婚同居等婚外性行为泛滥,影响婚姻的严肃性,对结婚登记等婚姻制度构成冲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能,推动适度生育,以达到改善人口结构的目的。这意味着我国已由控制生育正式进入鼓励生育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改变晚婚晚育的婚育政策,以生理科学为基础,倡导人口均衡发展〔45〕参见原新:《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载《人口学刊》2016 年第5 期。及适龄婚育理念。修改法定婚龄,使其适应老龄社会的需要,已迫在眉睫。〔46〕笔者在有关法定婚龄的调研中发现,无论普通民众还是有关机关均普遍存在下述观点,即认为晚婚晚育已是现代社会趋势,当前我国男女实际结婚年龄远低于法定婚龄,故降低法定婚龄对于优化人口结构的意义有限。这显然低估了法律对于人们行为与观念的影响。一方面,降低法定婚龄不再将部分有较早婚姻欲望的人排除在婚姻之外;另一方面,更主要传递了一种适时婚育的理念,这对于矫正当前一味强调“晚婚晚育”的生育观意义重大。
婚姻自由是现代婚姻规则不可逾越的红线。老龄社会法定婚龄虽以促进生育为重要目标,却不能复制之前为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然人设定结婚义务的做法,亦不能偏离未成年人保护、子女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等诸种法益,还要考虑婚姻稳定等问题。故法定婚龄对于生育的促进应主要通过及时松绑自然人生育意愿,并倡导适时婚育的理念实现。具有婚育能力是设定法定婚龄之基础。未达生理发育成熟年龄者不具备基本婚育能力,婚姻影响其身心健康,故不应允许结婚。在具备婚育能力之后,婚姻回归民事主体自主抉择,国家不再干预。笔者认为,鉴于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的依据就是达此年龄者身体和智力已经发育成熟,我国法定婚龄的调整,应对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进行设计,并参照视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规则作适当缓和,使其适应于有特殊需要的特别人群,以满足民事主体复杂多样的婚育需要。
四、适应老龄社会人口结构之法定婚龄调整
诚如前述,我国法定婚龄制度的突出问题,一是允许结婚之法定年龄过晚,二是限制过于严格,不存在缓和与变通的路径。完善适应老龄社会的法定婚龄制度,既应摒弃单纯人口控制之婚育观;也应构建监护人同意、家事法院许可等配套制度,增加例外事由,使之更具弹性。
(一)法定婚龄的调整,应以自然人正常发育水平为基础,结合行为能力制度、教育制度、民众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1.社会老龄化形势。较之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老龄化形势更复杂。尽管从老龄化进程来看,日本、美国和欧盟多数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期比我国更早,老龄化程度更深,但较之其他国家,我国老龄化更加严峻。首先,老年人口基数远比其他国家大,随着二十世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我国年增老龄人口1500 万至2000 万,相当于年净增一个中小型国家的老年人口。按照这一发展趋势,至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 亿人。届时,全世界每4 个老人中就将有一个中国老人。其次,我国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在从1949 年至2001 年53 年的时间里,我国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仅提高了2.95%。但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自2001 年至2022 年仅用21 年时间我国就进入深度老龄时期,这一过程远比其他国家要短。〔47〕从65 岁以上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进入占比超过14%的老龄社会,法国为126 年、英国为46 年、德国为40 年、日本为24 年。参见陈泉:《美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再就业》,载《人口学刊》1991 年第5 期;郑秉文:《从“高龄少子”到“全面二孩”: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人口转变”的国际比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 期;王莉莉:《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载《日本问题研究》2011 年第2 期。考虑到计划生育的因素,我国社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进程将更快。再次,我国养老储备严重不足,具有未富先老的突出特点。我国的人均GDP 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老龄化程度却高于这些国家。〔48〕参见郭金华:《中国老龄化的全球定位和中国老龄化研究的问题与出路》,载《学术研究》2016 年第2 期。就此而言,为应对严峻的老龄化挑战,我国应将法定婚龄提前到一个相对较早的水平,以实现人口结构的代际均衡。
2.自然人生理发育水平。自然人在什么年龄发育成熟有待医学上的权威结论。笔者在知网变换关键词多角度搜索,并没能找到权威的结论。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女孩的青春发育呈现出年代提前的趋势,而关于男孩青春发育是否提前的结论尚不一致”。〔49〕朱铭强等:《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发育现状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 年第4 期。换言之,自然人发育成熟的标准是一个尚存争议且不断变化中的问题。不过,通常认识是,自然人发育年龄男女存在差异,女孩发育年龄通常要比男孩早两岁。如前所述,男满十六周岁、女满十四周岁,即基本发育成熟,此是基本共识。正因如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的实践认知。若单纯从发育的角度言,男满十六周岁、女满十四周岁即为可以考虑婚姻缔结事宜之最低年龄。
3.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是自然人“理智地形成意思的能力”。〔5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409 页。自然人只有能够判别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否则,须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限制,确保其行为合乎理性。婚姻不仅意味着男女结合,而且意味着组建家庭、共事生产并共同生活。婚姻缔结行为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亲属关系,产生配偶间的相互忠诚、彼此照料和扶养、日常家事代理等权利和义务,还牵涉到血脉传承等重大问题,事关当事人重大切身利益。故缔结者理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然,考虑到自然人个体发育差异,婚姻对于亲属关系、家庭功能、代际传承等的重大影响等,部分自然人即便未达到完全民事行为年龄,比如年满十六周岁,但已思想成熟,在其具有结婚意愿时,经监护人同意允其缔结婚姻,亦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从比较法上来看,以十六周岁作为法定最低婚龄者,多为未成年婚姻当事人设置了法定监护人或代理人同意这一程序,即属此理。
4.与教育制度及学制的衔接。婚姻虽非年轻人专利,但规范初婚年龄显系以年轻人为对象。年轻人身处发展提升黄金时期,所受教育之深浅、系统性程度对人生之影响至为关键。确保未成年人完成基本的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定婚龄之设置虽与教育制度无直接关联,但客观而言,过早地涉及婚姻必然对青少年接受教育构成冲击。故法定婚龄应与学制衔接,充分考虑婚龄对于青少年教育的影响,至少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前不得结婚。
5.民众的婚育意识。我国民众的婚育意识,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极大。如前所述,我国古代一直有早婚早育传统。自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几千年的历史中,早婚早育思想一直是主流。相应地,“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婚育观主导了我国的婚育政策。但随着晚育意识的不断提倡,加之教育水平提高、同居现象的普遍化〔51〕参见王仲:《结婚年龄之制约性条件研究——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推迟了》,载《西北人口》2010 年第1 期。、信息化时代人机交互满足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提升年轻人自我意识等因素叠加,我国年轻人婚育意识发生显著改变,晚婚晚育成为绝对主流的婚育观念。持不婚不育观念者亦不断增加,早婚早育变得不可想象。与之相伴的,则是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和生育率的不断降低。
6.比较法上的通常做法。比较法上之做法一般可从两方面管窥:一是联合国相关文件,二是各国法律上的规定。首先,童婚通常被认为有害健康,为使儿童免受暴力和胁迫并接受良好的教育,应严格禁止童婚。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除歧视公约》)第16 条第2 款规定,童年订婚和童婚应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关于成年标准,一般为十八岁,但可以依实际情况而有差异。《消除歧视公约》第1 条规定,儿童系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任何人。但若其本国法规定成年年龄小于十八周岁,则也可以小于十八周岁。故比较法上,各国多将年满十八周岁作为允许结婚之通常年龄〔52〕参见金梦:《比较法视域下的法定婚龄研究》,载《学术交流》2017 年第1 期。;或正视男女在发育周期上的差异,基于女孩生理发育较早之事实,将女孩的允结婚年龄适当下调,而以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作为本国允结婚年龄。
笔者认为,为应对严峻的老龄化计,宜在不损及当事人身心健康的情况下,采用一个相对较早的年龄。以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作为我国法定婚龄,并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结婚需经特别许可、或法定监护人同意,是较为理想的方案。原因如下。
1.如前所述,我国老龄化形势异乎寻常的严峻。规模大,速度快,且与代际人口失衡、未富先老叠加,多种问题交织,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威胁,这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的最大国情。
2.晚婚晚育并不能代表我国民众的婚育观念。虽然晚婚晚育已成为当代占绝对主流的婚育观念,但若将时间拉长则可发现,这不过是特定婚育政策主导下长期教育和宣传的结果。相反,我国古代一直存在早婚早育传统。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的允结婚年龄在中国古代尚是一个相对偏晚的年龄。何况,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发展,未成年人发育水平逐渐提前是一个世界性趋势。计划生育前后我国生育观念的迥然差异充分证明,国民生育观念远没有想象中的牢固,而是极具可塑性。
3.女孩比男孩早发育两年左右系客观事实。男女发育时间不一乃生理发育正常现象。婚姻既然以自然人发育情况为基础,则理应正视男女发育年龄的不同。基于男女发育的年龄差异规定不同法定婚龄,系基于生理发育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合理规定,无关性别歧视,故仍应坚持。
4.不会对义务教育构成不合理冲击。接受必要的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若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自然人结婚,势必对义务教育构成冲击。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入学年龄为六周岁,完成义务教育时年已满十五周岁。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的允结婚年龄并不会对义务教育构成冲击。虽然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绝大多数青少年会继续更高阶段的学习,但此时已非强制的义务教育阶段,部分青少年将不会继续学业而走向社会,一律禁止结婚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没有必要。
5.不会损及未成年人权益。虽然按照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十六周岁的人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难以充分认知结婚这类影响广泛的行为对其一生的重要影响。然而,首先,十六周岁是可以附条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民法典》第18 条第2 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分说明法律认可自然人在年满十六周岁时,符合一定条件即可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既然自然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时,可以作为具有足够识别力之证明,则当其识别力得到父母、恋人及亲属等关爱之人肯定时,肯认其具有理性识别能力也就具有正当性。其次,为十六周岁年龄的人缔结婚姻设定法定监护人同意程序,通过监护人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弥补其认知能力的不足,能够有效地补足其行为能力缺陷。
6.比较法实践支持。尽管禁止童婚是各国通例,而《联合国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界定为十八岁以下的自然人。但《儿童权利公约》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允许各国根据本国实际界定成年标准。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基于本国实际情况采用了男满十八岁、女满十六岁作为允结婚年龄标准。个别国家甚至基于严重老龄化之国情,而将允结婚年龄设置得很低。如俄罗斯最低可至十四岁〔53〕参见冯秋燕:《中俄婚姻缔结法律制度之比较》,载《西伯利亚研究》2005 年第1 期。。从实践效果来看,并没有出现系统性侵害青少年权益、降低人口素质等负面后果。
7.契合我国传统。《大清民律草案》与1929 年民法均规定了男满十八岁、女满十六岁的结婚年龄。澳门地区〔54〕参见《澳门民法典》第1479 条。和香港地区〔55〕参见叶英萍:《中国大陆与香港婚姻法的比较》,载《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2 期。实施年满十六岁的法定婚龄制度,效果良好,并没有造成冲击教育、生育率失控问题,这充分说明即便将发育较早的女性允结婚年龄适度提前,亦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相反,是较为契合中华民族婚育传统的可行制度。
(二)在将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确定为法定婚龄的情况下,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探讨
1.应否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上增设一个特殊民事行为能力
在一般观念中,年满十八周岁的人虽具对一般问题之辨识力,但仍属懵懂混沌年纪;而婚姻作为组建家庭、影响血脉传承的大事,实属重大。此时,是否具备一般民事行为能力即为已足?是否需要将婚姻行为规定为一种较一般民事行为更复杂,对行为能力要求更高,需具有更高行为能力始得为之的特殊民事行为。比如,在达到十八周岁成年标准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仍需父母同意始可以结婚。此种做法在比较法上已有先例。比如《法国民法典》第148 条规定,子未满二十五周岁,女未满二十一周岁,非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在理论上,我国一些学者也多用特殊行为能力解释法定婚龄问题。〔56〕参见姜大伟:《体系化视阈下婚姻家庭编与民法总则制度整合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4 期。
笔者认为,现实中确有一些特殊复杂事务需要行为人具有更高的意思能力,故设立特殊行为能力有讨论空间。但就法定婚龄领域而言,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上另设特殊行为能力没有必要。其一,另设特殊行为能力属于民事法上的重大问题,牵涉民事行为能力理论的根本变化,需特别慎重。所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亦即自然人通过自主的意思表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全面能力。“完全”的含义,即对于各类民事事务均得自主为之。若因事属重大而予突破,则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变得不“完全”,因之将出现理论不周延问题。婚姻固属大事,但为此而另设特殊民事行为能力,在必要性上还需特别专门论证。订立巨额合同、开设公司等无不事属重大,若婚姻事宜成立特殊行为能力,则前述事项似也有成立特殊民事行为能力之必要。若作此规定,如何避免动摇民事行为能力理论的根基?何况,从父爱主义角度观之,子女总属于难以独自面对风雨的雏鹰。多数时候,对于子女能力之担忧不过是关心则乱的遁词。至于学者常论及的《法国民法典》第148 条关于男满二十五周岁、女满二十一周岁始得独立为婚姻意思的规定,宜置于特定时期历史地看待。一方面,《法国民法典》制定之时,法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其时父爱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受制于理论积淀不充分之时代影响,《法国民法典》不太注重理论的周延性,始终是其难以弥补的缺陷。其二,在将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确定为法定婚龄的情况下,已能将婚姻行为融入民事行为理论,达到运用民事行为能力理论解释婚姻行为的效果,无须另行创设特殊民事行为能力概念。
2.在女满十六周岁而具结婚意愿的情况下,其行为能力如何补足
从比较法的做法来看,在女满十六周岁而具结婚意愿的情况下,通常建立特许制度,赋予父母、监护人、监护监督机构或法院补足其行为能力之权利。
第一,就补足之人而言,在比较法上既有规定补足之人为法定代理人者,也有规定为监护人者。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是监护托管机构或法院。前者如我国1929 年民法第981 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中者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487 条第1 款规定,“满十六岁而未满十八岁之未成年人结婚,应获行使亲权之父母许可或获监护人许可”。后者如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487 条第2 款规定,“如存在应予考虑之理由显示婚姻之缔结为合理,且未成年人之身心已足够成熟,则法院可透过批准取代上款所指之许可”;《俄罗斯民法典》第27 条后段规定,“即便未经父母、收养人或者受托人同意,也可以经监护托管机构决定,或者法院判决,取得完全行为能力”。
笔者认为,补足之人宜规定为监护人而非法定代理人。婚姻系人身行为,须亲自为之,不得代理,同意或许可之行使乃在于给具有婚姻意愿之未成年人添加一道程序,一方面补足其行为能力,另一方面使其更审慎地对待婚姻大事。同意或许可之行使非涉代理,故不宜规定为法定代理人。人民法院作为专业裁判机构,享有同意许可之裁量权显然具有合理性。但就监护托管机构而言,其仅为特定情况下的监护受托者,故不宜享有许可同意权。我国曾有学者主张建立行政特许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未达法定婚龄但有特殊原因或重大事由确需结婚者的审批权〔57〕参见周文洋:《关于我国现行法定婚龄的法律思考》,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6 期。。民政部门在监护监督方面具有独特地位,由其享有许可同意权似具有一定合理性,专门行政管理机构的地位亦使其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若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许可很可能使其陷入具体事务的海洋,因而并不现实。在笔者看来,此种许可由负责婚姻监督管理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即可为之,但要严格法定事由、设置特别程序、强化许可责任,以防止许可行为随意化。
第二,就父母行使同意权而言,在父母只有一方健在的情况下,健在一方同意即构成父母同意自不待言。但在父母均健在的情况下,单方同意是否构成父母同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比较法上,有规定父亲同意即可者,如《法国民法典》第146 条后段〔58〕《法国民法典》第148 条后段规定:“父母意见不一致时,有父的同意即可。”;有规定单方同意即为已足者,如《日本民法典》第737 条〔59〕《日本民法典》第737 条规定:“(一)未成年的子女结婚,应经其父母同意。(二)父母一方不同意时,有他方同意即可。父母一方不明、死亡或不能表示其意思时,亦同。”。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基于父权主义的父亲单方同意权实不可取。在仅有父母一方同意的情况下,鉴于年满十六周岁即已具备一定意思能力,可一定条件承认父母单方同意的效力。若同意一方为与子女共同居住之父母,鉴于其对子女的情况更为了解,此时宜承认其同意之效力;若非为共同居住之父母,鉴于其与子女的关系相对不如共同居住一方密切,则不宜承认其同意之效力。同时,为防止共同居住父母一方滥用同意权损害未成年人利益,应赋予不同居父母一方异议权。若父母均非共同居住,则只有父母一致同意方构成父母同意。除非出现如《法国民法典》第149 条所规定之事由,即父母一方不能表示其意思时,一方的同意方构成父母同意。
第三,就同意权之行使,需要明晰以下问题。一是意思表示是否必须明示,可否以默示方式作出;二是若须明示,是否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就法理言之,无论明示与否,似均可行使同意权。就默示而言,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法定监护责任,自身亦是婚姻之间接关联者。当其得知子女婚姻意愿而不予阻止,则视为尊重子女婚姻意愿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明示而言,婚姻毕竟事关重大,父母同意不宜适用推定。笔者认为,无论从意思表示的慎重性抑或纠纷防止的角度,同意权之行使均应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为之,沉默意味着拒绝。至于是否以书面方式为之,则宜区分监护人情况。在父母或其他近亲属为监护人的情况下,做出同意之意思表示即可;在其他个人或组织为监护人的情况下,由于其与被监护人关系相对较远,为未成年人负责计,同意之表示须以书面方式为之。
第四,就监护人滥用同意权的规制而言,若婚姻明显存在有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之事由,而监护人视若无睹,则监护人违反《民法典》所规定之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构成滥用同意权。此时,应赋予有关个人和组织向人民法院申请否定该同意之后果的权利。较具争议性的问题是,若存在未成年人心理成熟之明显证据,而监护人拒不同意,是否构成同意权滥用。笔者认为,监护人是否同意,系其依据自主判断做出的决定,同意或者不同意均属同意权的正常行使。通常情况下,当监护人不予同意时,亦不存在同意未成年人婚姻意愿之急迫需要,故不宜认定属监护人滥用同意权。惟在涉及未成年人非婚生育等当事人子女利益特殊情况下,为子女利益考虑,方可通过法院改变监护人不予同意之后果。此时,应认为系属法院依申请而进行合理裁量,亦不宜认定监护人构成同意权滥用。
五、结语
婚姻本系成年人私事,是否缔结婚姻,与何人缔结婚姻,在何时缔结婚姻均应依当事人自主意思。惟在对公共利益构成挑战、使环境不堪重负、使可持续发展难于实现之时,始有施加干预与限制之必要。至少对成年人而言,此种限制和干预注定是非常态的。在一个正常社会,维持过晚法定婚龄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就老龄化社会而言,既然低生育率已成为困扰社会的新问题,则对成年人婚姻意愿不再加以限制,使其回归自主也就理所当然。以冲击教育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对法定婚龄进行调整,不仅法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会加重人口结构失衡,加剧老龄化。由是观之,应对法定婚龄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