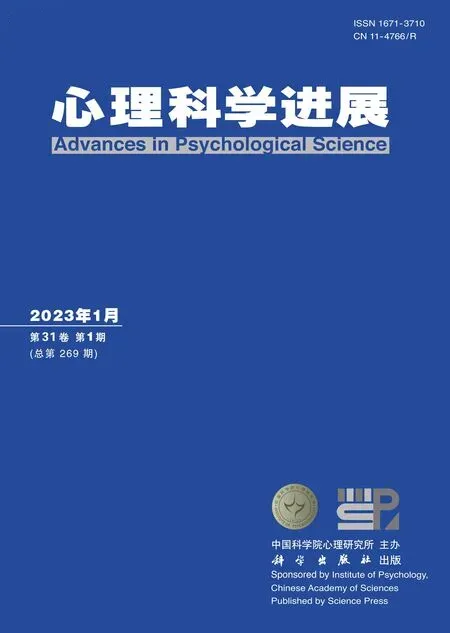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的双刃效应:压力交互理论的视角*
2023-01-07郑银波黄华东李爱梅
郑银波 李 馨 黄华东 李 斌 李爱梅
(1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1 引言
死亡提醒(mortality cues)是触发个体死亡心理体验的特定事件与经历(Grant & Wade-Benzoni,2009)。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便是一种显著的死亡提醒,实时更新的死亡病例与新闻信息导致个体心理与行为显著变化,并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工作状态(Hu et al.,2020;Pyszczynski et al.,2021),导致部分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工作表现不尽人意,不仅出现更高的抑郁与焦虑症状,而且早退缺勤等怠工行为更为频繁(Pauksztat et al.,2022;Shao et al.,2021)。然而,在疫情期间也有医疗人员不顾自身安危驰援疫区(金振娅 等,2020),更有建筑工作者在10 天内迅速建成工期需要2 年的火神山医院(新华社,2020)。为何员工面临同一死亡提醒会出现大相径庭的工作表现?诸多学者近年开展的职场死亡提醒研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前人在解释死亡提醒效应时,常采用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与创生(generativity)两种理论视角(Erikson,1963;Greenberg et al.,1986)。两种视角均认为刻画个体死亡心理体验的死亡意识(death awareness)是解释死亡提醒效应的核心因素。基于情绪与认知差异,死亡意识可以分为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与死亡反思(death reflection)。其中,死亡焦虑反映个体对死亡感到忧虑恐慌的消极情绪状态(Nyatanga & de Vocht,2006),恐惧管理视角认为,个体为缓解死亡焦虑而产生的自我保护动机,会诱发其在职场敌对排斥那些引发自身死亡焦虑的同事,并做出缺勤与离职等工作退缩行为(Grant & Wade-Benzoni,2009;Mejia et al.,2018)。尽管该视角为死亡提醒消极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却难以解释死亡提醒积极效应的内在机制。在创生视角的解释中,个体面对死亡提醒时会积极反思生命的长远意义,并产生持续为社会贡献价值的利他动机,进而促进其在职场中做出利他行为(Shao et al.,2021;Wei et al.,2021)。然而,部分研究表明死亡焦虑在特定情况下也能推动员工绩效(Hu et al.,2020;Stafford,2016;Zhong et al.,2021),这说明已有研究仍未就“死亡提醒如何以及何时对员工绩效产生双刃效应?”这一问题提供统一稳健的理论解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恐惧管理视角与创生视角的研究各侧重于解释死亡提醒的单一效应,并忽略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的内在联系(Zhong et al.,2021),从而导致难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解析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共同机制与边界条件。
基于此,有研究尝试通过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Hobfoll,1989)为死亡提醒双刃效应提供统一的理论解释(Luta,2021)。资源保存理论强调个体的压力感知取决于压力源本身而非个体差异(廖化化 等,2022)。而有研究发现,个体死亡焦虑的产生源于对新冠疫情的主观认知加工,而并非取决于客观的疫情每日死亡人数(Hu et al.,2020)。这说明,个体死亡意识可能受到主观认知与客观死亡提醒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压力交互理论(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Lazarus & Folkman,1984)这一强调环境刺激和与个体认知共同影响个体压力的理论,可能更适合于解释死亡提醒双刃效应。
本文首先归纳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产生双刃效应的表现,指出并解释当前研究存在分歧的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然后,依据压力交互理论从统一视角探讨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内在机制。最后,通过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启示。
2 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的双刃效应
基于绩效的行为视角,员工绩效可以分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以及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Rotundo & Sackett,2002)三个维度。任务绩效是组织要求员工完成并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工作行为(Motowidlo & Van Scotter,1994)。组织公民行为是对组织及其成员有益但未得到组织明文奖励的利他行为,依据对象可分为亲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s to organizations,OCB-O)与人际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s to individuals,OCB-I) (MacKenzie et al.,1998;Jacobsen & Beehr,2022)。反生产行为是损害组织及其成员福祉的消极工作行为,如消极怠工与伤害同事等行为(Rotundo & Sackett,2002)。基于此,下文将梳理死亡提醒通过死亡反思与死亡焦虑对员工绩效产生的双刃效应。
2.1 死亡反思对员工绩效的积极效应
死亡反思对员工任务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死亡反思促进组织成员有助于任务绩效实现的积极组织行为。员工层面,高死亡反思员工做出更多创新行为。这是由于此类员工更加注重自我成长与满足社会需求,会偏好采取创意性策略以应对死亡提醒带来的工作挑战,从而推进自身工作与组织目标的实现(Grant & Wade-Benzoni,2009;Takeuchi et al.,2021)。领导者层面,高死亡反思领导者会采取更有成效的领导行为。反映死亡反思的遗产信念(legacy beliefs)是指个体对自身行为是否具有持续影响的信念。高遗产信念领导更愿意做出具有角色模范作用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并为追随者营造公平稳定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低遗产信念领导则倾向于聚焦自身工作与职位晋升,而对追随者采取放任自流的领导行为(Zacher et al.,2011)。因此,高死亡反思领导者更能积极完成自身的领导角色任务。另一方面,死亡反思减少组织成员妨碍其任务绩效的消极组织行为。死亡提醒引发的死亡焦虑导致员工为保存资源而违背职场安全规范(Hobfoll,1989;Yuan et al.,2019),而高死亡反思员工会将维护职场安全视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进而更愿意做出工作安全行为以实现更高的安全绩效(Jacobsen & Beehr,2018;Yuan et al.,2019)。这说明,基于积极认知与意义追求的死亡反思能促进员工适应性地应对职场死亡提醒,从而实现更高的任务绩效。
高死亡反思的组织成员更倾向于做出利他的组织公民行为。OCB-I 方面,由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性,强调内在价值与自我超越的死亡反思促使员工从事组织公民行为(Grant & Wade-Benzoni,2009)。比如,高死亡反思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会为同事提供更多的指导帮助(Luta,2021),而高死亡反思的普通员工也愿意在疫情期间付出额外的时间精力协助团队成员(Wei et al.,2021)。另一方面,死亡反思增进组织成员的OCB-O。Chen 等(2020)发现,企业高管的死亡会激发在职高管的死亡反思,进而积极履行对自身无直接利益但促进企业声誉的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死亡反思的组织成员在面临死亡提醒时能够产生利他动机并展现更多组织公民行为。
2.2 死亡焦虑对员工绩效的消极效应
组织中的情绪研究存在一种对称假设(symmetrical assumption),即员工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员工绩效,反之消极情绪会阻碍员工绩效(Lindebaum & Jordan,2014)。死亡焦虑与员工绩效之间也遵循这一对称假设,即代表个体消极情绪状态的死亡焦虑阻碍员工绩效。具体而言,死亡焦虑状态下的员工更难以高效执行工作任务,导致任务绩效难以令人满意。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员工会为了摆脱死亡焦虑而采取行动抑制死亡相关的负面情绪与认知(Greenberg et al.,1986)。然而,这种死亡焦虑应对会持续消耗员工心理资源并使其在工作中分心,最终使员工陷入情绪耗竭并难以投入工作(Hu et al.,2020;Sliter et al.,2014)。例如,高死亡焦虑医护人员和消防员表现出更高的工作倦怠与更低的工作投入(Sliter et al.,2014)。同时,组织外部恐怖袭击蔓延的死亡威胁会引发教师与公务员的死亡焦虑,进而降低其工作绩效(De Clercq et al.,2017;Raja et al.,2020)。这说明,组织内外部死亡提醒会引发员工死亡焦虑,并阻碍员工维持积极工作状态以实现较高的任务绩效。
另一方面,死亡焦虑不仅阻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还会诱发员工从事反生产行为。死亡焦虑之所以阻碍组织公民行为,是由于个体为减缓死亡焦虑更倾向从事能直接维持自尊的活动(Greenberg et al.,1997)。因此,死亡焦虑员工更愿意投入产生直接效益的角色内工作任务,从而减少那些未获得组织正式奖励的组织公民行为。例如,高死亡焦虑的医护人员与消防员更不愿意为同事提供指导与帮助(Luta,2021;Yuan et al.,2019)。在Jacobsen 和Beehr (2022)的研究中,死亡焦虑通过削弱员工利他动机抑制了员工的OCB-O 与OCB-I。反生产行为方面,伴随死亡焦虑而来的负面情绪使员工更难以控制非伦理行为,进而让员工做出损害组织与同事利益的反生产行为(Kouchaki & Desai,2015)。员工不仅会由于年龄线索诱发的死亡焦虑而排斥高年龄同事(Mejia et al.,2018),也会因新冠疫情引发的死亡焦虑而缺勤早退(Shao et al.,2021)。综上所述,作为个体对死亡提醒的负面情绪反应,死亡焦虑会阻碍员工任务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并通过激发反生产行为损害员工所在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
2.3 死亡焦虑对员工绩效的积极效应
新近研究开始挑战情绪与员工绩效间的对称假设,并逐步探索其非对称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即消极情绪能够促进员工绩效,反之积极情绪也可能阻碍员工绩效(Lindebaum & Jordan,2014)。学者们发现,死亡焦虑与员工绩效也呈现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死亡焦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员工绩效(如Hu et al.,2020;Zhong et al.,2021)。
任务绩效方面,死亡焦虑能够增进个体工作参与意愿。根据恐惧管理理论,死亡焦虑员工会将工作价值作为一种抵御死亡威胁的自尊提升策略(Greenberg et al.,1997;Jonas et al.,2011),从而愿意积极参与工作以缓解死亡焦虑。例如,Stafford(2016)发现特质死亡焦虑与员工离职意愿无关,但与工作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实验研究也表明员工在死亡焦虑被成功操纵后报告了更高的工作参与热情(Yaakobi,2015)或实验任务投入(Hu et al.,2020)。这说明,死亡焦虑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可能存在积极效应。
组织公民行为方面,死亡焦虑可能增加个体对特定群体的组织公民行为。恐惧管理理论认为,死亡焦虑个体会对其认同的文化群体做出利他行为以彰显自我价值(Jonas et al.,2002)。基于此,如果死亡焦虑员工对其所在组织具有较高组织认同感,则可能会将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缓解死亡焦虑的策略。Jacobsen 和Beehr (2022)的研究显示,员工组织认同感越低,则死亡焦虑会更显著地阻碍组织公民行为。在新冠疫情期间,能够促进员工组织认同的服务型领导显著增强员工状态死亡焦虑与利他行为间的正向关系(Hu et al.,2020)。此外,当员工死亡反思水平较高时,即便其处于死亡焦虑也会做出组织公民行为(Zhong et al.,2021)。这说明死亡焦虑与员工绩效存在非对称效应,但已有研究并未明确和解释其具体发生条件,这与死亡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广泛忽略有关。
2.4 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的解释
关注死亡意识内在联系有利于解释死亡焦虑的非对称效应。已有研究多基于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在情绪与认知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其单一后效(Grant & Wade-Benzoni,2009;Shao et al.,2021),却忽略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员工绩效的共同作用(Zhong et al.,2021)。为此,下文将系统梳理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在稳定性、构念关联性与时间共存性三方面的联系,并基于此解释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
首先,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的稳定性(stability)联系体现在两者兼具特质性(trait)与状态性(state)。个体特质性方面,死亡焦虑源于个体对死亡必然性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具有难以消除的特质性(Sliter et al.,2014);而死亡反思作为一种认知加工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Yuan 等(2019)发现死亡反思跨期3 周的重测信度达到0.6 的显著水平。个体状态性方面,死亡焦虑更为急促短暂,而死亡反思在一定情境下也具有可塑性(Shao et al.,2021;Yuan et al.,2019)。据此,未来研究应明晰并根据研究重点控制状态死亡意识(即状态死亡焦虑 vs.状态死亡反思)或特质死亡意识(即特质死亡焦虑vs.特质死亡反思),才更能揭示不同死亡意识的单一效应与共同效应。
其次,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在构念上密切关联。由于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均是个体的死亡心理体验,若干同时测量两者的研究亦发现两者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Luta,2021;Shao et al.,2021;Takeuchi1 et al.,2021;Zhong et al.,2021;Yuan 等(2019)的研究除外)。最后,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具有时间共存性。在Jacobsen 和Beehr (2022)的研究中,死亡反思与死亡焦虑显著正相关,并且当假设模型中不包含死亡反思时,死亡焦虑与组织公民行为便不再显著相关。Zhong 等(2021)的研究也发现,部分员工在疫情期间并非总是处于单一的死亡焦虑或死亡反思状态,而是能同时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这说明,个体在一定周期内的不同状态死亡意识能够共存,割裂地探讨死亡焦虑或死亡反思难以揭示其共同作用。
基于死亡反思与死亡焦虑的密切联系,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可能源于死亡反思的影响。部分员工即便处于死亡焦虑也能实现高安全绩效,或者在疫情期间也做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原因便在于这些员工拥有较高的特质死亡反思或状态死亡反思(Yuan et al.,2019;Zhong et al.,2021)。尽管Zhong 等(2021)明确指出死亡反思是影响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其并未对此提供进一步的解释。而揭示死亡焦虑与死亡反思在时间共存性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能够有力支撑死亡反思为何是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进而厘清关于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的研究分歧。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文献对死亡意识内在联系的忽略也暴露当前研究的理论局限。一方面,恐惧管理视角与创生视角均侧重于解释单一的死亡提醒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死亡意识的内在联系,并阻碍学者从统一的理论视角解释死亡提醒双刃效应。因此Ferris 等(2016)建议使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将不同构念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能够简化与澄清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的双刃效应。本文响应这一呼应,引入压力交互理论,将员工面临的死亡提醒定义为一种压力源,并阐释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如何影响其状态死亡意识与工作绩效,最后依据理论从个体资源与情境资源的角度梳理该机制的边界条件(本文模型参见图1)。

图1 压力交互视角下死亡提醒影响员工绩效的概念框架
3 压力交互视角下死亡提醒影响员工绩效的心理机制
3.1 压力交互视角下的死亡提醒
压力源(stressors)是令个体感到压力,并能够阻碍或促进个体目标实现的因素(Cavanaugh et al.,2000)。压力交互理论认为,压力源对个体施加恶性压力(distress)还是良性压力(eustress)主要取决于个体对压力源的自我相关性与利害程度的初级评估(primary appraisal) (Lazarus & Folkman,1984;Mitchell et al.,2019),其中包括对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threat appraisal)与挑战性评估(challenge appraisal)等认知评估倾向(Cavanaugh et al.,2000)。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将死亡提醒定义为一种会对个体施加压力,并威胁或促进个体目标实现的死亡提醒压力源。同时,个体会对该压力源进行威胁性评估与挑战性评估。具体而言,当个体对死亡提醒做出威胁性评估时,则会视死亡提醒压力源为一种与自身相关并威胁目标实现(如保持生命健康)的威胁性压力源;反之,当个体对死亡提醒做出挑战性评估时,会将死亡提醒压力源视为一种与自身相关并有益目标实现(如增进生命意义与工作价值等)的挑战性压力源(Hillebrandt& Barclay,2022;Webster et al.,2011)。
依据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不同的认知评估倾向,个体随后可能产生差异化的状态死亡意识与工作行为。根据压力交互理论,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差异使个体产生不同的情绪与认知反应(Lazarus,1991;Lazarus & Folkman,1984)。具体而言,对压力源进行威胁性评估的个体更容易情绪消极;而对压力源进行挑战性评估的个体更不易被消极情绪干扰,且更关注压力源的问题解决(Folkman,1984)。已有研究发现,员工在面临死亡提醒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情绪与认知反应,其既会出现焦虑与情绪耗竭等适应不良的压力应激症状(如Sliter et al.,2014;Hillebrandt & Barclay,2022),也表现出生活满意度提高与价值追求转变等积极认知(如Grant & Wade-Benzoni,2009;Yuan et al.,2019)。因此,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差异可能使个体体验到不同的死亡心理。此外,压力交互理论还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是联结压力源与员工绩效的关键机制(Lazarus & Folkman,1984: LePine et al.,2016)。这说明,员工可能会对死亡提醒压力源进行威胁性评估或挑战性评估,而这些认知评估差异会使员工产生不同状态死亡意识,从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双刃效应。
3.2 死亡提醒压力源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
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可能影响其状态死亡焦虑。首先,生命是个体竭力保护和培育的重要资源,这导致个体会将死亡提醒压力源视为一种威胁性压力源(Hobfoll,1989;Sliter et al.,2014)。例如,员工会由于新冠病毒的致命性而产生严重的威胁感知(Hillebrandt & Barclay,2022)。其次,个体会在压力源威胁自身目标实现时出现状态性的消极情绪(Lazarus,1991)。焦虑是一种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典型的消极情绪反应,当个体感知到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与威胁时便容易产生焦虑感(Lazarus,1991;Ma,Liu,et al.,2021)。这说明,个体所产生的死亡焦虑也与其对自身生命感到失控与受到威胁有关。例如,当癌症患者认为其癌症复发会威胁生命,便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死亡焦虑(Curran et al.,2020);员工在疫情期间对新冠疫情的威胁性评估也显著加剧其一般状态焦虑与状态死亡焦虑(Hu et al.,2020;Hillebrandt& Barclay,2022)。因此,当个体对死亡提醒这一压力源做出威胁性评估,会认为死亡提醒压力源与自身相关并威胁生命健康维持等重要目标,从而产生状态死亡焦虑这一消极死亡心理。
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可能影响其状态死亡反思。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影响状态死亡反思体现在角色责任、个体成长与积极情绪体验三方面。首先,当个体对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时会产生更强的责任感(Cavanaugh et al.,2000),而个体处于死亡反思时,也会产生为社会持续做出贡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Grant & Wade-Benzoni,2009)。其次,个体对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意味着其将应对压力视为促进成长与幸福的机会(Li et al.,2020),而个体经历创伤后的死亡反思使个体将死亡应对与工作职责视作一种更具挑战性与社会价值的使命(Yuan et al.,2019)。最后,个体对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促进个体更积极的情绪和认知体验(Cavanaugh et al.,2000),而高死亡反思员工面临死亡提醒时也体验到更高的生活满意与更低的情绪耗竭(Yuan et al.,2019;Zhong et al.,2021)。因此,相较激发消极情绪的威胁性评估,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更可能促进其死亡反思。综上所述,当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会认为死亡提醒压力源与自身相关并能够促进生命意义实现等重要目标,从而产生状态死亡反思的积极死亡心理。
3.3 死亡提醒压力源评估与死亡意识的动态关系
员工由死亡提醒触发的不同状态死亡意识具有共存性与波动性。在Zhong 等(2021)基于新冠疫情死亡提醒的潜在剖面研究中,存在反映员工状态死亡意识具有共存性的“高死亡焦虑-高死亡反思”等潜在剖面组合。同时,员工的状态死亡意识在一定周期内具有波动性。员工疫情期间的状态死亡意识不仅在一个月内动态变化(Takeuchi et al.,2021),而且在十个连续工作日内也存在显著的日间变化(Hu et al.,2020),因此,员工死亡意识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共存性与波动性,但现有基于恐惧管理等理论的研究却并未清晰解释该动态过程。
压力交互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能为上述问题提供潜在的理论解释。一方面,压力交互理论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是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Folkman & Lazarus,1985),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倾向会随压力源变化而改变(Liu et al.,2022)。基于体验取样法的研究表明,员工对工作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存在每日间的波动变化(Ma,Liu,et al.,2021)。另一方面,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具有共存性,个体可能会对同一压力源既做出挑战性评估,又做出威胁性评估(Lazarus & Folkman,1984;Li et al.,2022)。在Li 等(2022)的研究中存在三种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剖面组合,这些剖面组合表明,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同时对压力源进行挑战性评估与阻碍性评估,且单一的阻碍性评估和挑战性评估均会随时间转变为这一评估模式。这说明,个体对同一压力源的不同认知评估是一个既共存又动态变化的过程。基于此,员工状态死亡意识的共存性与波动性可能是受其动态评估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影响。另外,压力交互理论也能为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提供独特的理论解释。以死亡焦虑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效应为例,员工之所以在处于死亡焦虑时仍做出组织公民行为,原因可能在于员工即便处于死亡焦虑,也可能会对死亡提醒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从而产生对员工行为具有积极作用的状态死亡反思(Zhong et al.,2021)。
3.4 死亡提醒压力源、死亡意识与员工绩效
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差异及其产生的状态死亡意识可能差异化影响员工绩效。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对工作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促进其工作绩效(Li et al.,2020;Ma,Peng,et al.,2021),而对工作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阻碍其任务绩效(LePine et al.,2016)和组织公民行为(Parker et al.,2019)。这说明,员工对工作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差异对其绩效具有双刃效应,该理论预测可能也适用于解释死亡提醒双刃效应。具体而言,在不考虑状态死亡意识的动态化与其他调节因素的前提下,对死亡提醒压力源进行威胁性评估更多使员工产生状态死亡焦虑并阻碍其工作绩效,而相应的挑战性评估更多使员工产生状态死亡反思并促进其工作绩效。
3.5 死亡提醒压力源影响死亡意识的调节因素
压力交互理论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受限于个体可利用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Lazarus & Folkman,1984;Liu et al.,2022)。因此,本文根据压力交互理论的观点,从个体资源和情境资源两个角度整合已有研究中的边界条件,基于统一的理论视角为死亡提醒压力源何时影响员工的认知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提供合理解释。
3.5.1 影响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个体资源
特质死亡反思、特质正念、心理权力感与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是个体应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重要个体资源(Belmi & Pfeffer,2016;De Clercq et al.,2021 Liu et al.,2022;Yuan et al.,2019)。首先,特质死亡反思是个体由于高龄或长期暴露于死亡提醒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积极死亡认知,其能够减缓个体在面对死亡提醒时的消极心理反应(Grant & Wade-Benzoni,2009)。例如,消防员的高特质死亡反思减缓工作安全威胁对其幸福感和安全绩效的消极影响(Yuan et al.,2019)。因此,特质死亡反思可能能够减缓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与死亡焦虑反应。其次,正念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专注当下且不加批评地对待当下经历与体验,已有研究发现高特质正念能够减少个体对死亡提醒的过度认知加工与情绪反应(Niemiec et al.,2010)。与低特质正念员工相比,高特质正念员工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出现更少的心理压力和失眠症状(De Clercq et al.,2021)。这说明,特质正念可能有助于减少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与状态死亡焦虑。
再次,产生安全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心理权力是个体应对死亡提醒的重要个体资源(Belmi & Pfeffer,2016)。以控制为核心的权力感能给员工带来丰富的心理资源,从而减缓死亡对个体控制感的威胁(Frazier,2020;李馨 等,2020)。在Belmi和Pfeffer (2016)的实验中,高心理权力员工在死亡提醒后体验到更少的死亡焦虑并做出更多利他行为。因此,高心理权力感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威胁感知与死亡焦虑可能更低。最后,促进定向特质是个体评估压力源时的重要资源(Liu et al.,2022)。高促进定向个体不仅拥有更强的理想信念,并对成长机会也更敏感(Higgins,1997)。Li等(2021)发现,高促进定向企业高管将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视为成长机会并产生更少自利导向,进而做出更多企业慈善捐赠。这说明,高促进定向员工更可能对死亡提醒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并产生更积极的死亡认知。综上所述,特质死亡反思、特质正念、心理权力感与促进定向等个体资源对于个体应对死亡提醒压力源具有重要作用,这些资源可能能够减缓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与状态死亡焦虑,并增强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挑战性评估与状态死亡反思。
3.5.2 影响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组织情境资源
企业内部社会责任(in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CSR)与服务型领导是个体应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重要组织情境资源。一方面,组织资源流动是个体积累资源的重要渠道,以促进员工身心福祉的高ICSR 能够使个体从组织中获得资源补充(廖化化 等,2022)。例如,疫情期间企业的高ICSR 增进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知,从而减缓员工对新冠疫情死亡提醒的威胁性评估与状态死亡焦虑(Hillebrandt & Barclay,2022;Shao et al.,2021)。另一方面,领导者及其有效领导行为是影响员工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情境资源(Cooper et al.,2018),以道德利他为导向、为下属成长提供资源的高服务型领导有效减缓员工因疫情引发的状态死亡焦虑,进而促进员工工作投入和利他行为(Hu et al.,2020)。这说明,组织中充足的ICSR 与服务型领导等情境资源有助于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产生更积极的认知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产生的双刃效应,并基于压力交互理论解析该效应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文章基于压力交互理论提出,死亡提醒可以被视作一种使个体产生压力并阻碍或促进个体目标实现的压力源,个体对该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与挑战性评估分别影响其状态死亡焦虑和状态死亡反思,进而对员工绩效产生双刃效应,且该过程受到个体资源与情境资源的影响。文章提出的理论模型兼具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本文基于压力交互理论的核心观点,从统一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产生双刃效应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不仅细化了死亡提醒通过认知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影响员工绩效的心理机制,而且能够从动态视角为死亡焦虑非对称效应等研究分歧提供合理解释。实践意义方面,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在统一理论框架内为组织干预提供清晰直接的指导。例如,压力交互理论相关的研究表明,相较组织责备氛围,组织学习氛围更有利于员工对压力源做出挑战性评估(Ma,Liu,et al.,2021)。基于此,管理者可以鼓励员工在新冠疫情等特殊时期学习与分享新的工作知识与技能,从而营造良好的组织学习氛围以促进员工积极应对死亡提醒带来的挑战。
尽管诸多学者开始关注职场死亡提醒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但该领域研究仍有许多值得深挖之处,如深化压力交互视角下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过程机制,并拓展其边界条件以及组织干预措施。
4.1 检验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过程机制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压力交互视角下的死亡提醒双刃效应。首先,实证检验死亡提醒作为一种压力源的构念有效性。尽管本文在理论上论证了死亡提醒作为压力源的可能性,但仍然缺乏直接的实证证据与测量工具。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压力交互理论将新兴的工作体验建构为一种压力源并探讨其工作结果(如Cho & Kim,2022;Li et al.,2022)。例如,Cho 和Kim (2022)基于压力交互理论揭示了不健康饮食这一新型压力源的存在及其对员工绩效的影响。这些研究为如何实证检验死亡提醒压力源提供了参考,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这些思路检验死亡提醒压力源的理论有效性并开发相关的测量工具。
其次,未来研究可以拓展引发员工死亡意识的组织内部因素。现有研究更多聚焦新冠疫情等组织外部死亡提醒,组织内部的死亡提醒仍有待挖掘。以工作负荷为例,工作要求与工作控制的不匹配使员工死亡几率增长 15.4% (Gonzalez-Mulé & Cockburn,2017),因此高工作负荷可能对于员工自身或同事都是一种显著的死亡提醒。另外,更为直接的同事死亡也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有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意外死亡显著影响在职高管的战略决策(Chen et al.,2020)。因此,员工工作负荷与同事死亡等因素可能是组织内部潜在的死亡提醒压力源,未来研究可以检验员工是否会将其视为死亡提醒压力源并对其进行认知评估,进而产生不同的状态死亡意识与工作绩效。
最后,厘清死亡提醒压力源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的因果关系。本文根据压力交互理论指出,个体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认知评估可能影响其状态死亡意识的产生。然而,这一推论所使用的文献多为相关性研究,因而无法做出明确的因果推论。例如,Simonelli 等(2017)提出癌症患者的死亡意识可能会改变其对癌症复发这一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评估倾向。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纵向调查与实验法等研究设计检验员工对死亡提醒压力源的认知评估与状态死亡意识之间确切的因果关系。
4.2 拓展工作-家庭层面下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情境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组织情境资源因素对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拓展跨领域的情境资源因素。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指出,个体在一个领域的资源获益将促进其在另一个领域的绩效表现(ten Brummelhuis et al.,2022)。因此,家庭领域资源可能影响员工在工作领域面临死亡提醒压力源时的死亡心理与行为反应。已有研究表明,家庭领域的配偶等亲密关系是个体重要的情境资源,这些亲密关系可以有效缓解个体死亡焦虑(Hobfoll,1989;McCabe & Daly,2018)。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亲密关系等家庭领域资源是否影响员工对职场死亡提醒的心理反应。从跨领域视角拓展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边界条件,将能够更立体地理解死亡提醒双刃效应。
4.3 研究死亡提醒双刃效应的组织干预措施
如何培育员工在死亡提醒情境中维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与工作行为,是未来研究职场死亡提醒的一个重要方向。考虑到正念对个体认知与情绪的积极影响(申传刚 等,2020),组织开展正念培训可能是一种促进员工积极应对死亡提醒的有效措施。尽管已有研究发现特质正念能减缓个体对死亡提醒的负面反应(De Clercq et al.,2021;Niemiec et al.,2010),但当前尚未有研究检验正念干预产生的状态正念对员工应对死亡提醒的有效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组织中实施正念干预项目并追踪其对员工死亡心理的干预效果。然而,一般的干预项目周期较长且难以应用于高特质死亡焦虑员工,而有研究发现企业提倡洗手便能有效减缓员工由疫情引发的健康焦虑(Sliter et al.,2014;Trougakos et al.,2020)。因此,未来研究也可以充分挖掘更多便捷高效的干预措施,以助推组织员工在特殊时期有效应对死亡提醒。
致谢:作者感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马捷副教授与沈婷婷研究生、乌特勒支大学李培凯博士、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李睿怡研究生、《心理科学进展》匿名评审专家和编委对本文给予的建设性意见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