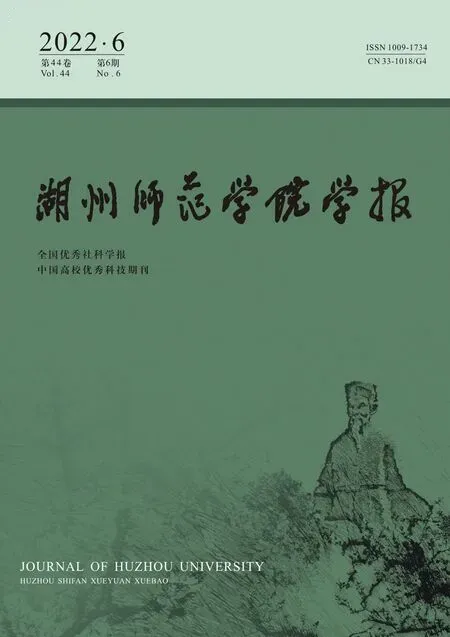论孔子的语言教育观*
2023-01-06周扬刚吴凡明
周扬刚,吴凡明
(1.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学者对其语言教育观的研究并不仅局限于具体的语言、文字、结构,而更注重研究语言文字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语言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加强彼此的联系,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1]169歌德在《浮士德》中开篇便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2]8。语言学习不能只把握它的意义,更需要理解它的用法;只有了解语词的用法,才能够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同时,语言也只有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才能深刻体现它所具备的重要德育价值。
孔子在《论语·尧曰篇》中指出:“不知言,无以知人。”[3]209可以看出,“言”和“人”是相互联系的。“言”是一个人的外部表现,通过语言表达,可以了解一个人,而且“言”蕴藏着一个人重要的内在品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为了了解一个对象,必须了解它的所有内在性质。”[4]30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明确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3]144“言与德”的关系深刻揭示了语言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教育价值,即德育。孔子的语言教育观主要是通过对言与实、言与行、言与礼、言与德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而体现出来的。
一、言与实:言实一致是语言教育的内在要求
“言与实”是我们探讨孔子语言教育观的前提和基础。言实一致是孔子语言教育的内在要求。在《论语》中“言与实”具体包括“言忠”和“言信”两个方面。忠,尽己之谓忠。“言忠”,即说话忠于内心,不夸大,不掩饰,讲真话。信,以实之谓信。“言信”,即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诚实守信,说到做到。
首先,在“言忠”方面,孔子以身作则,在《论语·卫灵公篇》中,他指出:“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3]165意思是孔子对他人说过谁的好话,说过谁的坏话?凡是孔子称赞的人,一定有他值得称赞的地方。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注释道:“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父子无是也。然或有所誉者,则必尝有以试之,而知其将然矣。”[5]247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言我之于人,无毁无誉。而或有所誉,称扬稍过者,以斯人皆可奖进而入于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观也。”[6]632这里孔子告诉我们,不能随便评价别人,只有在经过严谨、认真的考察之后,我们才可以再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子贡在孔子语言教育观的影响下,对“言与实”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论语·子张篇》中记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3]201子贡认为商纣王的残暴无道,并不像当时人认为的那么严重。言外之意是人们在发表对人或事的看法时,往往倾向于夸大其好的地方,贬低其不好的地方。此处子贡借用民众对商纣王的评价,指出人发表言论时要不夸大、不修饰,并且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随波逐流。
其次,在“言信”方面,孔子将“言信”放在具体的言行关系之中,他认为凡是答应别人的皆要努力将其实现,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提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132君子说话不能随便、马虎,一旦说出去就要去实行。孔子也强调“言信”在做人中的重要性。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4孔子认为说话谨慎、讲求信用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忠信”是一种道德规范,不仅需要体现在语言表达中,而且需要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贯彻落实。只有将“忠信”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才能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后,孔子不仅从正面直接强调“言与实”的重要价值,也从反面揭示了它的重要性。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3]21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如同缺少关键部件的马车,仅如空壳,根本无法行驶。朱熹对其注解道:“輗,辕端横木,缚轭以驾牛者。軏,辕端上曲,钩衡以驾马者。车无此二者,则不可以行,人而无信,亦犹是也。”[5]98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又云:‘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威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皆言不信则不可行之失也。”[6]68事实的确如此,西周时期的周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信誉全失,遭遇灭国之灾。春秋时期,齐襄公也因失信于人而招致杀身之祸。《左传·庄公八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7]30齐襄公派连称和管至父等人去看守蔡丘,承诺瓜熟时节就召回,但期限已过,齐襄公仍然没有派人替换。连称等人十分生气,于是勾结公孙无知发起叛乱,杀了齐襄公。由此可见,无论何时“言忠信”都将对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言与行:言行一致是孔子语言教育的具体要求
如果说“言与实”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真假问题,那么“言之必可行”则是强调语言必须落到实处的具体要求。
首先,孔子强调言行一致。言行一致是孔子言行观的基础和前提。在《论语·子路篇》中,他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132此处孔子强调“言之必可行也”,是指所说的话一定要能够履行,如果光说而不去实践,就不是君子。在《论语·为政篇》中,子贡向孔子询问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君子,孔子回答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3]17孔子认为,一个君子只有在自己真正做了之后才可以对别人说,而不能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孔子强调行在言之前。与此同时,孔子也从反面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在《论语·公冶长篇》中记载了孔子对学生的评价:“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3]44孔子曾经对待别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即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而他的学生宰予就如同腐朽的木头不能再雕刻,粪土一样的泥墙不能再粉饰,对于这样一个白天睡大觉的人,“听其言而信其行”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即听了他的话还要考察他的行为,才能合理判断这个人。通过宰予的言行,可以看出孔子对言行一致的高度重视。
其次,孔子强调慎言敏行。在《论语·学而篇》中,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3]9朱熹对其注解道:“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然犹不敢自是,而必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5]88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说文:‘敏,疾也。敏于事谓疾勤于事,不懈倦也。’焦氏循论语补疏:‘敏,审也。谓审当于事也。圣人教人,固不专以疾速为重。’案:‘焦说与孔注义相辅。’”[6]32这里孔子主要说明了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要求,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物质的丰盈,日常的居所和饮食能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即可,在工作当中,言行应该做到敏捷和谨慎,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请有道德之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纠正。这种不追求外在享受、关注内在修养、追求真理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热爱学习,即“君子当安贫乐学也”[6]32。与此同时,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指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3]39古之君子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十分谨慎,因为他们以食言为耻。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曰:“言古者。以见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5]118古之君子极其看重言行一致,担心自身行为达不到言语的标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言慎行。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3]40孔子强调君子应该说话谨慎,但做事却要敏捷,即少说话多做事。诚然,“讷于言”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即少说话,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语言是沟通交流的重要介质,但应该避免多说,正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话说多了必然也会招致不良后果。其二,少说废话和空话。废话和空话毫无益处,说多了反而会沦为别人的笑柄,战国时期的赵国将领赵括便是一个例子。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8]2 447。赵括熟读兵书,却只会纸上谈兵,毫无作战经验,不懂得灵活变通。孔子不仅强调“讷于言”,更强调“敏于行”。那么为何要“敏于行”?许多事物具有利、弊两面性,也许看似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实则却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隐患。事物复杂多变,说来容易,往往做成却非易事。因此,需要我们谨慎说话,善于观察,理清思绪,合理判断。只有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清楚什么事情应先做,什么事情该后做,才能真正做到慎言敏行,提高办事效率。
孔子在强调“慎言敏行”的同时,也反对“巧言令色”的行为。在《论语·公冶长篇》中,他强调:“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3]51意思是说好听的话,扮成一副恭敬的样子,阿谀奉承,左丘明认为这是可耻的,孔子也这样认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曾子言:“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6]202巧言令色的人,仅仅依靠一些小聪明是很难达到仁的境地的。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进一步提出“巧言乱德”的观点[3]165。意思是巧言令色会败坏道德。孔子对“巧言令色”这一行为进行批判,其目的是突出“慎言敏行”的重要性。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指出:“敏讷虽若天资,亦由习。轻言矫之以讷,行缓励之以敏,此亦变化气质,君子成德之方。”[9]106他认为,虽然“讷”“敏”是先天特征,但更需要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与培养。说话不慎重,但予以矫正,也能做到“讷于言”;行动迟缓,但予以激励,亦能实现“敏于行”。如此可以不断培养“讷”“敏”品质,这是君子成德的途径。由此可见,“慎言敏行”这一品质不仅极其重要,更是可以通过不断培养而获得的。
最后,孔子也强调“言忠信,行笃敬”的言行观。《论语·卫灵公篇》中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3]160学生子张请教孔子,如何才能让每件事情都进行得顺利称心?孔子回答说,说话要诚实守信,做事要笃厚恭敬,即使到了偏远地区,也是行得通的;反之,如果说话虚情假意,做事投机取巧,即使在家乡,也是行不通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孔子的话进行阐释道:“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恃,必免于患矣。”[6]616孔子探讨了“恭”“敬”“忠”“信”所蕴含的价值,作为重要的君子品质,具之则免于难,失之则忧于患。孔子认为做到“言忠信,行笃敬”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理解。如果说话言而无信,做事投机取巧,就会导致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三、言与礼:语言必须受到礼的规范制约
孔子的语言教育观不仅强调要将语言落实到行动,而且对如何落实以及落实的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礼”作为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同时深入贯彻于他的语言教育观之中,对后世的语言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礼”解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0]2在祭祀活动中履行“礼”,能够达到敬神求福的效果。而此处孔子所崇尚的“礼”,是对“礼”内涵的深化,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符合“礼”的规范。孔子强调“礼”的重要性,在《论语·尧曰篇》中有所体现:“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3]209孔子认为,不知道礼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礼”是指周的礼制,他认为周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是最接近理想社会的标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重要转折时期,他希望可以恢复周礼,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
在语言表达的具体要求上,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明确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121不符合礼的不能看,不符合礼的不能听,不符合礼的不能说,不符合礼的不能做。孔子在《论语·微子篇》中赞扬柳下惠、少连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3]195虽然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但他们的言论合乎伦理,行为经过了深思熟虑。在《论语·卫灵公篇》中,他批评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3]163意思是终日聚在一起,所谈论的内容也和义理不相干,却爱卖弄小聪明,这样的人不仅对他人和社会毫无益处,而且还很难成就一番事业。耍小聪明有两种情况,如果此人本身笨拙却爱耍小聪明,只会一眼被人识破,闹出笑话;如果此人确实聪明,但自恃才高,只会遭人嫉恨,受到排挤。由此可见,一个人不管是否聪明,都不应该故意炫耀,言谈举止都应该合乎“礼”的规范。
语言表达要合乎“礼”这一具体要求,在《论语·述而篇》中也有体现:“子不语:怪、力、乱、神。”[3]71孔子是反对探讨怪异之事的,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是拿捏不准的事情,他都不会妄下结论。孔子认为,暴力之事的发动会违背追求恢复周礼的目标。对于叛乱之事,孔子提出德治。统治者只有以德治国,才能平复国家的动乱,促进社会的和谐。对于鬼神之事,孔子的态度在《论语·雍也篇》中有所体现:“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3]60朱熹对其注解为:“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5]152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王曰:‘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鸟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正义曰:‘不语,谓不称道之也。’大戴礼曾子立事篇:‘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即此义。’”[6]272对于不合乎于“礼”的怪异、暴力、反叛和鬼神之事,孔子概不谈论。孔子对“怪、力、乱、神”的评价,既体现了语言运用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他对“仁、礼、德”的信仰。
语言表达要符合“礼”的规范,要根据特定的场合灵活调整。《论语·乡党篇》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3]96朱熹对其注释道:“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辞气如此。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但谨而不放尔。”[5]179孔子强调说话要分清场合,在家乡时表现要恭敬谦虚,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在宗庙、朝堂之上表达要清楚、流畅,只是要注意态度。
语言表达要符合“礼”的规范,要根据特定的对象灵活调整,否则不仅将“失人”,还将“失言”。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记载:“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3]161对于可以交谈的人却不与之交谈,将错失人才;对于不可以交谈的人却想与之交谈,是说了错话。真正聪明的人是不错失人才,不说错话。《论语·乡党篇》中记载:“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96意思是对待下大夫、上大夫和君主的谈话要各不相同,与下大夫谈话时要温和且快乐,与上大夫谈话时要恭敬且诚恳,当要对君主进行禀报时,要表现得庄严且谨慎,但步态却显得安详。因此,孔子认为谈话时要分清楚对象,对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话,这不是一种世故、老练,而是一种说话的艺术。
语言表达要符合“礼”的规范,要根据特定的时机灵活调整。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3]174为了防止“躁”“隐”“瞽”现象的发生,孔子认为需要择时而言,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发言,即“言及之而言,言未及之而不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盲目发言,要“见颜色而言”。孔子语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灵活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语言表达时应该根据特定的场合、对象以及时机进行灵活调整。
综上所述,孔子既强调语言表达合乎“礼”的重要性,也强调语言表达合乎“礼”的具体要求,可以看出,孔子极其重视语言表达的内容,强调言辞要合乎其“礼”的规范。
四、言与德:成人之德是孔子语言教育观的最终归宿
孔子语言教育观中的“言与实”“言与行”“言与礼”分别探讨了言自身的真假、言必落实于行动、言落实过程中的规范问题,最终探讨“言与德”,即语言教育的最终归宿。由于儒家思想从根本上主要探讨人如何从“成人”最终走向“成圣”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思想品德教育既是孔子语言教育观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孔子认为道德是语言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明确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3]144即道德高尚的人必定是善于表达的人,但善于表达的人却不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人。此处孔子强调了语言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在《论语·学而篇》和《论语·阳货篇》中,孔子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3]3/185孔子认为经常花言巧语、伪善的人是没有“仁德”的,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孔子“有言者不必有德”的观点。朱熹也对其注解道:“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5]82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能有仁也。’”[6]9孔子对这种花言巧语的人是极其憎恶的,在《论语·公冶长篇》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3]51那么,为何孔子认为善言之人都是缺乏仁德的呢?这就有必要追溯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品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记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345“修身”是儒家极其看重的,通过自身道德和人格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从而影响他人,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和抱负,最终奉献社会。因此,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内在品德,反对巧言令色的人。
孔子进一步探讨了“言与德”之间的关系。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巧言乱德。”[3]165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其注解道:“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5]248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注释道:“孔曰:‘巧言利口,则乱德义。’巧言乱德,所谓恶侫足以乱义也。”[6]634这里主要是说花言巧语将会使道德败坏,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指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3]184孔子认为将道路上随便听来的东西到处传播,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中也记载:“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家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12]599成语“穿井得人”便是由此而来,出现了从丁家打井获得一个人的劳力,误传为打井挖出一个人这样的笑话。由此可见,对待传言不能盲目传播,应该保持审慎态度,认真分析,辨别其是非真伪。
一言以蔽之,孔子语言教育观的最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德育。首先,关于道德标准的评价问题,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阐述了自己的义利观,他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8他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通晓长远的大义,而小人则仅仅局限于眼下的小利。值得注意的是,君子并非不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是在事物面前强调对义的优先考虑,并且以此作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原则。其次,孔子还强调有志之士不应局限于满足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要努力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在《论语·里仁篇》中,他告诫学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3]36他认为读书之人如果已经确立追求真理的伟大目标,但在生活之中却又介怀于物质生活的贫瘠,以食粗粮、穿破衣为耻,那么对于此类人,他认为是不足以与之谈论真理的。孔子不仅以身作则,主动践行其思想主张,并且他的学生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他的学生颜回就表现出优秀的道德品质。在《论语·雍也篇》中,他指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58他称赞颜回十分贤能,具有安贫乐道的优秀品质,即使衣衫褴褛,陋巷菜羹,别人皆难以忍受,他却依然不改其乐。与此同时,颜回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在《论语·为政篇》中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3]15颜回与孔子整日呆在一起,在面对老师的讲学之时,颜回表现出极少的疑惑,并且不急不躁。因此,在孔子的印象中,颜回是一个愚蠢的人。然而,孔子在私下观察后发现,颜回能将之前学过的内容有所发挥地加以诠释,这个时候,孔子才发现颜回并不愚蠢。并且,颜回的这一表现也反映出“慎言敏行”的特质,即在面对老师的讲学之时,即使内心明白也不急于发表意见,而是在课后,按照老师的讲授内容去积极践行。
孔子的语言教育观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即通过语言本身出发,进一步探讨语言与人的行为的关系,并最终上升到语言与人的道德的关系,进而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实现最终目的,即促进个人理想品格的完善。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语言教育观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语言教育观主要探讨“言与实”“言与行”“言与礼”“言与德”四个方面的内容。“言与实”探讨语言本身的真假问题;“言与行”探讨语言落实到行动的必要性问题;“言与礼”探讨语言落实到行动的规范,即符合“礼”的问题;“言与德”探讨语言教育的归宿,即德育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哲学注重探讨语言本源的问题,孔子谈语言教育时更多的是探讨语言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德育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本宗旨。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语言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学生语言进行规范、语言能力进行培养等语言问题的探讨,更在于通过语言教育对学生进行德育,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使学生真正“成人”。